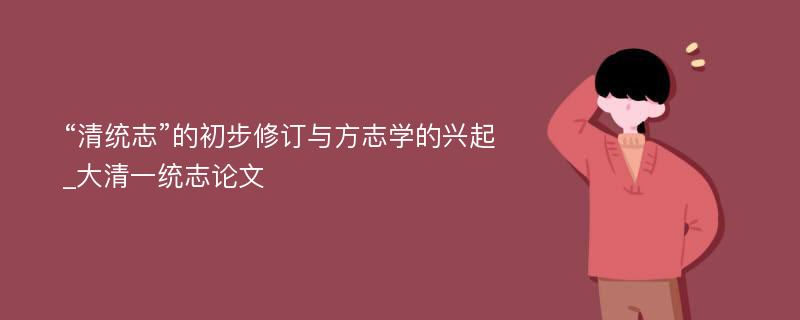
《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清论文,一统志论文,方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地方志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典籍。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均接续性地纂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而方志纂修的兴盛时期乃在清代,方志学理论的趋于成熟亦在清代,其原因除了历代修志经验、认识积累提供的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大清一统志》初次纂修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一、《大清一统志》的初修
《一统志》与方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方志”,在严格意义上应以确认全国统一政权为前提,并按国家当时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述某一区域内的地理、历史与社会人文状况的典籍。方志纂修的本身,即有着从小的区域聚合为较大区域,直至全国性志书的趋向。因此,伴随方志的发展,全国性志书也代有修撰,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等。元朝的全国性志书正式定名《大元一统志》,部帙达一千卷,明代仿其义例,纂成《大明一统志》。
清入关后,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积极作出仿从汉族封建政权的举措。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清圣祖令礼部予以议奏。此事在《清史列传·卫周祚传》中略有述及,而其奏疏及礼部议奏文件,为《清实录》等所不载,惟康熙《天津卫志》卷首载有当时一件原始文献,弥足珍贵:
礼部尚书臣哈尔哈齐、臣龚鼎孳、左侍郎臣常鼐、臣董安国、右侍朗臣顾巴西、臣田种玉等,为遵谕条奏事:
康熙拾壹年柒月初壹日礼科抄出少师兼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二级臣卫周祚奏前事,本月初六日奉旨:“这应进讲书籍知道了,馀著该部议奏,钦此。”钦遵于柒月拾壹日到部。除各部事宜应听各该部议复外,该臣等议得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文献也。迄今各直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各省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等因前来。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省督抚,详查各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等因。
康熙拾壹年柒月贰拾肆日,本月贰拾柒日奉旨:依议。
这件文献明晰反映出清廷议修《大清一统志》的行文过程与时间,照录了卫周祚奏疏的原文,表明清廷敕令各省皆修通志,但河南、陕西可采用顺治朝已成之书,而且礼部提议各省通志皆依《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亦得旨准。由此,可以推知,初修《大清一统志》形成定议后,整体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修志,并颁布《河南通志》、《陕西通志》款式,依照纂修;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因此,当时一统志尚未正式设馆纂修。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起,战云密布,举国震荡,全力平叛为清廷首要之务,纂修《大清一统志》事暂被搁置。这是初修《大清一统志》经历的一大周折。
平定“三藩之乱”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又提到议事日程,然而由于清廷缺乏经验,组建馆局即颇费摸索。《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载:“大学士明珠等奏曰:‘……至于各省纂修通志送部,前奉谕旨极当。《一统志》关系典制,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所修通志稍觉迟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上曰:‘是。纂修《会典》之处着依议,各省所修通志作何察催,及应修《一统志》事宜,着礼部确议具奏。’”据此,清廷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再次敕令各省修志。《康熙起居注》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载:“又礼部纂修《一统志》,请给桌饭银两,其纂修处应交与内阁。”然而清圣祖并未对有关建议明确答复,却认为修《一统志》“不过誊录,并非撰文,岂宜迟缓!”要求定出完稿期限。次年正月,有大臣上疏称:“近礼部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1]这表明《一统志》设于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前后,而仍附于礼部。礼部官员权位较低,很难有效承担纂修的组织工作,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清廷任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吴正治、宋德宜、户部尚书余国柱、左都御史陈廷敬为总裁官[2],规格甚高,显然已不是礼部所能统辖。四月初八日选任副总裁时,《康熙起居注》则明确记载为“内阁会同翰林院以编纂《一统志》”。清廷已认识到纂修《一统志》并非易事,副总裁要选取学问优长者充任,清圣祖亦决定专委一、二人纂阅,以期速成。于是,以徐元文、徐乾学、张英、郭棻、高士奇、曹禾为副总裁,而以陈廷敬、徐乾学专理纂阅之事。[3]五月,清圣祖专发敕谕给《大清一统志》馆各总载,这虽是一件官样文章,然而标志着《一统志》馆组建完毕,正式开笔纂修。此时,已任命彭孙遹、吴任臣、姜宸英、万言、金德嘉等二十人为纂修官。[4]
《一统志》馆总裁、副总裁大多身兼数职,纂修之事实由徐乾学专理,进展较缓。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徐乾学因事被劾,被迫乞奏归乡,疏中称《一统志》“考究略有端绪”[5],请将之携归继续编辑,特旨允许。于是,徐乾学得以书局自随,并奏请姜宸英、黄虞稷随同襄助。[6]又延请胡渭、阎若璩、黄仪、顾祖禹等有名学者参与其事,先后在洞庭山、嘉善、昆山等地开设纂修《一统志》书局。[7]康熙三十三年,徐乾学逝世,遗疏进呈《一统志》稿。清廷依其志稿继续修订,令韩菼总裁其事。[8]韩菼尚简,对徐元文稿本大加删削,另成一稿,俱存馆内。[9]韩菼于康熙四十三年逝世后,清廷未再着力修订,《大清一统志》事实际又被搁置,终康熙朝未得成书。
雍正三年,清廷再组《一统志》馆,“以《一统志》历久未成,特简重臣敦就功役。”[10]至雍正六年十一月,《一统志》总裁蒋廷锡奏言: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缺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清世宗指示:“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内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至于书中各项分类条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项,著照所请,将各省所有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即详查确核,先行汇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11]这个上谕,又提出各省续修新志的详细指令,将之作为《大清一统志》取资的重点,但也采纳了蒋廷锡的建议,令各省先行报送本朝人物的有关资料,增强《一统志》的人物事迹等历史内容。
乾隆五年十一月,《大清一统志》告成,全书三百四十二卷,记载范围包括十八省,统府、州、县一千六百多个。采取分省叙次方式,每省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等门类,皆专载统括一省之事。而府、直隶州各为立表,下系各县。每县所载内容加详,分二十一类目,即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外藩及属国五十七个,朝贡之国三十一个,皆附录于后。清高宗亲撰序言,冠于卷首。至其全书刻成,已至乾隆八年。[12]。
初修《大清一统志》从定议至告竣,前后历经三朝,共七十余年,为时之久及起伏周折仅亚于官修《明史》。其间清廷反复摸索与尝试,为官方史学活动积累了经验。在当时,纂修《一统志》是最为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笼络明遗民学者、招揽人才的作用。《一统志》馆设立不久,黄宗羲就向徐乾学推荐裘琏入馆[13],顾祖禹则亲身加入徐乾学归乡后的《一统志》书局。许多学者先后参与纂修,裘琏、郑江、劳孝舆等皆因参修《一统志》方驰名学界。由于康熙时期清朝对新疆等地尚未实施直接的行政统辖,初修《大清一统志》自不能将这些地区像内地各省一例记叙。乾隆中期,清朝扩大直接统辖范围,加强统一与中央集权,与此相应,于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清一统志》,经二十年后告成,在内容结构和门类上一仍初修体式。嘉庆年间第三次纂修,内容进一步增新,时代下延,初修《大清一统志》遂被取代而流传不广。然而,它在清代文化上却有深远的影响,其中以推动方志纂修的兴旺发展尤为显著。
二、康雍时期纂修方志的兴盛局面
明朝纂修《一统志》,曾谕令各地纂修方志,对方志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清初一些地方官,承袭明代修志之风,注意到续修本地方志问题,特别是顺治年间贾汉复任河南、陕西巡抚之时,令所属各府、州、县皆修方志,并汇辑成通志,在清初颇具影响。然而这些仍为个别现象,方志的纂修真正普遍展开,是从清廷定议纂修《大清一统志》开始。
清朝在初修《大清一统志》过程中,于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二年、雍正六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清廷抑或地方官,在檄催各地修志时,皆有详明的规定,十分认真,公文传达较为迅速。康熙十一年,清廷令各省修志,礼部于闰七月初五日发下公文,三日后直隶已拟文下传,其中广平府于二十三日已将修志牌照发至各县。牌照详细规定县志要写成八部交送到府,府志要上报六部到省,而礼部要求各地报送一式三部志书。公文中强调“此系内阁特疏条奏,且系进呈御览事宜,该道务须加意详慎,毋得草率从事,以致遗漏舛错,自干严谴。”[14]康熙二十二年檄催各省纂修通志,曾要求三个月成书[15],十分急迫,这是将此次谕令修志视为康熙十一年谕令的接续。雍正六年第三次诏谕修志,如上文所引,清世宗提出了对地方官奖励与处分的问题。次年,又规定方志隔六十年必应续修[16],这等于将修辑方志列为地方官的职责之一。康熙二十六年,康善述在新修《阳春县志序》中称:“康熙十一年奉檄修志,仓卒未有成书,兵燹之后,副本无存……第欲续修而未遑。会奉宪檄遵承部文重修邑志”,于是修成此书。这反映出每次赦修方志,省、府的“宪檄”和清廷的“部文”都抵达各县,对于修志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雍正年间,山西、甘肃、浙江、江南、广东等等多数省分,皆纂修了通志,这乃是雍正六年敕谕修志的结果。
有些地方官往往未等朝廷的督催,主动地接续康熙十一年后因“三藩之乱”停滞的修志活动,康熙十九年成书的《保定府志》是在“上官檄征郡志,严且急”[17]的情况下修纂的。可见康熙十九年直隶已经严催各所属府、州、县修志。灵寿县国学生傅维枟,康熙十一年间曾参与纂修县志,因三藩叛乱而未能成书。他私下“网罗放失旧闻,汇辑成编,藏于家塾”,待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清廷再令修志时,被用为官修底本,稍为更定而刊刻成书。[18]康熙四十五年,清廷已不再催促各地修志,《大清一统志》稿已被搁置,而有些地方官修志热情不减。如江西赣州知府主动以纂修府志请示巡抚,经允可后便“檄行赣属十二邑,俾各修志,以备采择”[19]。以上事例,都显示了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在纂修方志上的积极、热心态度。康熙四十余年至康熙末年纂修的方志,大多是由地方官或地方士绅主动倡导促成的,表明清廷诏令全国修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纂修方志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若使方志失修,则“纪载缺遗,无以继残编而昭盛典,固邑中士大夫之辱,而亦长吏之所不得辞其责也”。并且认为“凡有民人有社稷之区,其不可无志以传信也明矣。顾或刑名钱谷之外,视一方文献为无裨名实,坐听废堕,岂知为政之先务者乎!”[20]表现出清廷初修《大清一统志》激发起的地方官纂修方志责任感与主动精神。
康雍时期,清廷与地方官、地主士绅皆对纂修方志采取积极、热心的态度,使全国性修志活动形成高潮,各省府州县,均纂有方志,并反复续修。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及今已难于查考所修方志的确切数目。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21]登载的资料初步统计,自康熙十一年议定纂修《一统志》并敕令全国修志,下至《大清一统志》告成的乾隆五年[22],前后68年间共有方志1560种,而乾隆五年至嘉庆末共80年,计有方志1384种,即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所纂方志超过乾嘉时期170多种。若单以康熙十一年至六十一年(共50年)计算,则有方志1349种,而乾隆元年至六十年仅有1042种,前者超过后者300余种。实际上,康雍时期所修方志,远比乾嘉时期志书佚失严重,很多在乾嘉及以后纂成的方志中追述的康雍时旧志,时已不存者屡见不鲜。不少学者及其著述,认为清乾隆时期方志的纂修才进入繁荣阶段,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清代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各地纂修方志已形成高潮,出现了繁荣兴盛、蓬勃发展的局面。
早在顺治朝后期,《邹平县志》纂修过程中顾炎武即为之校编,马骕为之讨论,康熙初叶,施闰章参修了《临江府志》、《袁州府志》等等。学者参修方志,早萌其端,但仍属偶见。康熙十一年之后,不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支持或参修各地方志者也显著增多。如黄宗羲参与康熙《浙江通志》的纂修,陆陇其主修康熙《灵寿县志》,汤斌主修康熙《吴县志》,顾栋高参修雍正《河南通志》,沈德潜纂修雍正《苏州府志》,黄之隽、程延祚雍正时纂修《江南通志》,储大文纂修雍正《山西通志》,邵远平纂修康熙《仁和县志》,王源于康熙时纂郃阳县志书,查慎行纂康熙《西江志》,博学鸿儒严绳孙曾纂修康熙《无锡县志》,乔莱纂修康熙《宝应县志》等等,皆当时有名文人、学者参与修志之例。至于如郭棻、陈祖范、蔡方炳一类进士、文人应聘修志,王士祯、毛奇龄等为方志撰序,在康雍年间更不胜枚举。可见在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纂修方志已成为当时许多学者、文人所乐为之举,修志作为已获得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日益被学界所重视,渐被看作著述立言、学术经世的一种形式,这对整个清代方志的纂修与方志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方志学探讨的广泛兴起
中国古代的纂修方志的实践中,很早就对方志性质、作用、修志方法等有所探讨。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23]。明孙廷臣嘉靖《唐县志序》亦称“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24]至于清代,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逐步深入,朱鹤龄认为:“夫郡邑之有志,昉于《周官》小史,由来尚矣。史局开纂,大者据实录,小者据家乘稗编。然实录分修,主裁皆非良史,稗编杂出,采摭或误传闻。家乘略可信矣,而碑志半谀墓之词,子孙多溢美之语。惟郡县二志修之得人,则闻见真而网罗备,一方文献即国史权舆,其事岂不重哉!“[25]这里明确地将方志视作国史可靠的史料来源,强调了方志的重要地位。清廷决定纂修《大清一统志》及谕令全国修志以后,关于方志学的探讨广泛兴起,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朝廷对纂修方志的倡导和督催,造成全国性的修志热潮,修志的必要性、方志的重要地位为地方官、士绅、学者所认识。修志既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业,必然促使人们思考方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二,由于纂修方志是为了逐级向《大清一统志》提供资料,很自然地要求各地方志应有基本一致的内容门类和纂修体式。康熙十一年颁发修志谕令,规定以顺治年间《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定式,要求各地依其门类纂辑。然而全国具体情况不一,省、府、州县级别与方域不同,很难按一种格式纂修方志。统一体式的要求与不同具体情况的矛盾,迫使人们探讨更为完善的修志义例和方法。初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方志学上的探讨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对于纂修方志和续修方志必要性的认识。在清廷反复督促各地纂修方志的形势下,纂修方志是否必要,已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修志者对修志必要性的论述,仍反映出方志学上的认识深度,这是地方官由被动地奉檄修志转变为主动积极修志的思想基础。康熙《新会县志》贾雒英《序》认为:“省有通志,郡有府志,县有邑志。府职其要,县职其详,盖耳目近则蒐罗广也……迄于今土田日益辟,户口日益稠,钱谷军资日益繁,学士大夫日益众,五礼六乐、三物四维、畜牧耕桑、营建规制日益踵事而增华,使传之既往者无以续之将来,致杞宋无徵,日就湮泯,谁吏兹土而可谢其责乎?”对方志保存史料的作用,时世对修志的迫切需要,地方官的修志职责等皆有深刻的见解。康熙《河南通志》祖文明《序》称:“庶几今日信志,即可备他年信史,备巡方而昭文物,示劝励而树风声,以上副圣天子修明统志之盛典。岂不伟哉!夫莫或先之,虑其湮也,莫或继之,虑其堕也。”这不仅论述了纂修方志的必要性,也涉及了应当续修方志的问题。而刘士麒《新修翁源县志序》指出:“方志的功用在于“稗乘所未周,国史所未及者,悉取而纪之以登天府,藏之太史”,其修志《义列》称:“志书所以记载古今事迹,前者修而后者续,盖以一时有一时之事,一代有一代之人,非若山川疆境,亘古如常,故随时书之,以俟续纪无穷。”[26]这精辟地论述了方志的资料应随时记载积累、方志须以复续修的道理。至康雍时期,方志应当纂修和予以续修已成为朝廷、官吏、士绅、学者的共识,而不再有异议,这是保证清代方志纂修兴盛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关于方志撰修基本原则和态度的论述。清初学者中,有过将“郡县之志”与“氏族之谱”并列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的见解[27],指出了纂修方志面临的种种导致歪典史实的弊端。康雍时期,在肯定修志必要性的基础上,人们探讨了撰修方志应取何种态度、应掌握什么基本原则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记述失实的问题。康熙《堂邑县志·述例》篇批评了一些方志中“观天察地则道听而途言,稽古证今则吠声而逐影”的倾向,提倡严谨、审慎的态度。康熙《保定府志》纂修者主张采取“公而不刻,厚而无私”的撰修准则。[28]王源以实例抨击某些方志中的“踵讹袭谬之弊”,反对不认真考核而“胧朦迁就”、“随俗苟同”的态度,认为“不穷其原不足以成书,不辨别其非不足以存是”[29],这是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纂修方志。雍正《山东通志》则重于严订义例,提出“谨书法”、“审详略”、“正讹以传信”、“阙疑以慎言”等原则。康熙《程乡县志》刘广聪《序》认为:“事贵核而词贵间,核取其徵,简取其严。去伪存真,以绝附会,循名考实,以示信从,乃修志之大端也。”所有这些论述,反映了康熙时期在方志的撰述态度、编纂原则问题上,达到了较高的认识水平。
(三)关于方志性质与修志义例的探讨,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清廷修《大清一统志》而令各地皆修方志,造成“一统志该各省,省该其属府州,府州该其属县,县志不綦重乎哉”[30]的观念,使人感到方志应是属于地理系统的典籍;而清廷修《明史》、修《大清会典》,皆征集方志之书,方志中本来具有历史性内容,这又造成方志为一方之史,可以备正史、国史取材的观念。于是,认为方志为地理专书与认为方志是一方之史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朗和对立,这是整个清代在方志学理论发展上的重要特点。
主张方志为一方之史者,往往用上古列国之史相比拟,以证其说源远流长。如刘柏《江南通志序》称:“直省之有通志,与古列国之有史同。”[31]师若琪康熙《保定府志序》认为:“志与史无以异也,后世缀文之徒以志视志,不以史视志,志之为书微矣。”杨以兼《续修邑志跋》[32]认为:“窃以邑之有志,与国史无异。且国史之足以信今传后者,悉本于省、郡志,省、郡志皆集邑志而成,使邑志舛谬,即他日国史亦不足据。”明确地表达了要以县志为基础,逐级取裁,最终为国史提供史料依据的见解。刘广聪的康熙《程乡县志序》也明确提出:“志者,邑之掌故,指利弊以资兴革,昭是非以寓劝惩,盖与《春秋》、国史相表里焉。”由此可见,康雍年间持方志为一方之史见解者已颇为普遍,对方志性质为史籍以及方志在史籍系统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
但是,康熙十一年令各省修志的文告,强调方志所要记述的是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所突出的是地理内容,颁为定式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也以地理内容为全书主线,这在主志学上的影响亦不容低估。康熙《黎城县志凡例》认为:“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戒,志则志其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33]学者王源极力主张方志应以记载地理内容,考其沿革为主旨,他说:“夫近代地志之失,其体正在专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于《禹贡》、昉于《职方》……夫人物之纪固亦不轻,然其专责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后世之体耳,《禹贡》、《职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应重者不重,而独以人物为重乎?”[34]王源的见解,开乾嘉时期戴震、洪亮吉等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应重于考证地理沿革主张之先声。
康雍年间,方志体式相当庞杂,并未完全依照《河南通志》款式,这反映的是纂修热潮中多方探索、各自尝试而尚未发展成熟的状况。其中有些方志已逐步摆脱重于地理内容的束缚,形成了较为妥善的地方史体式。例如康熙五十七年陆师纂修的《仪真县志》,卷一为旧序与图说,用以载明历次纂修本县志书的情况及本县区划和地理概况;卷二为沿革及职官表,以下依次为选举表、建置志、山川志、民赋志、学校志、军政志、祠祀及艺文志、名迹及祥祲志、列传。全书二十二卷,人物列传占四卷之多。形式是以史为纲,内容以史为主,符合史籍义例,又不失地方色彩。据记载,陆师,康熙十四年进士,时为仪真知县,后迁转入京为官,与方苞、何焯、张伯行等人友善,“宜乎政事文学卓荦不凡,能出贤有司绪余而为此佳志也。”[35]《仪真县志》的出现,表明康熙年间不仅普遍形成方志为一方之史的观念,而且在修志实践上也取得按史籍拟定义例的成功。
雍正六年,清世宗在关于纂修《大清一统志》与纂修通志的谕旨中认为:“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36]皇帝以上谕形式肯定了方志为史载的性质,对方志学的发展影响颇大,这表现于雍正九年始纂、乾隆元年成书的《江南通志》。《江南通志》以康熙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学者黄之隽为主笔纂修,体例一准史载。卷首先以四卷载清帝有关诏谕,正文门类分为舆地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类志等十志,其《凡例》特别申明“志与史相表里”的主张,以附合清世宗的谕旨。本书的多篇序言皆赞扬“例准史载”“以史才抒史笔”的修志方法,主张方志应“为他年史氏之征信”,“盖志书之作,所以彰往察来。镜制度之得失,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污隆,运会之升隆,固非徒侈称疆域之广、户口之繁也已。”[37]康熙中曾参修《大清一统志》的郑江在《序》中认为方志“亦足以补国史之阙遗,而兴起斯人敦行砥节之思,是其权尤与史官埒。”类似的论述尚有很多,使《江南通志》成为将方志视为一方之史的主张与纂修实践上例准史裁相结合的典型,集中总结了这一方志学流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部《江南通志》随即被清廷部颁为修志定式[38],标志着官方在方志学认识上的一大转变。
乾隆年间,史学家章学诚力主方志为一方全史,并按志为史裁的原则研究修志义例,与主张方志应重于考证沿革的戴震、洪亮吉一派辩难争议,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究其思想渊源,乃是直接承袭了康雍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时期已经形成的有关见解,是在康雍时期方志学思想基础上作出的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项牵动全国的文化事业上的系统工程,为官方摸索出在人员组织、上下配合、书籍资料征集等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统志》纂修体式的范例。而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直接推动了方志的纂修,使之在康雍年间即形成高潮、进入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纂修方志的责任感和主动积极精神,奠定了方志学理论探讨的基础,这是清代方志学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正月甲申。
[2]《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末。
[3]《康熙起居注》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丁酉。
[4]《清圣祖实录》卷126,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
[5]《憺园文集》卷十《乞归第三疏》。
[6]《憺园文集》卷十《备陈修书事宜疏》。
[7]《清史列传》卷68《胡渭传》、《阎若璩传》。
[8]《清史列传》卷9《韩菼传》
[9]见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一统志馆总裁书》。
[10]雍正《畿辅通志》卷首,唐执玉《序》。
[11]《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
[12]见《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四库提要》卷68《史部地理类》。
[13]《清史列传》卷71《裘琏传》。
[14]康熙《威县志》卷首《遵谕》载广平府修志牌照。
[15]见光绪《吉安府志》卷首,定祥《序》。
[16]见光绪《吉安府志》卷首,定祥《序》。
[17]郭棻《纂修郡志记》,载康熙《保定府志》。
[18]康熙《灵寿县志》卷首,陆陇其《序》。
[19]杨以兼:《续修邑志跋》,载康熙《瑞金县志》。
[20]康熙《藁城县志》卷首,刘元慧《序》。
[21]中华书局1986年1月出版。
[22]乾隆初告成的方志,皆因雍正时敕令修志而纂辑,且多自雍正时着手纂修。
[23]《郑忠肃公奏议遗集》卷下。
[24]载光绪《唐县志·艺文》。
[25]《愚庵小集》卷十,《复沈留侯论修志书》。
[26]见康熙二十五年《新修翁源县志》卷首。
[27]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
[28]康熙《保定府志·纂修郡志记》。
[29]《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康孟谋论修郃志书》。
[30]康熙《阳春县志》卷首,康善述《序》。
[31]载乾隆元年《江南通志》卷首。
[32]载康熙四十八年续修《瑞金县志》卷首。
[33]参见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第五编。
[34]《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康孟谋论郃志书》。
[35]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第六编。
[36]《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
[37]《江南通志》卷首高斌、姚孔鈵、刘柏、赵国麟《序》。
[38]道光《观城县志·凡例》,转自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第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