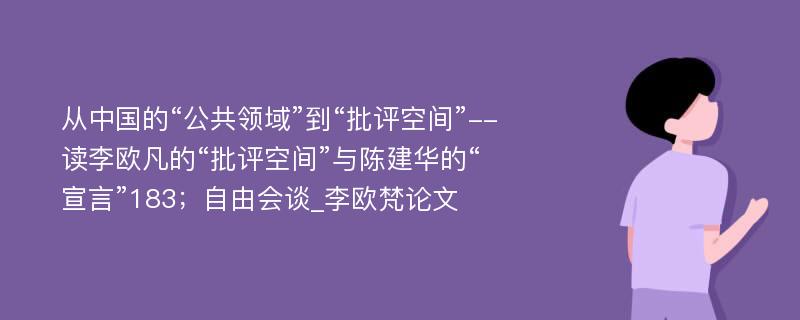
从“公共领域”到中国的“批评空间”——读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与陈建华《申报#183;自由谈话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空间论文,中国论文,领域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引出的话题
1962年,德国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同特权统治阶级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理想模式,是在一个国家政权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从而间接参与公共事物,影响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其发展大致可分为文学和政治公共领域:前者指公众在咖啡馆、沙龙、宴会、报刊杂志等机制中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它成为公众自由讨论和运用理性的场所;从文学公共领域里产生出政治公共领域,指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需求加以调节。公众舆论形成公共权力话语。话语虽不具有统治功能,但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哈氏此书虽在早期反应冷淡,但80年代以降却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和多种讨论。加之近年北美学界开始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性进行重新思考和批判,引发有关第三世界等的“本土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即以哈氏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理论陈述为参照,检视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开创新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批评空间的开创”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李欧梵在反思“本土现代性”和“公民社会”等当下话语时与历史的对话,以及对历史的“发明”。
二 中国批评空间的开创
李欧梵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空间”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由对哈贝马斯“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论述的“故意误读”,他把原本不应混为一谈的“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两个观念产生关联,在“公民社会”的架构下来淡“公共空间”(注:李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里所用的“公共空间”是指英语的public sphere,而在其后不久的一篇与人合作的文章里用的是英语public space:Wang Hui,Leo Ou-fan Lee,with Michael M.J.Fischer,"Is the Public Sphere Unspeakable in Chinese?Can Public Spaces(gonggong kongjian)Lead tO Public Sphere?",Public Culture 6,no.3 1994:597-605。这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比哈氏理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能指要小,)。李欧梵不认为中国有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民社会,但曾经存在过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空间”,并且他最终聚焦在民国前后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的“批评空间”上。李认为,打上现代烙印的中国“批评空间”开创于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它在一个立宪共和与军阀混战的历史罅隙里形成,但随着政治理想的破灭与公共理性的失落而变成历史的昙花一现。
值得澄清的是,李欧梵笔下的“公共”并不是指一般的“公民共有”概念,而是指梁启超的“新民”观念落实到报纸所产生的影响。那什么是“新民”观念呢?根据李在专文《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解释,“梁启超办报之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出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注:《李欧梵自选集》,李欧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72页。)而这种新的社会声音的形成和表现,创造出一种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有弹性的模糊空间地带,亦即本文所谓:在报纸这种印刷媒体的影响范围下,中国产生的批评空间。
《申报》创刊于1872年;其副刊《自由谈》始于1911年8月,并伴随到1949年5月《申报》停刊。李从《自由谈》里最有特色的“游戏文章”一路说开去,认为它们通过“滑稽讽世”的特殊文体提供了一种处于中心话语边缘的“边缘型批评模式”,所以,自由谈“这个半公开的园地更属于开创的新空间,它至少为社会提供了一块可以用滑稽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地方。”(注:《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第106页。)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前夕,“游戏文章”的题目越做越大胆,且直接针砭时政,开倡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
李先生行文至此,基本结论已出来了,但他的精彩还在后头,那就是对鲁迅《伪自由书》生产的分析。李发现,“文抄公”鲁迅用故意剪贴抄袭、作注、让读者填空和自己填空等技法,创造了一种“多声体”似的评论文字,结果是“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注:《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第115页。)。但,李的思考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张着“公共空间”的理论大旗一直勇往直前,他的结论就是:鲁迅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所以他也没有为“公共空间”争得自由!鲁迅身后的三十年代及往后就更不用说了,“公共空间”愈益缩小,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终究没有为中国建立足够的“公共空间”。
不用说,李对鲁迅的分析是精彩而又不乏争议的,他从对《自由谈》的梳理而引出的中国批评空间的理论构架也是启人思迪的。
距李欧梵发表《批评空间的开创》后事隔十一年,陈建华发表《申报·自由谈话会》,与李文遥相呼应。“自由谈话会”是“自由谈”里的一个专栏,开始设置于1912年10月23日,止于1914年9月29日,维持了将近两年400余期。陈文较详尽地考察了“自由谈话会”的“中立”立场、“讨论”性质,进而肯定《申报》上的“自由谈”和“自由谈话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批评空间”。更为可贵的是,他充分利用地方史志等对《申报》及其文学副刊和专栏的运作做了历史性和社会性上的探讨,补充了李文没有深入探讨的隐藏在“文本”后的资本经济和复杂历史纠葛,并揭示,这个“公共空间”最终由资产阶级的软弱而早夭。
三 关于“批评空间”更多的话题
由李对鲁迅的评论及陈对“自由谈话会”的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与历史语境的复杂关系,引发我们对批评空间的进一步思索,如:批评空间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及广告主在当代“批评空间”所扮演的角色问题等等。在这些力量的相互牵引下,所谓的“批评空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现代化的电子媒体所产生的现象是否就是当代的“批评空间”开创?
(一)强势的管理权力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古希腊罗马时期,公民可以在广场上站在箱子上随意演说形成论坛(forum),并且进而形成了现代报纸的前身,例如罗马的《日报》,专门报导官方消息,并且公开悬挂在公共场所。这些或许可以符合哈贝马斯所提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但是公民仍然没有“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政治上的事务仍然是由元老院中的元老们来掌握。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兴起,民主时期个人意识开始抬头,与此同时,资本力量的强大往往可以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比如大型公司或商业组织所称的“托拉斯”(Trust),惯常以捐赠方式,以“商业行为的投资”资助“重点候选人”的选举经费,以期当选后能在政策上予以方便。当知识分子发现政客不可信之后,唯一能发泄心中不平之气的途径就是大众传播媒体,最早的当然就是印刷媒介的报纸。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革新发展,新兴电子媒体的影响力也应当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当政治公共领域被压缩之后,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会对管理权力(或称“公权力”)施加影响,似乎现代的公众舆论拥有的有效工具就只有大众传播媒体了。
然而“管理权力”会不会对因此而对公众舆论让步呢?这答案似乎很复杂。以鲁迅为例,李欧梵先生认为鲁迅的《伪自由书》格局不够大,仅仅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批评空间,而无助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之开创。而我们认为更多的关切应当落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时空等等复杂交错的背景,因为这些盘根交错的力量才是真正对于批评空间的开创拥有更多的控制或限制权力的根源。首先,鲁迅所要挑战的政府,就拥有非民间力量可比拟的强势管理权力;其次,报老板及广告商所代表的强大资本力量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似乎又非理论概括的那么简单。在当时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Censorship)箝制下,期望鲁迅在《申报》上,短短四个月中的“多声体式的评论”,就能开创出中国式的批评空间,似乎过度简化管理权力的影响,也对鲁迅过于苛求了。其实,李对鲁迅的结论是有点自相矛盾的。既说鲁迅以剪刀加浆糊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那么,这点为个人争得的自由空间为什么就不能看作是“公共空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呢?李有一个“公共空间”的幻想,而个人争得的空间不也在其中吗?难道还有现实中的另一个空间吗?这么说来,他对鲁迅的批评也只能算是一相情愿了。鲁迅找到了针对新闻检查的新方式,而他的同辈人或我们后来人还在幻想有一个自由言说空间来一番大刀阔斧的砍杀?鲁迅对语言终极性的理解,对现实的清醒,可能要比很多人深刻得多。再说,当时已经是中国第一大报的《申报》,在知识分子中有其影响力,能在其上刊登专栏,可以说多多少少都是尝试某种“批评空间”的开创方法,开疆辟土式的开创或者是伟大目标,在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却注定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知识分子理想。
(二)报老板及广告商所代表的强大资本力量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
除了管理权力以外,还有陈建华先生文章所探讨的另一种强大的资本方力量,他说:“事实上‘自由谈话会’所代表的不止是一个商报的利益,而确实以沪上资产阶级一度增长的实力作后盾,其抨击党派政治的‘中立’立场,鼓吹以法律和议会为支柱的共和立宪,都反映了这一阶级政治上的要求。”(注: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的2004年2月号。第96页。)当时,清朝扮演官方意见传声筒和公文政令传达的“邸报”功能逐渐衰退,而中国新的报业,也就是被梁启超赋予“新民”观念的社会声音,到了三十年代因为沪上资产阶级实力增长而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报社老板和广告商所拥有的力量可以左右报纸舆论的走向和空间。换句话说,传媒的立场绝对会受到拥有者和广告提供者的影响,而公共空间的弹性却又依赖于传媒的立场。
《申报》是完全民营的报纸,表象上,在1912年开始的《申报谈活会》专栏,“通过某种‘来者不拒’的方式给读者提供沟通机会”(注: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的2004年2月号。第89页。)。不过加拿大籍的传播学先驱麦克卢汉(Marshall H.McLuhan,1911-1980)在1967年提出了“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就是信息)的概念,(注:McLuhan,Marshall H.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64.)并且在观察大众传播媒体、资本主义及国家权力机构的互动关系十多年后,晚年更近一步修正自己的理论,推出传播界著名的理论——“The Medium is thePower”(煤介就是力量)。他认为传播媒体本身就是第一道“过滤器”(filter),而记者和编辑都是在扮演重重把关的“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所以西方报纸流行的“读者投书”(letter-to-editor)方式,或“读者来信栏”(letters column),基本上都是舆论的制造或引导,而引导、制造舆论当然是有企图或目的(引导舆论不见得是负面的,只能说为了符合某些目的)。以此理论来反观《申报》,那么在“民国伊始,它对于革命的热情拥戴,……褒孙抑袁,旗帜分明”(注: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的2004年2月号。第89页。),而《自由谈话会》以“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注: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的2004年2月号。第96页。)为日常话题,也都不难理解了。
(三)反思当代“电子媒介”与批评空间的新关系
在深入这次的主题之后,我们的确发现“批评空间的开创”和“政治”绝对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两者都是“众人之事”。在舆论能不能形成力量之前,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力量就开始产生纠葛。所以笔者对于批评空间的开创基本上是不持乐观态度的,或者说它至少是需要长期的、众人的努力。
然而,电子媒介的兴起,似乎又给“公共空间”的概念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首先回顾电视的发展,似乎就是一页“媒介就是力量”的写真,能够拥有庞大财力创设电视台,不是大财团就是国家机器,所以掌握电视台这个有庞大魔力的媒介,就是掌握了绝对的影响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这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大型财团手中,英美等国家在无计可施下,想出用“公共电视”(Public TV Station)的固定频道方式,制作一些不受商业影响的“高品质节目”。幸好,“公共电视”还可以算是电视媒体中的可发展空间。
当代的新兴传播媒介——网络煤体的蓬勃发展,似乎也给传煤公共领域的存在提供了新转机。不过张志安在《传媒与公共领域——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注:《传媒与公共领域——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张志安。资料来源自“文化研究论坛”,网址:http://www.cul-studies.com/,20 June 2004。)中,认为传媒存在着管理体制,而对这种新兴传播媒介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开创,抱持着“无法存在的公共领域”的悲观看法。其实,由中国历史的现象观察,所有批评空间的开创,无论是文学公共领域和还是治公共领域,都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获得成果的。而是由许多拥有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点一滴开创而来的,所以批评空间的开创,我们可以再多等一下,再多努力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