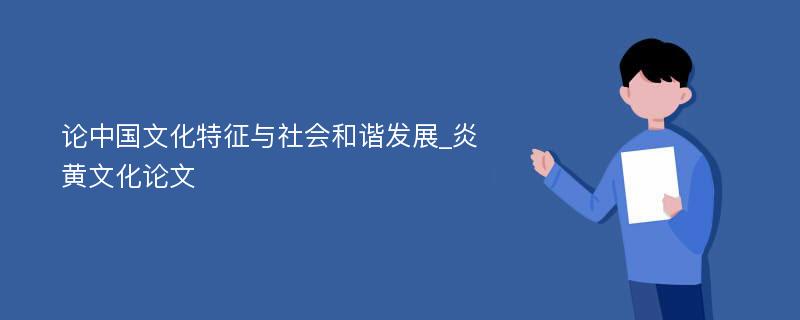
试述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特质论文,和谐发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华文化的专著篇章,可谓汗牛充栋,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华文化的发端、背景、特征、价值、传播、发展、影响等。本文拟从这一庞大文化体系的多样性根源出发,剖析它的几种与海外文化显呈不同的物质,并发见中华文化对海内外社会之平和与发展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多宗教长期并存、 互融的历史产物
(一)酿育古代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
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在产生的早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尤其是地理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从整体地理环境看,上古人类大致分为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在典型的海岛条件下,人们生活与生产的空间较小,而海洋交通则较为便利,所以商业、贸易较发达,且易产生向外拓殖的动机和条件,这一特点直至世界近代史仍在突出地表现着。而在远离海洋及大江大河的高纬度内陆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低,唯有牧牛羊为生最为便捷,由此而产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资料较贫乏,群体移动性大,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主动者。古代西欧罗马帝国和东亚的汉晋帝国在同一时期内遭受着相同程度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此种入侵被认为是导致两大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这视为震撼世界古代文明进程的一个悲壮的历史现象。与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迥异,拨动农业民族的地理杠杆则为较适中,例如,有广大面积的疆域,温和的气候,较多的江河湖泊和适于耕种的土地,等等。充分的考古证据表明,远古至史前期,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了若干大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和中国。其中范围最大、人口最多、成就最丰、延绵最长者,当推中华文明。
我们可以这样扼要地分析古典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格局:
1.中国大陆恒亘万里,两大河流横贯东西,中部平原辽阔,没有天然的屏障阻隔其间,因此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上都较自然地趋于统一,虽时有分割,但毕竟以和为主,且愈合愈广,愈合愈紧,以致即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或轻扰自退,或在极短时期内自行融合于中原主体民族之中。其他几个古典农业民族,均先后沦于外族入侵,一蹶不振。而中国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完整体系,延续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2.在中国大陆的四周,有着对原始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东南海域万里,西北沙漠戈壁,西南高原深壑,北临冻土荒原。这种在大面积内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环境,使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民族专心经营,不谋拓殖,更养成和平温顺、消纳异端之秉性。
3.东亚大陆季风性气候,也对这里的民族及其文明产生影响。中国大多数地区处于温带,四季分明,林木繁茂,物产丰富,加之矿藏资源较多,使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使用石油和煤炭,且早在公元前就发展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冶炼术、炼丹术。
4.由于以上原因,虽然中国有二万公里的海岸线,也有悠久的航海史和辉煌一时的造船业,但中国民族依然以大陆为本,以海内为家。这里的人们安守故土,勤奋劳作,生息繁衍,宗族亲和,进而在多个地域、各种层次上形成互相依存的强大凝聚力。
(二)中华文明的构成和融合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只是现代意义上反映中国境内多部族融合的整体概念,而不是国内任何一族(如汉族)的扩大和代称,但它亦可以包括这一民族移居海外的部分。考古及文献研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氏族林立,族类繁多,依《史记·王帝本记》,除炎黄居于河洛、江汉之地外,又有四大少数民族集团,即共工氏(流于幽陵而变北狄)、欢兜氏(放于崇山而成南蛮)、三苗氏(迁于三危而变西戎)及鲧氏(趋羽山而变东夷)。这几个大集团经二三千年的交叉、发展,至秦汉之时,形成了整合强大的中华民族,紧接着,在两汉、三国、两晋时期,又结合了匈奴、羯、鲜卑、氐、羌诸西北、东北民族,拓宽了农业民族的边界,尤其是唐代汉藏联姻,更具深远意义。其后,直至当代,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而最早出现于太史公笔下的“中国人民”,更是自古迄今地包含着数十个民族的共同特征。
(三)中华文化中的宗教构成
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但与西方文化极大不同,主要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构成极为复杂,不像西方及其他主要外族文化那样多为单一宗教,前者的宗教情绪也远不如后者那样强烈。中国本土产生的主要宗教当属儒教,但儒教又不是彻底意义上的宗教,更多的却是中华民族在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集中反映。另有道教,但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历史上,外国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袄教、景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也在不同范围内流行过,但都没有成为国教,也不曾有其中一种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尽管佛教的信徒人数比别的宗教信徒多得多)。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来看,也是相当鲜见的。究其原因,主要可归功于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各部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亲和性,这种文化对传入中国的各种宗教均不排异,以至形成民间的多神信仰,而在政治上则始终是帝王至尊,甚至地方行政长官也可凌驾于宗教之上。中国封建统治的专制性十分严酷,却从不限制臣民的文化倾向和宗教信仰(即使皇帝成了某一教义的信徒,他或她也决不强迫统治下的人们改变原有的教义),历代王朝的开科取士,只要求应试者按先贤经义破题立论,并不介意其尊奉的是孔孟之道,是列祖列宗,还是释加牟尼、耶稣基督、安拉真主。人们对所信仰的宗教之敬重,主要出于自觉皈依的程度,可以终身矢志不渝,坚守教义,也可以根据实际不断地改变,有许多“双重教籍”、“多重教籍”者,更有大量无教籍者(实际上是信仰上无定式的、更贴近世俗生活的无神论者和多神论者)。这里,笔者想起早在公元15世纪初叶开辟中国至西洋航线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他本是一位专一的回教徒,但中华民族的宗教宽容性在他身上有着典型的表现。他第二次西驶经过锡兰时,曾立一碑(现存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有拓片),即举世闻名的郑和碑,正面刻有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各自的意思是向佛主、向婆罗门教神毗瑟奴、向伊斯兰教真主表示敬意,并祈求平安。这反映了郑和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政府、所象征的中国人民对多种宗教的尊重,希望他们所从事的中外经济文化及政治的交流活动在多种宗教的氛围中得以顺利开展。这也正是郑和以后的历代中国人谋生海外所遵循的历史原则。
二、中华文化的几种特质
文化的涵盖广泛,在不同场合有不同所指,例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钱穆则说文化指“人类生活多方面的综合体”,或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这个概念较多地用于考古学或历史学,这是广泛的。也有狭义的,多指人的知识水平或单指文学、艺术。这里,笔者在文化的中间阶段取其义,即一个民族基本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受之指导的共同的日常生活行为及方式。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意识,或其基本精神,按张岱年的说法(注:见《中国文化集刊》第 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主要有四点:其一,刚健有为,即“自强不息”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二,平和中庸,即“和实生物”、“中庸为法”;其三,崇尚道义,经世致用;其四,天人协调,既改造自然,又随附自然。还有其他要素,但主要可归为以上几点。囿于篇幅,有关基本意识形态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下面简述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人们较为共同的行为方式。
(一)勤劳节用,质朴俭约
这是中国先民早在洪荒时代就突显的美德,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其故事为世代传颂,其精神一直感染、激励着后人,成为在艰苦环境下开创事业的精神基础,不仅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中国人对此坚守不渝,最突出的反映便是近代中国人为生计所迫移民海外,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恶劣条件下,其生存、发展的唯一动力,便是与身俱来、溶在血液中的这种精神。遍阅世界各国华侨史,其开篇无一不是赤贫如洗和血泪斑斑,而他们超出常人的勤奋、自强与节俭,最终都赢得了包括排他性极强的民族在内的当地社会的容纳、认同以至融合。这一点,在世界其他民族的移民史上亦是罕见的。
(二)仁爱与中和
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道德内涵。
仁为孔子学说之核心,儒学视为“全德”。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由己推人,由人及物。墨家进一步主张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仁爱这一主体,经数千年之久,遍海内外之广,一直随中华文化而传播、而弘扬、而发展,更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沟通、共处的主要准则。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夫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乃人伦之道,简单地说,它要求人们坚守正道,行不偏激,情欲平和,兼顾各方。这一点,朱熹在其《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说得平常易解:“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实事求是地说,中庸不光是旧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士大夫执着推行,亦被当今各层明智的领导者、各界人士所渐多采纳;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传扬,更是海外华侨华人在陌生、复杂环境下生根、成长的行为法宝,甚至构造了他们中的精英在异域团结友族、建邦立国的基本方略。
(三)合群团结,以德处世
中华文化贵群体凝聚,倡道义相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详解能诵。亲仁善邻,德洽乡里,是中国的千年民风,也是维系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社会纽带。当中国人远离故土谋生海外时,尤明此理。梁启超析之曰:“人所以不能不群者,以一身之所需求、所欲望,非独立所能给也,以一身之痛苦、所急难,非独立所能捍也。于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后可以自存”(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因而更有“合群分明,则是以御他族之侮”(注:章炳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的结论。
合群团结,毕竟还是封闭的体系,而交友善邻,才可以共同进步发展,这也是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即使是在中世纪辉煌、强盛之时,中国从未侵略奴役过邻邦友族,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威震四海,除了联络友邦、交际经济之外,并未谋求一寸疆土。对此,西方历史家、政治家、军事家大惑不解。实际上,只要明了中国人的此种文化精髓,便也不足为怪了。明清之后,中国人移居海外者渐增,当然多数属寄人篱下,小心求存,但其中亦不乏成就卓越、超然出世之雄才和群体,而无德乱世之大局却从未出现。究其根源,莫非如此。
(四)改造自然,人定胜天;顺应自然,轻松随和
中国自远古就十分注意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和平衡,既强调人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注:《庄子·齐物论》。),又强调对自然的驾驭和改造“人强胜天”(注:《逸周书·文传》。);“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注:刘禹锡《天伦·上》。)。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侧重不同,或者更多的是潜心论证“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对于历代直接参与生产实践的劳动人民乃至科技人士来说,却并没有受到思想的约束和禁锢(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宗教绝对统治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几千年来不曾停顿或滞缓过。这大概便是所谓“华人聪慧说”的历史基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社会稳定,政治升平,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人的才智和成就往往总是上流的。
在人与社会(或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中国文化则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随和性,保持着“顺其自然”的宽松心境(这里“自然”指的是主观世界和人的思维与情感)。例如,中国人较其他民族更爱交友,热情好客,“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妇孺皆知的。朋友熟人之间不言利,讲究礼尚往来、人情世故,决无西方民族那种“人情如纸”的淡薄。由于互相交往较多,一般性的礼仪也就较为简洁、自然。此随和性就像一种润滑剂,消弭了冲突,增进了社会的和谐。
(五)淡己尊他,谦敬礼让
这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大特质。“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宁人负我,无我负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责己要厚,责人要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分别见于《礼记·坊记》,《晋书》卷一二九,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吕坤《续小儿语》,《论语·卫灵公》。),这类名言警句充斥古今典籍,而为广大国人所遵循。在自谦与敬人方面,中华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将谦虚视作美德,语言文字中谦词甚多。如在提到自己时,总是很谨慎,不是“鄙人”,就是“拙作”,不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太满,有成绩总是归于集体或领导;对别人则恭敬有加,问别人姓名用“贵姓”、“尊姓大名”,称对方父母用“令尊”、“令堂”,称对方单位总要冠以“贵”字。诸如此类,虽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看上去也似乎有点繁琐细微,但实际上在人群中默默地酿造着一种宽广豁达的美好人格和昌济和睦的社会正气。
(六)除淫崇孝
中华文化对淫最为禁忌,而对孝则最为崇尚。这一点又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淫之所以为万恶之首,远在中国古代就有着人类学的科学成分,因为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血缘关系的混乱。同时,也是破坏家庭结构、导致社会不安的最大祸根。因此,淫历来为华夏各族及其文化所不齿。而孝在中国古今的社会、家庭、伦理、思想等传统中居于主要的地位,被视为延续祖宗生命与传统的唯一形式,故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训。儒学最高道德准则“天地君亲师”中,最核心的便是“亲”,即孝,其形式已不是简单的养亲,更在乎敬亲、爱亲、尊亲,而且由家庭扩至家族、宗族,再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有一个由亲属、族人、同宗、同乡、师长、朋友组成的密切的人际关系网,从而形成特有的社会关系基本模式。在中国语言中,表达亲属关系的词汇特别多,而且经常用家庭的称谓来称呼别人,用高一级称谓来称呼平级甚至低一辈的人,以表示尊敬、客气和热情,而且的确起到亲近、和善、尊重、爱护和扶持共事的积极作用。西方民族的成员,几乎在一切场合、对一切亲属(甚至父母)都可以直呼其名,这对中国人来说,最多可以理解,但却是难以吸纳的。
(七)尊师重教
中国古代以德教为治国之本,重教也成为中国突出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劝学。无论天子还是庶人,均以勤学修身为本,即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注:《礼记·学记》。)。苏秦发愤刺骨、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照读、王育折蒲学书等古人勤学的故事,几乎为每个中国儿童所必读能详。在中国文化圈中,家长为子女读书不惜破财弃家,孩童奋发求学辛苦万状,其历史之久远,其景象之壮观,堪称天下之最。无论其中可能有多少弊端,但对优秀传统之继承,对知识文化之昌明,对社会进步之作用,是应当大加肯定的。
其二,尊师。中华文化中“天地君亲师”并提,将师放到极高的地位上。“师严然后道尊”(注:《礼记·学记》。)这一道理,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韩愈的一篇《师说》,成千古佳作,不在其文采,而在其师道。在西方,最严肃的地方是教堂,在中国,最严肃的地方是课堂。这恐怕也是中西文化之大不同的一个典型表现。众所周知,教师所授之业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流和方向。因此,尊师重教,只能推进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尊师这一文化特质,在任何社会背景之下,都会是一种积极的因素。
(八)以言会友,以友辅仁
中国人较之其他民族,更重交友,也善于交友。比较特有的一点,反映在交友之初以及平时相会的话题上。中国人初次见面总是相互问对方的个人或家庭情况,与熟人见面也常问些私人的事情,而不是像许多外国民族通常只用固定的几句招呼语,交谈也局限于天气之类的话题。这里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西方人无论初次还是熟人见面,使用着永恒不变的那几句程式化的词语,纯粹是为了打招呼,毫无深入交谈或交友的意思。而中国人则不同,见面总是先根据对方的状况顺势发问,对方酌情回答,可简可繁,即使是一句“去哪儿”,也足以引出一个内容丰富的话题,用餐前后问一句“饭否”,表达的不仅是问候,更有一丝关怀和体贴。首次见面者,问一些轻松的个人情况,决无“管闲事”之嫌,其中的文化内涵却是深厚的,因为在交际时,总要以别人的情况与自己相映照、比较,例如了解对方的年龄、职业、家庭、教育程度等,以判断对方的兴趣所在,找到进一步交往的共同点。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在一起,哪怕是旅途中的同路人,话总是比较多,而且越来越热情,越来越投入,是难以理解的。其实他们不理解的是这种映照性的文化特点,而不是这种现象本身。人们多交一个朋友,社会便多了一份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朴素的大同思想,其中交友的份量是极重的。以言会友,以友辅仁,不失为中华文化的一缕异彩。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及其贡献
随着人口的迁移,文化也在相应的范围内流动着,愈是优秀的文化,其流动性愈强;反之,比较落后的文化,或某种文化的糟粕、低劣部分,则往往局限于产生它的本土,难以外传。文化流动还有另一个条件,即受容民族的接受程度。文化之优劣并非单方所能决定,更主要的是受方的选择。强加于人的文化,是不可能久远的。同时,真正优秀的文化,也决非闭关锁国所能彻底排拒的。因此,只要回顾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对各地社会进步的影响,这种文化的价值也便不言而喻了。
(一)中华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中西交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最为著名的便是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公元三世纪,中国烧瓷技术已臻成熟,之后,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及其他生活、文化产品(如药品、矿物、真漆、茶叶、雨伞、风筝等)的西输,不断地改变着西人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较早的有马可波罗介绍其中国见闻,引起罗马世界的轰动。明清以后,西方传教士大量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在欧洲刊行,系统介绍中国儒家思想和文化特质。17世纪欧洲最博学最权威的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 )几乎对中国哲学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惊叹地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他甚至承认,他的伟大发现——现代计算技术的基础二进制竟远落后于中国人几千年(注:莱布尼兹《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庞景仁译,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3-4期。), 因而古代中国人不仅有忠孝道德的完满成就, 而且在科学方面也早就超过了近代欧洲人。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文化更加赞扬,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特征便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霍尔巴赫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注:霍尔巴赫《社会体系》第1卷,86页,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欧洲的哲学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方向的美妙境界”(注: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82页。)。
至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文学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内容更是博大,限于篇幅,此处不赘。总的来说,中国文化的许多基本构成及其产生的物质形式,对欧洲古代至近代社会发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二)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
朝鲜与中国接壤,文化的接触也较直接和便捷。中朝间的交流,在《战国策》、《山海经》、《史记》中早有记载。儒家学说的典籍几乎全都在朝鲜流传,甚至被定为“国学”,忠孝思想逐渐融入朝鲜民族的“新罗精神”,而且历代都发现了大量儒学师宗。实际上,朝鲜半岛的传统文明浸透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日本早在信史开端就大量吸取中国各种文化成就。公元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其政治制度、地方建制、农工赋税、文字学术、宗教信仰,甚至衣冠文物,尽以中国为典范,为日本后世社会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日本遣唐史的队伍延续260余年之久,这些硕学大师, 不懈地倡导儒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纲常名教等思想观念,形成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壮观景象。
中华文化在朝、日等国的影响至深至远。1994年,韩国著名学者安炳周教授在纪念孔子诞生2545年学术研讨会上说: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因为儒家思想对人的积极向上、奋发自强上进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沟口雄三教授认为:儒学的作用在于其强调对整体负责的精神,这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注:见许肇琳《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的传播》,载于《华侨与华人》,1997年第1期。)。
(三)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
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虽不如朝鲜、日本那样直接,但亦相当密切、久远。
越南,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越裳国、交趾,汉代在彼处置郡,两千年来与中国一直保持亲密关系,尤以文化互补为重,从典章制度、伦理思想、文字艺术,乃至风俗民情,莫不如此,儒家的礼义忠信孝悌等道德观、文化观一直伴随着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黎宪宗于景统二年(公元1499年)颁发诏书,博引中国经典,作为德治和正风俗的依据,历代王朝均强调以德治国,以忠孝为纲,提倡温良恭俭。
柬埔寨在中国古籍中称真腊、扶南,三国时朱应、康泰出使彼地,滞留多年,是后中国文化大量入传,对当地几乎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大大推动了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两国交往频繁,关系一直友好无间。
泰国古称暹罗,历代与中国交往频繁友好。中国人至少在明代已大批流寓于此,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亦不乏以农业、渔业为生计者,他们带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深深地影响着当地土著民族,赢得暹罗人民和王廷的信任、尊重,不少华人被委为国家重臣,或担任各类地方长官。明清以来,暹罗赴华朝贡使团频频不断,其中大批要员(如贡使、副贡使、通事等)均为华人。可以说,他们在泰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占有特殊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将佛教的三宝与郑和联系在一起,设三宝庙,香火鼎盛,当为中国文化发扬于此的象征。
中国与菲律宾仅巴士海峡之隔,民间往来甚久。《宋史》中已有记载,据《岛夷志略》,元代时,菲岛居民到泉州贸易,因“习俗以其至唐(中国),故贵之也”,中菲两国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历代保持密切,史不绝书。
马来西亚是中国古代航海家最早抵达的海外国家,也是中国西汉时期通往印度、西亚、非洲远洋航线的枢纽之地,成为历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五次到访马六甲,此处更成中国丝绸、瓷器、布帛、药品及其他物资的集散地。同时,精神文化的传播也从这里向南洋各地展开,各种手工业和农业技术极大刺激并推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些地区的人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几乎与中国一样,语言中也大量借用汉语发音。据说,在印尼爪哇,有著名的三宝洞等郑和遗迹,三宝垅之地名,便由此而来。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明清以后,大量中国人移居到东南亚各地,上百年来,这些华侨华人有意地保存了中华文化,也无意地传播了中华文化。不可否认,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冲刷磨砺之后,这种局域的文化可能在适应所在地社会的过程中发生许多变化,吸收大量当地文化的内容,从而成为越华文化、菲华文化、马华文化, 这既是文化的变异,也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同样地,在中华文化所到之处,无不产生与当地文化自然嫁接的现象,随之可见中国农工技艺、建筑造船、医药卫生、饮食服饰、文字语言、思想伦理、生活习俗、天文历法等等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的巨大作用,而且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在当今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不论其移民历史多么久远,我们仍可看到种种中华文化的特质,在承传,在发扬,在支撑着他们一代又一代后裔的文化精神,帮助他们在自立、自强的同时,与当地民族共同建设多元文化的家园。在这一点上,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以侵入歧视统治为目的的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从其主流和整体上说,堪称是世界最文明、最和谐、最具友谊和善和奉献精神的“融合性文化”。对于这样的文化,任何开明的社会,有什么理由不去张开双臂欢迎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