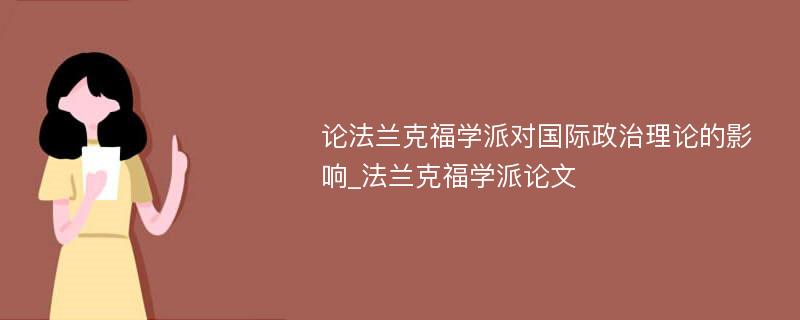
试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政治理论论文,派对论文,试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加剧,并以爆发全球石 油危机的特殊方式,全面挑战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震惊了整个国际政治学界,(注: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和理论应用,是政治学理论被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产 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有着相似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参 看: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欧洲》,1998年第2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年版;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促使它不得不进行理论上的反思。20世纪8 0年代初,居于国际政治理论正统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越来越无法解释所面临的国际政治 现实,特别是诸如主权国家是否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研究要不要 注重“过程层次”的分析和能否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权力究竟是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 惟一目标、国际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还是社会建构、国际政治研究还要不要将人类解放 这一主题置于首要地位等问题,成了新现实主义的“阿基利斯之踵”。由于其本身理论 上的局限性,在上述问题面前,新现实主义显得力不从心、无所作为。于是,各种非主 流的国际政治思潮自动汇合成一股批判的洪流,猛烈地冲击了正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 现实主义。在这个批判的阵营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也有已经元气大伤的科学行为 主义和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注:约翰·米歇海默曾于1994 年将自由制度主义与批判理论归于一类,作为制度理论进行批评。后来,罗伯特·基欧 汉等人专门撰文进行纠正,说明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十多年前批判理论的代 表人物理查德·阿希利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参看: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94/1 995;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5,p.39;Richard K.Ashley,“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Oganization,Spying 1984,pp.225—286.)( 或称新自由主义),还有受欧洲社会学和后现代哲学影响颇深的批判理论。本文试图对 在20世纪80年代这场批判大潮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批判社会理论”及其与法兰克 福学派的理论渊源,进行若干探讨。
法兰克福学派与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风暴”
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包括以理查德·阿 希利、沃尔克和德里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以伊曼努尔·奥德勒、克拉托奇 韦尔、卡赞斯坦和亚历山大·温特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批判理论,以罗伯特·考克斯、斯 蒂芬·吉尔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彼特森·西尔韦斯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以及以 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和生态政治学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1)它们 都反对现存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反对推崇以政治权力界定利益的新现实主义; (2)它们都认为世界政治是由社会建构的,是社会活动和话语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应 从动态的历史角度去关注世界政治;(3)它们都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能够影响国家行为 主体的认同与利益。狭义的批判理论专指受欧洲社会学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而成 长起来的国际政治批判理论,它与继承了法国传统的美国后现代国际政治理论有所不同 ,与世界体系理论、女权主义等也有明显差别。(注:把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 来的做法较为普遍。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8年版,第647页;Jim George,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ulder 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4;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MacMillian Press,1996;Fuat Keyman,Globalization,State,Identity/Difference: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97,p.98.)本文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批判理论一词,即将广义 的批判理论称之为“批判理论”,因为批判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世界体 系理论等都属于20世纪80年代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狭义的批判理论理解为“ 批判社会理论”。
“批判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它与康德、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尼采、韦伯等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论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的最直 接的来源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指20世纪中期,由团结在德国法兰克福社 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著名社会学家所组成的一个影响较大的社会哲学流派,它以批判的 社会理论著称,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姆、阿都诺、H.马尔库塞和J.哈贝马斯等。法 兰克福学派因其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的“物 化”思想,提出并构建了自成体系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所谓的 “彻底批判”,所以又有“新马克思主义”之称。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 整个理性世界已经坠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异,它 不为自由服务而为奴役服务,科学和技术也发挥着“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因 此,为求得人在精神方面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中包括理性、科学和技术在内的所有意 识形态都在批判之列。(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1991年版,第53~54页。)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社会理论家,虽然改变了早期 激进的批判立场,调和了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张力,汲取了实证科学的思想、概 念和内容,但理性批判这面大旗始终未曾丢弃过。
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解放主旨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贬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对知 识批判功能的推崇、对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讨伐,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的深刻反省 ,它不仅引发了20世纪中期关于认识论的哲学大辩论,也对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整个 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欣赏法兰克福学派批 判社会理论的学者们如法炮制,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等诸方面,质疑占正统地位 的新现实主义及其由它所代表的国际政治学科本身,掀起了一场在国际政治学理论发展 史上所罕见的“批判风暴”。在这场理论批判风暴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持批判社会 理论立场的国际政治学者,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理查德·阿希利和安德 鲁·林克莱特等,正是他们把批判社会理论应用到了国际政治学领域,并各自提出了一 些富有创新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见解。
从霍克海姆的“传统理论”到考克斯的“问题解决理论”
考克斯教授是较早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应用到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学者之一。早 在1981年,他就以《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文,揭开了这 场“批判风暴”的序幕。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分类理论,认为理论有“问题解决理 论”和“批判理论”之分,并将新现实主义作为“问题解决理论”的典型加以揭露。考 克斯关于“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的命题,为后人 所广泛接受。一般认为,考克斯关于“问题解决理论—批判理论”分类的思想渊源,就 是法兰克福学派领袖M.霍克海姆关于“传统理论—批判理论”的分类思想。(注: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ian Press,1996,p.147.)霍克海姆认为,在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里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念,即“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传统理论”遵循一 种自然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将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理解为与自然界演进相似的东西, 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客观现象。“传统理论”将主体与客体区别开来,以求达到 某种所谓的价值中立,排除政治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主观偏好对理论研究的干 扰,有利于做到科学研究的客观、公正和准确。一句话,“传统理论”认为,理论研究 要远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尘嚣,回避人文关怀、社会公正之类的道义追求。与“传 统理论”相反,“批判理论”则坚持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具体历史情境”的产物,不 仅根植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服务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服 务于一定的意图和功能,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因而也就能够作为一种力量推动社会 变迁。理论与知识的这种不可避免、不能推卸的社会功能,要求理论行使一种批判功能 ,以揭露、废除现存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及根源为己任,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将被压迫的人从不公正的现存社会中解放出来。
考克斯在霍克海姆“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问题解 决理论—批判理论”的分类,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理论”更替为“问题解决理论”这个 更富战斗性、挑战性的概念。在考克斯看来,“传统理论”表面上采取一种纯中立的、 客观的态度去进行规律性研究,但脱离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没有人 文关怀介入的理论,本质上还是服务于一定的“问题解决”目的的,因而自我标榜为“ 传统理论”的理论就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具体地讲,所谓“问题解决理论”就是 “将世界的现状,包括占优势地位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以及将它们组织起来的各种制度, 作为既定的行为框架(的理论)。”(注: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08.)这 种理论不去挑战世界现状的不合理因素、不去关注社会变革和社会力量,客观上为现存 世界秩序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而“批判理论”则坚持认为,一定的理论产生并服务于 一定的历史社会情势和意识形态,现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秩序不是给定的、必然的,而 是历史的产物,“批判理论”有责任把全球权力结构及其起源、变迁和未来图式作为研 究对象,探索理论与权力的结合条件,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代替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存 全球秩序。沃尔兹及其新现实主义就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开篇 之初貌似价值中立,大量陈述自然科学家或科学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关于理论的界定 ,颂扬了将主客体加以区别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将理论的任务界定为“剔除即使在其 他原则起作用的情况下也存在的驱动性原则”,但后来又承认理论的检验标准既有真实 性和证伪性,又有实用性,也就是对维持国际秩序和获得国际权力有用处。(注:K.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acGraw-Hill,1979,pp.1—10,p .124.)所以,新现实主义是服务于某种现有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地讲,服务于论证冷战 期间特别是冷战初期美苏争夺霸权、共同管理世界的国际权力结构之合理性。沃尔兹不 止一次地提及“两极稳定论”,认为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国际体系,(注:Robert,O.Keohane,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MacGraw-Hill,1979,p.248.)显然从 侧面印证了考克斯对于新现实主义之“问题解决理论”本质的揭露不无道理。
新现实主义对理性的张扬、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实际上代表了理 性对自由的压抑,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统治,国际霸权秩序对社会力量的压迫,它是 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一种阻挠。要清算新现实主义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人类解放事业 的危害,必须重视批判理论的批判功能,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则可 以成为批判社会理论的指南,有助于纠正新现实主义的错误。唯物史观中对将社会冲突 作为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对将帝国主义纳入国际权力结构来考虑和对国际意义上的国 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都有重要的论述。考克斯的历史结构理论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和葛兰西关于霸权、世界秩序学说之上的一种批判理论,它以“世界生产进程 ”定义社会力量,强调社会力量对国际社会发展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力量的具体组 合构成历史结构,历史结构并非以任何直接的、机械的方式决定行动,而是制约行动。 行动在结构里展开,个体与组织在结构的压力下互动、共存、互惠,没有任何一种历史 结构可以占据统治地位。一旦出现这种压迫意图的社会结构,个体与组织就会组成另外 一个与统治型结构相对立的结构。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是三种互不决定的力量,它们 在具体的世界历史演化语境里分别外化为社会力量群、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一句话, 国际社会结构是历史结构,是由社会力量界定的。
从哈贝马斯的旨趣学说到阿希利的《政治现实主义与人类旨趣》
阿希利教授长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执教,是20世纪80年代“批判风暴”中最为引人 注目的理论家之一。在这10年中,他的理论批判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4年以前 他属于批判社会学派,主要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汲取思想,以解放、公正为主旨,来 攻讦居统治地位的新现实主义的“技术统治”实质。他是第一个将哈贝马斯学说引入美 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并将对哈氏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体现在其早期的代表作《政治现 实主义和人类旨趣》(1981年)一文中。1984年以后,他意识到批判社会理论由于强调“ 人类解放”主题,本质上也是一种基础主义和普世主义,这在多元主义和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的新时代已大成问题,因此转向后现代立场,开始关注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 义,对新现实主义及其代表的国际政治学科进行更猛烈的批评,其理论转向的重要标志 是《新现实主义的贫困》一文的发表。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也是当代世界最具影响的社会哲学家之 一。他从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那里继承了理性批判精神,希望建立起一个既批 判现代性又设法完善之、以实践为导向的批判社会理论。他不赞成霍克海姆等人对现代 性的过分批评,认为现代性只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计划”,因此既需要批判其启蒙理性 压抑人性的一面,也不能放弃完善启蒙理性和解放的一面。现代性需要在科学技术、民 主体制和个体自由之间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但事实是,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畸形发 展打破了这种平衡,使现代性发生合法性危机。现代社会被分裂成科学、道德和艺术等 三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出现了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的霸权。要打破这种工具理性的压迫 和霸权,解放被压抑的力量与理性,就要重新树起理性批判的精神大旗,倡导一种具有 解放旨趣的理论。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三种“理论旨趣学说”。他认为,“存在着三 种探究范畴或过程……经验分析的方法体现了技术认知的旨趣;历史的和解释的方法体 现了实践的旨趣;以批判为导向的方法体现了解放的认知旨趣。众所周知,这是传统理 论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切人类知识的背后都有着一定旨趣的影子,总的来说所有理 论大致都与三种旨趣相联系:(1)工具旨趣,它是“对客观化的过程实行技术控制的认 识旨趣”,它关注经验事实及其技术依赖,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旨趣;(2)实 践旨趣,它赞成对自身的历史和理论根源进行反思;(3)解放旨趣,是一种批判的自我 反思,能够解决实践旨趣和工具旨趣的内在冲突,揭示出工具旨趣的所谓“无旨趣”虚 幻,指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解放旨趣是所有旨趣的出发点和前提,只有批判的自我反 思才能把知识从一切独断主义中解放出来。
阿希利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旨趣分类全盘应用到对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分类之中,并强 调指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在改造传统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背叛了后者固 有的实践旨趣内涵,实质上是一种以实证主义的技术统治旨趣压迫实践旨趣的过程,从 而使得现实主义几近沦为考克斯所谓的“问题解决理论”。在阿希利看来,以E.H.卡尔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历史 —人文科学味道和实践旨趣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为例,政治现实主 义只是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为了维持和平需要最大化地追求权力,这只是有意 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和平困境提供了一种实践出路,而并不必然将无政府状态“物化”。 在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中、在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中、甚至在摩 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政治现实主义都注重历史分析、价值分析和定性分析,并不 排除和否定道义、偶然性和特殊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都将科学实证主义分析局限在 一定的范围以内,对无政府状态的强调也只是作为整个权力政治研究的一个实践框架。 但在沃尔兹那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代替了原有的历史、价值、反思和实践关怀,使 无政府状态上升到一种物化的国际结构,国家只能在它的统治下行事,除此之外别无他 途。在现实主义主导和解释下的国际政治理论由此而堕落成一种技术统治工具、一种问 题解决理论。为了正本清源,解放国际政治理论中被压抑的实践旨趣,有必要抵制新现 实主义的实证主义技术统治,将批判社会理论纳入到国际政治理论中来。(注:Richard K.Ashley,“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38,1981,in Fuat Keyman,ed.,Globalization,State,Identity/Difference :Toward a C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97,pp.99-100.)
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到林克莱特的革命主义
英国凯尔大学教授林克莱特也许是20世纪80年代“批判风暴”中最后一位重要的批判 社会理论学者。(注:林克莱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批判社会理论活动,但他的 主要学术成果直到1990年才得以系统地出版。参看:Alastair J.H.Murray,Reconstructing Realism,Kiel University Press,1997,p.183.)他也是从哈贝马斯的 批判理论中获得了智慧和启迪,发展出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分析方法,并 以此展开了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是林克莱特批判社会理论的 出发点。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一直致力于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过分 地重视生产力的作用而对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地位缺乏足够强调。他认为,生产形态对于 社会变革固然至关重要,生产力的理性化也确实不可低估,但不能因此而忽视社会生活 中的符号生产,即由构建社会互动的规则、规范和制度所生产的巨大能动性。因此,要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转换范式,从马克思的生产与意识范式转换到 语言的范式,将普通语用学作为分析个人认识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基本工具。具体地讲, 人类理性可以分为认知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而与理性相联系的行动,也可分为遵从 认知工具理性的行动和遵从沟通理性的行动。因此,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理性及其行动模 式:工具理性(行动)、战略理性(行动)和沟通理性(行动),其中沟通理性是一切话语的 前提,是评判个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标准。而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高扬人类的沟通 理性,将之从技术工具理性和社会战略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 自由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条件。(注: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Boston,1979,p.130,p.118,p.120;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1~222页。)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被20世纪80年代国 际政治学界的不少学者用来作为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武器,而在林克莱特那里则体现得最 为充分。
林克莱特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析之中,并赋予三类理性以 动态含义: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理性化,即技术—工具理性化、道德实践理性化和战 略理性化。技术—工具理性化是指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化是指学习如何建 构秩序和社会公意,战略理性化则是指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 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化与强调生产力作用的、强调世界经济决定世 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有联系;道德实践理性化与林克莱特等批判社会理论为代 表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之间有内在一致性;战略理性化则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 (注:A.Linklater,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ian Press,1990,pp.171—172;Richard Devetak,“Critical Theory,”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62—163.)显然,林克莱特教授与受法兰 克福学派影响的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一样,重视国际间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的作 用,并致力于探索在国际体系内重新实现道德生活、自由沟通秩序的可能性,反对与自 然科学联系密切的实证主义技术—工具理性以及社会领域中以实施政治控制为目标的战 略理性对人、国家等行为体的压迫,他关于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可以有共处原则的 理性化模式的思想,反映了自康德以来的、经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的理性批判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理论界的某种内在的、强烈的诉求。
林克莱特认为,不论代表批判理性的革命主义,还是代表技术—工具理性的马克思主 义,或是代表战略理性的新现实主义,都必须相互学习、和平共处和多元并存。但目前 的问题是,新现实主义必须从其他理论特别是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汲取应有的营养。 具体来说,新现实主义“战略理性”最应当检讨的是它对人类解放机制的忽视。新现实 主义对国际体系中国际结构对行为体的物质性限制过于重视,对其他强调实践理性的理 论模式大加讽嘲,只知道研究如何控制对手、如何服务于两极格局下美苏斗争的需要、 如何鼓吹“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国际体系”,而对全球范围内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危机 则漠不关心,实际上限制了个体对普遍人性的认同、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类解放进程的 期望。林克莱特认为,与人类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 的界定,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证。新 现实主义将国家概念绝对化、静止化的做法“实不足取”,因为它没有认识到,国家本 质上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主权与主权制 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为此,需要提倡一种“国家结构的社会学”,以解释国家是如何 被人类历史建构,解释国家如何建构其法律或道德权利、责任以及这些制度创新如何推 陈出新,特别是要解释那些促使主权国家形成并将国家与外部世界疏离的社会纽带,又 是如何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等等。这将意味着对新现实主义的“有界国家”、“绝 对国家”、“静止国家”等概念提出怀疑,有可能动摇新现实主义整个理论的基础。而 国家理论的动摇则是国际政治理论实质性发展的开始,也是人类共同体向更高层次迈进 的开端,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解放。因为,人类的自由、自决,人类每前进一 步,都有相应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最初有家庭,随之是部落,后来是国家的出现。国家 有其进步性,但离创造“一个由拥有与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权利和责任的自由人组成的 社会”这个人类的美好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人类社会处于共处原则的理性化 与普遍道德律令的理性化之间的地带,亦即由公民身份向人类身份转换的过渡阶段。公 民身份的丧失过程,人类身份的强化过程,也就是普遍道德律令的理性化不断取得主导 地位的过程。人具有公民身份的事实说明,每一个人只能通过承认其他公民而非一般意 义上的人类而确定自己,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制度将国家内的个人与周围世界疏离开 来。因此,新现实主义强化国家、主权,目的在于为国家阻碍个体向拥有人类普遍责任 意识方面发展做理论辩护,反映出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这是“战略理性”的本质之 所在。(注:Linklater,“Men and Citize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ian Press,1982,p.138,p.167,p.205,pp.17-18,pp.134-136,p.171.)
结语
综上所述,批判社会理论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旨,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 诸方面对新现实主义及其代表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其合理性。从认 识论上看,人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不可能如新现实主义那样持客观、价值中立的态度,任 何理论、知识都有一种预先规定的利益,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动物,是处于一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和环境中的人;理论也都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理论这样的社会科 学尤其如此。那种用认识自然界的方式来认识、理解国际政治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批 判社会理论的这种认识论转向,为其以人类解放为主旨的新启蒙运动做了理论准备,也 反击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过分干预。从方法论上看,批判社会理论弘扬了与实践旨 趣相联系的人文—历史—释义学方法,反抗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技术工具 统治,并试图通过批判的方法来缓解两种方法之间的内在张力。事实表明,批判社会理 论的崛起有利于国际政治理论界对于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欧 汉也不得不承认,目前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制度研究中有两大思潮:一是以新自由主义为 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一是以批判理论为代表的反思主义思潮。(注: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James Der Derian,ed .,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284.)这种反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即不能照搬自 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说明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而应用释义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 方法来理解国际政治。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发轫后一直影响着国际政治理 论的发展。但是,批判社会理论对国际政治的震撼,在于其在本体论上的激进立场,即 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而不是物质结构,不是新现实主义所谓的物质力量 之对比,国家、国际体系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改变的。这成为后来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最难反驳的领域,也是建构主义的最得意之处。主流建构 主义正是在“本体论革命”的基础上建构起较为完整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除此之外 ,批判社会理论提出的实践概念和人类解放主题,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总之,批判 社会理论对现有的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洗礼,尽管是粗 糙的、不全面的,但毕竟动摇了新现实主义某些假定和命题的基础,促使主流理论开始 检讨自己的理论缺失,并在一定限度内开始与边缘理论进行对话。
标签: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