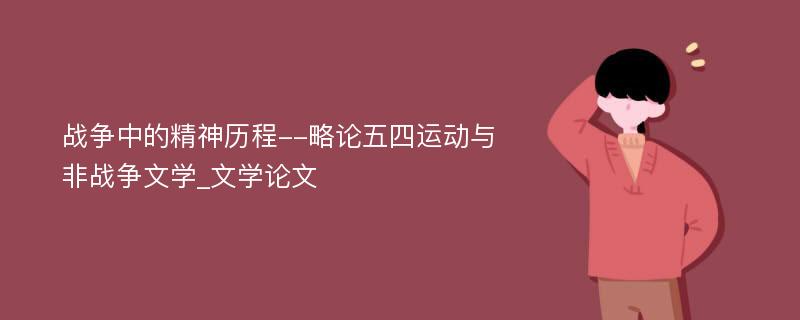
战火中的精神历程:“五四”“非战文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火论文,历程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和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人类和民族的命运,震撼着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无情地将无数个个体抛向苦难的深渊。难以数记的生命、财产被毁灭,人道与正义在战火中苦苦挣扎。文学作为人类和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为我们记录下了历史的苦难行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挖掘出一批久已被人们忽视的军事文学作品,而在于通过这些艺术上不无缺陷的作品,去领悟中国现代作家在战火中的心路历程。
一、战火中的人生:“兵祸”备忘录
从1916年至1928年,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在这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政局动荡中,容纳着历史上那些令人作呕的污垢:复辟、兵变、贿选、暗杀……。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被这些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与政局动荡相伴随的是军事斗争。各路地方武装像失群的游蜂左冲右突,全国遍地狼烟滚滚。地方上小规模的战争难以数记,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四次:1920年直皖战争就持续了10天;1922年直奉大战持续了7天,但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前者;1926 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一场残酷的战争打了8个月,伤亡极其惨重。 而在此之前,1917年中国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数以万计的良家子弟化为累累白骨,难以数计的妇女遭受蹂躏,无辜的民众在兵车和战马下挣扎呻吟!是谁给了军阀们挥霍生命的权力?他们的滔天罪行应该由谁来审判?我们总是说“历史是公正的”,这“公正”究竟要到何时何地才能体现呢?历史是沉默的,所有的疑问没有人能够回答。带着这所有的疑问,我翻开了那些发黄的书页,终于发现,在军阀们烧杀奸淫的时候,已经有人将他们的罪恶“记录在案”,并写下了他们的“审判结果”。只是因为后人的漠视,这一“审判结果”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公之于众”。这位伟大的“审判者”就是文学,它的记录员就是“五四”那一代有良知的作家。
在时代的动荡中,作家既是“在场”的当事者,又是最清醒的见证人。他们凭借着手中的笔记录下阴谋与罪恶,呼唤着人道与正义,成为罪恶年代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作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新青年》、《新潮》、《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著名报刊上,留下了他们的“观察笔记”。在1924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的时候,《小说月报》以超常篇幅(是正常篇幅的一倍)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茅盾撰写了长篇论文《欧洲大战与文学》,通过对世界战争文学的宏观论述,奠定了战争文学的理论基础。
“五四”文学在“为人生”的旗帜下,密切关注着中国下层民众的命运。而当时置民众于水火的首先是战争,因此对军人存在价值的质疑及对战争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成为“五四”军人作品创作的突出特征。在战火的焚烧中挣扎的中国文人,被和平的渴望灼痛了眼睛。他们朦胧地意识到“和平与兵绝对不相容”(1),“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 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2)。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似乎中国的武人一向就享有法律上的豁免权。但到了“五四”时期,知识者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清算历史的旧帐和现实的罪恶。《小说月报》“非战文学”专号上,刊有几幅美国的战争讽刺画:一位因痛苦而面部抽搐的母亲,扛着一座巨大的墓碑,碑文是“纪念我战死的儿子”;另一幅画题名为《日蚀》:画面上越来越大的黑斑上写着“战争”,越来越小的太阳上写着“进步”。这两幅画从理性(战争吞食进步)和感性(丧子之痛)、群体(人类)和个体(母亲)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负面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一主题的阐发。
战争的苦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双方的伤亡,另一方面是兵对民众的蹂躏。“五四”作家对后者更为关注。他们以民众为本位,记录下了“兵”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未满月的产妇被强奸(叶伯和《一个农夫的话》)、为逃避蹂躏被逼跳河的母亲(普生《完卵》)、叔父被兵打伤在风雨中哭嚎一夜而死(徐玉诺《一只破鞋》)、成群的人被强行拉夫(冯西玲《战争的一幕》)……战争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人间地狱”(陶雪峰《人间地狱》)图。这一时期,控诉战争长篇叙事诗,也空前繁荣。李之常的《战栗之夜》以160多行的篇幅, 描写了诗人听到枪声后的恐怖心理,充分反映出人们杯弓蛇影、闻兵丧胆的“临战”心态。在分不清是往事、是现实还是虚幻的事件中,诗人仿佛清楚地“看”到:“十个兵”轮奸并杀死了一个姑娘:“五个兵”抢劫了一家洋房,污辱了一位50多岁的婆婆。最后随着枪声的逼近,兵闯到自己的家里,自己挨了一枪!“战栗”正是战争年代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态。
如果说战争是一道溃烂的伤口,那么兵匪就是成群吸吮浓血的蛆虫。他们所到之处:
方圆数十里外呵!/不曾有一人走路,/不曾有一缕烟火,/ 不曾有一声犬吠,/原有的沃壤呵!/原有的村落呵!/生满了野草,/……凄凉呵!/破荒呵!兵匪蹂躏过的乡土!(3)
“白骨露天野,千里无鸡鸣”的历史场景,在20世纪中国再次被兵们制造了出来。祖国各地处处可以听到《大兵过境时的饮泣声》:
军阀是衔着屠刀的屠夫。/ 小百姓不过是躺在杀床上四肢受缚的瘦猪。/我们的命运呀,/怕只有白刃一闪的瞬间了吧……(4)
陈大悲的剧作《虎去狼来》正是对军阀混战的形象概括。作家们对兵祸的记述,为罪恶的年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灾难备忘录。
二、战火中的“法庭”:军人在审判、忏悔中的觉醒
现实的苦难强烈地刺激着作家的心灵,使他们无法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致使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愤激情绪。出于情感渲泄的需要,审判处罚模式和忏悔反思模式成为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倾向。惩治战犯,使恶兵有恶报,是人们的共同心愿。但在现实社会中,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作家便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虚构的形式将这一心理释放出来,达到对这一心理渴求的替代性满足,形成了小说创作中的审判处罚模式。这既是对现实的抗争,也是给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小说《一个逃兵》(5)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性作品。 败兵吴得胜和他的兄弟们在一个小镇(南市镇)上进行抢劫,并纵火烧了南市镇。吴得胜极其凶残,他甚至为了一只金表,将一个女人的手剁了下来。由于他抢的东西太多,没有赶上撤离的队伍,一个人在山野间迷了路,被抓回了南市镇。南市镇的人围着他义愤填膺,决定将他活埋。在活埋之前,村长公开审判了这个“天理国法人性难容宽恕”的人,宣布了他的所有罪状。吴得胜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临死时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忏悔:
“……现在我底命运,我底将来的希望,已完全明了了!圹穴已经深洞洞地显在我面前,只须把脚一提,我的一生便算完了!这样我还有什么希求,还有什么话说呢?……但是我想,一个恶人,最后的觉悟,总比把罪恶带进坟墓里好得多!我以前在军队里过生活,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的!……从这一次打了败仗,到南市镇烧抢杀掠以来,我才感觉我到现在这个时候打止,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罪恶的,没有一桩不是远背公理正义人道的!……”
审判与惩罚及明显与人物性格不符的忏悔陈述,处处透露出作家的良苦用心和主观意愿。这是在精神世界里“私设”的法庭,公理、正义和人道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作者成了法官。在这类作品中,与其说我们读到了社会的真实,不如说它暴露了作家情感世界的真实!
有时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就让生活本身去“惩罚”恶兵。小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一心理的反映。义勇军进城后,第二营六队队长陈勇和副队长王忠深夜带了步兵出城寻找酒色。因酒馆老板不开门,他们放火烧酒店,引起罗茜村火灾,村庄变成一片焦土。后来王忠在村外强奸一老女人,事后发现是自己的母亲,便自杀身亡;陈勇收到三叔的遗嘱:将罗茜村的房产留给他,陈勇望着化为焦土的罗茜村,亦自杀而死。跟随的步兵不知详情,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6)作品带有明显的虚构痕迹, 但作者欲使“恶兵有恶报”的强烈愿望是非常真实的。正如鲁迅批评的那样,这类小说“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7)。然而不如此, 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情怀。
反对战争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让士兵充分意识到战争的危害,使他们幡然醒悟,放下屠刀,改过自新。中国少一个兵,就少一把屠刀,就会少一些悲剧。因此让士兵现身说法,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进行忏悔,另一方面,对战争进行反思,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战争的价值,这对于正在行凶的士兵,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手段。作者这一强烈的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化为情节设置的忏悔反思模式。它常常与惩罚模式相伴使用。《一个兵的忏悔》中的士兵胡欺人在部队“奸掳烧杀”,后来得到消息,他的母亲被别的兵杀了,他的妹妹被别的兵轮奸后杀害了。胡欺人在丧失亲人的刺激下,开始忏悔:“上帝!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奸,掳,烧,杀——都是罪恶。我底手染满了兄弟姊妹底血!我把灵魂交给与你,慈悲的上帝!求你接受我的灵魂……”(8)中国的士兵, 到底有几个临死时向上帝忏悔是个未知数,但“五四”时期“士兵忏悔录”小说的大量出现,倒真实地显示出文人“逼”士兵忏悔的痕迹。
对自身罪恶行为忏悔必然导致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一粒子弹》中的根,在他舅舅的帮助下退学当兵。他认为很快就可以当上军官了,所以趾高气扬,看不起仍在上学的同伴。后遇兵败逃回家,死前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对他的同学说:“我的死是很不值得的,哥儿!……冤枉了!……人生的蜡烛,总要点在人群经过的通衢上;不要送入风雨的场所,……我走错路了,走入子弹箱里去了!……已经是一粒子弹了!……唉,一粒子弹!”(9)士兵是军官手里的“一粒子弹”, “子弹”炸裂时鲜血染红军官们的领章和肩章。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使他从根本上对自己军旅生涯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冰心是“五四”时期名作家中写军人题材最多的人,1920年,冰心集中创作了大量的军事题材的问题小说,其中《一个军官的笔记》,是忏悔反思题材的代表作。这位下等军官在战争将要打响的时候,得知对方的指挥官是自己的弟弟——他伯父的儿子。兄弟自相残杀,给他很大震动。后来受伤往进医院,开始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问:“为谁牺牲,为谁奋勇,都说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条狗一般,半点价值都没有,真是从何说起!”(10)他曾经认为,军人为国效力,是无上的荣誉,但“自从赴欧观战以后,看见他们的苦境,已经稍稍觉得战争是不人道,而且是无价值,眼看得我们为少数的主战者,努力去做这不人道,无价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这是继“五四”“人的觉醒”、妇女解放和儿童的发现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革命——“军人的觉醒”,是人道主义对军国主义的胜利。它预示着人的觉醒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它向人们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人也是人,他们不再甘于做“一粒子弹”,而是要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审判、忏悔主题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五四”军事文学创作的价值体现。
三、战火中的“艺术”:战争小说创作中的“三无”特征
战争小说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水浒传》、《三国演义》为这一题材的创作树立了两座丰碑。从这两部作品来看,他们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他们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三国演义》中刘备为匡复汉室而战,与曹操形成一“正”一“邪”的对峙;《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给自己的反叛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二、英雄成为小说表现的核心。《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关羽、张飞、赵云、周瑜、李逵、武松等掷地有声的英雄人物,使作品焕发了迷人的光彩。在英雄的映照下,士卒成为战争的材料——他们只是以“数目”出现在战场上,他们的命运和性格得不到表现。三、作战过程交待详细。这两部伟大的战争小说,对战争场面进行气势恢宏的展现,对每次战争的摆兵布阵也有着极为详尽的描写。“五四”时期的战争小说,没有继承这一古老的创作传统,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无“主义”、无英雄、无战争过程,成为典型的“三无”小说。
(一)无“主义”。“主义”是战争的灵魂,它决定着一场战争的性质、意义及最终的价值实现方式。从主战者的立场来说,“主义”是他赖以发动群众和鼓舞士气的工具。从走向战场的每一个军人的角度来看,“为谁而死”是他们首先面对的问题。自然除了“主义”这一高远的目标之外,每一个军人还有着更为浅近的利益。如可以借机报自己的私仇或获得奖赏等。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军阀混战,本质上是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他们为自己寻找的“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已不再具有诱惑力,其欺骗性也昭然若揭,所以对走向战场的军人来说,高远的“主义”已化为泡影,只有浅近的利益可以追寻。这就必然使战争失去了人们预想中的崇高感,成为纯粹的生存之战。事实上,在军阀的军营中,大部分士兵是为了吃饭而从军的。连年的军阀混战陷民于水火之中,没有生路的农民被迫走向军营,使军队的人数急剧扩大,它反过来又会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民穷而兵多——兵多民愈穷。在1916年至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尽管人员伤亡惨重,但军队的服役人数仍然在持续上升。据统计,1916年中国从军人数约有50万,到1928年上升到200多万,许多人“把当兵看作吃粮的手段”(11)。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创作“主义”的缺席,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军队是等级制度最严重的地方,“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现代军人已经觉醒了,他们愤怒地谴责他们的营长:“我们挺着饿肚皮,去碰敌人的热钢子,替你争功劳,加头街;你倒陪着小老婆,花天酒地的,闹闲情,开玩笑;真个把我们看得太傻了!”他们的营长振振有辞地说:“我千辛万苦地熬得个营长,是易得吗?……当营长要仍和当兵一样,谁还去当营长呢?……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当营长呢?”(12)营长这一番表白,道出了军阀混战的实质:为官位而战,为“威福,子女,玉帛”而战。既然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吃饭,那么参加哪支部队就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 “一个中国士兵在3至4支不同军队中服过役已非罕事”(13)。 一位俘虏被劝说投降时表示:“只要团长恩典,有什么不能呢。那里是四两二,这里是六块大洋,那(哪)里干不是干,还分什么彼此吗?”(14)另一位受伤的士兵说:“我们吃七八块钱一月的饷,一时在这部下,一时在那部下;有饷就来,无饷就走。就是主帅也未尝不是这样。某人的势力大,就同某人去攻打从前的伙伴,等到敌人用饷来引诱,又即刻倒戈反攻。我们随他们的指挥,今天合拢东边去打西边,明天又合拢西边去打东边了……”(15)这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小说《风雨之下》、《谁哭》、《一粒子弹》都揭示了为吃粮而当兵这一社会现实。“主义”的丧失,使战争变成了谋生的职业,就连祖宗“替天行道”的大旗,都被淹没在利欲熏心的血泊之中!但毕竟还有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军阀混战中顽强地寻找着生命瞬间的辉煌,寻找着战争的崇高和神圣、根源与结果。但苦苦追问的结果,依然是迷惘和困惑,最终还是走向对战争的彻底否定之中。《龟头桥上》的作者就试图找到战争存在的合理性。他借主人公子心的口说:“我认为战争性是人的天性,世界倘然不沉沦,战神也决没有匿迹的一日。我想,世界是演化的,没有战争世界便不会动了。”子心是一位书生,他希望能从人的天性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上,为战争寻找存在的理由,但他的“高论”立即受到曾经参加过战争的老仁叔的有力驳斥:“你说什么?战争,打仗,是好的吗?一方打败,一方使会有一种新东西产生出来的吗?嘻!这倒也不错,打仗产出的新东西是什么?是那活龙鲜跳的人,会说话的人,打成了几根骨,几张皮,几点血了!是把一个人分成三样东西了!这就是你所讲的新产出的东西!你说战争是天性,打仗是天性,我尤其不懂……”。战争就是毁灭,就是屠杀——“两支大军相打,就像一支更大的军自杀”(16),这就是没有“主义”的战争的本质!
(二)无英雄。英雄是战争的“副产品”,也是人类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所谓英雄,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临危不惧、 勇于牺牲,并在关键时刻能够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人物;2、 他必须是为了捍卫某种被公众认可的、甚至是积极的、进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观念和原则。只有前者,不过是一介武夫,只有后者,可能会成为一个懦夫。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就会发现,从1916年到1928年的军阀混战,是注定塑造不出英雄来的,因为没有“主义”的战争中,只会出现“莽夫”、“武夫”和“凶手”,决不会出现英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十余年的战争中,“拼命三郎”不乏其人,我们却说不出一位英雄的名字。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现代战争文学创作“无英雄”现象的产生。不是没有人想成为英雄,而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军阀混战,将战争变成罪恶,使那些想成为英雄的人陷入了一个怪圈:你越是勇武,罪孽就会更加深重——它与成为英雄的目标就会越遥远!所以那些做着英雄梦的青年,最后发现成为民众的罪人,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忏悔。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这一时期军人忏悔小说极一时之盛,正是这一心理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些不想成为英雄而是纯粹为了谋生走向军队的人,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内心就会充满恐惧。所以贪生怕死成为大部分军人的特征。当一位军人负伤回家时,他感到痛苦的不是被“乌鸦啄伤了面皮”,而是他的内心。他没有享受到英雄凯旋的荣耀,而是用带血的声音向人们倾诉他的凄伤——他的母亲、妻子、弟弟都在战火中丧生!他愤怒地质问:“咳吃人的沙场哟,/是谁将你赶在我们的颖水之滨; /你有红喙吞食我一家人的肝胆,/你有血口嚼碎了我凄酸的心。”他痛苦地祈祷:“我的亲人呵,/别再来吧,/别再怕我孤寂伶仃;/ 那是我黑夜里的好伴侣呀——/凄冷的鬼哭,/晶绿的磷灯,/跳动着的心悸, /颤落着的泪声!”(17)这不是英雄凯旋的乐曲, 而是被战争蹂躏的生灵的叹息!在没有英雄的战争中,“人道主义”浮出血污的海面,成为作家观照战争的基本立场。因此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人道主义超越了各军阀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人们在罪恶年代里赖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撑,成为人们抵御战争、医疗创伤的凭籍。至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兄弟或表兄弟在战场上无可奈何地火拼,成为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情节。作家们是想借拳拳亲情来昭示干戈之惨烈,以便唤醒在战火中变得麻木的心灵。当一个负伤的士兵遇到一位负伤的敌兵时,他们没有将子弹射向对方,而是坐在一起相互问候。相同的命运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那位“敌兵”说:“我身经几十战,打死了不少的人。但都是我所不愿意打的呵!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故乡的人……”(18)冰心笔下的那位无名的“兵丁”(19),在战争的间歇,碰到一位叫“小玲”的孩子,他把枪给小玲玩,以便他喊“胜儿”时让小玲答应——胜儿是他的儿子!女性作家以其细腻柔婉的笔致,揭露了战争对人性触目惊心的摧残!在人道主义的烛照下,作战“英雄”不过是杀人凶手,又何来英雄可言呢?因此,英雄的消解,人道的呼唤,构成了“五四”军事文学的主要特征。
(三)无战争过程。每一场战争,都具备一些基本的因素,如时间、地点、作战双方及战略部署和战争过程。但中国现代作家在写战争的时候,这些基本因素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既使像《梅岭上的云烟》、《一个军官的笔记》这类写到战争过程的小说,也重在表现作品主人公作战时的心理,没有像后来我们熟知的《保卫延安》、《红旗谱》、《林海雪原》那样,对战争过程作如此详尽的记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战争小说其实是“没有战争”的小说。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据现有资料证明,“五四”时期军事文学的创作者中,无一人属行伍出身,也没有一人像托尔斯泰、海明威一样曾亲临战场或做过战地记者。而中国军队中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他们大多是文盲,所以中国的军队中几乎没有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这必然使作者创作时缺乏实战经验,不能把握战争的复杂性。第二、“五四”文人在心理上鄙视军人,甚至将军人看作社会的一大“公害”,必然使他们与军人保持一定距离,导致战争文学创作中出现浅尝辄止的现象。第三,将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对立起来,使这一代作家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不同性质的军事斗争。在作家的眼中,似乎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对个性的扼杀和人道主义的践踏。“一切战争都是恶”是那一代作家共有的观念。这一牢不可破的认识,使他们对战争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他们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战争宣扬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军人成了一种符号,所以大量的战争文学作品没有塑造出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第四,对人生——主要是个体人生的关注,使这一代作家漠视了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次次规模宏大的战争和北京政权的频繁更替,在“五四”文学创作中没有得到反映。相反,人力车夫的不幸和在苦难社会中挣扎的生灵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补史之阙”的“诗史传统”就此失落。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作家写战争的时候对作战的时间、地点、作战双方、战争目的等“社会性”的内容懒于交待,而重在表现个体士兵的战争体验。很明显,“人生”的内容掩盖了“社会”内容,作品像断了线的风筝,飘摇在社会的上空。这不能不说是“五四”文学“为人生”走向极端的表现。正是上面诸多因素,造成了“五四”军事文学的“战争缺席”症。“为人生”的观念成为支配创作的动力,社会事件必须经过这一观念的筛选以后,才能进入作品。大的社会事件被筛除掉,细微的人生感受被留了下来,必然会使战争小说中有“战争的人生”而没有“人生的战争”。
军事文学的“三无”特征,在深刻揭示军阀混战实质的同时,使小说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对“民生”的热烈关注固然使小说具有了直面现实的真实性,但对社会重大事件的漠视,又使文学丧失了宏观把握时代发展的能力。因此说,“三无”小说的流行,既有其成就,也有着致命的缺陷。清理这笔文化遗产,认真反思这段文学史,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战争的态度有着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左联和解放区作家们在战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化,也没有“文协”作家们极为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基本上是以旁观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对战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这一特殊的人文视角,既决定了他们战争小说创作的成就,也铸成了他们创作中的不足,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