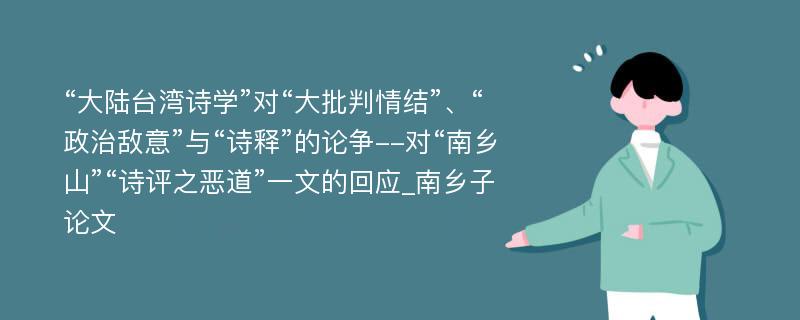
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关于“大批判情结”、政治敌意、诗的诠释诸问题——对“南乡子”《诗评家的邪路》一文的答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邪路论文,诗学论文,台湾论文,敌意论文,一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华夏诗报》1993年6~7期上刊登的《诗评家的邪路》(作者“南乡子”)后,感到有些话要说,特对文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如下:
一是陈绍伟先生是否“有‘大批判’情结”问题,诗歌界自有公论。据说在《华夏诗报》今年春天牵头发起的国际华文诗人惠州诗会期间,就有与会部分著名诗人指陈先生为“棍子”。关于这一点,陈先生本人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造谣诽谤”。他写的重头文章《重评北岛》,以人废诗,严重混淆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北岛诚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出走后的言行本人也毫不赞同。但前期北岛与后期北岛毕竟有一定区别,不应借批北岛为名将“朦胧诗”一棍子打死。陈文的效果,正起到了向明先生在《不朦胧,也朦胧》一文中说的把朦胧诗“批判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一股逆流”的作用(《华夏诗报》转载此文时,此句只剩下含糊其词的“被批判为有负面意义”。编者自然可以删改别人的文章,但既标明是“转载”,删改时却不作任何说明,这不是老实的态度——尤其是删改境外诗人的文章)。对陈先生这篇文章,大陆诗坛当时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他批北岛时,连北岛写于“文革”时的反“四人帮”的诗也给予无情挞伐,这未免“太离谱了”。
二是“南乡子”是否是“陈绍伟”化名问题。陈绍伟先生在今年6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把《华夏诗报》的‘南乡子’栽到弟头上,是道听途说了。”其实,我在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1992年第2期上著文时,还不敢完全肯定,只是说“或许是‘陈绍伟’的化名?”现读了“邪路”一文后,更证明了我这一猜测的正确。请看“南乡子”先生的自白:“我们当中的诗友确实写了不少批评大陆《诗歌报》前几年搞的所谓‘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及所谓‘后新诗潮’之类的诗作评论。”查近几年出的《华夏诗报》,陈绍伟先生在该报总第12期(1986年)上写过一篇批评“大展”的文章:《眼花缭乱之后的沉思》,后来又在《作品》1987年4月号写了《诗人的迷途与诗的迷失——再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还在《羊城晚报》上写过批评谢冕及“后新诗潮”的文章。现在不去评论这些文章的是是非非,只是想证明:“南乡子”说的“我们”的确包含原为《华夏诗报》副总编、现荣升为总编之一的陈绍伟先生在内。既然“南乡子”有陈先生的份,现在又由“南乡子”出面声明“南乡子”与陈绍伟先生等同便是“张冠李戴”,这岂不是有点滑稽?!陈绍伟先生左手编发批判大陆“台港热”和《台港朦胧诗赏析》的文章,右手又在撰写专著《台港爱情诗赏析》参与“台港热”,这岂不是把马列主义当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三是“南乡子”出面声明陈绍伟先生“没有参与”批评余光中先生一事,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陈绍伟先生在《华夏诗报》是分管理论版的,那么多批判或批评余光中的文章难道没经过他的手编发?编发难道不是一种“参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的确陈先生没用本名写过批余文章(这是掌握舆论工具的人方便之处),但我在1991年7月14日晚6时30分到他家时,谈及他不久前编发的头版消息:余光中这尊精神“偶像”“轰然自行崩塌”(《华夏诗报》1991年5月25日出版)欠妥,因台湾出版的《这样的诗人余光中》(大汉出版社1977年初版),是台湾某一派对另一派的攻讦,把20多年前的文章当作头版新闻用套红大字标题发表,且是“自行崩塌”,不是“耸人听闻”又是什么?余光中先生是位爱国主义诗人,有他《当我死时》等诗为证。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两岸读者有目共睹,他的某些诗作和某些评论,也有局限性,对此完全可以批评乃至批判,但总不能不顾时间地点乱批一气,向读者报告余光中先生已“轰然自行崩塌”(请注意“自行”二字)这样近乎“造谣”的完全不确凿的消息。我记得当时陈绍伟先生就承认此条消息编发得不妥——不过,当时未曾录音,在场者只有我们两人。他现在也许会说我在“造谣诽谤”,但他编发的这条消息(或许是他亲自动手写的??)白纸黑字俱在,有报为证。在大陆编发这样的台湾诗讯,编者是不是考虑到有利于两岸文学交流,有利于两岸诗人、诗评家、诗编辑家的团结?讲团结当然不能一团和气,但《这样的诗人余光中》的观点是有极大争议的。在台湾,对余光中先生的评价已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乃至三派、四派,难道也要把隔岸的战火引进到大陆燃烧不成?如果余光中先生这尊“偶像”真的像《华夏诗报》说的“自行崩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不久怎么还会邀请他到北京访问讲学?他真的“自行崩塌”,《华夏诗报》又何必花这么多的篇幅去批判他的对戴望舒等人的评价文章?他的作品在两岸怎么又还会有这样多广大的读者群?!
四是我从未写过《台湾朦胧诗赏析》,只写过《台港朦胧诗赏析》这本小册子。《华夏诗报》在今年第2期转载向明先生的文章时,连大标题都把我的书名弄错,这次又多处把我书名弄错,这真够“离谱”。对照“南乡子”先生的大文,精心校对、精心修改,甚至印成报纸时还留有修改后“开天窗”的痕迹,可拙作转载时,从头错到尾(从开头“一直有增无减”错为“真有增无减”始,结尾“季刊”错成“委刊”止),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先生编此版时的所谓“严肃”态度。不过,这是技术(?)问题,下面再说说“甚至要查封、禁止拙著发行”一事。这“甚至”一词应如何理解,作为总编的陈先生当具有起码的语文常识,它不等于已经实行,我的另一“版本”已说明“幸好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及时发表了……”,此事才未发生,陈先生应是读过此文的。另外,我说的不是一本书,他未调查另一本书的出版遭遇,陈先生的“查证”工作显然粗心了。所谓“史实”不符,是他自己没读懂拙文的原意,调查工作又这样贪图方便,舍远求近。
五是向明先生对大陆的政治敌意问题,作为以政治敏感著称的陈绍伟先生自然不会不知道。如不知道,他转发此文时怎会将向明先生攻击大陆“一贯”实行的“教条式的文艺政策”,还有“朦胧诗人”被迫“亡命海外”这类词句删去?向明先生批评我是借赏析台湾诗“丑化台湾”,这里的“敌意”陈先生应该嗅得出来,这是连《台湾诗学季刊》编者“前言”都承认了的。不过,陈先生虽然以政治敏感著称,但不知怎么搞的,他有时好象患了伤风,鼻子失灵了。如《台湾诗学季刊》创刊号批我的同时还有一文批古继堂同志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此文作者一向持“独台”(不是“台独”,虽然这无本质差异)观点,这次批古继堂同志也不例外。可就这样的文章——连台湾的吕正惠先生也认为此文“太重视在意识形态上面”(见《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3月)。作为大陆的诗歌报竟然转载(据说已排好版,后又取消这个计划。陈先生尽可否认此事,但在今年第2期转载向明文章时,“编者按”已分明说要继续转载下去的,这有文字为证,用不着我“造谣”),真不知何用意?!
六是关于向明先生对某些诗作的诠释我未作正面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某首诗的评价有不同的理解,是很正常的,用不着多费笔墨。如果硬要我作具体回答:向明先生说我选的诗没有一首是“朦胧古怪”的,是因为他用的是台湾读者的视角,而我用的是大陆读者的视角。就是用境外读者视角,拙著赏析过的覃子豪的《瓶之存在》,连台湾、香港、澳门众多诗人和诗评家都感到难于索解,或虽索解了,各人说法不一,这怎能说此诗不晦涩?周梦蝶的诗的一大特色,也是难懂。向明先生在批评我时对此诗的解释就颇为“朦胧”,使人不得要领。还有叶维廉早期的诗以及洛夫的诗,总不是以明朗著称的吧?向明先生还批评我把郑愁予的名诗《错误》解释得不对,可在台北召开的“大陆的台湾诗学”讨论会上,台湾诗人李魁贤先生说:
有关郑愁予《错误》一诗的争执倒颇有趣。记得1990年8月陈千武在汉城的第12届世界诗人会议上发表论文评论此诗时,也是指为对情人的怀念。会后,郑愁予亲自在大家面前向陈千武解释,是对母亲的思念。究竟古远清是有所根据,还是歪打正着?而郑愁予的诗普遍令人认定是写情人,是不是在表达上发生问题,似可以探讨……
我事先并不知道郑氏本人有这样的解释。我解释此诗时不局限于“爱情说”,而说成是对亲人的怀念,与郑愁予自己的解释正好不谋而合。当然,解释诗并不一定要完全吻合作者原意,但向明批评我理解此诗时“扭曲颠倒”,显然过于武断。对《错误》出现的不同解释,正证明《错误》确实写得朦胧,并非如向明先生说的“理路明晰可寻”。他批评我赏析的每一首台湾现代诗都不朦胧,显然不符合郑愁予还有以不按牌理出牌即“古怪”(不带贬义)著称的管管、商禽等人诗作的实际。
七是南乡子的文章多有断章取义之处(此文风与陈绍伟先生行文颇为相似,妙哉)。如他说我讲过“洛夫先生是‘台湾朦胧诗’的首创者”的话,完全违反了我的文意。请读者诸君对照我的原文:
把台湾现代诗称作“朦胧诗”并不是我首创。在大陆诗歌界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看的。在台湾,洛夫先生认为:大陆的“朦胧诗”,宜正名为“现代诗”(《对大陆诗变的探索——朦胧诗的真相》,《创世纪》64期),可见,把台湾“现代诗”看作“朦胧诗”也是可以的。
只要不存心歪曲和学过逻辑知识的人,都知道洛夫先生的话是我推理的依据,要说“首创”也是大陆诗人、评论家先“首创”,这怎么能把我讲的“不是我首创”的话栽到洛夫先生的头上,说是他“首创”的呢?在“大陆的台湾诗学”讨论会上,倒是洛夫先生帮我说了公道话(虽然他对我的赏析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我写此书的用意决无把大陆的“精神污染”嫁祸台湾诗人的意思:“公平的说,据我对作者和大陆情况的了解,未必如此,而是另有原因。”游唤先生在《大陆有关台湾诗诠释手法之商榷》(《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3月)一文中,也不似向明先生那样将我的赏析一棍子打死,而是认为我对某些台湾诗的解释有独到之处:
把爱情主题作哲理化诠释的,如古远清《台港朦胧诗赏析》诠释白萩的《重量》可算一例。这一首在意义与意图上的多元可能(古按:可见这也是一首“朦胧诗”),是来自诗技巧的拟仿,内在独白,与隐喻效果。在书面语中即含有丰富讯息,先决条件就比较适合做“读者之心未必然”的主体性诠释。所以,古远清直觉地将之解读成人生时光青春年少的伤逝感,而不从书面语明显的爱情主题上去找讯息,算是有新解的诠释。……
像如何理解这一首诗一类的具体问题,如要一一作答,实在太浪费精力,还是就此打住吧。不知《华夏诗报》有无这样的气量,将此文刊出,“以期兼听则明”?(注:《华夏诗报》已将此文退稿,可见他们言行不一。)
1993年10月29日夜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