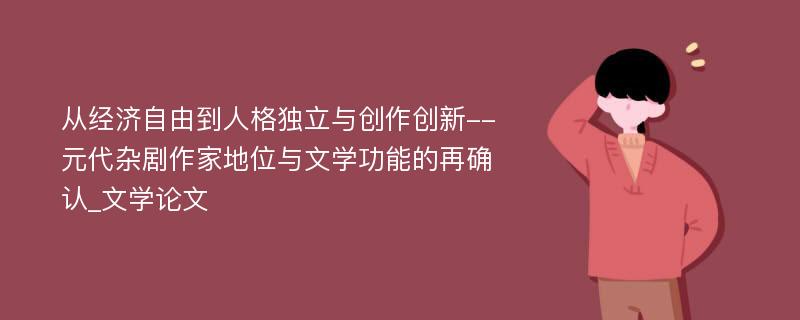
从经济自由到人格独立与创作鼎新——元代杂剧作家地位以及文学功能的重新确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元代论文,人格论文,地位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明朝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中评价前朝“元以功利诱天下,众欢趋之,而习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而宋之旧俗微矣”,论断虽有偏颇,但确实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元朝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本质区别以及士风的根本转变。元朝重视商业,城市经济极为活跃,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层面。不仅在思想上冲击着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传统观念,而且在诸多方面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旧有秩序。以杂剧为代表的俗文学商业化程度加深,改变了文坛基本面貌和整体格局,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俗”文学迅猛发展,赢得了与“雅”文学分庭抗礼的半壁江山,而且带来了文学功能、作家地位等一系列的深刻革命。
元杂剧本身就是城市经济发达的产物。繁荣的商业、富足的生活以及相当程度的文化素养等因素,促成人口密度较高的都市出现了足够多的消费观众,也为戏班、剧作家、编导、演员提供了足以维持体面生活和延续创作新品的物质基础。元杂剧已经彻底脱离了戏剧敬神娱神的最初本源,也走出在宫廷里愉悦君王的基本形态,蜕变为以满足精神消费为手段赚取商业利润的商业行为。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就形象地再现了某地杂剧演出的情景,这里不仅有相当于商业广告式的招揽:“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也有“要了二百钱放过自咱”纯粹商业性演出的清晰交代,还有“层层叠叠团栾坐”①专业演出场所的介绍,都可以看出元代杂剧演出,已经具备了商业化性质的所有必备元素。
一个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是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大都(今北京)富足繁荣,人们注重物质和精神享受,看剧听戏成为最重要、最普遍、最基本的休闲文化活动,具有民众的广泛性。无名氏[般涉调·耍孩儿]《拘刷行院》套曲中写道:“穿长街蓦短衢,上歌台入酒楼,忙呼乐探差抵候,众人暇日邀官舍,与你几贯青蛾唤粉头。休辞生受。请个有声名旦色、迭标垛娇羞。”②高安道的[般涉调·哨遍]《嗓淡行院》写道:“暖日和风清昼,茶余饭饱斋时候……待去歌楼作乐,散闷消愁。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矁一会皓齿明眸,趓一会闲茶浪酒。”③结伴看戏邀约听曲已经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而这种休闲娱乐是需要付费的。这是一个庞大市场,众多的艺术爱好者,常态化的消费习惯,造就了杂剧的极度兴盛繁荣。这为包括杂剧作家在内的杂剧生产者提供了较为稳固而丰厚的经济保障,使得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市场获得经济独立成为可能。
二
体制上,元代承续前朝,依然实行教坊乐籍管理制度,所不同的是,在籍的乐工、艺妓在完成官府规定的应招任务之余,可进行纯粹商业演出,并获取报酬。《青楼集志》云:“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④《马可·波罗游记》也说,在大都“附郭之中”居住的艺妓“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⑤。一般艺妓尚且如此,名家名角更是受到市场热烈追捧。顺时秀是大都名重一时的优秀演员,明初高启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赞扬她的歌舞出类拔萃:“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燕国佳人号顺时,姿容歌舞总能奇。”而她的演出是如此的频繁:“晚出银台酒未销,侯家主第强相邀。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⑥其演出邀约之多、之频繁、之殷勤、之迫切简直令人应接不暇。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非常清晰明确的品牌意识。一旦一种商品具备了品牌效应,那么,它就具备了超值价值。消费名牌,对购买者来说,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象征,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让荣耀之心得到极大满足。这说明杂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商业属性发展已经相当完备、成熟。观众对于优秀剧作家和演员不仅以掌声,更以酬金多寡来表达自己的评判。我们从《青楼集》以及其他元人诗词笔记中可以管窥当时一些著名艺妓的生存状态。如大都艺妓张怡云“名重京师”,她住在大都最为繁华的黄金之地海子(今北京积水潭)附近,家中日夜高朋满座,经常性地举行大型文化沙龙活动和豪华歌舞宴饮,赵孟頫、商道、高克恭等清贵近臣为其画像写真,卢挚等名公显贵为其题字作曲,姚燧、阎静轩、史天泽等高官与其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其所用“酒器皆金玉”,这样豪华排场必有雄厚的物质资本支撑。张怡云席间献歌一曲,史中丞马上取银二锭相酬,报酬可谓丰厚⑦。关汉卿说珠帘秀“富贵似侯”([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张玉莲因为丝竹各种乐器皆精,通晓音律,贵公子多与之往来,所以“集家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靳惜”⑧。歌伎樊事真所用梳篦竟然是金质的⑨,连身居高位见多识广的胡祗遹对此也不无感慨:“富贵贤愚共一尘,万红千紫竞时新。到头谁饱黄粱饭,输于逢场作戏人。”⑩这些杰出的演艺者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艺妓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的艺术水准较高外,缺少优秀剧目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与杂剧作家、优秀剧作三者之间有着极高的依存度。
商业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商品差异化。杂剧演出市场同样遵循这一经济规律,由于演出团体众多,竞争激烈,甚至“对棚”也就是演对台戏的情形时有发生。杂剧是表演艺术,演员技艺固然是这个生产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杂剧作家富于创造力的作品是同样重要的另外一环。为了更大规模地占有演出市场,所有的演出团体都期望拥有更多、更新、更适合不同观众审美需要的杂剧作品,这种需求源源不断,《青楼集》记载:“勾阑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11)查《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诸多演剧皆在剧目名称之前标明“大都新编”、“新刊关目”、“新刊的本”、“新编”、“新编关目”、“大都新刊”、“新编足本”等字样,在名称之后又分别注明是由关汉卿、高文秀、郑廷玉、马致远、武汉臣、尚仲贤、石君宝、张国宾、王伯成、纪君祥等创作。同时,当时的许多杂剧脚本都在宾白与唱词中特意说明是才人所编或新编,如无名氏《蓝采和》杂剧第一折,末唱[油葫芦]:“甚杂剧请恩官望着心爱的选,俺路岐每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12)可见出自名家,属于原创、新作,剧目丰富,已经成为争夺市场的决胜条件。观众对作家清晰的品牌意识,使得优秀作家的号召力丝毫不输于优秀演员。既然作家如此重要,他们价值就一定会在市场链条中以经济的方式得到充分体现。依据价值与价格对等原则推断,优秀的杂剧作家经济境况理应相当殷实。关汉卿在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描述自己的生活是:“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13)这样的生活,必有雄厚财力作后盾方能支撑。贾仲明为剧作家李宽甫所作吊词称其:“西煮令史合肥官,局量胸襟怀抱宽,银鞭紫马驿蜚窜。宴秦楼,宿谢馆。肉屏风,锦簇花攒。金叵一醉,醉斟琼酿。青定瓯,茶烹风团。红烧羊,玛瑙犀盘。”(14)奢侈豪华不减王侯,可见财力雄厚非同一般。关汉卿、李宽甫都是大都作家,他们收入和生活,理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谈及元代士人的经济地位时,现代史学家钱穆先生颇具真知灼见,他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指出:“元虽不贵士,然其时为者之物业生活,则超出编户齐氓远甚……故元代之士,上不在廊庙台省,下不在阎闾畋亩,而别自有其渊薮窟穴,可以藏身。”又说:“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在山林江湖可安,歌咏觞宴可逃。”(15)个人价值通过市场回报得以体现,经济的自立是杂剧作家建立独立人格发展自由精神的物质基础。与传统士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相比,杂剧作家能够抛弃“不仕则隐”二选一的规则,自由地行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他们摆脱了千百年来文人士子附庸于统治集团的窠臼,闯出了一条以文为养的独特职业道路。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史无前例,具有开创性的革命意义。而这种变革得以最终实现,是元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
元科举制度的废弛堵塞了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但对剧作家的成长和壮大却绝非仅有灾难性的负面意义。科举自产生之日,就是为国家招揽、选拔、聚集人才,但同时也是传播、灌输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渠道,发挥着禁锢思想,限制人才成长与发展的作用。科举产生后,绵延数百年,即使是辽、金这样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也从未彻底中断,惟有元朝成为一个异数。《元史》记载:“帝(忽必烈)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16)在不谙汉文化本质的蒙古政权最高统治者眼中,华夏传统文化所尊崇的孔孟之道与诗词歌赋毫无价值,甚至不如小国匠人的一技之长。科举废弛,阻断了文人士子传统的仕进出路,但却将他们从“四书五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上少了些“学而优则仕”功名利禄的追求者,多了一些寻找各种途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目标更加多元。由于由科举而入仕途道路的阻断,以往可以预期的辉煌前程化为乌有,社会地位骤然降低,原本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子被迫走出书斋,走近民众,开始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这种感情的转变成为杂剧产生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失却从政期许的文人士子立场也悄然游移,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传统社会除了赢得君王赏识,政治上别无选择。如今科举废除,政治的羁绊和束缚随之松懈,既然荣辱穷通都与统治阶层无关,那么谁还愿意拜倒在皇权之下,委曲求全,甘当附庸呢?虽然之初确曾感受到被抛弃的痛苦,但发现获得的却是“粪土王侯”的自由。杂剧作家们普遍追求放达适意,明显表现出对帝王、对统治政权的疏离感。庾天锡云:“名缰厮缠挽,利锁相牵绊。孤舟乱石湍,羸马连云栈。宰相五更寒,将军夜渡关。创业非容易,升平守分难。长安,哪个是周公旦?狼山,风流访谢安。”([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名缰厮缠挽》)(17),在这位杂剧作家眼中,出将入相不过是烦心多多,即使贵为君王,也不值得羡慕。反倒是风流自适的谢安,可以引为同道知己。关汉卿在[越调·斗鹌鹑]《女校尉》中也明确地表示说:“平生肥马轻裘,何须锦带吴钩?百岁光阴转首,休闲生受,叹功名似水上浮沤。”(18)他要追求悠然自适无拘无束的生活:“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19)马致远也说过类似的话:“图甚区区苦张罗?”他希望能够“远红尘千丈波”([南吕·四块玉]《叹世》),王实甫说得更直白:“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后庭花])为此,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明哲保身:“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梧叶儿])(20)这些杂剧作家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这些传统诗文作家的人生是何等的不同:一个是积极入世、强颜谏诤的形象;一个却是悠然自适、远离红尘、充分享受生活的态度。
杂剧创作同样表现出自由、解放的精神。《窦娥冤》曾借角色之口发出了愤怒的呼唤:“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21)在将天地视为最高统治者代称的古代社会,这样的叛逆之言,在其他王朝根本听不到,也没有哪个诗词作家敢于说出口。说到与统治政权关系的疏离,杂剧作家与文学史上展现“魏晋风度”的群体表面看倒是有着几分形似。但魏晋士人寄情山水,注重内心体悟,追求清静无为。而杂剧作家却始终关注社会、民生。二者有着鲜明的本质区别。杂剧作家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表面看,尽管是由元代特殊的民族政策、人才选拔制度、官吏任用制度所造成的,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却是杂剧商业化所带来的。对于杂剧作家来说,观众才是衣食父母,是安身立命的根基。杂剧不仅是个人表达激情的渠道,抒发感情的依托,更是他们立足社会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为赢得观众,占有更广阔的艺术演出市场,他们就必须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以民众的喜怒哀乐为创作立场,以民众的喜好作为杂剧创作的审美追求,这使杂剧作家敢于大胆地发出前人未发之论见,唱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对黑暗现实的呐喊、抨击,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艺术创作也更趋个性化。
尽管杂剧作家对进宫为皇家演出依然有所期待。但在他们眼中,皇帝已失去了神圣的光环。高启的《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有言:“当筵按罢谢天恩,捧赐缠头蜀都绮。”(22)既然皇帝观看演出给予的赏赐如此丰厚,又有谁不愿意招徕这个财大气粗且非常大方的“主顾”呢?何况,进宫演出对编剧和演员来说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金字招牌,可以作为标明艺术水平、拓展市场时进行宣传的诉求亮点。《元宫词一百首》就记载说“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入九重知,奉宣赍与中节省,诸路都教唱此词”(23),这里所说的“传奇”也就是杂剧。由词中可见皇帝的提携称赞对杂剧的传播大有裨益。
四
元代杂剧作家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解放,改变着文学创作的基本形态,杂剧这种新的文学样式,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无论诗词文赋还是其他形式,儒家文学观贯穿始终。从《诗经》的诗言志开始,文学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它要代统治阶级行克己复礼的“教化”之能。后世文学更将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能和最终目的。此“道”在大多朝代就是孔孟之道,核心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培养知足常乐的内心安宁。甚至由于对“道”过分强调,有些创作沦为解读、宣讲“道”的教科书,寡而无味,真情尽失。杂剧作家虽然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印痕,他们关注现实民生。但是,其作品所透射出的却是以人为本、思想解放的光辉。如对妇女的尊重与歌颂(《救风尘》),对真挚爱情的大胆追求(《西厢记》),无不彰显着对伦理、道德等社会旧有秩序的反叛精神。元杂剧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以,寄居尼庵却春心萌动的少妇(《望江亭》)、都市中沦落风尘的弱女子(《救风尘》)、甚至是打家劫舍反对皇权秩序的绿林好汉(《李逵负荆》)都作为智慧、勇敢、正义的化身,成为站立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备受歌颂。而“高贵者”,包括飞扬跋扈的皇亲国戚、大权在握的地方官吏、财大气粗的商人,却都成了贪婪、丑恶、愚蠢的代名词,受到辛辣讽刺和无情揭露。剧作家甚至敢于将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嘲笑他面对强敌的软弱无能(《汉宫秋》)。更令人鼓舞的是,杂剧作家通过一系列妇女形象的成功刻画,直接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尊卑观念、男女不平等观念进行了大胆批判。如罗梅英面对恃财逼婚的李大户不仅敢于大打出手,还痛骂了离家十年归来后竟然调戏自己的丈夫秋胡,表现出自尊、自强、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魅力。更为惊世骇俗的是,她竟对“夫纲”提出挑战,公然宣称“要整顿我妻纲”(《秋胡戏妻》)。须知,那是儒家纲常中被视为不可撼动的律条。《汉宫秋》中,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是柔弱女子,王昭君“情愿和番,得息刀兵”,被塑造成救国救民的盖世英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竟是将相大臣这些国家栋梁的惊恐失色,是天命化身皇帝的软弱无能。元人创作中这些“离经叛道”的反传统观念,正是杂剧的光辉所在。在杂剧的功能上,胡祗遹在其《赠宋氏序》开篇进行了生动描述:“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于斯时也(指观剧——作者注),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眸睬,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24)这说明元代人们对杂剧的功能有着非常清醒、深刻的认识,他们是为了娱人,即满足观众精神需求而创作,并不以“载道”为目的。
圣人立德,君子立言,被视为世上不朽盛事,是文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深受儒学传统熏陶的中国传统士人,期望通过立言,影响君王按照儒学理想规范社会秩序,以达到立德之目的。而元代的杂剧作家甚至冲破了“立言”这个创作的基本底线。既不在意讨好皇帝,也不关心身后是否能够树立起千古流芳的“立言”牌坊,在他们眼中,观众才是真正的上帝。尽管周德清认为杂剧创作之社会功能是:“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25)但是创作的出发点并非是要立言、立德。这从杂剧作家很少注重作品的流传以及生平传记的撰写都可以得到印证。对此王国维先生看得极为透彻,他指出:“该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26)自娱,就是以独立自由之精神抒写情志;娱人,就是立足观众。杂剧市场上,观众是作家的衣食父母,因而文学功能由注重教化向注重娱乐的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对艺术功能认识的改变,同样也使得杂剧创作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迥然相异的风格面貌。传统文学观本于儒学“中庸”理念,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艺术衡量标准,讲求中和含蓄。但对此过分强调,难免流于道貌岸然、平庸寡味。而杂剧无论歌颂真善美,还是抨击假恶丑,都充满激情,无不表现得直率、真诚、大胆,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同样是因为杂剧是市场化的艺术,是消费艺术。观众的娱乐需求就是衡量标准,决定了杂剧创作的文学立场和基本面貌,谐谑、蒜酪味道等特色无不由此而生发。
杂剧开辟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新天地,作家摆脱了对统治集团的附庸地位,这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是这种独立自由忠于现实的精神,这种视观众为上帝,把与民众的和谐共振视为创作宗旨及艺术最高追求,并将其置于重于一切的认识,为中国俗文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这也为后来明清之际《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和《金瓶梅》等名著和奇书产生奠定了历史基石。
收稿日期:2012-10-15
注释:
①(元)杨朝英选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5页。
②(元)杨朝英选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第342页。
③(元)杨朝英选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第346页。
④(元)夏庭芝:《青楼集志》,崔令钦等:《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一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8页。
⑤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卷二第九十四章《汗八里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79页。
⑥李圣华选注:《高启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页。
⑦(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18页。
⑧(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第31页。
⑨(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第25页。
⑩(元)胡祗遹:《赠伶人赵文益》,《紫山大全集》卷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11)(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集,第38-39页。
(12)谭志湘、郭汉城编:《中国戏曲经典》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10页。
(13)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典词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14)(元)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页。
(15)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1964年第2期6卷。又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164页。
(16)(明)宋濂:《元史》卷一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6页。
(17)(元)杨朝英编、许金榜注:《阳春白雪(注释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页。
(18)周振甫主编:《全元散曲》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36页。
(19)陈乃乾编:《元人小令集》,上海:开明书局,1935年,第215页。
(20)周振甫主编:《全元散曲》第一册,第113页。
(21)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元明部分),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22)李圣华选注:《高启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页。
(23)(元)杨维桢:《元宫词》,(元)柯九恩:《辽金元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20页。
(24)(元)胡祗遹:《赠宋氏序》,《紫山大全集》卷八。
(25)(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国戏剧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第173-179页。
(26)王国维:《元剧之文章》,《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24页。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论文; 作家论文; 北京演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青楼集论文; 戏剧论文; 关汉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