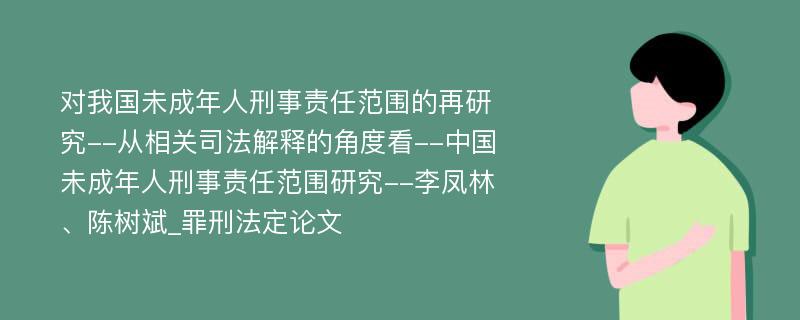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再研讨——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Studies of the Scope of Juvenile Criminal Liability in China——Li Fenglin,chen shubin,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成年人论文,司法解释论文,刑事责任论文,视角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7)06-0148-0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6年1月23日施行,该解释整体上贯彻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①但笔者发现,该解释第5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应当依照刑法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②从而大大扩展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形成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指出,“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立法者、社会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本文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进行研讨,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说争端及评价:限制论和罪名说之提倡
学界及实务界就我国刑法典第17条2款的争端,由来已久。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询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后者以法工委[2002]12号作出答复,指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而不是具体罪名。但该答复就如何确定罪名,并未涉及。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就此作出回应,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确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及至本文开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最新司法解释,又作出了不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应当依照刑法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显然,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也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上述司法机关的一系列努力,其初衷在于平息学界就该问题的争端。然而,事与愿违,司法机关的努力非但没有平息学界的争论,反而引发了就此问题的更大争议。就刑法第17条2款的争端,主要是限制论、罪名说与扩张论、罪行说的对立③:
限制论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仅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限于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这八种故意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突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限定,也不应超出此八种犯罪的限制追究刑事责任。[1]其理论根据在于:1.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2.限制论符合保障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宗旨;3.限制论、罪名说较之扩张论、罪行说更具合理性。
而扩张论者主张,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非只对刑法第17条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承担责任。除了八种犯罪外,还应对决水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汽车罪,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限于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强迫卖淫罪(限于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承担刑事责任。[2]其立论根据主要有:1.该主张充分考虑了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以及公众视野下的司法乃实现公平正义之活动的法感觉;2.上述结论是根据刑法理论及结合立法精神得出的;3.刑法第17条2款立法本身并未明确罪名;4.没有故意重伤或重伤致人死亡的罪名;5.立法规范的只能是犯罪行为。
笔者以为,限制论和罪名说更具合理性,也符合立法的初衷,是可取的,也是本文通篇所欲极力鼓吹的对象。而扩张论和罪名说提供的上述理由并不具备说服力,其观点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如下:
首先,限制论和罪名说符合保障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宗旨。对于扩张论者认为其直接回应了司法实务现实所需,充分考虑了刑法的社会保障机能以及公众视野下的司法乃实现公平正义之活动的法感觉的论调,笔者以为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刑法固然有社会保障的机能,但在法治社会建构过程中,刑法人权保障的机能更是亟待提倡的,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3]显然,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是有其深意的。早在百年之前,刑法鼻祖李斯特便提出:刑法更应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尤其应提请扩张论者注意的乃是,这里司法的对象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其优于成年人的特殊人权保障机能更显必要。
其次,限制论和罪名说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而扩张论和罪行说有违罪刑法定之嫌。现行刑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属于“列举”式规定,较之旧刑法的“列举+概括”式的规定,避免了立法规定的模糊性,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初衷在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本质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国民的人权”,[4]而扩张论和罪行说却试图超越立法原意对刑法17条2款进行扩张解释,是明显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的。
再次,限制论和罪名说符合现代刑法应有的谦抑精神。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谦抑原则,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它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5]限制论者和罪名说对刑法17条2款的解释,符合刑法应有的谦抑精神,而扩张论和罪行说是以牺牲对未成年人犯罪应有的谦抑精神和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为代价的。这种削足适履的解释方法,不仅有客观归罪之嫌,尤其不符合对未成年人应有的谦抑精神,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对于扩张论者和罪行说的其它几个论据,笔者认为,所谓扩张论者认为其结论系根据刑法理论及结合立法精神得出的,实属无稽之谈,立法的真正精神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非随意地对未成年人入罪;其认为刑法第17条2款立法本身并未明确罪名也是不符合立法实际的;即使立法本身规范的对象只能是犯罪行为,也并不能否定立法条文中罪名规定的存在;至于刑法中没有故意重伤或重伤致人死亡的罪名,可能算是罪行说最为有力的论据了,但其仍不足以形成其立论的充分根据。因为法条表述上应尽量清晰简洁,这也是立法技术上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刑法17条2款的法律表述方式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
虽然笔者认为上述论证可谓充分,仍不得不承认,扩张论和罪行说是通说,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认可,特别是最高院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更使其大行其道。然而,前已述及,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之间的意见,也是有冲突的,同样效力的司法解释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适用,却做出了并不一致的解释,暴露了司法解释自身的缺陷,其对司法实践乃至刑事法治造成的危害、尤其对未成年人权益带来的伤害是最令笔者担忧的,这也是笔者极力提倡限制论和罪名说的原因。
二、现行立法: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应该对哪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二是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他们能够对那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第一个是立法选择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是司法适用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立法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为他们所知;二是该犯罪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极其严重的犯罪。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标准,原因在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知识、智力、生理方面的发展,还未达到为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换言之,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刑法意义上一切行为的能力,因此立法应充分考虑该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具备的责任年龄能力的特点,规定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刑法中危害性质严重且易被其认知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之所以限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是因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接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阶段,若动辄给予刑事处罚,便会使他们丧失学习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将来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再则,未成年人犯罪多由于家庭、社会、个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社会病症,仅仅靠刑罚来解决无疑会导致“只堵不疏”恶果。
以上述标准衡量,我们来看79刑法到97刑法的发展轨迹,就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79刑法如是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不难看出,即使是79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也是持限制态度的,但就“杀人、重伤”是否包括过失犯罪,“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如何理解,争议颇多,造成了法条适用范围的极度不确定。[6]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97刑法第17条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而明确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笔者以为,97刑法对八种犯罪的规定,基本上应合了上述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立法标准,满足了保障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讲,现行立法是合理的。
然而,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让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贩卖毒品罪承担刑事责任,又是不合理的,这是现行刑法立法的缺憾之一。贩卖毒品罪是现行刑法347条规定的罪名,根据该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本罪属于选择罪名,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中的一种,即可构成犯罪。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行为,也只能以一罪论处,而不实行数罪并罚。让笔者疑惑的是,立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贩卖毒品罪应承担刑事责任,而未将与贩卖毒品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甚至更为严重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纳入其中,显然是有问题的。故笔者认为将贩卖毒品罪规定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尽合理。原因在于:
首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贩卖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足够准确的认知。刑法理论上,犯罪以行为是否违反社会伦理为标准,可以分为自然犯、刑事犯与法定犯、行政犯。[7]自然犯,“指无须等待法律规定,其性质上违反社会伦理而被认定为犯罪者,也称刑事犯”,[8]例如,杀人罪、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刑法典中规定的多数犯罪,都是自然犯。由于这类犯罪具有违反社会伦理的性质,其危害性易为人们所认识。法定犯,“指原来没有违反社会伦理,然而根据法律被认为犯罪者,也称行政犯”[9]这类犯罪的特点在于,都以违反一定的经济行政法规为前提,它们原来都没有被认为是犯罪,由于社会的变化,在一些经济行政法规里首先作为被禁止的行为或者作为犯罪加以规定,随后在修订的刑法中予以吸收而规定为犯罪。贩卖毒品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规定的犯罪,属法定犯。在违法性问题的认识上,由于行政法规错综复杂,所以,对法定犯的认识较之自然犯,要困难得多。而且,行政法规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因而法定犯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更增加了对之认知的困难性。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要是以家庭、学校传播给他们的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因而对诸如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等自然犯的危害性质能够有准确的认知,而对诸如贩卖毒品等行政犯的社会危害性质,该年龄阶段的人尚缺乏足够准确的认知。
其次,贩卖毒品罪并不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上看,自然犯较之法定犯要严重得多。因而贩卖毒品罪作为法定犯与刑法第17条2款规定的其他7种自然犯相比,是有一定差别的。虽然这8种犯罪的最高刑都是死刑,但其法定刑的最低刑却有异,贩卖毒品罪的最低刑只是管制,而其他7种犯罪的法定最低刑事3年有期徒刑。而且,司法实践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绝大多数情况是被成年犯罪人利用和教唆的,其人身危险性较小。
三、立法建言:突出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之保障
虽然笔者极力主张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进行特别地限制而不是扩张,但现行刑法第17条2款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除了将贩卖毒品罪“入罪”欠缺合理性外,当下争议的关注点集中于刑法第17条2款所列举的罪名是否失之于狭窄。而失之于狭窄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甚至于理论界的公认,否则,最高司法机关也不会通过司法解释反复强调其“罪行说”的观点了。然而,如前所述,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刑法17条2款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其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成倍的扩大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结果将是不得不诉诸于立法来裁决。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伤害、杀害被绑架人的,其行为如何评价?最高检认为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而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上述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而笔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该行为既不能定性为绑架罪,也不能定性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罪。原因在于:我们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要看其是否符合犯罪的成立条件、符合何罪的构成要件。我国通行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的要件由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组成。[10]在这种“齐和填充”式的理论体系中,行为只有同时齐备这四个方面的要件,才成立犯罪,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要件,犯罪便无存在的余地。按照犯罪构成理论来解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行为的定性问题,因为绑架罪的主体要件要求行为人年满16周岁,因此主体要件是不相符合的,这导致其他要件失去了评价的意义。
或许正因为最高院看到了最高检对该行为定性为绑架罪的明显不妥,才对之作出了修正,指出“应当依照刑法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从而将上述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大大拉近了与刑法第17条2款的距离。而将其定性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其理由主要有: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过程中实施的伤害、杀害行为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与单独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没有本质区别。2.按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单独实施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既参与勒索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行更重,反而不负刑事责任,在逻辑上说不通。3.绑架过程中实施的伤害、杀害行为并不是与绑架罪密不可分的必要要件,不并罚不等于说其伤害、杀害行为没有触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罪名。[11]面对以上理由,力主限制论的笔者也不得不承认,其理由是有相当说服力的。然而,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尤其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笔者仍坚持认为,在没修订刑法之前,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过程中实施的伤害、杀害行为只是绑架罪的一个情节,既然作为主行为的绑架行为不能构成绑架罪,也就不能对作为绑架的情节行为即伤害、杀害行为定罪。而就此可能带来的司法失衡,只能理解为是由于现行立法存在缺陷造成的,应通过完善立法来解决,而且,现阶段司法的失衡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应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罪刑法定原则所提倡的法治理念很难得到贯彻,更毋论深入人心了。
当然,从应然的层面观之,绑架罪作为刑法理论上所谓的自然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其社会危害性是有认知的,而且,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于犯绑架罪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绑架罪的起刑点为10年,从这一点看,其危害比刑法第17条2款所列举的犯罪要大,更为重要的是,行为人在实施绑架犯罪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暴力或危及受害者人身甚至生命安全,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行为并伤害、杀害被害人,而按照现行刑法却无法定罪,不能说不是刑法立法上的缺憾。这也是扩张论者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将其“入罪”的原因。因此,对于绑架罪,笔者是主张将其“入罪”的。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笔者主张通过修订刑法将绑架罪“入罪”,但出发点却是为了限制司法对立法的随意侵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长期以来,中国存在司法解释大量侵入立法领域的情况”[12]。如上所述,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行为定性为绑架罪的情况即属此例。当前,司法解释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要求,即在于防止司法权侵入立法权。即使建议将绑架罪“入罪”,笔者也是采取审慎态度,经过反复考量、价值取舍得出的结论。
关于有的学者建议立法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扩大至对决水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汽车罪,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绑架罪承担刑事责任。[13]笔者认为,这样简单地一概而论,成倍地扩大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是有失严谨的,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权益的极端漠视。比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破坏交通工具,结果致使撞车事件发生,导致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对于该结果,行为人往往持间接故意,在意志态度上,直接故意表现为希望或者积极追求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表现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两者在主观恶性上存在差异,间接故意相对直接故意而言,明显较小,其人身危险性也较小,仅仅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明显有客观归罪之嫌,实不足取。[14]又如劫持航空器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几乎可能实施该罪,中外司法实践也极为罕见,即使将来会有,也多被成年犯罪人利用和教唆,不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区别,而径直将其“入罪”,从而以成年人标准衡量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是很难有多大说服力的。
所以,笔者主张,应严格限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入罪”范围,确保未成年人特殊权益的保障。在确定该年龄段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之范围时,必须严格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讲,该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质足以被他们所认知;从客观方面论之,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如前所述,现行刑法第17条中容纳的贩卖毒品罪是不合理的,而通过修订刑法将绑架罪“入罪”却确有必要。至于其他更大范围的扩张,均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
收稿日期:2006-12-04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
②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已修正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笔者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③罪名说的主张者往往是限制论者,而主张罪行说的往往是扩张论者。
标签:罪刑法定论文; 贩卖毒品罪论文; 法律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制论文; 绑架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