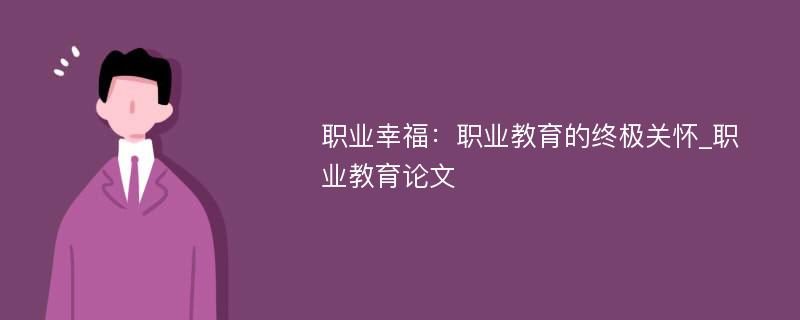
职业幸福感: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幸福感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2)07-0031-06
一、“职业”与“幸福”
(一)什么是“职业”
职业是人类社会追寻幸福生活的劳动形态,在这种劳动形态中,人们需要投入专门的时间且能够因此而获得生活保障。这个定义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职业是人类社会的独有现象。动物世界不存在所谓“职业”,因为动物不懂得追寻幸福生活。(2)职业具有时代性和创造性。追寻幸福生活,人类永无止息。“追寻”二字体现了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发现的过程。因此,在不同时代,职业的劳动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3)职业是人类社会劳动的载体。对于个体而言,当他从事某种劳动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从事某种职业,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从事了人类社会的某种职业劳动。(4)职业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劳动形态。“职业”是与“物质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职业的”一定是能够“获得物质报酬的”,一个人从事职业劳动并为此而投入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其目的在于获得生存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某个人从事某种职业,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从事这样的劳动,而是他不得不为此投入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否则,他的生活无法保障。(5)每个职业都有其“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群体活动的必然产物,是维系某个职业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它规范了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具有约束性,所以每个从业者都渴望“自由”。
有人可能会问,照上述定义,依赖抢劫、杀人、贩毒来谋生的人,他们的职业是强盗、刽子手、毒贩子——难道这些职业也是“追寻幸福生活的劳动形态”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对于“幸福生活”的不同理解来分析。前面我们从人类的社会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就是追寻幸福生活,谁也不愿意过痛苦生活。问题在于,人类的幸福之路总有痛苦阻拦,人类善性总有恶行相伴。如果我们把强盗、刽子手、毒贩子这些职业看作人类社会“追寻幸福生活的劳动形态”的话,那么它们就属于异化的劳动形态。但是,就个体而言,幸福感的体验是“个体性”的,虽然社会认为某些人所追求的所谓“幸福”只有痛苦,但是这些个体的人宁可对抗社会也要追求他们的“幸福”。事实上,在强盗、刽子手、毒贩子看来,他们的劳动毫无疑问也是在“追寻幸福生活”。
(二)“幸福”在哪里
理解“什么是幸福”和“幸福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职业”的定义。
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人人都能回答,但是谁也说不清,因为当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产生了语义混乱。翻开古今中外的书籍,谈论幸福的话语俯拾即是。最近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一部书是《哈佛幸福课》,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开设课程专门谈论“幸福”,吉尔伯特承认“世上根本不存在计算幸福的公式”,因为“幸福是一种很难对自己和他人解释的主观感受,因此,判断一个人宣布自己幸福的说法是否正确,是一件让人特别困扰的事情”。[1]
以前,中国人很少在人性上谈论幸福,如今中国也经过了工业化时代的财富积累过程,像西方社会一样,也水到渠成地开始思考“财富与幸福”问题。因为职业创造财富,所以“财富与幸福”问题便转化为“职业幸福感”问题。近几年,一些官方或民间研究机构根据传媒需要,纷纷发表了不同类型和范畴的幸福指标排行榜,例如“城市幸福指数排行榜”、“职业幸福指数排行榜”、“地方公众幸福指数排行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某个“幸福指数排行榜”公布之后,网上都是一片质疑声,主要是评价指标是否正确、采样是否确有代表性、被调查人当时所处环境和心态如何,等等,这些都会左右评价结果。
幸福在哪里?由于幸福不属于逻辑系统中的理性事件,所以幸福很难通过外在客观事件(行为)来测量。幸福与职业、财富、自由都有关系,但是幸福不在职业里,也不在财富和自由里,这些只是承载幸福的表象,而不是实质。
幸福是个体内心的即时体验,具有即时性、相对性、个体性和社会性。即时性,说明“幸福感”很容易受到当事人心境的影响,一个正在饥饿中痛苦的人突然见到丰盛的食物白白给他,他马上就有幸福感。相对性,说明“幸福感”容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对于一个人的感受不同。个体性,说明“幸福感”是个人体验,同一件事,由于每个人诉求不一样,他们的幸福感也不一样。社会性,说明“幸福感”是受到社会意见影响的,个体幸福感与其德行的社会评价有关;人生活在社会中,没有与社会意见无关的纯粹个人幸福感。
既然幸福具有即时性、相对性、个体性和社会性,是不是表明幸福感不可测量呢?幸福感可以测量,但是就现有测量条件而言,我们只能依靠被测者的即时、诚实的描述来进行。那么我们又如何确保被测者的描述是诚实的呢?这就要求全部测量过程符合“大数法则和概率法则”。比如,要测量某人在某个时间段的“职业幸福感”,就要在这个时间段持续地跟踪他,并且请他即时描述其幸福感;要测量某个城市某职业的“幸福指数”,就要在这个城市跟踪调查大多数该职业从业者的“职业幸福感”。
二、“职业幸福感”与“职业教育”
(一)“职业幸福感”可否通过教育获得
职业是人类在追寻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创造智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累积而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职业通过教育获得”。
幸福与职业有关,但不在职业里,而只是人对于职业生活的情感体验。那么一个人如何获得“职业幸福感”呢?应当说,现代人绝大部分都过着职业生活,人们需要在“职业生活”中寻找幸福,所以“职业幸福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我们看到,许多人并不喜欢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但是或迫于生计压力,或迫于父母期待,或受所学专业限制,或为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等等,他们又不得不继续做此职业,毫无疑问,这些人很难获得“职业幸福感”。进一步说,没有“职业幸福感”的人,大多数是被动工作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人工作很敬业,但是他们不会有工作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一个人没有“职业幸福感”,对个人发展和所从事职业都是损失。历史地看,人们缺乏“职业幸福感”是一个普遍现象,著名的例子有爱因斯坦和卡夫卡,这两个人赖以生存的职业都是公务员,但是他们并不喜欢那样的工作,我们看看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就可以知道他有多痛苦。再比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父亲原本让儿子从事律师职业,但是痛苦的巴尔扎克宁可忍饥挨饿也要从事他喜爱的作家职业;齐白石原来的职业是木匠,但是他的“职业幸福感”不在此,他把想象力和创造性才能用在了绘画上。
那么,职业幸福感能否通过教育获得?如果可以通过教育获得,为什么有不少人放弃了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业,却在其他职业上取得了成功?比如,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在大学所学专业是英语,却在电子商务领域大获成功;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并且从事了20余年的车辆研究工作,却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如果不可以通过教育获得,那么本文谈论“职业幸福感”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就毫无意义。
解决上述命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教育“教”的是什么?通常意义上,人们心目中的所谓“教”实际上是“传授知识”,即训练学生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人才,这时候,教育其实已经被异化为福柯所说的“规训”①了。如果我们在“规训”的意义上谈论幸福感教育,上述命题就不成立,因为作为个体内心“体验”(自由)的幸福感被抽象为“社会知识”强加给了学生。体验是独特的,不可复制,否则,幸福就会转化为痛苦。简言之,“规训”之下无幸福。
在教育的原初或本质意义上,教育的所谓“教”实质上是引导、启迪,按照《新约圣经》的说法,基督救赎并不强加于人,而是通过神子的榜样(宁可受辱、被钉十字架,也不显神迹惩罚罪人)和话语引导人自省。我们可以说,教育担当了救赎的使命,救赎需要引导人回归他的内心世界,发现他那隐藏的独特灵性,并和灵性对话:“你知道你是谁了吗?”当救赎者听到了这个独特灵性回答说“是的,我认识了我自己”之后,教育就成功了。如果恢复教育的原初意义,“职业幸福感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这个命题就是成立的。教育者引导和启迪学生找到他自己的天赋潜能(兴趣点),以及这种潜能与未来职业的契合点,这个过程没有呵斥、训诫,也没有强加的爱,试想,在这种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如何不幸福呢?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教育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的教育状态,除了神子,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实施这种教育的教师。
哈佛大学“幸福教授”吉尔伯特引用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梭伦的话说,一个人只有充分发挥了他自己的潜能,他才是幸福的。不过,人活着终究是痛苦的,因为在人的有限里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潜能。但是,人类不应当放弃“恢复教育原义”的努力,我们应当从学生的幸福感来反推和调整教育方式,进而引导学生自己判断其最大潜能,否则,人类的持久幸福就只能永远在天上。
有人又会问,我知道了我能做什么,但是没有那种职业怎么办?其实,人类的脚步确实是朝着“职业”与“潜能”相契合的方向不断趋近的。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财富的革命》一书中预言,未来将产生巨大的“产消合一经济”(Prosumer Economy),这种经济将创造无数个符合个人兴趣、发挥个人潜能的职业,也就是说,你愿意做什么(当然是无伤害的)就能做什么,因为“产消合一者”是指“那些为了自己使用或者自我满足而不是为了销售或者交换而创造产品、服务或者经验的人”。[2]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获得“职业幸福感”并非遥不可及。
(二)“职业教育”的误区
现代人在物质上比过去丰富多了,但是幸福感好像并没有增加,也许因为人们对于幸福感体验的需求增加了,故而显得愈发缺乏幸福感。无论怎样,现代人仍然没有找到幸福感,或者说,事实证明那些把物质富足和随意消费作为幸福的人,他们找错了方向。幸福感不在外面,而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现代社会的“成功主义”理念误导人们在外面去寻找,于是人就变成了制造他人眼中“成功”的机器,“人们被迫去百折不挠地争取成功,任何挫折对其自我估价都是一个严重威胁,失落感、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就是其结果”。[3]无疑,失去了自我的人永远不会有完美的幸福体验,一个人的职业幸福感只有在职业与他的自我潜能构成为一的时候才会产生。
“职业教育”能否给学生职业幸福感?职业教育是直接满足职业市场对于能工巧匠需求的教育,如果某职业院校的学生就业率很高,就可以证明这所学校的职业教育质量很高。这种判断使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炽烈的“市场情结”,职业教育活动的核心就是研究如何把学生销售出去,无论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还是“订单式培养”、“生产性实践课”,其目的都是让学生在毕业时找到好工作,甚至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事业成功”,成为学校教育的光荣。我们说,职业教育的上述种种行为都没有错,问题是,当我们醉心于“市场需求”的时候,有没有问问“学生需求”在哪里?我相信,如果当下中国职业教育仅仅停留在这种外在的技术性追求,作为教育成果的学生在未来的职场上将很难获得他们的职业幸福感体验。换言之,当我们的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只重视社会市场需求而忽视学生职业志趣,或者只强调鼓励人的外在职业成功和物质满足而无视人的内在职业潜能和幸福体验的时候,其实已经走入了职业教育的误区。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分析说:“具有市场心向的人,他自己的力量则成了异化于他的商品。他的力量不但已不属于他,而且还要千万百计掩饰这一点,因为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在使用这些力量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而是如何在出卖他们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他的力量及其所创造的,变成了外在的、与他自身相脱离的东西,变成了供他人判断和使用的东西。”[3]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仅仅以市场的视野培养“具有市场心向的人”,就不是完全的职业教育,因为它忽视了就业者的职业幸福感;也许在短期内看,职业教育的就业效果还不错,但是从长期来看,其“教育效益”很低。
事实上,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不高。《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2010届中国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毕业半年后)为88.1%,但是50%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低于岗位要求,44%的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即离职或者失业。笔者曾经对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的原因做过调查分析②,发现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和学生就业选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现象”,有的专业一个班级60人,毕业两年后仅有1人到2人从事本专业。据此,我们可以坦诚地说,我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忽视了学生的职业志趣。在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下,考分是唯一评价指标,许多学生的天赋潜能被抑制了,进入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就是潜能被抑制者。在长期被否定的氛围中,职业院校的学生也无法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了;教师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学生的确“很差”,认为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主见。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全然取代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当然,我们承认,学生的天赋潜能被抑制是应试教育种植了许多年的恶果,指望职业院校这个端口全然解决并不现实,但是若不做解决的努力岂不更糟?因此,还学生专业学习自主权,是各个职业院校的重要功课。现在,一些职业院校采取专业群招生、部分学分制等办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远远不够。
三、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终极关怀
(一)职业教育何处来
职业教育是劳力者争取公平教育权的产物。
最初,教育是与自然生活融合在一起的,随着人类物质财富增多,教育被作为一种精神财富独立出来了。从此,教育就被握有权力的贵族阶级(“劳心者”)所独占,他们称之为“闲暇事业”或“自由教育”,而那些整日用双手忙碌的奴隶阶级(“劳力者”)则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了。贵族不承认奴隶有“精神”存在,认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因此,凡是劳力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原理”都不是教育内容,只有哲学、文法、修辞、礼仪、数学等“精神产品”才能被作为教育内容。但是,劳力者争取公平教育权的斗争从未停止,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斗争也随之进入强势期;十七世纪,职业教育从思想孕育进入了物质形态,进而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教育制度所接纳,因为工厂里的机器需要大量受过专门教育的劳力者。但是,职业教育并未争得完全公平的教育权,作为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仍然被看做是低层次的。这里所谓“低层次”是和普通教育相比较而言的,普通教育脱胎于原来的“自由教育”,仍然没有“贵族性”。人类是分等级存在的,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他们也就把“自由教育”据为己有了,虽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被认可了,但是地位却不高。
(二)职业教育的“确定性寻求”
职业教育的地位之所以不高,就在于人们认为它是指向劳力者及其劳动技能的。通常,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劳动技能有多少“精神含量”?然而,既然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职业也无高低贵贱之分,那么职业教育又为何会缺少“精神含量”呢?在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看来,教育的精神含量体现在传授理性、真理、善、美等等“内在性”话题中,而“职业教育”只涉及动手、操作、技术、行动等等“外在性”话题,所以它是缺乏精神含量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教育的哲学基础——“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才得实现”[4]被打破了,凭着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工具,人类可以在行动中把握“行动的确定性”。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家通过他们的大量论著为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追求事实,强调功用,诉诸特殊和具体;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尊重崇高,也尊重平庸。在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看来,所有的劳动都可能是有生命意义的,关键是我们是否发现了这种意义,即证明这种劳动的效用。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否有意义,关键是他自己的体验,在根本上说,如果他的天赋才能(通过浓烈的兴趣和悟性体现出来)在这个职业上,他就不会使该职业平淡无奇,而是在职业的劳动中体现其生命意义,成为职业的“英雄”或“大师”。
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确定性知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在行动、实践、操作和工作过程当中,职业教育同样可以把握“确定性知识”。职业教育也是人类认知的“确定性寻求”——和劳作、探究、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也有了“精神”意义;职业教育不是训练执行命令的刽子手,而是引导人在职业中找到生命的趣味——自由、尊严和仁爱。事实上,“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不是要分作两家,教育只有一个,那就是“善的构成”,教育的目的是在不断探索前进的人类世界中去构成“善的境界”。
(三)职业教育何处去:创造职业生活的幸福感
上面之所以大篇幅谈论“职业教育何处来”和“确定性寻求”问题,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职业教育并不是单纯给劳力者提供“技能训练”的教育,职业教育有其精神意义,它能够而且应当给从业者提供“职业幸福感”。
职业教育是面向职业的教育,但不是面向某一些职业,而是面向所有职业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指出:“职业是唯一能使一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找出一个人适宜做的事业并且获得实行的机会,这是幸福的关键。天下最可悲的事,莫过于一个人不能发现一生的真正事业,或未能发现他已随波逐流或为环境所迫陷入了不合志趣的职业。”[5]就职业的理想状态而言,“每个人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是勉强的,而是明智的,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和自己的能力倾向相投的。”[5]在杜威看来,职业是人追寻幸福生活的表现形态,一个人求得“有尊严的职业”和“工作过程的享受”,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职业。这一点似乎过于理想化,因为使人“各得其所”实在太难了。杜威也承认,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现在的社会距离这样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完全实现这种纯粹的职业状态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理想的追求,在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求知的实践环境”,使学生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天赋才能和兴趣特长得以更好地利用,进而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
职业教育属于人的教育,而非工具的训练,因此,“职业幸福感”应当是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没有专门指向哪些人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归宿就是人类的幸福生活本身,职业幸福感就是生活幸福感,不能给人生活幸福感的“职业教育”一定是失败的教育。职业的脸上贴着生活,工作的过程中住着生活,教学的活动里写着生活,生活对于职业教育效用的检验无处不在。
注释:
①福柯笔下的“规训”是古典时期的酷刑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是人性的张扬,而是一种控制和塑造人性的新型权力机制。
②详见徐平利.专业与就业“错位现象”探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