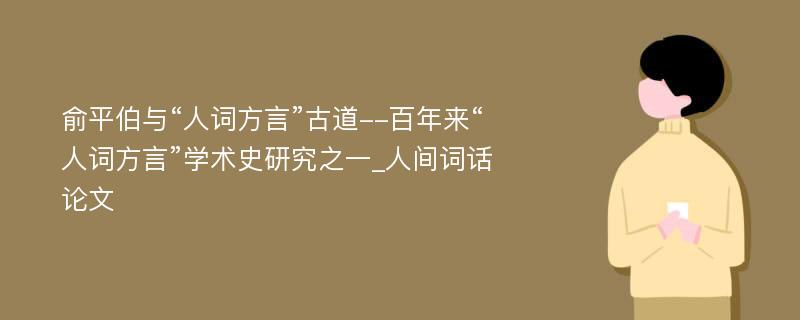
俞平伯与《人间词话》的经典之路——《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人间论文,之路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2-0132-07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20世纪的学术经典之一,被誉为中西文学理论最初的交汇点。因其随笔札论的著述体例而成为古典文学批评的终点;又因其理论自成体系,内蕴着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与交流,而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这些高度评价,验之于《人间词话》,洵非虚誉。但如果追寻其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人间词话》的经典之路其实并不平坦,不仅中间有曲折,而且有空白。在1908年《人间词话》开始发表之后的近20年间,居然游离在学术视野之外。一直到年近五旬的王国维已巍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之时,他这本沉寂已久的文字,才被洗去尘埃,重现人世,并由此迅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这种由沉寂到热点的转变,俞平伯厥功甚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由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看到的
王国维从1908年夏秋之际撰写《人间词话》126则,到1908-1909年之交因《国粹学报》之邀约刊发其中的64则,再到1915年王国维在手稿和《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基础上斟酌删订为31则,再度刊发于《盛京时报》,王国维以一种浓缩文本的方式不断做着扩大《人间词话》学术影响的努力。但事实证明反映是冷漠的,王国维一直没有看到《人间词话》被关注的情形,不用说专题的研究,就是重要的引论,也没有出现。自1926年俞平伯将《国粹学报》的64则标点并撰序交由北京朴社出版后,《人间词话》才开始以“著作”的方式而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俞平伯的,《重印人间词话序》(序作于1926年2月4日),也是最早对《人间词话》进行学术定位的文字,不仅提出了境界说的核心地位,而且对其丰厚的理论意蕴表示了关注。这种对《人间词话》理论核心的揭橥和对其总体水平的评判,也确实可以用“惬心贵当”来回评俞平伯自身。
俞平伯的序言有四点应特别注意。
其一,认为《人间词话》是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的有机结合,所以立论“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俞平伯在序言开头即云: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1]
俞平伯的这一评论虽然来自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一则,但也确实符合王国维撰述《人间词话》的实际。盖此前王国维不仅观览百家之词,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编撰《词录》,而且自己也创作了《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合共100多首词,对于创作实践确实是“局中人”;而王国维此前对中西哲学、文学理论的涵养,也使他具备了颇为广阔的理论视野,故能担当发表“公论”的“局外人”角色。验之于王国维之前诸家词话,也果然多以“局中人”眼光来评骘词人词作,体会固然不乏敏锐细微,而于统观衢路,则不免略有所欠。所以俞平伯揭橥《人间词话》中的王国维兼有“局中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堪称别具只眼。俞平伯说:“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者寥寥。此重刊《人间词话》之意义也。”这当是俞平伯标点单行《人间词话》的主要原因。
其二,点明“境界说”乃《人间词话》之理论核心,并以此裁断词史。《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开头九则,皆关乎境界说的阐释,此就词话序列已见端倪。然就《人间词话》学术史而言,最早拈出此点者当为俞平伯。序云:“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有‘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俞平伯序文简洁,故没有全面深入展开他的这一看法。而且“隔与不隔”是否为“词境”之区别,在此后的学术史曾引起颇为广泛的争论。但试推衍其论,俞平伯持王国维以境界说批评词史发展之说,当无疑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不仅揭出此点以为《人间词话》之核心,而且称赞其理论及相关评论“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对于王国维的这一创见表达了赞赏。此与稍后七八年展开的对王国维词学是非功过的讨论,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其三,认为《人间词话》非一单纯论词之著,而是包孕着巨大的理论拓展空间。俞平伯序言开笔即是“作文艺批评”五字,又言及“此书论诗人之素养”,复言“自来诗话虽多”云云,似皆非局限于词体一端以论《人间词话》,而是立足于大的“诗学”范畴来确立其诗学地位。俞平伯认为《人间词话》“虽只薄薄的三十页”,然“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是在丰厚学养基础上提炼而成,并借词体一端以发表己说,“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并说自己“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凡此所论皆涉及到《人间词话》理论本体与拓展空间的问题。俞平伯的这一说法,不仅准确,而且富有远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盛的对《人间词话》的研究,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艺学、美学等角度来审视其价值和地位。俞平伯未加引申固然是个遗憾,但其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丰富意蕴,也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四,对“词话”著述方式的认同。对于《人间词话》以短札的方式论词评词,后人颇有微辞。或以其标举理论,但文字精干,未加展衍,令人难以准确把握;或以其评骘诸家,言短意长,不易明察其衡鉴尺度;或以其论哲学、论小说、论戏曲、考证史地文字等,皆具论文之形态,独于论词之著,承传“话”体,遂使著述形态过于传统,缺乏体系性。此种种议论,皆不为无见。①盖20世纪初,新的学科意识和治史观念已渐由东瀛而传入我国,文学研究方法和著述体例因之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人间词话》中,这种新的气象确乎较为淡薄,后之学者引为遗憾,并非过甚其词。然而,俞平伯却对“话”体文学批评的方式独致青眼。他一方面大力肯定《人间词话》极具拓展的理论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复表示“话”体著述,贵在可玩味,而不在供分析。因此他虽然认为《人间词话》的端绪众多,若引发申论,可成庞大之著述,但“其耐人寻味之力或顿减耳”。换言之,《人间词话》价值之一端正在其具供人玩味的艺术魅力,若引申发挥,则魅力顿减。为此俞平伯特地就“话”体文学批评著述的特点和价值而阐述自己的理由说:
明珠翡翠,俯拾即是,莫非瑰宝,装成七宝楼台,反添蛇足矣。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不因世间曾有masterpieces而遂销声匿迹也。[1]
俞平伯说自己也曾有“引申其义”的想法,终因担心“佛头著着”而作罢。俞平伯的这一观点,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正体现了他对王国维在形式和学理上“以旧瓶装新酒”这一特色的认识。因为是“新酒”,故具时代之价值;因为是“旧瓶”,故具传统之韵味。这种中西荟萃,在俞平伯的心目中,正有着异常独特之韵味,故三复致意,心有戚戚。
二、俞平伯对《人间词话》的后续评论
俞平伯在标点《人间词话》七八年后,撰写《读词偶得》(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对《人间词话》的借鉴和评论显得更为冷静和理性。《读词偶得》借用张惠言、谭献论词之语最多,往往引以为裁断之依据;引述《人间词话》的次数则不多,而且颇为客观。如在解释李璟《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时开端即云:“《人间词话》说首两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王氏此言极有理解(虽其抑扬或有过当)。兹既已征引,便不必词费。荷衣零落,秋水空明,静安先生独标境界之说,故深有所会也。”又说:“这两句(笔者按:指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千古艳称,究竟怎样好法,颇有问题。王静安就有点不很了解的神气,但说它不如起首两句呢,那文章也有点近乎翻案。”对勘这前后两节文字,可以看出,俞平伯既认同王国维的独标境界、深有所会,同时也认为王国维的相关评论也存在故意翻案的痕迹,则王国维学术之公心在俞平伯的心中已略微有些倾斜。
俞平伯对于王国维以摘词人原句回评词人本身的做法,似乎是认同的。《读词偶得》解释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时曾引用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形容温庭筠词风,以“弦上黄莺语”形容韦庄词风等,乃评词之一法,并进而“效其语而补之”云:“恰似一江春水流,后主语也,其词品似之。”俞平伯对李煜词的评价总体较高,而对于王国维对于李煜的评价也深以为是。又如,《读词偶得》在解释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时曾引《人间词话》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等等。俞平伯在引述后云:“固知古今虽远,赏契非遥,文章天下之工,岂不然欤!静安极崇后主,有极精至语。”看来王国维对于李煜的仰慕,在俞平伯那里得到了延续。
俞平伯对于《人间词话》的评判,从总体上来说,并非以阐释其精义为目的,故能引以为佐证者则引述之,与自我观点未尽相合者则辨析之。俞平伯在《读词偶记》所附录的《词选·凡例》中,于第六条中即明言:“迄于清真,非主北宋也,清真虽佳,宁观止耶!偶然而已。”如果把这一条与《人间词话》之推崇五代北宋相对照的话,几乎带有对立的意味了。俞平伯在追溯自己的词学渊源时,似乎更倾向于他的老师黄季刚。1948年,他在《清真词释·序》中说自己在两宋词人中“独选美成的作释”,“‘不妨说受之于师’”。这个“受之于师”的背景其实是指民国五年六年间黄季刚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词辨选”课程。据俞平伯序中所说,黄季刚对于周济《词辨》的选录之精极为叹赏,因从中选录22首为诸生解析,俞平伯便是课堂受教的学生之一。黄季刚讲授的清真词只《兰陵王》、《六丑》、《浪淘沙慢》三首,数量不多,但黄季刚将词中清真与诗中杜甫并举,给俞平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俞平伯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黄季刚的观点的,他在释清真《凤来朝》(逗晓看娇面)一词时即云:“自诗家有杜陵,而唐以后诗皆不得不与古人为敌国矣;词家有清真,而北宋以后词皆不得不与古人为敌国矣。虽曰气运使之然,若夫二子者岂非英霸之奇才乎!”[2](P101-102)在黄季刚开列的参考书目中,“源流”一项列张炎《词源》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两种;“选本”一项列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等七种;“专集”一项列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四家词集。这些源流、选本和专集中透露出了浓烈的常州词派的气息。如果把黄季刚开列的书目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关论说对勘的话,其矛盾甚至对立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俞平伯既然盛称黄季刚此书目“的当难改”,则心香独奉,也是很自然的。无论是《读词偶得》,还是《清真词释》,其多引周济、谭献所论(谭献有《谭评〈词辨〉》),至此也可略见分明了。俞平伯对于王国维后来写的《清真先生遗事》倒是极为推崇,赞其“立说精确”,[2](P84)而《清真先生遗事》对清真本人的评价,与《人间词话》的相关论说有着一定的矛盾。俞平伯在释清真《凤来朝》(逗晓看娇面)一词时曾有简要说明:“王静安《人间词话》尚以为美成劣于欧、秦,而于《遗事》则曰‘词中老杜断非先生不可’,盖亦自悔其少作矣。(《词话》在先,《遗事》在后,见赵斐云先生撰王年谱)知人论世,谈何容易!”[2](P103)其《唐宋词选释·前言》亦云:“周邦彦词,令、慢兼工,声调方面更有大大的进展。虽后人评他的此‘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固有道着处,亦未必尽然。”抑扬之间,俱见微意。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俞平伯撰写《唐宋词选释》(原名《唐宋词选》),其“前言”梳理词史,对于《人间词话》的态度似乎仍然温和而理性,赞弹兼有,很少有意气的痕迹。如前言有云:“王国维关于冯延巳、李后主词的评述,或不符合史实,或估价奇高;但他认为南唐词在‘花间’范围之外,堂庑特大,李后主的词,温、韦无此气象,这些说法是对的。”[3](P11)至于具体是哪里不符合史实,哪里估价过高,俞平伯将这具体的情形写在注释中了。其云:“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上:‘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袈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此皆推许太过,拟于不伦。又如:‘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花间》结集时代较早,故不收南唐的词,这里的理由也是错的。至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评价也还恰当。”俞平伯的辨析现在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如果没有俞平伯,《人间词话》很可能仍将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沉睡在《国粹学报》中,所以俞平伯之于《人间词话》的经典历程,功莫大矣。从20年代后期开始的有关《人间词话》的研究,无一例外是针对著作形式的《人间词话》而言的,即此我们可以估量出俞平伯的学术贡献了。如1927年2月刊发在日本《支那学》四卷之二上的吉川幸次郎撰写的《人间词话》书评,便特别标明其立说版本为1926年北京朴社出版之俞平伯标点本。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刊发赵万里辑录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在文末“编者识”中特地说明:“《人间词话》刊载于《国粹学报》,未全。朴社尝录之,发行单本。”则《小说月报》刊发《人间词话》之未刊部分,也可视为是对俞平伯标点本的补充而已。而俞平伯的《重印人间词话序》首次对《人间词话》的学术内涵及学术地位作了重要评估,尤值得重视。事实上此后的《人间词话》学术史或引申端绪或裁断是非,也确实是大体按照俞平伯的评估方向前进的。1933年北京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编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沈启无在《编者小引》结尾说:“茶衲至再说过,并非专家,免遗后悔,慎重为是。苟有问我者,请进之吾友。吾友为谁?俞平伯、顾羡季、郑百因是也。”语虽涉谐谑,但俞平伯在《人间词话》学术史中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地位,倒是确凿无疑的。
三、关于“国维记”的辨疑
在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最末一则之后,另有一列文字:“光绪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宣武城南寓庐国维记”。从落款的语气来看,似为王国维亲笔。然俞平伯在序中既曰“重刊”,则原刊自然是重刊的文本来源。而原刊《国粹学报》的时间是1908-1909年之交,乃是开卷可见的事实,其文末也并无此列文字。何以在1909年初即发表完毕,而“脱稿”却要署上“光绪庚戌”?若重刊本经王国维过目,何以忽略原刊时间?若原刊本未经王国维审读,则结尾的这一列“国维记”从何而来?若王国维误记原刊时间,俞平伯是标点并撰序的人,自当需要细读原刊文本,也自然能明辨原刊时间,何以将“误记”照录?如此种种疑问,确实令人费解。
这一赘笔所带来的后果是:此后诸家论述《人间词话》,因为多未翻检《国粹学报》原刊,以致纷纷将《人间词话》的脱稿发表年份定于光绪庚戌年。如出版于1928年的罗振玉主编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在第四集中收录的二卷本《人间词话》,即在卷上之尾署此一列“国维记”文,但易“光绪”为“宣统”。1936年赵万里等编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录和题款的情况一如罗振玉本。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徐调孚校注的《校注人间词话》(三卷本),在卷上结尾即大体照录朴社本的这一列文字,但与罗振玉、赵万里本相似,易“光绪”为“宣统”,并删去了“国维记”三字,而徐调孚校注本又误“宣”为“定”字,其易、删、误的原因未作说明。1944年由出版界月刊社出版的徐泽人编辑的《人间词话、人间词合刊》,在《人间词话》(一卷本)第64则后则是全文照录朴社本文字。而解放后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徐调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订之通行本《人间词话》(与况周颐《蕙风词话》合刊),亦与徐调孚原校注本无异。至于各家论说将《人间词话》的原刊时间定于“宣统庚戌”或“光绪庚戌”者,更是不一而足,其实大体都是沿袭了朴社本的这一说法。
但朴社本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在清代历史纪年中,光绪纪年至1908年即已结束,而1908年从干支纪年来说是“戊申年”。整个光绪35年间,并无任何一年是“庚戌”,何以突然出现一个匪夷所思的“光绪庚戌”?靳德峻《人间词话笺证》、蒲菁《人间词话补笺》、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均删去此列文字,或许正是发现了这一帝王纪元的错误。而罗振玉、赵万里、徐调孚诸本《人间词话》皆易“光绪庚戌”为“宣统庚戌”,盖宣统二年(1910)恰是庚戌年,故随笔修改。则后人误将《人间词话》的脱稿之年定于1910年,固非王国维自定——实际上王国维署名的时间是子虚乌有的。但将王国维原本虚无的“光绪庚戌”改成实际存在的“宣统庚戌”,最早当是罗振玉的手笔。这个谬传很久的问题,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朴社本这多出的一笔,从落款的语气及现在的材料来看,似乎出于王国维原意或手笔的可能居多。因为王国维大体完成于1908年春夏之时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在诸家词辑的跋文中,除了《南唐二主词》的落款是“宣统改元春三月海宁王国维记”外,其他19家词集跋文均署“光绪戊申季夏海宁王国维记”。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25种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中,王国维在王炎《双溪文集》、杜安世《寿域词》等书的跋文中即落款“国维记”。看来这是王国维比较常规的行文落款方式。而王国维在朴社本出版之前又确实参与了这一单行本的校订工作。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泽主编之《王国维全集》书信卷,收录多封与朴社本有关的书信,当可作一旁证。大约在1925年7、8月间,与俞平伯同为朴社成员的陈乃乾致信王国维,提及《人间词话》的重印问题。1925年8月29日,王国维在复陈乃乾的信中,对于《人间词话》的印象已然淡漠,除了记得发表在《国粹学报》之外,对于与主编邓实的“如何约束”已忘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还说:“……(《人间词话》)此书弟亦无底稿,不知其中所言如何,请将原本寄来一阅,或者有所删定,再行付印,如何?”1925年9月16日,王国维收到陈乃乾所寄《人间词话》一册,两日后回书曰:“前日接手书,并《人间词话》一册,敬悉一切。《词话》有讹字,已改正,兹行寄上,请督入。但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今觅得手稿,因加标点印行云云,为要。”[4](P422)这里所谓“原本”、“手稿”,当是《国粹学报》的过录本。王国维初拟删定,但在接到陈乃乾寄呈原本之过录本后,实际上只是改正少量讹字而已。因为原拟的对《人间词话》的删定没有实施,而现今自己的词学观念可能已有较大的变化,故对这个即将重印但其实与原刊并无区别的本子及其中言论,王国维要求发行时注明“十五年前”所作,乃存其旧说原貌,以明其学术嬗变之轨迹耳。而1925年的“十五年前”正是1910年,即宣统庚戌年,罗振玉、赵万里、徐调孚等易“光绪庚戌”为“宣统庚戌”的理由大概出于此了。
如果过录本已标明原刊发表年份期数,则这个“光绪庚戌”年要么是王国维错误推算所致,要么是俞平伯在由民国纪元到清代帝王纪元转换过程中发生了差错,要么是王国维故意为之。如果陈乃乾的过录本只录文字而未著年份,由此引起的发表年份差错就与王国维无关,但“重刊”云云便也立脚未稳了。从王国维在信中的特别告诫来看,朴社本以“国维记”的名义书写的一列,似乎也有可能是俞平伯在接受了陈乃乾转告王国维之语后模仿王国维语气自行加上的。若是王国维亲笔添加上去,谅不致糊涂若是,造出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年份。检诸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王国维所书若干种词曲专书跋文,其注明“宣统庚戌”年份的凡六见,[5](P313-338)这充分说明“宣统庚戌”才是王国维的常设语境。朴社本易“宣统”为“光绪”是否含有故意模糊写作年代的用心?我们也只能猜想了。联想王国维在晚年对于自己早年治西方哲学、中国文学的这一段经历的“不乐道”,②则一方面悔其少作,一方面又碍于情面。两难之中,或出此“下策”?总之,若非误记,便属故意。惜不能起王国维、陈乃乾、俞平伯以问。
四、陈乃乾及其朴社与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之关系
因为俞平伯的标点本《人间词话》是最早由朴社刊行的,故于此略微交代朴社之缘起。朴社于1923年1月6日成立于上海,由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发起,当时约集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等10人组成,成员每人月存10银圆,本利相生,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开办书店并出版书籍,以免枉受书局盘剥,此即为朴社成立之宗旨。朴社之名乃周予同所起,因其聆听钱玄同讲授清代朴学而深为敬服,故以“朴”名社。朴社成立当年,又有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规模日甚,影响日大。但上海朴社不久即解体,次年在北京重新组成,由顾颉刚任总干事。1925年10月15日,在北京景山东街17号租房,开办景山书社,后来在文史研究界掀起巨大波澜的《古史辨》最初即是在朴社出版的。《人间词话》只是其出版书籍之一种耳。
明乎朴社的性质及其人员组成情况,我们对于何以由朴社来重印《人间词话》也当多了一份体认。北京朴社虽成立于1925年10月,但在同年8、9月间,陈乃乾即致信王国维谈及《人间词话》的重印问题,则其出版计划是先期就已经开始了。由陈乃乾来联系王国维,盖因两人皆为浙江海宁人,有地缘上的亲切感,且已认识交往多年,早在1923年6月间,陈乃乾即曾致信王国维商谈《曲录》的再版问题;[4](P352、353)而标点、撰序工作由俞平伯来完成,或与俞平伯因受家族影响特别是父亲俞陛云之影响,具备较好的诗词修养有关,加上俞平伯本为朴社中人。③在促成朴社本《人间词话》出版过程中,陈乃乾堪称功臣之一。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在当时的《人间词话》文本中留下痕迹,但随着1926年8月开明书店的成立,朴社与未名社等先后为开明书店受盘,所以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虽然在内容上将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其实仍可视为是对朴社本《人间词话》的修订再版而已,这不仅因为此书仍以俞平伯的《重印人间词话序》冠诸弁端,而且因为两家出版机构源流相承,本属一家。④1947年开明书店再版《校注人间词话》时,又将陈乃乾从王国维旧藏《六一词》、《片玉词》、《词辨》等辑出的眉间批语凡七则附于徐调孚原来补遗之后,陈乃乾的名字至此与《人间词话》文本才真正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而追溯《人间词话》的经典之路,陈乃乾的作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五、余论
王国维晚年对于再版自己早年的文学研究著作,似乎并不热心。1923年6月间陈乃乾致信王国维,希望再版其《曲录》,王国维在回信中即曾婉拒过。[4](P352、353)对于再版《人间词话》,王国维的态度也同样并不积极。先是在致陈乃乾的信中说“不必由弟出名”,校点一过后又要求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4](P420、422)但俞平伯标点本《人间词话》的通行,还是迅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眼光。如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在民国十五年(1926)夏季即已初步完成,⑤距离俞平伯标点本的出版仅四、五个月而已。1928年,赵万里将《人间词话》手稿未刊部分择录44则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有关《人间词话》的增补工作由此拉开序幕。此后徐调孚、陈乃乾、王幼安、刘炬、滕咸惠、佛雏等续有扩充,关于王国维的词学文献遂逐渐突破初刊《人间词话》64则的限制,而向两卷本、三卷本、重编本、增广本方向扩展。而笺注类著作在靳德峻之后,也有蒲菁的“补笺”、许文雨的“讲疏”、徐调孚的“校注”、滕咸惠的“新注”接连问世。这些文献征录和校订笺释为同时或此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从30年代前期开始,朱光潜、许文雨、任访秋、唐圭璋、顾随等纷纷展开对《人间词话》理论范畴和体系的研究,《人间词话》也由此成为众所关注的对象,并在不断的阐释中走向经典。而经典旅程的起点,就实际影响来看,倒不是初刊的《国粹学报》,而是俞平伯标点并序的朴社本《人间词话》。此非余之私言,乃学术史在在可证之公言也。
注释:
①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即云:“王先生批评为散漫的,其形式仍用过去的诗话体。就好的方面说,很耐人寻味,以其言短而意深也;就坏的方面说,有时太抽象,不善读者易于误会其意,或竟不了解其意之所在。”转引自何志韶编《人间词话研究汇编》,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
②赵万里在《人间词话来刊稿及其他》的后记中即云:“其(按,指王国维)壮年所治诸学,稍后辄弃之不乐道。故其绪论,舍《静安文集》、《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并世人欲窥其一鳞一爪,亦无由得焉。”《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
③王国维在致陈乃乾的信中虽同意出版,但明确说重印一事“不必由弟出名”。参见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0页。
④徐调孚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之《校注人间词话·跋》即云:“……今朴社诸书改归开明重印,爰于斯书,易以全集两卷本未据,而于文字则发原载诸志相对校,冀得其真,俞序仍冠卷首。”《校注人间词话》,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版,第89页。
⑤靳德峻(署名“极苍”)作于民国十九年(1930)之《人间词话笺证·再版赘语》云:“笺证是书,在民十五年夏季,乃为一己诵读之便,非欲出而问世也。搁置年余,文化学社邵先生,以是书颇便后学,遂取而付印。”北京:文化学社193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