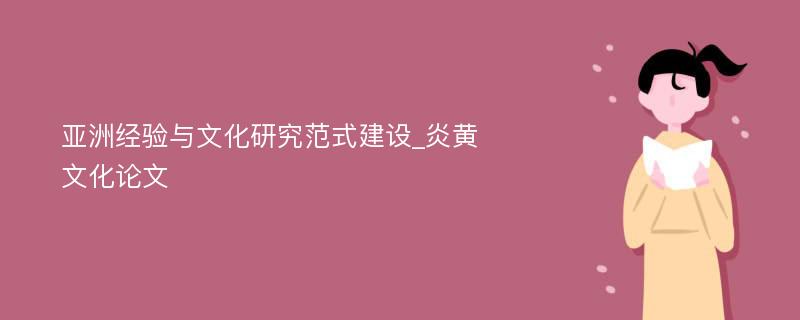
文化研究的亚洲经验与范式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亚洲论文,经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10-0142-08
一、如何瘦身的巨无霸?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个渗透各学科的“巨无霸”。由于抵制学科界线,几乎任何学科都可以挂上文化研究的快车。加上文化研究的方向与课题常常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当今世界新问题层出不穷,新课题发展不断,导致文化研究发展的庞大与不可节制。虽然文化研究如今依然风头强劲,其研究本身臃肿不堪已是事实,急于瘦身。
国际知名的文化研究期刊《连续统一:传媒与文化研究》于2011年出版特刊,专门讨论由于文化研究的庞杂而引起的“复杂性”(complexity)。洪美恩(Ien Ang)作了名为“导航复杂性: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智力”的序言,认为成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其扩张已超出任何人的掌握和想象,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亟待梳理:
21世纪复杂得可怕的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经验的重要部分。如何为我们备受挑战的时间导航定位?作为文化研究者,我们面临这一任务能扮演什么角色?过去几十年的人文社科学术已经拥抱复杂性,将之理论化和目的化,使之成为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洪美恩看来,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过去三十多年来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的批评理论:从结构主义到文化主义,从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反本质,反简约到后殖民主义,几乎所有批评理论都“拥抱”复杂性。文化被定义为“是永远流动的,多元的,不可能简约到一个单一的起点”。德里达认为“意义要由语境决定”,而“语境是不确定的”。文化研究对复杂性,用洪美恩的话来说,是“崇拜”。同时洪美恩还抱怨这些复杂性也常体现在日常的文化研究教学和研究中。以学本会议为例,一些会议文章“常常使问题更复杂而不是更清晰”。因此洪美恩提出了她的新观点,那就是“如果真正跟现实世界联系去处理复杂的现实,文化研究必须走出解构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文化智力”。世界复杂问题的可持续要求承认复杂性,因为简单的结论是不能持久的。同时文化智力承认对付已呈瘫痪状的复杂性需要单纯化。发展单纯化不等于简单化:“一句话,如何简化而不简单化?”①
寻找亚洲经验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范式有助于梳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简化文化研究,意义非比寻常。②在复杂的文化研究世界格局中关注亚洲的独特经验与研究范式,不仅可以为文化研究“瘦身”,同时探索亚洲文化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可能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开辟新的研究前景与研究思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意义与陷阱同在。建立亚洲文化研究的多元范式,会遇到诸多理论挑战。如何梳理亚洲身份认同的问题?如何定义亚洲经验?为什么要寻找亚洲文化研究?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在汉语和英语的文化研究学术界是否有共识?本文仅就亚洲经验与亚洲文化研究范式建构为文化研究“瘦身”的意义进行讨论,同时也探讨亚洲文化研究这一领域面临的身份认同,他者与意识形态的问题。
二、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的意义
“亚洲经验”(Asian Experiences)一词最早来自经济领域,主要指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以及后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在西方国家,“亚洲经验”亦指亚洲移民讲述的个人经历。大学或社区常常举办这样的多元文化讲座,以增加社会的亚洲意识(Asian awareness)。澳大利亚的一个旅游网站也叫“Asian Experiences”,主要鼓励年轻人去亚洲旅游,“认识自己的邻居”。
除了跨学科,文化研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非主流,二是研究当下性,三是研究范围通常由关键词主导,如权力,身份认同,再现,抵制,被看,空间等,不囿于传统学科,更不仅仅局限于地域。因此纵观文化研究探讨的全球化各种问题,“亚洲经验”和个案在文化研究中似乎从未缺席,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西方各国都有“亚洲研究”,关于亚洲的会议和出版物源源不断,只要看看《连续统一:传媒与文化研究》近年来的出版,基于亚洲经验的研究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有极强的本土化能力,为什么还要提出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有必要为文化研究“画地为牢”吗?其实“画地为牢”是一种身份认同。三A文化研究圈的划分亦如此。现在用“亚洲”来限定文化研究的领域甚至方法,理论上并不矛盾。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在亚洲以外的立场(比如西方)研究亚洲,与亚洲本土的研究始终存在“在场”与“缺席”的问题。虽然文化研究关注全球化下本土文化的变化和影响,有极强的本土化能力,但汉语学术界与英语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并不同轨。其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都有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英语与汉语的文化研究仍在自说自话。没有研究证明双方的观点有足够的交流。
“亚洲经验”的呼吁,首先是身在亚洲的文化研究学者感觉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用或不一定够用,在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介绍之后,有一种走自己的路的要求,进而寻求适合自己特点和经验的亚洲文化研究理论和范式建构。这既是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走向世界”意识形态的必然。
当前一些媒体和媒体人不无得意地宣扬全球化正将世界推向单一的同质性文化(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的确,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正在抹去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互联网传递的文化超出一个国家的实体管理(超出国境线)。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健康都依赖于全球市场。当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和经济掌控无能时便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威胁。然而全球化也让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更注意到文化的差异性。文化研究对全球化下当地经验的解读,让各种边缘或弱小的文化和人群得到关注,使各种文化的差异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其研究理论都有相互可借鉴的地方,而其研究范式通常可以复制。
所谓范式(paradigm),原词来自古希腊,意为“模式,样板”。柏拉图在著作中将之用为“样式”或“范例”。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科学界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概念。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不仅“为研究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同时还是“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旦“范式转变”完成,其结果的可能性便难于挑战。虽然人文社会科学可以游离于几种理论范式之间,但是库恩认为“范式转变”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范畴概念,在人文科学不具有合法性(legitimate)。③不过加拿大社会学家寒达在库恩理论的基础上,将“社会范式”引入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社会学的“范式转换”。④范式就是一种哲学或理论架构或典范,有足够的具有普遍性的经验研究数据支持,并已经广泛应用或“转换”到其他领域的人类经验研究。人文社会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可以有范式转换。然而关于“范式”的争论始终不断,法国社会学家马蒂·多甘就拒绝承认社会科学有“范式”,他认为“范式”一词多层意义,不同学科可有不同解释。⑤
在文化研究方面,最早用范式一词的是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霍尔分析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两种范式,从此成为经典。⑥同时霍尔1980年在《制码/解码》一文中对电视观众的研究成为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电视观看中的意义不是电视生产者“传递”的而是作为观众的接受者“生产”的。其中的三种电视观众立场为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提供了一套新理论和新的分析话语,成为新的电视话语研究范式。⑦然而并不是所有文化研究理论大师都用“范式”这个词,比如特立独行的福柯在接近这一意义上用的词就是“话语”(discourse)。
在文化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复制方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澳大利亚学者佐伊·绍弗里斯将文化研究引入悉尼市供水系统研究中,对于所谓官方的“平均供水用户”(average water user)的界定提出挑战。⑧悉尼市供水局按照每年供水量和用水量的出入,从而量化出“平均供水用户”的平均用水量,并以此作为用水管理的基准数据。一如当年洪美恩对《达拉斯》电视观众的研究,⑨佐伊·绍弗里斯也采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选择固定用水户,研究他们的“用水日记”,从而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水概念千差万别。日记中有人每天洗两次澡,有人两天洗一次;有人衣服穿几次才洗,有人穿一次洗一次,有人用水浇菜园,有人拒绝这样的“水浪费”……同时通过分析从官方获得的大量数据,佐伊认为所谓平均划一的“平均供水用户”用水标准,忽略了用户的社会、文化、种族、性别等背景。此标准无视供水工业面对的是多元社会,多重利益与非均等化的用户(比如供水局的广告也只有白人及其家庭),从而会导致节水环保等公共政策制定的偏差,与社会现实脱节。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干预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一贯传统。该研究的意义不仅是挑战来自工业社会标准化的用水管理“理性”范式,对于如何节水环保以及如何更合理用水提出了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新思路。同时该研究与霍尔对电视观众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某种意义上是霍尔的《制码/解码》模式的借鉴,即对某些固有的、毫无差别的、简单的、工业社会的大一统观念进行文化研究的解构,从而将全球化下多元社会的“差异”性纳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亚洲的范式建构在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英语学术界曾就后殖民时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爱尔兰及英国等英语国家的认同问题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差异极大,但是在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少数民族(种族或文化)等方面不是毫无范式可循。⑩英国的亚洲移民与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也许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问题,这些研究甚至可以作为中国农民工文化认同研究的范式参考。
周志强在研究赵本山的电视剧去政治化的傻乐主义时,认为这是“以俗为雅、以丑为美、以傻乐为娱乐的反智主义市侩美学……其喜剧的品质,迎合了那些渴望安定和保守的小市民们,对日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深藏着怎样的忧虑、警惕和不安。”(11)其实全球娱乐的去政治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范式”。中国也未能幸免。毫无“营养”的所谓“傻乐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掩耳盗铃”的娱乐模式,日益西风东渐。这是一个急需得到关注的新领域。亚洲有着世界最多的电视观众,最大的手机用户群,最庞大的网络贴吧/微博与最活跃的网上虚拟用户。不管学者们是否无法忍受,无可奈何或无所畏惧,都不能忽略“傻乐主义”这一文化现象的隐形意识形态及背后的经济“黑手”的存在。“亚洲经验”与亚洲文化研究也许能为此提供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三、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的问题
文化研究没有学科界限但有研究方向,这是长处也是短处。在这样一个学科界限模糊的领域,劈出一块亚洲文化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文化研究“瘦身”,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亚洲。同时亚洲文化研究的成果与范式能够借鉴或复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用一个不可复制的亚洲来界定文化研究,有必要厘清三个问题:首先是亚洲的身份认同,其次是亚洲文化研究“他者”的认定,最后是意识形态问题。
1.身份认同(identity)
人类学家格兰特·伊文思对亚洲文化的多元性有一个生动比喻:“文化马赛克”。(12)从地缘政治来说,亚洲也是“马赛克”:中日韩属于“东北亚”;新马泰、印尼、菲律宾、越南等是“东南亚”;“南亚”则是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中亚”是苏联解体后新疆以西的哈萨克斯坦等国;“西亚”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耶稣基督也是亚洲人”是一句笑话,也是事实)。亚洲各国历史长短不一,中印文明悠久,但“东南亚”一词仅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3)中亚四国历史也不过二十多年。
在《亚洲:全球时代的文化政治》一书中,大卫·伯奇一开头就提出亚洲概念的挑战性:“称之为亚洲的地区总人口超过三十亿;人们说着几百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它的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特点的多样性超过世界任何地方。无论从任何角度想象,当代亚洲都不是一个同质体……亚洲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或文化实体。”(14)作者还强调:
“亚洲被想象地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语境中……亚洲的概念不是基于亚洲之所以为亚洲的现实——存在于如今确定为亚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前——而是基于亚洲的一种文本,一个概念,一种文化结构的想象,是想象的亚洲而不是自然存在的亚洲。”(15)
西方各国的“亚洲研究”最早来源于美国军方的国防部和五角大楼。(16)后来才进入学术界。但是“亚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一直受到挑战。大多是依附于西方各大学的亚洲语言教学才得以生存。上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大学一些名为“亚洲研究”的科系其实只是日本研究,让当时“文革”后第一批迈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目瞪口呆。目前西方大学的亚洲研究大多附带亚洲语言:如汉语、日语、印尼语、韩语、泰语等,依靠语言支撑,研究背后的国家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
在文化研究领域,比“亚洲经验”更常用的是“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一词,源自上世纪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讲话。由于新加坡经济越来越发展,国家也越来越西化。李光耀因此担心其亚洲的身份认同问题,提出“亚洲价值观”,以确认新加坡国家的文化认同。有意思的是,事关国家文化认同,李光耀却没有用“新加坡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儒家价值观,也就是经济领域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圈”。这一说法引发了一场近20年的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论争。(17)“新加坡学派”因此得名。苏瑞恩(Surain Subramaniam)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指出,“新加坡学派”认为亚洲价值优于西方价值,用亚洲价值话语对付西方的社会价值观,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与亚洲文化本质上不相容”。(18)因此“新加坡学派”被看作是亚洲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挑战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洲价值说”在文化上是武断的,是一种“非自由民主”的精英话语。(19)澳大利亚的加利·罗丹(Garry Rodan)认为源自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之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亚洲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20)
这场论战,后来从对“亚洲价值观”的质疑归结到对亚洲文化的质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亚洲文化”?格兰特·伊文思在他的书中答到:“回答也许是出人意外的,没有。”(21)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亲历论辩双方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一个研讨会,题目就是“亚洲文化不存在”(There is no Asian Culture)。如大卫·伯奇所说,“亚洲”归根究底只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不存在这样一个文化实体,如同不存在“西方”的文化实体一样。它只是一种赛义德东方主义式的西方想象。然而身处亚洲,生活在亚洲的学者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感觉得到自己文化的存在,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研究亚洲文化研究,亚洲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关键问题。
2.“他者”(the Other)
文化研究从产生的那天起就面临一个“他者”问题。面对当时精英主义与中产阶级价值观垄断的英国主流学术界,伯明翰学派作为“他者”出现在二战后的英国社会。它关注的也多是那些被忽略和边缘化的社会与文化的“他者”: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等。从此打开了一个研究非主流社会的突破口。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非主流性。
上世纪80年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漂移”到澳大利亚,风靡一时。一些学者在挪用伯明翰理论资源的同时,声称自己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为“英国文化研究”。但是这种划分有歧义。在另一个意义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原是“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 Studies)的传统领域。学术传统上,“澳大利亚研究”的对象多为主流社会,包括源自英国的文化遗产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等;而后来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注的多为非主流社会,如移民的文化和政治认同,电视的公共政策等等。如果说“澳大利亚研究”也探讨主流社会对移民的认同和接受态度(是否要接受他们,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标准等);那么“文化研究”更偏重于移民本身的利益(他们是否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歧视,移民自身文化的传承问题等等)。所以“澳大利亚研究”关注的是传统的学术范围,而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新兴的或被传统忽视而不能进入精英视野的“角落”。它把被传统精英学术屏蔽的领域彰显出来,使之具有“平民化”学术的特征。这两个领域实际上互为“他者”存在。
关于“他者”研究的二分法来自后殖民理论。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发表《东方主义》一书,(22)批判西方文化霸权,探索东方文化主体性。这本书的影响使得后殖民理论,尤其是“他者”理论成为一种知识话语,并广泛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美国学者朱莉·詹森曾移植后殖民的知识谱系来分析各类“病态”的粉丝。她在“粉丝病理学:鉴定结果”一文中研究大学精英们如何把粉丝作为一个“他者”进行文化机制的考察,用二分法把受教育与未受教育,精英与大众,理性与感性等进行文化上的对照,梳理出关于精英的知识和价值取向,用以对照粉丝的非理性和不正常。朱莉·詹森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答。她认为把粉丝当做“他者”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在大学里自以为是的社会精英。她用的英文“我们”是WE,“他者”是THEY。她不无嘲讽的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安全感”。(23)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不是像《东方主义》那样期望摆脱“西方影响决定东方“的单向文化交流模式,而是提醒“我们”在对粉丝的研究中不能无视大学精英的话语霸权。
亚洲文化研究若要建立一个亚洲范式,理论上也面临“他者”问题的挑战。在定义亚洲文化研究的时候,“他者”是谁?西方文化研究?还是亚洲(各国的?本国的?)的主流文化研究?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共同体是不是对立面?亚洲文化研究与本国的主流文化研究是什么关系?笔者曾经有幸与国内一个认识多年的学者交流,他问道:“你那文化研究是什么?你们到底懂不懂中国文化?”这位学者不是恶意,问题也不难理解。一是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中国古典文学是绝对主流。二是笔者身在海外。研究中国文化,人不在中国自然就没有“在场”的话语霸权。
当年大众文化研究兴起时,也不可避免“他者”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不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缺席的那个“他者”是定义大众文化的关键。它是高雅文化,还是精英文化?是民间文化还是民俗文化?或者说还是群众文化?陶东风曾列举中国的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群众文化等,以撇清它们跟大众文化的关系。(24)当然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在西方争论也很多,有些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比如托尼·巴奈特(Tony Bennett)就认为大众文化的定义毫无用处,只能引起意义上的矛盾和混乱。(25)约翰·斯托雷(Jonh Story)认为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类别,意义如何,它有什么意思,要看你放进什么内容,针对什么而言,而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大众文化的论争很容易误导进理论的死胡同。(26)
亚洲文化研究可以先去做,而将理论问题暂时搁置。但这会不会被理解为亚洲的一种自我“他者”化?文化研究“厚颜无耻”地挪用各种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但是挪用不等于食古不化,盲目的理论照搬。笔者2011年为陆扬主编《文化研究导论》(27)撰写第八章“粉丝文化”,后发现“粉丝”一词改成了“粉都”,说是中国的翻译惯例。遂去文解释。主编认为有道理,并建议找机会更正,以免贻误后进之辈。现附文如下:
……在我用粉丝的一些地方,你改成了“粉都”。这是一个小小的争议,是我不认同的地方。因为“粉都”是一个生造的词,一个谁都不懂的词。
费斯克的《粉丝文化经济》你改成了《粉都文化经济》。因为老费的英文用的是fandom,“粉都”是fandom的中文翻译。其实fandom跟不同的词搭配时,在汉语里就是粉丝的意思。比如粉丝文化,粉丝理论,粉丝研究,这些词倒回英文翻译都可以是fandom。我个人以为没有必要将fans译成“粉丝”而将fandom译成“粉都”。何必生造一个词呢?又比如free和freedom,中文的翻译都是“自由”;bore和boredom都是“无聊”;rebel和rebeldom都是“造反”。还有跟“粉丝”相对有一个词“明星”(stars)。英文里有star和stardom。难不成要将stardom译成“星都”?再有英文里“dom”作为后缀的词很多,例如kingdom,queendom,popedom,princedom,dukedom,chiefdom,heirdom,martyrdom。除了词性的转变,意义上变化不大。当然象condom和random是另一回事。
换一个角度来看,汉语里有“老”和“旧”两个词。我们都明白它们的区别。可是到了英语就只有一个词“old”。经常听人说“他的妈妈很旧。”“我的男朋友很旧。”英语世界竟没人想造一个词去对二者进行区分。同样的还有“中国的”“中国人”“中国话”“汉语”“中文”……这么多词在英语中只有一个“Chinese”。你知道此间有多少人被这个简单的“Chinese”弄迷糊吗?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不赞成用“粉都”,就像不赞成用“迷们”一样。文化研究应该用尽可能接近社会的词而不是反之。因为文化研究为之骄傲的是给予那些非主流的人和现象以学术关注。“粉都”这样的翻译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我觉得象是一种研究者的自我“他者”化。也许言重了。但是唯英文马首是瞻,生怕翻译错了或翻译得不准确而完全忘了自己的国情,忘了什么人读它,这些人懂不懂?这就是文化研究要研究的问题……人在江湖,我们不时会碰到一些不解的汉语,待看到英文才知道意思,“粉都”又是一例子。可汉语是我们的第一语言而英语是第二语言。连母语也要英文帮忙,你说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或是我们自己母语退化的悲哀?
3.意识形态(ideology)
关注当下性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传统。用霍尔本人的话就是“帮助人们了解当下的现状”。当今社会的发展会有无数的问题需要解释,需要的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文化研究扮演的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其疆界一直在发展。全球化背景中的各种新文化,新事物,新现象与新冲突几乎都在文化研究的关注之中。
虽然与时俱进是文化研究的生命力,当下性也有陷阱。不同的国情,意识形态会对当下性做出不同的解释,因而有不同的学术立场。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在他最新出版的《全球化中国的电影,空间与多元地点》中认为,在西方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很少学者愿意做观众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在一些学者看来观众研究就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电影工业提供分析数据,“因为它评估宣传机器的效果”。(28)他们不愿意为资本主义体制服务,要的是保持自己学者的独立性。而在中国,电影与电视的观众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不同,立场也不同,做学问的方法不同,选题也不同。
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的要求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要求超过学术的要求?文化研究的当下性是否意味着需要为当下的体制服务而失去独立的学术立场?亚洲各国家体制不同,其当下性也有不同解释。文化研究是社会需要还是体制需要?学者是服务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监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因为它可以在最具体的层面体现出来,比如说研究经费的分配。这中间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甚至也很难用价值观去评判。即使西方的一些学者,声称学术独立,但是某些时候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众或学术界也可能达成短暂的一致。
美国9·11事件后人们对安全(或不安全)的焦虑造成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后面既有政治操纵,也有媒体的利用甚至“火上浇油”。2010年5月墨尔本大学召开了“媒体与安全文化”(Media and Security Cultures)研讨会,讨论澳大利亚媒体与安全文化的相互作用。会议还讨论了政府在传媒立法的论争与政策要求,观众对电影电视剧等媒体再现的安全文化的反应。(29)这样的研究,即有社会当下性的迫切,也有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及学术界的责任感。二战后西方对伤痕的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国对“文革”记忆的研究,(30)都不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关系也从来没有理顺。当下性是一种真正存在的体验。但是文化研究如果能梳理出亚洲范式,一种基于地缘文化的文化研究范式,而不是霍尔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能否从此引领出非洲范式,拉丁美洲范式?那么伯明翰就是欧洲范式或西方范式?换句话说,伯明翰学派在澳大利亚称之为“英国文化研究”,以区别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还有几乎与格罗斯伯格成为同义词的“美国文化研究”。同理推之,应该还有“中国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印尼文化研究”……。放眼国际,还会有“非洲文化研究”和“拉丁美洲文化研究”等等。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殖民地”化?一个非英语(如汉语、日语)为媒介的文化研究,如何主导话语权?如何走出孟繁华式的悲哀:“对于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国学者来说,我们仍是全球化话语的‘局外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边缘性的地位也许就是宿命式的。”(31)
四、结语
全球化下的文化研究正面临挑战。即使在三A轴心的文化研究共同体,也是喜忧参半。格罗斯伯格在《未来时态的文化研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兴奋,认为跨学科甚至无学科界限代表未来的研究方向,所以文化研究前途无量。(32)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正在呼吁为其“瘦身”。在英国,由于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关闭,更有人以为文化研究气数已尽,翘首以盼等待下一波研究热点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亚洲的文化研究的崛起显得特别有意义,为全球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
本文讨论文化研究亚洲范式的意义与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亚洲文化”从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讨论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时,首先要考虑这些定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文化里或者什么样的亚洲国家里产生的,它对另外一个亚洲国家或者说另外一个语境里的亚洲文化现象是不是有说服力,是不是能够解释这些文化经验和文化现象。其次,亚洲的文化研究,与亚洲之外的文化研究需要更多的对话与合作。双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能开辟更多文化研究新领域,学者们在亚洲以外研究亚洲,与亚洲本土的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立场。
注释:
①Ang,Ien,"Navigating complexity:From cultural critique to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Volume 25,Issue 6,2011,pages.779-794.
②本文为2012年6月29日至7月2日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亚洲经验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会议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中文系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
③Kuhn,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the preface.
④ Handa,M.L.,"Peace paradigm:Transcending Liberal and Marxian Paradigms"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New Delhi,India,March 20-25,1987,Mimeographed at O.I.S.E.,University of Toronto,Canada,1986.
⑤Dogan,Mattei.,"Paradig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ume 16,2001.
⑥Hall,Stuart,"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vol.2,1980,pages.57-72.
⑦Hall,Stuart,"Encoding/decoding".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Hutchinson,1980,pages.128-38.
⑧Sofoulis,Zo?,"Skirting complexity:The retarding quest for the average water user",in 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Volume 25,Issue 6,2011,pages.795-810.
⑨Ang,Ien,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London:Methuen.1985.
⑩See Bennett,David.ed.,Multicultural States: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
(11)周志强:《从现实主义到傻乐主义——论赵本山乡村叙事的去政治化》,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12)Evans,Grant,ed.Asia's Cultural Mosaic: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1993.
(13)SarDesai,D.R.,Southeast Asia:Past and Present,Westview Press,USA,2003,p.3.
(14)(15)(16)David Birch,Tony Schirayo and Sanjay Srivasiava,Asia: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Global Age,Allen & Unwin,2001,p.vii,p.iv,p.ii.
(17)(18)(19)Subramaniam,Surain:"The Asian Values Debate:Implications for the Spread of Liberal Democracy",in 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ume 27,Issue 1,2000,pp.19-35,p.19,p.28.
(20)Rodan,Garr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conflict:Asia's new significance",in The Pacific Review,Volume 9,Issue 3,1996,pages.328-351.
(21)Evans,Grant,ed.Asia's Cultural Mosaic: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1993.
(22)Edward W.Said,Orientalism,Harmondsworth:Penguin,1985,C1978.
(23)Joli Jensen,"Fandom as pathology:The consequence of characterization",in Lisa Lewis,ed,The Adoring Audience: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New York:Routledge,1992,p.24.
(24)陶东风:《双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大众文艺》,载《电视艺术》1993年第4期。
(25)Waites,B.,Bennett,T.and Martin,G.,eds,Popular Culture:Past and Present.A Reader,London:Croom Helm,1981.
(26)Jonh Stor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Pearson Prentice Hall,2006.
(27)陆扬主编:《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8)Zhang,Yingjin,Cinema,Space,And Poly locality in a Globaliz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p.33.
(29)参见Continuum: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Special Issue:Media and Security Cultures,Volume 25,Issue 2,2011,pages.142-278.
(30)参见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2011年第11辑。
(31)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32)参见《关于理论与问题的探讨——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的对话》,《文化研究》2011第11辑,第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