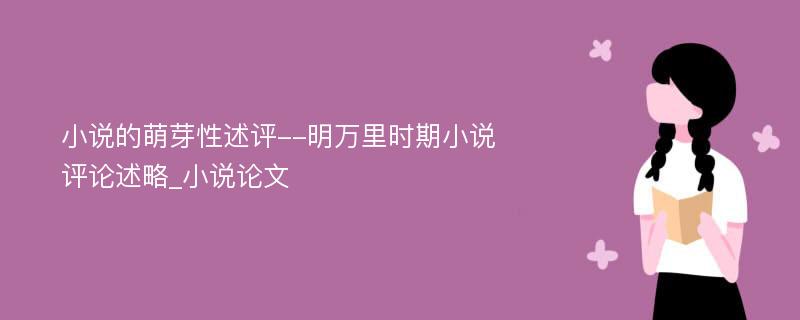
小说评点的萌兴——明万历年间小说评点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年间论文,明万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自明万历年间(1573—1620)发端,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是古代小说批评之主导形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批评形式,近年来已备受研究者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其实绩不容轻视。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对于小说评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名家、大家,如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张竹坡等,而小说评点的发展态势,至今仍不甚了了。诚然,这些评点大家确乎是中国小说评点美学生命的“脊梁”,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形态,小说评点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而非单个出色的评点家及其著作所能概言。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看,小说评点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垦的领域。对此,笔者拟就作为兴起时期的明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一阶段性的描述。
一
我们将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为一个阶段加以描述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时期是中国小说评点的源头,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我们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和脂砚斋等评点大家的著述中均可寻到万历时期小说评点所烙下的印迹。同时,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年间开始引入白话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中国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如果说,万历时期是中国白话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开创期,那么万历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小说评点的奠基时期。同时,万历时期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期,它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征、宗旨目的等诸方面都趋于稳定。因此,将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作为一个阶段来加以描述一方面是为了理清此时期小说评点的基本态势,同时更重要的乃是为中国小说评点寻求其源头活水。
确切地说,小说评点在万历年间的萌兴,实则是以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为起始的。故所谓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仅有二十七、八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小说评点却颇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出版的小说评点本约20种,约占嘉靖以来出版小说的三分之一强。
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年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万历十九年,“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①]越一年,李卓吾开始了《水浒传》评点,袁小修记云:“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②]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了小说活动,仿佛向我们兆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这就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娱性,小说评点正是主要顺着这两种态势向前发展的。我们不妨先缕述一下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基本情况。
就现存资料而言,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是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有《识语》云: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仇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据《识语》所云,此书在校正上做了五项工作:圈点、音注、释义、考证、补注。其校正文字均为双行夹注,正文中标有的批注形式有这样数种:《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其中《释义》《补遗》《考证》《音释》是比较单纯的注释,而《论曰》《补注》和《断论》却已颇富评论性质,如《刘玄德襄阳赴会》节,玄德与刘表论胸次抱负,“史官有诗赞曰:曹公屈指从头数,天下英雄独使君,髀肉因生犹感旧,争教寰海不三分。”《论曰》:“此言玄德不忘患难,安得不为君乎?”再如“诸葛亮博望烧屯”节,徐庶评孔明:“某乃萤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亮哉。”《补注》:“此是徐庶惑军之计也。”此类文字显已越出一般注释,带有了更多的评论成份。故此书虽未明确标出“批点”或“批注”字样,实已具备了评点的功能,只是在体例上较多呈现校注本的形态而已。
万历二十年,余象斗弃儒从商,经营世代相传的书坊业,这是一位兼小说编撰者,小说评点者和小说出版者于一身的人物。就在这一年,他首先刊行《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首次明确标出了“批评”字样,且与“全像”相并列。“全像与批评”是明万历以来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小说的流播。全书正文页面分三栏:上评、中图、下文,这是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基本形态,惜此书已流至海外,难以得见。越二年,余象斗又刊刻了《水浒志传评林》,该书外部形态悉同前书,故以此为据可概见余氏评点本的一般面貌。全书正文前有《题水浒传叙》,余象斗撰,对《水浒传》予以高度评价,其曰:《水浒》“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昔人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视之哉。”《叙》之眉栏又置《水浒辨》一文,概括了此书特色:
《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编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云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有漏,皆记上层。
此为本书之广告语,亦可见出本书之基本特色:首先是余氏对原书作了有意的删改,这主要是文中的错讹和“不便览者”之内容;其次,余氏在原书上端添加了评语,对《水浒传》作出赏评;第三,余氏削去原书中之“失韵诗词”,但为便于观者阅读,仍将其置于“上层”,并特为标出。可见,余象斗对《水浒传》的评点乃是“改与评”二位一体的。这种在评点中删改原作的做法是否恰当,其删改又是否确切,我们姑且不论,但综观中国小说评点史,“改与评”二位一体却是中国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格局。无疑,余氏之评乃小说评点中此种格局形成的始作俑者。而这与古代小说的创作背景相关,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其独特性,这便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这些作品从一开始便非以独立的创作面貌问世,而是在流传中逐步得以修正、增删和完善。小说评点“改与评”二位一体的格局正是在小说的这一创作背景上生成的,它说明了在中国小说史上评点者也一定程度地参与了小说的创作,而这种参与使得小说评点本不仅是一种理论批评著作,同时也获得了在小说发展中的版本价值,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即是在《水浒》流传史上简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之一。而小说评点史上一些重要著作同时也正是该小说在自身流变中的重要版本,如“容本”、“金本”《水浒》,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等等。
余氏《水浒志传评林》在理论批评上也颇有特色,该书评点均为眉批,置于上栏,每则批文均设标题,如“评宋江”、“评李逵”、“评诗句”等,紧扣每回局部内容阐发评判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虽不出色,但对于一些主要人物的品评,尤其是将其分散的对于单个人物的品评缀合起来,也不失为一篇完整的人物评。我们试将书中有关李逵的评论拈出几则并作一缀合,以见其特色:
观李逵思取母兄一事,一见孝心可钦。
李逵闻杀便喜,此若《三国》翼德之性无异矣。
李逵欲杀李鬼,闻李鬼说有老母便以金白(应作白金)赠之,叙不杀戮,见李逵此处勇有慈心。
观李逵此段义气凛然,真一丈夫也。[③]
以上数条虽都只是寥寥数语,但缀合在一起,就把李逵的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了。
从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双峰堂本《水浒志传评林》,小说评点在书坊主的控制下在小说的流播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书坊主自身艺术理论素养的局限和商业性的制约,小说评点在其理论品位上相对比较低下,因而小说评点要张扬自身的美学生命和求得发展正亟待着高品位文人的参与和高质量评点著作的出现。对此,李卓吾醉心于评点并慧眼识中《水浒传》,恰为小说评点获得了一次在理论批评的台阶上腾挪而上的契机,这我们留待后文详论。
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以万历二十年左右为界可划出一个阶段,由上文分析可知,这一阶段的小说评点有其明显的特色。一方面,作为小说评点的开端,此时期是文人参与和书坊主控制齐头并进,这为以后小说评点的发展开凿了两个基本源头。同时,对评点对象——小说作品的选取乃是那些流传既久且已有相应知名度的作品,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没有将评点伸向新创的小说之中。这种现象的形成就文人一端而言,固然表现了他们的眼力和识见,而从书坊主一端来说则仍然是从商业性考虑的,因为此时期毕竟是小说评点的发端时期,带有某种尝试性质,能否有利于小说的流传对于他们来说还心中无底,因此选取业已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且销路看好的作品相对而言比较保险。万历二十年以后,随着小说评点的广泛流传,以及社会的逐渐接受,小说评点便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
二
从万历三十年左右到万历四十八年,除了继续刊刻《三国演义》评本和将李卓吾评《水浒传》公开出版外,十余年中出版的小说评本几乎都是新创的小说。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新创小说的评点本有十余种,计有:《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东西两晋志传》《春秋列国志传》《隋唐两朝史传》《片壁列国志》《全汉志传》和《绣榻野史》等。在上述作品中,除《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和《绣榻野史》外,余者悉为演义小说,而评点者的成份也仍以书坊主为主体。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评点已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冒用名人评点之举在此时期也开始风行,如《春秋列国志传》伪托陈继儒,《绣榻野史》冒用李卓吾,《片壁列国志》也署“李卓吾先生评阅”,但实际上并无评语。此风之盛行说明了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仍然控制在书坊主之手。
由于上述原因,也因了评点之小说本身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故此时的小说评点除了分别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和万历三十九年左右的“容与堂”本和“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外,整个评点的理论批评成就不高,“音诠”“释义”仍是评点之主要内容,如曾刊刻评点《水浒志传评林》的余象斗,此时没有将“评林”的批评思路作进一步发展,却在其《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中,于每回末分别列“释疑”、“地考”、“总释”、“评断”、“鉴断”、“附记”、“补遗”、“断论”、“答辨”等名目,这些批注文字虽数量较多,但几与文学评点了无关涉,又回到了万历十九年刊刻的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老路上去了。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小说评点中较可注意的是《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和《绣榻野史》二书,前者属神魔小说,后者大致可归于世情小说,这是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中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各自唯一的评点本。不难发现,这两部小说绝非万历年间出版的这两类小说中的佼佼者,但为何较其更为出色的《西游记》和《金瓶梅》反而没能赢得评点者的青睐呢?对此,《金瓶梅》的境况较易解释。因为《金瓶梅》虽然成书于嘉靖年间,但正式刊行却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在这之前,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以抄本的形式辗转流传,流传的不广使人们还无法对它作深入的品评,就是有幸得见抄本者,也显得颇为局促,如袁宏道得《金瓶梅》半部抄本后,曾借与谢肇淛一读,后见数日不还,竟特去信催问:“《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对《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巨制作出详细的评点显然是颇为困难的。《金瓶梅》刊行之后,大约在崇祯末年就出现了批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那刊于万历二十年(1592),且曾引起一股神魔小说创作风潮的《西游记》为何也没获得评点呢?这是一个颇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或许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西游记》作为一部有着广博内涵的小说,非一般神魔小说可比,故从书坊主一端而言,这种小说评点对他们来说绝非易事,而就文人一端来看,《西游记》的虚妄幻诞又与他们素来信奉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思想有悖,朱之蕃即指斥云:“《西游》近荒唐之说,而皆流俗之谈。”[⑤]故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这部小说的充分认识要有一个相应的较长的过程。一直到明末清初,《西游记》才成为了评点之热门,有清一代所出版的评本竟有七种之多,这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是一个颇为罕见的现象。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之所以获得评点,很大程度上即在于此书虽为神魔小说但又颇富现实内涵,顾起鹤评之云:
顾世之演义传记颇多,如《三国》之智,《水浒》之侠,《西游》之幻,皆足于省醒魔而广智虑,然未有提撕警觉世道人心如兹传之刻切者。彼其姓名事迹真实者过半,就中生一派光明正大之规。[⑥]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署“九华潘镜若编次,兰隅朱之潘评订。”书中评语仅为眉批,甚简明,多直接评述书中细节,评者颇重小说的情趣,故“趣”字在评点中触目皆是。书中《凡例》有一节专门论及评点,是小说评点史上较早对评点作出专门评判的文字。其云:
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圈,而其次用点,至如月旦者,落笔更趣,且发作传者未逮。[⑦]
文中涉及圈点与评两个方面,这正是评点的两大组成部分,但圈点其实在小说评点中并不显得重要,圈点源自经注和诗文评,于小说实无太大价值。因为从总体上而言,小说之成功与否不在于个别词句之警拔,而在于全部规模之完善。
《绣榻野史》存世有万历年间醉眠阁刊本,署“卓吾子李贽批评,醉眠阁憨憨生(卷三、四又署憨憨子)重梓”,正文有眉批,回后有评及“断略”。署李贽批评显系伪托,理由有二:一是此书据王骥德《曲律》乃吕天成“少年游戏之笔”,吕天成约生于1580年,卓吾卒于1602年,李贽作评似乎可能性不大。二是《绣榻野史》有憨憨子作序,序中明言“……余慨而归,取而评品批抹之,间亦断其略。”从该书评点体例而言,显系憨憨子作评。[⑧]《绣榻野史》是中国古代一部知名的淫秽小说,对淫秽小说作评,以此书为起始,明代以来,淫秽小说虽屡屡禁绝,但创作与出版仍不绝如缕,而对其进行评点者也颇不乏人,形成了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一大系列。《痴婆子传》《浓情快史》《肉蒲团》等均有评本问世。对淫秽小说作评,首先针对的便是所谓的“淫”字,“以淫止淫”乃是此类小说评点的一个认识前提。《绣榻野史》评点正开其端,憨憨子《序》云:
客有过我者曰:“先生不几诲淫乎!”余曰:“非也,余谓此虑深远也。”曰:“云何?”曰:“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不必不变也。”[⑨]
在《绣榻野史》的评点中,评点者对此书实则作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评品”,二是“批抹”,即对原作作适当涂改,三是“断略”,书中结尾处带有劝惩性的语言或即由评点者所增入。
三
毫无疑问;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之巨擘乃李卓吾,他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文人评点小说的早期重要人物。当小说评点在书坊主的控制下缓缓行进之时,在书坊主们对小说作出简略的、功利性的赏评注释时,李卓吾以其慧眼卓识在小说评点中注入了新的血液。他首次将个体的狂傲之性和情感内核融贯到小说评点之中,从而使小说评点成为了一种带有个体创造性的批评活动。
李卓吾是明中叶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异端思想带有浓烈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色彩,在明中后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李卓吾对小说的注目和评判有两个基本特性:首先,李卓吾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惠顾小说的,故是一种高层建瓴式的赏评,他所注目的不是技巧层次的小说,而是在其整体思想的统一标领下对小说作出重意、重主体的认识。其次,李卓吾的小说评点是一种带有自娱性、不求功利目的赏评活动,是一种在阅读过程中的随意“批抹”。在《焚书》卷六中,李卓吾有《读书乐》一诗概括了这种阅读赏评特色: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在《寄京友书》一文中李卓吾又谓:“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⑩]李卓吾的小说评点与这种阅读赏评特色是相一致的,他所追求的正是那种“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的境界,这种在艺术赏评活动中主体意识的贯注对中国小说评点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尤其在金圣叹、张竹坡等评点大家身上更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李卓吾评点《水浒传》有一个过程,他最初接触《水浒传》大约在万历十六年(1588),“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11)四年以后,袁小修访李卓吾,见其“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但又四年之后,评点尚未结束,他依然醉心于《水浒传》的赏评,“《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12)一部作品的评点越八年仍未结束,正充分证明了李卓吾之小说评点纯是一种在阅读过程中的自娱活动。他甚至从未想到要将其出版问世,所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的著作难有可靠之人可以托付:“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又恐弟死,书无交阁处,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13)
李卓吾小说评点的这个特色使得其《水浒》评点成了中国小说评点史上一个最大的疑案。李卓吾于万历三十年(1602)系狱自尽,万历三十八年和三十九年左右,两部同署名为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几乎同时问世,这便是“容与堂木”《水浒传》和“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对这二书真伪的辨析,自明末迄今,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近十年来的争辩更为深入(1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或认“容本”为真,或定“袁本”为真,其理由均凿凿有据,双方都有证据为自己立论,但都无法彻底辩倒对方。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现存的材料已基本穷尽,但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另辟蹊径,窃以为,当现有材料无法证实其真伪时,“假设”的力量不可低估。对此,本文拟设这样一个“假想”:我们设定李卓吾于万历二十四年完成了《水浒传》的评点,以后在朋友之间传阅。李卓吾死后,流传渐广,或原本,或片言只语,或直接以其评点文字流传,故在万历三十八年之前,李卓吾之《水浒》评点已流散在外,于是书坊主假借其盛名,在其评点之基础上聘请文人加以模仿、增改、扩充,使其形成了完整的《水浒传》评点本,“容本”或由叶昼所为,“袁本”或由冯梦龙、袁无涯所为。因此我们的假设结论是:“容本”与“袁本”均非李卓吾之真评本,但又都以李卓吾之《水浒》评点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中之精神血脉犹然是李卓吾的。(15)
那流淌于“容本”和“袁本”《水浒》中李卓吾评点的精神血脉是什么呢?概而言之,约有二端:其一,如上文所说,李卓吾评点《水浒》持有一种强烈的自娱心态,他的评点主要是在作品的规定情境中求得内心的精神快慰,而这种精神快慰的获取乃是直接抒发郁积于内心的情感思想。这种小说评点的主体性在“容本”和“袁本”《水浒》评点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容本”《批评〈水浒〉述语》云:“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又云:“据和尚所评《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16)此类评述既可视为对“容本”《水浒》评点的概括,也可看作对李卓吾评点《水浒》之精神的张扬,而书中评点确乎也是以此为特点的。“袁本”《水游》评点亦然。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云:“非卓吾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老之精神。”(17)而其评点也多抒发主体的愤懑牢骚之情。其二,李卓吾批评《水浒传》现存唯一完全可靠的是《忠义水浒传叙》。该文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乃在于两点:一是视《水浒》为“发愤之所作也。”二是以“忠义”许《水浒》之英雄。而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抬高《水浒传》的社会地位。此序不仅在“容本”和“袁本”中直接引用(袁本略有修改),书中评点也大多张扬此说。当然,两者在具体评价上也颇有不同,论述风格、思想内容也有歧义。但上述两层内涵所构成的李卓吾评点《水浒传》的精神血脉却犹然存在。
从小说评点史角度而言,“容本”、“袁本”《水浒》评本其实并不会因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而会贬其身价,这是万历年间出现的两部最为出色的小说评点本,也是对后世的小说评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因而视其为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之双璧也实不为过。而这种地位的确认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其主导线索是在书坊主的控制下沿着商业性和功利性的道路向前发展。李卓吾加入小说评点行列突破了这一格局,但由于李卓吾没有可靠的评本问世,人们还无以从整体上得见李卓吾评点的批评风貌。“容本”“袁本”以李卓吾评点的精神血脉为根抵,作模仿、生发和延伸,从而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小说评点的发展史上。这是一种强化主体创造性的批评精神,其中“创造性思维的贯注和主体情感的投入”可谓开启了一条小说评点的新路,后世之金圣叹、张竹坡等评点大家缘此而日益发展了小说评点,并由此壮大了小说评点之声威。
其次,“容本”和“袁本”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实际奠定者。小说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形式,有其自身的形态特征,这一形态特征又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容本”“袁本”所奠定的小说评点的基本形态为:开首有序,序后有总纲文字数篇,相当于后世的读法,如“容本”有署“小沙弥怀林”文章四篇,“袁本”有杨定见《引》和袁无涯《发凡》。正文部分则由眉批、夹批和回末总批三部分构成。这一形态遂成后世小说评点之定制。在“袁本”《发凡》中,评点者还就小说评点的宗旨、特色及意义作了分析。其云: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家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夐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之所最贵者也。
这是小说评点史上难得的一篇批评文字,而由上述文字可知,袁本在批评形态上确已是相当自觉和成熟的。“容本”在批评形态上还有一异处,即在批评过程中对作品文本作出某种删改,但又不直接删去,只在正文中设删节符号,或上下钩乙,或句旁直勒,中刻“可删”字样,这种做法上承余象斗,下启金圣叹,成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一大传统。
第三,“容本”和“袁本”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贡献更在于完成了中国小说评点在批评内涵上的转型。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在形式上一般不脱训诂章句和音诠释义,在内容上则大多为历史事实的疏证,真正对小说作出艺术的、情感的赏评还并不多见。而“容本”和“袁本”则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从整体倾向而言,“容本”的理论批评价值要高出于“袁本”,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小说创作理论问题上,“容本”往往能高屋建瓴,提出精到的理论见解。相对而言,“袁本”则在小说具体描写的赏析上颇见功力。尤可注意者,“袁本”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首先借用八股文法,对小说艺术文法作出归纳总结的批评著作,其提出的一些文法诸如“叙事养题”、“逆法”、“离法”等,虽无甚理论价值,但可视为中国小说评点史上文法总结之开端。
小说评点的产生,其最初动机乃是为了促使小说的流传,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这与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所特有的艺术商品的特殊性相关,故小说评点在书坊主的控制下常常以疏导、诠释为其主体,其目的也主要是有利于读者,尤其是下层民众的阅读。这是万历年间小说评点之主流。随着文人的参与,小说评点在理论批评的层次上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文人最初从事小说评点却是其在阅读过程中一种心得的记录,一种情感的投合,而并无有意于导读和授人以作法。这是小说评点走向成熟并获得发展的契机。而当将文人阅读过程中带有自赏性的阅读心得与带有商业功利性的导读结合起来时,小说评点才最终成了一种公众性的文学批评事业。这一结合在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中,就是由李卓吾评点《水浒》到“容本”、“袁本”《水浒》评点的公开出版而得以完成的。
作为中国小说评点萌兴期的万历小说评点,虽然其理论批评成就并不突出,但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尤其是李卓吾等著名文人的加盟,对小说评点的发展更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万历以后,小说评点进一步呈发展壮大趋势,作为一种批评形态逐渐占据了中国小说批评的主导地位。而奠定这一地位的无疑是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
注释:
① 余象斗《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自叙。
② 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
③ 《水浒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余氏双峰堂刊本。
④ 袁宏道《与谢在杭书》。
⑤ 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叙》《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明万历白门万卷楼刊本。
⑥ 顾起鹤《三教开迷引》,同上书。
⑦ 《三教开迷传凡例》,题“九华山士谨识”,同上书。
⑧ 据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憨憨子或即王承父。承父初名胤,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号昆仑山人、梦虚、憨憨人等。”可备一说。
⑨ 憨憨子《绣榻野史序》,明万历年间醉眠阁刊本。
⑩ 李贽《焚书》卷三。
(11) 李贽《复焦弱侯》,《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版。
(12) (13) 李贽《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
(14) 详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中的有关章节和马成生《容与堂本〈水浒〉李卓吾评非叶昼伪托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15) 在对于“容本”和“袁本”真伪的考辨时,人们都无法完全解释两种评本有着相同内容这一现象。或认为此乃后出的“袁本”参阅了“容本”,并将“容本”内容有所择用所致。此说粗看似属有理,但两种本子的出版相隔不长,按当时的出版刊刻条件,此种现象似不可能出现。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底本可资参考、模仿。
(16) 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本。
(17) 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忠义水浒全书》明万历三十九年袁无涯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