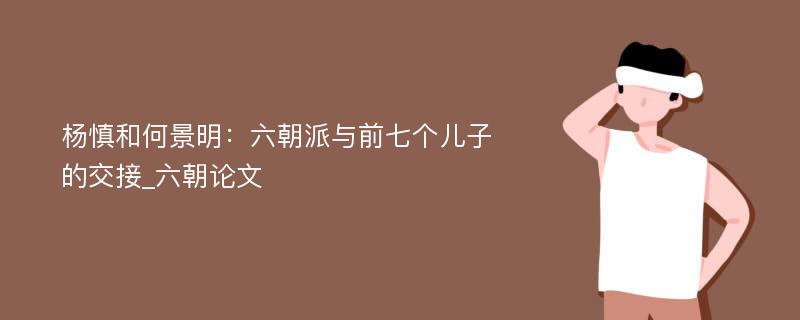
杨慎与何景明:六朝派与前七子的交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七子论文,何景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491(2012)03-0054-05
杨慎为六朝派领袖①,而何景明为前七子派领袖。二人在弘治、正德年间,同居京城,颇有交游。考察两人的诗学关系,有助于理解前七子派的转变和六朝派的兴起等重大问题。
李梦阳是前七子派前期的领袖,何景明是前七子派后期的领袖。但杨慎与李梦阳的直接交游较少,而与何景明的交游较为频繁。因此,探究六朝派与前七子派的关系,应从杨慎与何景明的交往入手。
两人有学术的交流。杨慎《丹铅总录·地理类》卷二云: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骆谷,从洋入东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所从皆殊。旧志谓首尾一谷,非是。其栈道有四出:从成和阶文出者为沓中阴平道,邓艾伐蜀由之;从两当出者为故道,汉高帝攻陈仓由之;从褒凤出者为今连云栈道,汉王之南郑由之;从城固洋县出者,为斜骆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关南之险阨,攻取所从来固矣。旧志云:骆谷、傥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1]
杨认同并推衍何“三谷四道”之说。何景明著《三秦志》当在任陕西提学副使之后,即正德十三年(1518)之后。此条材料并不是杨、何直接交往的证据,但可以看出杨慎对何景明的关注。
两人也有诗文的唱和。《升庵集》卷三十载《无题丁丑岁同何仲默张愈光陶良伯作追录于此》诗。丁丑岁系正德十二年。张愈光,名含,为“杨门六子”之首。陶良伯,名骥,华亭人,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进士,正德七年任礼部员外郎。与何景明、边贡、陆深等前七子派人物和杨慎、张含等六朝派人物均有交往。惜何、杨集中未载其他交游诗文,仅略知正德中何杨两人的交游圈有张含、薛蕙、陶骥等人,而其中,杨、薛、张均为此后的六朝派主将。可见,正德六年以后,为官京师的何景明除与李东阳茶陵派圈子交游外,还同杨慎、薛蕙“六朝派”圈子交游,而此时,前七子派主要成员仅何氏一人留守京城。茶陵派、前七子派、六朝派在此时耦合。不难想像,何景明应该受到六朝派的影响。另外,杨慎《升庵玉堂集》卷一载《狼山凯歌》,有方豪评语,云:“此为词苑一时擅场,惟何仲默十二首可与并传。”[2](P222)可见,杨慎似乎在此时文坛上已颇有诗名,间或与何景明并提。
而两人更多的是诗艺的探讨。《升庵诗话》“荀子解诗”条云:
予尝爱荀子解诗《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贰以周行。”深得诗人之心矣。小序以为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为文王朝会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却陟岗饮酒,携仆望岨,虽托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原诗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岗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若后世诗词所谓“计程应说到梁州”、“计程应说到常山”之意耳。曾与何仲默说及此,仲默大称赏,以为千古之奇。又语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诗,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从毛郑可也。”[3](附录一)
杨慎对《诗经·卷耳》的解说,颇得何景明的称赏,是为杨、何直接交往的证明。若何言“以为千古之奇”,则揄扬太过,杨慎似有借何景明之话自我吹嘘之嫌,不过事当实有。《升庵诗话》“帆字音”条云: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风也。舟幔则平声,使风则去声,盖动静之异也。刘熙《释名》曰:“随风张幔曰帆。”《注》:去声。《广韵》曰:“张布障风曰帆,音与梵同。”《左传·宣十三年》注:“拨斾投衡上,使不帆风。”谓车斾之受风若舟帆之帆风也。舟帆之帆,平声,帆风之帆,去声。《疏》云:“帆是扇风之名。”孙绰子曰:“动不中理,若帆舟而无柁。”《南史》:“因风帆上,前后连烟。”《荆州记》云:“洞庭湖庙神能使湖中分风而帆南北。”晋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诗》,又有《还都帆诗》,谢灵运有《游赤石进帆海诗》,刘孝威有《帆渡吉阳洲诗》。《选诗》“无因下征帆”,徐陵诗“南茨大麓,北帆清湘”,刘删诗“回舻乘派水,举帆逐分风”,张曲江诗“征鞍税北渚,归帆指南陲”,张燕公诗“离魂似征帆,常往帝乡飞”,赵冬曦诗“帝城驰梦想,归帆满风飚”,杜诗“浦帆晨初发”,韩退之诗“无因帆江水”,包何诗“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孟浩然诗“岭北回征帆,巴东问故人”,徐安身诗“暮雨衣犹湿,春风帆正开”。近苏州刻孟诗改“征帆”为“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锦帆’亦改曰‘锦棹’,可乎?”盖浅学妄改,非初误也。[3](附录一)
杨慎精于音韵,此条系杨与何讨论字音。证帆字音,举20余条例证,可见杨慎好博习气。最后又借何景明之语以自重。由上两例可知,杨、何谈诗之深细。
总之,正德期间,六朝派主将杨慎与七子派孤军何景明在学术、诗歌等方面颇多交流,可称诗友。
上文所举均为意见相同者,意见不同的争论,则更有价值。《升庵诗话》“莲花诗”条云:
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洲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3](P532)
宋有无好诗,是争论的焦点。何景明宋无诗观点,见于其《杂言十首》其十,云:
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4](卷三十八)
其意诗至宋而亡,此观点过于绝对。至于何景明对宋诗的具体看法,见其《与李空同论诗书》,云:
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4](卷三十二)
对宋诗、元诗均持批评态度。对宋诗的具体批评又透过批评李梦阳诗体现出来:
试取丙寅间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后之作,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读之若摇鞞铎耳。[4](卷三十二)
丙寅即正德元年,“丙寅间作”是指李梦阳于正德元年前后在京城所作之诗,“尚中金石”,颇有盛唐之气象。而“间入于宋”则指其正德六年任江西提学副使以后之诗,特点是“辞艰”、“意苦”、“色黯”、“理慢”,也就是“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之意,简意之,就是“宋诗谈理”,与此相对是“唐诗工词”[4](卷三十四)。因此,何景明是从文学审美的特点出发来否定宋诗。杨慎批评何景明“宋无诗”观点的策略是“宋有唐诗”,并未能根本上驳倒何氏“宋无诗”论,但却体现出杨氏博学通贯的诗学思想。关于何、杨论争,张含是完全站在杨慎一边,他对宋诗还有一层意见,可能也代表了杨慎的想法:
余昔论诗于仲默。彼曰:“行空之马,必服衔控,高才之诗必准古则。”予曰:“九方堙之识马,不知毛色牝牡,得其神而已,诗贵乎神,奚贵于古体之同乎。”
宋人转移机轴,言自成家,何则于古而入,有言曰宋无诗。[5](卷六)
张含主张“诗贵乎神”,而反对僵化的拟古思想,而这正中前七子派之弊。七子派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而将其他各代之诗一概抹杀,此为不学之弊。杨慎、张含等六朝派的主张,有异于此,承李东阳意见而来,是学古而不拟于古。虽然六朝派学诗宗旨在于六朝初唐,但并不否定它代之诗,主张博学众体。从这个思想出发,张含给予宋诗以肯定的评价。
因此,我们认为六朝派文学理论通过批判前七子派,而表现出相对通达的特点,为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何景明可能并未公开接受杨慎对“宋无诗”论的批评,但李东阳、杨慎等人“学古而不拟古”的观念,却对何有所影响。我们拿代表何景明思想转变的文本《与李空同论诗书》试作分析。此书当作于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三年之间。书云:
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仆之愚也。……
体物杂撰,言辞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尔。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词有高下,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后取则,既主曹刘阮陆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诗坛,何以为千载独步也?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上考古圣立言,中征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比空同尝称陆谢,仆参其作,陆诗语俳体不俳也,谢则体语俱俳矣,未可以其语似,遂得并例也。故法同则语不必同矣。仆观尧舜周孔子思孟氏之书,皆不相沿袭,而相发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广,此实圣圣传授之心也。后世俗儒专守训诂,执其一说,终身弗解,相传之意背矣。今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隉。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4](卷三十二)
何氏自认与李为诗的区别在于:李是拟古(“刻意古范,铸形宿镆”),何是学古(“富于材积”,“不仿形迹”)。“学古”的目的何在?学古不是求同(“例而同之”,“例其同曲”),而是要“领会神情”,以“舍筏达岸”,即“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至“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同上),所谓成自家之面目。对比何景明同六朝派争论时的言论(如“贵于古体之同”),已有较大的变化。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何景明受到了李东阳、杨慎等人的影响。又可说明,何李论争在何杨论诗之后。
但是,何氏思想与杨慎等还是有很大不同。第一,博学通贯思想不同。何景明的学古是有限制的,就诗歌而论,仍持“诗亡”论,即古诗亡于谢(灵运)(“诗弱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近诗亡于宋(“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宋无诗”)。这个思想颇有割裂不学之弊,与杨慎等辨尽诸家、博学众体说有异。第二,取法的典范不同。何景明古体汉魏,取“曹(植)刘(桢)”,稍延及“阮(籍)陆(机)”;近体盛唐,专取“李杜”。而杨慎于汉魏盛唐之外,还宗尚六朝初唐,又欲打通古体、近体之鸿沟。取法对象不同,其审美理想亦有不同。
不过,似乎是随着同杨慎、薛蕙等人深入交往之后,何景明对六朝初唐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升庵诗话》“黄鹤楼诗”条云:
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为第一。二诗未易优劣,或以问予,予曰:“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以画家法论之,沈诗披麻皴,崔诗大斧劈皴也。”[3](P168)
由“近日”一句可知,此事发生在正德时期的京城。何景明同薛蕙取初唐诗人沈佺期一诗为唐人七律第一,沈诗意蕴深密,与崔诗的盛唐气象异趣,表明何景明已关注初唐诗。这与前七派的宗旨稍左,颇与薛蕙、杨慎等人打成一片。又《升庵诗话》“萤诗”条,先迻录唐代刘禹锡、宋代张文潜两首萤诗②,作为前代萤诗的典范。接下来,分别列举自己和何景明的萤诗③。最后,议论道:
何仲默枕籍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如此篇,“明珠按剑”及“鲲鹏斥鷃”,皆与流萤无交涉,可以知诗之难矣。[3](P303)
杨慎想要说明的,主要有二个意思:其一,何景明学作六朝初唐体诗,是受杨慎、薛蕙的影响。何景明《明月》、《流萤》二篇均为歌行体、咏物、寓男女相思之情、流丽婉转,正是典型的初唐体诗。其二,但是,何景明写的六朝初唐体诗,如《流萤篇》,并不如自己。毕竟何专力学的是杜诗,六朝初唐诗乃偶一为之,而自己写的六朝初唐体诗才是当行。杨慎的《流萤篇》作于戍滇之后,晚于何作。则杨慎争胜之意显然,门派的意识也是显然的。我们再看何景明在京城创作的《明月篇》,其自序云: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暇日为此篇,意调若仿佛四子。而才质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词芜紊,无复统饬,姑录之以俟审声者裁割焉。[4](卷十四)
此序表明何景明诗学思想之转变,由专宗杜甫而兼及四子,有意补习汉魏至唐初诗歌之课。其分析杜诗的缺失:一是“调失流转”而不可歌,二是罕言夫妇,而缺“风人之义”。当然,杜诗并不能包治百病,四子自有不可替代之价值。何景明的意见得到六朝派人物的肯定。张含跋《华烛引又别拟制一篇》云:
六朝初唐之作绝响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尝云,三百篇首雎鸠,六义首乎风,唐初四子音节往往可歌,而病子美缺风人之义。盖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萤》诸篇拟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太史公增损梁简文《华烛引》一篇,又别拟作一篇。此二篇者,幽情发乎藻绘,天机荡于灵聪,宛焉永明、大同之声调,不杂垂拱、景云以后之语言。外史小子含缓读七八过,飘飘然有凌云之思。洒然独醒,不觉骨戛青玉,身坐紫府也。噫!吾与古人交久矣,吾与仙人游久矣。安得起仲默九原而共赏之耶。张含跋。[6](卷十三)
永明(案:齐武帝年号)、大同(案:梁武帝年号)指代六朝诗,垂拱(案:唐武后年号)、景云(案:唐睿宗年号),指代初唐诗。张含虽然肯定何《明月篇序》所言为名言,但于其实作,却有微词。同杨慎《华烛引》两篇相比,极赞后者,以为是六朝初唐绝响后的继响,欲树立六朝初唐派之正宗地位。颇可玩味。
从杨慎、张含事后叙述来看,均采取相似的策略,即以何景明为竞争对手,欲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压倒对方。最后,往往有可惜何氏已逝,不然定会叹服之类的话。这些都表明杨慎、张含争取六朝初唐体正宗的意图,可见其立派意识颇为强烈。也说明杨慎谪戍云南后,六朝初唐派当已成立。不过,杨慎、张含还是给予了何景明足够的尊重,将他当作文字之友。《升庵集》卷三十二有《存殁绝句八首》,怀念八位亡友,其一为何景明,诗云:
何逊重泉别,范云清泪多。他年淮隐处,肠断八公歌。
杨慎以何比何逊,以己比范云,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慨。
总之,正是由于何李两人积极深入的争论,双方均受益匪浅。一方面,何景明受杨慎等人影响,转而学习六朝初唐,美学宗尚由沉着向流转变换,最终形成“俊逸”之诗风[7](卷八),且为何李之争之动因。另一方面,正德期间,何景明已是成名人物,而杨慎、薛蕙适为后进,杨、薛借与何论争而欲扬其本派之旨,借与何争胜而欲立本派之名,在京城是如此,在云南也是如此;在何生前是如此,在何死后也是如此。
从交游来看,杨、薛与李疏而与何亲。因此,六朝派与七子派颇有纠葛。而其策略是贬李褒何,以此可以理解薛蕙“粗豪不解李空同,俊逸怜何大复”的宗派意义。六朝派就是在与前七派的纠葛中形成和发展的。
注释:
①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父廷和,弘治、嘉靖两朝首辅。杨慎24岁中状元,授编修。37岁因“议大礼”案,谪戍云南,死于戍所。他是明代学术大家,以博学著称。杨慎为明代六朝派领袖,见拙作《明代六朝派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6年2期。
②即唐刘禹锡《秋萤引》,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纷纶辉映半明灭,金炉星喷灯花发。露华洗濯清风吹,攒茅不定招摇垂。高丽罘罳过蛛网,斜历璇题舞罗幌。襮衣楼上拂香裙,承露台前转仙掌。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辨鲁鱼。行子东山起征思,中郎骑省悲秋气。铜雀人归自入帘,长门帐空来照泪。谁言向晦常自明,儿童走步娇女争。天生有光非自衒,远近低昂暗先遍。撮蚊妖鸟亦夜飞,翅如车轮人不见。”又宋张文潜《熠燿行》,云:“碧梧含风夏夜清,林塘五月初飞萤。翠屏玉簟起凉意,一点秋心从此生。方池水深凉雨集,上下辉辉乱凝碧。幸因帘卷到华堂,不畏人惊照瑶席。汉宫千门连万户,夜夜萤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盘月中露。银阙茫茫玉漏迟,年年为尔足愁思。长门怨妾不成寐,团扇美人还赋诗。避暑风廊人语俏,阑下扑来罗扇小。已投幽室夜分明,更伴残星天未晓。君不见建章宫殿洛阳西,破瓦颓垣今古悲。荒榛芜草无人迹,只有秋来熠燿飞。”
③即杨慎《流萤篇》,云:“沉沉雁沼郁栖连,隐隐龙宫熠耀然。濛晴零雨东山下,转薰风南陆边。可怜合晕辉玄夜,可惜纷华簇绛天。绛天玄夜景微茫,冰簟银床漏未央。谁家院落非天烛,何处园林不夜光。夜光瀼露洒天烛,凉氛泻阴火遥穿。翡翠帘流星,近度鸳鸯瓦。此时蟋蟀罢宵征,此际蜩螗停沸声。长门团扇班姬闼,阿房卷衣秦后屏。苏妇下机妆不理,卓女当垆酒半醒。为见流萤思远道,为感流年惜芳草。暝看双星炯不眠,晓望长河白如扫。荡子从军向月支,闺人对影滞秋期。蚕书宛转连环字,雁帛殷勤织锦诗。愿得逢君拾光彩,不教贱妾敛愁眉。”又何仲默《流萤篇》云:“广储六月清无暑,流萤暗逐薰风举。始见昏连万户星,更看夜照千门雨。千门万户竞高低,拂槛萦廊乱复齐。碧莎映水光初迥,绿柳栖烟影乍迷。水光烟影飞还歇,肯使炎精易沦灭。带火终须避太阳,含辉却自亲流月。长信宫中一叶秋,玉阶金阁见萤流。贵嫔罗扇开香匣,侍女珠帘卷画楼。谁家怨妇缝缣素,当窗忽见流萤度。蟋蟀床空宝瑟寒,鸳鸯机暗孤灯暮。萤飞萤度自年年,却笑明珠按剑前。莫言腐草无生意,莫道寒灰不再然。还将斥鷃鹍鹏语,三复庄生第一篇。”案:此诗收《大复集》卷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