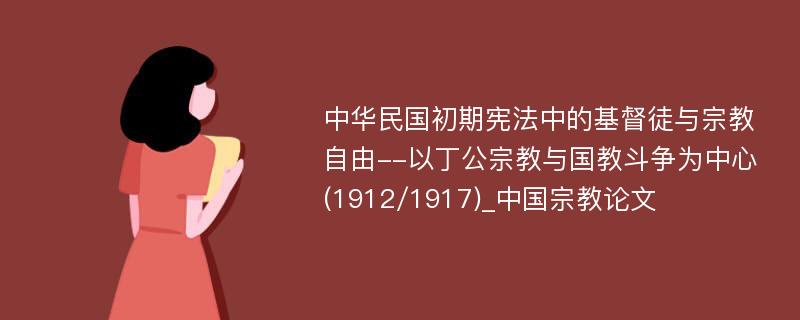
基督徒与民初宪法上的信教自由——以定孔教为国教之争为中心(1912—191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国教论文,基督徒论文,之争论文,宪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是现代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它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革命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宗教乃个人心灵的事情,属于私人领域。信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任何公共权力不得加以干涉。相反,国家机构应给其以法律上的保障。同时,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信教自由也是西方国家处理教争的经验结果。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多教并存,互相争执,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宗教战争,给国家和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信教自由的提出和确立,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这也多为后来支持和提倡信教自由者所反复强调。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王权与教权相互提携和支持,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信教自由,是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以及中国基督徒队伍的壮大与自觉而发端的。同时,清王朝在危机中追求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则为其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契机。1901年,清政府预备实行“新政”,并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旅美华民耶稣教联会陈翰芬、刘维硅、梁廷美等人上书考察大臣,请求为“永息教案,潜消外患”,“许宗教自由列于宪法,以崇政体而保民安。”[1]这大概是近代中国史上最早的信教自由请愿。1908年,清政府准备实行宪政,并于1910年在北京召开了资政院会议。与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相伴,1910年,许子玉、诚静怡、俞国桢、刘芳等人发起宗教自由请愿会,请求在宪法中规定宗教自由,如此“上可以助国势之安,永息教祸;下可以造民生之福,浚沦性灵。”[2]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推翻,该请愿也因此而中断。
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3]在中国历史上,信教自由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得以确立,并由此取得了法律上的保障。此后,孙中山先生又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允诺中华民国保证公民的信教自由权利(注:孙中山先生的论述可参见《在广州耶稣教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在法教堂欢迎会的演说》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0—361页,第446—447页,第568—569页。)。袁世凯上台后也答应在全国将实行信教自由[4]。约法上的规定以及最高元首的承诺无疑为信教自由的实施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然而,此后的经验却表明这些承诺和保证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民初由定孔教为国教问题而引发的信教自由之争即因此兴起。
1912年10月,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5],是为民初尊孔复古潮流第一声嘹亮的号角。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命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返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国民关于祀孔的意见,“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5]同年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认为:“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6]9月9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致电国务院、参众两院及各省都督、民政长、议会,支持陈焕章等人的主张,要求定孔教为国教[7]。这最终在宪法起草会议中达至高潮。
宪法起草委员于大纲十二条议毕后,尚有陈铭枢提出孔教应否于宪法中定为国教之议案。汪荣宝、向乃祺赞成。朱兆莘则提出:“以孔教为国家教化之大本”。黄赞元提议:“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风化大本。”何雯、徐镜心、伍朝枢、汪彭年、卢天游、谷钟秀等反对。表决结果不能成立,该问题被打消。等二读会结束,汪荣宝又动议于十九条下加一第二项:“国民教育以孔子教义为大本”,蓝公武以为不如改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陈铭枢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之大本。”孙润宇主张“伦理之大本”改为“修身之大本。”朱兆莘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大本。”陈善、黄云鹏等赞成。张耀曾、吴宗慈、何雯、汪彭年等反对。表决数次均无结果,最终互相让步,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通过。此即为“中华民国宪法史上教争之发轫”也[8]。
际此信教自由面临危机之时刻,中华基督徒奋而起之,再接晚清宗教自由请愿之大旗,成为了此次斗争的主要力量。北京的基督教会(指基督新教)率先发起组织,后各教相继加入,共同组成“宗教联合请愿团”,以“请愿信教自由,不定国教,并防杜一切妨碍各教平等之法律”为宗旨。陈请国会与政府,慎守临时约法规定,维持信教自由,使各教均为平等,不容一教于宪法上偏有轻重,不得于行政司法上对各教稍有轩轾[9]。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各教会,或联合请愿,或派代表谒见总统、副总统、总理以及两院议员,积极努力,不取得信教自由誓不罢休。这直接执掣了国教案的推行,加剧了宪法起草委员们的激烈争论。国教案在一片反对声中步履维艰。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称:信教自由为万国通例,中华民国由五族共同组成,其历史习惯各不相同,宗教信仰也很难一致,因此,“自未便特定国教,致戾群情”。“至于宗教崇尚,仍听人民自由。”[10]国教案被打消,但草案中之十九条二项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基督徒的请愿活动本不应结束,然而,一方面由于请愿直接目的的实现,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会,竭力推动帝制,宪法会议被中断,民初的信教自由之争也由此暂告一段落。
二
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不遂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下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对1913年的宪法草案进行审议。前此争论不休的国教与信教自由问题再次被点起,基督徒的请愿活动也由此被引向高潮。信教自由会即是其中的中心组织。
1916年11月,信教自由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总机关设于中央公园内,前司法次长徐谦被公推为会长[11]。该会以“永久保持中华民国人民,在宪法上有完全信教自由”为宗旨,定名为“信教自由会”。总事务所设于北京,并在各地设分事务所。规定:“中华民国已成年之男子及女子,无论信教与否,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均得为本会会员。”[12]总事务所干事会分为四部:总务部、交际部、文书部和会计部。四部设总干事一人,每部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无定额。徐谦任总干事兼交际部主任,其他各部主任分别为雍涛、马良和魏丕治。分事务所之组织,由设立之处自定;大会由总事务所或分事务所于必要时招集;干事会由各部联合议定;会费由干事量力捐助,并得自由募集;会费须存储于可靠的银行,由总干事负责保管[12]。
信教自由会成立以后,开会演说,拍电投函,布告宗旨,极力鼓吹,并向各地发出公函,请速成立分会,以联合请愿。随着各地分会的设立,信教自由会日益庞大,会务日趋繁杂。而且,鉴于各宗教团体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办事很难统一进行。因此,基督教(指基督新教)方面遂有人提议各宗教团体分头进行,每周举行一次大会,以保持行动一致。各方面赞同后,信教自由会即分为三部进行:总机关仍设于公园,称为“信教自由总会”;公教(即天主教)方面,称为“信教自由会公教部”;基督教(指基督新教)方面则称为“信教自由会基督教之部”;其他宗教团体则构成第三部[11]。
总会的活动主要有:(1)召集大会。每周由总会约请各教领袖会集一次,由各部报告各自的情况,共同讨论决定后,仍分头去做。(2)选派代表晋谒总统。这总共有两次:第一次由天主教、基督教各选二人,基督教方面为黄瑞祥和诚静怡,天主教代表为艾达天和英实夫;第二次由公、耶、回、东等教各派一人,分别为徐风人、艾达天、王浩然、容耀舫等。两次谒见,总统表示信教自由会请愿理由充足,并请将该会主张条陈国会,由国会裁定。就个人方面而言,则难于为力。“由知总统对于此举,大致赞成。”(3)联络两院议员。信教自由会成立以来,各宗教领袖,或单独晋谒,或偕同拜访两院议员,使议员得以熟悉了解信教自由会所持之理由。议员中,“单其具世界眼光,因是赞成此主张者,几达三百人,相继入会为会员者,亦复不鲜。”[11]
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之部则尤为活跃。自各宗教分进以来,北京基督教会领袖公推诚静怡为该部主任,借北京中华基督教会为通信机关。直、鲁、奉、晋、豫、鄂、陕、蜀等省,相继成立分会约二十余处。其他未组建分会各处,也多表示赞同。其活动主要有:(1)派代表外出。该部为了征集多数人的意见,以求各省教会协力进行,遂由北京教会领袖中选出李引之、曾洞忱、谷子容、孟省吾、史焕臣等人,分赴山西、奉天、山东、通州、河南等地,进行鼓吹宣传。(2)选派驻京代表。与上一活动相应,南方成立的政教分离请愿团也派黄瑞祥、梅云英、罗运炎、聂承益、余士廉等代表北上投书国会,请愿政教分离,同在京的各教会领袖共同努力斗争。(3)发收函电、印件及捐款等。该部先后拍发各省教会电报四十余通,快信九十余件,印刷件万余张,并印刷热心信徒及赞成信教自由者著作论说三十余种。主任诚静怡将关于请愿种种手续及情况随时汇集,以《请愿自由近讯》为名,印刷分送各省教会。而且,他们还将各省寄来的电文印刷,按两院议员寓所逐家邮寄,以保证议员能够看到。最后,自成立至最终获胜,该部共收到捐款洋一千三百余元[11]。
信教自由会的思想,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从消极的一面讲,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从积极的一面讲,则是对信教自由的坚持和争取。在不同的场合,信教自由会的侧重间有不同,然而这两个方面实乃一体两翼,相互提携。坚持信教自由,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主要原因;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则是争取信教自由的现实途径。说到底,定孔教为国教有碍于公民的信教自由;要坚持信教自由,就必须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二者相互对立,不可同时并存。试观信教自由会的论述,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教争与信教自由。参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基督徒认识到,信教自由是对残酷的宗教战争进行反思的结果。信教自由会在宣言书中指出:欧洲中古史上的宗教战争,导致各国纷乱,人民颠沛流离,其情境可谓触目惊心。“然后于战争之余生,群相警悟,乃知非信教自由,不能弥人类之争,而保安宁之福。于是确定于宪法,为诸大自由之一。而宗教战争,自是不复再作。盖于创巨痛深之余,而后乃得之也。”至于美、日等国,则信教自由是国民的重要自由之一,不得妄加干涉。而且,这两国也是多教并存,“与其大纷争之后,而使之自由,毋宁先许其自由,而弥其纷争也”。满清政府,尊崇王室,排斥外族,导致民族相争,教案层出不穷,并由此而引起列强干涉,割地赔款。尤其是1900年的庚子之乱,更使中华民族几近亡国灭种的边缘。民国成立,信教自由在约法上得以确立,“此不徒尊重国民之自由,且免国内教争之惨祸”,此后五载之内,教案几将在中国绝迹。“是故夺国民信教之自由者,满清之所以亡。而予国民以信教自由者,民国之所以兴也”。因此,请诸君“慎勿削减此宝贵之自由,蹈欧洲宗教战争之覆辙,酿近代庚子之拳祸,乱吾可爱之民国,而授列强以宰制之机也。”[13]
(二)国教与五族共和。北京信教自由总会在为国教问题敬告诸大议员书中指出:所谓国教者,一国之教也。无论满汉蒙回藏,凡隶属中华民国、得以称为中华民国公民者,俱在此国字范围之内,亦即都在此国教所概括之中。“夫以共和国家,而行宗教专制,微论各教人民,抵死不从,惟问其与共和原理,不大相悖反耶?”它驳斥那种坚持信教自由与国教并存的调剂方法,认为中华民国乃五族各教共和以成,在约法上无种族阶级宗教区别,一律均为平等。各教人民,本不需要一种调剂,才得为完全国民。“且使宪法规定孔教为国教,则各教人民,在根本大法上,已经判分阶级,欲求平等,其可得乎?”[14]《各省基督教会请愿书》一文则指出:“共和国无论何一宗教,俱不得立为国教。盖有一国教,即破坏共和。显然有国教非国教之区别,有区别即生离心,有离心即启争端,有争端即陷于分崩离析之祸矣”[15]。参议员马君武说得更清楚:西藏蒙古与中国之联合,不仅仅在于武力,而且在于宗教之包容。元清历史,潦然可证。“今忽以孔子之道,载于宪法,强其服从,予恐宪法朝布,蒙藏夕去,即不然,因此‘一句话’,促蒙藏全部之解体”[16]。
(三)孔子之道与国民教育。这大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国民基本权利的角度讲,是否可以孔子之道为国民修身大本;一是从孔子之道本身来讲,能否以它作为国民修身之大本。相比而言,前者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后者多由前一问题引出,是对前一命题的佐证。信教自由会请愿书指出:“居今日之域,中国立政体制,无论如何,决无强迫人民信仰之理由,即人民亦无服从一教一家师说之义务”。国民教育乃一国人民不可缺少之教育,缺则不足为国民。而且,国民既有五族,教育即应分为五教。五族之语言文字不同,蒙、藏、伊、犁、回等,至今仍不用孔子之文,怎能强之以孔子之道呢?而且,五教之源流也各不相同,又怎能以一教之道强迫他们必从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一教之道,枭食其他各教,其可哉?”[17]与此同时,孔子之道本身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受到质疑。该文指出:孔子学说启称帝之野心,生排外之拳祸,导致列强干涉,革命蜂起。而且,孔子之道中含有迷信思想,“处科学之世,而落人后,是犹以教育之方针断送国民,为奴为隶。”[17]
(四)信教自由与公民权利。信教自由会的论述,最终归结到公民的信教自由权这一问题上来。自一开始,它即以“永久保持中华民国人民,在宪法上有完全信教自由”为宗旨,以“信教自由会”相标称。那么,何谓信教自由,约法上之信教自由又当作何解呢?
所谓信教自由,从字面上解,“不过有宗教之信仰者,得择其所崇拜之教而信之,不受何等干涉。即无宗教之信仰者,亦应任他人择其所崇拜之教而信之,而不加以何等干涉。”[13]“夫信教自由云者,自由各信其教之谓。即其人于教无所信,亦不能限制之,使失其自由。此世界各国宪法之原理也。”[13]
从本质上讲,则信教自由的含义在于:宗教信仰乃个人良心上的事情,政府不得干预。由马相伯起草的《信教自由会约法上之信教自由解》一文对这一问题做了较具体的说明:
“信心者,以按良心而有不信。不信某教规,不从某教礼,则国法国俗,不得强其信从。信教者,以研宗教而有所信,信其教规,从其教礼,则国法国俗,不得禁其信从。简单言之,凡涉有宗教意味者,不信不强,所信不禁。一切宗教,皆不信,对于宪法无罪也。始信甲者,继信乙,对于宪法无罪也。此之谓宪法上信教自由。对于良心,有罪无罪,此幽独功夫,无关宪法。譬之人或济贫而意在诱淫,于良心有罪矣,于宪法则一无罪也。故无论是宗教非宗教,及自问是独一无二之真宗教。但以宪法言,信与不信,皆自由也,国法国俗,皆不得干涉之。”[18]
区分良心上之罪与宪法上之罪,亦并区分神圣世界的法与世俗世界的法的不同,并由此各向划分自己的所属范围,这正好是对现代政教关系基本蕴义的确切理解和把握。基督徒对信教自由的认知无疑是处于当时最先进水平之列的。
此外,基督徒关于信教自由的论述,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关系的论述;一是对信教自由与中国传统意义上宽泛的宗教自由的区别。
《各省基督教会请愿书》一文明确指出:坚持信教自由,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它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1)从国家礼制方面言,我国改建共和,袁世凯等非但不废除祭天祀孔等专制时代之弊政,反而变本加厉,有碍于信教自由的原则;(2)从国家学校而言,基督徒有捐输之义务,但却因为学校拜孔之规定而不得受国家教育,是为对信教自由之大破坏;(3)从国家财用而言,人民公财自当人民公用,“若以国家之公财,供一宗教人之私用”,则不仅两受其害,而且全国亦因此而受累[15]。该文主要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对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但并没有理清二者在逻辑上的直接相关性,自是一种缺憾。然而,它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并指出二者之间某种难分彼此的亲密关系,这无疑是触到了近代政教关系的某些内容,是为一种认识上之进步。
公教人士马相伯对另一问题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意义。针对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并存、今日信佛而明日敬道的现象,马相伯指出:“自由云者,非一无所信,件件都信由我;非信也可,不信也可;非信张信李,由我改变,教门不一,我信一门,便干涉他人,既得其真,可不劝化他人之谓也。”[19]此前他也曾指出:信教自由,“非今日进孔教,明日入道教,异日改投佛教,又奉耶教,渺渺茫茫,不知归向之谓也。……夫信教自由,非从俗之谓也。”[19]人“不得真宗教则已,既得之,不能由我信或不信,不得由我今日信某教,明日信某教也”[19]。马相伯的论述固然有捍卫其公教信仰的成份在里面,然而他却点出了信教自由的一大重要内容:自由并不是放任,相反,它却内含对某一宗教虔诚信奉的蕴义。这对克服在信教自由理解上的含混、区分信教自由与中国传统意义上宽泛的宗教自由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基督徒既抱定必胜之决心,力争完全之信教自由。然而,反对一方的势力也不甘示弱。如诚静怡所言,对宪法草案的重新审订,“为以前斗争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契机。坚信信教自由原则的人获得了为删除那引起反对的条款而斗争的机会。而希望看到孔教定为国教的人则同样得到了为在宪法中加入新的条款而战斗的机遇。”[20]几乎在信教自由会成立的同时,孔教会方面也成立了国教维持会等组织,并再次提出了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甚至要求删除草案中关于信教自由的规定。双方竭力鼓吹自己的观点,各相拉拢支持者,在多方面展开了旗鼓相当的较量。斗争的白热化则体现在宪法会议中多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中。
1916年9月5日,宪法会议正式开幕。8日,由提案人朱兆莘说明第十九条二项之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是为初读阶段之主要审议内容。后由于有人再次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对十九条二项的审议随之转化为对国教案的讨论。在初读阶段,这主要有两次会议,分别于1916年12月27日及1917年1月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上,提案人王敬芳解释增加国教的问题,认为我国自古至今,之所以能维持不堕,实赖孔教潜移默化之力。我国名义上虽无国教,而文化礼教则均以孔子之垂训为依归。因此,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孙光庭等赞成此项提案,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无教争,自不必引外国之教训为杞忧。何雯及朱某则反对,认为中华民国成自五族,法律上既属平等,在信仰上当然自由。第二次会议,王葆真力呈中国无规定国教之必要,认为以之定为专章,加入宪法,其弊必不可言。孙光庭以我国与他国国情不同相驳斥。王葆真则举德国的例子再反驳,认为我国今日之政体与孔子之宗旨不符,倘定为国教,定有人利用此来推翻共和。后将“以孔教为国教,仍许信教自由”进行表决,结果在场人数519人,赞成票255张,反对票264张,均不满三分之二的法数,因此都不能成立[21]。
自1917年1月26日起,会议进入二读阶段,分别于2月2日、5日、7日、9日讨论孔教问题。会议中,由于陈光寿提出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关系密切,主张合并讨论,经会议议决后实行,因此这两个问题遂合而为一。到9日集体表决之时,议员们共提出九种修正案,分别为:孙光庭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依历史习惯,以孔子之教为国教”;张琴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以固有之孔教为国教,其他各宗教之传布,均以法律保护之”;陈善修正案:“将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第二项一并删除”;布尔格特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以孔子之教为国教,至满蒙回藏人民,亦得各依其向来所习惯之教为宗教”;魏肇文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子之道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刘恩格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子及其他各教之自由,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李文治修正案:“赞成规定孔教为国教”;瞿富文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旧有之信仰,以孔子之教为国教,有信仰其他宗教者,亦听其自由”;易宗夔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教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会议依次对这九种修正案及原案两条付诸表决,均不足三分之二的法数,以致此项议案几乎被废除。后又有李景濂与秦广礼两项提案,但均未获通过。最后,议长声明,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另付审议,会议暂告结束[22]。
1917年4月30日,宪法会议对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二项进行三读。邵瑞彭提出于第十一条后加一项:“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孔子之道须崇敬之”。因附议者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为议题。陈景南提出:“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孔教及其他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其尊孔典礼别以法律定之”。讨论中,除参议员焦易堂反对原案第十一条、王泽颁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外,叶夏声、吴宗慈、褚辅成等均赞成第十一条,反对第十九条二项。后以各修正案分别提付表决,均未能通过。最后以刘恩格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付表决,赞成者293人,也不足三分之二的法数。有人提起反正表决,反对者113人,不足三分之一的人数,即证明前次表决已获通过。但仍有人提出异议,试图推翻表决结果,会场顿时秩序大乱。议长宣布审议结果应报告大会,遂散会。5月14日再次开会,汤松年、陈景南、蒋羲明三人提出修正案,但均未能通过。最后再以刘恩格修正案付表决,以483票赞成通过。议长宣布:本条通过,第十九条二项当然打消[23]。由此,第十一条与第十九条二项的审议,以国教案失败、信教自由的确立而告终。
5月15日,信教自由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青年会讲堂举行,庆祝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除报告成绩、总结经验外,一项重要议题为《信教自由会永久保存案》。会议中,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信教自由在宪法上已得完全保存,妨碍信教自由之条件也已经完全打消,本会目的已达,因此信教自由会自无继续存在之必要;另一种则认为,信教自由虽已在宪法上确定,但孔教的支持者必不肯善罢甘休。我们请愿无非是为了保护信教自由,而孔教徒则意在遏阻其他宗教之自由。而且中国政变无常,很难防其不借题发挥,刚刚过去的这番争论即是明证。因此,信教自由会有永久保存之理由。最后,第二种意见得到大多数赞成通过。翌日,选举职员,曾洞忱当选为会长,刘馨庭与徐季龙为副会长,其他职员也都由票选产生。17日,信教自由会在北京美以美会礼拜堂举行庆成大会,到会人数约两千余人。徐季龙主持开会,马相伯、诚静怡等人相继演说。最后,会议在高呼三声“信教自由万岁”中解散。信教自由会作为永久性机构成立[11]。
三
请愿成功,信教自由在宪法上得以确立,这可谓是近代中国宗教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件。它从多方面促进了中国政教关系的现代演变:
第一,对封建王朝统治下政教合一制度的突破。杨庆坤指出:“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宗教一直支持政府,给统治集团以超自然的认可,成为加强传统的价值工具,以维持伦理道德秩序。而中国政府为保证从宗教那里得到需要的支持,同时也想减低宗教机构对政治权力的竞争,则对宗教信仰和机构加以严格的控制。”[24]这可谓是对中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经典论述。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一方面可以解脱各宗教沉重的政治神学负担,促成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另一方面则可以解除政府机构对各宗教的直接干预,让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事情,并给其以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和保障。这最终打破了皇朝体制下教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局面,开启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先河,是为中国政教关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第二,对传教条约保护下非正常政教关系的改变。近代中国政教关系的一大怪相在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纠葛以及“宗教问题的政治转化。”[25]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以及“教民”凌驾于中国政府和法律之上,形成一种“政受制于教”[26]的政教关系模式。传教问题不再是“民间的事务”,甚至不属于中国的“内政”,而是“国与国间的国际政治事务。”[27]同时,“教民”又因为与传统思想文化不合而产生的“轻视与敌视”,成为了一种“次文化。”[28]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替代了条约对传教自由的规定,将宗教问题统一到中国政治的范围内来,基督徒也由此实现了从“教民”到“公民”的身份转换,取得了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可。这是结束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维护中国政治自主,更是将中国宗教问题合法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政教关系现代递嬗的另一条主线。
第三,信教自由在民初宪法上的确立,对于中国政教关系史的另一大重要含义在于,它既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赖于皇权的恩赐,也不像近代社会那样是帝国主义枪炮的威胁,而是通过国会这一现代议政机关以及议会的合法程序而实现的。斗争双方,无论是孔教还是基督教方面,都在场外极力鼓吹,向总统、国会上书请愿,然而却没有直接介入国会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是由议员们亲自讨论、投票而达成的。在民初政局动荡、民主共和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信教自由问题却能在议会中通过合法程序而实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政府的弱势,另一方面,则也是民国宪政(尽管是表面性的)在宗教这一问题上的具体体现。通过请愿来争取合法权利,通过议会来解决争端,通过宪法来制定规则,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信教自由在宪法上的确立,是民初宪政运作中的一朵奇葩。
最后,客观地讲,这些新的转变又是不能予以过高估计的。尽管基督徒的努力为这一问题的达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袁世凯死后权力中心分散、利益取向转移以及因分赃而引起的混乱政局的结果。基督徒自身即对这一问题有所承认。从当时双方争论的情况来看,的确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基督徒是靠了“上帝”的保佑才得以侥幸得胜的。信教自由固然是写在宪法草案上了,然而在民国继续演绎的动荡中,这一规定又能担当多久呢?远的不说,不久国会再次被解散,直到1923年宪法才得以正式公布。而且,在“训政”的旗号下,国民政府一直对基督教百般限制,信教自由很难得到实际的贯彻。信教自由在近代中国的历程,仍旧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③关于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杨庆坤先生的全面论述是:“认可功能、政府控制宗教的企图以及不时爆发的宗教对控制的反抗和宗教在反对政治权力斗争中的积极参与,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政治作用的特征。”见C.K.Young,Religionin Chinese Socitey,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ly,Los Angeles,1961,p105.另外,其他对中国传统政教关系的研究,可参何光沪:《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76—202页;黄心川:《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第七章第二节:王权下的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2—255页等。
标签:中国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中华民国大总统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宗教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