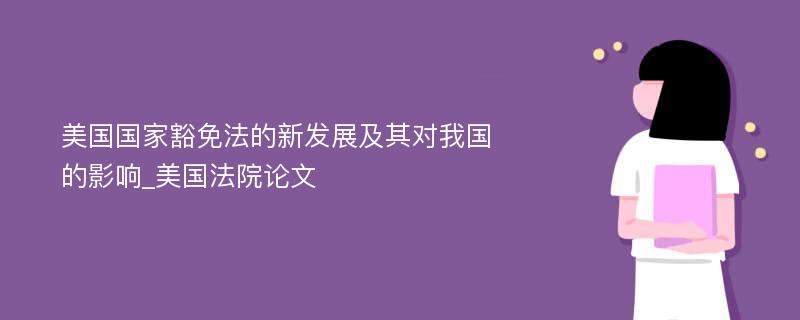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新发展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7)06-0805-05
一、美国国家豁免法新发展之一:国有企业子公司豁免主体地位的否认
1976年出台的《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以下简称FSIA)是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核心和基础。该法规定,在美国法院享有主权豁免的“国家”包括外国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外国国家的机构或部门。“外国国家的机构或部门”又被定义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实体:(1)是独立的法人、公司或其他;(2)是外国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或者大部分股权或其他所有权权益属于外国国家或地方政府;(3)不是美国公民,也不依任何第三国法律建立。根据上述规定,商业目的的国有企业也属于国家豁免主体的范围。但FSIA对以下问题未作回答;如果一个企业的股权或其他所有权权益不直接属于外国国家,而是由另一个国有企业所有,这个企业能否被认定为国家豁免主体?换言之,国有企业拥有大部分股权或其他所有权权益的子公司是否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享有与其母公司同样的待遇?这就是所谓的“层级问题”(Issue of Tiering)。
因为对FSIA条文的理解迥异,不同法庭对“层级问题”的回答截然不同。比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坚持文义解释,认为既然国会立法时没有在“大部分股权或其他所有权权益属于外国国家或地方政府”之后加上“或外国国家的机构或部门”这一用语,法院就不能进行扩大解释;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则依据目的解释方法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美国法院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持续了整整26年,互相矛盾的判决层出不穷,直至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在“Dole食品公司案”中首次就“层级问题”作出权威性阐述。
最高法院基本上采用了文义解释方法,同时借助公司法上关于公司结构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它指出既然FSIA的立法者选用了“股权”、“独立法人”等正式的公司法概念,就说明他们了解公司法原则,并且是以之为依据选择立法用语的;而美国公司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司与其股东是互相独立的实体,股东拥有其股权,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公司的资产,股东因此对公司的子公司并不拥有股权或其他所有权权益。由此可见:外国国家对其拥有股权的公司的子公司并不拥有股权,国有企业的子公司不符合FSIA关于国家豁免主体构成要件的要求。
目的解释的拥护者认为,以上论述是“没必要的技术性解读”,因为就FSIA的目的而言,公司组织结构只是形式问题,无关实质。客观地说,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确实与美国国家豁免法一贯遵循的职能主义立场不符。“职能主义”主要以“行为性质”作为判断豁免的标准,在国家豁免主体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泛,不同于主要以实体的法律特征作为豁免标准的“结构主义”[1](第148-156页)。美国是适用职能主义最彻底的国家,而在本案的审理中,最高法院对豁免主体内部结构和法律特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等保护的政策考虑:因为欧洲国家绝大多数采用“结构主义”立场,美国企业不论是国家直属企业还是国企子公司,都不可能在这些国家获得国家豁免主体资格,所以,美国最高法院也没有选择对本国法上的国家豁免主体范围进行扩大解释。
二、美国国家豁免法新发展之二:不溯及既往规则的颠覆
美国国家豁免法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2](第344页)。1816-1952年,美国法院一般遵循绝对豁免原则,即主权国家及其财产,不论行为及财产的性质如何,都在其他国家国内法院免受司法管辖,除非该国自愿放弃这种豁免。1952年美国国务院对司法部发出“泰特公函”,阐述了“限制豁免”的新政策:国家豁免仅针对主权性的公行为(jure imperii),而不针对私行为(jure gestionis),从而开启了美国的限制豁免主义时代。1976年,限制豁免主义的法典化成果《外国主权豁免法》(FSZA)出台。而当外国政府因FSZA出台之前(尤其是绝对豁免主义时期)发生的行为被诉时,FSZA溯及既往与否往往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但该法并未对其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中国在海外被诉的早期案例中,“湖广铁路债券案”堪称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一起。因为“湖广铁路债券”的发行日(1911年)与到期日(1951年)都处在美国的“绝对豁免主义时代”,审理该案的阿拉巴马州北区地方法院认为:中国政府在行为时有理由相信,支配中美两国及两国公民之间关系的,应当是当时国际通行的“绝对豁免原则”;中国无法预料它将因为债券事宜被卷入美国法院的诉讼,而本案原告的先辈们在购买湖广铁路债券时,也不可能期待通过在美国诉讼实现债券利益;既然FSIA对中国的先前权利有影响,而FSIA的条文和立法历史又不支持FSIA的回溯适用,那么FSIA应当是没有溯及力的,法院不能依据FSIA确立对本案的管辖权。第11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阿州地方法院的判决。“FSIA不溯及既往”从此也成为美国各地法院面对同类案件时的普遍主张[3](第192页)。
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纳粹劫掠艺术品案”的判决颠覆了上述做法。最高法院认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为了避免当事人赖以塑造其行为的法律规范发生不必要的“事后”改变,但外国主权豁免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外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依赖美国政府关于豁免的承诺来调整它们的行为,这种豁免其实反映的是当下的政治现实和关系,它的目的是给予外国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一些“现在的”保护,使它们免受诉讼的不便,这是一种“礼让”的表示,而非“权利”的赋予。否认“法不溯及既往”这项一般原则的约束力之后,最高法院又从FSIA的立法用语、整体结构和立法目标等各方面找到了国会意图让FSIA回溯适用的“清晰证据”,最后得出FSIA可适用于本案的结论。
纳粹劫掠艺术品案的判决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赞美该案显示了美国法制的力量,使二战时期人道主义灾难的受害者在有生之年终能获得救济;而反对者认为该案体现了“司法保护原告维护平等的冲动”和“司法激进主义”,超越了司法应有的界限,使外国国家面对大量被诉的威胁,也使美国在外交上限于不利局面。
三、美国国家豁免法新发展对中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一)国有企业子公司豁免主体地位的否认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中国台湾企业“中华航空公司”在美被诉的案例非常直接地反映了Dole食品公司案的影响。华航的控股人“中国航空发展基金”是FSIA上的“国家机构”,所以在案件之初华航被认定为国家豁免主体。然而,该案审理期间恰逢Dole食品公司案的判决出台,“国家机构”下属实体的国家豁免主体地位被否认,华航随即失去了国家豁免主体资格。
虽然国家豁免主体资格仅是获得豁免的第一步,但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空头衔。如果国家豁免主体从事商业活动,它的商业活动必须发生在美国,或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与境外的商业活动有充分联系,或在美国境外的商业活动对美国境内产生直接影响,美国法院才对该主体有管辖权。相对于普通主体而言,这个条件是比较严格的。换句话说,国家豁免主体即使从事商业活动,其行为置于美国法院管辖之下的风险也比普通主体小。即使最终没有获得豁免,国家豁免主体资格本身也会对豁免主体在案件中的权利产生一些实质性影响。比如,FSIA规定对国家豁免主体禁止惩罚性赔偿;国家豁免案件采用无陪审团审判方式(一般认为无陪审团审判的法庭审判更快捷更专业);国家豁免案件由联邦法院审判(一般认为联邦法院比地方法院对待外国当事人更公正更有经验);国家豁免主体在送达、审判地、关联财产、判决执行等方面,都有比较有利的程序性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讲,国有企业子公司失去国家豁免主体资格等于在美国法院得到的保护相对削弱。
虽然Dole食品公司案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子公司在美国法院获得的保护相对削弱,但同类案件判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将会增强。这对中国国企子公司来说十分有利。2001年的五金矿产公司案和2002年的中国银行案都涉及“无陪审团审判”问题。五金矿产公司的子公司希望法院采用陪审团审判方式,因此主张自己不是国家豁免主体;中国银行的子公司则希望法院驳回原告的陪审团审判请求,因而主张自己具有国家豁免主体资格。最后,二者的主张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案例是由同一个法院在间隔仅一年时间内审理的,而且判决都对中方当事人不利。Dole食品公司案的判决杜绝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中国国有企业将可以更准确的预见判决结果,从而选择适当的诉讼策略。
(二)不溯及既往规则的颠覆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1949年解放前中国旧政府曾经在海外留下大量恶债未予清偿,很多老债券的所有者看到湖广铁路债券案中“FSIA不溯及既往”的规则已被推翻,便闻风而动,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要求清偿旧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刚刚作出判决的莫里斯案。“FSIA不溯及既往”规则的改变,确实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因所谓“陈年老账”在美国法院被诉的几率提高,但在大多数案件中,外国政府只是失去了一个最初级的抗辩理由,FSIA以及相关法律仍然有很多其他的制度和规则可资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国政府在美国被滥诉的困扰。
首先,原告必须证明FSIA上的某项豁免例外成立,美国法院才能获得对外国政府的管辖权。“莫里斯案”的原告依据FSIA的商业例外条款要求中国政府清偿袁世凯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法院认为中国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商业行为并未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所以,虽然“FSIA溯及适用”,但是因为商业例外不适用,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其次,外国政府可援引国家行为理论、非方便法院原则或政治问题原则来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在以日本政府为被告的“慰安妇案”中,法院最初以“FSIA不溯及既往”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但在纳粹劫掠艺术品案之后,法院又对该案进行了改判。改判时法院仍然驳回了原告起诉,但此次适用的是政治问题原则:“慰安妇案”涉及二战后和平条约的解释,属于法院不宜管辖的政治问题。
再次,在美国法院起诉外国国家豁免主体之前,原告必须首先“用尽本地救济”,只有在本地救济明显不足以保护原告利益时,才能获得美国法院的支持。在纳粹劫掠艺术品案之后,美国法院很可能更倾向于严格适用“用尽本地救济原则”,用来平衡“FSIA溯及既往”给外国政府造成的困扰。
然后,在纳粹劫掠艺术品案判决之前,美国国务院曾通过“法庭之友陈述”方式建议法院认定FSIA不溯及既往,但最高法院认为这是关于法律解释的纯司法问题,因而没有接受国务院的建议。但最高法院同时指出,如果国务院就某个具体个案提出国家利益声明,法院将把它视为行政机构对外交政策上特殊问题作出的判断,遵循国务院的意见。可见,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国务院就个案问题向法院发出国家利益声明也是外国政府谋求豁免的一种可行途径。
最后,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曾签订过一揽子解决旧债的条约,在莫里斯案中,中国政府曾提出过这一主张,但法院在用“无直接影响”为由判定中国政府胜诉以后,就没有继续讨论该条约的问题。但这一条约的存在仍不失为面对旧债诉案纠缠时一个很好的抗辩理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FSIA回溯适用不一定在每个个案中都有损外国国家的利益。如纳粹劫掠艺术品案之后改判的“法国铁路公司案”,适用FSIA就对被告法国铁路公司更为有利。
(三)中国在美被诉的总体形势及应对策略
截至2007年6月,中国在美被诉并涉及国家豁免问题的案例已达23件,其中1980-1989年3件,1990-1999年5件,2000-2007年激增到15件。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此类案件仍在审理之中。此类案例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待不同性质的案件,中国应当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国在美被诉的案件出现了一些典型的政治性问题,特别是法轮功组织在美国法院对中国政府官员掀起的诉案绵延不绝,甚至已有美国法院对此类案件作出了对中国的不利判决。对于此类案件,我国政府绝不能接受美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早期的湖广铁路债券案,虽然法院判决中国政府胜诉的理由是“FSIA不溯及既往”,但事实上该案的胜诉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外交压力的结果。在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今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所有国家被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典型的政治性案件,还是应当运用外交途径解决。虽然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都竭力促成国家豁免问题的纯司法化,但是在具体个案中,法院判决还是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立场的影响。在纳粹劫掠艺术品案中,最高法院明确表示愿意遵循国务院在具体问题上作出的政府利益声明,这足以作为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交涉的依据。
中国在美被诉案件激增,最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加深。对待商业纠纷案件,中方被告应当充分利用国家豁免主体资格,积极主张豁免。前面提到,作为遵循“职能主义”最彻底的国家,美国国家豁免法关于豁免主体的规定非常宽泛,外国国有企业也可以被赋予国家豁免主体地位。比起完全否认外国国有企业豁免地位的欧洲国家来说,外国国有企业在美国国家豁免法上的地位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争取尽可能有利的程序性权利和最终的豁免结果。事实上,我国在美被诉的国有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最后都获得了管辖豁免。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可为后来者借鉴。除了国有企业被诉的案件以外,还有一些我国地方政府被诉案件也牵涉到商业纠纷。这类案件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国政府现在对此类案件基本上也选择了积极应诉的方式,这是一条解决问题的较好途径。如果具体个案牵涉到重大国家经济利益或社会问题,也可以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国务院向法院提出国家利益声明。
最后,对于因“FSIA溯及既往”激起的“陈年旧案”,应当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本文前面提及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如对豁免例外的限制、国家行为理论、非方便法院原则、政治问题原则、用尽本地救济原则、中美之间的双边条约等,都可作为中国政府面对历史性案件时摆脱美国法院管辖的方式。一旦此类案件的胜诉率低得以实现,被“FSIA溯及既往”这一新规则激起的诉讼动力就会自然减退。
收稿日期:2007-08-08
标签: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