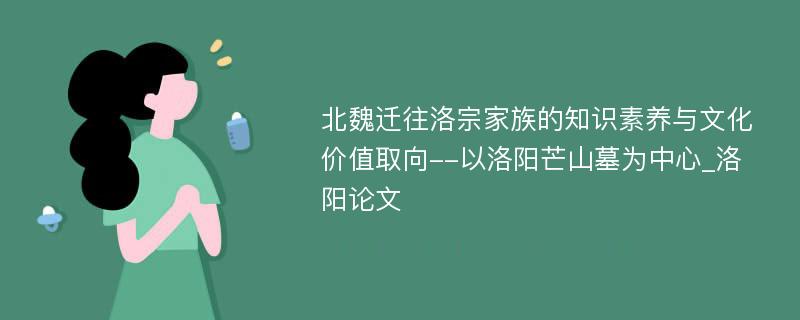
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室论文,洛阳论文,北魏论文,墓志论文,素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1-0184-06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帝国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拓跋社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方面,以拓跋宗室①为代表的广大胡人勋贵汉化及文士化进程加速,不仅知识素养和气质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其行为旨趣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向汉族名士靠拢。前人对此多有阐述②,这些成果着重探讨宗室群体认知水准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观,但并未触及结构类型和价值取向等本质性因素。故笔者试图结合中古文化恢弘激荡的总体背景,在剖析宗室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找寻其在心态导向上的趋势性特征,进而管窥五六世纪交替时期河洛地区文化交融的实景。记录此项内容的传世文献比较有限,洛阳邙山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墓志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标榜墓主高洁文雅的华美言辞正可汇聚成规律性线索。这些镌刻在石材上的宝贵文字,或是逝者生前的真实写照,或是倾心向往、不懈追求的目标,褪去文学色彩后具有十足的说服力,人们常说的“树碑立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北魏洛阳的多元性文化生态 中古时期,国家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不安。不过,文化事业却因此摆脱官方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桎梏,焕发蓬勃生机,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文化高峰。中古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而地域差别是其建构的基础。[1]20在宏观角度,华夏与异域文明冲突,华夏内部又有南北学术的争衡。不同文化因素相互摩擦碰撞,共同演绎出绚烂多彩的景象。居于“天下正中”的古都洛阳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成为文化交流的舞台,置身其间者受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深深打上多元文化的烙印。 北朝时期的洛阳是南北拉锯的战略缓冲区,这里不只是兵戎相见的战场,更多的时候还是南北学风接触的场所。中古文化层面的南北界限本指黄河而言,魏晋洛阳是玄学等时尚新风的发祥地,而同期的河北、江南则处于相对保守、滞后的状态,魏晋新学只是后来随着东晋南徙而播迁江左。[2]361故下文使用的专词“河北学术”兼指北方学术,“江左新风”则是魏晋河洛新学。关于南北学术的差异,时人即有评述。《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隋书》卷七五《儒林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又《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唐长孺先生据此推断,以河北学术为主体的北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大成的郑玄之学为宗”;南迁的河洛名士则世传时尚玄学。[3]226综合各家之说,南北文化之辨可归纳为五点:在传承关系上,北学是汉代经学的孑遗,南学则是魏晋新风的延续;在研究对象上,北学专攻儒家经典,南学则弃儒入玄;在学术风格上,北学艰深刻板、渊综广博,南学清新洒脱、超然自我;在治学方法上,北学讲求名物的训诂考释,南学侧重义理的诠释阐发;在价值导向上,北学务实进取,南学任诞虚无。当然,文化之间并无森严壁垒,所以这只是个因势而异的柔性原则罢了。不过,借助这套标准判读北魏洛阳的文化格局,对迁洛宗室的文化素养及取向进行粗略的定性分析还是大体可行的。 应该说,北魏洛阳文化的主旋律是南北学术之融汇,而佛教等异域元素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妙和弦。这种立体式的层叠架构在杨衒之生动描绘洛阳风貌的名著《洛阳伽蓝记》中有集中展现。北方学术的经学传统得到始终如一的尊重,该书卷三《城南·报德寺》:“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这些石经均以古拙字体书写,作为汉代学术的结晶专供洛阳士子观摩,学术魅力丝毫未减。江左新风此时风靡洛阳,不乏以名士自居者。卷二《城东·景宁寺》载,弘农士族杨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为时羁。乐水爱山,好游林泽。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我们知道,弘农杨氏乃北方儒学强宗,但从杨元慎的性情好尚来看,他又具备了魏晋名士的风范,这绝非个别案例,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状况。宗教的崛起是洛阳文化的显著特征,上至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皆崇信佛法,正可谓“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卷四《城西·融觉寺》载,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于禅学,讲《涅槃》《花严》,僧徒千人”。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已成为铸炼河北学术、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的大熔炉。北魏宗室久居洛阳,长期耳濡目染,势必形成相应的文化特质。 二、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 掌握知识是综合素质的基础,决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举止和发展程度。宗室是拓跋政权的管理者和上流社会的主体,其知识素养关乎重大。据史料记载,北魏后期的宗室造就大批知识精英,其活动遍及各个文化领域,整体能力水平照比前期大有改观。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提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曲折的历程。比较而言,早期宗室愚鲁粗俗、格调低下。典型事例如《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毗陵王顺传》:“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拓跋)顺独坐寐欠申,不顾而唾。”同书卷五九《刘昶传》:“(刘昶)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宗室精通骑射、能征惯战者占据压倒性优势,文士则寥寥无几。相形之下,洛阳时代的宗室有了质的蜕变,邙山墓志中有大量关于迁洛宗室文化素养的记录,内容林林总总,包括研究对象、兴趣爱好、人生态度、治学风格、人际交往、生活式样等。根据前文所述洛阳的学术流派,我们可就其类型细加剥离,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宗室的知识特征,并为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分析奠定基础。 墓志材料中渲染最多的是迁洛宗室对儒学的钟情和对儒家经典的熟稔,这显然受到河北学术的影响。对出身游牧蛮族的拓跋鲜卑而言,要维持长治久安,必须捡拾儒学的利器,儒家经典自然是无法逾越的基本教材。史载,道武帝入主中原之际,便确立了“以经术为先”的国策,并于天兴四年(401)通过恢复释奠礼的方式昭告天下。[4]他还曾咨询朝臣:“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5]卷三三,789儒家经典治国纲领的地位就此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宗室钻研儒学蔚然成风,即便迁都洛阳沐浴时尚,兴致依旧高昂。致力儒学者有元扬“优游典谟之中”[6]《元扬墓志》,75;元秀“栖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薮”[6]《元秀墓志》,131;元显“爰始志学,游心坟典”[6]《元显墓志》,359;元毓“韵致渊凝,性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祐“锐志儒门”[6]《元祐墓志》,107;元晖“长爱儒术”[6]《元晖墓志》,110。宗室经过长期努力,涌现出很多精通儒家经典者。如元悦“六藉五戎,不待匠如自晓”[6]《元悦墓志》,63;元尚之“六艺居心,五礼宅身,论经出俗”[6]《元尚之墓志》,141;元叉“学综坟籍,儒士攸宗”[6]《元叉墓志》,182;元灵曜“该镜众经”[6]《元灵曜墓志》,137;元钦“三坟五典之秘,丱岁已通”[6]《元钦墓志》,249;元子邃“洞观坟籍”[6]《元子邃墓志》,401。迁洛宗室普遍皈依儒教堪称独特的文化景观,因为中古儒学式微,士族名望大多实现玄学化的转变。[7]86北魏宗室却反其道而行之,照旧奉儒学为圭臬,其宗旨是用儒家思想规范宗室言行,强制灌输君臣父子间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这不仅是草原民族统治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也是拓跋族由血亲氏族向宗法制大家族演进的必然举措。墓志还特别强调迁洛宗室对仪礼的掌握。礼是等级社会维护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秩序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外在的仪式程序之总和。儒家格外注重礼的约束作用,讲求克己复礼,承载华夏名教伦常的礼仪,浓缩了儒学的精华,故礼学的精进程度也可作为衡量宗室儒学水平的标尺。我们发现,精通礼学的宗室为数不少。如元绪“偏爱诗礼”[6]《元绪墓志》,53;元秀“尤善礼传”[6]《元秀墓志》,131;元焕“爱诗悦礼”[6]《元焕墓志》,168;元弼“敦诗悦礼”[6]《元弼墓志》,280;元阿耶“观图践礼”[6]《元阿耶墓志》,340;元纯陀“诗书礼辟,经目悉览”[6]《元纯陀墓志》,261。由此可知,宗室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切实践行了儒家贯彻礼法的信条。总而言之,中原传统的儒学是宗室思想意识的主宰,是决定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惯性的内因。 中古时期,儒学是河北学术固守的主阵地,南朝尽管并未完全放弃,但热衷程度和研究水平远不及北方。迁洛宗室专注儒学,表明他们是河北学术的忠实拥趸。且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方面,其与河北学士也最为接近。首先,宗室学问偏重艰深、务求甚解。如元灵曜“该镜众经,深穷隐滞”[6]《元灵曜墓志》,137;元毓“韵致渊凝,性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天穆“八素九区之理,靡不洞其幽源;三坟五典之书,故以极其宗致”[6]《元天穆墓志》,277;元袭“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6]《元袭墓志》,295。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正史中亦有体现,可与墓志相呼应。宗室硕儒元延明风流造次不及同侪,“而稽古淳笃过之”[5]卷二○,530;元顺“笃志爱古”[5]卷一九,481。也就是说,元延明和元顺继承了汉代经学保守严谨的实证主义,而这正是河北学术的本色。其次,宗室学识广博引人瞩目。如元怿“学通诸经,强识博闻,一见不忘。百氏无遗,群言必览”③;元端“五典六经之籍,国策子集之书,一览则执其归,再闻则悟其致”[6]《元端墓志》,233;元赞远“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揽”[6]《元赞远墓志》,309;元子正“搜今阅古,博览群书”[6]《元子正墓志》,246;元子邃“博极古今,洞观坟籍”[6]《元子邃墓志》,401;元熙“好学博通”[6]《元熙墓志》,169;元湛“博读经史”[6]《元湛墓志》,239。传世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元脩义“涉猎书传”[5]卷一九,451;元勰“博综经史”[5]卷二一,571;元略“博洽群书”[8]卷四,224。渊综广博无疑是北方学者的招牌,宗室以此见胜足证其对河北学风的恪守。不过,应当注意到,宗室尽管尊奉河北学术,但并不排斥同期南朝的优秀成果。如元彧“博览群书,不为章句”[5]卷一八,422。唐长孺先生认为,章句训诂是汉代经学的传统,后为北朝经学所承袭;南朝经学则深受魏晋新风的影响,侧重义理的阐发。[3]232据此可知,元彧已经摆脱烦琐枯燥的名物考据,开始趋向南朝追求义解的“约简”之风。此外,经学南宗推崇的某些经典文本也获得宗室的青睐,如元顺“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5]卷一九,481。孝明帝和孝静帝分别师从青齐士族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研习《杜氏春秋》。[5]卷七二,1615《杜氏春秋》是西晋杜预注释的《左传》,盛行于江左,而北方主要流传东汉服虔注。④所以说,江左新风的北渐一改宗室学术僵化呆板的形象,为其增添了新的活力。 江左新风对迁洛宗室影响至深者莫过玄学。玄学兴起于魏晋时期的洛阳,本为现实政治语境下的名实之辩,后经正始名士王弼、何晏等人的改造,引入老庄道家思想,逐渐延伸到自然、名教之争,系统推衍虚玄理论,产生了抽象思辨的味道。玄学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与士族门阀制度相结合,成为名士自我炫耀、博取声誉的资本。实际上,北魏皇族接受玄学甚早,平城时代的献文帝“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5]卷一四,3038。皇帝既好于上,宗室群臣必定群起效仿。迁都洛阳后,宗室对玄学的热忱更加高涨,擅玄谈者比比皆是。如元鸾“虚心玄宗”[6]《元鸾墓志》,46;元显俊“若乃载笑载言,则玄谈雅致”[6]《元显俊墓志》,68;元焕“味道入玄,精若垂帷”[6]《元焕墓志》,168;元彝“清思参玄,高谈自远”[6]《元彝墓志》,226;元湛“玄同阮公”[6]《元湛墓志》,240;元子正“穷玄尽微,义该众妙”[6]《元子正墓志》,246;元袭“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辨类悬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6]《元袭墓志》,295;元显“工名理,好清言”[6]《元显墓志》,360。皇室玄谈方兴未艾,“世宗之在东宫,特加友异,每与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6]《元怿墓志》,172。宗室致力玄学非唯附庸风雅,更重要的是以玄学为媒介拉近与汉人士族的距离,从而跻身名流社交圈,归根结底是要涤荡蛮夷的鄙陋,在政治权力之外获取崇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贵族化的终极目标。与玄学紧密伴随的是放荡不羁、超然洒脱的生活方式和个性气质,宗室在此方面不甘落后。典型事例是元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8]卷四,201。此番风雅不啻当年的竹林七贤。宗室墓志中不乏类似的记载,元扬“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渌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代而同侣”[6]《元扬墓志》,75。元斌“心栖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林潮,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6]《元斌墓志》,140。元钦“秋台引月,春帐来风,琴吐新声,觞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6]《元钦墓志》,250。宗室一如江左名士好宴饮、重结交,游园赏月、觥筹交错间吟诗作赋、抒发胸臆。需要说明的是,宗室在此类活动中能够自觉地以主体身份与汉族士人平等交往,实现了文化角色的历史嬗变。[9] 深刻改变宗室学术面貌的还有江左的文学,东晋南朝的文学盛极一时,北魏孝文帝受此影响大力提倡。[10]特别是在官员铨叙上,文学之士通常备受垂青,此举势必会对宗室文化产生巨大的牵引效用。因此,精通文学成为宗室文化修养的重要环节。如元晖业“亦颇属文”[5]卷一九,447;元脩义“颇有文才”[5]卷一九,451;元勰“雅好属文”[5]卷二一,571;元善见“好文学”[5]卷一二,313;元略“文学优赡”[8]卷四,225;元尚之“属辞韵彩,彪昞离文”[6]《元尚之墓志》,141;元熙“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文艺之美,领袖东观”[6]《元熙墓志》,169;元怿“文华绮赡,下笔成章”[6]《元怿墓志》,172;元祐“游心文苑”[6]《元祐墓志》,107;元固“优游文义”[6]《元固墓志》,211;元炜“雅好斯文”[6]《元炜墓志》,218;元湛“元好文藻,善笔迹,遍长诗咏”[6]《元湛墓志》,239;元子正“雅好文章”[6]《元子正墓志》,246;元馗“文义早著”[6]《元馗墓志》,301;元赞远“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6]《元赞远墓志》,309。另外,宗室精于“文史”者值得关注。如元勰“敦尚文史”[5]卷二一,582;元悌“博览文史”[6]《元悌墓志》,219;元斌“研兹文史”[6]《元斌墓志》,140。胡宝国先生认为,“文史”是南朝文学、史学分离后二者的合称,但仍以文学为重,史学则微不足道。[11]68换言之,“文史”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学问,即广义的文学。事实证明,文学在宗室内部大行其道,竟成为展示文化实力的工具。 由上可知,迁洛宗室往往兼具南北学风,这种特点还体现在他们的书法风格上。六朝时期,书法变成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北魏宗室书家辈出,且书风各异,也可作为研判文化类型的标准。如元举“六书八体,书妙超群,章勾小术,研精出俗”[6]《元举墓志》,215。所谓“六书”,据《汉书》卷三○《艺文志》,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八体”则是《说文解字》中所述古篆的八种书写风格,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表明元举不仅通晓汉字,而且善于书写古朴浑厚的篆书。这种书体曾盛行于北魏上层社会,风格技法严格遵循汉代的传统。[12]421元举师承汉法,无疑属于北方学派。与之类似的是元悌“尤好八体”[6]《元悌墓志》,219。当然也有不同者,如元炜“草隶之工,迈于钟索”[6]《元炜墓志》,218;元显“善草隶”[6]《元显墓》,360。“草隶”是楷书、行书、草书和行草的总称[12]446,这种书体经过晋人钟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的发展上升到艺术高度,并以其清新雅致、秀逸灵动深受江左士夫的喜爱。元炜、元显精于此道,无疑是时尚潮流的追随者。 以上从经学、礼学、玄学、文学和书法五个方面探讨了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构成。不难发现,其中南北差异体现得最为清晰。不过,南北之别毕竟囿于华夏,宗室文化中还包含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元素。中古佛教方兴未艾,宗室是最虔诚信徒群体,精通佛教教义及相关的天竺文化者不绝史乘。如元举“洞兼释氏,备练五明”[6]《元举墓志》,215。元举信奉佛教自不待言,他还熟悉“五明”,即古印度五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⑤,说明他的学识已经超越宗教的局限。此外还有元悦“好读佛经”[5]卷二二,593;元鸾“妙贯佛理”[6]《元鸾墓志》,46;元叉“尤精释义”[6]《元叉墓志》,183;元纯陀“博搜经藏,广通戒律”[6]《元纯陀墓志》,261。宗室学术融入了异域成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 除去先进的华夏和异域文明,拓跋鲜卑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宗室文化体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全面汉化的洛阳时代,这些旧的文化要素也不容抹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尽管文士化是演进的总体趋势,但墓志中崇尚武人气质的现象仍时有出现。如元平“好弓马,蔑浮荣典籍”[6]《元平墓志》,143;元天穆“雄光桀出,武艺超伦,弯弧四石,矢贯七札”[6]《元天穆墓志》,277;元玕“慷慨弓马,慕气终古”[6]《元玕墓志》,315。正史可与之相印证,《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附鸾传》:“(元鸾)以武艺著称。”同书卷一二《孝静帝纪》:“(元善见)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其次,虽有礼法体统的约束,但即兴盘旋歌舞的遗俗始终保留。《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宣忠寺》载,孝庄帝为铲除尔朱荣,遣元徽假托皇子诞生召其入宫,徽从容镇定,“脱荣帽,欢舞盘旋”。宗室来自草原,性情豪爽直率,借助歌舞抒发情感乃为常态。再次,生活方式日趋汉化,但以羊肉、乳酪为主的饮食习惯未有改变。王肃、萧正德等南朝士族北归后因此产生强烈的不适感,还会遭受宗室的刁难奚落,“酪奴”和“水厄”的典故由此产生[8]卷三,147,足见拓跋旧习的顽固性。客观地讲,来自草原的民族风俗的衰减有其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并非完全同步,更不会因猝然变革而消失。 三、北魏迁洛宗室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成因 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整体趋向文士化,单纯武将的比例由建国之初的54%锐减至38%。[13]97与此同时,宗室的行为修养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凸显出多元化特征。具体而言,宗室的知识来源丰富多样,除本民族的固有习俗外,还囊括了中原传统的儒学,魏晋南朝新兴的玄学、文学及异域传播的佛学等。就源流风格来看,既有河北学术的专精广博、严谨务实,又有江左新风的率性任情、洒脱自然;既有草原文化的粗犷豪迈,又有人文宗教的慈悲清静。总之,宗室个体绝非局限于某一特定术业,儒释兼综、礼玄双修、文史荟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前文各条目中所列人物重叠互见便为明证,如元顺、元熙、元勰、元怿、元扬、元尚之、元焕、元叉、元举、元炜、元子正、元钦、元袭、元纯陀、元馗、元赞远、元显、元鸾、元略等人皆具百家之长,是典型的文化综合体。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中古不同文明因素的冲突与融合,而北魏洛阳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分裂与战乱不能真正阻绝文化的沟通,北魏治下的中国北方也就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陈寅恪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吸收整合江左、河西等区域的文物典章,成为中古制度传承的关键枢纽。[1]3这充分说明北魏是中华多元文化实现凝聚的平台。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在这些文化的共同推动下破浪前行的,参与这场历史变革的既有李冲、游明根、高闾等河北学者,也有刘芳、王肃、蒋少游等江左士族,深受改革影响的迁洛宗室因此带有不同文化的印迹。此外,拓跋统治者对各文化支脉没有潜意识的偏见与歧视,使得他们能以宽阔的胸怀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且北魏朝廷采取开明的文教政策,为宗室创造自由的发展空间,任其畅游学海,这是形成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外部保障。 人的知识体系通常是复杂的组合体,各结构要素间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均衡,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者决定了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的取向类型塑造了风格迥异的学术群体。北魏迁洛宗室即是如此,其四大知识要素不可等量齐观,其中河北学术为基础和骨干,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乃时尚装点,草原遗俗则无足轻重。通过梳理材料,我们发现宗室格外在意自身传统旧学的修养,相关记录数量最多,语汇精彩至极,表明底蕴深厚的河北学术是宗室精神世界的绝对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北学术是宗室文化的根底,这种导向驱策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展现出强烈的事功精神。如元纂“每怀济世之经,乃慕刘章之节”[6]《元纂墓志》,175;元诲“少忼慨,有大节,常以功名自许”[6]《元诲墓志》,274。宗室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推崇实际的干才。如元庆智“有几案才”[5]卷一六,394元朗“涉历书记”[5]卷一九,485;元徽“颇有吏才”[5]卷一九,510;元羽“有断狱之称”[5]卷二一,545;元怿“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5]卷二二,591。显然没有受到南朝士族安富尊荣、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习气的熏染。[14]623这令他们更适合担当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据统计,宗室控制从中央到地方近三分之一的实权要职,并且每每出任外藩征伐的主帅,仕宦比率远超任何王朝,堪称政权的坚强柱石。[15]253宗室垂青河北学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的就是河北学士。永嘉乱后,滞留北方的汉人大族被迫与胡人统治者建立合作关系,他们大量进人北魏朝廷供职,顾问应对、出谋划策,典型事例是代人燕凤、许谦、张衮,清河冠族崔玄伯、崔浩父子。至太武帝神麚征士,应征者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勃海高毗、京兆杜铨、赵郡李灵、太原张伟、范阳祖侃、河间邢颖、广平游雅、上谷侯辩等35人俱河北翘楚。[5]卷四八,1078他们与宗室交往频繁,如高允、张伟同任乐安王范从事中郎,高允又任乐平王丕骠骑府参军、秦王翰傅,游雅任东宫少傅,杜铨任宗正卿管理宗室。宗室还跟从河北学者系统学习儒家经典,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书”,尚书左仆射元赞师事常爽。[5]卷八四,1843、1848宗室因此先入为主地奠定了河北学术的牢固基础,诚如钱穆先生所论:“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16]279降至洛阳时代,江左时尚尽管席卷上流社会,但河北学术的主体地位却不容撼动,宗室照旧与北方鸿儒保持密切的联系。《魏书》卷八四《儒林列传》载,刘兰“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徐遵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董征“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孙惠蔚任皇宗博士,教授宗室子弟。可见,宗室对河北学术的认同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这还与北魏特殊的统治形势休戚相关,众所周知,拓跋鲜卑以寡少之旅驾驭幅员辽阔、民户众多的中原地区,宗室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奉行入世哲学的河北学风可使其长久维持进取心和实干性,有助于政权的巩固。 综上所述,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汉化及文士化进程加速,其知识素养和文化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迁洛宗室在经学、礼学、玄学、文学、书法和佛学领域颇多造诣。就其学术源流而言,渊综广博、务实进取的河北学风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超然洒脱、任诞虚玄的江左时尚是为浓重装点,还有以佛教为核心的异域文明和植根北亚草原文化的鲜卑旧俗。这种多元化格局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因素激荡融合的结果,也是北魏统治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之文教政策的集中反映。若进一步抽象概括,宗室的思想观念可视为动态的多元化构造,各组成要素间此消彼长,保持相对的平衡。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变革下,原有的均衡态势就会被打破,新的文化因素夺占主导地位,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则代表着进化阶段和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外在的文化特征。 从根本上说,北魏宗室的文化类型由一元走向多元,是顺应汉人门阀社会,实现自身贵族化蜕变的客观需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让鲜卑族同化于汉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17]25换言之,拓跋族的汉化究其实质是以宗室上流阶层为主导的贵族化。中古贵族固然以累世积淀的阀阅等第为根基,但底蕴深厚的家学门风具备同等重要的象征意义。北魏宗室欲跻身北方精英社交圈,必须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而融汇南北、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乃唯一的选择。 ①“宗室”一词在此专指皇帝的同族。据《魏书》《北史》“宗室列传”的记载,北魏官方以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宗室的范围。 ②相关成果如孙同勋先生《拓拔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宋燕鹏先生《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何德章先生《北魏迁洛后胡人贵族的文士化》,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版;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元氏研究——北朝隋唐时代における鲜卑族の文人士大夫化の一轨迹》,《中世の文物》1993年版。 ③《元怿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清河王怿传》:“(元怿)博涉经史,兼综群言。”可与墓志相印证。 ④《隋书》卷七五《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5页。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载,广宗人潘崇和在洛阳城东昭义里聚众讲授《服氏春秋》。《魏书》卷八四《儒林·徐遵明传》:“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徐)遵明乃往读之。”其在北方受众之广可见一斑。 ⑤五明是梵文Pancavidya的译文,分指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声明是语言、文字的学问,工巧明是各类手工技艺,医方明是医药学和治疗技术,因明相当于逻辑学,内明是佛教、婆罗门教等古印度宗教教义,五明基本涵盖了南亚次大陆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