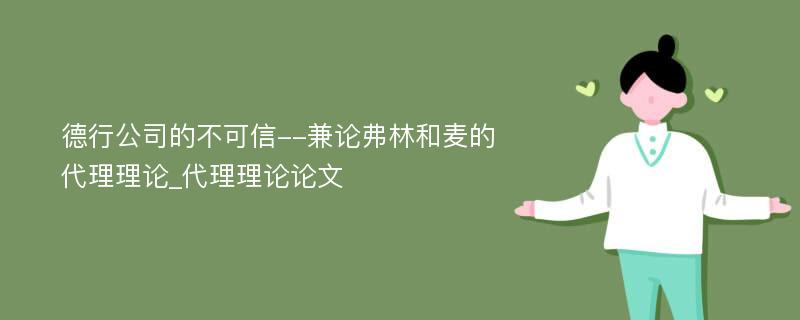
有德行公司的不可信性——兼评弗伦琴和迈的代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琴论文,可信性论文,德行论文,理论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界定公司的道德责任仍然是社会与职业伦理学讨论最广泛的问题之一。正如多数哲学难题一样,两个派别的辩论勾画出这一问题的轮廓。一方面,有许多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企业对社会不承担道德责任,因为公司的主要利益跟股东一样,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这一被人熟知为古典观点的主要支持者。这一观点的主要信条可以从下面的推论得到公式化的表述:
A)企业的决策是由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管理者制定的。
B)股东的主要利益是从所制造的产品获取利润。
C)有关使用公司的利润为社会事业服务的决策超出了企业的角色和股东的利益。
D)所以,公司的责任仅仅是利润最大化。
另一方面,有许多哲学家反对企业只有这种原始责任的观点。反对派的主张是“经济机构确实对社会负有比使利润最大化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领域常常被“一般公司责任”的呼吁所覆没。支持公司对社会负有更多责任的主张有好几种理论模型,代理机构模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理论提出了公司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可以引申出慈善人格理论。虽然迈(Larry May)的观点是作为对弗伦琴(Peter French)观点的批评意见提出的,但它也存在接受一个类似弗伦琴的、狭隘的公司道德生活观的漏洞。
弗伦琴代理理论的出发点是要证明公司负有责任的合理性。这一点是通过运用图表阐述公司内部决策结构是人的理性的创设,并以此将公司塑造成思虑成熟的人完成的。迈不同意弗伦琴关于公司集体有本体论地位的提法,认为公司做出的各种理性决策是通过人完成的;所以从代理角度看集体行动是公司是否讲道德的动因。
我在这篇文章里要做的是:(1)通过重构这两派的论点来讨论这些观点是否能成功地捍卫“公司负有道德责任”的断言;(2)考察公司决策结构的必然性并在概念上判断公司是否可能有道德意识。
公司是否能承担社会责任呢?在从这两种模型的任何一种出发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考虑责任问题所由产生的推定性的社会合同问题,这个问题是“公司是否能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变相说法。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合同是隐含的,即它的特征是隐含性。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两个意在相互满足的人之间存在的已经被人接受的行为模式;就企业而言,有可能在追求与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同时希望为公众利益服务。“企业在彼此竞争着这样做时,以顾客需要的产品与劳务的形式给社会创造了利益,顾客则通过在企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上就业而挣取满足他们欲望的货币购买力。”[1]这种公司与公众之间的一致性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强化。随着公司利润的增长,公众的利益总的来说得到了提高。按照梅尔维·安申(Melvin Anshen)的观点,关于这种进步的指标没有达成明确一致的意见,而企业强调的主要指数是经济增长。结果,那些关于社会性的、由环境污染者造成的生活质量状况降低的各种问题,按照实际成本效应进行估价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在要求企业为环境保护支出费用时,企业能实现利润吗?或者一个公司能否保持在一个满足高薪水要求的状态呢?这里存在违反合同的问题。经济增长指数变成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而其他各种价值观在社会中慢慢地黯淡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各个地方都在使用技术设备,人们对经过加工处理的化学产品与生化药物的需求不断增长,人类无止境地搜寻各种替代能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速满足这些需求而导致的工业副效应始终构成对我们环境的威胁。同时,产品成本不断增加而没有相应的质量提高,企业没能建立公正的就业惯例是对社会更明显的危害。这些问题伤害、玷污了人们对公司的信任感。人们不相信公司有关心公众利益的眼光。
为了缓和公众与企业的这种离异分裂的情势,安申和其他人诉诸社会合同的修改。这将是利用每一方的专业知识而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就企业来说,首先要作的事情是确定为避免各种社会危害(包括企业员工暴露给污染物的健康危险)而引致的成本估算,以及如何运用会计术语衡量花费在这些方面的成本。企业和社会通过协同努力,给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支持而获益。企业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扩展他们的生产能力,培训和雇佣少数弱势群体。这一点能改善现存的各种有损城市景观与风气的状况。第三项要做的事情是成立混合的公私合营公司以代替公众签约方,这样的公司雇佣的员工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等几方订约人,从而双方共同关注的特定需要是一目了然的。
由于这样的合同给公司拥有各种权利与承担各种义务确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它就暗含着企业的道德角色只可能是利润最大化的延伸这样的假设。要使公司的这两种角色彼此相容匹配,就要具备公司采纳道德观念的条件。这两种关于公司代理机构的论证都是一种尝试,试图把公司看作是有道德的公民,以此证明公司的这种延伸角色有其合理性。
弗伦琴是其中一种代理理论的先驱,他论证了公司负有社会责任的合理性。他的理由是:公司决策结构的设计方式就给任何既定的行动提供了行动的方式,并代表了这种方式、为这种方式寻找理性的根据。公司职能部门的安排勾画出了公司决策结构的轮廓,不管这些部门在机能上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行动注定是要和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的决策结构“准许各种事件的限制性转换,这些事件的转换在另一种视域下可以看成是通过显露这些事件的公司特征而把生物学的人(那些在组织机构图表上占据着各种职位的人)的行动视为公司的行动。”[2]这样,按照弗伦琴的观点,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都可以描述成是为公司的理由而付出的行动。“是由与公司的信念孪生的公司愿望所引起的,换言之是和公司的目的有关的行动”[3]
公司的组织机构图是为各种指令所统制的规章制度的有条理排列,这些指令给有关部门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付之于实施的行动遵循的是由公司的决策路径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规章制度。既然公司的各种理性使得公司的各种行为成为必要的,那么就不难推论并赋予公司人的形而上地位,也就是说将公司塑造成讲道德的代理人和命定要承担道德责任的人。这一点给那些谋事于公司职能部门的人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给予了心理上的空间,而无须考虑他们是否与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虽然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信念可以与公司的目标发生分歧,但公司的理性始终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弗伦琴可能的推论是,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作为代理人发挥职能的,应该被认定为是有道德责任的,因为公司的各种理性有其自身的逻辑。
这种代理论证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困境。第一个是公司需要“因理性而行动”的标准提出了一个狭隘的理性模式。就人的代理而言,因理智而行动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行动的理由可能不仅仅是遵循一项既定的政策。比如,给一个人提供贷款用于家庭的杂货店或者出于同情给其提供药店禁售的化学药品。这类因各种情感而发生的作用在这一公司代理模式里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带给他们所担任角色的各种信仰和情感是不可能得到考虑的,因为他发现给人以强制性深刻印象的不是什么“深层基本道理”,而是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条理排列。这个问题根源于这一理论的第二个困境,即未能区分两种类型的“因理性而行动”:(1)经过深思熟虑“有理由去做‘X’”和(2)“按照计划有理由去做‘X’”。
第一个表述式蕴涵着权衡从事一项选择时的信仰和态度。比如,一家烟草公司的产品研究开发部的主管就可能持有与实现本职能部门各种指令相对立的种种理由。在这种意义下,选择一种理由通常寄寓选择本身一种价值观,亦即涉及选择者对其他价值观,诸如尊重生命、尊重正义、富有同情心的各种态度。不论这些价值观对做出抉择的讨论可能施加多大的影响,唯一记录在案的考虑只能是集体的决议。例如,据报导Dow Chemical/Shell Oil为增加水果产量在哥斯达黎加使用二溴氯丙烷(DBCP)控制虫害,结果导致标准水果公司的81位雇工与哥斯达黎加的农民患上了各种疾病,包括不育症。假如Dow Chemical/Shell Oil的某位雇工出于同情,对使用二溴氯丙烷(DBCP)的方案投了反对票,那么这一票因为是同情受害人的选票而不会被记录下来,但公司的政策将依然得到贯彻。在烟草公司事例中,产品研究开发部主管可能同情香烟受害人或者含毒杀虫剂受害者,但他的道德动因会受到另外某个职能部门规定的遏制。他决策所根据的理由是防止不必要的伤害,但从公司政策的角度看那也是“坏的理由”。
就人类的行为而言,一旦酿成错误的后果,良心就会把它内化为懊悔的感情而通过各种道歉、补偿受害人的意愿、以及各种悔过改新的态度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公司选择了有害的行动方式,才将公司的生活与社区公众分割开来,由此也突出了公司不讲道德的惯性。由于公司的组织机构安排缺乏深层的感情向度,它就只能按照线性的、受规则管制的方式行动。简言之,公司的行动不是从各种深思熟虑的理由引申出来的,从而与各种感情对立的矛盾也不会发生。这是更具限制性意义上的“因理由而行动”,它使得弗伦琴所说的那种公司封闭孤立起来,丧失了慷慨、同情的各种机会而只是“在”社区而已。
运用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按照计划有理由去做‘X’”。根据这种解释,不管在达到目的时使用了什么理由,都可以从目标的“到达”证明它是合理的。只要理由所提供的手段和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协调一致的,任何理由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考虑商界所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就可以证明为达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解释代表了弗伦琴所描述的那种公司机构,其判断“好的理由”的标准是它的利润最大化。公司的这种推理不受各种理由之间冲突的影响,那些与利润最大化政策不符合的理由将不是“有生存力的理由”,从而因与公司的制度不协调而得不到考虑。可见,与这些理由连结在一起的唯一价值观是坚持赢利方针的价值观,一个其逻辑在本质上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动机。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当公司未能根据它“知道的”行动时,它就是在无知的状态中行动。确立各种规章制度涉及公司的各个职能部门,而公司的行动后果是由各个职能部门预见的。比如,挑战者火箭上的O型套环。人们知道这些套环是有缺陷的,也知道如果发射失败就会造成几百万元的损失。但是,关于更为普遍的原则—“安全运行”的知识却被忽视了。现在,我们对这种忽视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所造成的结果都非常熟悉。按照弗伦琴的观点,除非这种知识被写进公司政策的基本原理,否则不会表现为行动的一种理由。因此,利润最大化的理由依然是使用O型套环决策的最主要动机。
弗伦琴用以说明问题的公司决策结构,只是为公司始终一贯的各种理由提供了证据,证明公司不能选择所想望目标以外的其它目标。比如,选择任何利润赠予转让的理由。无疑,一家为贫民区公立学校主动提供资金支助的公司可以为自己赢得让人赞许的形象。但即使利润额极其丰厚,财力足以向地方校区做出贡献,公司从容许捐助的利润额中拨出的支助金数量还是在税收起征线以下。这种行动的动机只是为了适应“做生意的价格”,是已经被唤醒的慷慨或慈善的外投。它是一项谨慎的社区计划,不象其它投资那样等待利息收益的回报。客观地描述此类行动,这种决策表现了一种不受道德价值观、社会呼吁与社会判断影响的特征,因为这种决策的反应动机是“装饰门面”,由此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利润。
上述各种决策可能表现为是一个有着各种理由与多重意图的代理人,但就其适用的范围而言都是非常狭隘的代理人。这只是一种类比的代理论,不能保证伦理学家们强加在公司头顶上的形而上地位是合理的。
迈对此观点提出了批评。迈首先是否认公司存在弗伦琴所设想的各种形而上特征。他的观点是公司的决策是董事会会议室将公司各个管理人员的目的进行综合而成的有目的的行动,但这种有目的的行动是错误的。按照迈的观点,这些有目的行动实际上只是替代公司目的的个人意志和目的。“虽然没有一个公司成员需要坚持属于公司的所有目的,公司却不可能持有任何一个最初不是由公司的某个成员所抱有的目的。”[4]所谓公司的各种目的不过是个体成员的各种目的而已。
迈认为公司对每个职员所实施的行动只承担代理上的责任。当公司要求的某项行动未付之实施或者实施时与公司的政策发生偏离,这一点就会得到更确切的表露。公司管理人员行动的失败程度只能由公司负责,因为公司的行动只有通过其成员才能发生,每个成员行动的失败将成为公司的失败,但不是每个成员的行动都必然成为公司的行动。迈提出:如果存在公司代理上的疏忽,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因果关系要素:公司成员受公司的特许或者授权而被赋予了能力或者享有各种便利条件,可以实施有害公众的行为。
第二,过错行为要素:本来有机会预防错误的发生,但却没有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阻止。[5]
迈模型的意图是要为公司承担绝对责任的观点找到一种替代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违反了法律,不是要公司充当挡箭牌承担责任,而是要识别个体罪犯。然而,个人所在的办公室是被占支配地位的公司任务剥夺了公权的地方。决策的流程图规定了行动的计划,公司的区别在于其安排的职能部门是不同的。比如,储蓄贷款机构在其决策结构里将要任命的各种职务就不同于一家生化制药公司或者石油公司。各层管理级别都是由“流程图基本原理”联结起来的。在上述公司代理疏忽发生的两个条件中,任何一条的满足都不一定是由个人直接实施了违法的行为。例如,可能发生下列的情形。一个任职于某家制药公司的产品研究开发部门监管,是处在享有授权的因果关系位置上的,他可能因为一种药品有严重的副作用而建议公司不营销该药品。但是,公司的营销主管却需要抢在其它公司之前将这种有竞争力的药品推销给消费者,他通过投票表决击败产品研发部监管,进而否决了该监管的建议。产品研发部监管的职责是要对各种新产品进行调研,调研的指导原则是为公司服务并符合各种安全标准。营销主管的职责则与公司销售额的衡量有更密切的关系,在营销活动有竞争的情况下就需要尽快采取行动,以新产品树立公司的形象。在此,发生公司代理疏忽的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即研发监管和销售主管都有权阻止或准予药品品质通过检验进入市场。如果不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要保持竞争力和赢利性的话,两人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阻止该药品进入市场的。“代理”疏忽的责任归咎于谁呢?条件满足了,但公司的利润动机宣布了它的无效。
其实,弗伦琴和迈之间的分歧没有初看之下那样大。弗伦琴的观点是公司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迈则认为公司管理人员是公司的代理动因。这意味着什么呢:代理人代表着公司的利益吗?代理人是公司目标的代表吗?代理人是代替公司的人吗?没有公司成员的行动,就没有公司:没有公司,就只有无目标的代理人。在此,他们作为各种代理人和各种角色,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在决策程式里,这种角色的公权被自己与其它角色的更高层关系给剥夺了。比如,他们与董事会、股东利益的关系等。没有董事会与股东的参与,公司管理人员的任何行动都是未决的。这既不是代理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与公司的直接相关性,而是因为公司缺乏占支配地位的任务。最后,针对弗伦琴观点的批判意见也同样适用于迈的代理动因理论。
在上面评述关于公司责任的主要理论中,我已经反复论证:认为公司能够持有道德观念的观点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公司也许是有着各种权利与义务、有模拟人格的人,它们生下来就负有各种法律责任,它们必须清除各种有毒废物排放,遵循公正地雇佣工人的惯例,遵守诚实借贷的原则,服从顾客安全管制条规。除了履行它们的法律责任外,公司不会为了自己的美德而在乎自身的行动是否公正、慷慨和仁慈。它们不可能“说一句善意的话语或者付出人格的感动,明确表现出有人在乎美德,而这样一种表现对于德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6]简言之,公司是作为一个没有感情的、狭隘的理性模子在运转、在经营着为生存与繁荣所必须的各种事务,而不会象“一位一定要拥有美德的人,按事物所必须给予的关心程度关心公共事务”。[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