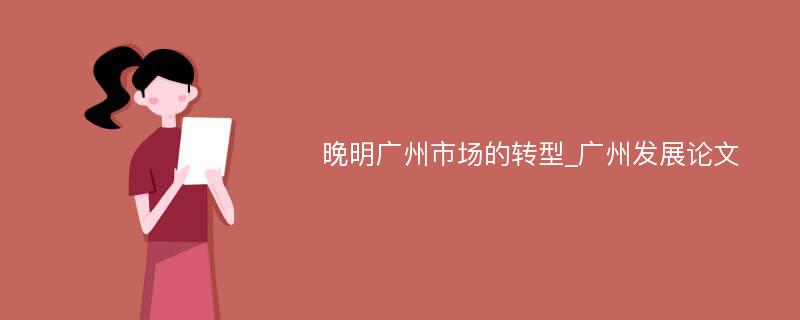
明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后期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之前,广州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特权阶层和富户所集聚的北方各大都会城市,尤其是京师和运河沿岸、长江三角洲都会城市的需要。由于当时广东农村市场的发育水平甚低,广州市场与农村市场的联系并不密切。到了明后期,广州市场开始发生转型,从服务于北方都会城市富人消费的高值奢侈品外贸中心,到兼做岭南经济区中心地转化,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从贡舶到商舶贸易转化
朝贡贸易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周边的国家都以通过朝贡得到回赐的方式进行贸易。从晋代起,南海诸国前来朝贡,皆取道广州。从太康五年到八年(284-287年),扶南、林邑及其他二十余国曾相继前来进贡,以恢复与中国的正常通商关系。据统计,从南朝刘宋永初元年至陈祯明三年(420-589年),林邑、师子、婆皇、盘盘、扶南、于陀利等六国先后派来的朝贡使团便达100次。唐、宋、元三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除接受朝贡外,允许外商前来中国自由贸易。朱明王朝建国后,一改前朝海外贸易自由的方针,实行闭关禁海和备战的海防体制。只有经过钦允朝贡的国家才能前来进行贡舶贸易,贡期和贡舶规模,视朝贡国对中国驯服态度而定。入贡期限一般规定为1至10年一次。来船的艘数与人数,也作不同的规定,一般不超过3艘200人,而且“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在广州设有市舶提举司,负责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的贡舶贸易。从洪武元年至正德四年(1368-1509年),“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
各国来使所带货物,属贡品者加封识,造册报户部,随贡使一起运解京师;附带的货物,先由市舶司按需要收买,余下部分才“许令贸易”。官府名为给价收买,实则未必等价交易,对贡品的回赐更是从怀柔的动机出发。
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起,广州的贸易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官府控制逐渐向民间自由贸易转化。
首先,对贡舶附带的货物实行“抽分制”。据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夷三”记载,惟正德四年(据《武宗实录》卷67记载,此事在正德三年,即1508年为是),该(广东)镇巡等官都御史陈金等题,将暹罗、满刺加国,并吉阐国夷船货物,俱以十抽三。正德十二年(1517年)改为“抽其十二”。这里是说贡舶附带货物,经按成数抽收实物后,允许出卖。“抽分制”是一种征收实物的税饷。税率原为30%,调整为20%。
再有,放松了对贡舶贸易对象、贡期、规模等的控制。正德九年(1514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了收购龙涎香,以满足朝廷的需要, “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冲破了贡期和贡舶规模的限制。尔后,有不属朝贡国者,也假冒他国名前来进行贡舶贸易。例如,葡萄牙便冒充朝贡国要求通市。终经照例抽分后,允许与民间贸易。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贡舶贸易体制已愈来愈不适应双方的需要。如果说从对贡舶贸易控制的放松已见其端倪的话,那么嘉靖年间(1522-1566年)海上走私贸易的盛行更是明显的证据。从明中叶起,东南沿海的居民冲破海禁,百十为群,结伴走私于东南亚各国者日多。嘉靖年间更发展成与官军对抗的连舡结队的武装海商贩运集团。王直、林凤、林道乾等就是当时横行海上的著名武装贩运集团的首领。这种走私在广州市也公然出现。明人霍与瑕在《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中写道:
“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
由此可见,在广州的内地商人也参与了走私活动。走私贸易的盛行,更有力地推动了贡舶制向商舶制转化。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实行“引票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所谓“引票”,即一种出海贸易的通行证。凡持有官府颁发的引票者,可以合法前往海外指定地点贸易。虽然引票制受到指定地点和票额的限制,是有限度的开海贸易之举,但它使原来的走私贸易因领到引票而合法化。
与此同时,对海外来舶,税收方面也从原来的抽分制改为“饷银制”:一是水饷,由抽分制改为“丈抽法”,即通过丈量,按照船的广狭征税,这是征于舶商之税;二是陆饷,即按照货物多寡或价值高低计算而征收的进口税,这是征之于收购进口货物的铺商。税制趋于完善,无疑有利于广州商舶贸易的正常进行。
王临亨在《粤剑编》卷3<志外夷>写道:
“西洋古里(印度西岸科释德),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赉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贸易。”
这是作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从苏州来广州阅狱办理案件时据其所闻所见写下来的,当属可信。从此可见,海外来舶只要交纳税饷后就可入广州贸易。古里商人所赉的“白金”,即白银。南洋、西洋各国,因没有足够的货物和中国进行交易,有时只携带银元前来购物。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美国商人,都是如此。
广州商舶贸易的繁荣,还表现在专设与外商贸易的定期市集。从万历六年到崇祯四年(1578-1631年),为了适应海外商舶采购中国商货的需要,每年夏、冬两季在广州举行定期市集。每次历时数星期,乃至数月不等。岭北各地商人源源运来丝绸等商品,以供外国商人选购。葡萄牙商人是市集上的主要采购者,他们从澳门前来广州,在定期市集上收揽丝货,把其中一部分运往菲律宾出售而大取厚利,另一部分,则运往长崎和印度的果阿。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写道,葡萄牙商人“每年两次到广州去购货。他们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比马尼拉商人(按:指西班牙商人),或我们(指荷兰商人)更多的利润”,颇有垂涎之态。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形式,有贡舶制和商舶制两种类型。贡舶制从以怀柔为主趋向计值贸易,并日渐式微;商舶贸易迅速发展,明后期商舶制终于取代贡舶制成为外贸的主要形式。
二、经营商品从高价奢侈品到民生日用百货
明中叶之前,经广州出品的商货是所谓“随其乡宜以为货”,亦即各地出产的传统的土贡式产品,并不考虑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汉代至明中叶的一千多年间,出口的产品无外乎是丝货、漆器和陶瓷等中国传统名产。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的,“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进口的也是南海沿岸所出产的珍异、犀象、香料之类高值奢侈品。商品结构决定贸易的性质,这种高值奢侈品贸易只为满足少数特权阶层生活的需要,不可能惠及平民百姓。
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东南亚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通过东南亚市场而转运欧美地区,出口的商品不仅需要量大,品种也增多;已经扩及民生日用商品,尤以丝、糖、铁器、陶瓷等为大宗。贸易的对象已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
出口的商品是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据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3,“夷情”上记载:
“东洋贸易,多用丝……回易鹤顶等物;西洋贸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
这里所谓的东洋,主要是指菲律宾。当时马尼拉的生丝市场是太平洋丝路的中转站,对丝货的需求量很大。16世纪末,墨西哥丝织业有14000多人,其需要的原料生丝,就靠广州运往马尼拉丝市,然后由西班牙商人转运供应。全汉升先生经过深入研究,指出江南蚕丝业就是在马尼拉丝市的影响下急速发展起来的。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这一市场取向的刺激下创造出“桑基鱼塘”这一以蚕桑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经营型式,蚕丝业也于此时抬头。明晚期,珠江三角洲所生产的广纱、粤缎为东西二洋所贵。他们奋起急追江南,以力争在马尼拉丝市上占一席之地。其余的产品,如丝绸、糖、果箱、铁器、蒲葵等所谓“广货”,则成为西洋贸易市场的主要商品。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的: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指荷兰)、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
从上可见,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取向,直接影响广州出口商品的结构。产销关系,也从传统的“以产求销”,转为“以销求产”。顺带指出的是,同样是丝货,此时的丝货生产同传统丝货生产已有所不同,它已经不是“因土所宜”的传统土贡式生产,而是趋向专业化,成为广大平民百姓的生计。
广州市场商品结构从高价奢侈品趋向民生日用百货品,从“随其乡宜以为货”到“以市场取向为货”的转变,冲破了传统出口贸易从属于进口贸易的格局,从而使出口贸易取得独立的发展。这就导致广州贸易出超日益加剧,墨西哥、秘鲁的白银便成为这一失衡贸易的补偿。据梁方仲先生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估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的72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这还未包括广东商舶从吕宋等地运回的银元。白银的大量流入,对明后期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庶民海贸商人的兴起与引票制
基于海贸的性质与特点,广州贸易历来皆为官府、势家豪绅所把持。唐代及其之前是由地方帅臣和越族豪酋,宋、元则由官宦豪绅所垄断。明代后期,海外贸易趋向民间,平民百姓充当海商者日益增多。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顾炎武也说:“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懋迁居利。”可见此时的海贸已经不是特权阶层的专利,庶民百姓不仅插足,而且是靠以为生的一种行业。珠江三角洲“望县”之民参与广州海贸固不待言,就是内地商人,尤其闽商、徽商,也前来广州从事外贸活动,“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时人称之为“走广”。据咸丰《顺德县志》卷24<胡平运传>记载:
“闽商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万人。”
这里说的是明末时事。闽商在澳门者已不下万人,在广州的当属不少。又据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记载:
“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
……曰走广。”
因利之所在,“走广”成为时尚。广州南城的濠畔街,是“外省富商”云集, “番夷辐凑”之地。
明代广州牙行商人,因明后期牙行转为承销外国商品的商业团体而成为广州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充牙商者,必系殷富之家,并要彼此互保,经官府批准,发给牙帖,方取得合法资格。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在同外商洽谈贸易中,容易得到比普通商人优惠的价格。为厚利所诱惑,未领到牙帖者,也冒充牙人从中渔利。牙行有客纲、客纪之设。客纲,是由若干牙行结成一纲的纲首,总理该纲行事宜。客纪,即牙行经纪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整顿牙行时, “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据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记载,此时“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从此可见,他们同外商利益攸关,联系密切。他们对广州商业利润的垄断,表明其拥有商业资本之雄厚。牙商的职责比明前期有了扩大。外商货物上岸之前,广州牙商先到船上估价商货,议定税额,并负责征收。他们还负责供给外商船上人员所需的粮食和日用品,从中攫取30%~50%的利润。脱胎于元代舶牙的明代牙商,在明代后期负责管理外商生活,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起的半官方的作用,为后来清代广州特殊的行商制度开启了先河。
广州商人主动地走出去,在东南亚地区开拓市场,他们“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据《马尼拉帆船》一书记载:“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州和澳门。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一些备办货物来广州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内地商人,在夏、冬两季广州定期市集上看到葡萄牙商人运丝货到马尼拉贩卖有利可图时,竟然将卖不出去的货物用自己的船运往海外销售。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有现款购买他们的市镇和海港。……但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就用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
广州商人在国内外已经建立相互联结的网络。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各国时,已经在此居住的华侨为之接应,并准备好回程的商货。据哥尔勒民斯·德·侯德猛《航海日记》记载: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在下港(万丹),“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平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后经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后,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y)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8艘至10艘来航。每船只能装50吨。”
这里没有说明这些船来自中国何处,但当时去万丹的船都是从漳州和广州启航的。当广州商人从海外回到广州时,则有揽头负责接应。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
“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赏其值。”
这里是说,揽头向舶主海商取得银两,用以分发制造服食器物的手工业者,作为预支工本。手工业者再按照揽头所规定的式样、规格,制造产品用来抵偿。
当时的海商已聚集大量的商业资本,据《孔恩文件》第一卷第167页记载,万历四十年(1615年)已出现拥赀达5500英镑至7500英镑的帆船商人,这已接近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赀8100英镑的数额。
从上可见,庶民商人冲破了势家豪绅垄断广州海贸的格局。广州商人不仅主动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而且还建立了国内外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
四、与广州相联系的市场网络变化
随着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市场蜂起。江南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已经很高,开发较晚的岭南地区农村市场也在发育之中,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发育尤其迅速。此时的广州市场同岭北广阔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前述的江南、安徽、福建等地区商人以“走广”为时尚“争趋”,即一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此时,由于珠江长期统合作用,岭南经济巨区已具雏形,而广州成为其市场的中心地。
市场网络和水运网络的形成是同步的。大凡市镇,皆有港口,或码头、津渡的设施。所有的郡县治所,都有水道可通。新兴的市镇更是以水运条件为最优原则。随着民生日用商货进入流通领域,自然水道便作为商路被利用。
最明显的是珠江三角洲,它是由西、北、东三江汇成的河网区。佛山、澳门、江门等市镇兴起,形成不同等级、功能各异的地方性市场,并与广州市场相联系而形成市场网络。珠江三角洲也因而成为广州市场腹地的核心区。
广州贸易的海外市场,仍以传统的南海沿岸的东南亚市场为主,但南海贸易的格局已因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而发生了变化。东南亚市场日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划地分割而占据。因此,广州商人在东南亚市场上与西方殖民主义商人相贸易,已带有同西方国家贸易的性质,与广州市场相系的海外市场也伸展到欧美地区。
五、广州市区的更形扩大
自古以来,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驰名中外,其市区的更形,自与海贸联系一起。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增建东、西二城,据《唐垧记略》记载:
“广于五岭为大府。地控蛮粤,列郡倚以为重。其商船物货之聚,盛比杭、益,而天下莫及。旧有城在广州之东,规模迫隘,仅能藩篱官舍及中人数百家,大贾巨室生齿之繁几千万,皆处其西,无以自庇。”
可见宋代增建东、西二城是为了适应唐代以来海外贸易繁盛的需要。明初,将旧城与东西二城连接起来,并向西北、东北扩展。这表明南宋末年至元代,由于政治地理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广州曾屈降泉州之下,但广州的海贸依然较前有所增长。朱明王朝一建立,广州便恢复了传统的中国主港的地位。
正统年间(1436-1449年),王莹《重建羊城街记》记载:
“(城内)使价之客与守土之臣参半,而豪商大贾,珍物奇货,亦于斯萃焉。”
这说明市区居民是由政府官员、富商大贾及为之服务的市民组成。同宋、元时期一样,市面的商货依然是“珍物奇货”。
嘉靖以降,市区出现了新的气象。店铺摆卖平民百姓的日用百货日渐增多,集散的珠江三角洲和省内外的农产品也越来越多。这同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密切相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徽州人叶权在《游岭南记》一文中写道:
“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高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
可见居民构成,市面情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庶民商人、小商贩,也活跃于广州市区,旧城区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商业活动场所。城南门之外一带空地,即濠畔街一带及其以南地带,因以成市,且繁盛一时。时人霍与瑕曾说:
“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7“宫语”,‘濠畔朱楼’条也指出,濠畔街一带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又说,在那里“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当时流传的“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等说法,反映了时人对广州的艳羡。
出于治安的考虑,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围绕着城南这片商业区扩建城墙,即扩建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1124丈,高2丈8尺,周3786丈。为门八,其东曰永安,西曰太平,南曰水南,曰永清,曰五仙,曰靖海,曰油栏,曰竹栏。广州的人口也从洪武年间的27500人增至嘉靖四十一年的300000人。
从上可见,广州市场从明中叶起开始发生转型,从服务于京师、长江三角洲及运河沿岸城市富人消费的高值奢侈品外贸中心,向兼充岭南经济区中心地转化。过去,广州作为外贸转运中心,其发展不受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作为岭南经济区中心地,广州的盛衰则与其贸易腹地珠江三角洲密切相连了。
广州的市场转型,给珠江三角洲经济以强烈的刺激,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珠玑巷人”善于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大力发展商品性农业,由此带动各个行业的发展,并引起当地社会的全面变迁。
标签:广州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