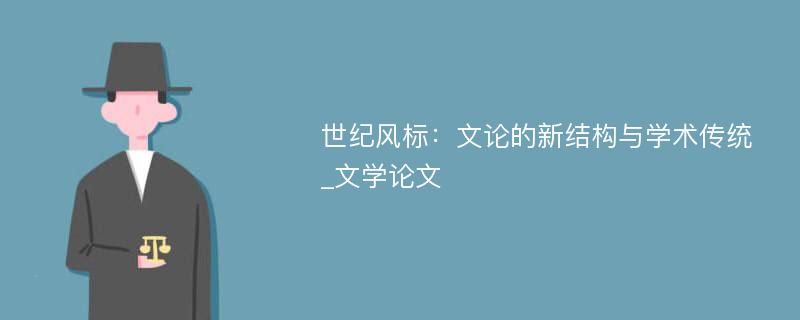
世纪风标:文论新构与学术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标论文,文论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4-0098-06
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认识到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封建机体来说,小打小敲的修补已经不能使它起死回生,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而此时日渐腐朽的封建统治者还不允许对被他们视为立足根基并奉为神圣的制度与文化稍加改良。于是,新进人士不得不借助于激烈的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与当时正在涌动的变革时潮相配合,发动了文化革命,反传统遂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作为深受时代感染的文学,也开始了自己适应时代的新变。各种以“革命”命名的文学样式纷纷登台亮相。
“五四”新人清醒地意识到新思想与旧学术之间对立的本质,陈独秀针对守旧派的攻讦,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有人判定胡适是“五四”新人中的右翼,说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温和的,仿佛胡适是那个时代情绪激动的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例外。美国人格里德还“注意”到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结果所持的谨慎态度,“虽然他(指胡适,引者注)说白话是‘正宗’,但他在1917年时又说,这只是有待于文学家的实际证明的‘一个假设之前提’”[1]。诚然,在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各方中,胡适确实显得较为平和,他赞成文学革命,在表述其主张时,他并不忌讳使用“革命”这个词语,但在最初特别需要明确地表明“五四”新人的态度时,他打出的旗帜却是“改良”。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因此可以否认他在“五四”时期对文学传统所持的与当时人一样的激烈态度吗?在作为格氏例证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对传统所持的同样是一种整体否定的态度[2]。当然,因着个人的学养、着眼点,乃至气质性格的不同,些微的区别还是有的,那就是熟悉西洋文学的胡适可以从容地辨析中西文学的差距,向国人热情地推荐西洋文学的创作方法、技巧和美学旨趣。此外,胡适从他的实验派的哲学立场出发,在对旧文学表现出轻蔑的同时,也意识到新文学建设的艰难。所以他在同陈独秀的对话中,特别强调了建设的意义,提醒这位在前台摇旗呐喊、颇有些草莽习气的文坛英雄,注意破后之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化风习自此大变,趋新趋洋已成为一时之风气,对传统作辩证的分析和开展积极扬弃的实际操作已不复可能。“五四”人物打出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否定孔子,无疑会让被儒家思想所统制所浸染的传统文化陷入被全面讨伐彻底否弃的境地,而“五四”人物所倡扬的“科学”与“民主”也与传统十分隔膜。正是因为这样,“五四”时期的领袖人物在建设新的理论体系时,似乎只盯着国外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概念名词。正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论文中所表示的,旧文学若“无裨于现实生活”,那么,即便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到了20年代初,固守传统、固守文言文的人就像“咸与共和”的民国大街上偶尔见到的拖着大辫子的前清遗老,他们被常人目为怪物,已很难撑持下去了。
“五四”时期,鲁迅进入状态显然要比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迟,但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迟到者,一旦慨然入盟,立即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巨大的战斗力,后来者竟成了队伍内立场最为坚定、持论最为彻底的战士之一。针对守旧的思想家们要求青年们回避时代矛盾,退出现实斗争,回到书斋读经的呼喊,鲁迅写了《青年必读书》,指出此时“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3]这样的论断矫枉过正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20世纪初的20年中,文学界关于文学的思考与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文学革命”展开的话,那么2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形成,这种争论渐渐演变为“革命文学”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显然,“文学革命”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旧文学的批判,而“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视野,则要宽广得多,他们一方面继续坚持文学革命的立场,即将中国的文化传统排除在新文学建设的各种参考项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渐渐地从侧重批判向关心建设的方向转移,开始站在社会革命的立场思考新文学的建设问题,革命文学将整个社会作为革命的对象,企图发挥文学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与传统的更全面更深刻的决裂。简言之,文学革命对旧文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荡,革命文学的建设便将是一个拒绝参考旧传统的建造,并因此规定了与传统彻底分离且方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
对历史发展的反复观察,使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种事物乃至一种理论,只有发展到它的极点之后,才有可能既全面地展示它的合理的方面,又能充分地暴露出它必然带有的缺陷,并因而能启动其内部存在的纠偏机制,使其回归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思潮亦复如是。虽然在建国之前它的合理性及与此相伴随的严重缺陷已经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它可以达到的极限,因此,它还能够继续其包含严重问题的运作,并在这一运作中进一步展现它的悖谬。
检之事实也确实如此。建国后不久,便出现了叶蠖生等人全盘否定文艺遗产的言论。也许是因为叶蠖生的错误过于明显,反以响应者不多。但不久,否定文艺遗产价值的错误观点标举“厚今薄古”,以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流行起来。平心而论,“厚今薄古”若作为一种总体要求,就它表现了革命者、创造者的自信、勇气,体现了社会发展今胜于昔的总趋势而言,是合理的。然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将“厚今薄古”理解为对古代文学遗产批判得越严厉越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对当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肯定得越多越好。这就成了对“古”的盲目排斥和对“今”的盲目自信。此外,“厚今薄古”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口号,这个缺乏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抽象口号,极易为错误的文学史观开方便之门。譬如,在“厚今薄古”的旗帜下,有人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搬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在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认为批判就是一切,批判就是目的;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估上,强调“价值不能夸大”,而消极或反动部分“不宜估计过低”(注:参见《新建设》1963年第12期。)。表面看起来,“厚今薄古”比之对古的全盘否定是一种进步,但在实际操作时,却无法避免“薄”——贬古倾向的膨胀。当年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陈伯达也对“厚今薄古”十分钟情,他说,新时代的学术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吗?难道仅仅依靠我们历史上那些旧知识,就能够填补吗?当然不是这样”。直白地表露了他贬低继承遗产的价值的观点。但碍于情势,他又不能断然否定继承,于是提出了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口号。既然遗产只不过是堆“腐朽”的秽物,那么它之能被继承,不全得靠陈伯达这样的“高人”展示其呼风唤雨点铁成金的法力?可见,陈的观点实际上是鼓吹随心所欲、实用主义地对待遗产。他标榜历史主义地对待传统,但他对待传统的态度却完全是反历史主义的[4]。
在这股反传统的思潮的影响下,对古代文学作品乱批乱评一时成了文学界极为热闹的现象。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北师大中文系三四年级师生“七一”前“响应党委号召,进行教学改革所突击出来的战果”——“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初稿”,用当时人谭丕模的话来说,这是他们“以敢想、敢干的精神,鼓足干劲、苦战七昼夜,完成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大纲”[5]。文章称赞“大纲”“做了许多翻案文章”,主要“功绩”包括:“过去文学史上所肯定的作家,大纲加以否定……过去文学史上评价过高的作家,大纲适当的降低……过去文学史上评价很低的作家,大纲给以提高……过去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的作品,大纲给以地位或很高的地位……过去文学史对作家只肯定而不批判,大纲实事求是地把该肯定的肯定、该批判的批判……对作家的时代局限、阶级局限不加保留地加以指责,让同学对古典作家有全面的认识。”1963年《新建设》杂志组织学者讨论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批判继承的问题,但由于立场、视角上存在严重的偏差,讨论很难获得积极的成果。如王士菁的《古今界限不可混淆》一文,说:“我国古代文学遗产基本上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即使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我们也无法从中找出社会主义思想;即使像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也不可能找出他是如何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6]依我看,作者思考问题的视角本身就已经严重地偏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
反传统固然令人痛快,但新的文学创作却不能缺少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经验借鉴。因此,像周扬、何其芳这些受到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在思考新中国的文艺实践时,对那种目空一切的反传统思潮存了几分狐疑。何其芳此时写了一系列以古代文学为对象的研究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文章中,何其芳对优秀的文学遗产有较多的艺术分析与肯定性的评价,激起了人们对尘封已久的历史遗存的兴趣。何其芳的文章中肯地指出了虚无主义地对待传统的危害,意识到当新文学已经站稳了脚跟,需要完善、需要优化的时候,那种拒绝借鉴拒绝承认文学传统的价值的态度是非常狂妄和有害的。
何其芳当然无力推倒“厚今薄古”的时代思潮,但这并不妨碍聪明、机智的何其芳对这一口号做出自己新的解释,他提出了这样两点看法:第一,“厚今薄古”虽然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口号”,但究竟还是一个针对学术界一定时候的偏向提出的口号,而不是学术工作的根本方针、根本政策[7]。第二,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他们不是“薄”的问题,而是应当古为今用,即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使之成为新文学建构的营养。何其芳有意识地为“厚今薄古”确定了时间的界限和划出了空间的范围,他还断然表示:“厚今薄古绝不应理解为对于古代杰出的作家可以随意否定、随便贬低。”[8]这些意见对于纠正错误认识,澄清混乱思想,是有意义的。在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何其芳的这些言论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指责他在遗产面前“挺不起自己的腰杆”,认为他的继承标准是纯艺术的,缺乏政治上的考量[9]。
“文化大革命”将否定传统的取向推演至极端,亲历过这场来势汹汹的运动的人们都曾目睹过“文革”中怵目惊心的焚书场面,古籍燃烧时冒出的青烟终于唤回了迷失的良知,当人们再一次聚集在理性的旗帜下的时候,理论运行自身的免疫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纠偏遂成为“文革”结束后理论界的一项急务。
80年代,形而上学的反传统的观点,已经失势。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重又发现了传统的价值。不少学者翻检出尘封的古籍,进行全面的清理。郭绍虞、钱仲联、钱钟书、王元化等老学者,着鞭在先,在阐解古代文艺理论的价值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整理遗产最初是以孤立的文本研究开始的,在长期与古代文学遗产隔绝的年青一代面前,标点注解古籍成了当时的急务,由标点、注解到阐释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价值是当时较普遍的研究模式。由注释《文心雕龙》到对其美学体系的分析和学术价值的评价便集中反映了当时对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般进展;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的典型形态——诗话的研究亦复如是,由对个别文本的研究进入到诗话发展线索的梳理、对诗话理论系统的描述和诗话学术价值的评估。综合性研究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也渐入佳境,逐渐进入到分析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语言系统、理论范畴、整体价值的学术境界。概括起来,80年代古代文艺理论遗产的研究有这样两点认识进展:第一,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总体性的价值评估,确认它是一种具有完备的思想体系、独特的话语系统的学术形态,具有对文学艺术进行整体把握、深度透视的有效性,是一种具有逻辑一贯性的思想体系;第二,确认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具有与西方文艺理论系统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并且认为只有坚持这个民族的理论传统才能获得对话的资格,真正有效地进行中西文化的交流,取长补短,实现文化的融合,完成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任务。
三
世纪之交,人们对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否定文学传统的取向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要“五四”前辈为蔓延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负责并不公平,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的反传统特征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第一,发端于“五四”的对传统的否定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赖肖尔先生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变革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的重心深埋于中国内部。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于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模式的惰性和固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自给自足,相对来说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产生了抵抗力并使它无视这种挑战。”[10]当传统成为拖累人们前进的惰性力量时,对这种力量的反拨也就在所难免了。中国封建社会演进到19世纪中叶,突然改变了它的发展轨道,政治格局、文化风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所谓“撞击与回应”来解释20世纪中国文化独特的发展形态[11]。现在看来,外力的推动,固然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获得了动力,却不是惟一的和最后的动因,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早已涌动着一股变革的潜流。虽然在19世纪中叶它还不足以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但这些异端思想足以在精神文化领域给统治阶级的思想专制制造许多麻烦,使其再不能按照旧有的统治模式来处置国事,管理思想文化方面的事务了。像李贽、金圣叹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对封建的正统思想说不,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见解、为他们信奉并捍卫的思想自由付出代价,这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不良”的预兆。鸦片战争前夕,思想界要求变革的呼声又一次亢奋了起来。特别是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政治变革要求与思想变革要求互相策应,推波助澜,形成壮阔的声势。由此可见,即便没有列强的入侵,中国学术界也已经不甘于抱残守缺,仄守阐解理义的所谓学问和为求功名而不厌其烦地操习已经操习了上千年的帖括之术。思想界的反叛精神已经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觉悟,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形成已经是时代的趋势。
第二,对传统的否弃也是文学创作出现新的事变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在其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诗为正宗的基本格局。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诗的形式还是诗的境界,都已经开发得相当完备和十分充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也形成了“诗话”一枝独秀的局面。自孔子论“诗”开始,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涉足诗论,至宋代便形成了专门的论诗格局——诗话。中国的诗话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问世时,其理论已臻成熟,诗学成了中国文艺理论中的显学。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中国近代都市的兴起,适应市民需要的艺术形式如小说、戏剧勃然而兴。20世纪初,随着白话文学的繁盛,文学创作完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切换,中国的以诗学为本体发展完备的理论传统除了惊愕地对之出神之外,一时间竟找不到可以言说的相应的语言系统与学术范畴。理论对实践的失语不可能维持长久,创作领域中尽去旧观的新变,急切地企盼着一种能够给因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学注入强大活力促其质变的理论,梁启超的新小说论正是对文学艺术的新事变的最初的理论的反应。20世纪人们在阐释自己关于文艺的见解时,突出了人的审美需要,肯定了个性化的表现。这些变化正是新的社会生态、文学格局在理论上的反映。
第三,对传统的否弃也是西学东渐引起的情绪化的反应。随着国门的洞开,中国学人完成了对西方的学术文化从坚决拒绝到痛苦接受再到盲目西化的转换过程,西学的东渐也是引发否定传统的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世纪之初中国新小说理论的勃兴,就深深地烙上了日本政治小说影响的印记,日本的政治小说在日本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五四”新人激烈的言辞中,总是可以发现西方文学是支持“五四”新的文学观发生的一个因素,我们只要翻看一下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不难明白这一特点,在胡适“中国”、“中国”的批评声中,处处可以发现作为批评参照物的那一个西方文学发展的影子。我认为,对传统采取形而上学的绝对否定的态度与人们对文化进步的线索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关。不懂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尤其是不懂得文化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新旧文化间仍旧有一定的继承,不承认新文化和旧文化存在着联系,把中国封建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一律当成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要求一律弃绝,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在文化问题上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绝地——这就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在创立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同时所犯的一个致命的方法上的错误。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新的学说的兴起,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批判,因此问题只是在于“五四”在对传统做出严厉的批判的时候,没有将包含在传统中的合理因子分离出来,给予其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他们在对传统说不之后,便将传统弃置不顾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艺术辩证法的思想,且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语言和概念范畴对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做出了富有张力的涵盖,代表了世界古代文艺理论的最高成就。当惯于对事实做出精细思辨的西方文艺理论面对文艺这种复杂现象显得呆板、拘泥和笨拙的时候,东方的整体的略带模糊的理论把握却日益显示出它那富有张力与弹性的优点。因此,我认为回眸传统,吸收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应当是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新的生长点。
纵观中国文学理论关于传统的认识发展,一个问题常在笔者心中盘旋:理论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在革命之外,选择别的能够减少震荡、减少思想混乱的方法?其实,即使是20世纪之初的当事者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曾经认真地权衡思考过各种社会变革的方案的优劣利弊,力图避免破坏性大的极端的革命。这使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既然深受传统“荼毒”的当事人,仍然能对传统持一种宽容的批判态度,那么,今天我们不是更能接受和首肯一种非决绝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历史、对待前人的理论成果的立场?
收稿日期:2001-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