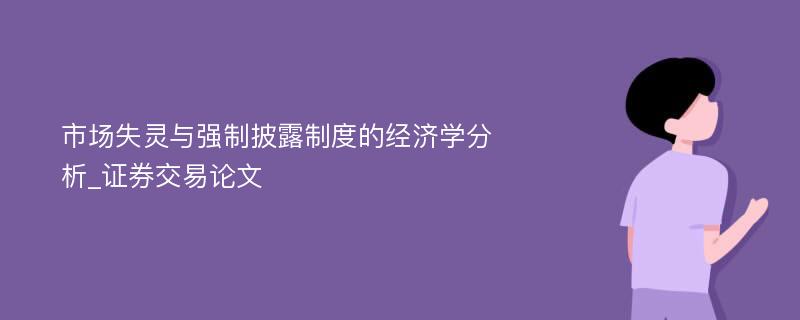
市场失灵与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分析论文,制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证券法的学术争论就像历史学上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论战一样,都明显地有着类似的阶段性:先是传统主义学者把历史事件看成是一部正义与邪恶的道德戏剧,然后由修正主义者来揭穿一切,指出貌似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坏蛋,最后由工匠式的学者纠正修正主义者言过其实的言论,做出一种比较折衷、客观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证券法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上述第一阶段,认为美国证监会(SEC)实际上起着保护欺诈的作用。以斯蒂格勒、本森、曼尼教授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证券法导致了高额的成本支出而无收益可言。按照本森教授的论点,证券法甚至没能明显提高投资者所获信息的质量。这些观点引来了一片批评声,既有来自学术界的亦有来自SEC的。批评者认为斯蒂格勒教授的研究方法是不严密的,认为内幕交易将会诱发违法的冲动;研究SEC历史的权威史学家有效地驳斥了本森教授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生效前证券市场环境的描述。
我们也许正面临着“后修正主义”阶段,其特点是:(1)至少把“有效率资本市场假说”(ECMH)当作概括一切经验证据的普遍性理论①;(2)更明显地感到难以依赖大量的统计证据去证明或批驳披露制度的作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②;(3)焦点已由对联邦证券法50年来作用的争论转移到对现有市场结构的检验及在现有条件下对投资者保护的领域上来③。
作为这一阶段的里程碑,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的文章④可被看作开启“后修正主义”的钥匙。这么说也许过分夸大了斯蒂格勒、本森教授的论文与伊斯特布鲁克、费雪教授的论文的差距,但至少后者的文章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是明显地没有积极作用,并且对投资者而言,仍有从强制披露制度中获益的某种可能。在另一方面,他们还讨论了导致发行人有可能信息披露不足的原因,认为只有一个是合理的。
比较而言,一种简单的理论完全能证明强制披露制度是正当的,并能解释强制披露制度所应关注的焦点。这一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内容:
首先,信息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因而证券研究就具有供给不足的趋势。这种不足一方面是发行人信息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行人以外的渠道搜寻重大信息的不足。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减少成本战略,它通过对搜寻信息成本的社会补贴来确保信息的数量及信息的准确性。虽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证券买卖双方之间的地位,甚至不能很大地影响分配公平的总体目标,但它的确改进了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而这种改进反过来又推动形成一个更具生产效率的经济体系。
第二,没有强制披露制度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低效率。由于投资者为追求交易利润,往往分别、独立地去搜寻信息,这将造成社会成本的不必要增加。而一种集中信息搜寻机制能减少因经济资源不当配置而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
第三,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⑤所推崇的“自愿披露”,尽管在公司理论学者中间颇为流行,但其作用是有限的。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忽视了公司控制权交易的重要性,而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完美合作想得过于容易。事实上,一些学者在有效自愿披露机制中所设置的必备前提并不能被满足。尽管能通过激励机制把管理层自身的利益与股东价值最大化挂钩,但仍存在一些对管理层的利益引诱,例如可折价购买股权,参与内幕交易或杠杆收购。由于这些利益刺激极为诱人,所以管理层就可能通过向市场释放错误信号的方式从中谋利。
第四,即便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理性投资者仍需要一些信息以优化证券投资组合。这些信息最好由强制披露制度来提供。
Ⅰ.从公共品的视角
今天我们很容易评价联邦证券法产生的理论基础。例如,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旨在帮助小投资者发现并投资于高质量、低风险的证券。由于证券法的目标已经改变了,所以前述的理论对我们已不再有任何意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市场正经历着重要的进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专业证券分析师的出现⑥。由于在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存档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网络能够及时、低成本地为分析师所得,使得分析师成为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机制。这在1934年是无法想像的⑦。
证券分析师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分析师从发行人以外的渠道搜集有关公司证券价值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发行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因素,例如利率、竞争者行为、政府行为、消费者偏好、人口变动趋势等。在这些方面,发行人本身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相反却是分析师的长处所在。二是分析师证实、比较发行人披露的信息,以防止恶意欺诈并消除偏见。
尽管个人投资者也能完成搜寻及证实信息的工作,但专业证券分析师能凭借规模优势与专业优势,以较低的成本来完成。因此,多数解释证券市场效率的理论都十分强调分析师之间在获取证券信息方面的竞争。
原则上说,证券分析师所提供的信息数量取决于市场各方实力,一般能产生均衡数量。分析师会不断证实并获得有关证券的重大信息,直到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通常个体均衡也会导致社会配置效率:为搜寻及证实证券信息而投入的社会资源在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在这简单的新古典分析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不论公共品究竟何时生产,都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A.市场失灵:证券研究不足的一个原因
公共品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经济学概念,但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从非发行人渠道得来的有关证券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品。公共品的主要特征是对未付消费者的非排他性,即无论消费者是否在取得公共品时付出成本都将从公共品的消费中获益。任何一个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对同一公共品的消费,如公园、公共频道、国防。由于人们可以成为“搭便车者”,所以就有一种少付费的冲动,即使他们明知这些公共品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能免费搭车,他们也会在公开市场中购买一些公共品。由于这些原因,公共品的供给总是不足的⑧。
证券信息体现了非排他性这一重要特征。证券信息的使用者几乎不可能限定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人们往往有泄露信息的动机。当内幕人告诉他的朋友一个有关公司的即将到来的重大发展,这一信息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听者身上,信息链还会继续延伸。事实上这对听者利益至关重大。听者已经买了该证券,所以他会告知其他人,刺激他们的行为以造成市场价格的上扬。否则持有被低估证券的听者获得的仅是一种不确定的收益。华尔街有句行话:还需要讨价还价的交易不是交易⑨。后来获知这一重要信息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额外收益,尽管随着市场的快速调整,该利润空间会很快消失。
把公共品理论用在分析师上,即意味着分析师不可能从他们的成果中获得与之相当的经济回报。这将导致分析师做比投资者期望更少的研究。对证券研究的公共品特性,我们可以借用一句有名的商业行话:“当E.F.Hutton说话时,人们仔细在听”⑩。事实上,还有一些没有付费的偷听者在听。他们就是搭便车者。证券研究的成果只能采取“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供给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的回报只能是向这些机构投资者提供经纪及其他投资银行方面的服务。因为规模效益与专业优势,这样做比投资者自己聘请人员进行研究更有效率。一旦证券研究以这种形式传播,搭便车者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因为研究报告很难长期守密,再加上机构投资者有利用报告来刺激旁人参加交易的利益诱惑,所以泄密立刻就会发生。此外,一旦泄密又不会对分析师做出任何补偿。所以证券研究往往是补偿不足的,这自然导致对证券研究的投入不足。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经典的公共品命题:只要搭便车者存在,商品供给就会不足。
与证券研究相关的另一问题在于,很难为证券研究订立合同。一般来说,投资者不可能事先知道证券研究的价值,所以,即使给予报酬也往往是事后的。不仅证券研究存在这一问题,商业秘密、专利等有价值信息的交易都面临着这一问题。投资建议的价值只有在预期的市场反应最终形成之后才能确定,尽管购买信息方愿意为证券研究支付报酬(至少买方期望将来仍能从分析师中获知信息),但这种事后单边定价的报酬肯定会低于双边议价的报酬。
更为复杂的是,支付给分析师的报酬并不是以现金形式,而是信息使用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把一部分经纪业务委托给投资咨询公司,即投资者是用未来经纪业务佣金溢价的形式支付报酬。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折扣经纪公司”,这些公司只提供结算服务而不提供咨询服务,故而其佣金比提供投资咨询的公司低50%。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仅仅提供结算服务或提供清算与咨询服务。
这种奇妙的机构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而这两点启示在强制披露的新古典理论中却被忽视了。其一,存在对购买证券研究的利益引诱:投资人可以暗藏操作,利用全能经纪商的投资信息,而把大部分业务委托给折扣纪经商;其二,在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形下,全能经纪公司及分析师仍能生存,这说明个人客户及机构投资者的确需要证券研究及投资建议。因为信息的消费者包括了最精明的机构投资者,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非理性的表现。
证券研究的公共品特性及订立合同时存在的问题能够解释为什么强制披露制度对投资者是有利的。简单地说,当市场力量不能产生证券研究的社会最优产量时,管制就会被引入来解决问题。尽管投资顾问是受联邦证券法最少约束的行业之一(11),但却是获得帮助最大的行业。“1934年证券交易法”(SEA)对今天的影响不在于向终端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在于减少了分析师的成本。事实的确如此,从证券交易法关于提交详细的定期公告这一规定中受益最大的不是普通交易者而是专业分析师。所以当看到职业投资界对证券交易法确立的持续披露制度的长期坚定支持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12)。
那么对证券市场效率与结构而言,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什么?强制披露降低了专业人士获取与证实信息的边际成本,刺激了证券研究的总供给。因为作为一个合理的经济人,分析师的生产会在降低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实现新的均衡,这自然意味着将生产更多的信息。而高利润又会引致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从而加剧市场的竞争。非正式的实证数据已经证实,上述推断的情况在1934年后的证券市场确实存在。当然,今天的证券研究的数量要远远多于1934年,尽管当初证券分析师这一称呼并不为人所了解(13)。
但是,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在证券交易法通过后,成本减少为什么没有以股价的攀升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14)由于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有关证券交易法通过后市场反应的研究没有能捕捉到当时市场发生的变化。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成本减少所带来的收益都被内幕交易者及其他市场专业人士所攫取了,因为虽然这些人在SEA通过的前后都获得几乎相同数量的信息,但在SEA通过之后,他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当然这个回答是不完善的,它忽视了证券分析师及其前辈在较低的边际成本情况下应当生产出较多信息这一事实。
有关低成本导致信息产量增多的争论仅仅到此为止。虽然,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清楚地意识到,生产的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必须适当地告知投资者这些信息,才能使市场更有效率。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仅仅指出了这一点,而更深入的分析才刚刚开始。
根据SEC咨询委员会的资料,证券分析师仅仅定期跟踪1000家左右的公司,而按照证券交易法注册发行股票的公司却有1万多(15)。缺乏分析师的监视,又身处在不稳定的交易中,完全有理由置疑剩下的9000多家公司股票的市场是否是有效的。尽管证券市场还存在其他的机制来实现效率,但这些公司的效率是不能被证明的,并存在很大的疑问。为提高小盘股的交易效率而扩大社会资源的支出,对这种想法也有争论的余地。似乎只有对提高分析师搜寻与证实信息的边际成本所导致的后果,大家不存在争议。如果我们废除证券交易法,将导致边际成本的提高,分析师跟踪的企业数必会低于1000家。简言之,边际成本降低,被跟踪公司的覆盖面将扩大,如提高则相反。这一结论可引出以下推论:分析师跟踪的公司越多,将越能保证证券市场的效率。
这1000家被跟踪公司(或现在的跟踪数量)并不一定就是均衡数量,但可以看到政策背后的理论构架:证券分析师是证券交易法的产物。的确,证券交易法是分析师唯一的衣食父母,现代分析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必须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以支持其证券研究。由于很难实现证券研究的契约化,所以分析师的生存需要某一类投资者的出现,例如从事频繁大额交易的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只有他们才可以以远期委托式的承诺作为对分析师成果的支付方式。
在1934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只占一小部分,市场交易的主导者是职业交易人。他们更依赖传闻、内幕消息及私人渠道而不是数据来从事交易。只有到了60年代,机构投资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才有力支持了证券分析师。从这一角度看证券交易法可以回答我们至今仍面临的问题:如何提高证券研究数量,尽管1934年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当时证券交易法所带来的收益全部被职业交易人这一小部分人所吞食了,但随着证券行业的扩张,证券交易法所带来的成本降低还是有助于分析师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这一结果或许是偶然的,但却是理想的。
B.社会资源的浪费与过度研究的问题
强制披露制度导致成本降低的假说还产生了另一重要推论:通过建立证券信息的集中机制,节约了追求交易利润的总支出,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从社会福利学的角度来看,交易利润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因为一方的收益等于另一方的损失。搜寻与证实信息的背后是所付出的社会资源。尽管证券研究有时也创造社会财富(完善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帮助企业提高创造财富项目的融资能力),但证券交易法主要影响的是二级市场。如赫希雷费尔(Hirschleifer)在其经典论文(16)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假设追求利润者的行为不会影响股东的总财富,那么追求利润的支出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耗费。强制披露制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减少这部分成本,如果SEC建立了集中的证券数据库,那么各咨询公司就没必要各自另起炉灶。所以即使如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所说证券交易法产生了过多的信息,但证券交易法同时减少了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
强制披露制度带来的成本降低与由于具有公共品特性而导致的证券信息生产不足这两者是否存在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金融界人士为获得并证实信息可能同时存在投入过少或过多资源的可能。如果被跟踪的公司过少或进行不充分的研究就会出现投入过少的情况,过多的情况往往产生于几位分析师同时分别在做同一项研究。SEC数据库的存在至少可以部分缓解两种情况。
C.配置数据:充足证券研究的社会利益研究
是过多研究带来的后果严重呢还是研究不足寻致的后果严重?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优披露制度的设计就取决于该问题的回答。而两种情况在证券市场中都可能存在。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看做是公平的,证券价格也是公正的,那么法规的介入就没有必要了,当然对内幕交易的控制除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就成了一种“零和博弈”。每一交易一方的获益必然等于另一方的损失。此时政府就没理由去鼓励交易方为追求利润而做的对社会而言无效的努力,所以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追求交易利润前提下减少资源浪费的重要手段。
相反,如果我们把证券市场当作资本的重要配置机制,那么证券价格的重要性不是主要体现为财富在投资者之间的分配上,而是体现为证券价格对配置效率的影响上。所以游戏公平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资本的准确定价。如果为获得资本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或低于有效市场的通常代价,那么在竞争者中分配稀缺资本的社会机制就会被扭曲,即使游戏的规则对买卖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核心问题就从联邦证券法是否有助于提高对投资者的平均回报转移到是否能缩小回报之间的偏差。如果联邦证券法做到了一点,那么对新发行人而言,市场就有更高的配置效率。正如斯蒂格勒教授所说的:“价格的偏差是市场无知的表现”(17)。证券收益更大的偏差,意味着投资者期望值差异性越大,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也很可能更低效运转。当然此时证券市场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效率,如价格的随机游走,强制披露不能调整股价。
一旦我们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强制披露制度存在与否对证券价格偏离程度的影响时,经验主义的争议就被缩小了范围,每一位研究联邦证券法影响的学者如斯蒂格勒、本森、贾雷尔(Jarrell)、弗兰德(Friend)都认为证券交易法通过后价格偏离度减少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配置效益提高了,投资者也从中获益。而联邦证券法的社会效益又超过了对投资者的效益。当配置效率提高时,获益的不只是投资人,社会的全部成员都从中获益。从这一角度看,认为SEA仅仅是对投资者的资助或仅仅有益于交易利润是相当短视的。
在关注配置效率的同时应描述证券研究的未来。我们应关注更现实的问题,而不应再纠缠于近半个世纪有关证券法作用的无休止争论。例如,伴随近来证券交易法项下放松的管制,会不会出现证券价格偏离度的提高或市场波动性的提高?不回答是对该问题的最好回答。像这样的假设性问题还有许多,例如1982年实施的“统一披露制度”及“搁架式登记声明”(shelf registration statement)的采用会不会导致价格偏离度的增加?如果不会,那么这些改革带给发行人的成本减少则是合理的。当然我们不能仅凭市场对此的即时反应或对投资人平均收益可能的影响来坦然回答这一问题。一旦认识到存在一种与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有关的社会利益,那么我们就得既计算给发行人带来的成本也计算给投资人带来的收益。
Ⅱ.自愿披露的理论
在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看来,公司管理层有较强的自愿披露重大信息的动机,所以强制披露制度是多余的。这一论断起源于詹森(Jensen)—麦克林(Meckling)代理成本理论(18)与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oery)(19)。
上述理论并不否认在现代企业中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会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产生利益冲突。但他们认为冲突的后果往往由管理层承担。为了初次发行时能售出证券或为了维持公司股票的价格,公司管理层必须让市场相信相关信息已经披露了,否则管理层是首当其冲的失败者。所以根据这些理论,管理层与股东在公司层面有共同的利益,故而市场应相信所有的重大信息已经披露。
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的文章就技术层面做了论述:公司雇佣会计师以保证公司报表的可信度,公司通过股票期权计划使管理层持有相当的公司股票以刺激管理层;承销人也会自己购买相当一部分发行人的股票。管理层的声誉也会阻止管理层从事损害股东的行为,这些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能阻止管理层犯机会主义错误,能约束他们提高个人的薪资,减少逃避责任的可能。尽管理论上听起来强制披露制度已无必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代理成本仍然存在(20),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使管理层侵害了股东的权益而获得了公司控制权。
A.对理论的批评
自愿披露的理论假设了一种前提,认为管理层会因为公司业绩的变化做出自己的“赔偿”,这样管理层就会只为公司的利益而服务。事实上这种赔偿机制的实施是困难的,而且并不能拒绝管理层一切的机会主义行为(许多经济学家简单地把这些问题剔除了)。所以以此认为强制披露制度是无关紧要的显然是错误的。
例如在斯蒂芬·罗斯教授的“激励信号理论”(incentive signaling theory)中就对自愿披露机制的前提做了详尽介绍:管理层的赔偿仅以居于同类岗位所可能获得的合理工资为限。换言之,在时下通行工资为10万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公司愿意花100万美元雇一管理人士,而且罗斯教授自己也认识到严厉的赔偿机制会导致内幕交易的行为:无论公司怎样,从事内幕交易的管理人员都有利可图。罗斯教授在这一理论关键处的论述表明了他并没有把赔偿机制实施所带来的问题当作一回事。他写到:“股东不会允许一位年薪只有10万的经理人拥有借公司交易为自己赚100万的自由……。这并不是说管理人员没有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牟利的冲动,而是由于股东认识到了这一冲动,并会通过合同的形式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
股东的确希望阻止公司管理人员进行内幕交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成功地付之于实际。事实上,罗斯教授只是那个“假想有个开罐器”的经济学家(但仅此而已,这对控制内幕交易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任何帮助)。罗斯宁愿解决因内幕交易难以被发觉而导致的问题。即使内幕交易被发现了,公共手段也远比合同制裁更为有效(21)。事实上,人们从没有尝试用任何的合同方式来解决内幕交易的问题(22)。所以,内幕交易一直存在,自愿披露理论的前提并不被满足。
虽然,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利益缺乏一致,需要相应的反欺诈条款作一规范,但是否需要强制披露制度却存在争论。因为一旦发现未披露信息的重要性,管理层几乎能同时进行交易。一旦交易,管理层又有很强的冲动去释放积极的或消极的信息,以期市场做出回应。所以滞后的信息披露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尽管证券交易法项下存在期报制度。
尽管传统的内幕交易没有为强制披露制度的存在提供正当的理由,但新现象的出现给了强制披露以用武之地。在过去的几年中,杠杆收购(LBO)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LBO是管理层(和少部分股东)通过质押其在公司的股份以融资收购本公司的一种方式。以LBO形式收购的数量占购并总量的比例正由1982年的20%上升到1983年的50%。虽然存在一些其他的经济原因,但LBO的盛行可以被解释为对恶意收购威胁性不断增强的回应。管理层做出LBO的决定会进一步激化管理层与股东已有的矛盾。结果会使得管理层内幕交易的规模不再小打小闹,而上升到控制公司的层次上。如今LBO都会采用高溢价收购的方式,看上去这是一种善意的理想的现象,其实这是强制披露制度导致的结果。
如果没有强制披露制度,LBO会更为盛行,会加剧两种不道德的冲动。一是管理层为少付溢价而封锁或低估利好的信息;二是管理层慌报利空的信息。后一冲动与罗斯和麦克林自愿披露理论的观点有关。他们认为管理层必须详尽准确地披露不利信息。因为任何公众对公司信息流的怀疑都会导致金融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这些学者认为如果过于坦率地披露坏消息,市场会做出过激的发应。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有如下准确而扼要的描述:“对坏消息的反应过程就如同利好消息一样。市场的反应不仅限于披露应当引起的调整,因为投资者都会担心有最坏的结果。只有披露利空消息的同时披露利好消息,才不会使投资人产生这种更坏的担心”。
简言之,如果不披露信息会导致市场的崩溃,管理层完全可以利用不披露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停止披露以造成经济上不合理的股价下跌,然后买入被人为低估的股票,甚至可以利用沉默造成市场的恐慌,然后采取LBO。
投资者也会有一天认识到管理层的伎俩,不再把不披露与市场崩溃必然地划上等号。但信息披露的中断潜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披露导致的市场过度纠偏这一初始前提将不复存在。于是管理层又会隐瞒利空信息。
如果不披露意味着灾难,那么管理层会利用它来获得公司的股票或资产;如果不披露不意味着灾难,那么管理层则不需要正常的披露利空消息。自愿披露理论的内在矛盾性与对强制披露制度的需要有何关联?答案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在强制披露制度下,如果LBO的价格低于正常值,就会出现价更高的第三方。该第三方对投资者而言是一种理想的救济形式——自发的,又是无偿的。仅有反欺诈法就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反欺诈向投资者提供了诉因,但它却不能通过信息的有效传播提高市场对公司的控制。并购方在并购前需要信息。强制披露满足了并购方的需求并有助于各方的竞争。虽然反欺诈条款能向受害人提供补偿的救济,但由于对违规者而言,补偿并不会对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难以阻却私下违规交易。事实上,对违规者仅仅罚没其收益。但第三方的出现却能有效阻却这种违规行为,因为一旦收购成功,违规的在职管理层必然会去职。
另一方面,存在不披露利空消息的冲动时(或引诱市场下跌以期收购,或管理层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推迟市场反应的时间),强制披露制度是对反欺诈条款的理想补充。反欺诈在面对不披露情况下存在严重的概念性局限,而且它不能简单地处置管理责任人。如果管理层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位而不是为了交易而不披露利空信息,法规的可操作性就更差。也许可以追究公司的责任。但对公司而言,不披露引发的交易仅仅意味着股东的变化。
在前段分析中,市场力量会迫使充分的披露依赖于一个有缺陷的前提:管理层只有把自己看作是市场的“长客”(repeat player),才能从个人长期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呵护市场的信用。在通常情况下,该前提是正确的,但当市场充斥LBO与恶意收购时,管理层就不可能再把自己当作市场的长客。如果管理层认为股价的下跌会引发恶意收购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时,很难奢望管理层再抱有长期的眼光。管理层于是开始琢磨如何拖延利空消息的出台。由于担心被收购,所以管理层决定进行LBO(尽管这意味着其不能够实现多元化投资),于是开始隐瞒利好消息。只有在稳定的社会中,管理层才会有控制公司的自信,才会抱有市场长客的长期眼光。可惜的是今天已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了。
B.实证比较
可能性不应该是理论的最终检验结果。市场自动披露所存在的缺陷并不表明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是否存在经验证据以衡量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的效率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森对证券交易法通过前后的比较研究引来了一片批评。即便今天重做这项研究,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使依证券交易法通过前后的股票收益比较来分析该法对今天影响的努力付之东流。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反欺诈的现代证券立法都在证券交易法通过的几十年后才出现。证券交易法的重要性只有与这些发展相结合才能展现。所以简单地比较证券交易法通过前后的市场,不足以衡量证券交易法的影响。而二战后个人投资者的大规模涌现增加了代理成本,减少了证券投资回报,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23)。结果是由于存在抵销性的影响,使得今天的研究更为折中。
也可利用其他社会学方法来获得至少是对强制披露的推论性理解。当社会学家不能控制实验本身时,他们经常期望凭借“自然实验”来做解释。在塞伦(Thorsten Sellon)有关死刑的经典研究中,他比较了有无死刑的相邻各州之间犯罪率的差异。相应地,我们可以比较处在SEC监管下的公开证券市场与不受监管制约的市政债券市场之间存在的差异。
对市政债券市场披露水平与操作水平的评估已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但无论70年代发行的纽约市政债券还是80年代华盛顿公用系统债券(Washington Public Power System)的失败都显示关键性的信息并没有向投资者披露。多数观察家都如此认为。但新古典经济学者认为投资者不需要知道信息,因为穆迪与标准普耳的评级已能保护投资者。这些评级公司收集并消化信息,了解证券的风险水平然后给予一合适评级。
如果我们用新古典学者的望远镜远距离观望市场,必需会招来批评。一旦我们近距离地审视市场,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在纽约财政危机中,穆迪公司直到危机人尽皆知时才下调了纽约市政府的信用评级。第二,由于发行人向评级公司支付评级费用,所以存在利益的冲突。第三,评级机构并不自己做调查研究,而是依靠发行人提供的数据。据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调查显示,数据的准确性存在严重的问题。1983年对557家市政府的调查显示,54%的市政府所提交的财务报告存在不完整或瑕疵情况,以至于独立会计师只能给出合格意见。
这些问题的产生部分是因为对政府机关及非盈利机构的会计准则并不完善。但是评级如果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数据上,那么评级就不能保护期望规避高风险的投资者。垃圾的数据造成垃圾的评级。这一结论导致了对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教授及其他有关自愿披露学者的广泛批评:他们没有注意到机构间内在的利益联系,也没有注意严格的统计是否剔除了观测数据。
那么我们应持何种立场?尽管有这些批评,自愿披露理论在初次公开发行时还是适用的。但在证券交易法主要规范的二级市场上则缺乏说服力。由于高额代理成本的存在(近年来收购溢价在50%与70%之间),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对股东有利的收购中管理层能够隐瞒利好消息。对管理层而言,最有效的方式是隐瞒利空消息,以使不可避免的股价调整滞后产生,这也拖延了公司成为恶意收购牺牲品的时机。但强制性信息披露却能通过降低收购方信息搜寻成本(也强化了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控制能力)及在代理纠纷中激活股东与管理层斗争的地位部分地解决问题。
Ⅲ.向投资者的披露:有效市场中投资者导向的披露机制
有效市场一般被定义为:证券价格能即时反映所有可能的公共信息的市场。即便在有效市场中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也是被用来向证券分析师等专业人士提供信息的。因为他们被视为保持市场有效性的发动机。当价格已充分反映了可能的信息时,如何提供个人投资者导向的披露机制?如果个人投资者不能发现证券价格的偏差,向其披露的意义何在?
对此问题已存在两种回答,尽管分别来看每个回答都谨慎地认为投资者不能有效主导市场,但合起来却能看到仍有许多信息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密切相关。
A.披露作为一种多元化投资的有效手段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证券风险与两种因素有关,β衡量单个股票收益对市场收益变动的影响,α是对非市场及其他因素的衡量,与单个股票无关。在充分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中,α可以被忽略。这时投资者需要明确的是β值,并依其风险偏好予以调整。因为证券组合的β值是组合中所有证券共同影响的产物,所以其中一种证券发行人的披露只能起到较小的作用。而且根据传统理论,价格的历史数据比基本投资数据更能反映β值。所以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并不需要联邦证券法下要求的基本财务披露。
但大多数投资人并没有持有充分多元化的证券组合,因此他们对每一证券的β值感兴趣。但是潜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与发行人要为没有实现多元化证券投资的投资人的愚蠢行为提供补贴?事实上,投资者要想实现充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并不困难。他们可从任何证券交易商购买指数基金。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对此做过研究。问题在于投资的目标是实现合理的多元化投资组合而不是实现充分多元化的证券组合。为实现前者,就不可能做到后者。
许多个人投资者除持有公开发行的证券外还持有或希望持有其他形式的投资。例如不动产、保险、股票期权或私人公司。投资者的真实愿望是实现包括证券投资组合在内的全部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例如中高层经理有可能持有或希望持有其所在公司的股份,把充分多元化的证券投资组合添加到其他未多元化的投资中就无法分散其在公司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为实现最佳的多元化投资,管理层必须平衡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风险。现代投资理论认为,投资必须通过负的协方差(反周期表现)的投资来分散投资风险。通过反周期投资操作,投资人可以减少投资组合的总体方差(或风险)。该理论为向个人投资者提供分行业数据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为在混业经营的时代,难以清楚地知道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或参与的程度)。所以,即便在有效市场中寻求高α值的股票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许多类似的数据(指分行业数据)仍然会对理性投资者分散投资起到作用。
B.风险评估与组合投资修正
应向个人投资者提供详尽披露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基础分析与组合投资风险评估存在重要关系。知道证券被有效定价并没有告诉投资者证券所含的风险与其表现是否相容。虽然这需要个别披露的机制,但金融学者告诉我们如果多元化投资足以充分规避除系统风险外的一切风险。尽管这是CAPM的核心内容,但今天的金融学者在如何衡量及怎样定义系统风险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无人认同个股β值的准确性,而且即使能准确地衡量组合投资的β值,投资者也将会经常面临修正证券组合的需要。他们必须评估新股加入对证券组合总体β值的影响。在组合投资的调整中披露基本的财务数据和原先股价水平对个人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虽然金融学者认为通过股价的历史数据可以最好地衡量出β,但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对投资基本面(主要是传统证券分析师凭以预测的资产负债表、收入数据)的分析才能最好地评估β。尽管存在争论,但在现实中机构投资者确实需要基本面数据,所以在认定市场对这些数据的需要是非理性前,金融学者应更为谨慎。这不是说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才是在后修正主义时代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向普通投资人披露基本财务信息及分行业数据至少存在两个理由:一是为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寻找负方差的证券,分散现有投资,实现最优的组合投资;二是即使在已经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也需要这些信息来评估个股的β值以修正投资组合。
Ⅳ.结论
在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对强制披露制度的评估中,公平性因素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对象:投资者信心、投资者保护,阻吓欺诈。他们认为效率性因素是肤浅的,所以他们把目光主要集中于与财产信息有关的领域。对公平的关注甚于效率,这并不奇怪。因为强制披露制度的支持者一直也强调前者甚至后者。
但是最支持强制信息披露的观点却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经验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强制披露制度的采用减少了价值的偏离,增强了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即使我们不依赖于历史数据,仅凭经济学的逻辑我们也能推出强制披露制度的缺乏将导致证券研究的不足。
在证券市场计算机化的未来,个人投资者审视公司披露将成为个别现象。无论在选择个股上还是在提高投资组合多元化的效率上,人们会更多地依赖证券职业人士。在当今的世界,通过SEC建立金融数据中心能使证券分析师及其他市场专业人士更便捷更有效地利用数据,减少不必要的重要建设,覆盖更小规模的企业。
詹森、麦克林及罗斯认为,即使没有强制披露制度,重大信息仍能被披露。虽然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但却存在许多重要例外。他们忽视了管理层所处的环境越来越不稳定,而管理层对此又无能为力这一事实。管理层于是就有较强的冲动去隐瞒利空消息,或隐瞒利好消息以优先收购自己所在的公司。简单地说,强制披露制度能降低公司监管的平均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降低,完全多元化投资者也将从中受益。因为这能减少组合投资本身不能减少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代理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都不会与强制披露制度相冲突。但两者都要求强制披露制度关注更具体的领域。代理理论更关注敏感性方面(LBO与收购防御),而组合投资理论更关注投资决策方面(如风险水平的选择,对现有非证券投资组合的多元化投资)。
虽然证券研究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不可能向证券研究提供无限的补贴,但为验证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所应做的、详尽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却尚没有人做,也许这一问题可能存在别的解决方式。但未知的恶魔总比已知的恶魔更为可怕。在放松管制渐成时尚之前,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放松管制给市场配置效率带来的影响,特别应更仔细地关注价格的偏离与波动性。在这里,公众的利益高于投资者利益。
感谢Bruce Ackerman,Susan Rose-Ackerman,Ronald Gilson和Joel Seligman对本文的建议与批评。——作者注
注释:
①有效资本市场假设可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形式。在当时,司法与行政决策都开始接受ECMH,但在进一步研究时,数据出现了一些异常。因此对ECMH提出一些质疑,主要是:股价的速度反应,小企业非正常的高回报以及季节性、星期性或相似的周期性背离。尽管这些异常看上去并不能动摇投资者无法基于勤奋搜寻努力来影响市场这一基本观点,但却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利用ECMH来作为放松管制的理由,特别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时。本文认为强制披露制度应致力于能帮助投资者评估β值及更好地减少多元化风险。对小企业更深层地披露要求也是正当的。
②尽管对统计数据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社会学者的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利用观察得到的数据,而不做必要的处理。
③20世纪20年代以来市场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主要有(1)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出现,这在1934年前是非常少见的;(2)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正占据主导地位;(3)证券分析师的成熟并成为真正的职业人士。这些变化至少可追溯到二战结束时期。但这些趋势并不是同向发展的。
④见Easterbrook和Fischel,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70Va.L.Rev.669(1984)。
⑤见Easterbrook和Fischel,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70Va.L.Rev.669(1984)。
⑥据SEC公司披露咨询委员会资料显示,到1977年有14646名职业分析师受雇于各种金融机构、经纪公司、咨询公司。由于提供了有用的服务,所以该行业能一直延续至今。过去分析师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来自于与管理人员的私人沟通。管理人员通过这种方式披露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下文所提及的自愿披露理论。
⑦虽然个人投资者也能获得信息,但分析师与经纪人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
⑧伊斯特布鲁克和费雪因此分析为什么股东不会为自己的权益抵制管理层。因为任一股东或任一部分股东的抵制所带来的利益会由全部股东享有。对分析师而言,也可因此理论解释他们不可能获得与他们的成果等值的经济回报。见Easterbrook和Fischel,“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s 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1994Harv.L.Rev.1161,1171(1981)。
⑨“A bargain that remain a bargain is no bargain.”
⑩E.F.Hutton是美国一家著名的证券咨询公司,1974年首先为非机构投资者提供证券咨询服务,后被莱曼兄弟公司收购。“当E.F.Hutton说话时,人们仔细在听”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公司广告词。——译者注
(11)相对于经纪商、交易商而言,对分析师的监管相对显得宽松。即主要是需在IAA(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项下注册,并受报告及反欺诈的约束。
(12)尽管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还有些微词,还举行Seligman形容的“资本罢工”,但当1964年对SEA修订时把拥有股东数大于500的及一定量资产的公司也纳入监管的范畴时,业界人士还是表示了欢迎。
(13)现代证券分析师真正的发展阶段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证券分析师的雏形1934年前就出现了,但真正的发展则是在Graham与Dodd理论发展以后[见Security Analysis: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Lst ed.1934)]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出现。
(14)见Benston,“An Evaluation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5)Kripe教授认为这个比例还要低。
(16)Hirshleifer,“The Private and Social Valu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Reward to Inventive Activity”,61Am,Rev.561,1971。
(17)见Stigler,“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69 J.Pol.Econ.213—214(1961)。
(18)见Jensen &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l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Fin.Econ.305(1976)。
(19)见Ross,“Disclosure Regul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Implications of Modern Finance Theory and Signaling Theory,in Issue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177”(F.Edwares ed.1979)。
(20)虽然组织结构的改变与购并盛行都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减少管理的机会成本与代理成本。见Williamson,“Organizational Form,Residual Claimants and Corporate Control”,26 J.L.&Econ.351,363(1983)。
(21)公共手段有规模经济的优势,纽约证交所与SEC投资了市场监控系统能快速发现不正常的交易行为。联邦检察官也采用了大陪审团的形式。见Coffee,“Rescuing 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Why the Model of the Lawyer as Bounty Hunter Is Not Working”,42Md.L.Rev.215(1983)。
(22)鉴于合同手段的局限性,卡尔顿教授与费雪教授认为内幕交易应合法化。见Carlton & Fischel,“The Regulation of Insider Trading”,35 Stan.L.Rev.857(1983)。
(23)Jenson和Meckling认为,如果1934年后股权更为分散,则会提高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于是就会降低股票价格。因为小股东监管公司管理层的支出更低。见Jensen和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Fin.Econ.305(1976)。
标签:证券交易论文;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论文; 股票分析师论文; 证券投资分析师论文; 市场失灵理论论文; 证券法论文; 证券论文; 费雪论文; 投资论文; 分析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