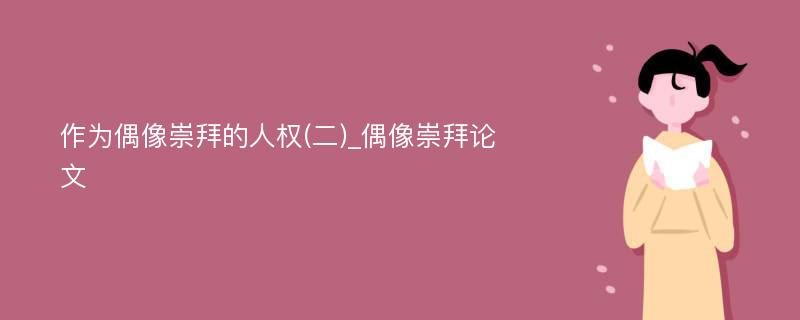
作为偶像崇拜的人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人权论文,崇拜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精神危机
人权的文化危机触及到人权规范的跨文化有效性,而精神危机触及的是这些规范的最终的形而上学基础。首先,为什么人有权利?是人类和个人的什么东西使他们享有了权利?如果人具有某种特殊的因子,那么为什么这种神圣性在践踏中得到的赞许常常远胜于其在遵守中得到的赞许?如果人是独特的,人们为什么要如此恶劣地相互对待?
人权已经成了一种世俗信条。但是,这种信仰的形而上学基础还远远不够明晰。《宣言》第一条省去了一切正当性辩解,而只是声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宣言》对权利作了清楚表述,但它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有权利。
《宣言》起草的历史表明这种沉默是有意的。1947年2月,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她的华盛顿广场公寓召集了一次起草会议。在会上,中国的一位儒家学者与黎巴嫩的一位托马斯主义者就权利的哲学和形而上学基础陷入了一场不可开交的争论。罗斯福夫人总结说,前进的唯一道路在于西方和东方同意分歧的存在。(注:See Morsink,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因此,该文件有意地对人权文化的核心问题保持了沉默。《宣言》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利存在并向它的细节进发,而没有提出一套用以解释人权为什么是普遍的正当性根据,也没有——就像杰弗逊为美国独立宣言所写的永垂不朽的序言那样——提出可以追溯到最基本原则的那些理由。
在终极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沉默使得一种全球人权文化更容易出现。一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人权概念“如果与它的一些根本的正当性理由分开,会更加容易传播”。(注:Charles Taylor,“Conditions of an Unforced Consensus on Human Rights,”in Bauer and Bell,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p.126.)《宣言》所自诩的“普遍性”既是起草者们在《宣言》中所包括的内容的证明,也是他们在《宣言》中所回避的内容的证明。
《宣言》预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如果人们发现他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他们仍然能够在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基础上诉诸保护。换言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基础是“自然权利”。不过,人权与自然权利或者“人的”与“自然的”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什么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呢?
人权的目的在于,在公民义务和政治义务不能阻止虐待或者这些义务全部瓦解的情况下,以司法手段将人类良知的自然义务正式化。人权教义似乎假定,如果管制社会的奖惩机制消失,人权规范就会提醒人们要自然正派。这只是假定正派行事的能力是一种自然的态度。能够证明这种假设的经验证据又在哪里呢?一个更可能的假定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道德和特定意义上的人权代表着矫正和抵制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然倾向的系统努力。我们正努力抵制的特殊倾向是:虽然由于遗传和历史方面的原因,我们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关心那些与我们比较亲近的人——我们的孩子,家属,直系亲属以及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伦理和宗教起源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很自然地漠视在这些圈子外面的所有人。历史地讲,人权教义的出现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关爱伦理圈上的特殊主义和排斥主义倾向。一如阿维赛·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所言:“为了克服我们对他人自然的冷漠,我们需要道德。”(注:Avishai Margalit,“The Ethics of Memory”(The Horkheimer Lecture, May 1999,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感谢马格里特让我阅读这些演讲稿。)
《宣言》起草之前的那段历史为人类的冷漠的天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大屠杀显示出,怜悯、关爱这些被假定的自然人性在其不再作为义务受法律实施时存在着严重不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指出,当欧洲国家的犹太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直至当他们最后被剥得一丝不挂,只能作为简单的、赤裸的人向逮捕者求助时,他们发现,哪怕他们的赤身裸体也不曾唤醒施暴者的怜悯之心。恰如阿伦特所写:“一个除了是人之外什么都不是的人,似乎也丧失了那种可能使其他人把他当作同胞看待的属性。”(注: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and Brace, 1973, p.300.)《宣言》恰在人们在自然人性找不到任何人权基础的历史时刻开始了人权理念的重建。
对于这一悖论,我们所能说的是,它界定了我们在人权理念方面一直存在的分裂意识。我们把人权作为普遍道德原则加以辩护,但同时我们又完全意识到人权必须抵制而不是反映人的自然倾向。
由此,我们不能把人权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自然怜悯或团结上。因为,有关这些倾向是自然的这一理念暗含着,这些倾向是天生的,普遍散布于个人之间。现实并不如此,就像大屠杀和其他数不清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必须在对人的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培养一种对人权的信仰。这种信仰应该建立在对我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这一假定,而不是对人类的最美好的期望之上。换言之,我们不把人权建立在人性上,而把它建立在人类历史上,建立在当人类缺乏权利保护时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之上。我们建立在恐惧的见证上,而不建立在希望的期盼上。对我来说,自大屠杀以来,人权意识似乎就是这样被建立的。人权是朱蒂斯·希克拉(Judith Shklar)所称的“恐惧的自由主义”的一项成就。(注:Judith N.Shklar, “The Liberalism of Fear”, in Stanley Hoffman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pp.3—21.)同样,柏林在1959 年指出,在后大屠杀时代,对道德法则必要性的觉悟不再靠对理性的信仰,而靠对恐怖的记忆得以维持。“因为这些自然法规则遭到了蔑视,我们被迫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注:Isaiah Berlin, “European Unit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1, pp.204—205.)不过,在他那里,这些规则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没有法院,也没有权威能借助于一些被认可的程序去让人作伪证、随意实施酷刑或者为了取乐而杀戮同胞;我们不能想像这些普遍原则或规则被废除或被改变。
大屠杀向我们显示,当纯粹的暴政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人类残忍本性为自己服务时,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大屠杀,就没有《宣言》。由于有了大屠杀,也就不存在对《宣言》的绝对信仰。大屠杀既表明人权的审慎必要性,也表明人权最终的脆弱性。
如果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最终产物是纳粹灭绝性的虚无主义,那么,当人类理性开始使它自己的灭绝计划合理化时,任何只以理性为指导的道德规范看上去必定是软弱无力的。如果理性把大屠杀合理化,那么,就只有一种从高于理性的来源那里获得其最终权威的伦理才能够阻止未来的大屠杀。所以,大屠杀不仅对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而且也对西方的人文主义本身提出了质疑,并且还把人权置于被告席上。毕竟,人权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一种不以神的或最终的制裁为基础、而只以人类的审慎为基础的伦理。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大屠杀之后,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一系列宗教都对人权提出了持久的知识挑战,它们都提出了一个实质的问题:如果人权的目的是限制人类的权力行使,那么,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必定是超越于人类本身的某种宗教权威。
例如,维克·佛瑞斯特大学法哲学家麦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认为,人权理念具有“无法消除的宗教性”。(注:Michael J.Perry,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Four Inqui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41.)他说,除非你认为人是神圣的,否则,似乎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来相信他们的尊严应该用权利来保护。只有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这一宗教概念才能支撑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应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普林斯顿神学家马克斯·斯达克豪斯(Max Stackhouse)认为,人权理念必须以神的理念为基础,或者至少以“超越的道德律”理念为基础。为了解释人为什么“有权利享有权利”,人权首先需要一种神学。(注:Max Stackhouse,“Human Rights and Public Theology”, in Gustafson and Juviler,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pp.13, 16.)
从一种宗教的观点看,人的位置本来是在泥土之中,而世俗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把人抬高到了神坛之上。倘若人权的存在是为了划定并维持对虐待人的行为的限制,那么,人权的基础哲学最好把人性界定为需要遏制的兽性。而人权使人性成了权衡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从宗教的观点看,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人文主义者的偶像崇拜是危险的,这有三点明显理由:首先,因为它把人类的要求、需要和权利置于所有其他物种之上,从而有把人类将其他物种完全当作其工具的做法合法化的危险;其次,因为它认可人类与自然和环境之间同样的工具性和掠夺性关系;最后,因为它缺少限制人类在诸如堕胎、医学实验等情况下利用人的生命所必需的形而上学主张。(注: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J.M.Coetzee, The Lives of Anima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人何以如此神圣?确切讲,为什么我们认为,普通人不分种族、信仰、教育和成就,都能被视为拥有平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偶像崇拜在于把任何纯粹的人类原则拔高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地位,人权看上去就真的像是偶像崇拜。(注:Moshe Halbertal and Avishai Margalit, Idola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当然,人文主义者并不真的崇拜人权,但是,我们使用崇拜的语言宣称:每个人在尊严上存在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崇拜这种隐喻暗含着一种像狂热膜拜一样的轻信,也暗含着一种无能,它不能像人文理性主义质疑宗教信仰那样去质疑人文主义自己的前提。这种对人文主义人权观的批评的核心在于,人文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它批评一切形式的崇拜,但不包括它自己的崇拜。
为了不自相矛盾,人文主义者必定会对此批评作如此答复:人没有什么神圣的,没有什么值得崇拜或得到最终尊重。关于人权,能够说的是,它们对保护个人免于暴力和虐待是必需的,如果问为什么,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历史的。人权是一种语言,个人通过这种语言来保护他们的自主不受宗教、国家、家族和群体的压迫。不难想见,用以保卫人的其他语言也能被发明,但此时此刻我们所能够使用的就只有人权这种语言。而且,人文主义者还必须补充道:人权语言在道德争论中不是一张最终的王牌。任何人类语言都不具有这样的力量。事实上,权利冲突及其判决牵涉很困难的权衡和妥协。这正是为什么权利不是神圣的、那些持有权利的人也不是神圣的原因所在。做一个权利持有人,并不意味着持有某种神圣不可侵犯性,而是让自己在共同体中生活。在这一共同体中,权利冲突通过说服、而不是通过暴力而得以判定。伴随着权利理念的是这样一种承诺:尊重他人合理的承诺,使争端以裁判方式解决。权利要求的基本道德承诺不是尊重,更不是崇拜,而是协商。(注: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1996.)与另外一人协商的最低条件不一定是尊重,而仅仅是消极容忍。这是一种留在同一间屋子、聆听其不想听的主张的意愿,其目的在于达成妥协、防止相互冲突的主张以对任何一方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告终。这就是对人权的共同承诺所要求的。
这种答复不可能使一个信教的人满意。从宗教的视角看,如果像人文主义者那样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尽管他人认为神圣的东西有权得到保护,那就等于是解除了对人的权力行使的任何限制。
神圣的理念——存在超出了人类知识或表述的某些领域、永远存在超出人类洞见的西奈山这一理念——应该对人的权力意志设置限制。即使作为隐喻——与任何形而上学主张相脱离——神圣也暗含着这一理念:必定存在着没有人能够越过的道德底线。很明显,人权思想试图对该底线作出界定。但是,从宗教的观点看,任何对人的权力行使设定严格的世俗限制的企图都必定会弄巧成拙。没有神、神圣的理念以及对理性和权力设置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理念,就不可能有使我们人种免受自己伤害的可行保护。争论最后落到一点上:宗教方相信,只有当人跪倒在神的面前时,他们才能够避免自我毁灭;而人文主义者则相信,人只有在站立起来之后才能拯救自己。
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论,每一方都能从历史上找到有力的论据。宗教方面最有力的经验证据是,为宗教确信所激励的男男女女能够站出来抵制暴政,而那些没有这类确信的人则不能。在苏联劳改营,犹太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树立了令人鼓舞的尊严不可摧毁的榜样。同样,在战争期间促使波兰的一些天主教牧师和普通信徒掩护犹太人的也正是宗教确信。最后,除非我们记住宗教领袖、隐喻和语言在激发个人冒死争取选举权中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这些例子比形而上学的论证更加重要。不过,世俗主义也有它的英雄。抒情诗人安娜·阿克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作品代表同她自己一样在苏联劳改营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全部女性发出了苦痛之声。 普利默·列维(Primo Levi),一位世俗的犹太人和科学家,为那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毁灭的人提供了见证。他的著作是世俗理性能够表述邪恶暴行的警戒性证词。道德勇气可以从它所能够找到的任何地方汲取资源,世俗的和宗教的发源地都有卓绝的英雄。
如果我们从英雄主义的发源地转向邪恶的发源地,宗教方就不能主张,对上帝的恐惧阻止了人们穷凶极恶。至少人的道德需要用神圣感来维持这一说法的经验基础非常虚弱。事实是,神圣的目的经常被用作实施不公正的借口。毕竟,宗教是一种让其主张无可争议的基本教义。相信你拥有不容置疑的信仰基础,而且上帝命令你去传播信仰,这为酷刑、强行改变他人信仰、对异端定罪、烧死异教徒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根据。就普通个人的人权而言,一切基本信仰都是其长期存在的威胁。
另一方面,很难否定宗教抗辩的力量——20世纪所发生的令人憎恨的暴行是世俗傲慢以及人类被其所掌握的科技所陶醉,丝毫不受伦理的限制的权力的真实写照。如果历史可以被看作一位相关的证人的话,那么它的证言既没有印证信教者的主张,也没有印证不信教者的主张。在极恶面前,世俗的人文主义以及古代信仰要么是彻底的受害人,要么是热情的帮凶。
我们由此如何作结呢?人文主义者将指出,宗教声称它们的上帝是神人同形的,但同时却又声称,它们的上帝不能被人所代表。此种矛盾是偶像崇拜的,但它又是一种必需的偶像崇拜,信仰者必须崇拜某一事物。他们的虔诚必须落到某种能够给祈祷者以焦点的影像或对象上。因此,在大多数世界宗教中,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偶像或神像。偶像崇拜由此成了任何宗教的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如果宗教如此,那么人文主义也必然如此。人类可能无权自我崇拜,但是人类需要对自己有某种信仰,以支撑保护自己的承诺。不言而喻,此类信仰只能是有条件的,因为有证据表明,人类有时连禽兽都不如。
偶像崇拜理念要求所有的信仰者,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保持清醒;它要求他们不断省察自己的热情和过剩的正直感。认识到偶像崇拜的危险的信徒,能够仔细省察自己的信仰,以发现傲慢、狂热以及对其他信仰者不宽容的征兆;不信教的人则应提防对他人宗教确信的那种伏尔泰式的轻蔑。此种轻蔑假定,人类理性能够评判各种竞争的信仰形式的真理内容。世俗的理性没有这种权能。因此,不管是对教徒还是对俗人而言,偶像崇拜的隐喻是一种既是对轻信,又是对轻蔑的限制。对不信教的俗人而言,如果他们认为“出埃及”只是对宗教轻信的一种警告,那他们就严重误读了“出埃及”这一故事。这一故事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警告,它告诫我们:无论信不信教,人是易犯错误的;我们有崇拜自己制造的偶像的弱点;我们不能不停止崇拜那些纯属凡人的东西。崇拜人、因自己是人而引以自豪的人文主义无疑也像那些声称知道上帝为人所制定的计划的宗教信仰一样是有缺陷的。并不崇拜偶像的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它拒绝提出它不能充分证明的形而上学主张,它具有充分重视“出埃及”的可怕警告的智慧。
不过,哪怕一种卑微的人文主义原本也应有勇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权在根本上需要神圣的理念。如果神圣的理念意味着人类生活应该被珍爱和保护,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理念需要神学基础呢?为什么人类需要一个上帝的理念来支撑有关不能对其同类为所欲为、不能对他人实施殴打、酷刑、强制、灌输或者以任何其他违背其意愿的方式要其做出牺牲这些信念?这些直觉只是源于我们自己的痛苦经验以及我们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相信人是神圣的,并不必定强化这些律令。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常发生:人们往往以某种神圣目的来为酷刑和迫害行为提供正当性。的确,纯粹世俗伦理的力量在于,它坚持没有所谓的“神圣”目的能够为不人道地利用人类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一种反基础的人文主义看上去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它有利于阻止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残暴的正当化。
对人权的一种世俗辩护依赖于道德相互性理念:即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简单测试来判断人类行为。既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我们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人希望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虐待,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类做法应该被禁止。我们的这种思想尝试——即,我们对他人的痛苦和屈辱感同身受的能力——只是有关人类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有这种有限地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所以我们都有良知。因为我们都有良知,所以我们希望自由地表达那些正当性。有些人对他人的痛苦很冷漠,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良知,而只表明良知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令人遗憾的:它使人能够自由地选择恶行,但是这种自由正是良知的构成要素。关于人类的此种事实——即他们能感受痛苦,他们能认识他人的痛苦,他们能自由地弃恶从善——为我们有关一切人应得到保护以免遭暴行的信念提供了基础。这种有关人类共有的、最低限度能力的概念——同情、良知和自由意志——从根本上描述了一个人要想成为任何一种意志主体所需要的东西。保护这一主体免遭暴行意味着授予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核心权利。那些坚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需要配以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人提出了一种正确主张——个人权利只有在集体权利的规定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行使——但它们也可能遮蔽了个人优先于集体的这种关系。没有集体权利的个人权利将很难行使,而没有个人权利的集体权利则只会以暴政告终。
而且,权利膨胀——把任何可欲的事物都界定为权利——会以腐蚀权利保护内核的合法性而告终。只有那些为任何形式的生活所必需的权利才可以被正当地视为核心权利。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张是,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是最终获得社会和经济保障的必要条件。没有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没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财产自由,意志主体就不能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社会和经济的保障而斗争。
一如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所认为的, 言论自由权并非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而是拥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森评论说:“在任何一个拥有民主的政府形式和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不会发生真正的饥荒……”(注:Amartya Sen,“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 in Bauer and Bell,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pp.92—93.)在亚洲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人民的“发展权”和经济进步的权利优先于他们在表达自由和民主政府方面的权利。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此类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既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基本动力,也是防止政府的强行计划和方案的重要保障。引用森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的标题来说:自由就是发展。(注: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宗教思想家对人权的这样一种世俗辩护必定会感到不满。对他们来说,世俗的人文主义是欧洲晚期文明的偶然产物,它不可能在非欧洲和非世俗文化中博得赞同。因此,人们付出了大量努力来证明《宣言》的道德基础来源于世界主要的宗教教义。《宣言》由此被解释为长年积淀的道德智慧的总和。保罗·戈登·劳伦(Paul Gordon Lauren)的人权理念史著作一开始就对世界各宗教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如此作结:“没有哪个单一的文明、人民、民族、地区、甚至世纪能够声称,有关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的信仰是它自己所独有的。”(注:Lauren,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11.)
这种宗教调和论作为一种鼓舞性的辞令无伤大雅。但是,就如劳伦自己所承认的,只有西方文化把广泛被分享的有关人类尊严和平等的命题转化成了可行的权利教义。这一教义并不起源于吉达或北京,而是起源于阿姆斯特丹、锡耶纳和伦敦以及任何欧洲人试图捍卫其城市和庄园的自由和特权不受贵族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侵犯的地方。
指出权利的欧洲起源并不在于认可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历史先前性并不赋予道德优越性。就像杰克·唐纳利所指出的,《宣言》的历史作用不在于使欧洲的价值普遍化,而在于把其中的某些东西——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永久禁止。(注:Donnelly in Bauer and Bell,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p.68.)非西方的人权反对者将有关“普遍性”的宣称视为西方骄慢和麻木的一个例证。但是普遍性也意味着连贯性:西方不得不实践它所鼓吹的东西。这使西方被置于永久的考验之中,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
五 西方与自己悖反
在“西方”与“非西方”的道德争论中,争论双方都犯了这样一种错误,它们都假定对方在用一种声音讲话。非西方世界在看待人权时,不无道理地假定该话语来自主要西方国家所共有的一系列历史传统。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对各自的权利传统的核心原则的解释非常不同。共同的传统并不必定导致有关权利问题的共同观点。对权利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西方文化——英国的、法国的和美国的文化——对隐私权、言论自由、煽动、持有武器的权利、生命权等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宣言》颁布后的50年里,相互竞争的西方权利传统之间的这些分歧更加突出。事实上,西方的道德一致——一个从外面看总是比从内部看更具说服力的神话——正在瓦解并暴露它不可改变的异质性。美国的权利话语曾经属于欧洲共同的自然法传统和英国的普通法。但是,这种与欧洲同根同源的意识现在受到日益明显的美国道德和法律例外主义意识的挑战。
过去二十年里的美国人权政策越来越与众不同和自相矛盾:美国是一个有着伟大的国内权利传统的国家,并领导世界抨击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行径,但是它自己却拒不批准国际权利公约。对国际权利规范在国内实施的最重要的抵制并不来自西方传统之外的无赖国家,或来自伊斯兰和亚洲社会。实际上,它来自于西方权利传统本身的核心,来自这样一个把权利与人民主权联系起来,将国际人权监督作为对其民主的侵犯而予以反对的国家。在《宣言》通过以来的人权史上所有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中,最让埃莉诺·罗斯福吃惊的一个就是她自己国家现在竟然在人权问题上已变得如此不合群了。
我们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50年中支撑1948年《宣言》的道德共识将进一步发生分裂。无论人们如何大谈共同价值,美国和欧洲在权利问题(如堕胎、死刑)上的差距可能加大,就像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加大一样。没有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道德全球化。事实上,有理由认为,随着经济将其商业实践、所有权、语言、通讯网络统一起来,一种旨在保障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本土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的完整的反向运动正在逐渐形成。
这并不预示着人权运动的终结,而是预示着人权运动迟到的成熟:它将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中,在有关我们对人类能或不能做什么、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讨论中,每个不同的文化都有权受到平等的考虑。实际上,这可能是人权在人类进步史上最核心的历史重要性:它废除了文明和文化的等级制。直到1945年,认为欧洲文明对受其统治的文明具有固有的优越性仍是正常的。很多欧洲人依然如此认为,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更中肯地说,一些非西方人也想当然地认为统治他们的文明具有优越性。他们不再有任何理由继续这么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理由在于人权的全球扩散。该语言最一致地表述了地球表面一切个人的道德平等。但是,它同时也在权利主张的意义、实施和合法性上增加了冲突程度。权利语言认为:在有关我们彼此应该如何对待的实质对话中,所有人都有权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一旦授予这种讲话和被倾听的普遍权利,就必定会带来混乱拥挤,必定会出现嘈杂声。为什么呢?因为,欧洲的声音曾经以其专横的统治来平息喋喋不休,但它现在不再有这样做的特权了,那些跟它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人也不再授予其这样做的权利。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进步,是朝为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所梦想了几千年的理想世界——一个所有人道德上真正平等的世界——迈出的一步。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一个道德平等的世界,也是一个冲突、协商和争论的世界。
重复前面提到的一点:我们不应再把人权视为王牌,而是要开始把它视为一种为协商奠定基础的语言。在此见解中,我们共同的基础事实上非常有限:至多是这样一种基本直觉——对你来说是痛苦和羞辱的事情对我必定也是如此。不过,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这样一种被平等分享的未来,权利不是全球社会的普遍信条,也不是一种世俗宗教,而是更为有限、但依然弥足珍贵的事物:我们的争论得以开始的共同词汇,人类繁荣理念得以生根的质朴的人类最低限度。
胡水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