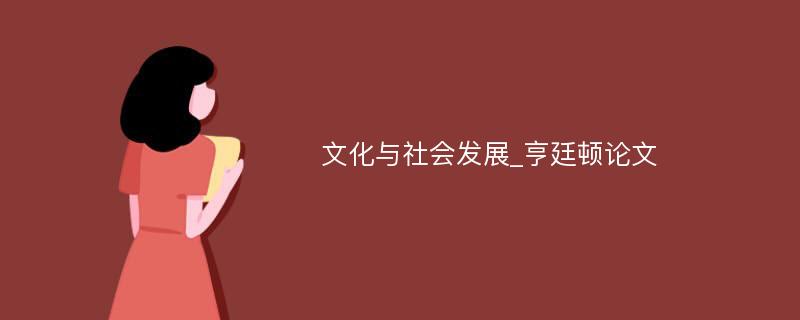
文化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2—0161—05
一
文化能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文化价值观念能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构成阻碍吗?假如答案为是,那么此种阻碍了生产力的文化形态,有无可能使之转化成为积极的因素?如果可以,转化又如何进行呢?强调文化跟发展的关牵,是否会导致大国沙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蔓延?这些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判断可以解决的。本文主要围绕美国两位学者劳伦斯·哈里森与塞缪尔·亨廷顿近年主编出版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发展》一书,来深入探讨以上显然是一言难尽的文化困顿。
今日全球化一路畅行的直接结果似乎是世界发展愈益不见平衡。贫富悬殊不见弥合,反见扩大,富国愈富,穷国益穷,财富分配没有公平可言。何以贫穷终是难以消除?何以第三世界少有国家走上富裕之路?是不是这一切都要怪罪于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主义侵略?劳伦斯·哈里森与塞缪尔·亨廷顿2000年主编出版的这本大著《文化的重要作用》,反过来是将眼光投向文化领域,以为工业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以及穷国底子薄、教育基础差、国民素质低、缺乏机会和资金、市场不健全和基本设施薄弱等等这些老牌因素,都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不发展的根本原因。那么根本原因又在哪里?是在文化。正是这一文化决定论的视野,令此书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异军突起,它想要说明的实在是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化有高下优劣之分吗?在人类创造自由和繁荣的过程中,某一些文化是否要优于另一些文化?
《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收集了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和记者的文章。两位主编之一哈里森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发展,1965年到1981年曾任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官员, 负责美国对五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事务。亨廷顿更是大名鼎鼎无须介绍,这位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学院主任1993年在他的题为《安全环境的改变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报告中,即已提出有名的“文明冲突论”,断言冷战以后的世界冲突将从意识形态冲突转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化的重要作用》前言中,亨廷顿称1990年他比较了60年代初非洲的加纳和亚洲的韩国的经济资料。发现这两个国家当时的条件惊人地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同,原材料、制造业、服务业在经济中的结构相似,都大量出口原材料。只是韩国稍多一点制造业而已。此外,两个国家得到的国际援助也大致相同。30年后,韩国成了工业巨人,经济居世界第14位。拥有汽车出口和电器产品的名牌跨国公司。人均收入大约与希腊持平。同时国内政治也日益民主化。加纳呢,恰恰相反,停滞不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是韩国的1/15。如何解释如此巨大的发展差距?亨廷顿认为这里面固然有不少因素,但是文化是主要原因:韩国人崇尚节俭、精于投资、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而加纳的价值观念却不相同。一句话,文化导致了它们巨大的经济差别。
劳伦斯·哈里森也是个招致争议的人物。1985年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出版其著作《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个案》。书中哈里森提出拉丁美洲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来自其本身的文化,而不是殖民主义影响。他列举了一系列国家作为对比: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巴巴多斯和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结论是文化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差距。哈里森还比较了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系拉丁美洲,比较它们文化的相似性及发展结果。此书一出,如众矢之的,引来经济学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片抗议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亨廷顿和哈里森指出,长期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和依附理论等。首先谈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帝国主义顾名思义是征服和控制,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饱和之后,必然要寻找新的投资市场,向外扩张,开拓殖民地,掠夺资源,寻找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控制他们的经济,愈见贫困。其次,中心和边缘理论。它又称世界体系理论。说是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就形成了全球经济中心,围绕中心依次是半边缘、边缘和外围地区。中心国家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半边缘包括南欧、意大利及地中海国家。边缘地区指更远的波兰等国。亚洲和非洲均属尚未与中心建立联系的外围地区,逐渐被殖民主义强行拉入世界系统。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加上了美国和日本。边缘则是整个第三世界。今天虽然老牌帝国主义如大英帝国消失了,但是作为中心的工业化国家利用经济优势依然牢牢控制着世界贸易市场。最后,依附理论。它意味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关系使得第三世界始终无法解脱对工业国家的依附。第三世界以出口原材料为主,工业大国压低全球市场原材料的价格,同时抬高制造产品的价格,从中获取超级利润。这便是何以拉丁美洲与北美洲近在咫尺,经济发展却有天壤之别的缘故。
但是《文化的重要作用》的两位编者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自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引进自由市场机制,亚洲四小龙在世界市场崛起,墨西哥加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经济圈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曾是学界热门话题的“依附理论”如今已成昨日黄花,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解释今天的世界发展,同样已经不能令人信服。二战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之所以令人失望,是因为各国政府及组织只顾经济,而忽略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影响。这导致上个世纪最后10年的发展理论出现了一个理论真空。对此亨廷顿在该书前言中断言,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而文化毫无疑问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对于“文化”这个定义多不胜数的概念究竟作何界定,亨廷顿也毫不含混表明了他的看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定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①。
很显然,亨廷顿是舍弃了文化的物质层面而专取文化的精神层面。要之,文化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二
以文化为社会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强调它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并不是亨廷顿和哈里森的独到见解,它至少可以上溯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中韦伯明确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就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我们是按照这个个体的文化意蕴,而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概念整体。换言之,它毋宁说就是一种文化。很显然韦伯已把文化视为独特的价值体系,认为它是历史运动背后的推动力。由此他反对物质决定观念的思想,反对把社会变化看作是经济法则直接决定的客观历史过程。依据韦伯的文化社会学模式,人类行为不是哪一种特定物质力量的自然的产物,在其背后交集着物质和观念的复杂动因,这些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层面的复杂因素,就是文化价值。
韦伯以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崛起的根本动因,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文化就不复是经济基础的一个简单反应,而是本身同经济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甚至反过来,经济将因为文化的形态而得到说明。但是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前景显然都不乐观。他这样描述现代性的特征和命运: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结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②
世界既然已经祛魅,那么现代社会的命运就不复再现前现代社会中那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最高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体现自治和自由的各个不同领域。韦伯对此的看法极为悲观。而此悲观情绪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尼采对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像价值的多元性、历史发展多重性,以及对现代工业社会自治和自由前景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都是尼采和韦伯思想的显著特征。这可见,认可文化的重要作用,还远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即便立足文化来解释社会、人类的发展,问题依然接踵而至:何种价值观念促进发展?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何种文化因素促进或阻碍发展?如果传统价值观不发生大的改变,民主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否仍旧能维持?此外,何种政策和体制反映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相冲突时又当何论?如此等等。针对上述问题,亨廷顿将人类发展定义为:通向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变化。而达成这一目标,对文化价值观就必须进行微观层次的分析。关于文化价值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给价值观下的定义是:人类个人或群体所持有的关于什么是必须的、恰当的、好的或坏的思想。故价值观代表人类文化的重要差别,吉登斯进一步解释说:文化由特定群体成员的价值观,他们的准则,及所创造的物质事物组成。价值观是抽象思想,而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原则或惯例。准则代表社会的“可行”和“不可行”。因此,一夫一妻即忠于一个婚姻配偶,是多数西方社会的价值观。③
吉登斯指出价值观念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不计任何代价。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放弃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国家而献出身家性命。在这方面,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的“伦理”范畴。遵循内在价值观的行为即是“道德”。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会按其内在价值观行事,是价值观又是工具性的。持某一价值观是因为这价值观会带来好处,如教育、投资、发展经济。所有的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性的。吉登斯认为,促使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工具性的。比如一些国家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还是像贫困的时候一样努力工作,投资竞争,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已经不复需要如此拼命。故而,只有在“发展”或“致富”成为内在价值观念的情况下,经济才能有出色发展。如果价值观是纯粹工具性的,那么饱暖思淫欲,或者即便不好淫欲,也自有别的享受和诱惑,总是富裕便不思进取了。这似乎还是典型的清教主义价值观。
三
亨廷顿和哈里森注意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如研究东亚的学者发现亚洲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是儒家的价值观念。日本与东亚的四小龙都受儒家精神影响,与新教国家相似,都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快速发展。显而易见,勤奋工作、注重教育的价值观对这些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拉丁美洲呢?哈里森过去20年悉心研究了拉丁美洲文化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指出亚洲的发展直到最近才引起拉丁美洲研究者的注意。而对这些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则经常是被忽略了。哈里森旁征博引,两相比较,进而归纳出他所谓的十种动态文化和静态文化价值观念,言下之意,拉丁美洲还是流连在多少已经显得跟不上趟的静态文化价值观念之中。以下是哈里森归纳的动态和静态两种价值观的区别:
其一,时间观念取向上,动态文化强调未来,静态文化强调过去和现在。而未来的取向意味着进取的世界观。其二,对于动态文化,幸福生活的核心是工作与成就。勤奋工作、创造与成就的奖励不仅是物质,同时也包括满足、自尊与威望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工作与成就在静态文化中就不是那么举足轻重。其三,动态文化强调节俭与投资;静态文化强调平均主义。其四,动态文化视教育为发展的关键;静态文化中则除了社会的少部分精英,基本上不重视教育。其五,动态文化强调个人能力;而静态文化中家族关系更为重要。其六,动态文化中社会认同与信任的辐射半径超越家庭界限进入社会;静态文化则反之,只局限于家族,从而容易导致腐败、裙带关系和逃税现象,同时家族观念重则较少关心社会慈善事业。其七,动态文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代码比较严格,比较清廉;静态文化的社会大体反之。其八,动态文化中公平与正义是非个人的,因而被广泛执行;静态文化中的公平与正义则常常与熟人和黑金有关。其九,动态文化的权威是分散的、平行的,鼓励不同意见。静态文化的权威是集中的、从上至下的,鼓励正统。最后,动态文化中宗教对公民生活的影响较小,静态文化中宗教的影响较大。前者鼓励异端和不同政见,后者强调正统与一致性。两相比较孰优孰劣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去除上述文化价值观的所谓“静态”特征,使之向明显更具有竞争力的“动态”模式发展,似也为当务之急。但是,这种两分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说的,英美帝国主义是拉文化作为殖民侵略的遮羞布,这还令人颇费猜测。哈里森本人也承认这十种区别比较一般化和理想化。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并非如此黑白分明,而是具有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点。
应当说,文化决定发展的结论,人文学者可能举双手赞成,经济学和人类学者未必会以为然。文化可以从外部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吗?进而视之,既然认可民族无分大小,一律平等,何以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有优劣高下之分?所以说到底,亨廷顿等把文化的重要作用一路重申下来,是不是最终肯定现代欧美社会的根本优越性,强化欧美自鸣得意的文化和文明观?谁给了两人对其他文化说三道四的权力?的确,文化究竟又能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呢?这些问题思想起来,确实是耐人寻味。毕竟,发展如今已成全球四海之共识,让文化出来担一点肩膀,也是势所必然了。即便回过头来看亨廷顿和哈里森悉心推崇的马克斯·韦伯,其将文化的自治原则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加以分析,固然能为大多数人首肯,但是韦伯将文化结构从它同其他社会力量广泛且复杂的关系中抽绎出来,将文化界定为一个独立的独特王国,只服从它自己的独特原则,也遭来了不少非议。如英国社会学家斯温基伍德在其《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一书中,就对韦伯提出了以下批评:(韦伯)强调文化的内在性质,有可能冒将它同历史过程割断开来的风险,而把自治原则看作某种比如区分过程的自动产品。文化的自足性不是先天给定的:它必然是个人和集体行为两相结合所造就。说到底,自治原则一定不能转化为非历史的抽象,而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具体性上面。④
这个批评意见无疑是比较中肯的。文化价值观肯定不是抽象的东西,而必然有它的历史具体性。就以上亨廷顿和哈里森以“动态文化”而标举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应当说凸现的更多是一种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在我们的土地上不是过剩而是依然有待启蒙。而且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价值理性的黄金时代可以缅怀流连。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它涉及到一系列彼此间不断强化的现代性过程,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率的提高,政治中心权力和民族意识的培育,以及扩大规模教育和更新价值观念等,这一切都涉及到制度层面上的改革。而《文化的重要性》一书的一个母题是文化是制度之母。由是观之,多视角来深入探究文化价值观对进步和发展的影响,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
收稿日期:2005—10—25
注释:
① L.Harrison and S.Huntington,eds.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Basic Books,2000,p.15.
②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3页。
③ Anthony Giddens,Sociolog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31.
④ Alan Swingewood,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