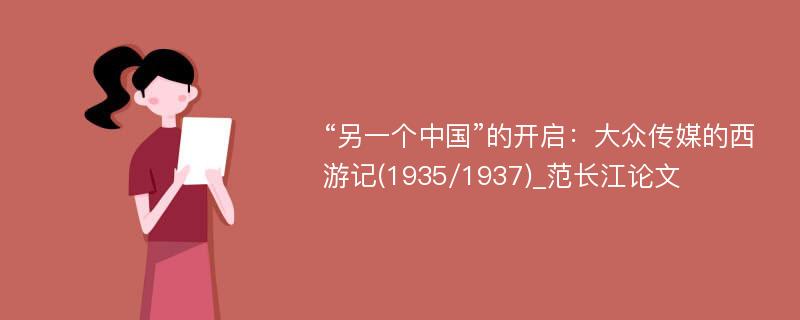
“另一个中国”的敞开——大众媒体的西部行记(1935-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中国论文,西部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1-0152-08
晚清以降,中国历史进程重峦叠嶂,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关涉现代文化走向的重大转变发生。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的放弃华东而被迫开发华西,使之现代化,也许终要被人视为当代最富于革命意义的事件”。①《孟子·尽心上》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抗战后的西迁固然波澜壮阔,但千万人的心史,难以把捉的程度也同样惊人。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想象有深厚的关系;抗战前夕媒体的西部行记提供了具体渠道,从可把握的文学角度,提前透视战后民族共同体经验塑造中,西部中国的华夏边缘因素、西方现代化的因子、红色中国的建立等所发挥的作用。
从1934年年底开始,向西南和西北进行的红军长征和“剿匪”,作为互动事件,不断吸引大众媒体,把它们对“剿匪”的兴趣,从江西引向中国西部,也使1928年后媒体对“剿赤匪”的关注,与“九一八事变”以来因“开发西北”不断升温的对西部中国的关心两者合流。②拔得头筹的《大公报》,就有诸如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等亲历记,而记者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系列西部行记,又最为成功,在创造销量奇迹的同时,还被沈从文、曹聚仁等新文学家不断表彰,认为他“值得人特别注意”③,是“时代的骄子”、“开创报告文学的彗星”。④西部中国与东部现代化差异性的文化因子,经由多种语词的塑造、透视,分外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眼中。而埃德加·斯诺等后紧随范长江的脚步,亲历延安红区,他们敞开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其风景与人物、精神与生活,因与国人“世界想象”的特殊关联,更是备受瞩目。
语词与西部中国的呈现
范长江跟随红军,穿行在现代化滞后的广阔西部。洮河地区为汉、藏、羌、回交合地。祁连山南北分别是青海、甘肃两省。南北延伸的贺兰山,东面宁夏,过黄河接陕北,西临阿拉善蒙古,南望兰州,北眺大青山而向包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界定西北地理与文化的畛域。据《明史·地理志》载,自明代以来这里就属于中华帝国腹地内陆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带,既是防止北面蒙古势力来犯,沿长城而设的宁夏固原、陕西榆林、延安和绥德等“九边”之西面重镇,又在维护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安全而筑的松潘和洮河等“诸边”沿线,而1930年代此地的民族态势还多少有明朝的遗绪,比如洮河藏族杨积庆土司“受封于明代,世袭已十余代”。⑤范长江用“我们东方人”称呼读者,也是1935年如张恨水《西游小记》等惯常使用的观察视野。⑥现代汉语受舶来印欧语系影响,人称代词“我们”并非许多可识别身份的客体之叠加,而是“我”与“非我”的联结。“我们东方人”的表述中,“我们”意指记者“我”和言说对象、报刊的读者“你”;而与之区隔的“非我”,即他,乃是与东方相对的“西部中国”。范长江及其周边媒体《国闻周报》、《大公报》上众多西行记,通过“旧”、“新”、“无”三类语词完成东西“两个”中国,及其背后现代性关系的述说。
所谓“旧语词”,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关于西部的诗文世界、传说故事、羁旅、远征的文人感受和历史史实。如杜甫《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明杨一清《边城》“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四时常见雪,五月不知春”;唐岑参《送崔子还京》“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等,都内化到作者自己的西部书写中。几乎无一事不曾咏,无一景不相似,无一物不承载历史记忆因子;亲身经历证之以历史记载,酿就古今同一的感受。拥有共同历史记忆的人们,在如今,才可能切实成为同思共感的共同体。
另一为“新语词”。它们既有1935年长征的红军和“剿匪”的国民政府新近带入西部引发冲突的词汇、对西部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又有当地社会受新入语词冲击,龃龉、摩擦中,予以回应的本地方言,对于“我们东方的读者”来说,也是“新奇”的。1935年的红军长征和“剿匪”,直接引导两种现代力量进入西部中国。一是红军带来的现代力量:打土豪、分田地,贴标语,贯彻苏维埃,开学校,开群众大会……正如奥托·布劳恩(李德)事后回忆,在占领遵义和桐梓后,“中央红军……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组织宣传鼓动队,召开群众天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储存物资和劳动工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穷人,建立自卫队和征募自愿兵,甚至还规划了土改的最初步骤”。⑦“展开”、“组织”、“召开”、“成立”、“没收”、“分发”、“建立”、“征募”、“规划”这一连串动词引导的动宾结构短语,生动地描述红军对当地的主动介入和改造。二是国民政府为追剿红军,在西部修公路,输入统一的国家理念和现代国民意识,完善现代政治运作模式和军队管理等。以四川及周边为例,为便于剿匪,川鄂、川陕、川黔三大公路开始修建,西南和西北跨省级的公路网络得以连通。⑧而蒋介石亲到西部督剿,强调落实“新生活运动”,“剿匪”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⑨
可以说,重振社会价值伦理、行为规范,重构一个现代的秩序化社会,是国共两方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军事之斗背后,亦是两种现代秩序的对抗。当时在西部乡村随处可见的标语,如徐向前部队在涪江旁的中坝留下的“平分土地”、“赤化全川”、“武装拥护苏联”,岷河沿岸镇集处处是表现国民政府政绩的“××委员(或×长)为开发西北而来!”、“欢迎××委员保护西北民众”⑩等等,即是这两种现代力量对抗最外在的表征。有时候,一块墙壁被反复书写。《黔滇川旅行记》的作者薛绍铭在遵义发现:“城内标语,多被洗刷,乡间则因不胜洗刷,残留者仍多。其标语下所书部队番号,多为暗号,如‘红教政’、‘红南政’、‘红贵政’等。国军之标语亦然,如‘广东政’、‘天津宣’、‘台湾政’、‘明光党’等。”(11)受苏联及欧美影响的敌对两方,现代化的宣传手段,有相似之处。在强大的现代化潮流面前、滞后而边缘的西部中国,各种文化元素急剧冲突。
范长江等人的西行记,正是抓住这种冲突,敞开了“另一个中国”光怪陆离的文化面相。范长江在四川江油附近发现:
“白石堡仅三五家居民,徐向前部占白石铺时,此间居民亦曾被召集开会,组织‘苏维埃’。据一壮年男子与记者谈: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职大小。记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员’。农民头脑简单,不了解复杂名词,故只记得‘土地’二字,令人发笑。再叩以归何人管辖,答以‘苏先生’,问‘苏先生’之名号籍贯,他又茫然无以对。问其见过面否,答以‘未’。继而曰:‘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记者始恍然,所谓‘苏先生’,乃‘苏维埃’之误。”(12)
对“苏维埃”的误解,张国焘《我的回忆》后亦曾记述。(13)薛绍铭的描写则更为风趣:
“据谈番民中有土司苏永和者,茂县、理番等处番民多受其管辖。共军初至,他向共军问以‘你们是不是皇兵?’共军答以‘我们不是皇兵是红军。’他又问道:‘红军是谁家的兵?’共军答以‘红军是苏维埃的军队。’苏永和一听到个苏字,就高兴起来说道:‘原来你们是我本家的军队,我的本家坐了江山我还能蒙点福呢。’乃赠共军以牛羊腊肉等食物。后来参谋团派高级参谋李某前往抚慰番民,番民见李参谋,均头上顶一木盘,内盛核桃仁等物,跪地以迎,不敢仰视,只呼钦差大老爷皇上爷爷万岁。番民尚不知有民国,对他们宣传共产主义当然是‘对牛弹琴’了。”(14)
当红军带来的现代新名词(或翻译,或组合),遭遇到西部社会时,当地人熟悉了这些词语,但并不了解其应当如何使用的“语法”——词语之网背后的“物之序”和意义世界,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他们仍在旧有的认知轨道,来理解这些词语。如“土地委员”,他们单取“土地”一词,担任此职务时,脑海中出现的是土地庙中的土地爷,至于什么是“委员”,“土地”和“委员”组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不甚了然了。归“苏先生”管辖背后是传统官民社会的常识,他们并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怎样的、新的组织模式和社会秩序。对义素进行组合、表示西方新概念,是现代汉语构词的主导方法。对当地人来说,“土地委员”之所以不被正确理解,但可在“误解”的基础上使用,正在于新汉语词汇建立过程中,那些旧词、旧字的义素仍然残留。值得注意的是,产生趣味的基础是,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少是先于此地的人,明白这些现代词汇的大致意义。
蒋介石在四川输入国旗国歌、贯彻执行命令的能力、善于组织训练与赏罚等现代国民常识及革命建国举措。(15)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昌裕、丁东“剿匪在四川”等亲历记,以故事的方式、通过方言与国语之冲突,描写了当地社会遭遇国军这些整齐划一的现代理念、知识谱系时的不适应,在调侃滑稽中展示“另一个中国”匪夷所思的面相:
“(各路军阀)从六路会剿发动时起,便不约而同地采用‘不来气’(川谚,不理的意思。)或‘你来我不来’的法子来敷衍刘湘。”
“那时竟有那样的流言,说各路军中怀着‘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鬼胎的大有人在。在第四次剿匪会议中,被恐怖驱迫着的他们……‘剿赤以后究竟如何’提了出来。还怕会议上的话是‘水的’(川谚,不可靠的意思)。”
“过去十个月四川剿赤军如果说是‘打’赢了的,确实有点夸大,只好算是‘蹬’赢的(‘蹬’是川谚即普通话‘熬’,北平话‘耗’的意思)。”
“老兵这样感奋地说过:‘我们这回打赤匪,得到这些东西吃,真算是‘开洋荤’,不过这一下可把人‘方倒’了!吃人家一支纸烟,穿人家一双草鞋,也不好意思不努力呀!如果还像以前打那样的仗,我早就开小差了!’(‘方倒’川谚,是被情面拘住的意思)。”(16)
地方军阀们对国民政府的命令“不来气”,源于其自我意识及现实处境都是游离于现代国家之外的武装,有时是破坏社会的匪,有时是捍卫正义的兵,彼此靠信用、义气而非科层制命令。他们担心国民政府承诺是“水的”,剿完赤匪后,再以“匪”的名义剿他们。因此,他们剿匪时才会“蹬”,在方言里,“蹬”有因怄气而懒惰的意思。兄弟义气,构成军阀对战争理解的基础,这与蒋介石革命建国的现代举措,显然不搭调。老兵则以“方倒”的人情感受,而非国民与国家权力与义务的双向关系,看待国民政府的慰劳。
这些方言词,既有中国古文化通语及俗语的遗留,又有地方文化,如四川帮会组织袍哥的暗语。(17)通过语言透视文化,当整齐划一的现代理念,冲击到各种文化芜杂并存的当地社会时,特派员、甲长等民国的痕迹,北洋军阀、义和团、地方宗教等东部不同时期的历史似都能共时地在这里找到影子。如老将军刘存厚,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头衔,“但是在脑海中依然憧憬着‘吴玉帅’统治时代”,“所用的国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标榜“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嘉禾章,崇威上将军”等北洋时代的荣誉,形式和精神上都“完全继承着北洋军阀时代的典章文物”。(18)对于“我们东方人”的读者来说,西部社会与输入的现代之间的冲突和龃龉令人忍俊不禁,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读者,似不会把当时国歌中的“咨—尔—多—士”错唱成“一—二—三—四”。(19)而正是这些不和谐音,“我们东方人”才有机会以西部为镜,审视自身现代诸观念的深浅。
范长江与他周边媒体西部书写的差异在于,并未停留在将“他世界”作为“我世界”的镜像,或现代观念、历史文化记忆的投射。他的洞见是,发现华夏边缘地域,也有“我世界”缺乏的文明养料。范长江不懂藏语,但他认为藏人“男女杂沓、红衫辉映,一双双,一对对,情歌缭绕,呼应和答”的男女关系,“比汉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美满得多”。藏女“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现在,所谓文明民族,办到这个程度,还不是短时间的事情”。(20)“无语词”、语词不通,背后是民族、宗教区别带来的文化差异,除为文本添加奇幻的文化色彩外,最终解决的是我们怎样共同“近代化”的问题;“他世界”成为“我世界”现代欲望的影子。平心而论,范长江的西部行记不以“稗贩异国情调”“夸世骇俗”,他情感上“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故文学表达上时有“汲彼醴泉,挹吾悬圃”的表现。(21)
范长江及其周边媒体的西部行记,擅长以多语词的复沓书写,在思考、反省中,使原本模糊的民族自我形象渐次清晰,预告了1938年左右因大西迁而被切实感知的民族共同体验。范长江预感到西北变革力量的蓄积,但他1935-1936年第一次西行,却并未真正走进一路跟来,带有神秘色彩的红色区域。
红色中国与世界想象
1936年《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范长江开始第二次西行。他从绥远、西蒙,几经周折,终于在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2月进入延安。嗣后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投鼠忌器,介绍相当隐晦。政治形势趋缓后的《陕北之行》,虽涉及延安见闻,(22)但在红区时间短暂及尺度考量,对红区领袖亦是印象式的简略勾勒,对红区社会的感受更付之阙如。《大公报》上诸如长城《陕北匪区视察记》、徐盈“旧匪区”江西行记等,或仍在红区周边眺望,或考察“旧红区”今貌。一方面弥补当时对陕甘宁红区视野的匮乏,另一方面,恰因文中渲染的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如“陕北共党的武力,最初便是由一些保贩烟土的‘烟匪’蜕化而来”(23),及关于共党匪夷所思的描写,如“共党以人血涂马首,而塞杜马鼻,马呼吸困难,张口狂奔,当者披靡,一时虽有马吃人之谣”(24)等虚假信息,客观上加重大众了解真实之陕北红区的欲望。长征结束后,大众媒体上,无论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员董健吾以“幽谷”笔名,在《逸经》上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陈云化名“廉臣”、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抑或参与过“剿匪”的湖南军阀何键的幕僚胡羽高的《共匪西窜记》,从不同角度对“长征”着墨颇多,但对红军“长征”结束后的状况,却罕有应答。
正在这时,美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将自己1936年6月至10月的旅行经历写成文字,在中文大众媒体山穷水复之时,响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从1936年年底到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发行期间,以各种形式,在中国传播(25),终于敞开了西部中国陕甘宁边区与白色中国迥异的“另一个中国”,红色中国。《西行漫记》及类似作品——传教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海伦·斯诺(化名尼姆·韦尔斯(Nym Wales))《红色中国内幕》,都打开了渴求现代的中国读者急需的“世界视野”。但由于《西行漫记》建立了“可以让读者信任的个人视角”(26),又最为成功。
无论是现代审美的视角,还是世界文明的视野,红色中国在资本主义帝国年轻一代的斯诺笔下,与他的世界想象奇妙地榫接。延安城召唤出斯诺夫妇审美感的,不是“中国的西北角”式的贫瘠、荒凉,而是中亚细亚古老阿拉伯想象的余绪:沟壑万千、黄土覆盖的陕北高原,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27)曾是“繁荣的穆斯林中心”的延安,常使海伦想起美国画家麦克斯菲尔德·帕里什(Maxfield Parrish)为《天方夜谭》所画的插图,“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紫色光辉,在清澈的沙漠气氛中像是磷光。萧然无物的黄土峭壁肌理光鲜,就像粉绘的一样”。(28)
斯诺以西方文化形象为喻,帮助西方读者进入红色中国充满寓意的审美空间:“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格列佛游记》中的有人性的马国)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封疆来统治的”。陕西“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在红色中国“外观”的荒原上,斯诺却书写了文明青春之花的绽放和希望:“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是)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marxist gospel)”;(29)在陕北,斯诺找到了西方世界新的福音和启示录。“gospel”,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斯诺看来,就是新的神谕、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及治疗西方现代病的良药。
斯诺阅读过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而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早就在中国散布开“西方文明破产”的讯息,他恐怕不会料到,当美国青年斯诺真的来寻觅“中国文明的救拔”时,找到的却并非“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30),反而是西北荒原上,新兴的共产主义文明。欣赏种类繁多的红色舞蹈,斯诺颇为窘迫:“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从审美的贴近到文明的救赎,斯诺以世界眼光打量红色中国,思考西方的危机。但这在“另一个中国”找到救拔,甚至发出自愧不如感慨的作品,经由中文媒体的译介和传播,竟鬼使神差地使中国读者感到:原来红色中国竟是我们现代追摹的对象欧美也及不上的呀!文本书写目的及实际传布结果之间存在着歧异。
撇开时代特殊的信息需求,《西行漫记》的诱惑在于,它所敞开的红色中国,有青春飞扬的气质,而红区大众主体性无比强烈的原因,也恰与世界想象紧密相关。周恩来悉心安排了斯诺九十日采访的行程和资料。《西行漫记》主要是(而且也几乎只能是)对红区表象的描摹,重点展示红区公共空间和集体活动场面。
一则,红色中国通过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无线电等世界想象的表征,为社会上流动的、地位暖昧不明的人找到了身份。这些人既包括红色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等,又包括普通的红军战士、工人和西北农民。尽管程度不一,全民的自信感却跃动于斯诺笔下。毛泽东自述在《西行漫记》中最早为人关注,也是当时人了解红色中国的源泉。斯诺笔下的毛泽东,毫无架势、充满自信,他相信眼下的革命具有世界意义,“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红区普通农民对“世界”的关注也不亚于主席。当一个老年农民对红区表达些微不满时,一个青年农民诘问他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吗?世界是怎么样的(what the world is like),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你说这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31)虽然这话逻辑不甚通顺,为什么以前没有合作社,现在的合作社就能没有布?但却说明,对于红区大众来说,红军明确告诉了人们世界是什么,而过去他们一直“懵懂地”生活在世界中。
“无线电”在叙述毛泽东时被涉及,又被这位青年农民提到。山中居民通过无线电了解世界新闻,跟斯诺讨论法西斯蒂和共产主义的问题。(32)这与红区之外的中国村民,一般只了解当地村政的状况,很不一样。范长江在西北时,曾住在一幢西式的小亭中,当时他就感慨:“设使中国将来人人有如此一间住室,月白风清之夕,大家听听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和音乐,不知……将会如何的快乐。”(33)红区实现了范长江的期待。“无线电”广播成为现代前进生活的代名词,是红军在西北输入现代的表征。因为它沟通,并具象化了那个在地平线视野之外,大多数人永远不能脚踏眼见的世界。它是“世界”的物质象征,也是享受带来世界这一权力的物质象征。红区各地广泛播放的无线电广播,给西北山村带来的冲击,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曾言,“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无线电是现代媒介文化的先兆,在乡村,“力量从那些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的人那里,传到了那些掌握遥远地方有关信息的人那里”。(34)红色中国以类似无线电广播的物质手段,告诉村民世界是什么,在村民眼中,带来遥远地方信息的红军,成为真正有力量的群体。
再则,红区的青年、儿童、妇女是斯诺看到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究其原因,红区的扫盲工作,让百姓掌握文字,红军组织群众参与公共生活,使他们获得自尊,能够想象性地进入他们能接触的及从未见过的“世界”。一个刚参军不久的山西农民向斯诺炫耀:“‘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文字本身是符号,但在西北,文字更具有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农民指着自己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和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发现的古书上“歪歪斜斜”的字,心情截然不同。但文字的魔力,和来自别一个世界的操纵功能,却极为相似。西北边区农民对文字的掌握,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其魔术般的力量,那就是,通过书写,他们获得工具来认知、掌握世界。与此同时,公共生活则成为他们获得尊严感的场域。红军为当地带来了“世界”,也重建了宇宙的秩序感。在打乒乓球、放留声机、玩游戏(识字扑克)、唱歌等集体活动,列宁室红栏、黑栏(表扬,批评)的墙报展览,及最激动人心的群众大会和露天戏剧的公共生活中,红区大众感到自由、尊严和希望。
斯诺夫妇特别关注红区的露天剧场。斯诺认为,没有比保安“倾城而出”观看戏剧的场面,“更加民主的场合”了,这里“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在红区,剧场体现的公共生活,成为个人自我释放的全部依归,也是产生“生活的幻觉”(the illusions of life)(35)之所在。“生活的幻觉”使人相信,某种特定方式的生活轨道是应然的。海伦也发现,“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它是革命本身不可分的部分。它把几种机关合而为一——教堂、国家和政治集会”。(36)1937年,《大公报》记者徐盈江西老红区的诸多行记,与《西行漫记》遥相呼应。他问一位老人当年红区的情况时,“起初他说他在红军来的时候逃到山里去了,后来却又转到打土豪,看开群众大会,赞成的举手,‘那么多的手!’他也把老手举一举”。(37)尽管红军已经撤离,但当地人记忆犹新的,还是那些公共的集体生活。他们或许第一次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手举起来,决定他们原本不能参与、无法进入的世界。那位老人说起“那么多的手”,“也把老手举一举”的姿态,与西北红区大众参与公共生活的行为和背后的心理,具有同构性。
然而在斯诺等人笔下,红区的主体性建构与世界想象,也有隐藏的脆弱性。一方面,红区形态各异、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公共生活,固然帮助当地建立新的宇宙秩序感,但群众对戏剧太融入、信以为真,易忘记自我当下存在及周边的实际状况。薄复礼在红军中听说,一名战士将枪口对准了舞台上的蒋介石。(38)这里是蒋介石,后来更为典型的是黄世仁。也就是说,当个人完全依靠现代体制的力量自我确认时,体制的惯性也可能会湮灭个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红色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构造的世界想象。范长江记述传闻中刘志丹治下的西北红区:“经数年来赤华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达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39)知道遥远的具有象征性的人名、地名,却不了解切近的周边地域,其世界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相当封闭。当外在世界的物质侵入进来,世界到底还是不是我能掌握的世界,就值得怀疑了。斯诺笔下,红区干部傅锦魁向农民许诺:“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农民拣起斯诺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大概是日本货),问他:“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傅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40)傅锦魁“他们还要什么”的回答,在“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面前还是有些心虚的。
尽管有缝隙,斯诺等人笔下的红色中国,其荦荦大者,仍是获得主体性的自尊和自信,充满诱惑力。读者阅读《西行漫记》,弥补了由于其时中国肤浅的现代,而导致的双重匮乏感:既缺乏宽广的世界视野,又缺乏肯定自我主体性的能力。《西行漫记》中“红色中国与世界想象”的关联,在读者那里获得了最终的完成。青年们视《西行漫记》为黑暗中的火把,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望,“怀着朝圣心情”(41),1937年后,主动选择去大西北的延安。他们也汇入了自游牧时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庞大的苦难人流,即抗战打响后,千百万人组成的向中国西部大迁徙的人流。
1935年后,范长江以及他所在的《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媒体,书写了受到红军长征和“剿赤匪”两股现代力量冲击,与“东部中国”有别的西部中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等著作,1937年以后在中国传播,弥补了中文媒体的不足和期待,敞开了与白色中国相对的红色中国。不管是前者侧重于以红军长征为引子,讲述红色中国的西部周边,“寻求中华民族出路”(42);还是后者落脚在书写中国西北成长起来的红色中国内里,发现“未来更健康、更干净的世界的希望”。(43)相对对象各有差别的“另一个中国”——西部中国与红色中国书写的合流,从历史发生到文本叙述,都是抗战前夕引人瞩目的媒体事件。
在193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内忧与外患使中国的现代进程面临着巨大的变迁及转折。费孝通在创作于此时的《江村经济》中写道:“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44)如果说西部中国问题,更多的是对民族的过往和当下资源的重新整合,以过去和当下为根基,面向未来的话。那么对红色中国的想象,则具有一个未来的向度,以未来的期许为基础,切实成为民族反思当下和自我问题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成了我们一致艳羡追求的目标”(45)之际,这两种想象又都具有外在的参照因素,世界是什么?我们怎样现代?民族主体被远离它所在空间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在抗战前夕的历史当口,“现在”的民族共同体何去何从的紧迫压力,促使共同体对自身的过去和未来都要重新思考。因此,西部中国和红色中国两条“另一个中国”的“他者”线索,在此时的合流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西部大迁徙的到来,两条合流的文化想象线索开始分途发展。西迁,认识西部,是战后文化界的首要问题。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在“方言与习惯隔阂之地”、“原始”、“野蛮”的西部,找到“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46);“素不接触现实”的学者顾颉刚之《西北考察日记》,自叙他“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识其百余年来所以动乱之故”(47);诗人冯至的《十四行集》,则抒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西迁人群的集体经验。(48)临近抗战结束,红色中国的问题再次凸现,重庆《新民报》1944年7月底开始连载主笔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更被视为新的《西行漫记》(49),继续述说红色中国的故事。此后,依据共同体当时的文化需求,即整合固有的文化资源以应对当前的局势更紧要,还是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期望更加迫切。西部中国与红色中国二者,在大众文化想象中,又分别或隐或显、时强时弱的不断重现。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②红军长征后大众媒体西行记概况,参阅彭春凌:《抗战前夕大众媒体的西行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③沈从文(署名“炯之”):《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大公报》,1936年10月25日。
④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87页。
⑤长江:《成兰纪行》(十六),《大公报》1935年10月25日。
⑥张恨水:《西游小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2页。
⑦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⑧长江:《成渝道上》,《大公报》1935年7月9日。
⑨木公:《京滇导游》,《大公报》1937年6月27日。
⑩长江:《成兰纪行》(二)(三)(十四),《大公报》1935年9月21日、1935年9月25日、1935年10月21日。
(11)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翻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15—116页。
(12)长江:《成兰纪行》(三),《大公报》1935年9月25日。
(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14)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第170—171页。
(15)《蒋入川之观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0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1935年3月18日。
(16)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三)(二),《国闻周报》第12卷第13、10期,1935年4月8日;1935年3月18日。
(17)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268、276页。
(18)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一),《国闻周报》第12卷第9期,1935年3月11日。
(19)丁东:《中江别动队》,《国闻周报》第12卷第35期,1935年9月9日“剿匪在四川”。
(20)长江:《成兰纪行》(十八)(十一),《大公报》1935年11月1日;1935年10月16日。
(21)程千帆:《文论十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22)范长江:《塞上行》,天津:《大公报》馆,1937年6月13日。
(23)长城:《陕北匪区视察记》(一),《大公报》1936年10月31日。
(24)季鸾:《西北纪闻》(二),《大公报》1935年7月31日。
(25)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
(26)Robert M.Farnsworth,From Vagabond to Journalist Edgar Snow in Asia 1928-1941,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6,page2。
(27)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二卷,第27页。
(28)尼姆·威尔斯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29)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二卷,第188、291—292、102页。
(3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23,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5、38页。
(31)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二卷,第99、68、227页。
(32)斯诺:《共党与西北》,《中国红区印象记》,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版,第72页。此书是1937年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翻印本,有一些脱漏。
(33)范长江:《贺兰山的四边》(九),《大公报》1936年7月19日。
(34)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35)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二卷,第58、339—340、96、102页。
(36)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75页。
(37)徐盈:《记斫柴岗》,《大公报》1937年3月30日。
(38)薄复礼著、张国琦译:《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39)长江:《陕北甘东边境上》,《大公报》1935年11月25日。
(40)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第二卷,第224—225页。
(41)赵荣声:《沿着斯诺的足迹》,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42)周飞:《〈中国的西北角〉三版代序》,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7版,第2页。
(43)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封底,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44)费孝通:《江村经济》,《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45)尹瑞西:《现代国家的幸运与中国的厄运》,《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46)朱自清、闻一多《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版。
(47)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48)冯至:《十四行集》第16首,桂林:明日社1942年版,第40页。
(49)《〈延安一月〉重版说明》,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页。
标签:范长江论文; 斯诺论文; 剿匪论文; 红区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红星照耀中国论文; 大公报论文; 西行漫记论文; 苏维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