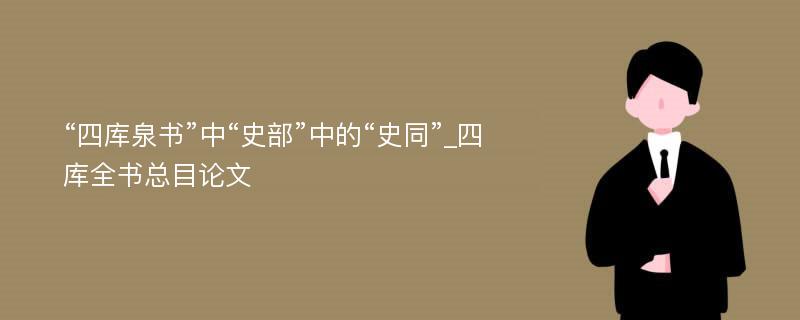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中的《史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目论文,四库全书论文,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7)06-0071-06
《四库全书》,即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在纂修期间,四库馆臣们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名为《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我们只用“总目”来简称之。)。《总目》对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一万余种,都写有介绍与其内容相关的提要,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遗产的一次大总结,映现出对这一遗产进行内在反省和完善的一种紧迫需求。《总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和编排,诸提要多为学术大家所撰,其中由学问渊博、有通儒之称的纪昀撰写和改定者甚多,学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史部”是专门对历代史书、史家和史学进行重点记载、全面评论和加以价值判断的类别,为史学中人所重。《史通》和“史部”都是史学中人常备案头之书,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认识,有助于我们较为具体地了解《史通》的重要史学价值以及对后世史学的一些影响,有助于我们部分理解四库馆臣的史学取向,明白(史通)和“史部”为历代史学中人所重的缘由所在,进一步明确它们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据笔者粗略地搜检,《总目》“史部”①直接引用并指明出自《史通》者有50余处,另在卷88有《史通》、《史通通释》二提要,在卷89有《史通会要》、《史通评释》、《史通训诂》、《史通训诂补》四提要;可以说,作为单部史书,在“史部”中的引用和记叙的数量之多是罕见的。为什么《史通》会受到自视甚高的四库馆臣的高度重视呢?总起来讲,一方面是《史通》本身具有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和思想倾向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四库馆臣的学术见解和史学取向的结果。
一、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以评判史书
“史部”是对历代史书进行重点记载、全面评论和实施价值判断的一次总结性的史学活动。评判史书首先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标准,评判标准的建立主要有理论的、现实的、历史的三大来源,而历史的来源既经过了史学实践的检验,又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史通》就是“史部”评判标准的重要理论和历史来源。这就是四库馆臣比较多地借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来评判史书的基本思想出发点。
四库馆臣以《史通》为史书评判标准的具体原由有:首先,四库馆臣对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已经有了初步的、直观的划分。“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②“史部提要”除介绍历代史书概貌,还涉及对史家思想倾向的评判,史书体裁、体例等的分析等。而对于以学术相尚的四库馆臣来说,“考辨史体”是“实学”;而“品骘旧闻,抨弹往迹”的史论有“虚学”之嫌。《史通》作为中唐以前唯一一部研究传统史学的专著,主要就是“实学”,为其所重,也就顺理成章。其次,四库馆臣为刘知几深厚的史学功底所折服。刘“子元于史学最深,又领史职几三十年,更历书局亦最久,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③“刘知几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④“刘知几深通史法。”⑤最后,刘知几学风严谨,引据确凿,结论准确。四库馆臣评刘“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⑥“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⑦如此多的称许之语集中在一位史学家身上,尤其出自四库馆臣之口,在“史部”是难得的。可以说四库馆臣深得“知人论学”之妙。这就不难明白他们看重《史通》的原因之所在。
“史部”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来评判史学、史书,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正史”一词的界定,对“通史”编纂困难的估计、对纪事本末体创新意义的说明、对史书语言朴实的肯定等。如,编年史是否“正史”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最后还是没有结论而不了了之。“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⑧四库馆臣对“正史”的看法,既避免了穿凿附会、无谓的争论,又表明了本“无他义”的正确态度。又如,编撰“通史”历来是中国史学家的最高追求之一,但其难度极大,成功的机会小。四库馆臣告诫史学家不要轻易为之,并引用刘知几所说:通史之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四库馆臣认为郑樵《通志》用力甚巨,自视甚高,而“全帙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⑨清陈允锡撰通史著作《史纬》三百三十卷,“积毕生之力为之,而卒之不协于体要,固其所矣。”⑩复如,四库馆臣通过借用刘知几对编年体和纪传体长短得失的分析,把它作为纪事本末体产生的重要条件。“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而《通鉴纪事本末》正是要补救二体的不足,“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11)“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12)再如,四库馆臣赞成刘知几“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3)的主张,认为史书语言只要“措词质实”,就“不必责以词藻”。其评价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全仿〈东京梦华录〉……而观其自序,实非不解雅语者。毋乃信刘知几之说,欲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方言世语,由此毕彰乎?(案语见《史通·言语》篇)要其措词质实,与《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均可稽考遗闻,亦不必责以词藻也。”(14)
第二,用以对纪传体史书内部构成的是否合理进行评判。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最为主要的历史记载形式之一。它的内部构成,即设立本纪、列传等类目,每一类目的内容都有经严格选取的人或事相对应,通过对类目进行搭配和排列,来体现其编纂宗旨。
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5)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宋陆游《南唐书》,于南唐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四库馆臣认为这种处理“谬矣”。原因在于“元宗于周显德五年即去帝号,称江南国主”。不宜再以“本纪”处之。陆游却以“《史记》秦庄襄王项羽本纪为例”,是不知《史通·本纪》篇对司马迁立《项羽本纪》已有“循名责实,再三乖谬”的严厉批评。(16)
载记介于本纪与列传之间,用于记载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分裂割据政权。有的史书作者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将有的分裂割据政权归入伪史或霸史。四库馆臣认为这种做法“皆非其实”。从而依据“《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因此在“史部”设立“载记”类,(17)避开了纠缠不清的争论,淡化了历来众说纷纭的“正统闰位”之说,也起到了为清朝统治的合理合法寻求依据的作用。
“表志”是纪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何处理上有较大难度,历代史学家对此颇感头痛。“史家之难,在于表志”,因其“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18)刘知几关于纪传史“表志”的主张,对后世纪传史编撰有一些直接影响。四库馆臣评《明史·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于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复申明,于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19)清朝尤侗撰《明艺文志》,“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20)又评郑樵《通志》“二十略”,“《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均为旧史所无,盖窃据是文。”(21)再如,评欧阳修《新五代史》编写志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余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征。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22)四库馆臣在没有认真研究、深入分析的情况下,就认为在“表志”问题上,得亦《史通》,失亦《史通》,不算是公允之论。实际上,刘知几并未有废表志之说,只是认为每一部纪传史都通记天文现象和图书情况,难免床上床、屋上屋的弊病。欧阳修典制从略,根源还在于他力图于《新五代史》中模仿和贯彻《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所至。
第三,用以支撑其对一些史书的评价,或作为设立史书“类别”的依据。荀悦《汉纪》历来有“文约事详,论辩多美”之誉。四库馆臣运用《史通。六家》:“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的排序和《二体》又称“历代宝之,有逾本传”之语来进一步证明这一评语是恰当的。(23)又如,袁宏《后汉纪》为史家看重。“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24)再如,唐朝所修《晋书》,因为事实有欠选择,文笔华美,历代对它颇有微词。四库馆臣在卷45《晋书》“提要”中没有作过多的批评。但在其所撰明朝蒋之翘的《晋书别本》“提要”时指出:“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抵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25)
如,四库馆臣“别立(宫殿)子目,冠于地理类之首”。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有:“刘知几《史通》所引有《晋宫阙名》,皆自为记载,不与地志相杂。”(26)又如,四库馆臣认为将《国语》“系之春秋,殊为不类”;“附之于经,于义未允”。而“《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因此把《国语》列在“杂史类”之首。(27)别立“宫殿”一目以显示皇帝高高在上的地位,将《国语》从经书中裁出,都以刘知几所论为依据,取得了其来有据的效果,体现了四库馆臣的良苦用心。
以上诸例说明,四库馆臣运用刘知几的史学认识成果,还是相当有史学眼光的,涉及一些重要的史学课题和史书编纂的问题,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其中不少结论性话语在今天也不失其学术意义,而为时人多所引用和发挥。《史通》和“史部”在不少史学问题上的认识非常的相似和接近,既体现了《史通》的史学价值,又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二者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联系和重要地位。当然,刘知几与四库馆臣对《史记》的批评,是封建学人的固有偏见也是不必讳言的。
二、引用《史通》的记载内容以资考证
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因自然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出现许多的“亡残伪误”,史书亦然。《总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清理乾隆以前图书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弄清、说明和解决“亡残伪误”的状况,考证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四库馆臣认为“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只有注重精核的考证,才能收到史书“谢彼虚谈,敦兹实学”的效果。(28)而要考证,前人的记载就是最重要的理据之一。《史通》恰巧具备这样三点有利于考证史书的条件:《史通》引书甚多。(29)更有利的是“唐以前书今(乾隆时)不尽见”。(30)再加上刘“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31)“知几之言不妄,是则可资考证之一端。”(32)因此,《史通》中的一些记载内容自然就成为四库馆臣用于考证的主要依据之一,有理有据地纠正了不少史籍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支持了一些正确的记载和说法,解决了部分史书“亡残伪误”的问题。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史通》的文献价值,而且也是四库馆臣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
四库馆臣引用《史通》的记载内容对部分史书加以多方面的考证,主要有:
考史书的撰写者和时代。如,《邺都故事》,唐志虽称肃代时人马温撰。“而《史通·书志》篇曰,……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则《邺都故事》在刘知几之前,唐志所言,亦不足为证。”(33)又如,《梁书》独署姚思廉名,“盖(魏)征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案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征总知其务,凡有论赞,征多预焉之文。)独标思廉,不没秉笔之实也。”(34)再如,考《隋书》只署魏征、长孙无忌二名的原因。四库馆臣列出《史通》所记有关《隋书》多位作者的姓名,再结合自己对残存于《隋书》中纪传表志的作者的姓名考证,提出“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征及无忌也”。(35)
考书籍的残缺以及补缺情况。如,《史记》存在缺文十篇的问题,张晏说是“迁殁后亡”。“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36)又如,魏收《魏书》发生阙佚,后人补之,但未指明出处,使人不明依据何书所补。《太平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此外,四库馆臣还进一步以“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的记载来印证与《太平御览》所记是相同的,以支持自己关于《魏书》“疑其取诸魏澹书”的说法。(37)再如,李百药《北齐书》至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有“残缺不全”记载。有后人取《北史》以补亡,但因收罗材料不广不全,出现“俱无论赞”、“有赞无论”或“有论无赞”的情况。“《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云……。今《魏收传》无此语, 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四库馆臣提出:《北齐书》“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的结论。(38)考史书篇卷的多寡。如,梁萧子显撰的《南齐书》,有60卷和59卷之不同记载,刘知几《史通》所记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四库馆臣“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有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39)又如,姚思廉《梁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据为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40)
考“十志”编入《隋书》的缘由。《隋书》“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于限断”。四库馆臣以《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记的相关内容为根据,云:“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于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来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其始末矣。”(41)
考《后汉书》的“论赞”置于卷末的时间。因“隋唐志”均别有范晔《后汉书论赞》五卷,而“宋志”始不著录。四库馆臣“疑唐以前论赞与本书别行,亦宋人散入书内。然《史通·论赞》篇曰: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蔚宗后书,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则唐代范书论赞已缀卷末矣。史志别出一目,所未详也。”(42)
考《洛阳伽蓝记》本有“自注”。四库馆臣据《史通·补注》篇所曰,认为《洛阳伽蓝记》“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然自宋以来,未闻有引用其注者,则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复考矣”。(43)考一书二名。“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44)引用刘知几《史通》的记载,以证明朝“万历以后”所“忽出”的《十六国春秋》百卷本,并非北魏崔鸿所撰,实为“伪本”。(45)清张愉曾撰《十六国年表》,其从父张潮写“跋”称:“不识崔鸿何以不列年表,今得此书,可以补其阙略。”四库馆臣曰:“考刘知几《史通》,崔鸿原书实有表。屠乔孙等作伪本时,偶漏撰此篇。潮未及考耳。”(46)以示因检书不全而出现结论不妥的毛病。等等。
四库馆臣充分利用《史通》的文献价值考订了唐朝以前的部分史书,是利于当时、惠及后世之举。不少考证结果,已成定论,而为近现代人阅读和研究唐朝以前史书扫清了不少障碍,有的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这些都是他们对历史文献所作出的共同贡献。由于四库馆臣并非专门进行考证,大致是根据“史部”编写“提要”所碰上的问题,随书、随人、随事等而考证,缺乏考证方法的总结。对于怎样去做考证,“乾嘉学派的考据家只偶而谈到三言两语。”(47)不过,在借用《史通》或其他典籍的记载来进行史书考证的实践中,四库馆臣治学严谨,引据详明,考订精审,辨析准确,大约也不算虚语。
三、利用《疑古》《惑经》以行思想批评
史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经世思想是意识形态中最活跃的部分,因为一切文化都是社会需要和经世的产物,所谓纯学术也只是经世思想的异化。”(48)“史部”作为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一次大总结,同时也担负起整肃思想的任务。四库馆臣的“经世”思想比较复杂和矛盾。一方面,“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49)另一方面,他们提出:“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为此只得用“论人而不论其书”和“论书而不论其人”的“变通”(50)方法以便保存更多的书籍和采择一些有用的学术主张。不过“人”与“书”相分离,本不是一种正确的评论方法,评论是很难到位的,但在当时考 证风靡一时的学术环境中,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史通》中的《疑古》、《惑经》等文,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要求出发,对于《尚书》、《春秋》、《论语》的记事多所批评。此后历代学人都对刘知几的“疑惑”颇多指斥。四库馆臣也不例外。
“《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即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尚书》不载八元八恺寒浞飞廉恶来闳夭散宜生,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曹沫公仪休宁戚穰苴,亦殊谬妄。……遽瑷位列大夫,未尝栖隐,而《品藻》篇谓《高士传》漏载其名。孔子门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虚诬,而《鉴识》篇以《史记》载此一事,其鄙陋甚于褚少孙。皆任意抑扬,偏颇殊甚。”(51)四库馆臣以对《疑古》、《惑经》的态度为标准,凡赞成或袭用刘氏者均被指摘;凡不赞成刘氏者,四库馆臣均加推奖。这就不免失之偏颇。如,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52)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对此“颇有纠正”,就被诩之为胜过浦书。(53)又如,“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乖谬。”清孙之马录“一概引用,漫无辨正,沈约注出依托,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诬,太甲杀伊尹之妄。之马录乃旁取异说,以荧耳目。云能补正沈注,未见其然”。(54)
对于刘知几为什么敢于“疑惑”圣人和经书呢?四库馆臣认为主要有二因:一是刘知几“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55)弦外之音,就是刘知几的性格出了毛病。二是“《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56)言外之意,刘知几所见的《竹书纪年》只是多种本子中的一种,难以为据,以此来“疑惑”圣人和经书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信的。这两个原因的分析曲折地反映出四库馆臣在封建思想与讲实学、重考证之间矛盾徘徊的复杂心境。
综上所述,《史通》对“史部”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四库馆臣推许刘知几为“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评价是很中肯的。他们通过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对一些史学、史书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评判,体现了《史通》的史学价值;通过《史通》的一些内容记载,四库馆臣对一些史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体现出《史通》的文献价值。通过对于《史通》的运用、引用,不但证明了《史通》,而且也证明了“史部”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对于《史通》思想价值的批评是乏力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和思想局限性。“史部”作为对中国传统史学、史书的一次划时代的总结,其学术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
收稿日期:2007-06-11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45- 90为“史部”。以下注释,凡只标出卷数者,均同出于此。
②③⑦(51)(52)(55)卷88“史评类序”,《史通》,《史通》,《史通》,《史通通释》,《史通》。
④(30)(53)卷89《史通训诂》,《史通训诂》,《史通训诂补》。
⑤⑧(23)(24)(56)卷47“编年类序”,“编年类序”,《汉纪》,《后汉纪》,《竹书纪年》。
⑥(14)(31)(43)卷70《洛阳伽蓝记》,《梦粱录》,《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
⑨(21)(25)卷50《通志》,《通志》,《晋书别本》。
(10)(32)卷65《史纬》,《南朝史精语》。
(11)(12)卷49《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类序”。
(13)《史通·叙事》。
(15)《史通·本纪》。
(16)(17)(33)(45)(46)卷66《南唐书》,“载记类序”,《邺中记》,《十六国春秋》,《十六国年表》。
(18)(34)(35)(36)(37)(38)(39)(40)(41)(42)卷45《读史记十表》,《梁书》,《隋书》,《史记》,《魏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隋书》,《后汉书》。
(19)(22)卷46《明史》,《新五代史记》。
(20)卷87《明艺文志》。
(26)卷68“宫殿”案语。
(27)卷51《国语》案语。
(28)(49)(50)《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29)《焦氏笔乘》卷三《史通所载史目》,列出《史通》所引的史书书目有146种之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4)卷57《晏子春秋》。
(47)罗尔纲:《说考据》,《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
(48)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0页。
(54)卷48《考定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