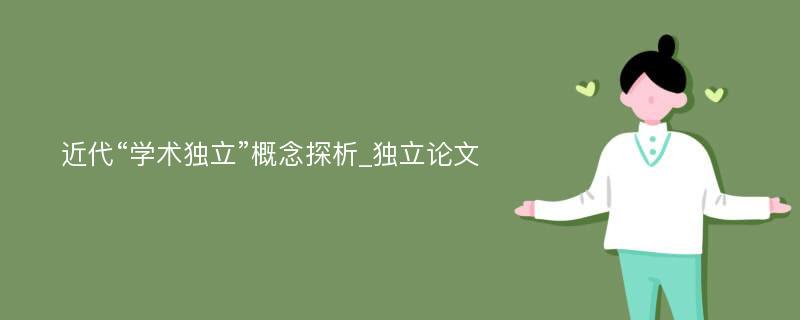
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观念论文,独立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6)03-0316-05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赞成者认为,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走学术独立之路,远离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生活;反对者认为,学术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了政治,根本上是学术与实用价值分离,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这种争议实成公婆之论,难分高低。然而细加考辨,发现百年来对“学术独立”观念的争议,都是以对“学术独立”本身含义的简单理解作为争议背景的。考察这种争议的历史,可发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学术与政治、现实生活、实用价值是否应该脱离,学术是否应该远离中国社会现实,做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简言之,就是争议双方把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理解为学术独立于一切现实“用途”。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仔细考察,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并非如此简单,其内涵多歧而微妙。因此,考察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观念,厘清其涵义实为必要。
一、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
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首先应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之论,并不能否定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观点,其实他们都说了中国近代历史现实的一个方面。中国近代历史有沿自身传统发展的一面,也有“冲击—回应”的一面。随着近代西学东渐过程的加速推进,民族保护主义(借用了“保守主义”而得来)的情绪必然日趋强烈。不管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还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都有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实行保护的思想存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一直受到后来国人的指责,实为未具“了解之同情”。“中体西用”确有后来国人所指责的“保守”,但其具有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一面也应予以正面理解;如果说张氏“保守”,至少他也同意“西学为用”,具有了那个时代的开放性。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学术的侵入,强调“中体西用”,就是因为“中学”已难以为体,才被迫提出“中体西用”的吁求,借以保护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保护中国文化学术传统的思想,实也是产生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之观念的源头。
清末,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蜂起,近代中国之西方教育体制的确立,西式大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具有强烈的冲击。中学渐退,西学疾进,实为中国近代历史无可否认的现实。相对于上一辈学人,清末民初学人的胸怀更为开阔。王国维认为,做学问应“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认为学术无中西之别。章太炎论中国学术时更有极为形象性的比方,“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中西学问一体同视。然而,章氏笔锋一转,“今日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2],明确提出中国学术独立性的严峻问题。其实,王、章二人主张应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就是因为面对西学的蜂拥而入,中学已面临生存的危机。王国维紧接他的上述观点说道:“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中学已面临如此的窘境,王、章二人提出同等对待中西学术,其中实有一番借以保护“中学”的苦心。梁启超也告诫国人:“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3]105一面吸收外来文化,一面仍需保持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不乏陶醉于欧风美雨中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鄙薄已成为近代国人的流行观念,“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即可印证,废汉字、废国医的激进举动,反映了当时人们反传统的心态。但是,在如此观念笼罩下却有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不无担忧与激愤,黄节对此予以申斥,他说:“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4]学术不能独立于西方而迷醉于西方学术之下者,即为“学奴”,指责虽为偏颇,但也反映了黄节的良苦用心,担忧中国学术依附于西方。如能体味出近代学人吁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忧虑,就不难理解革命党人章太炎为何会去保存“国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为何在“五四”后会去“整理国故”。《国粹学报》创刊宗旨就是“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正是针对此“醉心欧化”的狂潮。学报主办者邓实就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扬祖国之耿光”,实现“亚洲古学复兴”之愿望[5]。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的一次讲演中告诫当时的青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6]蔡氏认为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应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保持中国学术的特色,不为西方学术“同化”,否则,“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陈寅恪谈到治学方法时也指出:“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并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8]明确提出中国学术应独立于西方的观念。
30年代,追求学术独立于西方的思想在学人中也时有表露,《独立评论》上有关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的争论,立足于大学教育的视角,认为中国学术更应独立于西方,不能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其中姚薇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也标榜着学术独立,但那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全国所有大学直到现在还全是‘留洋预备学校’,甚至最近利用创设的大学研究院也包括在内,进研究院也不过利用环境作投考留学的准备而已,颇有住研究院数年每年投考留学而始终没动手写论文的。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10年20年大学研究,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9],表面上是反对留学,实则是对中国学术能否独立于西方的关怀,不致使大学流为“留洋预备学校”,研究院办成“留学补习班”。这是近代学人颇有见地的评论。
由此可见,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下,近代学人对中国学术独立于西方的吁求,并非一定是学术上的“保守”,而是立足于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学术传统,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性,甚至是追求创立具有本国“特色”学术的一种理想。
二、学术自由的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
近代学人时有学术附庸于西方的担忧,也长存学术受政治干扰或依附本国政治的焦虑。中国古代就有“师吏”的传统,以吏为师,实则官方政治在干预学术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张居正杀何心隐、囚李贽,以政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
传统如此之沉重,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事实上在为学术避免政治干扰树立一块挡箭牌。严复早就强调政与学的分离:“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0]主张政学分离,其立意是使学术能自由发展,保护学术自身的独立性。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等人纷纷脱离政界,从事学术研究。谈到政学问题时,熊十力认为:“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界思想锢蔽,而政治制度,何由发展日新?”[11]政府可以提倡学术发展,但不能干预学术“自由研究”,否则学术政治两者都难于“发展日新”。后来钱穆更从官办教育的角度指出政学不分的弊端,“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12]近代学人的“理想要求”究竟是什么?钱氏的议论中隐含的回答是政学分离,政不干学,期望学术独立发展,但不甚明朗。1938年国立四川大学“拒程运动”中,川大教授联名发表的《文化宣言》则做了明确回答。
在近代政府统治力度减弱之时,对学术的干预就小;而当其统治力度增强时,对学术的干预往往加强。因抗日的需要,国民政府对后方的控制力度渐趋强大,这种统治力也伸入到学术界。1938年12月26日,因反对国民党党员程天放任川大校长而起的“拒程运动”中,川大教授联名发表《文化宣言》,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反对党化教育,要求学术独立于政治,“不愿因政治之需要而牺牲学术之独立”。宣言集中表达了近代学人学术独立于政治的愿望,完全可以称得上近代学人的学术独立宣言。宣言中提出“学术之目的在于探求真理”,“绝非政治所能包举”,“更非任何主义所能限制”,学在求真,政学应分离,“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所谓学术独立者,并非强为高论,实学术本身之性质有以致之”,政学应分离在于学术本身的独立“性质”;“学校非政党之地盘,学术非政治之工具”,明确提出学术不是政治的工具,政治的附庸;政府的“指导统制”,“只求方向正确,不悖立国之精神,非谓举学者超然之品格而摧残之,取学术自由之空气而破坏之,置文化之尊严于政治需要之下也。”[13]川大学人的宣言表白了所有近代学者追求学术独立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心声。
三、治学态度的表白与超越:学术独立于“致用”
学以致用或“经世致用”本为中国学术的传统。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即华夏千古真理,强调了学术的致用性。“经世致用”的提出也不只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明朝中叶,“经世致用”思潮即已兴起。晚清“经世”思潮即承继明末清初顾、王、黄的思想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实为“经世”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寓政治思想于学术的典范,假学术之名,行变法宣传之实。
此处笔者无意评价“学以致用”的正确一面,但近代学人学在求“真”、求“是”的呼声也并不微弱,尤其在清末民初至为强烈。章太炎承乾嘉学派之余绪,虽说“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并认为“然以今日中国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14],但真正谈及学术时,章氏却明确立论:“学在求是,不以致用。”[15]并予以进一步申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6]151同时,“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况那些讲“致用的学问”,也“未必真能合用”,主张“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17],功业与学说分离,这已涉及到章氏的治学态度,“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16]151。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章氏强调“学在求是”,但他并没有否定学术的致用性,而是说学术有用与否并不计较,注重学术本身,这其中实深藏了章太炎对学术发展的殷切关怀。
王国维对章太炎的良苦用心颇具“了解之同情”,认为做学问应超越于这些“功业”类的现实需求,其治学胸怀开阔,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做学问不应计较有用无用。因此,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颇具深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以“学术为目的”其意就是为学术而去做学术,实质上即为“为学问而学问”的另一种表述。他紧接着又重申:“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学术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8]学术的“发达”在于学术能否“独立”,以“学术为目的”才可“发达”,王氏的意思最终是以“学术为目的”即可达到学术独立。以“学术为目的”也就是王国维理想之治学态度的内心表白。
以学术为目的而非手段,梁启超也有同感,他在论及乾嘉学派时指出:“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由学在求“真”求“是”到“为学问而学问”,此为学人治学态度上的升华。梁氏进一步谈及治学有用无用的关系时说:“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其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之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日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以学术为目的即是“为学问而治学问”,梁氏认为二者实为同义。然后说:“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3]49学问要独立,不必考虑是否有用,学术应独立于“致用”,超越于“有用”,而“为学问而学问”更是这种治学追求上的提升与超越,更重要的,梁氏表明这是“真学者”的治学态度。后来他分析晚清“新学家”时又从另一视角予以论述:“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并且认为:“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3]98学术须“离‘致用’”,才可“独立生存”,明确提出学术独立于“致用”的观念。
然而,“为学问而学问”只能是近代学人的一种治学理想,“学以致用”的理念毕竟深入人心。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学术独立”的观点,并高举“为学问而学问”的大旗,可在1926年他又改变看法,似也回归到戊戌变法时的立场,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甚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甚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19]近代也一直不乏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身影,学以致用于治国安邦,如胡适。但是,他毕竟能让政学分开,追求学术的“纯粹性”,提倡做学问“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20]有如前述,他虽未真正做到,但“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学理想却是追求过的,也启迪了后来学者。顾颉刚在思考学术与人生的问题时悟得:“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不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21]顾氏比较理性地协调了学问与应用的关系,这里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了,收获自然会有。
纵观近代学人,他们追求学术独立于“致用”的治学理想,借以表白个人的治学态度。这种理想,并非真正否定学术的致用性,而且也做不到完全脱离现实用途,做象牙塔式的纯学术研究。他们只是在追求学问的途中做一种努力,摆脱“致用”的羁绊,或者说是对“致用”的一种超越,营造一个做学问的理念,去求真、求是,试图达到“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境界,获得学术的自由独立发展。此处并不愿改变“为学问而学问”字面上的偏颇,但如果有了上述这种切近近代学人内心深处的理解,他们提出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想也就无可厚非了。
[收稿日期]2006-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