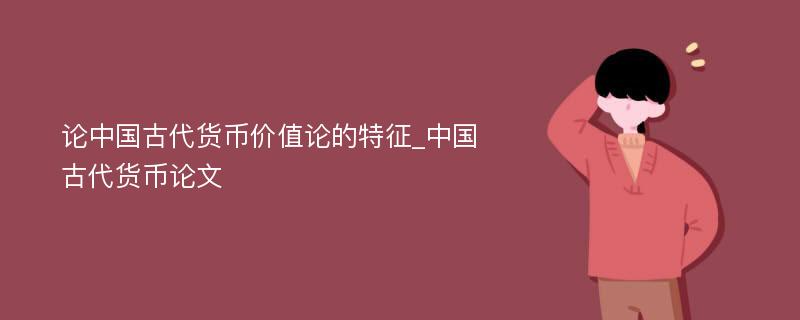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货币价值论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09)04-0059-07;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的思想言论中基本上都包含了诸如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制度等基本理论内容,但货币价值的研讨则相对薄弱。货币数量说一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比较流行的货币理论,虽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货币的金属价值,但并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货币价值论。货币数量说关注于商品和货币的相对比价关系,否认货币中价值的存在,是一种典型的货币名目论的观点。肯定货币价值的论者虽不否认货币本身的价值,但主张货币价值在交换中不起作用,自然也就不会去探讨货币的交换价值问题。货币价值论是货币理论的基础,货币理论的发展必然要以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为前提。中国古代货币价值论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到货币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宋元时期的纸币流通理论。这一切诚如胡寄窗先生所说:“正确的纸币流通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货币价值论基础上。在缺乏一般价值论从而缺乏货币价值论的条件下,又受到时代的局限,纸币流通理论的瑕瑜互见,甚至瑜不掩瑕是势所必然的。”[1]
对于货币价值的认识需要建立在对货币本质理解的基础上。什么是货币的本质,在货币思想史上一直存在有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古代都存在过,但不及西方发展得完备。例如单旗的“量资币,权轻重”就是中国古代货币金属论思想的萌芽,因为他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主张足值货币流通,其“轻重”的概念就涉及到货币的自然重量。战国后期的墨家思想中也有关于货币价值问题的讨论,《墨子·经说(下)》:“买,刀(铜币)籴(谷物)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这段话大意是说,交易中货币(“刀”)与商品(“籴”)相互体现对方的价值,货币贬值(“刀轻”)商品价值就上升,货币升值(“刀重”)则商品价格不变也不算便宜。法定货币(“王刀”)不变,商品价格则不断发生变化,商品价格年年发生变化,则货币价值也将随之发生变动。南朝孔觊在《铸钱均货议》中提出的不惜铜爱工的主张也一直为后世的货币金属主义者所称道,因为他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思想,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视货币为“无用之物”的论点。但他没有讨论货币价值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只是从货币价值角度论证了盗铸的各种弊端。唐朝的杜佑从商品的角度创见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货币观点,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2]提出货币“一物”是用来衡量商品“万物”之“数”的。这一“数”是指商品自然形态的量还是商品内在的价值量则不得而知,但他已经发现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等价关系。可惜在对金属货币的选择问题上,他仅仅根据历代货币流通的历史做了一些实用主义的解释,至于货币为什么可以“主”万物之数,他没有从货币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北宋时商品经济较唐朝发达,货币流通更为广泛,货币思想也就有了新的发展。苏轼在谈到私铸问题时指出:“私铸之币,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3]明确主张货币金属论的观点。沈括在分析对外贸易与钱币外流的关系时提到“而外之所泄无过珉山之铁耳”[4],说明他对货币的金属商品属性有所认识。马端临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岁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5]李觏《富国策》中也谈到货币,在论述货币的起源时,他说:“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散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不少学者认为“轻重之数无所主宰”表示李觏已经认识到了物物交换缺乏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但就李觏赞成西汉贾山的观点:“古之人曰: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来看,李觏还是倾向于货币名目论的。李觏将货币的起源看作是圣人主观的创造,他没有明确说明“钱者,亡用器也”是指没有使用价值还是指本身就没有价值。他的所谓“轻重之数”也未必是指商品背后的价值,可能仅仅是指现实中价格的表现和相互的比价关系,这和当时人们对于“轻重”概念的理解程度也是相符合的。况且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很难下定论说李觏已经触及到了商品的价值问题,但他将货币的产生和物物交换的不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前人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南宋时期纸币开始流行,关于纸币的流通状况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思想关注的主要内容,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对纸币流通的肯定和否定之争,如何稳定纸币币值的问题(主要解决纸币贬值问题),不兑换纸币和兑换纸币之争等方面。由于当时的思想家认识不到纸币仅是一种价值符号,是金属货币的代表,因此其主要的货币理论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纸币流通还是反对纸币流通,都未能从货币价值论的角度做出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货币名目主义者,在否定金属货币实际价值的前提下又将纸币等同于金属货币,自然提出的基本观点更是错误。如辛弃疾在论纸币时就提到:“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6]他从实际使用价值的角度考虑,将纸币和金属货币等同,承袭前人的数量价值论,将会子贬值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纸币发行量太大。宋孝宗是南宋比较重视纸币币值稳定的皇帝,他通过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用白银兑现和向政府输纳时钱会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贬值的纸币币值,并论述了纸币发行的数量和纸币币值的关系:“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7]这种观点,成为之后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关于纸币流通的基本观点之一。但这种观点缺乏对货币价值的深入思考,也只是说明了纸币流通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已。
相对于货币名目主义者对纸币发行数量的关注,宋元时期的货币金属论者大多反对纸币流通,并且或多或少是从对金属货币价值认识的角度来阐述纸币的价值。但囿于对纸币价值符号的认识,将纸币和金属货币等同,因此对纸币价值的研究只能从货币材料及使用价值方面进行考虑,往往得出纸币乃“无用之物”的结论,成为他们反对纸币流通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苏轼反对四川的交子流行,就是因为纸币无实质价值:“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币,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8]叶适主张以足值的铜钱为货币,认为用纸币则“一朝而轻千倍”,这里的“轻”指贬值,价值低。纸币价值低的原因是由于“赍行者有千倍之轻”[9],即纸币的重量轻,因此他反对纸币流通。许衡则将纸币的低价值和作为财富代表的实际商品相对比,得出不可“虚券以易百姓之实货”的结论,并把这种“虚券”和“实货”相交换的现象比作神仙的“点金之术”:“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亦何以过此。”[10]以此说明纸币和实货相比是没有价值的,认为这种“虚券”犹如“瓦砾”,“虚券以易百姓之实货”就相当于把低价值的瓦砾当成贵重的黄金来使用。因此,许衡反对这种无价值的纸币流通。宋末的马端临和王袆都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但两者不同的是,马端临认为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适用之物”、“可贵之物”,肯定了它的使用价值,而纸币是真正的“无用之物”,要使这种无用之物在流通中充当金属货币的作用,就必须以纸币的币值稳定为前提条件。王袆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无论是金属货币铜钱还是纸币楮,其无用就在于没有像商品那样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同样作为货币,“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11]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纸币是虚的价值符号,金属货币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实器”。
明朝的丘浚,有不同于以往数量价值论的货币价值观。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只有他从劳动消耗的角度看待价值问题,提出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他说:“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物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意思是说商品和货币交换必须等价。在批评官府为了私利而发行纸币的言论中,丘浚提到:“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值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然则钞法终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其不可行者,以用之无权耳。”[12]丘浚提出世间万物都是由“人力”创造的,“功力”的深浅决定了价值的多少。“功”即表示劳动,这是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当然,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不能区分价值和价格,但已认识到劳动耗费的多少决定价值的多少。在这里,价值的多少就表现了价格的高低。丘浚是一个金属主义货币论者,他认为纸币的成本低,用“三五钱”纸币来交换由“一日之功所成”的商品是违反等价交换原则的,是不合理的。他提倡足值币和以银为本位的钱钞兼行制度,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尽管他否定纸币流通的理论是错误的,但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他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的“价值”,提出价值和货币进行等价交换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他的这种朴素劳动价值论观点,在后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货币数量价值论占据主导地位。在众多的货币思想中,时常能看到货币数量说的理论影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名目论在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的主流地位。自西汉始,就有不少人认为货币乃无用之物,如贾山就说过:“钱者,亡(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13]晁错也认为:“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这里的“珠玉金银”代表了货币,说钱是无用之物,并不是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是指不能像生活必需品那样饥可食,寒可衣。在当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关注生活必需品是必然的。至于珠玉金银为什么会有较高的价值,晁错认为是“上用之故”,就是说是由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这是一种名目主义的观点。唐朝的韩愈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有权力规定货币的价值,只要给货币规定某种名义价值,就能使它以某种名义价值流通。《管子·轻重》中也有类似货币是无用之物的观点,“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15],当时的很多实例也表现出“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16],所以得出王权决定货币价值的结论。在处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上,《管子·山国轨》篇提出,只要控制住了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数量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商品价格:“国币之九在上(指政府)、一在下(指市场)。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据此,《管子》作者非常重视货币数量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主张由国家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以增加国家的财富。南宋的叶适也是数量价值论者,他主张通过废除纸币来恢复钱币的流通:“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在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认为物价贵贱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商品本身的数量,一是货币的数量。货币名目主义者往往主张后者。如周行已在理论上已看到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某种对等的关系,但他无法从货币和商品的价值上找到相等的结论,只是将这种对等关系归结为惯性的相等。他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本身不存在价值,“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轻重而物为之轻重,”[17]原本没有价值的货币,只有在和商品的交换过程中才表现出购买力的高低。“本无轻重”的错误观点阻碍了他对于商品和货币对等关系的货币价值论的进一步深入思考。
用货币数量来说明物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货币思想中比比皆是,大抵都跳不出“少则重,多则轻”的逻辑框架。如唐朝刘秩提出“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比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18],倾向于单纯从货币数量来看待物价的涨落。白居易在主张平物价论时也提出过这样的策略:“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19]认为通过调节商品和货币的数量就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由于各人的身份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他们在研究货币时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也都不同,提出的货币政策也就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但在认为商品和货币的数量价值关系上则是一致的,观点仍属《管子·轻重》的数量价值论范畴。持有这种观点的思想家们都强调货币可以成为国家调节经济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轻重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论述国家如何利用货币杠杆以调控市场和社会经济活动,但忽略了货币本身价值的思考,未能形成一套较完整的货币价值思想体系。
形成中国古代货币价值理论薄弱的原因,可能与中西方的经济伦理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有关。先秦时期,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观,代表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流价值取向。儒家伦理观的主要思想是强调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为上。“义”指道义、美德,“利”指利益,也可指利润,孔子认为“君子以义为上”[20]。儒家不反对求利,但在义利的关系中,强调义永远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以义为上。利的获得必须符合社会道义,并且认为行义也能产生利。反观西方,在古希腊的经济思想中同样包含了对义善、不义不善等伦理问题的思考。如柏拉图反对商人的唯利是图,主张国家应该制定法律,使商人只能得到适当的利润。但之后中西方的经济伦理发展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在中国,士人们把先秦带有经济色彩的伦理观重心移植到政治领域,却使经济伦理有所枯萎;在西方,古希腊带有经济色彩的伦理观在经济领域中却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不妨具体比较一下孟子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经济思想。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这两位东西方的思想巨人在当时对商品价值表现中的等同关系都有共同的认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直接论证了交换的正义,认为交换的正义就是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亚里士多德式的公正”要求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合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协调要求。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必然促使人们运用价值判断来思考商品货币关系和其它相关的经济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还将这种等同关系表现在对商品价值形式的理解中,提出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两者没有本质的不同。一种商品的价值可以通过任何别的一种商品来表现,床和屋之所以可以交换,是因为两者具有本质上的等同性。罗马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则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把它看作是商品交换的公平准则。中世纪时著名神学家马格努和阿奎那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述,认为“公平价格”是与劳动耗费量相符合的价格,承认公平交换的依据是劳动耗费,成为劳动价值论在历史上的思想渊源之一。阿奎那继承了市场交换追求公平公正的经济伦理,反对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商业利润的行为,他指出:“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21]“公平价格”的判断标准,直到19世纪对西欧经济思想都有影响。可见,古希腊带有经济色彩的伦理观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引导了西方对于货币价值的关注。对于如何解决价值悖论的思考,形成了西方经济思想中一个自成体系的价值理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先秦的经济伦理自孔孟之后,在经济思想领域并未引起重视。孟子也发现,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应该是由其中包含的某种东西所决定。但后人并未将“义利观”应用到对市场中商品和货币交换的公平性研究中,关注的价格问题也仅停留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数量对商品和价格比价的影响,孟子所看到的对商品价格起决定因素的“某种东西”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少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战国墨家也初步认识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问题,看到商品本身不能表现价值,必须借助另外的物品来表现。例如在《墨子·经说下》中就有“为屦以买,不为屦”;“买,刀籴相为贾”①的说法。墨家的这些思想已经触及到价值形态及其表现的问题,胡寄窗教授就认为“在先秦所接触到的各经济范畴中以墨家的价值概念最为珍贵”[22]。可惜的是,墨家的价值概念并未引起后来思想家们的重视,没有得到继承与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缺憾。直到明朝,才出现丘浚关于货币价值不拘一格的认识,和孟子的思想有几分相似。但他的这种朴素劳动价值论的出现,不仅在时间和内容上已经落后于西方,而且缺少后续的发展。
影响中国古代货币价值理论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春秋以后长达二千多年的自然经济结构模式以及经济政策上的重农抑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财富观主要强调农业生产出来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而鄙视货币财富观。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对商品经济的抑制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货币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货币流通作用的不断加强和封建国家干预权力的持续增大,古代思想家们往往因此感到忧虑,纷纷提出货币有害论,甚至提出取消货币的极端主张。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家肯定货币流通,但这也是从为统治者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关于货币价值的本质性思考一直未受到重视。
古代货币价值论的相对薄弱对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一些货币基本观点的错误,使得古代货币思想的关注点和着力点都集中在较次要的方面,且观点零散。基本观点的错误也导致了货币思想的混乱:一方面,对前人的货币思想作片面性理解和总结,甚至对同一历史事实作不同主观解释来支持自己的货币观点和货币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不同货币政策主张者争论的概念不明,比较混乱。这一切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无法形成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通过对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对货币价值认识的总结中,不难发现在缺乏对货币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古代学者对货币流通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倾向于将货币和商品价格的高低贵贱归结于货币和商品的数量因素,即数量价值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材料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无论是金属主义者还是名目主义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论及货币价值和货币购买力时,名目主义者完全撇开币材的价值,强调国家政令和货币数量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过分重视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在纸币流通时代,无论是货币金属主义者还是货币名目主义者都将纸币看作是等同金银、铜钱一样的货币。金属主义者肯定货币的价值,肯定充当货币的金属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但在对待纸币价值问题上往往是从货币材料入手,认为纸币太便宜,无法与金银铜等铸成的钱币同等使用,因而对纸币流通持反对态度。宋元时期,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现象时有发生,造成纸币逐渐驱逐钱币,持有纸币的百姓遭受纸币贬值的严重损失,国家也出现财政匮乏等一系列问题,纸币的否定者便以此为理由否定纸币流通,主张取消纸币制度,更有甚者直接否定货币的作用。如南宋的叶适批评纸币流通说:“天下以钱为患,二十年矣,……钱有轻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矣,而犹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担囊而趋,胜一夫之力,辄为钱数百万。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凡今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9]他说纸币造成了金属货币从市场上的退出,纸币的贬值使得持有纸币的人蒙受重大损失,并且造成市场上商品的匮乏,“天下以钱为患”,因而主张废除纸币恢复钱币的流通。应该肯定叶适对于纸币在实际流通状况中产生的这些不利现象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这些弊端不能直接归结为是纸币充当货币参与流通造成的,而是应该联系纸币贬值,纸币和金属货币的关系以及兑现纸币流通和不兑现纸币流通加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货币价值理论的探索。不仅叶适如此,古代许多思想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许衡也是坚决反对纸币流通的一个官员。他将纸币流通的弊病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政府可以有恃无恐地发行廉价的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而不去注意节约财政开支;二是纸币便宜,便于伪造。他强调纸币是一种“虚券”,没有实物的价值:“楮币之折阅,断无可称提之理,直一切罢而不行已耳。”[10]他对当时的统治者利用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财富的恶劣行径作有力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和其它反对纸币流通的思想家们一样混淆了纸币流通的弊端和纸币能否流通的问题,说明他对纸币的职能还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更缺乏对纸币价值的理解和思考。
货币名目论者作为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主流观点,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在对待货币价值问题上,或归结为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或归结为国家权力使然,或归结为上天的安排。将货币价值归结为主观意志,就已经放弃了对货币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元朝马亨的货币国定说就包含了这种思想,他在反对外国商人控制纸币发行的言论中就提到:“交钞可以权万货也,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23]如果将这个观点仅仅用于反对外商对纸币发行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纸币流通的确离不开国家的法律环境,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在市场中流通,不仅仅是法的作用,离开纸币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和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纸币的流通也是无法实现的。到了文宗至顺年间,刘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国定说。他在一首诗中提到:“八政首实货,钱币通有无。国朝币用楮,流行比金珠。至今垂百年,转布弥寰区。此物岂足贵,实由威令敷。”[24]比马亨错得更离谱,他不仅认为纸币流通靠法,而且无视货币的兑现、发行数量等问题,将一切都归于政府的德政、威刑和威令。在他所著的《郁离子》中明确指出:“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借主权以行世”;“币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后无用之物可使之有用。”[24]这种货币价值论其实是对货币本身价值的否定,既然货币价值是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那么金属如金银可以充当货币,纸币也同样可以赋予货币的价值。货币名目主义者通常是赞成纸币流通的,但他们考虑的角度和视点同样也没有抓住货币的本质,单从纸币的便宜易得、方便使用等较次要的方面进行阐述。如辛弃疾的纸币论就提到“铜楮其实一也”,认为会子的发行“本以便民”,便民的理由就是:“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6]他认为会子的流通解决了钱币不便于运输,不同种类钱币存在不同购买力也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便利。
货币数量价值论在我国古代货币价值理论中的主流地位,还导致了货币思想对于商品市场的忽视,而更多地关注政治,关注国家财政,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例如西汉贾谊的货币思想就带有浓重的“官富”和“末困”的意义,以盈利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他首先批评自由铸钱、货币制度不统一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国家对铸币权和主要币材金属铜的垄断,从而掌握调节商品和货币比价、控制市场管理经济的有力手段。这种手段的实现方式就是:“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5],即国家完全掌握货币的发行和回笼,“钱轻物重”时设法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以提高货币购买力,降低物价;“钱重物轻”时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以降低货币购买力,提高物价,如此实现物价的稳定和对市场的经济管理。国家利用货币调控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通过直接经营商业获得商业利润,一方面可以打击商人的势力,一方面也可获得大量财政收入。这实际上是剥夺商人的商业利润,而转为国家的经济收入。这一过程的实现方式就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25]《管子·轻重》的货币理论将这种通过国家调控商品流通从而获取商业利润增加财政收入的思想阐述得淋漓尽致。桑弘羊主张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也都是以《管子》的轻重学说为理论基础,因此他的货币思想、货币政策主张也是以增加国家财政为首要目的的。与汉武帝之前几次纯粹通过铸钱填补财政亏空相比,桑弘羊主张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财政困难,算是有了一些进步。唐刘秩在阐述国家应该垄断货币铸造权时也是从增加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出发,强调货币关系国家兴衰,“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25]他推崇《管子》的轻重理论,将货币视为治国要术,国家通过调控货币控制物价,使国家富强。他还引用管子的言论来支持他的观点:“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者,是为人主之权。”如果任民私铸,会导致国君不能御民,百姓不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了。陆贽的钱货国定说和北宋张方平“平准万货”、“国之重利”也包含同样的思想。到了南宋纸币流通的时期,这一思想观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辛弃疾和宋孝宗都提到了纸币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如辛弃疾强调会子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紧急关头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危机,“缓急之际,不过多印造会子以助支散,百万财赋可一朝而办。”[6]辛弃疾支持纸币流通的原因是基于解决封建国家财政危机的考虑。宋孝宗甚至认为纸币的发行是暂时性的,它的作用纯粹是出于对财政的需要,所以得出“朕欲尽数收上,它时终为民害”[26]的结论。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的货币理论因缺乏对货币价值问题的研讨,也就无法说明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根源,无法认识到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中国古代货币是否流通的争论中,反对者往往只看到因货币制度、货币管理、货币发行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货币弊端,从而提出否定货币流通的错误观点,无视货币的产生流通是商品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趋势;赞成者则过多强调货币对于解决财政危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无视滥发货币造成的严重后果。以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看,货币固然是国家实行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但这是以遵循货币内在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为前提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因缺乏对货币价值问题的研讨还导致了与西方相比无法形成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不能不是一件历史的憾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致谢!)
注释:
①关于《墨子·经说下》这两句话的断句和解释,本文依据胡寄窗说,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标签:中国古代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价值主张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