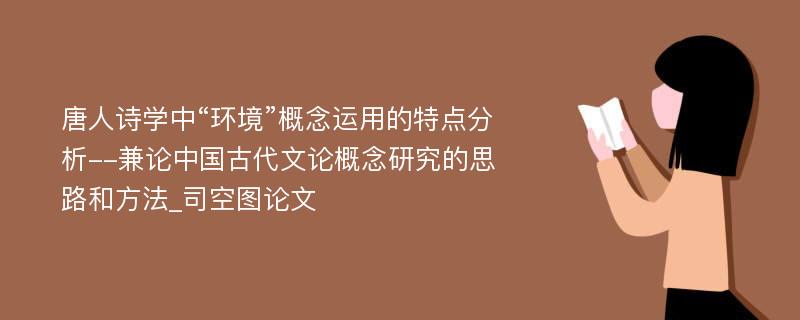
唐人诗学“境”概念使用特征之辨析——兼谈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研究的思路及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诗学论文,文论论文,唐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4-0084-06 自20世纪至今,经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的诠释与阐发,“意境”、“境界”已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它们一般被用来指称文艺作品的审美形态与特征,包含“创作主体情感与表现对象自然浑融”、“虚实相生”、“意蕴丰富”等要点。而回溯中国古代诗学,以境论诗,恰始于唐人,并首先在唐人那里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唐人诗学中有关境概念的言论,自然成为学界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唐人如何在其境论中揭示、完善前述“意境”、“境界”概念诸要点,乃是不少学人习惯性地加以关注、阐释的问题。这方面的努力,既是从概念史角度为当代意义上的意境、境界说探寻流变根源,也是在为论证意境或境界“核心概念”地位之成立寻求历史依据。 应该承认,在这种思维习惯牵引下的相关研究,确实为今人把握唐代诗学的诸多要义作出了贡献。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往往对几个关键问题缺乏警觉。它们包括:在具体诗学语境中,唐人的境概念究竟有哪些含义?以境论诗在唐代是否存在一个逻辑清晰、具有明确理论针对陛的演变过程?在探讨、总结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时,唐人是否自觉地以境概念为论诗的理论核心,该概念与景、味、“象外之象”等概念、命题又是何种关系?若不思考这些,而是径自认为唐人以境论诗存在与当代意境说、境界说相同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就很容易脱离文论史事实,产生失之主观的结论。进入21世纪,有关“境”的基本含义及该概念在古代文论话语中的地位问题,已经不断引发探讨。本文亦希望通过对“唐人诗学境概念使用特征”这一重要个案的辨析,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这既是认识境概念原貌的需要,也有助于把握唐人诗学真实特征,并对当下古代文论概念研究的思路及方法作出反省。 在现存唐人诗学文献中,自觉地多次以境论诗,首见于旧题王昌龄撰《诗格》。于此,首先针对该书中境概念的使用情况展开讨论。 众所周知,“境”之本义为“疆界”,由此引申为疆界所包容之范围、区域,亦引申为心理或精神世界的界限、范围、状态等。佛学兴起后,“境”又可指心所变造的虚幻存在,亦指修行、体悟所及之层级。这些含义在唐代均属常见。那么,《诗格》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境”的呢?在《文镜秘府论》所载该书“论文意”主题下,境概念先后出现于三条文字中: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 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1](P162)。 细读文本可知,第一条文字的要旨在于探讨如何在构思中获取精妙的文意。在作者看来,放松心绪“令境生”,乃是打通窒碍之文思的关键。既然如此,这里的“境”就不可能指身外的景象范围,而是指那种灵感生发时头脑构想的审美形态。《吟窗杂录》所载《诗格》论“生思”时所谓“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1](P173),与此旨趣相合。这一含义与来自佛学的“心所变造”观念无疑存在明显关联。相比之下,第二条中的“境”内蕴又有所不同。不难看出,作者此处是从古代文论中常见的“心物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创作问题的。在“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这段表述里,“境”显然是指“物”的整体范围,与主体晴感处于对待状态,其含义当与唐初孔颖达所谓“物,外境也”[2](P1527)一脉相承。《吟窗杂录》所载《诗格》论“取思”时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1](P173)其中的境概念即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强以“心所变造”这类佛学观念解释此处之“境”,文意反而会窒碍不通。至于第三条所谓“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云云,其实是在强调诗歌立意应具备超越他人的独创性。故将这里的“境”释为前举第一条中之“构思中生成的审美形态”似即合理,释为“程度”、“层级”亦通。 除了这些例证,《诗格》以境论诗的文字还有一处较为重要,那便是保存于《吟窗杂录》中的“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1](P172)这一著名观点。该处的境概念与前述诸意义有何关联呢?作者释“物境”曰:“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释“情境”曰:“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隋。”释“意境”曰:“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细思之,“诗有三境”说的主要目的,实在于指明创作活动中存在物、情、意三类特征不同的表现对象。所谓“物境”、“情境”、“意境”,亦即“物之境”、“情之境”、“意之境”。在作者看来,创作主体之思只有深度投射于这些境中,才能捕捉到其根本特征。由此推论,则三境中无论哪一境,都有待于同主体隋思融合,方可能产生具体的审美形态。所以,这里的“境”,仍然不过是取传统的“范围”义;在“表现对象”这一意义上,“三境”与前举“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或“搜求于象,心入于境”之“境”属于同类概念,只是具体所指不尽一致罢了。而首次出现在文论史中的“意境”一词,其含义自然与当代专指作品审美形态、意蕴的“意境”相去甚远。 通过上述用例辨析可知,《诗格》以境论诗,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种侧重于创作主体方面,涉及审美形态在构思阶段的酝酿生发;一种侧重于创作客体方面,涉及表现对象的类别、范围。那么,这种境论在《诗格》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处于何种位置,与《诗格》中的其他概念、命题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为了弄清这一点,需对《诗格》的现存内容作整体性把握。 作为一部带有“创作指南”性质的著作,《诗格》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立意、生思、构建句法章法这些带有实用色彩的问题。围绕这些话题,诗歌艺术的多种审美特性也随之可得到不同程度和广度的揭示。通读该书可知,当作者沿“心物关系”这一传统思路把握创作问题时,似乎尚未自觉发挥“境”的理论潜力。关于此点,读者在品味前引“论文意”部分里的“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一条文字时恐怕会有所注意。该段话在指涉“表现对象整体”时,不仅用“境”,还用到了“象”与“物色”。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并无突出“境”概念独特性、重要性的意识。再看“论文意”部分的另一条文字:“昏旦景色,四时气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妙……至晚间,气霭未起,阳气稍歇,万物澄静,遥目此乃堪用。至于一物,皆成光色,此时乃堪用思。所说景物,必须好似四时者。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1](P169)在这段话中,主体观照对象并非孤立物象,而是景观的整体形态特征,这似乎是最适合用境概念加以指称的。而在上文对观照对象颇为琐细的描画中,作者频繁使用的恰恰是景色、气象、景物、气色等词,完全未顾及“境”概念。再如下面两例:“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中手倚傍者,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此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1](P166)“诗有‘明月下山头,天河横戍楼。白云千万里,沧江朝夕流。浦沙望如雪,松风听似秋。不觉烟霞曙,花鸟乱芳洲。’并是物色,无安身处,不知何事如此也。”[1](P168) 两段引文其实涉及两种问题。一种是景句的整体审美特征,一种是构成景句的具体物象单位。以今看来,前者若用境概念加以诠释会颇为恰切,如此则文字思理也将更为清晰。然而作者似并无这种分别意识,而是在讨论时一概混用“物色”、“象”诸概念。不仅上举诸例如此,除前引“以心击之,深穿其境”那段文字外,在“论文意”其他涉及心物关系的各类内容中,作者也均难得对境概念一加青眼。与此相类,《诗格》中的“十七势”专论篇章结构、意脉经营,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创作主体之意(或理)与表现对象的结合关系问题。有趣的是,境概念在这类很容易找到自身发挥空间的语境中,偏偏鲜有出场。取而代之的,乃是景、景物、景象等概念。这些事实恐怕可以说明:作为“整体范围”意义上的境,其相对于物色、景、象的独特性并未得到作者的格外重视。无独有偶,前述境概念“头脑构想的审美形态”这一含义,在《诗格》中也缺乏充分的生发。在讨论“生思”问题时,《诗格》中分析最充分的几段文字,无一例外地沿袭了传统诗学中的感兴观念。今人论感兴问题时常引用的“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及“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1](P170)云云,均为其中显例。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始终找不到“境”的踪迹。 值得留意的情况尚不止这些。在《诗格》中,有不少文字不仅涉及诗歌的构成与形态,而且还涉及诗歌的意蕴。这由文字表象传达的深层艺术魅力,正好是当代“意境”、“境界”说特别关注的内容。可耐人寻味的是,在《诗格》作者言说这些问题时,境概念并不在场。如“十七势”中“理入景势”条曰:“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理欲入景势,皆须引理语,入一地居处,所在便论之。其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1](P157)“景入理势”条曰:“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1](P158)再如,“论文意”中的两段表述:“夫诗,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如‘孟春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1](P163)“诗贵销题目中意尽。然看当所见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1](P169)以上讨论均没有用“境”,而是自觉地沿用早已阐发于六朝的“味”观念来揭示意蕴之于诗歌的重要意义。比较可知,这些表述的理论渊源独立、明晰,自身意旨完足,很难说是为补充、完善“境”概念这一目的而发。换言之,它们与“境”并不构成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就此而论,当代部分学者将其视作《诗格》中境论的组成部分,也许并不符合作者之原意。 由上可知,《诗格》中的“境”概念,当被用来诠释创作活动特征时,专指构思问题;而被用以指称表现对象时,则不脱离“范围”意,在不少语境中与“景”、“物色”含义无实质区别。“诗有三境”说提出的“情境”、“意境”,指称内容确实与“景”、“物色”不同,但作者对此并无一以贯之的自觉使用。在《诗格》有关诗歌艺术特性的讨论中,境论只是诸多观念之一,而非理论思考的核心,也并不具有统摄其他概念、命题的可能性。“意蕴”这一当代意境说、境界说关注的重要内容,在《诗格》中确已得到了自觉思考,但对它的探讨并不是由境论承担的。 那么,中晚唐诗学中的“境”概念具有怎样的使用特征呢?正如时贤指出的那样,与初盛唐相比,在中晚唐文人处,心与境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可能与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不可分割。至于以境言诗,在这个时段也存在几个不同的侧重点。其中之一,是以境指称、诠释创作活动中的特定环节。皎然著名的“取境”说堪称此方面代表。《诗式》中的“取境”,主要是指创作活动中的构思与推敲。就此来看,该说或许受到了前述王昌龄《诗格》中“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这类观念的启发。以上内容诗学界阐述颇多,此不赘述。至于以境言诗的另一个侧重点,则主要针对诗歌文本,涉及其形态和审美特征等问题。这类情况便显得较为复杂,也是需要细心加以清理的。 我们的考察不妨从权德舆的“意与境会”和司空图的“思与境偕”开始。当代学人之所以格外重视这两个命题,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认为它们以“境”这个内蕴更为丰富的概念代替物、象、景等概念,体现出对“神与物游”、“情景交融”等命题的超越;其二则是认为它们已体现出对“意”“境”结合所生之审美特性(如意蕴丰富、虚实相生等)的自觉,与刘禹锡“境生象外”命题存在义理关联。事实是否如此呢?为此需回到这两个命题所处的原始文本语境中去作判断。“意与境会”,出自权德舆《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 建安之后,诗教日寝,重以齐梁之间,君臣相化,牵于景物,理不胜词。开元、天宝以来,稍革颓靡,存乎风兴,然趋时逐进,此为橐钥。绅佩之徒, 以不能言为耻。至于吟咏性情,取适章句者鲜焉。有许氏子者……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情性,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其道退,其徒寡,不交当世,故知之者希[3](P5002)。 “思与境偕”,出自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则前所谓必推于其类,岂止神跃色扬哉[3](P8486)。 权德舆、司空图均未明确阐发“境”的内涵,因此个中意味只能由我们审慎地推测。从《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的文本语境可知,权氏话题始于对既往文学现象的批评,并最终过渡到对许经邦诗作的赞美。他一则批评齐梁诗“牵于景物,理不胜词”,二则肯定唐开元、天宝诗“稍革颓靡,存乎风兴”,最后赞美许诗“意与境会”;贯穿于三者中的评判尺度,其实是相关作品中的“心”与“物”这对矛盾是否能保持平衡。换句话说,该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心物关系。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境”与“景物”同属与“心”相对待的“物”,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性质差别。这种理路,既与前举王昌龄《诗格》中的“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一致,也可在中晚唐其他诗学表述中寻得共鸣。举旧题白居易撰《文苑诗格》为例。该书“杼柝入境意”条曰:“或先境而入意,或入意而后境。古诗:‘路远喜行尽,家贫愁到时。’家贫是境,愁到是意。又诗:‘残月生秋水,悲风惨古台。’月、台是境,生、惨是意。若空言境,入浮艳;若空言意,又重滞。”[1](P365)“招二境意”条曰:“或于一句之中用物色,第五字招第二字为上格。今诗云:‘乱石不知数,积雪如到门。’”[1](P365)可见,在同样产生于中晚唐的这部著作中,境或指“家贫”这种人生场景,或指月、台这类自然景观,其内涵与“景”概念并无差别。尤其从“招二境意”一条可见,在专指景观时,作者仍然缺乏界说物色、境二概念差别的自觉。既然存在这些实际情况,那么专从“心所变造”这一佛学含义立论,认为权德舆“‘意与境会’的主导方面实在于意,境乃是意之境”[4](P11),就可能失之武断了。与此相同,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仅是说王驾“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而从前及中晚唐诗学背景来看,这里“诗家所尚”的“思与境偕”,可能包含了从“心所变造”思路阐释境的意图,也可能是指作为唐人诗学常识存在的心物交会、情景相融这类常识,因此,同样是未必具有特殊理论意义的。 再进一步看,从二命题各自文本语境中还可发现,无论权德舆还是司空图都没有自觉地揭示“意与境会”、“思与境偕”的作品应具备哪些审美特征。就权德舆来说,他确实提到了“所趣皆远”这一特征,但在文本中,与其直接相关的毕竟是“得之于静”,而不是“意与境会”。司空图又如何呢?我们当然可以作出如下推测:既然他对“趣味澄夐”的王、韦风致青眼有加,则他同样欣赏的“思与境偕”之作,或即应具备这些品格。不过,这种可能隐隐生长于作者思考中的模糊意图,毕竟在意旨上具有不确定性,与透辟的阐释分析在理论水平上存在高下之分。也就是说,在揭示“思与境偕”这一命题时,司空图并不具备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阐释“辩味言诗”时所达到的深度(此点详后)。而事实上,这种模糊表达,也代表了中晚唐以境概念阐释诗歌审美特征所能达到的常见理论水平。诸如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里以“五言之佳境”、“穷思极笔,未到此境”、“稍入诗境”等评语赞许诗人,白居易等屡次在作品中说及“诗境”等例证,今人均已颇为熟悉。这些事实自然可以证明,在文艺活动中,境概念的语用范围更为广阔;“诗境”等合成词的出现,可能反映出以境指称“艺术思维构造的虚灵世界”的思考倾向。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诗歌作品中所云“诗境”毕竟多是对抒情氛围、优美场面的笼统描绘。该词能否被视为已得到自觉反省与诠释的批评概念,还有讨论余地。而高仲武式的以“佳境”、“未到此境”诸语评诗,其意旨也是笼统宽泛的。它们固然可能特指“艺术思维构造的虚灵世界”(这是很多当代论者最希望证明的),但也可能只是指层级、水准。就此言之,在这类表述中,“境”概念那些被今人不断揭示、阐发的理论内涵,很难说已经得到理性、自觉的开掘。可以说,在中晚唐以境论诗的文字中,像刘禹锡“境生象外”说那样通过明确分辨意与言、境与象之差别来自觉阐述文本层次、虚实及意蕴问题的案例,实不多见。 那么,诸如文本层次、虚实、意蕴这些当代境界说、意境说的要害问题,是否在中晚唐人那里缺乏深细的省思呢?事实上,对这类问题的阐发,正是在该时段呈示出引人瞩目的理论深度。只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相关阐发中,中晚唐人往往运用并深化的乃是传统诗学中的味、象等概念或“重旨”一类观念;而“境”则在很多语境中处于缺席状态。细究之,中晚唐人的相关思考又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延续政教诗学思路,虽然自觉关注诗歌文本的层次问题、意蕴问题,但将物象、景句与特定意旨机械对应,亦将比兴观念及表现方法狭隘化、机械化。旧题白居易撰《金针诗格》、旧题贾岛撰《二南密旨》、僧虚中《流类手鉴》、徐夤《雅道机要》等著作中,均有表现出这种倾向的文字。这类观点对初学者的影响不容低估,但其理论价值终归不可高估。二是不纠结于政教思路,而是以把握创作一般规律为着眼点,揭示诗歌审美特征的诸般问题。这便显示出理论的相对通达。《文苑诗格》论“语穷意远”、王睿《炙毂子诗格》解说“模写景象含蓄体”、僧齐己《风骚旨格》申说“不尽意”等等,均有此类特征。而个中最具深度与典型意义者,则仍推皎然、司空图二公。在皎然的《诗式》、《诗议》中,相关分析或者是采用总论形式,如:“诗有七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至丽而自然。”[1](P226)“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1](P233)“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1](P242)“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巧,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1](P203)或者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加以申说,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物色带情句也。”[1](P209)“‘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使今古作者味之无厌。”[1](P247)“宫阙之句,或壮观可嘉,虽有功而情少,谓无含蓄之隋也。”[1](P252)“客有问予,谢公此二句优劣奚若?余因引梁征远将军记室钟嵘评为隐秀之语……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1](261) 以上引文,均为今人阐发皎然境论时所常用。不过,一旦我们跳出“境论乃是皎然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一思维习惯,就可以察觉:上述表达中涉及的概念、命题及思维方式,均存在自足的、传承有绪的诗学传统,与境并不构成诠释与被诠释的关系。的确,皎然在《唐苏州开元寺律和尚坟铭并序》中明确说过:“境非心外,心非境中。两不相存,两不相废。”[3](P9564)我们也有足够材料证明他惯于从佛学层面理解“境”的内涵。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皎然如何理解“境”,而在于他是否、而且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将其用于诗学研究的。从现存文献可见,除了前及“取境”说外,皎然尚在《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中以“盼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5](P2013)赞美画艺,在《诗议》中有“含境对”一条,并以“赋曰:悠远长怀,寂寥无声”[1](P212)解释之。笔者无意否认“造境”说的理论价值,也承认“含境对”中的“境”涉及了意蕴美问题。但比较后可知,这些文字在揭示有关审美特征问题时,无论丰富性还是深度,都是不及前举例证的。值得辨析的还有皎然《诗议》中的“境象不一,虚实难明”[1](P204)一说。细玩原文,可知该观点中心意图在于说明属对需要灵动活泼,不能“句句同区,篇篇共辙”,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套路、法则,否则便是“拘而多忌,失于自然”的“俗巧”。弄清这个整体语境的旨趣后,就可知道,皎然所谓“境象不一,虚实难明”云云,不是要揭示境与象二者在特性上存在虚实的差别,而只是在说:无论“境”还是“象”,都有很多种类,有虚有实,故很难为其作出精细准确的归类。讲这个意思,正是要为他“凡此等,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这类灵动活泼的对偶观提供理由。由此可知,该语境中的“境”与“象”或许存在范围大小的区别,但并无性质的区别。所以,这里的思考,与刘禹锡的“境生象外”并非一事。言说至此,我们或可以认为:在思考诗学问题的时候,皎然并未自觉将“境”当作核心概念。在探讨文本层次、虚实、意蕴这些当代意境说的关键问题时,其境论参与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司空图处。司空图提出“辨味言诗”、“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一系列重要命题的《与李生论诗书》写于唐天韦占元年(904年)或稍后,除开存在真伪争议的《二十四诗品》和讨论诗文风格关系的《题柳州集后序》外,司空图阐发诗歌审美特性时最具深度和启发意义的文字,显然不是“思与境偕”。尤其是最晚出的《与李生论诗书》,乃是司空图写于生命尾声、具有个人诗学总结意义的文章。在这篇今人熟知的作品中,司空图采用生动的譬喻揭示诗道,而他所信赖并运用自如的,仍然是“味”、“韵”这类传统概念,而不是境概念。就这些事实来看,境与境论,恐怕并非司空图青睐的说诗方式。与皎然相同,他有关诗歌审美特征的思考具备独立的诗学传统和自觉的问题意识,即便没有境论的参与,也同样是自足的、充实的。 总之,以境论诗,确实是中晚唐诗学的重要内容,但今人似不宜夸大其理论深度和诗学史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段的具体诗学文本语境中,论者未必均以来自佛学的“心所变造”义理解境概念;该概念诸义并存的特征,与王昌龄《诗格》呈现出的格局并无实质性差别。无可否认,中晚唐人对诗歌审美特征的理性反省具备了相当深度,当代“意境说”、“境界说”格外关注的诗歌文本层次问题、虚实问题、意蕴问题,在此时均得到了持续探讨,亦给后世重大影响。但归根结底,境论在其中承担的任务其实还是有限的。这一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命题均是阐释特定诗学问题的方式之一,彼此间并不存在上下位关系,也未必存在历时层面上此消彼长式的演进特征。 通过辨析唐人诗学境概念的使用特征,我们亦可对当前古代文论概念研究的思路及方法作出反省。 概念研究始终是古代文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时至今日,概念在不同原始语境中的含义及使用特征,仍然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古代文论概念的含义并非散碎无可归纳,不过其意旨多样、意随文设的特点终归非常明显。正因为此,今人在面对它们时,就应该坚持“语境优先”的原则,力避仅从有限的、局部的案例中归纳其含义,然后不加辨析地以之解读其他案例。做不到这些,就容易造成对概念及整个相关文本的误读。尤其是,当我们欲判定某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在特定文本中只存在一种解读可能性时,就需要注意,这种判断的成立,至少应满足以下三条件中的一个:其一,该概念只有在如此解释时,所处文本语境方才意旨通达。而用该概念的其他含义解读,文本意义则窒碍不通。其二,该文本作者只知晓该概念的这一含义,而不可能知晓其他含义。其三,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作者在该文本语境中使用此概念时,只可能赋予其这种含义,而非其他含义。以此为据自可知晓,本文所论之境概念,即便在中晚唐,也未必处处与“心所变造”、“境生象外”之思理保持一致。在解读古代文论其他概念时,这类判断的存在,同样可能使我们不至得出失之武断的结论。 那么,在研究古代文论概念时,今人何以会对其某些使用特征格外重视,以至于即便心存求真意愿,却仍时时陷入一定的误区呢?这其实与特定时代的学术背景所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可分割。而该情况恐怕才是相关研究更需要警觉的。近年来,罗钢、蒋寅等学者均已指出,当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概念无论内蕴还是核心地位均系今人重建的结果。但无论在有关境概念流变史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其他古代文论概念的考究中,“意境核心论”(或“境界核心论”)式的思维习惯,依然较普遍地存在。这种思维习惯的基本特征,是把古代文论丰富多样的概念世界理解为一个逻辑关系井然有序,各层级衍化脉络严谨清晰、目的明确的抽象系统。至于其在相关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则可分为四个方面:为古代文论寻找兼综众美的单一核心概念,认为古代文论流变特征体现于若干核心概念的历时性承接替代,夸大特定概念在某些批评家言论中的实际地位,夸大特定概念中某些含义的实际应用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可能让我们误解古人特定文论概念的内涵和文论史价值,亦曲解古人概念使用的习惯,于是对意义本来相对自由的概念作出严谨化、规范化处理,为地位平等的概念强分上位下位、主从关系,将同类概念的多样化使用视为不规范的混用、误用。诚然,某些概念在古代文论话语中确实具有格外突出的意义,而将古代文论概念系统视为混乱随机的聚合体也自然是研究的另一个误区。可不管怎样,在古代文论史中,概念的使用,总是服从于特定文本语境和特定问题意识之要求的。如果对这些实际情况缺乏明辨和省思,那么我们有关文论史流变的描述即便再过清晰明了,也终归无益于趋近真相。 什么是正确的、足以再现历史原貌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其实永远难以被我们获得。但不管怎样,尽可能从多样的角度审视问题,跳出既有思维定式,力避以今律古,仍是可被我们自觉察知的应然方向。当我们不再纠结于上述有关古代文论概念研究的思维习惯时,或许就能够发现:与境相比,众多重要概念(如神、气、韵、味等)在揭示文学现象时,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视角与优势。它们在文论史上长期共生,相互关系多样而复杂。这样的特征,正体现出古代文论运思方式的灵动与丰富;而今人又何必另立门庭,以单一的核心概念、机械的衍化逻辑剪裁之、容纳之。与此同时,摆脱前及思维习惯后,我们亦能更为从容地审视境及其他概念所处的具体语境、所从属的问题意识,对这些概念作出更为细致、完整的意义归纳,并判断其意义衍化与相关语境、问题意识的关系。以此为基础的文论史研究,庶几将具备更为扎实的起点。 [收稿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