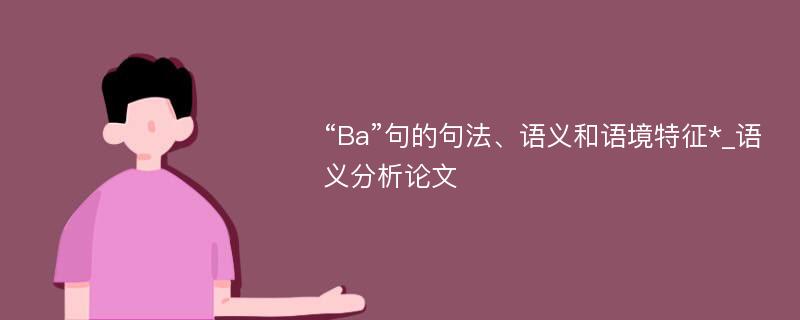
“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法论文,语义论文,语境论文,字句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本项研究试图改变以往语法研究的传统,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语法研究的目标在于对句法结构做出充分的解释,所要解释的问题主要是:1.结构的语法意义,什么样的结构表现的是什么样的语法意义,或者反过来,比如“被”字结构表现的是“被动意义”;2.某一类句法结构内部的结构规律,结构的组织过程;3.结构体的形成(选择)和使用上的规律。
中国现代语法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是第一种研究类型;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主要属于第二种研究类型;功能语法主要属于第三种类型。我们试图综合以上三种研究,力求在了解了某一结构体所对应的语法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这一结构体与使用这一结构体的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是一个运用中的结构体的价值,此时此地为什么它表现的是这样一个结构,而不是另一种结构,这是由什么因素来控制的?说话人根据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选择了适当的词以后,是根据哪些因素来选择这一结构的?
本文对“把”字句的分析作为一种个案性研究,它同时对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处理以及第二语言教学有一定意义。
1 “把”字句的结构特征
崔希亮先生(1995)把“把”字句的结构描写为:A把B-VP,并说明其中的VP典型形式是VR或包含VR的谓词性结构;其它形式的VP是动词的重叠或者在动词前面加“一”。V必须能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或动量补语、或重叠、或与介词共现,这些动词表示活动、动作、评价、感觉和生理活动,在“把”字句中使用最多的是动作动词。这一结论是很有价值的,确实比薛凤生(1994)概括的“A把B+C”涵盖了更多的语法事实。因为在薛先生的文章中我们没有见到下面Ⅱ和Ⅲ两种句法形式,尽管从形式上来看“A把B+C”的抽象度更高,可以把崔的结论包括在内,但是这一公式在薛文中所涵盖的句法事实实际上并不包括崔所描写的事实。更何况抽象得越高,其解释的功能价值也就越低。
崔对句法结构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即“把”字句的句法结构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类:
Ⅰ.A把B-VR(如: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Ⅱ.A把B-DV(动词的重叠形式,如:你把衣服洗洗/你把衣服洗一洗)A把B-V(“一”加动词,如:把头一甩)
Ⅲ.A把B-V-NM(动词+数量,如:把他批评了一顿)这样的概括和分类基本上包括了所有“把”字句的基本形式。尽管薛先生认为他的抽象“足以涵盖所有的‘把’字句”,但是显然还是遗漏了崔先生所描写的后两类形式。我们认为崔先生的这一分类和概括的价值还在于,它具备了与“把”字句的语义分类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的可能性(请见以下语义部分的讨论),虽然这种对应性还不严格,还不能说是使用“把”字句的充分条件,但是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崔先生对“把”字句中的动词的描写也比以往的研究更为具体细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贡献。
当然崔先生对“把”字句中动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1)崔先生对动词的分类中,“喜欢”属于“感觉动词”,而“讨厌”、“热爱”属于“性质动词”,分类的标准不太清楚。2)崔先生认为“行为动词”不能构成“把”字句,比如:“游泳”、“压迫”、“帮助”等。但是这些动词变成单音节后,还能不能?对动词的音节是否能影响构成“把”字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从崔先生的动词分类中看出了一个形式上的规则:凡是能够进入“V得”框架的动词都能构成“把”字句。
受马庆株先生研究的启发,我们觉得能够用于“把”字句的动词大多是“自主动词”,不能用于“把”字句的动词大部分是非自主动词(马庆株,1988),请看附录。
我们知道,任何对句法结构的描写,都仅仅是在结构形式上提供了一种形式上合格的句法框架,它只提供一种使用上的可能性,而永远不可能作为使用这一结构的充分条件,因为在理论上事物本身不可能构成它的运动。构成一个结构的理由必然存在于这一结构之外。所以崔先生对“把”字句结构描写的结论还仅仅是构成“把”字句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2 “把”字句的语义特征
2.1 对“把”字句的语义分析,崔先生原来分作两大类:结果类和情态矢量类。(金按:“矢量”这个词在数学上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既有方向(“矢”的意义)又有数量关系的现象,崔先生这个词用得不准确。结果类指的是“把脸冻得通红”这一类,而情态矢量类却包括了动词的重叠形式(你把地扫扫)、动词前加“一”(把筷子一拍)、动量补语(把地扫了一遍)三种。然而根据崔本人的研究,前两种具有“情态特征”(尝试态和即时态),后一种只表达动作的量。根据这一点,我们把它们重新作了分类,并且这种分类与第1节中的三个结构类是互参的:
Ⅰ.结果类(比如:把脸冻得通红)
Ⅱ.情态类(比如:请你把地扫扫、把筷子朝桌上一拍)
Ⅲ.动量类(比如:他把这些过程又演了一遍)
对“把”字句的语义特征的研究,不能仅仅是一种分类。无目的的分类研究不会有实质性的贡献,至少目前如此。对“把”字句的语义研究,理论上的目标是:求出若干类语义结构特征所对应的若干类“把”字结构的形式,并且尽可能做到二者之间具有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实际上这一理论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同一种语法意义可能对应于若干不同的句法形式(金立鑫,1993b)。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责任同时求出,在语义结构对句法结构的要求之外,其它控制“把”字句的结构的因素。如果一种语义结构仅仅是构成某一种结构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有其它因素也是构成这一结构的必要条件,那么语法学家就有责任寻求出所有的必要条件,如果能把所有的必要条件相加,就能够得出使用这一结构的充要条件。这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一种假设。我们想在崔先生和薛先生的基础上对“把”字句尝试作这一工作,实际上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标,还要看我们下面的研究。
2.2 根据崔和薛的研究,结果类可以表述为两个述谓结构之间(以动词为核心的述谓以及它和补语之间构成的述谓)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上面的“把脸冻得通红”中的“冻”和“通红”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际上薛先生所归纳的语义结构公式适用于这一类“把”字句的语义解释。薛先生的语义解释是“由于A的关系,B变成了C所描写的状态(而不是A如何处置B)”。这一结论与金立鑫(1993a)的结论是一致的。从这一语义结构能导出“B与C之间存在‘主谓关系’”,即把“把”以及它前面的成分砍掉,后面的结构可以成句,如上面的“脸冻得通红”,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把饭吃饱了”一类句子不合格的问题(因为“吃”的结果是“肚子吃饱了”而不是“饭吃饱了”。这个例子是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秦光豪教授提出来的)。
结果类的“把”字句可以作上面的解释,但是这一解释是否就是使用结果类“把”字句的充分条件,则还很难说。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我酒喝完了”这样的“小话题句”,它也同样满足上面的语义解释。那么,结果类“把”字句的使用还有其它制约因素在起作用吗?这是疑问之一。
另两类“把”字句的语义更是和上面的解释完全不同。
2.3 情状类“把”字句的语义,其结构中的VP描述的是动作 即时的或尝试的情状。但这些情状的指向,还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例如:
A 他把书一扔,掉头就走了。B 他把眼睛一闭,理也不理我。
你把地扫一扫。你把腿抬一抬。
A类的动词指的是前面的施事,B类的动词是否指向“把”后面的名词?如果它们的指向不同,它们的语义抽象就会不同。A类可以抽象为“A作用于B时,A具有突发的短时的情状”(或尝试的情状,而后者则是“A作用于B时,B具有突发的短时的情状”(或尝试的情状)。
同样,这一类“把”字句的语义作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语义结构还可以用其它非“把”字句表述,如:“他眼睛一闭”、“他一闭眼睛”、“你抬一抬腿”等等。也就是说,这样的语义表达并不能必然地构成“把”字句,它还不是构成这一类“把”字句的充分条件。很明显我们还没有找出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严格”的对应关系。还有什么因素在决定着“把”字句的形式呢?这是疑问之二。
2.4 动量类“把”字句中VP的语义,表达的是动作的量(动量)。我们大概可以把崔先生的意思化开来,这一类“把”字句的语义结构是V[A,B];C[V]……。比如:“他把这些过程又演了一遍”:演[他,这些过程];一遍[演]。也就是说,动量类的“把”字句中的VP结构里,其它的成分对动词核心有述谓的作用,它们分别说明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在数量上的特征。我们进一步把这一类“把”字句的语义特征归结为:“A作用于B的动作具有一定的量”。例如:“他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他读文章”的“读”有一定的量)。
同前面两小节一样,如果对这一类“把”字句的语义作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这一语义特征同样可以表述为许多非“把”字句。比如“他读这篇文章读了一遍”,也同样能够满足上面的语义特征。构成“把”字句的充分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疑问之三。
或许是我们的语义解释不够准确,或许还有语义之外的因素在制约着“把”字句的作用。我们在下面的几节中将作重点讨论。
2.5 根据薛凤生先生(1994)的定义“由于A的关系,B变成了C所描写的状态(而不是A如何处置B)”,对“把筷子朝桌上一拍”这样的句子,就要解释成:由于某人的关系,“筷子”变成了“一拍”的状态。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并且薛先生的语义解释也同样不是构成“把”字句的充分条件。
3 上下文语境的要求
在2.2、2.3和2.4节里存在三个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我们对“把”字句的语义解释并不严格地对应于“把”字句。这样的语义解释也可以用来解释许多非“把”字句。或者说,这样的语义表达并不是构成“把”字句的必要条件。说话人为什么要使用“把”字句,这里当然有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义要求,也就是他要通过结构形式来表达的含义。但是当我们在作了以上的研究之后,仍然夫法得出准确的结论时,我们不得不转向其它领域寻找答案。在没有任何把握之前,通过归纳性的调查和统计来获得理性的灵感,大概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调查了一部中篇小说中所有使用“把”字句的情况。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很多“把”字句的前接句都有成分与后面的“把”字句中“把”的宾语是同指性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把”字句中“把”的宾语绝大部分是定指性成分的根据原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当前接句中有成分与后续句的宾语同指时,后续句有使用“把”字句的倾向。〔1〕这一倾向可以用篇章的衔接来解释,两个成分如果同指,出于前后的照应关系,心理上要求这两个同指成分在物理距离上尽可能地靠得近一些。这一作用也同样表现在被动句中。
我们在中篇小说《红河》(《收获》1989-2)里,共收集到“把”字句66例。请看下面的例子:
(1)我拼命地跑,人们跑过来像抓小鸡一样把我抓住了,又给我穿上了新的衣服带上了新的花。
(2)我爸拿起杠门棍打接生婆,一棍下去接生婆便躺在血水里,又一棍就把她一根脚骨敲断了。
(3)她恨恨地看着这个像大肚子红萝卜一样的短腿男人,在心里把他咒了九九八十一遍。
(4)莽长开始东倒西歪地移动了,斜上了一道沉郁的岭坡,那道岭坡一点一点将他吞噬了。
(5)(莽长……),瘦荆牵红牯啃水草时把他弄醒了。
以上5个例子中的“把字结构”都可能用SVO的结构来表达,句法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篇章的衔接上稍稍差了一些。例如(1)改成下面的(6)、(7)和(8):
(6)我拼命地跑,但是人们跑过来抓住了我。
(7)我拼命地跑,但是人们跑过来把我抓住了。
(8)我拼命地跑,但是还是被(跑过来的)人们抓住了。从篇章的衔接上来说,(7)比(6)要好一些,而(8)又比(7)好。我们发现,当后续句的底层宾语〔2〕与前接句的主语同指,后续句倾向于使用被动结构;后续句的底层宾语如果与前接句的宾语同指,后续句倾向于使用“把”字结构。在上面的例子中,作者为什么不用(8)而用(7),可能与“被”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不宜太复杂有关。
再看后续句的底层宾语与前接句的宾语同指的情况,我们(金立鑫,1993a)曾经举过一些极端的例子,说明这种结构在篇章上的照应关系:
*爸爸买了一盆花,他在阳台上放着这盆花。
这个句子在篇章上的衔接明显不合格。如果后面的句子使用“把”字句,情况就会好一些:
爸爸买了一盆花,他把这盆花放在阳台上。
我们好像不能排除后续句使用被动结构的可能性。因为使用被动结构也同样满足了篇章上的衔接和照应关系,两个同指成分在物理距离上更近,应该更合理。确实如此,后续句确实可以使用被动结构。但是这涉及到后续句是否要转变话题、另建话题链的问题。如果后续句试图转移话题、另建话题链,就可以使用被动结构。
陆丙甫有一个关于“动不如不动”的说法,我们在这里理解为:如果并不是转换话题或其它特别的理由,最好不要轻举妄动。移动距离越远,越要有更为充足的理由。句法上的经济原则是: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要动,动不如不动,大动不如小动。相对静来说,必然有其“特殊含义”(比照语用学中的会话合作原则)。上面的例子如果作下面的变化:
爸爸买了一盆花,这盆花被他放在阳台上,(没想到后来竟被人偷走了……)
可以看出,如果使用被动结构,说话人很可能试图改变话题(见上面括号中的句子)。
4“把”字句的语义重心
通过上面第2和第3节的讨论,我们对决定使用“把”字句的条件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满足了第2节中对“把”字句的语义解释,也满足了第3节中的上下文篇章的要求,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情况下并没有篇章上的要求,说/写者却使用了“把”字句。可见我们以上的解释还不能满足这些“把”字句在决定是否使用这一问题上的解释。现在我们想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和“语义重心”联系起来,看看是否会有一些结果。我们这样做的假设是:在满足上面的语义表达要求和篇章接续的要求之后,语义重心的表达可能决定对“把”字句的选择。我们(金立鑫,1993a)曾经通过比较和分析证明一些“把”字句的语义重心可能是“把”后面的宾语。正是由于对宾语的强调,才促使了“把”字句的形成。请看下面的例子:
(9)瘦荆狠狠地嚼碎了马鞭草,把一口青绿的渣渣吐出来。
(10)油倌回来把榨看了好久,又把我看了好久。
(11)发痧了,痧已经过了肩背,快去把莽长喊来呀!
(12)那条命早晚也会送掉的。他把许多狗都逼疯了,整天在疯狗里转悠。
(13)莽长跟我走时,没忘了把他的针裹带上,那针裹里只有两根针。
以上例句可以换成下面的句子:
(14)瘦荆狠狠地嚼碎了马鞭草,吐出一口青绿的渣渣来。
(15)油倌回来看了榨好久,又看了我好久。
(16)发痧了,痧已经过了肩背,快去喊莽长来呀!
(17)那条命早晚也会送掉的。他逼疯了许多狗,整天在疯狗里转悠。
(18)莽长跟我走时,没忘了带上他的针裹,那针裹里只有两根针。
这些句子都没有问题,也不影响篇章的衔接。我们认为(9)—(13)是说话人为了强调句子的宾语而采用“把”字句的。这一结论和传统的“尾焦点”论以及崔希亮有关语义重心的结论相反。我们想证明这一结论,请看下面的分析:
例(9)的“吐”和补语“出来”属于同源性质,“出来”是冗余性附加成分,语音上也轻读,如果说这个成分是语义重心,恐怕不合理。(10)如果用“好久”处于“尾焦点”的位置来解释的话,那么例(15)中的“好久”同样是尾焦点,和例(9)相同。为什么说话人还是采用“把”字句呢?例(11)的“把莽长喊来”和“喊莽长来”也同样是“来”处于句尾,可以说“来”的位置并没有变动,而倒是“莽长”的位置变动了。
我们认为正是这一位置的变动才可能引起听话人的注意,从而实现了这种“把”字句的语用价值。根据“动不如不动”的经济原则,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要轻举妄动。“动”总是有它特别的理由。我们觉得,被移动的成分总是比没有移动的成分负载更多的特殊含义。在语用上,被移动的成分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作出移动的,在这里,移动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人更多的注意。(12)和(13)的情况同样如此。
当一个“把”字句可以转换成SVO的形式,而语义上又没有本质变化、前接句中也没有成分与后续句同指(即没有篇章上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主观上对底层宾语的强调的要求将构成使用“把”字句的决定性因素。
本节对语义重心成分的证明是否能够成立,并不重要。如果确实有能够充分说明“把”字句的语义重心在后的证据,那么我们可以作一些技术上的修正。但这不影响本文的思路。实际上这是在语义重心问题上两种不同假设的分歧。一种假设认为,“尾焦点”是恒常的(句尾永远是焦点),另一种假设认为,尾焦点是典型状态,典型状态中的焦点可以作某种移动,移动之后可能不在句尾,但仍然是焦点。本文持的是后一种假设。如果作前一种假设,那么本节应该将“把”字句的选择归结为对动词后补足性成分的凸显,“把”字结构前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5 句法和篇章的强制性
在研究“把”字句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把”字句的使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使用“把”字句,必然会造成句子的不合格(或语段的不合格)。如:
*我种花在阳台上。
有些句子中的动词后面跟着补语成分,而这些补语成分又无法和宾语同现,〔3〕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句法矛盾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让动词重复,两个动词,一个带宾语,一个带补语。比如:他洗衣服洗得很干净。另一个办法是让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动词前面的位置有两个:一是主语前,一是主语后。在主语前面的,有两种句子,一种是话题句,比如:衣服他洗得很干净。另一种是“被”字句。在主语后面的,也有两种,一种是话题句,比如:他衣服洗得很干净。另一种就是“把”字句。那么什么样的“把”字句是句法上和篇章上强制性的呢?请看下面的“把”字句:
(19)他把红牯牵出沼泽,又站在那里朝沼泽看了很久。
(20)卜月像初次见面把一坨泥损到我左脸上一样,把一个巴掌掼到我右脸上,然后就嘤嘤嘤嘤像苍蝇一样哭。
(21)我把她的衣服掀到乳房上,……
(22)我正打榨,我像以往一样狠劲把撞杠推向垫木。
(23)瘦荆那条褐红色的牯牛把四条沾满红泥的腿插进河里,嘴在水中吸出一个优美的漩涡。
(24)她解开怀,把莽长满是涕泪的脸贴在自己的胸脯上。
(25)他随随便便扯过卜月的手臂,又扯过两条腿,把袖管裤管都掳得高高的。
在上面的句子中,由于动词后面已有其它成分(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成分主要是一些时间、处所结构和结果补语,比如动词后接“在、成、作、到、给”等构成的成分,还有一些程度补语(你把话说清楚,她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它们不可能与宾语同现于动词之后,因此在句法上宾语的提前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上下文篇章中,使用“把”字句是最为理想的。如例(19),虽然可以使用“红牯被他牵出沼泽”这种句式,但是这种句式破坏了作为话题链的主导性成分“他”对话题的控制,,破坏了一个完整的话题链中两个句子之间的衔接,所以不可能使用。最可取的就是用“把”字句。
再如例(24),“‘她”是话题性控制成分,如果我们把后面的句子改成一个被动句,单单这个句子,语法上似乎也能成立,但是在篇章连接上是很难接受的。例如:
(26)她解开怀,莽长满是涕泪的脸被她贴在自己的胸脯上。除非是说话人试图转移话题,重建话题链。所以,更为具体的说法是,句法强制性地要求宾语必须提前,而上下文语境又要求宾语不能居于句首,因此它只能处在主语之后,由于这些因素,必然造成对“把”字句的选择。
6 说话人的风格和爱好
当一个“把”字句的使用并不取决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任何情况,也就是说使用“把字句”并不出于句法、篇章、说话人的主观强调的要求,也就是说使用或不使用“把”字句是绝对自由的,这时候如果说话人使用了“把”字句,那么我们似乎只有假设这是由于说话人的个人风格和个人习惯了。比如下面的句子:
(27)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结果一抬手就把桌上的一瓶酒给打翻了。
(28)嗨!真把我气死了!
上面的句子似乎都可以不用把字句,而且并没有句法、篇章、个人主观情态方面的特别表现。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暂时解释为是由说话人的风格或习惯决定的。
7 小结
“把”字句的结构一共有三种:A把B—VR;A把B一V;A把B—DV/A把B—V—NM。动词必须能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或动量补语、或重叠、或与介词共现,这些动词都能进入“V得”框架,大多是“自主动词”,非自主动词一般不能进入“把”字句。“把”字结构仅仅提供了一种使用上的可能性。它本身并不是构成“把”字句的充分条件。
“把”字句的语义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表示两个述谓之间的因果为主的,具体内容是:由于A的关系(因),使得B发生了某种变化(果);第二类是:A作用于B时,A或B具有某种情状;第三类是:A对B施行了特定量的行为,“把”字句的语义重心并不一定在后面的补充成分上,也有可能落在动词前的成分上,因此说话人能够利用这一语义特征使宾语得到强调。到目前为止对“把”字句的语义解释还不是构成“把”字句的充分条件。
“把”字句在语境上有它自己的分布特征,通常情况下,“把”的宾语总是和前一个句子的宾语有同指关系,这种同指关系既有篇章衔接作用,又照顾了话题链的延续。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认为选择“把”字句的表达方式是由句法、语义、上下文篇章、语句重点和个人风格等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强制性到非强制性的等级关系。它们依次是:语义上的表达要求—→句法的强制性(必须配合篇章上的选择)—→篇章上的选择—→说话人的语义重心—→说话人的风格和爱好。我们可用下面的语言来表达这一意思:
首先一个说话人必须有要表达意思的要求,根据他要表达的意思选择适当的词语。然后是作句型选择,这时要考虑某一句型所具有的语法意义是否与自己想要表达的一致,如果不是,那么考虑所选用的词在排列句子的时候是否有句法上的强制要求,如果没有强制要求,那么考虑篇章上的衔接关系是否影响句子的排列顺序,如果没有任何要求,那么自己对某一成分是否有特别的关照,这种关照是否与某句型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决定是否选用某一句型。以上所有肯定或否定的选择中,所有的肯定回答都可能构成某一句型(比如本文讨论的“把”字句)的选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竟成先生为本文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注释:
〔1〕〔3〕薛先生的推论一“作为句子的主要话题,B任何时候不能省略”。句子的话题和能不能省略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可以拿“不能省略”来证明一个成分是不是话题。薛先生的推论二说“B无疑不是‘宾语提前’”,理由是下面的例子;把我笑得肚子都疼了 一瓶茅台酒把他喝得烂醉如泥可是我们认为,“笑”影响施及“我“(我被笑得肚子都疼了、这事儿笑得我肚子都疼了);“喝”影响施及“他”(一瓶茅台酒,他就被喝得烂醉如泥、这瓶酒喝得他烂醉如泥),理论上不影响它们作为受事宾语的身份。其实,在这里讨论这些成分的归类,已无多大必要。因为最后会涉及到理论上的假设(可以参考生成语法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假设),或者体系的问题。不同的前提假设之间不可比。薛先生的推论三“‘把’字句里的B不一定非得是定指的”。如果Tsao(1987)认为B必须是定指的,那么薛先生证明了B定指或不定指都可能,但是薛先生不能够用这一点来证明B的主题性质,因为定指或不定指已经与主题的性质没有关系了。
〔2〕至少我们认为在汉语的底层结构中,宾语的标准位置是在动词的后面。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下面的结构中如果有宾语,宾语要求提前:谓语动词后的补语是一个介词短语,如果要引进宾语,宾语必须提前。比如;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他放书在桌子上。谓语是“VR”结构,并且R为一个带“得”的补语,如果宾语不包含在补语之内形成主谓结构的小句(也就是“V得+S”),宾语必须提前。比如:把字写得很端正。*写字得很端正。“得”后的补语如果是一个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宾语要求提前。比如:把字写得端端正正。*写字得端端正正 ?写得字端端正正。可能补语的形容词如果是一个多音节的复杂形式,宾语要求提前。比如:那些字我看得不太清楚。*我看那些字得不太清楚。*我看得那些字不太清楚。
标签:语义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