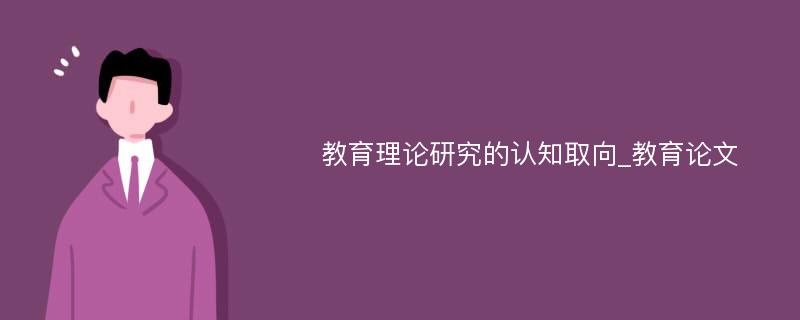
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定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我国的教育研究正在突破原有的认识框架,向着更深的层次演进。在这一方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学术界开始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几近实用主义的理论研究模式,转而在抽象层面上对教育理论体系本身进行多方位的反思,提出了包括“元教育理论”在内的新的研究取向。
笔者认为,在已有的各种理论探索和反思中,多半涉及到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作为教育的理论研究,其认识定位如何确立?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产生缘木求鱼之虞。
三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及认识定位特征
一、“经验-理论”模式及其对“教育实践(经验)”的认识定位
历史地看,对教育进行理论研究这一需要,首先来自于教育实践。于是,很自然地就产生了“经验-理论”这一古老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并且,直至当代仍有其影响力。
“经济-理论”这种建构模式其认识定位显然是教育经验的总结与概括。我们似乎不能忽视一个颇令人回味的“事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从古代到近代漫长的岁月中,著名的教育理论家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教育实践家(多半是学校校长);他们所阐述的教育思想直接来自于对自身教育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概括,并通过理性的感悟与整理,上升为教育的法则、原理、方法等。由此,我们似乎不难理解,留传至今的古典教育名著往往是叙述性的,指令性的,是经验概括的产物。
把教育理论研究定位于“教育实验(经验)”这种认识特征,将理论与实践直接地联系起来,旨在为教育实践寻找某个理想化的“操作样板”。由此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在价值观上倾向于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在方法论上满足于对优秀教育经验的描述、归纳、分类,再辅之以少许哲学思辨;在理论体系上表现为“大而杂”,教育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
客观地看,定位于“教育经验”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在教育研究史中有其特殊的贡献,尤其在早期的教育研究中更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教育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教育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1.提出了对教育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2.提出了教育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课题;3.作为优秀教育实践经验之归纳的早期教育理论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人们对教育现象的理解,并且为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与指导。也正因如此,这种教育理论能够满足来自教育实践的部分需要。英国教育学者卡尔(W.Carr)在考察了师范教育开设教育理论课程的起因之后写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师在某所示范学校中得到培训,这所学校由一位精通教学法的校长进行管理。到了19世纪末,由于小学的大批创办,人们感到师资培训的这种‘师傅带徒弟’方式再也不够了,有发展前途的教师在学习实际教学技能的同时,也掌握需要一些‘理论’知识。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在其1884年的论著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英国校长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理论;进而言之,大学在满足这一需要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随着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传播以及师范教育走进大学,各种‘教育理论’课程便大量开设”①。可见,由教育经验上升而成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活动还是有意义的,“经验-理论”建构模式也不失为教育理论研究的一种途径。
然而,这种建构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经验”定位特征具有“与生俱来”的弊端。具体也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定位于“经验”的理论建构往往局限于对教育现象的直观映照,并且缺乏对教育之整体的完整把握,从而导致对教育认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一缺陷在古代教育家那里尤为明显。
其次,由于在认识上向实践经验倾斜,对教育理论本身的系统构造缺乏足够的重视,被“归纳”的理论在诠释时往往采用非理性的形式,诸如直叙、比拟、类比、对答,甚或人为地设定一个“公理”,从而使理论所必须体现的理性力量缺失。
再次,“经验-理论”这种建构模式的实质是经验主义,奉行着“存在的即合理的”哲学信条,并且有意无意地走向理论虚无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采取让理论屈从于实践而不是让实践归约于理论这种态度,使理论成为实践的“奴俾”。这样一来,教育理论本身的“支离破碎”便势所难免。蒙台梭利在评论其祖母、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时指出:“她不是一个理论家,她没有构造一个不同的理论模式来为她以后的实际运用铺平道路。她在阐述已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常常从这些理论中借用一些术语,并将这些术语同它们原有的框架分离开来,运用到她自己的理论中。这就是对她思想的批评有许多误解的根源”②。这种理论建构而导致的“许多误解”决非只限于蒙台梭利一个人。
二、“心理理论-教育理论”模式及其对“心理规律”的认识定位
“经验-理论”建构模式虽然对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有一定作用,但这毕竟属于教育认识的“初级阶段”。随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化,随着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理论的建构模式开始转换,出现了“心理理论-教育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建构新模式。伴随着新模式的产生,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定位也由原先的“教育实践经验”转向“教育中的心理现象及规律”上来。
把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心理”上,这一认识新定位大致始于裴斯泰洛齐臻于赫尔巴特。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深深感到,“教学的原则,必须从人类心智发展的永恒不变的原始形式得来”③。基于这种感觉,他毕生都在寻找“永恒不变的”心智发展原始形式,也即寻找教学活动的“心理根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化”的主张。尽管裴斯泰洛齐所谓的“心理(学)理论”依然来自于他对自己教育实践的领悟和概括,因而依然是经验性的、“原始的”,但“教育心理化”这种主张反映了对教育理论“科学化”的要求,反映了对原有的以“经验”归纳为基本建构途径的教育理论的不满。诚如裴斯泰洛齐本人所呼吁的那样,“要把教育提到一种科学的高度,这一科学起源于并以对人类本性最深刻的了解为基础。”④到了赫尔巴特那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化”主张就进一步演变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命题:“教育者的首要科学,虽然不是全部科学,是心理学,人类活动的全部可能性的概要,均在心理学中从因到果的陈述了”⑤。在这样一个命题下,赫尔巴特构筑了他那个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其理论支柱(基础)是“统觉心理学”。赫尔巴特本人也因之被世人尊称为“教育科学之父”。从此以后,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定位,被强有力地根植于心理学理论的研究中,教育理论渐次地被演变为心理学理论或者沦为心理学理论的“附庸”。20世纪60年代,克龙巴赫(L.J.Cronbach)对当时教育理论研究状况作了如下评论,“绝大多数的教育理论属于心理学研究,虽则不是全部”⑥。这一评论可以解释下述“事实”:当代国际上著名的教育家首先是心理学家,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取得斐声成就后把自己的理论“移植”于教育之中,形成当代教育形形色色的新理论。
教育是人的活动,其基本形态是人际心理沟通和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认识定位于“心理现象及规律”的这种教育理论建构模式有其积极的作用,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验-理论”建构模式带来的直观性、非理性等缺陷,因而更具“科学”的意味。此外,心理学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人类心理活动基本规律,对教育实践的确具有不同程度的启示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了解教育活动的过程或机制。
但是,问题在于,“心理理论-教育理论”这种建构模式把心理学理论视为教育理论的基础,把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规定为心理学理论如何在教育情境中加以应用,从而在认识上出现误导。这种误导至少也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教育理论研究之对象的教育现象,其实质是要实现对个体后天发展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化干预,它不仅要依据心理规律,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根据社会的要求“塑造”一代新人,加速心智的发展。而心理学研究侧重于对已有心理现象“如实的”研究。因此,教育理论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指向,不能简单地构成“基础”和“应用”的关系。
其次,教育实践活动以具体的个体为对象,遵循着因材施教的原则,个性的充分发展是教育的理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复兴的“个别化教育运动”反映了人们对夸美纽斯以来那种班级“批量生产”的教育方式的不满。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职能是解释作为“类”的人的一般心理特点和规律,反映心理活动的共性,并且以大样本统计为主要研究手段。因此,两者之间难于构成共通的立足点,是一种典型的“非同构关系”。
再次,作为教育理论之研究对象的教育活动,是在现实条件下进行的,是动态的,并且包括着复杂的人际相互作用。心理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即便是心理学的自然实验,也极强调对诸条件(因子)的人为控制使其达到实验所规定的要求;更有甚者,心理学研究往往把人之心理“整体”人为地“分析”为诸部分,如记忆、思维、观察、气质、性格等,逐一加以研究,如此获得的“心理规律”之类的成果,也难免会“失真”。
三、“相关学科理论-教育理论”模式及其对“相关学科”的认识定位
大约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开始出现,即通过对相关学科有关理论的“嫁接”而形成教育的理论。
这种建构模式兴起的原因是整个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已步入交融汇合的新阶段,学科间的交叉组合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家开始重视教育,并把教育看成是其理论付诸应用的一个广阔领域;另一方面,教育理论因其自身贫乏无力亟待从相对发达的相关学科理论中寻找振兴的希望,陆续“引进”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学说和方法论。于是,教育理论迅捷地“繁荣”起来了,诸如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一大批新学科纷纷宣告诞生,教育理论研究也因之而“日新月异”。现在回过头来对它们进行反省和考察,不难看到,这种“相关学科理论-教育理论”的建构模式,其认识定位显而易见是摆在“相关学科”上,或者说,摆在“相关学科”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上。
定位于“相关学科”的这种认识特征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对当代教育理论的进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尤其是它对于活跃教育研究思路、繁荣教育理论、开拓教育认识新领域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这种认识特征客观上却有意无意地加剧了当代教育理论内在的深刻危机。
首先,任何相对独立的认识领域都有其相对严谨的“母体学科”,它具有自身的认识框架、理论基础以及概念、原理体系,分支学科应该是“母体学科”应用于特定方面而产生的、更为具体的学科。在形成分支学科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概念或方法,但决不能由相关学科“取而代之”。教育理论中的分支学科理论恰恰是如此:它们绝大部分是照搬相关学科已有的概念、原理、方法或学说,并且因此而沦为“相关学科”的理论在教育理论中的“应用”。例如,教育社会学这门分支学科就被定义为:“主要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教育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⑦。这不啻是教育理论的悲剧。
其次,“蓬勃发展”起来的当代众多教育分支学科,其创始人多半是相关学科的创始人或资深专家,他们在原有领域中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之后,把兴趣和注意力移向教育,这就势必导致用他们在原有相关学科研究中已娴熟的认识角度、研究方法、分析框架、概念或原理来审视教育,理解教育,规定教育。这样一来,演泽于相关学科的当代教育分支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原有相关学科的认识铭印,它们彼此之间缺乏一种统一的理论认识背景,缺乏一种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当代庞大的教育分支学科群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理论大杂烩。
对当前教育理论研究危机的一些思考
需要更加深入探讨的是,何以会产生上述不同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及认识定位?这就涉及到对“教育理论”之性质的认识。
从概念上来分析,“教育理论”显然是关于教育的理论,是人们对教育之理性认识的反映。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客观的“教育现象”和主观的“教育认识”。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具有功用性的实践活动。人们在从事教育工作时,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现象,引发了这样那样的探索与思考,于是就产生了对教育的主观理解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的认识来自于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研究的需要首先来自教育实践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合二为一。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主观指的是人的意识、精神,客观指的是人的意识以外的世界;主观世界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规律,客观世界也有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律。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⑧所以,经典作家格外推崇理论思维,反对单纯地描述事物的外部联系和特征的经验的方法。
把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人为地“合二为一”,忽视理性认识或者理论思维的特殊性,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证明”作用,让理论服从于(实践)经验,凡此种种,是教育理论发展史上极为明显的“误区”。这些“误区”以及由此而来的误导,使教育理论研究每每陷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
现代教育理论之鼻祖,一般公推夸美纽斯,因其写了一本《大教学论》,构筑了近代教育理论的基本认识框架和研究课题。但是,夸美纽斯的教育研究活动在导向上显然不是“理论”而是“经验”;不是教学“论”而是教学“术”。他非常明白地把“教学论(didactic)”定义为“教学的艺术”,而所谓“大教学论”就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⑨。那么,这种“艺术”来自何处呢?显然,来自实践,来自对实践的“观察”:“描绘艺术中的艺术(系指教育——引者注)是一件烦难的工作,是需要非凡的批判的;不独需要一个人的批评,而且需要许多人的批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眼光能够如此敏锐,能使任何问题的大部分不致漏脱他的观察”⑩。由此而来的种种“艺术”,加上“用先天的方法去证明这种种”(11),构成了夸美纽斯研究教育的基本范式。把教育研究完全导向实用的目的,强调这种研究成果的操作性和技术性,势必会把教育理论的认识功能完全依附于教育实践的操作功能,从而在价值观上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合二为一。笔者还注意到,百年之后,另一位教育理论秦斗赫尔巴特在致力于教育理论“科学化”的时候,令人费解地选择了“Pédagogik”作为其传世之作《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édagogik)的书名。德文Pédagogik一词源于拉丁文pédagogy(意为“教学法”、“教育法”),后者又是由拉丁文Pédagogue(意为“教仆”)演变而来。毋庸置疑,选择Pédagogik一词多少也反映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研究价值观。
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进行理性认识的产物,它不仅不是对教育现象的直观映照,而且也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认识规律。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价值观上加以明确的区分,这是教育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敏锐的教育理论家开始摒弃“功用性”的思路,直入理性层次对“教育理论”本身进行反思。
20世纪40年代初期,哈迪(C.D.Hardie)曾从分析哲学角度对当时的教育理论状况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存在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学说,教育理论的现状很难令人满意”。他进而呼吁:“在教育理论领域内普遍采用同样的态度,现在是时候了”(12)。当然,当时哈迪主要是针对教育理论中概念、术语、命题混乱不堪这一状况而提出规范教育理论本身这一主张的。其后,英国学者奥康纳(D.J.O'Conner)也开始对同一状况发难,指出“关于教育的理论经常是各种不同陈述的极其复杂混合体”(13),并且从教育理论本身原本应该具有的逻辑系统着手批判了当时的教育理论状况,“如果我们读一本教育理论或者教育思想史的教科书,我们能看到所提出的三种很不相同的作为教育实践基础的陈述。所谓不相同的陈述,意思是说,它们属于不同的逻辑系统,因此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加以证明”(14)。奥康纳所谓的三种“不同的逻辑系统”系指,形而上学逻辑系统、价值判断逻辑系统和教育经验逻辑系统。
暂且不论奥康纳的说法是否正确,在现有的教育理论体系中,逻辑层次不明、逻辑关系紊乱,已成为一个通病。教育理论中,大至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小至班主任工作、教师备课,无所不包,巨细无遗;内容的重复,概念的交叉,原理的模棱两可,屡见不鲜;教育理论所阐述的诸课题之间缺乏逻辑的联系,这典型地反映为教育学教材诸章节之间的“跳跃性”;倘若借用奥康纳的三种“逻辑系统”划分法,那么,不难看到,现有教育理论大量存在的逻辑系统是“价值判断”和“教育经验”。因此,教育理论总是存在着大量“指令性描述”,教喻人们如何如何去做。
教育理论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理论价值误导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关于教育理论之属性的认识错位上。如同夸美纽斯所坦言的那样,教育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要“证明”凭籍“观察”加“批判”(分析)的方式形成的“教育艺术”。这种价值导向很自然地把教育理论引向实用性、功效性,要求教育理论的研究直接服从教育实践的需要。
笔者并非反对教育理论应该服务于教育实践,应该满足教育实践的需要。但是,这种服务和满足不是直接的、具体的、对应的。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理论,有其自身的建构规律和严谨体系,是理性认识的产物;作为基础理论的教育理论,不应以实用性或功效性为特征。在自然科学中,教学理论、物理学理论都是如此。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实用性、功效性倾向,使得教育理论的基础研究严重缺失,至今尚未筑构起有机的、逻辑的理论体系,从而使教育理论原本应有的理性张力疲软,最终难于满足教育实践的需要。这种情况典型地反映在“心理理论-教育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教育理论”这两种理论建构模式中:当原有的教育理论难于解释、甚或难于理解教育现象和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要诉诸其他更成熟的理论了。
上述两种教育理论建构模式的出现,客观上繁荣了教育理论研究,并且为教育理论研究注入了不同程度的理性生机。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出现又潜在地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理论研究内在的认识危机。不仅没有纠正对教育理论性质的认识错位,反而把教育理论研究看成是其他学科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把教育理论看成是“应用理论”。奥康纳在对教育理论进行反思之后,居然认为:“‘理论’一词在教育方面的使用一般是一个尊称。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15)。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在西方绝非个别。恩特威斯尔(N.Entwistle)在其主编的《教育观念与实践手册》一书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番考察,指出:“在整个60年代,由于教育理论越来越依赖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母体’学科,故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理论维系于教育自身以外领域中的‘一些基础学科’。因此,在这一时期直言不讳的并且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教育理论规定为‘实用性原理’,这些原理正确与否完全是由‘基础’学科提供的知识来决定的”(16)。
这种把教育理论看成是“应用理论”的认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并且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了教育理论自身概念体系的混杂,自身原理体系的凌乱,而且还导致了教育理论“虚无主义”的倾向,使原本乏力的教育理论更趋疲软,教育理论的建构更趋模糊,最终使得教育理论更难满足教育实践的需要。例如,“心理学理论是教育学的基础”这一观点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几近“金科玉律”。然而,前法国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弗朗茜思·贝丝特认真地分析了“教育学”一词词义演变的情况之后指出:把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合理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对这门科学的错误利用,因为,它将教育的目标与受教育者的知识以及掌握教育手段的熟练过程混为一谈,结果出现了那个牛头不对马嘴的、概念模糊的词‘心理教育学’。由于这种观念的出现,‘教育学’一词便发生了一次演化:它变成了它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的一门科学(即心理学)的‘实际的’或者说是‘应用的’形态”(17)。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教育理论观对教育理论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把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的抽象模式附加于教育之上并据此来研究教育的主要后果就是:它表明这种做法业已放弃改善教育的任何努力,因为除非有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去改变社会或整个世界,否则(教育)什么事情也别去做”;“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它导致人们错误地认识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例如“倘若从‘多学科’角度视教育为诸学科的交叉点或所有社会科学的归结,那么,作为一种过程或一个社会子系统的教育也就融汇于众多的认识论理论之中了”(18)。
教育理论成为其他学科理论的附庸或“具体应用”、教育匮乏自己的基础理论,这一现象近年来也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陈桂生分析过“我国教育学是否被其他学科占领”这一现象,他认为已经出现了诸如“仿佛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其研究对象同‘教育’沾得上边,它就有资格成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之类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之下,我国教育学“甚少论及”下列问题:“(1)教育学为什么要以别的学科为理论基础,它能不能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2)什么叫做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它对于教育学意味着什么?它是教育学的‘指导思想’还是教育学的‘材料库’?(3)教育学是不是需要对与其相关的学科作出选择?(4)根据什么标准对相关学科作出选择?教育学怎样做到以必要的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而又不致成为别的学科的领地?”(19)看来,对这些问题,当代教育理论需要作出回答。但与此同时,更需要对“教育理论”本身应该是什么作出回答。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教育学者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各种有益的探索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由概念体系和原理体系有机地组成的,教育理论也然。有鉴于此,早在1958年,古德兰德(J.J.Goodlad)就呼吁构筑教育理论自身的概念体系,对教育概念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他写道:“所谓概念体系,是指一个精心构造的框架,它发挥着下述功能:鉴别在制定任何教学计划时都必须给予回答的重要问题;揭示把这些问题集聚在某个体系中的一些可区分的基本原理以及把这些问题彼此离析开来的基本原理;鉴别从属性问题并适当地对它们加以分类,以显示它们与主要问题的关系;揭示在回答现有体系所提出的问题时要加以利用的资料源(datasources);揭示从这些资料源中抽象出来的资料的正确性”(20)。显然,古德兰德的认识已触及到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在当时西方教育理论界泛滥着实证主义精神的情势下,这种认识是震聋发聩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斯坦纳(E.Steiner)的美国教育学者在这个方面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努力。她认为,以往的教育研究中,片面地一味只强调“归纳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是十分不足取的,正是诸如此类的方法论导致了教育理论的困境。在1964年举行的美国教育哲学第20届年会上,她猛烈地抨击了当时教育理论的研究状况及其内在弊端,呼吁教育理论研究必须采用诸如“反证(retroduction)”、“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等多种方法来建立教育理论的各种模式。进而,她在会议上提出一个新词“educology(教育理论学)”,并且宣称应致力于形成一门具有严谨逻辑体系的抽象的“educology”(21)。斯坦纳的这一观点在西方教育理论界旋即产生强烈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初,克里斯坦森(J.E.Christensen)把学术界的有关讨论与争鸣进行汇编,出版了《关于作为教育理论学的教育学的各种观点》(22)。越来越多的学者乐意使用“educology”这一新术语而不是“education”(教育学)来指称有关教育的知识、概念和理论(23)。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教育理论研究已出现一个新的契机和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开始摆脱单纯地在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寻找种种(现象的或本质的)联系的思维定势,转而对教育理论体系本身的系统建构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行各种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教育理论的建构思路
教育理论研究一直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的左右,把教育理论体系自身的构造及发育摆在一个次要的、甚或无关紧要的位子上,这是导致当代教育理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当代教育理论如欲摆脱困境,必须有新的认识思路,也即:按照理论构造与发育的内在规律来重新研究教育理论体系本身。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
一、超脱教育理论研究的功用性倾向,注重教育理论的自身建设,强化教育理论对整个教育研究的“母体”价值
在教育研究的历史中,从一开始,研究者的认识似乎就被某种切近功利的浮噪所牵制。诸如孔子、柏拉图这样的大教育家,都迫不及待地试图为当时的教育提供一种“蓝图”以供世人付诸实施,迫不及待地希翼借助这种“蓝图”来实现“国泰民安”。为此,他们对教育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给予了过分的关注,对教育的实际操作给予了过分的思考。如此而形成的教育理论中,思维与经验、抽象与具体、逻辑与教条、理论与实践,似乎都难分泾渭。教育理论成为一个无所不包、巨细无遗的“万花筒”。
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相对于“实践”而言的,它们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所谓“统一”,不仅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根植于实践的土壤、产生于实践的需要,而且是因为理论最终要服务于实践并由实践作为检验理论之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所谓“对立”,则是因为理论一经形成,往往独立于实践,在很多情况下甚或对立于某些具体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对立关系,所以,理论才发挥出指导、调控实践活动的重要功能。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失之辨证。
那么,为什么理论与实践之间会产生“对立”关系呢?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4)。因此,马克思在批评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时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25)显然,科学理论的使命在于通过对现象的审思而把握现象所间接反映的(有时是扭曲反映的)内在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客观规律,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象的阐述或总括。由于理论不是对现象、对实践的直观映照或归纳,不是一种感性认识的产物,所以,理论的形成需要超脱感官世界的抽象思维或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在本质上是对事物内在联系的理解与把握。恩格斯指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6)运用理论思维形成的科学理论,由于它能反映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使人们的认识超脱于实践、并因此而能够高瞻远瞩于实践,从而实现对实践的指导功能。更重要的是,“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象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27)。这便是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认识论原理。由于这种对立的客观存在,“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8)。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精譬论述,是我们研究教育理论、建构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
当代教育理论研究必须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实用主义认识倾向,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重视教育理论发育的内在规律,加强教育理论体系的自身建设,使教育理论成为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母体”学科而获得存在的价值。
二、强化教育理论本身的“理性力”,注重教育概念体系和教育原理体系的严谨构造,真正实现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使命。
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理性。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借助理论思维而揭示的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科学概念(体系)和原理(体系)深刻反映出来;而所谓的理论体系在形式上就是概念、原理的体系。在这里,科学概念的形成已成为衡量一门学科的理性力、衡量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
教育理论体系中的概念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英国教育学者诺亚(H.J.Noah)认为,“对一门科学的发展程度的一项检验是其术语的获得。在发展‘术语’时,我们经常借鉴日常用词,然后出于技术上的目的更精确地下定义。人们会立即想到速度(velocity)这个术语在物理学上的用法,它具有方向这一基本涵义,从而与‘速度’(speed)这个没有方向性的概念显著不同;或者,在经济学中我们力图把‘需求’(demand)定义为‘支付的能力与希望’,而不是简单的记住其‘需要’(need)或‘愿望’(desire)的普通涵义”。他进而认为应该“为‘比较教育’一词重新下定义”,应该“很快地从该词的日常涵义转到更为技术性的涵义”上来,并预料“对这一术语的涵义应是什么会有相当热烈的争论”(29)。西方教育界曾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一场关于“教育理论”或“教育科学”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对以“实在性”和“确定性”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教育理论给予猛烈抨击,反对公开标榜科学无须探求事物本质、惟以“描述事实”为已任的“实证主义”教育研究模式。此后,一些学者把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对西方教育研究的各种批评意见归纳为三条:“(1)对教育的大量经验性的研究如按这类研究的基本要求来看,是无效的……。(2)在此类研究中一个特有的且普遍的败绩是理性的欠缺。……(3)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事业的性质本身并不适宜于目前普遍从事的这种经验研究。……控制所有相关变量的奢望是徒劳无益的”(30)。这三条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西方当代教育理论危机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1983年8月于长春召开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代表几乎一致地认为,教育学尚未建立起科学的范畴体系与逻辑体系,概念比较混乱,从而成为妨碍教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1)。此后,有关的讨论与争鸣就不时见诸报刊,虽则未成气候。
就我国教育理论的现状而言,仍然很不尽如人意。所谓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五个方面所组成,其内容基本上停留在对上述五种教育现象(侧面)的归纳水准上,难以深刻地刻划教育过程的本质以及这一过程中诸要素的内在联系。上述诸“育”实际上是教育的不同形态,它们既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又反映了教育的实际运作,因此是诸目的和诸(直观)过程的综合体。教育诸目的和诸过程必然地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导致这些联系的原因是它们必然存在着的某些共同要素,这是教育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在这一方面,已有的教育理论中几乎成为空白。由于这一现状,教育理论不仅以描述教育现象为基本特征,而且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关系模糊不清(32)甚或错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教材是国内颇有影响的教材,在教材体系和理论创新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但是,这本教材体系在逻辑上难以称好。例如,该教材从第6章至第13章集中“分析了教育目的的各个组成部分”,即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其后用4章的篇幅专论“教学工作”。根据编者的意图,教学“是培养人材、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显然,这两部分构成了目的一过程关系。但是,编者在论述诸“育”(目的)时,又分别论述了各自的内容、过程、意义(任务)。于是,在逻辑上就出现了问题。试以“德育”为例。作为一种教育形态,编者详尽地论述了德育的意义、内容、过程、原则、方法、组织形式等,那么,这一完整系统与“教学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完整系统(子系统)与其他诸“育”(子系统)是什么关系?具体地说,“德育过程”与“教学过程”是什么关系?与诸如“德育过程”、“体育过程”等又是什么关系?进而言之,德育一章中论述的“德育过程”与“教学工作”一章中的“教学过程”是否构成如编者所构想的那种“目的—过程”关系?如果不是,那么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教育过程”是“教学过程”的具体化(抽象上升为具体)关系,还是德育现象归纳为教学原理的关系?凡此种种,似乎都难以找到答案(33)。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逻辑困惑,是因为我们尚未能从根本上把握教育的内在要素,并从要素间的辨证关系去理解教育诸形态、诸现象。
除此之外,教育理论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随意偷换、概念界定的非规范性也非罕见。就以“教育”概念为例,任何一本教材都要区别“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种,并规定教育学主要研究“狭义的教育”,因此是在这一界定基础上使用“教育”概念。但在具体表述时,“教育”概念往往被偷换。例如,德育有两条公认的原则: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影响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原则。但在这两条原则中“教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一致的。从学科概念规范化角度来看,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教育理论研究进展未臻“理性认识”阶段。
三、强化教育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解释与预测两大功能,真正实现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调控与指导作用
自从福禄倍尔首次提出“教育科学”这一概念(34)、赫尔巴特尝试建立“教育科学”体系以来,教育界对教育理论科学化的意识及愿望与日俱增,并投入了极为广泛而持续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风靡全球的实证主义科学思潮之左右,多少给人一种“南辕北辙”的印象。当代教育理论的贫乏与落后,与这一事实有极大的关系。
实证主义反对任何抽象的思辨,也反对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及联系。它认为科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实在性与确定性,科学的任务仅仅只是描述事实、经验、现象之间的联系,一旦这些联系描述清楚了,规律也就自然产生了。所以,实证主义只要求解决“是什么”问题,不去解决“为什么”问题。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主要是归纳,而非演泽。归纳法对人类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并且仍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的要害在于“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35),从而必然地导致认识上的局限性。长期以来,西方教育理论研究对实证主义,推崇备至几近顶礼膜拜。早在20世纪之初,美国著名教育学者桑代克(E.L.Thorndike)就曾宣称:“在今天,对教育理论持严谨态度的学者之主要任务,就是形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并掌握统计学的逻辑”(36)。这种观点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共鸣,并因此对西方教育理论研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研究史”条目的编写者认真地分析了从1900年至1980年间世界教育研究的基本进展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像医学一样,教育也是一门艺术。这便是为什么有关研究的进展并不能产生一门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教育科学只能为实践和政策形成越来越有力的科学基础。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只能说:从1900年到1980年间,教育研究已搜集了叹为观止的知识,其中包括有价值的观察资料和结论”(37)。法国教育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研究承袭了实证主义科学观并且往往以简单化思想为特点,长期以来为实证主义作出牺牲的主要是教育学(38)。
以实证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教育理论研究的最大缺陷,是无法运用抽象的演泽能力来建构有关教育的科学理论假设,从而使教育理论难于发挥其原本应该具有的对教育现象或实践的解释功能和预测(指导)功能。假设的形成、修正,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发展形式,“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39)。由于假说的存在,理论才对实践产生调控和导向,使实践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回答“理论要求是否能够成为实践要求”这一问题时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0)。理论反映现实、现实趋同理论,这是对任何科学理论因此也是对教育理论之科学性加以衡度的两个基本准绳。教育理论要赶超其它学科理论的发展水平,教育理论要完成科学化的使命,必须重视理论本身对实践所具有的解释与预测这两大功能。就当前教育研究的认识定位而言,教育理论对实践的预测功能之实现,显得尤为迫切。
在我国,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并且,解决这类问题的迫切性同样存在。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传统模式是对教育现状或优秀教育经验的归纳总结,其成果主要反映为对教育活动的指令性规范,并且体现为“处方式”的描述框架。教育理论匮乏合理的假设,其认识定位主要是告诉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揭示“为什么这样做”的因果关系,凡是可观察到的或感受到的教育现象、教育活动都可归纳成“理论”,并被纳入到教育学体系的某个方面中去。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大至“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小至“辅导、答疑”怎么进行,全纳于一个体系之中。事实上,我国教育理论界把教育研究方法片面地限定在几种具有明显归纳属性的方法上(41),极大地忽视了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演绎方法,这是导致这一“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cf.N.Entwistle,(ed.),Handbook of Educational IdeasandPractices,1990,p.101.
②蒙台梭利:《人的发展的教育》。转引自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页。
③裴斯泰洛齐:《葛多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转引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80页。
④转引自伊丽莎白·劳伦斯著、纪晓林译:《现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⑤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转引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66页。
⑥I.J.Cronbach,Educational Psychology,1962(2nd ed.),p.143.
⑦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⑨⑩(11)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页。
(12)哈迪:《教育理论中的真理与谬误》。转引自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页。
(13)奥康纳:《教育哲学引论》。转引自崔相录主编:《中外教育名著评价》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7页。
(14)奥康纳:《教育哲学引论》。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35页。
(15)奥康纳:《教育哲学引论》。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第440~441页。
(16)N.Entwistle(ed.),Handbook of Educational Ideas andPractices,p.103.
(17)弗朗茜思·贝丝特著、赵光新译:《“教育学”一词的演变》,《教育展望》(中文版),1988年第18期。
(18)cf.C.E.Olivera,Comparative Education:What kind of k-nowledge? In Jürgen Schriewer and Brian Holmes(ed.),Theories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1990.
(19)陈桂生:《略论教育学成为“别的学科领地”的现象》,《教育研究》1994年第7期。
(20)John J.Goodlad Toward a cenceptual system for curri-culum.In School Review,Vol.6,1958.
(21)见范国睿:《当代西方关于教育学理论性质问题的研究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1期。
(22)cf.James E.Christensen(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
(23)例如,阿根廷教育学者奥利韦拉(C.E.Olivera)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愿意用educology一词。cf.Jürgen Schriewer and Brian Holmes(ed.),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Education,1990.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页。
(2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26)《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2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页。
(2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29)见诺亚:《比较教育界说:概念》。赵中建、顾建民选编:《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30)R.Barrow,et al,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EducationalConcepts,pp.194~195.
(31)见徐毅鹏:《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讨论综述》,《教育研究》1983年第11期。
(32)教育学教材的章目之间匮乏严谨的逻辑推演关系,章与章之间难能看到逻辑意义上的前后呼应,就是一例。
(33)见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4)cf.J.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3.,1981,p.339.
(3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1页。
(36)E.L.Thorndike,Educational Psychology,1903,p.104.
(37)T.Husen,et al.(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Vol.3,1985,p.1597.
(38)参见加斯东·米亚拉雷等主编、张人杰等译:《世界教育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3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40)《〈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41)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就把“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地规定为“观察法”、“实验法”和“调查法”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