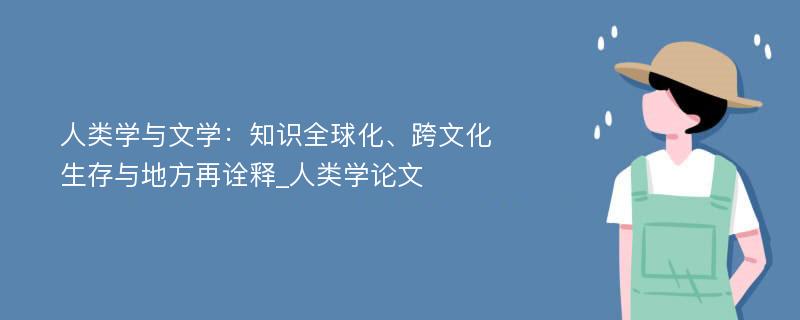
人类学与文学——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本土论文,跨文化论文,知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是入学。这是文学家高尔基的名言。
“人类学是人的科学。”(注:A.L.Kroeber,Anthropology,New York Harcourt,Braceand Company,1923,p.1.)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1章第1节写下的第一句话。
人学与人的科学,用字虽有繁简之别,但从常识判断,大致可以看成同义词。将这两个理论命题放在一起,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人的学问之间,在其对象上有怎样的相关性,在内容范围上有哪些重合点,在视角和方法上又会有怎样的外在与内在联系?二者的联系是如何开始的,又将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
如何系统地梳理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之间产生的互动、交叉和理论创新的主要线索(注:关于人类学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联,参看拙作《论20世纪文学与人类学的同构与互动》,《东方丛刊》2001年第2辑。),描述在这个重叠的边缘地带所滋生的新的理论与视角的变化轨迹,回顾文学人类学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的进展与成绩,展望它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与重构中的发展前景,是尝试文学人类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必要条件,期望能够对“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背景资料,为拓展我们的人文视野和重塑我们的文化身份与学科身份提供某种参照。
一、人类意识的形成与人类学的诞生
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同知识全球化的进程是息息相关和互为表里的。
没有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航行和全球贸易,世界一体化的实现就没有可能。建立在世界一体化基础上的知识更新和观念变革,直接催生出了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以及把世界各地的人视为同类的“人类”意识。人类学只有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意识和人类意识形成之后才得以诞生。“大发现”不仅是地理的大发现,而且也是人类的大发现(注:参看G.Geana,Discovering the Whole of Humankind,in Fieldwork and Footnotes,ed.byH.EVerme ulen Routledge,1995,pp.60-72.)。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人类学在整个人类知识发展中显得相当滞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作为新兴学科加入到晚生的社会科学的门类中来。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理性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在于发展出了“自我意识”。他还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古希腊文明时,人类才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人类意识的产生在世界史和思想史上之所以如此滞后,甚至还要大大晚于生物学、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各个社会集团过去始终无法超越“自我中心”的认识局限,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文化看成是属人的或高等人的,而将一切文化他者视为非人的或低等人的。人类在文化观念上的这种偏见和盲点居然伴随着所谓理性和自我意识延续了二千多年,乃至体现在黑格尔这样近代以来最渊博的知识体系构建者身上。他在《历史哲学》中把他所从属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描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代表时,他在贬低东方人不知道自由、不懂得自我意识时,显然仍深陷在传统的种族主义偏见中不能自拔。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在20世纪中期仍然坚信日尔曼种族优越论,并以此为理由对他们所认为的低等人类如犹太人等实行灭绝政策,这就充分说明了新建立的“人类”意识还是多么的不普及和多么的脆弱,而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又是多么的顽固和难以改变。
人类学者陈其南指出,人类的族群差别虽然有其生物性的基础,例如白种、黄种和黑人等一般性的分法,但是其连续性仍然十分清楚,有些族群实际上不能根据生物特质断然划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中国人在较早的时期对所谓“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往往主观地认为只有汉文化才算是人,否则便是“夷狄”。因此,我们往往在异族的名称上加了犬、虫、羊等偏旁。一百年前,我们还会用“英狤猁”称呼英国人呢!这是文化差异的生物化。异民族一旦被视为异类或“非人”,任何非人性的行为便可能发生。这些异类马上变成了可杀可吃的对象,如一般野兽。人类的弱肉强食便是由此产生。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滥杀无辜土著。为了使屠杀合理化,不惜捏造事实,把澳洲土人说成是动物不是人,把他们描绘成奇形怪状,似人似兽的样子(注:陈其南:《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把异族人看成非人的这种普遍现象,人类学家麦克杜格尔博士(Mcdougall)在1898年就有个说法:“任何动物,其群体冲动,只有通过和自己相类似的动物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满意足。类似性越大,就越感到满意。……因此,任何人在与最相似的人类相处时,更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本能作用,并且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那些人类举止相似,对相同事物有相同的情反应。”(注: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从这种解说来看,党同伐异似乎是人得自生物遗传的一种天性。由这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出发,人类种族之间自发地产生彼此敌视和歧视的态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人们在接受相似性的同时必然会排拒相异性。于是,丑化、兽化、妖魔化异族之人的现象自古屡见不鲜(注:参看W.D.O'Aahrty,Other Peoples'Myths,New York:Macmillan,1988;Clilstav Jahoda,Images of Savages:dncient Rootsof Modern Prejudice in Western Culture,London:Loufiedge,1999;拙作《山海经与文化他者的神话》,《海南大学学报》1998年2期。)。人类学家报告说,从某些未开化民族的古代文献和绘画艺术中,可以找到种族歧视的许多实例。在法国山洞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粗糙画像,就已显出这种倾向。
现在,人类经历了种族之间的无数次拼杀,在牺性了无数同类之后,总算开始认识到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原来都是具有同样本质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因而是可以和平相处,平等互补的。由于有了这种人类意识,人对自己同类的任何歧视、残忍和侵害行为,都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被看作是人性之中的兽性遗留的表现。人类学这样一门以整个人类为对象的学科,只有在上述的知识全球化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立和发展,而这门当初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少有些联系的新兴学科,在其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终于成为反对新老种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成为批判和解构殖民主义、西方文化霸权的学术先锋。
二、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进程
人类学是知识全球化进程的伴生物,反过来,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也积极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个边缘地区提供前所未有的“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广泛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客观的结果便是对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世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
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返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正如个体儿童认知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消解自我中心的过程,各民族文化也只有在摆脱了“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和情感定势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民和异族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
这样一种摆脱了自我中心定式的文化观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使研究者以相对中性的态度面对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出身于人类学专业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理论家的布尔迪厄,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在我看来,在社会科学中错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科学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即没有控制好科学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导致了人们将与对象发生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上。当我读社会学家写的一些作品时令我感到痛苦的是,那些其职业就是要使社会世界对象化的人,最后被证明他们很少能使他们自己对象化,他们很少能认识到他们那些形似实非的科学话语所谈论的东西其实不是对象本身,而是他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从布氏措词中这两个“很少能”的关系可以看出,研究者偏离客观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本位立场和社会偏见对自己眼光的限制。鉴于此,布尔迪厄提出,一种真正的反观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中心主义”(episte mo centrism)、“科学家的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of scientist)。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换言之,研究者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优越感犹如一副有色镜,使他无法洞见对象的本色。人类学消解传统的文化偏见的功绩,首先在于为跨文化认识的公正性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
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文史哲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注:参看C.Mukerji,M.Schudson,ed,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in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mnia Press,1991,Introduction,pp.1-61.)。
第四,人类学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知识体系内部划分的一种危机和重新整合的需要。人类学的核心术语“文化”,正是这种知识重新整合的有效概念工具。美国人类学家拉尔斐·比尔斯指出:“在众多有关人的学科中,人类学的特殊作用在于它是唯一汇集全面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全面的方法即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全部范型来研究人或人类群体。这样,人类学家面对诸如生态、社会关系、经济或艺术等特别领域与人本身和人类行为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人类学中,全面论的基本主张是:人类行为产生于文化系统中复杂的相互作用。”(注:拉尔斐·比尔斯等:《文化人类学》,骆继光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正是“文化”概念的这种全面论和整合论的特征,使它在20世纪的后期越出了单一学科的界限,催生出更加具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和反学科的研究新潮流——“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必须揭露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构成学科划分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揭露在大学的院系中支配着教学与研究的体制性因素,也就是揭露学院派的历史传承和现实运作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文化这一概念的超学科性正好给这场学科批判和反思运动带来一件有效的思想工具。“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质问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在不许在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注: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见《文化研究读本》,罗钢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由这种激进的打破原有学科划分的批判要求,我们不难看出晚生的学科人类学所给予的积极影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早在20世纪初叶就预示过,人类学应当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
斯蒂芬·努贞特(Stephen Nugent)在谈到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张力来源于它们的综合性的雄心的相似性。“人类学,由于它以他者的世界和他者的生活为导向,由于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他们的田野作业获得对材料的特殊把握方式,在突破官方的学科界限方面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庞杂无序的责难:一名人类学家可以做出一篇论文,涵盖亲属关系、政治、经济、动物饲养、医疗实践、宇宙观和认识论,不用说还有实用植物志、文身和幼儿抚养等方面。”(注:S.Nugent,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Pluto Press,1997,p.3.)人类学把人重新定义为“文化动物”,并且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它使一切与人相关的知识可以在文化这个整合的视野上获得重新的理解和建构,由此而带来的超学科研究的潮流成为20世纪后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变化,这种超学科的倾向甚至反过来也给当代人类学的课题设计带来新变化,如对后殖民问题,大众文化的重视,以及从女性主义过渡到性别研究,等等(注:G.E.Marcus,The Unbalanced Reciprocity between Cultur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T.Milled,A Compartion 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Blackwell,2001,p.178。笔者主持的“文学人类学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02)亦有意拓展文学的性别研究和少数话语等被昔日主流学术所压抑和忽略的方面。)。
三、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
跨国公司与世界性大市场格局的建立,资源与劳动力的全球共享,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些都在促使人类加速迈进所谓“地球村时代”。与这一进程相应,知识全球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成为精神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创新与发展的一种契机。史蒂芬·罗的《再看西方》一书中写道:“技术进步、能力增强和危险把我们带入了新的相互依存之中。为了在这种依存中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技术的奴仆生活,我们必须成为地球本身的世界公民。我们无法在太空中获得全球性。我们只有同时是来自某地的,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的。”(注:史蒂芬·罗:《再看西方》,林泽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这里自然出现了本土观点与全球观点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种种争议的问题。
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在经济生产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同质化最为明确;而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方面,文化的世界化并没有导致完全的同质化。虽然形成了大规模的理论旅行和文学艺术思潮流派的跨文化传播,但是民族特殊性的表达仍受到普遍的重视。在思想领域,同质化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全球性或人类性问题的形成共识。比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权问题、保护环境和生态伦理问题的提出等。
然而,在各个文化传统中孵化出的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概念,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之中难免要遭遇消解、调适与重构的命运。如詹姆斯·哈密尔所说,“与其认为知识的内容是事实,不如说是人们的各种思考方式”。多参照系的出现给本土视角的单一性、相对性提供了对照和反思的契机。千百年来既定的思考方式所建构的知识、所信奉的真理,也就不得不面对和异文化的思考方式进行对话的新现实,不得不在形成中的全球化语境中重新检验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存在的依据。因此,知识全球化自然会给本土学者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后发型的追逐现代化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是被历史牵着走的被动角色。西方作为一种“异文化”,从原来的敌对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榜样和未来文化发展的自我前景。这一现实给本土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失落感和错位感也是激发出文化身份焦虑的原因。
克服文化认同危机的常见心理反应模式不外乎:要么就是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地方本位的立场,自觉地和以外来异文化为代表的世界文化相认同;要么就是坚守国族本位的传统立场,并坚信本土文化的价值必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发扬光大,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本土主义的价值取向为人文学者提供的最常见的理论预设是:本族或本国的文化优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这样一种不经证明就当成公理的理论预设的作用下,倾向性结论早在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了。研究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成了按照既成的思路搜罗和排比相关资料,通过各种分论点的发挥,使我族优越的总结论由潜到显,获得又一次的具体说明。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人们对于这种本土立场的论证方式早巳司空见惯。观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可略知该派人士立论之心态。再往上溯,早在17世纪围绕传教士和西学问题的争议中,即可窥见此种自卫心态之表现。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对抗西方文化挑战、消解其影响压力的自卫策略,就是在本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文化要素相对应之处,进而以“古已有之”的逻辑将外来文化因素追根溯源到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去。这其实也是再阐释的一种极端表现。
杰缅季叶夫指出:民族情感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和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宗教信仰,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民族情感所具有的补偿作用和心理自卫特性越强,民族情感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就越鲜明(注:杰缅季叶夫:《论民族冲突心理》,张广翔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5期。)。当民族情感的道德要求高于一切时,跨文化认知的价值就会向本土一方倾斜。然而,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不以个人或个别民族的意志为转移。全球化的进程使那些传统深厚、历史悠久而又相对闭锁的文化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和思想、观念、情感的转型。在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从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transnational)、跨文化的(cfoss-cultural)和全球的视界去考察本土事物的观点。这种立场、角度、思路的转换必然会给旧的对象带来新的可能性,并因此促成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
作为推进知识全球化、倡导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人类学,在如何面对异文化,解决人文学者的身份危机方面,已作出具有先导性的有效示范。人类学在文化认知方面最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文化他者之生活的方法(注:Norman K.Denzin InterpretiveEthnography: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21stCentury,SagePublications,1997.H.F.Vermeulened.,Fieldworkand Footnotes,London:Roufilge,:1995.)。这种他者眼光对本文化有反观之效,有助于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与局限,从而消解我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主义的束缚,获得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使得理性关照下的再阐释成为可能。
人类学把再阐释当作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措辞。克鲁伯喜欢用“重构”(reorganization)一词;赫茨科维兹则叫“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后来的学者还有叫“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的,如胡适,也有叫“创造性转化”的,如林毓生。对“再阐释”过程的解说,在赫茨科维兹的《文化动力》书中有这样一段:“再阐释标志着文化变迁的所有方面。它是把原有的旧意义赋予到新的因素上,或是新的价值改变了旧形式的文化意义发生过程。”(注:M.Herskovits,Cultural Dynamics,NewYork:AlfredA.Knopf,1964,P.191.)我们把新旧两方换成外来的和本土的两方,也可以说,再阐释就意味着文化他者的视野在本土文化中的应用,或是赋予本土文化以新的资源价值。
不论哪一种情况,本土学者若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再阐释,那就要求再阐释者拥有超乎自身文化之外的眼光。这种眼光不可能象我们的视觉一样来自生物遗传,只能靠后天的培育。培育的最基本条件是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从一个地方社会的公民到一个地球村的公民。换言之,跨文化的身份或身份的全球化,乃是视野和知识的全球化之条件。关于跨文化身份的构成,人类学者大卫·托马斯《跨文化空间与跨文化生存》一书,以外来的西方人与安达曼岛原住民的最初接触与互动为素材,提供了非常精辟的人类学专题论述。他提出“跨文化生存”(transcultural beings,或译“跨文化的人”)(注:D.Tomas,Transcultural Spaceand Transcultural Beings,Westvies Press,1996,pp.97-99.)的新概念,说明不同文化的碰撞如何改造和重塑着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产生出与单一文化生存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方式。
从跨文化生存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在认识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人类学者通过到异文化中去做田野作业的方式,进行转换身份的训练;而我们本土学者要想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转换身份,建立跨文化的视野,确实有相当难度。但是没有这个“出得来”的前提条件,要想对自己的文化有“陌生化”的观察眼光是几乎不可能的。
越是传统深厚、历史久远的社会和文化,其成员就越难使自己获得超脱出来的眼光。这主要是千百年来早已形成惯性的自我中心式的感知和思维习惯,以及自古就受到社会鼓励的党同伐异心态。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世人树立了超越本土主义的人类观和全球观的可行范式。从黑格尔、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终于跳出本族本国文化限制的思想家,是如何拥有了俯视世界、洞观全局历史的宏阔视野的。
在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出现之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已有不少学者明确提出超越本土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要求(注:美国人类学者威廉·亚当斯便从人类学产生以前的哲学思想中探寻这门学科的根源,参看他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一书第2章“进步主义”。WY Adams,The Philosophical Rootsof Anthropology,Stanford:CSLIPublications,1998,p.75.)。德国人黑格尔在法国军队侵入德国之际,带着未完稿的《精神现象学》手稿逃出家,却依然在书中称法国的入侵是“一次光辉的日出”,因为它代表的是“世界精神”的历史行程。用今日的眼光看,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可以理解为先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前全球意识”。马克思在评价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时,表现出同样一种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高瞻远瞩的历史主义原则。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世界历史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对应人类学古典进化论派所构想的世界演进模式。马克思晚年如此关注当时的人类学的进展,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可知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工作,他对全球化世界观的渴望和解放人类的理念,已经使他先于时代而成为世界公民。马克思的全球意识得之于他在身份认同上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期不只是重复歌德的话,而是他在文化身份上与“世界公民”认同的必然结果。
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推崇的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尽管他的原始社会和婚姻家庭进化模式如今已经被主流人类学所放弃,但是从文化认同的转化方面看,他仍不失为超越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局限的先驱者。他身为白人律师,却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印第安人争取合法权益而打官司。作为人类学者,他不只转换了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而且在情感上也和印第安人相认同,乃至被印第安部落收为养子。这些先驱者的事迹为所有试图走出民族主义和本位文化束缚的后人树立了榜样。在他们那里,身份的全球化是先于知识全球化的。
标签:人类学论文; 跨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