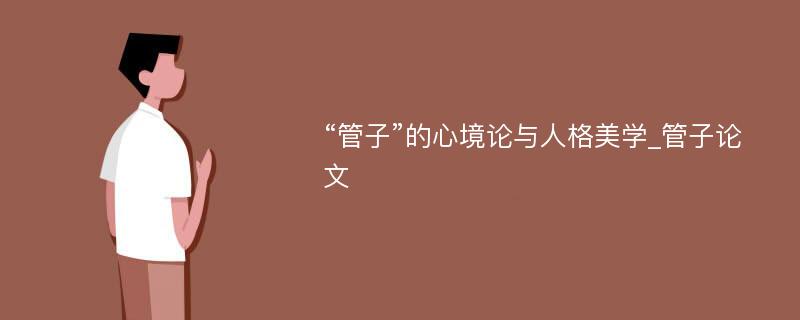
《管子》四篇的心气论与人格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气论文,美学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3)06-0021-05
从《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的篇名即可看出,《管子》四篇①主旨指涉的是一种内心之学,即如何让经验性的个我修养提升为一种超越性的宇宙之我。这种内心之学隐含的一个前提是现实经验中的个我人格是不完善或者是与道偏离的,而经过内心的修养则能复归或扩充为一种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所以,《管子》四篇本质上归属于一种内圣之学、德性修养之学。正因如此,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管子》四篇并没有得到重视②。而事实上,由于《管子》四篇的修心之学与“精气”概念相互绾合,故其修心和养气是同时发生的心理历程,这就使得其内圣之学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心性层面而同时又进入了可感的人格美学层面。所以,《管子》四篇“内静外敬”理想人格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存养扩充”审美人格的生成过程。因此,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管子》四篇应当得到更合理的考量。
一、从修心层面看理想人格的形成
要揭橥《管子》四篇的人格美学,必须首先明了其心性层面理想人格的生成机制,然后厘定出这一理想人格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被转换成一种审美人格的问题。
众所周知,《管子》对老子学说发展的一个主要体现在于将老子“玄而又玄”的形上之道以气为中介具象化落实到人心之上[1]51。《心术下》云:“气者,身之充也。”《内业》云:“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从《管子》四篇“道”“气”对举的文字叙述中不难看出,对《管子》而言,道化生万物和气流动生物是同一回事。在老子那里,无处不在的道化生万物并成为万物的本原。对《管子》而言,弥漫宇宙的精气则“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内业》)。这就是说,万物包括人都是秉承了精气的聚集方始成为万物,成为人。失之必乱,得之必治,精气实是万物生命的本质性存在。“心为精舍”,就人而言,《管子》四篇则认为,精气停驻在人之心中成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管子》把能停驻本质性精气的容受之心看作是一种藏于深处、先于经验言辞、空明灵觉的本源之心,称之为“心中之心”、“彼心之心”。《内业》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言。”陈鼓应据此认为,所谓的“心以藏心”,是在官能之心中还蕴藏着一颗更具根源性的“本心”[1]113。
虽然精气能停驻在心,但因其具有“一往一来,莫知能思”(《内业》)的神妙莫测之用,故心舍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到精气的聚散。所以,虽就本源性的生命来说,精气与本心并无隔膜,合为一体,成就一种与道相合的“心气”之生命原初形态。但就经验形态的生命而言,心舍和精气处于一种极为微妙的关联之中。稍有不慎,精灵之气就可能随之逃逸丧失。这表明了心灵的修持与精气的聚集处于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正向关系中。
所以,如果人的生命能沿着原初形态进而扩展,则其精气自然而然地能在“彼心之心”的本然性上“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内业》),成就一种与道合一的生命境界。但如果人的生命沿着对原初形态损害的方向发展,精气则会逃逸丧失,人则失性。然而,人生在世,这种原初形态的生命必然受到经验的干扰。在这种经验的干扰中,具有思维和欲望性能的心更是首当其冲。在外物的侵扰下,人心因智和欲的无度而丧失了其虚而无藏的本然状态。一方面,人心因主观成见的思虑巧智(“有设”)而陷入了认识的迷途。故《内业》篇云:“凡心之形,过知失生。”另一方面,人心还因物欲的无度而陷入“物乱官,官乱心”的泥潭。故《内业》篇云:“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这就是说,经验人格因人心对外物的偏执、对忧乐喜怒欲利情感的无度,导致了本心的流放与遮蔽,进而导致了心与精气的隔阂。心与精气的隔阂同时使得精气无法得以固守,从而导致了人之本质的丧失。
《管子》四篇正是从经验现实人格入手而展开其内心之学的论述。依前所述,人之本质的丧失在于过知和嗜欲对人之本心的遮蔽和流放。相应的,人格修养的工夫当在知和欲两方面入手,以期恢复或“反济”本心虚而无藏的本来面目。
针对心知过盛,《管子》四篇提出以内静之“虚”“静”“一”来排除主观的成见,以洁净心之尘垢。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心术上》)
虚者,无藏也,故去知则奚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心术上》)
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内业》)
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内业》)
“虚”即要让人在与外物交接时去除主观成见,不怀机心,不藏预设,不刻意图虑,如此则能保持心之本然面貌而以无损无益的“静因之道”无心应物;“静”则是让人保持安静,以求心意不乱;“一”则是要让心意专一,以凝神抟气。“虚”“一”“静”的修心之道是对老子虚静思想的继承,并在字面上影响到了荀子的“虚壹而静”观念③。
针对嗜欲充溢,《管子》四篇提出以外敬之“节”来调控欲望,所谓“节欲之道,万物不害”(《内业》)。与老子的去欲不同,《管子》四篇并不试图去除所有文明化的欲望,而是倡导对欲望进行有效的节制,使之“不过其情”。《内业》篇云:“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胸。”耳目之欲的节制,则能使得九窍合序而不至于让感官扰乱心灵的平正。同时,儒道融合的《管子》四篇对诗、乐、礼的态度也和老庄的排斥态度不同,而是主张通过诗、乐、礼的文明教化来正身节欲。《内业》云:“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管子》四篇吸收了儒家关于诗、乐、礼调和人的情志以及端正形体的文化功能,并认为这些外在教化同样有利于安心抑欲,让人复归本性。当然,相比外敬而言,《管子》四篇更强调内静对于修心的根源性之用。
当然,上述分析的去知和节欲的过程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条修养路径,相反,二者是修心时同时发生效应的。去除过知的干扰,自然就能节制欲望;同样,节制了欲望,心也能归于虚静。通过这种内静外敬、修心正形的修养工夫,经验之心带来的尘垢被打扫干净遂复归为平正和谐之本心;这样,实然、经验人格随转化为一种应然、理想人格。
经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管子》四篇关于理想人格的生成借助的是意识层面心灵的超越智慧来实现对“过知”和“嗜欲”的自我心理调适。如果这种自我心理调适就此完成,那这种理想人格的生成过程应该只限于是一种道德心性层面的理想人格而与美学无涉。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管子》四篇中有着心灵修持与精气聚集的正向关系,故其意识层面修心历程的每个环节都有着感性层面气的参与。由于本心与精气的本源相合性,故其本心被彰显的过程也是精气被涵养的过程。这就是说,在《管子》四篇那里,意识层面的修心之时即是感性层面的精气达至之时。这样,正是在修心养气相互牵扯的层面上,其理想人格的形成昭示的也是审美人格的形成。
二、从养气层面看审美人格的形成
由于本心和精气的原初统一性,修心层面对经验之心的洁净、对本心的复归,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精气在心舍的停驻聚集与涵养扩充。《管子》四篇对修心与养气的同一性历程有着大量论述:
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内业》)
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内业》)
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心术上》)
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心术上》)
可以看出,以上引文都采用了“如果……则精气……”同一充分条件句式。这种句式明确传达了如下信息:修心之时就是精气来至和涵养之时。这说明,本心复归的历程就是精气驻守与涵养的历程。精气在人体的涵养抟集,导致的是一种气化流行之可感性主体的呈现。这样,人的身体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精神和纯粹的生理器官的结合物而是由气整合的一种有机生命体。可以说,这种感性主体已经初具审美人格样态。
气化的感性主体还只是审美人格样态的雏形,其完全转化为一种审美化主体还有待于精气的扩充弥漫。《内业》篇云:“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这句话说明了本心具有一种使得精气自我充盈,自我生长完成的本性。随着精气在人心的停驻,精气可以随着修为的进展而不断存养扩充,自我弥漫。精气的存养扩充开始以心舍为中心辐射于全身,伸张到身体的各个角落。《管子》以形象的“源泉”为喻来说明了精气是如何由心舍向身体进行渗透弥漫的。《内业》云:“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精气在心就如同一口连绵不断的清澈源泉,只要一心维护,它就永不枯竭,它不断流淌,不断滋润灌溉着生命的每个毛孔促使生命茁壮成长。精气由心舍向身体的弥漫,导致了身体的气化流行,使得整个身心都处于一种可感的生命状态。同时,这种生命状态还能“诚于中,形于外”(《大学》)、“形于中,发于色”(《成之闻之》)、“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管子》四篇写道:
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内业》)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内业》)
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于形容,见于肤色。(《内业》)
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集于颜色,知于肌肤。(《白心》)
李存山先生说:“气是细微(不是指一般的细微,而是其细无内,至精无形)、纯粹、神妙之气,并且,它进入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人的精神。”[2]耳目、四肢、皮肤、筋骨、颜色等等都是一种外在的身体性存在,在精气的渗透之下,它们不再是一团简单的血肉,而是皆焕发出一种生命精神。这就表明,在精气的英华发外下,人的身体由一种生理性的存在而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并把人不可见的内在的精神人格彰显出来。这样,内在不可见的抽象精神因精气的弥漫就和生理性身体相互结合转化为一种可观赏的精神气质人格。于此,《管子》四篇中的理想人格遂完全转化为一种审美人格。所以,《心术下》篇云:“充不美则心不得。”这句话就明确点明了修心养气所臻于的一种“充美”之态。
审美人格不但可以让人感知、欣赏,而且还能突破个人人格的有限性而实现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在《管子》四篇看来,人格修为的最高境界应是让精气弥漫到人的整个身心,即达成一种“全心”的圣人境地。《内业》篇云:“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谓之圣人”。“全心”是说整个生命状态因去除了经验之心而呈现为一种“彼心之心”之全。从气的角度而言,“全心”则是整个生命包括形体都处于一种精气灌注的最完美境地,故“心全”也意味着“形全”。在此,心、形、气已化为一体,都朗现为精气之流行。杨儒宾先生就此精辟地指出:“‘全心’的意义,据管子说,乃是‘彼心之心’逐渐扩充渗透,渗透到经验意义的心也完全化为精气之流行,两层心复合为一,此时即叫‘全心’。”[3]这种心全形全之境是人格之美的最高形态,是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道合一的超越性生命境界。全心之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内业》),成就一种顶天立地、与道感通一体的生命精神。《心术上》亦云:“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这种通体皆气的生命状态作为一种“独”、“明”“神”的澄明透彻之境,理所当然也是一种审美超越之境,与《庄子》里的“朝彻”、“见独”等澄明之境相互呼应。
《管子》四篇的这种人格美学思想和《孟子·尽心下》所言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极为相近。孟子一度曾为齐稷下先生,则其与稷下道家之家有着相互影响之关系。《盐铁论·论儒篇》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孟子以志气的充盈来定义“美”,而以这种志气在身体上的“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的“生色说”来定义“大”,并以通体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来描述“大丈夫”人格。同时,孟子也以“圣”和“神”来说明人格的形而上超越境界[4]。可以说,《管子》四篇气的思想和孟子气的思想之间应该有一种影响关系④。
三、审美人格与心物感通
《管子》四篇审美人格的生成还可以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强调《管子》四篇心物的认识论关系。心物认识论关系注重的是外在之实和概念之名是否相称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获得客观性的知识而非人生的智慧。但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发现,至少在《管子》四篇中其对理想人格的定位主要集中在人生境界的问题。当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问题而非自然问题为其主旨时,很难让人相信其蕴含着丰富的心物认识论问题。特别是,当《管子》四篇以审美人格为其理想人格状态时,其心物认识论关系则更令人质疑。《管子》四篇中对经验之心的去蔽,虽然也有着更好地去认识外在名实关系之目的,但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对本心的复归以达至对道的体认。所以,当主体呈现为一种精气充盈的审美状态时,其与外物的关联主要体现的就应是一种与物感通的审美关系而非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关系。试看《内业》篇下面的论述:
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如上的文字往往被人用来说明《管子》四篇之“重智”说,并以此来区别稷下道家与老庄对智的不同态度。陈鼓应说:“‘思索生知’意指知识是由思索而来的。所谓‘知’指的是客观性的知识,这和《庄子》书中的‘知’有着不同的含义,《庄子》中所谓的‘知’大多是指主体性的智慧,两者有着极其不同的走向。”[1]122但是细究下来,不难发现,《内业》篇中对“智”、“思”的描述实际上并不归属于关于客观性知识的认识论,其体现的依然是一种主体性智慧。白奚先生就曾在其著作《稷下学研究》中提到:“《管子》四篇的精气论主要讨论精气同人的生命特别是精神现象的关系,探讨如何才能获得精气而有智慧,特别是如何才能在保有精气的基础上使之不断积聚而成为有大智慧的圣人。”[5]
上述引文所说的“德成智出”、“知乃止矣”、“遍知天下”、“鬼神将通之”都是讲的一种心之体验、感通乃至妙悟功能,而并没有逻辑思维的迹象蕴含其中。如果说以上引文中的“知”或“智”是一种客观性的认识论,那何必要谈“德成智出”呢?因为德的引入对于客观性知识的获得并不起保证作用反而有可能会给知识的获得带来主观性的效益。如果这种“知”是一种客观的认识论,所谓的“鬼神将通之”则只会令人认为这种认识论具有的是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同样,如果单纯地从心物认识论关系入手,引文中所说的“遍知天下”无非表明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诳语。因为就客观认识而言,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万物毕得”、“穷于四极”、“万物备存”的认识目的的。其实《心术上》篇中对这种知有着明确的表白:“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及虚之者,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客观的认识论是一种“智”,一种外“求”,为知识义。而圣人之知则是一种“所以智”、一种内“虚”,为智慧义。
所以,虽然《管子》四篇中包含着认识论色彩的形名理论,但其所言的心物关系不能被侧重理解为一种心物认识论关系。可以说,《管子》四篇中的心物关系依然继承的是老子“涤除玄鉴”的心物直觉论。其心物关系是一种“神明之极,照知万物”(《内业》)的“鉴照”关系,是一种心“昭知天下”、物“翼然自来”的玄感妙悟关系。“照”是一种精气流行的妙用,它意味着排除一切物欲和心智的干扰而实现对物的本质(道)的观看,最终达至与物玄同的精神境地。“鉴照”关系意味着心如明镜一般照耀周遭,正因其能做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知与故”(《心术上》),故万象能在心中全然显现。宗白华先生就曾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6]正是在这种心如明镜的“鉴照”关系下,作为有机整体的人才能与物感通,才能以“静因之道”与物相偶,“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内业》)。在此过程中,审美人格生命以一种整全之气去体贴、妙悟而非认识世界,而世界的美丑亦能在这种审美状态中不受主体偏好而自在呈现。这正如《白心》篇所揭示的:“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也正是在这种心物感通之中,个人生命能维持住“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内业》)的不为外物所役的自由精神;同时,在这种心物感通中,个我的主体精气能与道之精气相互契合,因而在达成天人合一的美妙化境之时,把个我超越进宇宙我,获得生命存在的回归与寄托。《管子》具有审美性的心物玄同关系和老庄哲学一起对中国艺术精神有着深远影响。清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中就说:“悬缣楮于壁上,神会之,默思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峰峦旋转,云影飞动,斯天机到也。”[7]
可见,《管子》四篇经由修心养气最终达成的一种人格状态是具有审美特性的。这种审美人格以通体皆气的生命光辉之态去感通着通体皆气的宇宙万物,最终复归道境,实现着人格的审美超越。
收稿日期:2013-09-13
注释:
①本文所引《管子》四篇文字均以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为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在比较流行的几本《中国美学史》著作中,《管子》美学思想研究多不被重视。相比而言,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比较早地关注到了《管子》四篇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上的地位。不过,叶朗先生侧重探讨精气和虚、一、静等范畴及其美学影响的问题,而对《管子》四篇文本中的美学思想并未深入展开。而在为数不多的《管子》美学研究论文中,多侧重于其虚静说及其对文艺创作心理的影响问题。
③学界普遍认为荀子的“虚壹而静”概念与《管子》四篇的“虚”、“一”、“静”有相互影响的关系。笔者有专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荀子的“虚壹而静”论与包含《管子》四篇在内的道家虚静说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要说二者有影响,可能更多只是字面上的影响,但二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见拙文:《刘勰“虚静”说理论来源再辨》,《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
④目前关于《管子》四篇和孟子思想孰先孰后问题尚有争论,故在养气说上也存在到底是孟子的养气说影响了《管子》四篇的养气说(李存山)还是《管子》四篇的养气说影响了孟子的养气说(白奚)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