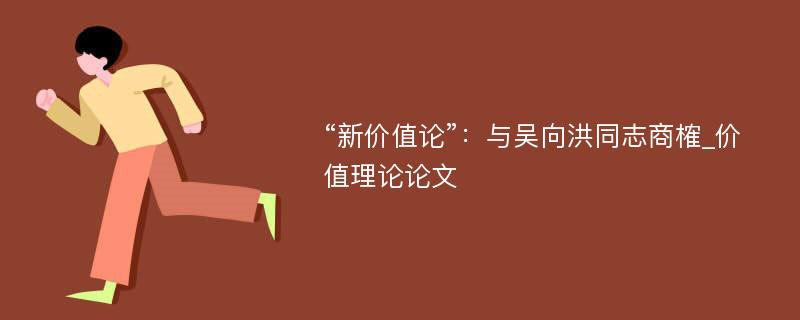
“新的价值理论”:插翅难飞——与吴向红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插翅难飞论文,同志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吴向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拜读了吴向红同志《劳动价值论:包袱还是翅膀》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以下简称吴文)之后,我们感到, 完全有必要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吴向红同志进行商榷。
吴文的基本见解是:由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与社会道德意义并不明显”,加之“它在解释实际现象时存在困难”,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用新的价值理论取代原有理论,从而更科学地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吴文的标题和结尾也在强烈地暗示:应该甩掉劳动价值论这个“包袱”,插上“新的价值理论”这个“翅膀”,飞向所谓“科学的共产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新的价值理论”呢?它宣称,“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价值学说——它们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如边际效用价值论、一般均衡论等等,在解释、控制客观经济现象方面,比劳动价值论有效得多,‘科学’得多。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采用这些经济学说,服务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目的呢?”显然,吴文所谓“新的价值理论”指的就是西方现成的种种庸俗的价值理论;而它所谓的“发展”也就是要用它们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如此“发展”“马克思原有理论”也算“天才”的话,那么早在吴文发表之前,这样的“天才”就已经数不胜数了。其实要论这种“天才”,恐怕至今仍无人能出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之右。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所谓“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这一客观事实恐怕却是吴文的作者所“没有注意到的吧”。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文献杂志》1971年6 月号所载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一文(注:参阅《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105~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中认为, 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价格可以直接由技术的生产函数导出,因而价值向价格的转化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步骤。他在该文中写道:“第一卷的新奇分析,即对‘平均剩余价值率’和‘价值’的计算,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是毫无结果的混乱。”他认为,马克思不是想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剥削吗?其实如果马克思“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斯拉法时代,那么,即使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他也可以简单地假设低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再一次不需要相等的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的帮助。”(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下册,32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应当指出,在论证“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方面,吴文的手法显然要比萨缪尔森拙劣得多。吴文既没有“低工资和高利润”的假设,也没有什么“生产函数”,更谈不上采用让萨缪尔森本人都洋洋得意的所谓“擦抹和替换法”了。吴文除了片面地强调“劳动对于人类类本质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只要“在最高层次上坚持了这一点,就完全能够坚持住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结论”之外,就是高喊“革命”口号:“只要资本家仍然没有与劳动过程真正地结合起来,那么他从最终分配的交换价值中,哪怕是只拿走一分钱,也是可耻的,也是剥削。”吴文似乎在竭力暗示,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只是“在最高层次上”才是罪恶的,因而它所提出的“彻底的批判”也只不过是大骂资产阶级“丧失了人性”而已。殊不知,这种口号式的非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只会授人以柄,使我们的批判变成了“五十步笑百步”。这里且不说就像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一样,资产阶级完全也可以炮制出另一套人性标准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单就吴文所“坚持”的标准而言,资本家们就可以反唇相讥说:从“最高层次”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没有把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呀!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怀疑,吴文的真正用意究竟是要“坚持住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呢,还是想把马克思主义推至万劫不复之境地?试想,如果仅仅依靠抽象的“人性”批判就想要资产阶级回心转意,参加劳动的话,那也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演变了。
其实,萨缪尔森在这方面就要高明得多。他是通过混淆“价值”和“价格”,进而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差别来达到歪曲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之目的的。他说:“‘解释’剥削,哪一种公式更好些?是‘价值’还是‘价格’呢?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的回答是‘价格’,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下册,13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饶是如此, 他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仍然暴露出,它实质上完全撇开了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的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赖以生存的剥削的本质。他的“剥削”概念实际上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剥削,而充其量也只是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关于剥削来自流通过程或来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论调之翻版而已;更遑论吴文所谓抽象人性意义上的“剥削”了。
其实,如果吴文的错误仅止于此的话,想必还不至于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论证“劳动价值论今天已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包袱”,吴文认为,劳动价值论“今天正面临着很大困难,它难以解释、更难以指导驾驭(?——引者)许多经济现象”。
应当承认,劳动价值论正面临着一些挑战;而且很显然,在这一轮讨论中这种表面上的困难是指所谓第三产业(非物质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但是,任何关注这次讨论的人都知道,这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注:可参阅吴易风:《第三产业劳动和高科技是否创造价值》,载《人民日报》,1996—04—20,第6版。)。让人惊异的是,吴文不仅没有正确地面对这种困难和挑战,反而把它们不断地进行夸大,乃至最终把劳动价值论当成了“一个包袱”,必欲先甩掉而后快。显然,这种观念的形成自有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源,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发生动摇,才会导致在经济问题上思路的混乱。这一点在吴文中有着或隐或现的反映,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至于吴文对劳动价值论本身的理解,更是耐人寻味的。吴文甚至连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都没有区分清楚就宣称,劳动价值论“论证的是‘劳动创造交换价值’”!吴文认为,由于“劳动创造交换价值”“隐含着承认了‘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所以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难免要“大打折扣”;同时,“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中根本不适用‘交换价值’这个概念”,所以它“对构建共产主义理想的意义也并不是很大”。殊不知,这些论述只能暴露出吴文根本不了解交换价值的相对独立性,不懂得首先由马克思批判地证明了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不理解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更谈不上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铁的逻辑所作出的结论了。
吴文还自以为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的“辫子”,紧紧抓住“生产资料”不放,宣称“马克思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一个疏忽”,亦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唯有消费资料才进入交换”。在这里,吴文的论证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段论表述出来:
大前提: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消费资料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小前提:只有个人的财产才能进入交换。
结论:“唯有消费资料才进入交换”。
这一论证过程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吴文不仅毫无觉察,反而还由此进一步推论说,社会主义货币总量“会大大超出可交换的总交换价值(消费资料的总交换价值)”;最后竟引申出的确有些“令人吃惊的”所谓“定律”:“亦即,如果劳动价值论成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就无法实现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在这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吴文错误的根源正在于陷入了把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分解为收入的斯密教条而不自觉。或者说,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生产费用价值论。这一点在后文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吴文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但资本和资源公有,连劳动也并不为劳动者私人占有,交换价值的概念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生产要素创造任何交换价值。”这一段话说白了就是一点: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创造进而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其实,从声称马克思的“疏忽”到引申出“令人吃惊的定律”,反映出吴文既没有掌握马克思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原理,也不懂得斯密教条的实质。因此,吴文不仅不能证明劳动价值论已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包袱,反而只能更加有力地表明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证明劳动价值论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再看吴文用来取代劳动价值论的“翅膀”,所谓“新的价值理论”,即“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价值学说”,究竟能不能像吴文所期待的那样,飞向科学共产主义呢?
首先,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谬误是极其明显的。其一,它以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为依据,以人的主观心理作用说明价值,这就把价值看作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看作是永恒的自然范畴而非历史的经济范畴;看作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主观心理因素与客观物品效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仅比之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还要庸俗,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衡量价值大小之可能。其二,它本身在许多问题上因为缺乏科学根据而陷入困境。例如,它认为商品的价值还取决于其稀缺性,可是稀缺与否又总是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的;再如,在生产资料价值如何决定的问题上,它往往无法自圆其说;又如,它与现实生活也背道而驰:不同的人对同一商品、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对同一商品都可能有不同的主观评价;而且,由于交换发生在作出主观评价之前,所以,它又无法解释新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总之,它所寻求的无非是要给使用价值概念一种数量的表示,并用这种表示来解释价值范畴及关系——这实质上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之前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上的那种混淆。其三,至于它引以自豪的两大规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所谓“每元的边际效用相等的规律”,对于前者,就连萨缪尔森都似乎缺乏信心,他无奈地说:“当较早的经济学者得知:声音、光线和其他感觉似乎呈现类似的韦伯——费克纳边际影响递减规律时,这就使得人们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具有甚至更大的信心。”(注:[美]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经济学》, 中文版,677~679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对于由戈森第二定律即享乐均等定律导出的后者,就连比较现实一些的经济学家如汉斯·迈耶等都没有忽略其不现实性。(注:参阅马克·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下册,113~11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其实,马歇尔式的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变为价格语言”的努力其结果必然把它与“需求向下倾斜规律”等同起来,而事实上,后者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而在于购买力的下降(注:参阅马克·林德:《反萨缪尔森论》下册,113~11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其次,生产费用价值论也是错误的。从理论根源上看,生产费用论无疑渊源于斯密教条,而斯密教条本身就存在以下错误:其一,它混淆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它把价值分配上从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到必须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变化看成了价值决定上由劳动决定价值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变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二,它混淆了商品价值和由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所谓三种收入,只是商品中由工人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即V+M,而不是价值的全部即C+V+M。因此,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说法, 显然把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部分C丢掉了。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 就是因为斯密还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也就看不到工人的劳动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又转移了旧价值。其三,它把价值看作由收入决定,可收入本身也是价值,因而也就势必陷入价值由价值决定的循环论证之中。其四,它又必然发展为庸俗的生产费用论。
至于生产费用论本身,马克思指出:“把费用价格(即生产费用——引者)和价值等同起来,——这种混同,在亚当·斯密著作中,尤其是在李嘉图著作中和他们的实际分析相矛盾的,而马尔萨斯却把它奉为规律。因此,这是沉湎于竞争,只看到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的市侩所特有的价值观。费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呢?由预付资本的量加利润决定。……预付资本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呢?马尔萨斯说,是由预付资本中包含的劳动的价值决定的。劳动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呢?是由花费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商品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呢?由劳动的价值加利润。这样,我们只好不断地在循环论证里兜圈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Ⅲ),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再次,以供求论为基础的均衡价格论也是不值一驳的。它玩弄的无非是把价格和价值混为一谈的老把戏,因而也就必然导致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论证。须知,所谓供求关系,实际上就是指二者的价值关系;而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是通过由它引起的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来发生影响的。从需求来看,“‘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从供给来看,由生产者提供的商品也是由分配到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具有价值的商品。因此,“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指供求二者的价值关系——引者)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事实上,供求变动只能说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根本不能说明价值本身。恰恰相反,由于价值关系是供求变动的基础,所以只有在解决价值问题之后,供求关系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仿佛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你们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着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绝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抵销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它们就互相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注: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131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
可见,无论是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还是供求论、均衡价格论,“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价值学说”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抽掉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抽掉生产关系,混同价值与价格,来肆意歪曲和诽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推翻资产阶级最仇视、最害怕的剩余价值理论,推翻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全部结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与自然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样,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即见到各种制度下生产的共性就忘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个性,正是那些企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所在。
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绝不可能有所谓“科学的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有剩余价值论,才能第一次真正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正是由于有了剩余价值论,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性即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并存,才能揭示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马克思的论证是如此之严密乃至于连资产阶级学者如庞巴维克等都不能不承认其“铁的逻辑”。换言之,在价值问题上只要稍有偏差便会导致严重的混乱乃至灾难性后果。这一点就连约翰·穆勒都认为:“在产业体系完全以买卖为基础,每个人多半不是依靠他自己参加生产的物品,而是依靠通过出售之后继以购买的双重交换而获得的物品生活的社会状态下,价值问题却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即使是极小的,也会使我们的其他一切结论产生相应的错误;我们的价值概念中存在任何含糊不清之处,都会使其他一切概念产生混乱和含糊。”(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文版,上卷,4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用经济学语言来说,经济理论的价值论“弹性”是如此之大乃至于在价值问题上容不得有丝毫偏差;然则,吴文的偏差绝对不是“极小的”:它先是觉得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包袱”,接着竟直接了当地要用所谓“新的价值理论”取而代之!
标签:价值理论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萨缪尔森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吴文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