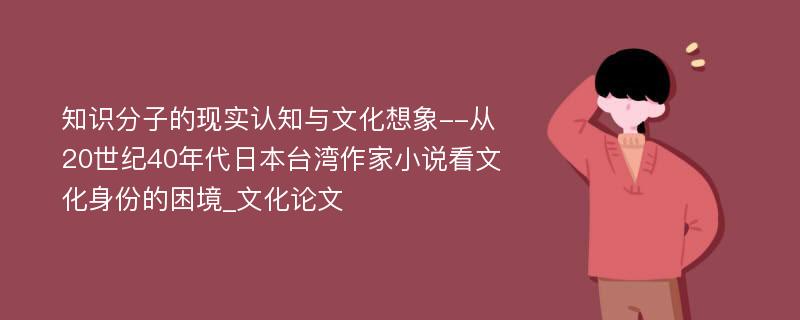
知识者的现实认知与文化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台湾作家的日文小说看其文化认同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日文论文,台湾论文,认知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构建“地方性知识”: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文化统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天皇嗓音沙哑的讲话声中,居住在 台湾一个名叫八斗村小地方的普通人家,正在黑暗中忙着为一个痛苦呻吟的女人接生。 只见大哥林文雄拿着三根香柱,在祖宗的牌位前虔诚地点燃,微微鞠躬、祈祷。基隆市 整个晚上都停了电,烛光中人影幢幢。很快地,女人壮烈产下一子,突然电来了,屋里 大放光明。婴儿嘹亮的哭声盖过了沙哑和杂音的广播。
这是侯孝贤1989年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里的第一个长镜头。
镜头语言是多义的,它不仅有台湾光复后获得新生的隐喻,更有意味的是其中政治性 与民俗性或文化性虽然混杂,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互不相干的指涉:日本天皇宣告投降这 么意义重大的事件,在镜头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镜头里并没有人们想像的一群人 如何凝神谛听收音机的重大新闻的画面,而是突出汉民族特有的民俗:敬祖的传统和对 于传宗接代这种仪式性的尊崇。显然电影给观众传递的,正是这种汉人最熟悉不过的民 俗所暗含的重大的伦理意义,在它面前,即使像天皇宣布投降这样突发性的“重大新闻 ”,这种可能会改变所有“殖民地”人们的命运的消息,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论是有 意还是无意,侯孝贤的这个镜头所包涵的意味,不仅是“美学”的,而且也是“民俗” 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这种“民俗”、“文化”和“政治”之间,还存在 着不易察觉的矛盾、纠葛和某种疏离的关系。整部《悲情城市》中,侯孝贤借助不同人 物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包括闽南语、日语、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国语(普通话) 等,把观众带入了一个有着复杂社会、文化背景的台湾,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带着不太相 同的文化记忆,这些不同的文化记忆共同构建着台湾复杂的文化身份和历史。《悲情城 市》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然而却很成功地通过这些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记 忆,把观众带入战前和战后的环境当中,展示出这些不同的文化记忆、历史记忆所激发 的冲突。让观众看到,不论是在日本殖民地体制下,还是在战后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新 的体制下,每种政治性权力和行为(包括战时利用国家暴力强制执行的“皇民化运动” 和战后的“二二八”事变)所面对的抵抗或者疏离,不仅是来自呈现在所谓“公共论坛 ”或媒体上的各种政治的、文化的论述,更来自已经内化为民族心理和基本人生观的民 间习俗。侯孝贤的电影准确体现了这种内在文化与外在政治权力之间相互纠缠、疏离的 复杂关系。
事实上,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以军人的身份,就已经了解到“本岛土民对历代祖先遵 守之旧惯故俗,如法炮制地尊奉到如同不成文法的程度”,因此,他虽然也明确指出“ 其与我国之习俗大相径庭而有可能成为施政上之障碍者当然需要废除”,但对于一些敏 感的习俗,如辫发、缠足、衣帽之类是否宜改,也不敢擅自决定,而主张“应交由土民 自行决定”(注:伊藤金次郎著《台湾不可欺记》(1948),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0年4月 中译本,第58页、第57~58页、第65~66页。)。说明当政者已经意识到这类涉及“内 在文化”的“习俗”直接影响到民心的掌握。从第十七任总督小林跻造开始,日本殖民 政府一方面以所谓建设“工业台湾”的名义加紧掠夺台湾的资源,另一方面在爆发了“ 七·七”事变后,为了“驱使台湾民众以诚实态度协助母国日本之施策”,积极开展“ 皇民化”运动,以求“统一其思想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整理废合岛内 各地寺庙,“抹杀传承,否定信仰”,“蹂躏习俗”(注:伊藤金次郎著《台湾不可欺 记》(1948),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0年4月中译本,第58页、第57~58页、第65~66页 。),但这并未收到统治者所意想的效果。
我们从伊藤金次郎所披露的一个秘密会议上可以得知,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在用强力 推行了他们所谓的“皇民化”和“皇民炼成”运动之后,对于已经部分跻身“高层”的 台湾士绅,并不信任。这个会议是台湾的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1944年4月某日主持召开 的,他把在台北的日本“有力人士”都请到糖业联合会馆,这些人士包括各个国策会社 的负责人、新闻事业首脑、台北帝国大学的校长以及名教授等所谓“居于指导立场”的 人,唯独瞒着台湾的上层士绅,这使参加会议的所有日人都怀有一种参加“秘密会议” 的感觉。安藤在会议上把心里话公开说了出来:
领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历任总督之政治成绩单共诸于世的时候。倘若统治甚得 民心,万一敌军登陆而全岛战场化,台湾同胞应该会与皇军合作,挺身与敌军登陆部队 做殊死战才对。真正之皇民化必须如此。万一与此相反,倘若台湾同胞中有敌人相互呼 应,甚至由背后突袭我皇军,这不是兹事体大吗?而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还不敢对台湾 同胞寄予绝对的信赖。换言之,历任总督之政治成绩单将会以何等样展现,这一点希望 与各位共同密切关注,并且做妥善对处。(注:伊藤金次郎著《台湾不可欺记》(1948) ,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0年4月中译本,第58页、第57~58页、第65~66页。)
尽管台湾有些士绅得知自己的“忠诚”受到怀疑而忿忿不平,但这件事情本身,正好 说明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真实状况。这种殖民 地的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虽然在某种国家暴力的形式下得以维持暂时的缓和,但由于 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性质以及在政治地位、文化教育诸方面所执行的种族 歧视政策,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方面彼此都心知肚明。因此,像伊藤那样的记者 即使有相当的反省能力,当他看到50年来在“日本帝国臣民”名下进入日本“命运共同 体”并对日本有“特别深厚的缘分”的台湾民众在日本战败后“立即翻脸”,“无视日 本及日本人的忧愁,普天欢腾到浑然忘我的程度”,特别是看到曾被日本敕选为贵族院 议员、担任“皇民奉公会”支部长的林献堂在日本败北之后立即飞往南京,并在1945年 庆祝“双十节”的大会上公开抗议日本的殖民政策后,那种惊讶和不解,还是显示了曾 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那种一厢情愿的感觉。如果他稍微了解一下长期以来台湾 民众在异族的权力压抑下对于自己祖国的感情,稍微了解像林献堂那样的士绅试图在殖 民体制内争取民族自决权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注:据叶荣钟先生所著《日据下台湾政治 社会运动史》(上卷),林献堂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关于台湾民族运动的方法问 题,即采取“改良主义”之方式,“效法爱尔兰人之抗英,厚结日本中央显要以牵制总 督府对台人之苛政”,参见叶著“梁任公给林献堂个人的影响”一节。台北晨星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第30~32页。),他就应该能理解并且敬佩他的长官安藤的直觉,而不 是简单地批评安藤对于他的前任们和对于台人的怀疑了。
内在性文化对于外在性政治的抵抗形式不仅存在于殖民地的民间,在日据时代台湾的 不同阶段,也都被知识者以不同的文学作品来加以呈现。且不说自赖和以来的使用中国 白话文创作的一批早期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台湾小说,从一开始就把殖民者的政治统治与 台湾汉民族社会内在的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作为表现的焦点,就是在1937年“七·七” 事变,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废止汉文媒体,强行阻断了台湾的中文创作,极力推行“皇民 化”运动之后,接受过日本教育、使用日文写作的年轻一代,也并没有在作品中放弃他 们的抵抗运动。我这里要特别提到张文环主编的日本版《台湾文学》杂志。这份创刊于 1941年6月的杂志,是继1937年“七·七”事变、所有报纸杂志的汉文栏目都被废止之 后,唯一以较大的规模存活于战时高压体制内的台湾知识者主持的纯文学刊物。我们知 道1940年在日人西川满主持下的“台湾文艺家协会”创办了一份极富西川满个人色彩的 《文艺台湾》,张文环、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都曾是该刊同仁。1941年2月, 为了配合殖民当局的“皇民化”运动和战时体制,“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张文环因 不满西川满那种“御用文艺家”的作派和《文艺台湾》的编辑方针,自己创办了《台湾 文学》(注:详情参见张文环遗稿《杂志<台湾文学>的诞生》和池田敏雄《张文环<“台 湾文学”的诞生>后记》(《张文环先生追思录》,1978年7月,台中),收入“新文学杂 志”丛刊复刻本之第8种《台湾文学》,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本。)。这份杂志从诞生 之日开始,其实便具有与西川满这位被张文环称为“御用文人”的“纯文学”作家主持 的《文艺台湾》“叫板”的姿态。因此,虽然它用的是“日文”这种表现形式,但所表 现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注意:其一是关于台湾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民俗”生 活进行细致描述的小说(注:例如张文环的《艺旦之家》(创刊号,1941年6月出版)、《 论语与鸡》(第一卷第二号,1941年9月号)、《阉鸡》(第二卷第三号,1942年6月17日) 、《地方生活》(第二卷第四号,1942年10月),吕赫若的《财子寿》(第二卷第二号,1 942年3月)、《风水》(第二卷第四号)、《月夜》(第三卷第一号1943年1月)、《合家平 安》(第三卷第二号,1943年4月)、《石榴》(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7月)等,王昶雄《 奔流》(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7月)等。)。这一倾向与当时对于民俗的关心似乎有许多关 系,在40年代的杂志中,《民俗台湾》(日文版,1941年创刊)就是很重要的参照。其二 是关于台湾文学的讨论(注:这方面的文章有黄得时的《台湾文坛建设论》(1941年9月 号)、杨逵的《台湾文学问答》(第二卷第三号,1942年七月)、《拥护粪便现实主义》( 署名伊东亮,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7月)。);其三是关于台湾文学史的初步梳理(注: 例如黄得时《台湾文学史序说》(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7月、第四卷第一号1943年12月) 和《晚近台湾文学史》(第二卷第四号,1942年10月)。)。这些方面,都显示出知识者 有意通过小说或文化论述的方式来构建本民族的“地方知识”,从而抗拒日本殖民者的 “皇民化”运动(注:值得一提的是黄得时的台湾文学史的初步梳理。他在“台湾文学 史序说”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台湾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把台湾历史划分为 “无所属时代”、“荷兰时代”(共38年,1624~1661)、郑氏时代(共22年,1661~168 3)、清领时代(共212年,1683~1985)和日据时代(1895至论文写作时间的1942年共49年 ),把这320年间在台湾的文人、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黄得时的这篇文章,给人印 象比较深刻的,是藏在这些文学史序说背后的作为“台湾人”的情结,他试图论证台湾 文学既区别于清朝的文学,又不同于日本的明治文学的“特色”。这一点显然深刻影响 了后人的台湾文学观,例如叶石涛的史观。)。
为了说明,不妨分析一下张文环的《论语与鸡》。与二三十年代的赖和为代表的抗议 或批判小说不同,使用日文作为媒介的小说,基本上都较少使用议论或感情色彩比较强 的叙事介入小说,因此,相对而言,他们的艺术性——就其比较委婉含蓄以及结构上的 精雕细琢而言——已经臻至比较成熟的阶段。《论语与鸡》这部小说是从一个少年阿源 的眼里去观察和感受汉民族社会里的种种活着的传统的。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 论语”意味着汉人重视文教的传统;而“鸡”指的是流行于台湾民间的一种习俗“斩鸡 头”,可谓大“雅”与大“俗”。小说的叙事并没有一开始便写出这两条并行不悖地流 行于汉人社会间的传统,而是渲染“拜拜”即将到来的节日气氛,特别提到汉人社会特 有的舞狮仪式,是“祭典时最叫座的”。接下来介绍了主人公阿源与父亲之间在传承上 的差异:父亲是功夫迷,而阿源已对汉人的尚武精神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从上一代人那 里听到的故事,譬如大家族制度,让长子读书好当官发财的传统等等,似乎都在式微。 “现在连这样山里的小村子,也在高喊日本文明”。小小的阿源很希望下山到街路上的 公学校念书,“戴上制帽”,操一口流利的“国语”(日语),便可“好好吓唬一下这里 的乡巴佬们”。但这些都是梦想。阿源生活在山上,生活在读论语,拜孔子,听三国故 事,看大人赌博这样的环境当中。父辈的历史也已经显得遥远而陌生。小说在铺叙了阿 源与小姑娘阿婵的朦胧的情感之后,很快让阿源见识了村民因发生纠纷而用“斩鸡头” 打赌的(类似原始的冥判)仪式。因为阿源向来从内心里敬畏的先生,竟然在众目睽睽之 下触犯禁忌,把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被斩了头的鸡抓来吃,还号称此行与“道教”并不 相违,阿源对先生的敬仰瞬间崩溃,对阿婵所怀有的感情也发生了动摇。小说所营造的 阿源想像的天地,与阿源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已经构成了分裂。而分析这种分裂的主要 原因,乃在于“日本”这个“他者”的存在:小阿源并不了解“日本文化”是什么,但 他知道一个很素朴的道理:只要他能到日本人办的公学校去读书,带上“制帽”,他就 可以吓唬一下那些“乡巴佬”们。“私塾”与“公学校”的对比,也就是落后的传统文 化与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对比,何况后者有着“权力”的支撑。张文环虽然有意让阿源失 望于他的先生的“不洁”的生活,但对于山村里的民俗生活却没有讽刺的意味。相反, 他对于民间仪式(包括舞狮、斩鸡头)和已经融为汉民族生活之一部分的历史故事,甚至 对于村民的有关禁忌的描写,都有着难以掩饰的欣赏的态度。
我还要特别提及《台湾文学》第二号(1941年9月号)上刊登的陈逢源的文章《梁启超与 台湾》。这篇文章是对30年前梁启超来台湾的追忆。这段追忆,令人想到梁启超当年与 台湾的“士绅”遗老们交往当中,对他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据叶荣钟所引的材料,梁 启超当时曾分析了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的现状,认为由于袁世凯行将窃国,帝制自为 ,全国上下致力讨袁,因此将无法帮助台湾;而日本是“未经过民权思想洗礼的国家, 视革命运动如洪水猛兽”,对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绝无同情”,一定会受到压迫,“ 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此,他建议台湾识者先“和日本中央权要结识,获得日本朝 野的同情,借其力量牵制总督府的施策,以期缓和他们的压力,或者可以减少台湾同胞 的痛苦”(注:据叶荣钟先生所著《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卷),林献堂受梁 启超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关于台湾民族运动的方法问题,即采取“改良主义”之方式, “效法爱尔兰人之抗英,厚结日本中央显要以牵制总督府对台人之苛政”,参见叶著“ 梁任公给林献堂个人的影响”一节。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第30~32页。)。 梁启超关于日本尚未经过“民权思想”洗礼的判断,有助于对日本殖民政权的认识。陈 逢源的文章则特别谈到梁启超1911年春在台湾的经验:他登陆之初,就遇上一件令人愤 怒的事情:当时在斗六附近的日本某制糖会社强制购买老百姓的土地,日本警察前来帮 助弹压。这一事件说明所谓的“资本主义化”其实是资本势力借助政治强权对被统治者 进行“掠夺”而已。梁启超当时仿白香山“秦中吟”写了三首诗:《斗六吏》、《垦田 令》和《公学校》,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土地收用制度、财产所有权制度、教育制度等进 行了抨击,为这个“伤心地”的所谓“现代化”留下了难得的记录。他在写给台湾朋友 的信中说:“吾兹行乃大失望!台湾之行政设施,其美备之点诚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国 所有事耳,不必求诸台湾也。吾所为殷然来游者,徒以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 ,同我内地,欲求其制度之斟酌性习而立者,与夫政术之所以因此性习为利导之者;吾 居此浃旬,而不禁废然思返也。”(注:梁启超《游台湾书牍·第四信》,收入《饮冰 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在他看来,殖民政策的制度,至少应该根据当地的民情民俗 来制定,因势利导,始可称“善政”。但日据时代的台湾,那些制度,不过是一个放在 哪里都适合的外在的空壳而已。行政如此,精神上的“催眠”何独不然?
以上列举种种,都在说明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者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来重新构建一 种“地方性知识”以对抗殖民者在所谓“内地延长主义”政策指导下的“皇民化”或“ 皇民炼成”运动。这里需要作区分的是,首先是现实里的民俗生活本身对“殖民化”所 具有的异质性抵抗力量;其次才是知识者对这种民俗生活的叙事和呈现,而这种叙事和 呈现——无论是以美学的方式还是文化论述的方式——所构成的“地方性知识”,恰具 有区别于前现代原始的“地方生活”(被殖民以前)的“现代性”特征。如果把台湾地区 的这种“地方性知识”看作是“台湾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很显然,这种“台湾意 识”从一开始就以对日本殖民者自以为“先进”的“皇民意识”或所谓“资本主义现代 意识”保持着相当距离,它不仅不是附庸于日本“带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反 ,它是对这一外来的“现代性”的审视、消解和抵抗。如果说,这就是“台湾意识”特 殊的地方,那么,它所体现的恰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强权压抑下所产生的被压迫 者的意识,与众多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意识”或“经验”息息相通。此外,这种“地 方性知识”之所以不仅仅是“怀旧”的(譬如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作一种“完美”的 形态来描绘和赞颂),乃是因为它本身也包括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性格,而知识者正是通 过这种自我反省或批判,来建立汉民族的文化自尊,并借此建立一种有别于殖民者的新 的文化理想。
二、从“困境”小说看知识者的文化理想
殖民地知识者依据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所建构的“地方知识”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性格 ,表现于20年代掀起新文化运动的一代知识者的启蒙主义精神当中,但也以隐晦、曲折 的方式存在于一些“困境”小说当中。我所谓的“困境小说”,指的是那种描述主人公 陷入文化认同的苦闷之中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可能未必具有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然 而,他们作品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却具有这种潜在的批判和反省的精神。比较典型的, 如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等。这里谨以颇引起争议的 另外一部“困境”小说、王昶雄的《奔流》为例,分析台湾知识者表现于文学作品中的 文化诉求,并剖析导致主人公陷入文化认同“困境”的原因。
《奔流》是一篇中篇小说,最初以日文发表于1943年7月第三卷第三号的《台湾文学》 。它并非因为作者的名声、作品的艺术性、作品所反映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而显得“重 要”,而是因为作品所提供的特殊的文化认同方面的经验,是人们所陌生的——无论是 日本读者、台湾读者还是大陆读者。因为假如作者在叙述的时候,纯粹把它当作一个还 乡(从东京返回台湾乡下)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类似陶渊明那样的富有田园牧歌情绪的故 事,或者一个单纯的“孝道”故事,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部写于皇民化运动最高潮的 作品,恰恰把当时最敏感的关于人种、民族、文化与政治的认同的问题,都理所当然地 加以处理了。他并不像张文环、吕赫若那样,有意避开当时最敏感的“政治”(皇民化) 来处理民俗的问题,迂回表达另类的立场。他基本上是站在“他者”的视野,从承认日 本人“皇民化”这一运动的“合法性”的角度,来处理民族、文化认同的难题。而这是 以承认台湾人自身的文化、民族身份的“劣势”为前提的。正如巫永福在2000年11月4 日王昶雄获得淡水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颁发的“台湾文学家牛津奖”之后写的文章《王 昶雄文学的管见》所说,“如果以日本人的立场来读《奔流》当可愉快地认为非常成功 的皇民化文学,如果以台湾人的立场来读,犹如俗语所讲‘一样米饲百样人’,认为皇 民化运动的激流时代,也有这样台湾人苦难让人心酸的文学”(注:《台湾文艺》2000 年12月第173期,第5页。)。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读后会感到“愉快”,而台湾人读 后会感到心酸?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王昶雄有意无意选择的“他者”的立场。他借助一个受过日本文 化洗礼的台湾人的眼睛来展开自己的故事。小说叙述一个在东京S医大留学的台湾青年 “我”,原本怀抱远大理想,希望能留在东京工作,却因为父亲突然病逝而不得不返回 台湾乡下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个普通的乡间医生。故乡风物虽然很美,但对东京的怀 念使他陷入“仿佛客愁狂暴的感伤”之中。一直到认识了在中学教“国语”(日语)的“ 伊东春生”(朱东生)这个人,才使他仿佛获得了一副“清凉剂”,从百无聊赖中重新意 气风发起来。伊东春生之所以有这个魅力,是因为他虽然生活在台湾乡下的典型的汉民 族社会环境当中,却仍然坚持他的“皇民”作风:不但勇敢地更改了名字,而且坚持在 公开场合讲日语。“像是内地人(即日本人)的这个伊东,从说话的腔调虽然没有办法识 别,但那脸的轮廓、骨骼、眼睛、鼻子,在我看来,很像是本岛人”。作者显然暗示“ 语言”甚至“精神意识”上的同化有时未必能掩盖“人种学”意义上的异质性。但即便 如此,伊东春生并不为此感到难过。他坚定地认为“人是需要梦的。人类的成长进化, 是受那梦的鼓舞而推进的”,然而“本岛人”并没有“怀抱太大的梦,直截了当地说, 殖民地的劣根性经常低迷不散,很伤脑筋”。在伊东春生的眼里,本岛人“视野很窄” ,“总是怯怯的,人都变小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运用“他者”视角时所具有的 独特性:“我”与“伊东春生”的一见如故,是建立在对日本现代性文化的共鸣之上的 ,“我”以及“伊东春生”所看到的“殖民地的劣根性”,其实也就是被西化改造之后 的日本人所构建起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曾经以中国的儒教文明为自己的思想主体的日 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采纳了作为“他者”的西方现代文化来建构自己的新的“现代文化 ”,日本文化的这一殖民性,反过来成为“改造”、“压抑”其他亚洲民族及其文化的 新的力量。这是近代以来亚洲内部的殖民最特殊的地方:作为被殖民者,它同时要面对 两种“他者”的压力,一种来自被日本人改造的西方(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有 不少东西经过了日本人的译介和诠释),另外一种是被西方改造后的日本(这个日本已充 满了野心勃勃的帝国想像,试图取代中国与西方抗衡)。但从这包含双重“他者”视角 ,恰也看出了作为汉族的“本岛人”那无法被日语、日本文化和日本的精神气质所全部 改造的体质性的东西:“脸的轮廓、骨骼、眼睛、鼻子”等等。
无法被“他者”的殖民精神所改造和压抑的,还有另外一种深藏在汉族内心深处的文 化传统。王昶雄笔下的“我”的心理的微妙变化,是他看到了小说的另外一个人物林柏 年之后。这个沉默而郁闷的林柏年,虽然是伊东春生的学生兼亲戚,但终于在无法忍受 的状况下揭露了伊东春生那不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他一直在逃避赡养亲生母亲的责任 。这使伊东春生在“我”眼里的正面形象发生了动摇。表面上看,作者是用了讽刺的笔 调塑造伊东春生这个人,因而也用这个“反面形象”来戳穿“皇民化”的虚伪。其实不 然。事实上,作者的理想人物——真正能投入时代潮流中的“皇民化”的人物——并非 伊东春生这种只从表面上“皇民化”的人物,而是像林柏年那样的年轻一代:他们从精 神上、肉体上都有更为充沛的坚强的信念和实践理想的能力。他似乎暗示着,只有把日 本的现代文化的精神与台湾人内心所具有的传统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塑造具有台湾本岛 特色的真正的“皇民”。作者让林柏年最后也终于去了“内地”,与伊东春生“殊途同 归”。
王昶雄《奔流》的特别之处,是不管他如何承认“皇民化”的合法性,并把这看作再 造台湾人精神的一个契机,他也无法绕开汉民族最基本的伦理的问题:孝道。“伊东认 为,要成为一个道地的内地人,甩开乡土的土臭完全去掉,为了这个,连亲生的亲人也 非踩越过去不可”。然而林柏年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伊东春生有根本的区别。这部作品显 然是王昶雄为台湾人“皇民化”提供的一种思考方向,如果抛开林柏年最后跑到“日本 内地”去“认同”这一点不谈,在作者看来,他把日本的“剑道”内化为自己的精神, 接受“纯日本化”青年教育,才有可能摆脱“本岛青年双重生活的深刻的苦恼”。这一 点,才是王昶雄所期待的“文化理想”。在这种“理想”的内面,其实对殖民者和被殖 民者都隐藏着某种诉求的:对前者而言,他似乎并不否定“皇民化”的合法性,但要求 照顾到本民族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是在对殖民者“进忠告”,因而显示出与 他们的一些差别;对后者而言,他也要求有所放弃,譬如在小说的最后,“我”为伊东 春生早生白发感到伤感,并辩护说:“也许伊东是为了抛弃俗臭冲天的父母而赎罪,才 会在感觉上格外激烈,对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颤栗的本岛青年,怀着粉身碎骨的献身 精神从事教育去吧。对柏年所表示的好意,不可光把它当作好意。无论如何,伊东的白 发,若不是这不顾一切的战斗的一种表现的话,又会是什么呢?”
王昶雄是否有试图借助官方的“皇民化”运动来刷新台湾人的精神的意图,我们无从 确证。但他所描绘的这些人物由于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他者”所提供的视角而陷入“认 同”的困境,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王昶雄所感觉到的“苦闷”,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台湾知识青年共有的。然而寻找解 决苦闷的办法,因个人的经历、出身背景、世界观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我这里想简单 提及一部在台湾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却久被历史所尘封因而从来未见有人提起的长篇小 说。这就是从1948年6月16日开始在台湾台中的《力行报》副刊上连载的《觉醒》。作 者署名志仁,曾是1948年8月14日在杨逵主催的关于新文艺建设座谈会的记录者。志仁 创作的《觉醒》这部长篇之所以非常重要,乃是因为这是战后,特别是在“二·二八” 事变以后由台湾作家使用流畅的中文创作的第一部反映从“七·七”事变前到太平洋战 争爆发期间台湾青年的苦闷和追求的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跨越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 三地,是一部很精彩的“三城记”。从1948年6月16日开始在《力行报》的“力行副刊 ”第71期连载。目前看到的连载的内容共十章:第一章“船上”,写两个台湾青年,李 长天和吴东轩,于民国廿五年三月开始乘坐日本的大和丸由基隆前往日本留学。两个青 年学生在船上用台湾话议论时事,不料被日人的鹰犬、同是台湾人、乘坐同船前往日本 接受警察训练的叶钦星给撞上了,并强迫他们留下了在日本的地址;第二章“码头”, 写两个青年到了日本之后所看到的景象,突出的是“阶级”情感与“民族”情感的矛盾 问题;第三章“高砂寮”,写住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因在日本感受到的歧视和差别待遇 而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情形;第四章“一封信”,写主人公在日本和台湾之间的通讯; 第五章“两条路”,写在台湾的吴东轩的弟弟和他们的“反帝会”被破获的情况;第六 章“井之头公园”把镜头重新转向东京,写李长天和叶钦星的女儿叶芳美的恋爱和最后 决定赴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选择。叶的父亲是台湾人警察,为虎作伥,这段恋情的展开 很富有戏剧性;第七章“三千里路云和月”,写李长天和吴东轩两人偷偷离开日本潜往 大陆参加抗日运动的过程,从东京到沈阳、北京、K城,再辗转西安,来到重庆。其中 包括五个小节:1.再会吧,东京!(取自李长天写给恋人的一首诗);2.沈阳通讯;3.北 京小姐;4.在日军宪兵队;5.希望中底(应为“抵”)重庆。其中叙述这两个充满了抗日 热情的青年从沈阳潜往北京后,因语言不通,被一个抗日地下组织当作台湾特务抓住, 后来误解终于冰释的故事,感人肺腑。第八章“志愿兵制度”,镜头重新转回台湾,写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在台湾强征所谓“志愿兵”的暴行;第九章“别离伤心”, 写被强征为志愿兵的台湾青年与在台湾的恋人的生离死别;第十章“献媚运动”,写战 时的“皇民化”运动,对“皇民奉公会”的会长林献媚(暗指林献堂?)配合日本人所做 的种种措施进行讽刺批判。这是一部很有创意、历史感和批判深度的长篇。它所提供的 “台湾经验”与龙瑛宗、吴浊流、王昶雄等颇为相通,但却贡献了另外一种走出“困境 ”的可能性,这就是融入祖国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这部小说有些类似“左翼”作品, 但又决非如此简单。可惜被埋没太久,从未有人提起。
三、台湾知识者文化认同的症结在哪里?
众所周知,日人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丰臣 秀吉就已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企图“合三国(中国、朝鲜、日本)为一”,“使其四百州 尽化为我俗”(注:赖山阳:《日本外史》,卷十六。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第52页。)。连横《台湾通史》卷三“经营纪”记 载:“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日本驻福州领事上野专一来台湾考察,归著一论,谓台 湾物产之富,矿产之丰,一切日用之物无所不备,诚天与之宝库也。然以台湾政治因循 姑息,货置于地,坐而不取,宁不可惜。若以东洋政策而论,则台湾之将来,日本人不 可不为之注意也。”这是甲午战前,日本人就企图掠夺那里丰富资源的一个明证。上野 专一所谓“台湾政治因循姑息,货置于地,坐而不取”是有意误判,垂涎于“一切日用 之物无所不备”这一“天与之宝库”才是真的。因为他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年,台湾首 任巡抚刘铭传恰还在任上。而在1885-1891年抚台六年间,刘铭传就已在台湾设防、练 兵、抚番、清赋,实施近代产业开发计划(包括修建南北铁路,架设陆海电线,创设邮 政事业,兴办和整顿各种实业等),整顿商政与外贸,兴办学校,培养现代化人才,积 极从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注:参见姚永森著《刘铭传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 5年9月初版。)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台湾的近代化过程也是可以 在中国人自己的规划下发展很好的,恰是这场战争,中断了中国进行和平改革的现代化 进程。
就在日本人垂涎于台湾的财富时,美国人也看中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日本德川幕 府末期,美国人培里(M.Perry)曾派部下到台湾北部一带调查,之后在《有力的美国人 》一文中称,“若能占领台湾便可以控制清朝的南部沿岸地区,也可以牵制东海的进出 。其战略位置正如古巴岛可以控制美国南部和墨西哥湾的出入一样。”(注:参见若林 正丈、刘进庆、松永正义等编著《台湾百科》,东京大修馆书店,1990年7月出版,第3 2~33页。)对此,刘铭传也十分清楚。他在给清廷上的奏折中,总结历史教训,得出了 “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则欲攘为根据”的结论,(注:《 刘壮肃公奏议》卷一《法兵以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转引自姚永森著《刘铭传传》 ,第133页。)因此,刘铭传抚台期间,才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正如郑成功 收复台湾时(1662)就对荷兰人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注:连横:《台湾通史· 开辟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修订二版,第17页。),作为高山族和汉民族共 同开发拓殖,生养于斯的土地,台湾始终是汉民族和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展的重要基 地。即使在中原被认为受到“异族”入侵的清朝,台湾的汉族也以完整地保留自己的中 原文化为荣,所谓“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郑经:《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 之说,愤而赋之》)。这个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传统并未因政权更替而中断过。在日据 时期,就更是如此。
从1895年到1945年50年间,日本对台实行殖民统治的目标,是在最大限度地掠夺台湾 的经济利益这一前提下,文攻武卫,软硬兼施,使台湾“尽化为我俗”。“俗”,就是 风俗习惯,就是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深刻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 包括语言,礼仪,宗教,甚至建筑、饮食、服饰等等。应该说,日本人的这一政策确是 “深谋远虑”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化俗”政策的发酵,它后来也的确对某些台湾人产 生了效果。例如主张“台独”的王育德在其《台湾——苦闷的历史》(1964)中就认为, “若以公平眼光观察”,日本在台湾50年的“治绩”,“使我台湾岛民成为地球和各国 人民中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处于跟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别的状态下,和日本人并肩活 跃。前往中国和满洲、南洋打天下的台湾人,被当地人视为日本人,体味到优越感。” (注:转引自贾亦斌主编《论“台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第43页、第 69页、第34~35页。)也是这位颇因成为日本人而充满优越感的王育德,在他的另外一 本书《走出历史的阴影》中说:“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 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的质变。”(注:转引 自贾亦斌主编《论“台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第43页、第69页、第3 4~35页。)有了这些准日本人的自我作证,就难怪有的日本政客会说:“就历史和种族 ,台湾和大陆均不同,台湾人也不像外省人要急于回去,……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 ,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的缘故,但我认为 最基本的是台湾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传 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语,1963年)“过去达50年之久的日 本对台湾之殖民地统治,尽管是错误地充满了不实之处,但尚有多数台湾人对日本怀抱 着深刻的依恋与亲切感,此等事实不容抹杀。”(日本关西大学神学系主任小林信雄,1 972年)(注:转引自贾亦斌主编《论“台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第43 页、第69页、第34~35页。)
台湾被强行纳入日本版图之后,殖民者就有意割断它与祖国历史的那种天然联系。他 们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强迫台湾人去认同那个在语言、文化、习俗上迥然不同的国家 。而那块生养了他们的祖先的原乡,则被想像为一个“落后”的“异域”。但台湾自郑 成功开始就具有的“遗民”精神,对日人的同化政策却具有天然的解毒功能。撰写了《 台湾通史》的连横说:“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古人有言,国可灭, 而史不可灭。”(注:连横:《台湾通史》,“自序”,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10月修订二版。)这里的“国”,应该指明末以来的中国。连横的七世祖兴位公之所以 渡海来台,乃是因为痛明室之亡。他来台之后,特意选择当年郑成功驻兵之处——台南 宁南坊马兵营定居下来,便自有其深意,而且连氏子弟不应清廷科举,兴位公临终遗命 以明朝服殓,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反抗异族统治的意志(注:林文月:《青山青史:连雅 堂传》,转引自陈昭瑛《台湾诗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第189~191页。)。 被林熊祥称为日据时代台湾三大诗人之一的诗人胡南溟(1869-1933)(另外两位是连横、 林幼春)“为文有奇气,诗亦汪洋浩荡,有海立云垂之概。”(连横语)。他写《黄河曲 》、《长江曲》、《登昆仑顶》、《江河二曲引》等作品,表现出不以南人自限的气魄 :“今之天下,风会又分南北;南人之中尚有能作北人声情者,挟幽、并之奇气,发燕 、赵之悲歌,独来独往,惊动千古。呜呼!文章一道,伦轨大同,又乌可自囿于江左一 隅哉!此南溟所以奋袂而起,匡坐而歌,作长江、大河二曲动天地而泣鬼神,信乎《国 风》之遗音也!……此吾辈读书所未可以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小之哉!天下之乱也,自北 而南;及其治也,则自南而北。……君子于此观运会焉。”(注:陈昭瑛《台湾诗选注 》作者介绍,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第242~243页。)林幼春1925年因治警事件入 狱,狱中诗曾有“丈夫肠似铁,得死是求仁”之句。他的诗《远因——沈阳事变时作》 有“近事何须说,吾宁咎远因。未闻清内治,纸解便私亲。贱种终当灭,苍天也不仁” 的句子(注:《文化交流》1947年第1期,第20,22页。),试图追究清朝亡国的原因, 诗里透露的是典型的明遗民精神。徐复观为林幼春的《南强诗集》作序时,称其诗“虽 于从容觞咏之中,亦无以抑其激烈悲歌之概,中原之山川文物常萦回盘郁于其笔端,固 结而不可解。故其诗意境深而宏,气象光而大,斯固不可以一岛之地笼而域之”。并认 为其诗“实万劫不磨之民族精魂之所寄”。因称幼春为“一代民族诗人”。(注:陈昭 瑛《台湾诗选注》作者介绍,第199~200页。)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汉文写作 中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台湾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前,知识分子或者通过创办诗社(如 林朝崧1903年创立“栎社”),撰写台湾历史(如连横于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在 精神上认同中国文化传统;或者组织政治团体(如林献堂等1921年组织台湾文化协会, 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设立“台湾议会”的运动,持续到1934年),直接争 取台湾人的政治利益,以对抗日本人的同化政策,解除文化身份认同上“身首异处”的 痛苦。
另一方面,为了让“天皇”治下的台湾人可以逐步接受他们已经是“日本臣民”这一 “事实”,日本人也真是费尽了心机。从1895年“始政”之后,很快就实施一套所谓“ 现代化”的生活制度:1896年开始,从军政过渡为民政。同时公布法律六三号(所谓“ 六三法”),赋予台湾总督以行政权、军事权和立法权,赋予未来的高压政治以“合法 性”。1896年1月1日开始采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并将台湾纳入帝国的“西部标准时区 ”。(注:根据吕绍理:《水螺响起: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作息》,第38页。转引 自施淑《日据时代台湾小说中颓废意识的起源》,收入施淑《两岸文学论集》,新地文 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111页。)1897年以后,台湾总督府陆续公布“货币法” ,采用金本位制,颁布“台湾地籍规则”、“台湾度量衡条例”等等。这一系列具有“ 西化”特征的民政措施,以其“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等“现代性”特征对台湾的 民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其实这是日本掠夺殖民地资源的重要步骤。割断被统治者与原乡的血缘关系,最好的 办法就是“洗脑”,而要让“洗脑”收到最佳的效果,不外乎极力抹黑“原乡”的一切 。日人在这方面的惯用手法,是利用人们对“进化”的“现代”的幻想,尽量用极肮脏 的字眼去形容描绘需要贬斥的对象。借助于“先进/科学/民主/自由/现代”与“落后/ 迷信/专制/奴役/传统”这样的二元对立的修辞方法,尤其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钟理和 写于1959年元月的《原乡人》曾生动描写了日据时代日本人和中国民间社会对台湾孩子 上的不同的“人种学”课。在日本老师关于“支那人”的种种故事中,带有蔑视意味的 “支那”这个名称取代了“中国”,并被塑造成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他者”,因而逐 步形成了这样的想像:“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 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等等”。“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 得怎样呢?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 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注:《钟理和小说选》,北京广播出版社1982 年10月出版,第6页。)虽然在民间俗民社会自有一套不同于日人叙事的说法,孩子们从 自己的奶奶、父亲和兄弟那里,可以听到关于自己的祖国和“原乡人”的完全不同的叙 事与想像,但是,在强权扭曲下的原乡的形象,依然作为一个概念化的“符号”,令人 感到屈辱。从小在日人差别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台湾新一代,在乡间的汉文私塾与官 方公学校之间,接受着关于本民族,关于自身的不同的想像,而渐渐滋生了导致“首” 与“体”分离的“双乡”心态。从3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的台湾知识者, 几乎都产生过这种“分裂”的心态。这是“孤儿”意识滋生的精神土壤,也是在台湾这 个“强权横行”的土地上,知识者的文化身份认同遭遇空前危机的主要原因。
标签:文化论文; 日语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台湾生活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认同论文; 张文环论文; 奔流论文; 张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