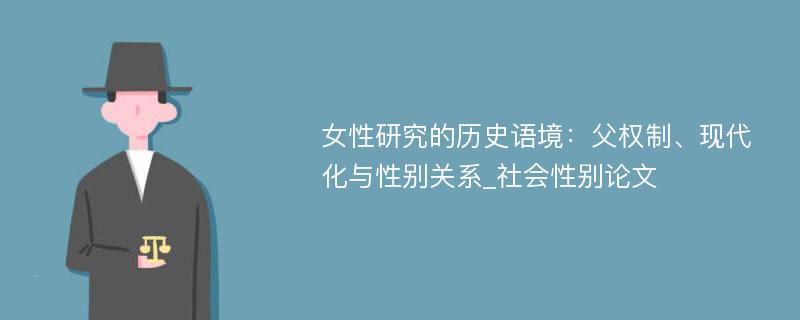
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与性别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权制论文,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以前:中国的父权制与性别关系
在近代以前的主流历史(华夏族)的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应引起妇女研究者的注意:1)由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的转变;2)父权制的确立;3)父权-夫权制的健全。考古学发现证实华夏族先民曾有过一个母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时期及其向父系社会转换的过程;在夏商两代父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以后,西周礼制全面建制,父权制成熟,从而奠定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宋代以降,父权制逐步演化为一种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父系的、父权的、父权-夫权的性别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将母系时代的两性天然平等的“伙伴关系”改变为性别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以压抑女性为特点和代价的,同时也束缚了男性。
(一)母系制-父系制-父权制的性别关系
1.母系时代 大约在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今天北京郊外的山顶洞人就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组织形态中。母系氏族典型的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和姜寨的聚落形态,反映出当时先民处于家庭和社会组织合一的、以对偶小家庭、母系家族和母系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以母系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形态之中。从墓葬反映的两性分工来看,虽然当时男女有了比较固定的分工,但没有主次、高低之分;相反,女性的生育还受到相当的尊重。墓葬也反映了当时以母系为中心的葬俗的流行,表明当时对偶婚从妻居的男子死后要葬到自己的氏族的公共墓地。厚葬女性和幼女的习俗,也反映了当时对妇女的尊重和重视。在这种以女系传承、生产生活以母系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组织中,男女作为氏族成员是一律“平等”的。换句话说,当时尊女崇母而不歧视男。
2.父系制取代母系制 当母系氏族处于鼎盛时期,“危机”来到了。首先,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动摇着母系氏族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产品的增加,分配的不均,产生了贫富差别,母系氏族公有制受到挑战。母系氏族组织出现了裂痕并可能分裂成各种形式的家族。利益的分化导致的团体之间的战争又强化了男性首领的权势、地位和财富增加的趋势,进而他们要求改变世系传承的传统——由女系变为男系传承。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提升,日益成为物质生产、社会组织中的主角,妇女更多地从事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产、家务和其它“私人事务”;性别奴役从男女合葬墓中男子直肢仰身、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甚至有呈跪伏状的殉葬女子上可以看出端倪。(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29-30页。)
3.父权制的建立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与考古学中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时期大体相当,夏商两代是父系制的发展时期。禹的儿子启的时代,“家室”(“私领域”)和权力(“公领域”)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其标志是权力的丧失伴随着家室的被夺(丧权夫妻与夺权得妻同时),但是女性在性关系上已经开始了色性的对象化和工具化,“女色”的观念和“美人计”的运用据载就是始于夏代。(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33-34页。)
商代的父系制是建立在明显的阶级分野基础上的贵族父系制,与此相关的是男性本位的男婚女嫁(不一定居于夫所)、一夫多妇(无嫡妾之别)的婚姻制度。在贵族家庭内部,还没有建立起男性之间的宗法等级关系,对于男子的亲属称谓,父亲的同辈兄弟一律称“父”,子辈一律称“子”(女儿亦然)。因此决定了对女性亲属的称谓,所有的妻妇一律称“妇”,没有嫡妾之别;生子之妇一律称“母”,没有嫡庶之辨。这种性别制度有利于贵族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商代贵妇有介入“公领域”的传统,如参与军政事务、准备和主持祭祀、管理农业等。在属于“私领域”的婚姻家庭领域,因为没有嫡庶制和嫡妾制,诸妇间的关系也没有立嗣争宠的紧张。作为商王的母亲,生前受到尊敬,死后还享有儿王的独祭。(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72-93页。)
西周初期,以周礼的制定为标志的父权制建立起来了。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由此决定了婚姻是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在这两个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男性贵族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丧服和庙祭等一系列的贵族等级制度。又由以上制度决定了贵族内部的性别等级划分:男女间分成了尊卑的位置、内外的分工及其价值界定,在女性之间也随着男性的地位身份分成了长幼、亲疏、尊卑的等级。具体来说,在性别分工上,周代贵族将“公”“私”、“内”“外”作严格判分:在国与家之间谈公私,在家的范围谈内外,私是相对于国事的家庭事务,由男女共同承担;在婚姻制度上,严格的外婚制将通婚的双方分为“内”和“外”——男家为内,女方为外;婚姻的原则是“利内则福,利外取祸”;其操作的方法是外嫁女儿,内娶媳妇,贵族男子要按照等级确定娶妇的数量,在诸妇间分嫡妾等级(嫡妻1名,妾媵不等)。在家庭、生育、立嗣和继承等制度方面,父权家族(庭)把“继祖传嗣”作为婚姻生育的主要目的(注:杜芳琴:《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载《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版,第72-93页。)。所以,不但认定只有生男孩才算有后,而且从原则来讲,要求嫡妻所生长子最有合法的继嗣权。对男女孩子的不同期望和好恶态度使父系时代重男轻女的风俗有了制度的根据。作为家庭角色的妻子,只生了男孩才能在丈夫的家中确立稳定的地位,甚至还会获得一定的“家庭母权”。
总起来说,周代建立的父权制的性别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性别等级的划分——男女间的等级表现为男尊女卑,妇女间的等级既随所“从”的父、夫、子的男人的身份地位而定,也据自己本身获得的身份角色而不同。分工的等级也明显地体现在“公”“外”事重要,而“私”“内”事比较受贬低上。
(二)父权-夫权制:性别制度的“因”“变”和“经”“权”
从公元前11世纪周代贵族建立起男性中心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以来,直到19世纪末,在将近三年的历史中,性别制度和两性关系的格局,基本上因循了周制;但因中有变,变中有因。在此期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转折:1)战国秦汉:由血缘贵族的父权制向官僚地主阶级的父权制的转变;2)魏晋南北朝隋唐:民族融合期父权制受到冲激和整合;3)宋元明清:父权-夫权制时期。
1.性别制度的“因”与“变” 从性别制度的“因”看,周礼奠定的父权制性别制度是建立在双重的等级制(阶级的和性别的)基础上的,只要血缘贵族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存在,其性别制度是不会根本改变的。如在性别分工方面,就是历代陈陈相因了基本的分工模式——男女公私内外的格局是主流社会所提倡强调的,也是事实上实行的;在婚姻制度上,男性本位的从夫居、一夫一妻多妾制一直上行下效地实行,至少是一种合法的存在;在家族制度方面,父家长制下的父子相承的继承原则也从未动摇,只是遇到“空缺”(无子)的时候,才由非嫡子继位和从同族中过继“儿子”以通融权变,但从来不将女儿的世系和继承考虑在家族制度之内。这一制度对妇女的基本道德规范——贞顺孝柔也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强调而已。
从性别制度的“变”看,有两种“变”:一是共时的出于制度的内在需要的“权宜”之变,一种是历时的时移境迁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量变和部分质变。
比如在两性分工方面,“妇无公事”女不干政是不变的原则,但中国的女主政治从一统帝国开始建立直到帝国的灭亡贯穿了两千年(注:杜芳琴:《中国历代女主和女主政治略论》,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这就是权变。再如男耕女织是生产分工的基本模式,但“健妇把锄犁”也不只是在战争时期,要视需要与习俗而定。宋代以来城市中妇女经营者的普遍,从事色艺娱乐业女性的激增,以及明清以降妓业的繁盛和“三姑六婆”(注:(明)陶宗仪《辍耕录》。)的活跃就是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
再如,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关系在两个通婚家庭(庭)之间是经过了漫长的调整的,妇女与父家和夫家两个家族(庭)的“距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典型的变化轨迹可以从出嫁的妇女与父母家族和丈夫家族的远近亲疏、自我归属感以及外在的规范、甚至强制性的干预等迹像上看出来。如史书记载,春秋时代舍夫救父是受到肯定的,至少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到了宋代,已婚的妇女就把丈夫的家族看成自己真正的和永久的归宿。
从婚姻形态而言,尽管祭祖和继嗣的婚姻目的和从夫的居制未变,但从周代贵族外婚制的国际通婚、媵婚到一统帝国、南北分裂再到一统的隋唐帝国盛行的上层阶级的门弟婚姻,进而演变到宋代以降的世俗化的重视财帛和郎才女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婚姻标准不断变化,婚姻形态也不断变化。
对妇女道德的规范要求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周代对妇女道德普遍的要求是贞顺柔从,孝的道德是对父母双亲的尊孝;汉代以儿子孝母作为表彰和选举的重要标准。但从元代开始理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对妇女的贞孝节烈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并更向夫家倾斜,元代强调“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注:杜芳琴:《理学初渐对元代妇女的影响》,载《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第171-172页。);明代最受推崇的女德是为死去的丈夫殉烈,到了清代,主流社会提倡寡妇应该守节承担丈夫家庭的义务。从孝德来看,元明清时期更多地强调妇女对夫家双亲的义务,而孝女不再成为表彰的重心。
2.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的“经”与“权” 所谓“经”,是指性别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模式决定的价值和权力关系上的尊卑贵贱和婚姻家庭制度上的男性中心的、夫家本位的、父权-夫权至上的礼制习俗。所谓“权”,在这里是指制度本身具有的弹性和空间。(注: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同上书,第15-16页。)“权”的存在不仅大大缓解“经”对妇女压迫的张力,也昭示着中国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本土特色。
这里侧重分析性别制度的“权”的表现。在性别分工的男主“公外”,女主“私内”的原则下,由于家国一体、同构的结构,在权力领域,两千年封建时代不乏以太后、后妃的身份参与“公事”的“女主”,甚至还出现过武则天那样长期执政的女皇。在经济活动中,妇女是主“蚕织”、“中馈”的,尽管以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在两性劳动分工有地域风俗的差别,但妇女下田从事农业劳动也不少见,至于城市中的妇女经营者宋代以后更是屡见不鲜。
在家庭角色身份上的“经权”之变更是呈现复杂情状——作为“经”,两性之间存在着支配与服从、主宰与依附、主动与被动等关系,经典性的表述是“三从”、“四德”、“七出”……但在“权”的一面,它又给妇女相对的生活空间,如“尊母”、“孝母”、“重妻”、“爱女”的机制在父权-夫权制家庭中周流自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家庭生活的压力,甚至成为妇女发挥能动性的工具。最明显的就是“家庭母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儿子,对儿媳而言,婆婆就是直接的“统治者”。“权”在不同阶级阶层的妇女中被使用的情况也有不同:士宦家庭中有文化的妻女可以在写作、交游等方面发挥潜能(注: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三期,1995,台北;胡晓真:“‘皇清盛世’与名媛间道——评介苏珊·曼的《珍贵的记录:漫长的十八世纪中的中国妇女》”,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第5期,1998,台北。),劳动阶级的妇女有时在礼制的“边缘”受到较少束缚,也因蓬门小户人家的势单力薄特别强调夫妻合作的家庭“整体性”而得到较多的自主和权力。当然,这些都是有前提的。因而当揭示性别制度的“权”的一面的时候,绝不能忽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压迫妇女“经”的一面。正如Marilyn Toung所说:“即使发现和欢呼一个妇女比较自主的领域,也不要看不见妇女所在的更广的等级权力框架;因为任何社会中的妇女的文化都是‘统治力量方面的控制动力和战略史,是妇女生存、协商、顺应、反对的自我肯定的策略史。’”(注:Marilyn Young,《妇女的实际性别利益和战略性别利益》及援引MarieFlorine Bruneat语,载邱仁宗等主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与妇女解放
近代以来(1840-),妇女和性别关系的变化既体现中国妇女在国际妇女觉醒运动中走向解放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延续历史和跨越历史的特性。总的趋势是:150多年中,旧的性别制度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对,这是一种历史的交织的合力——男人和女人,政党和国家,个体和组织,不断通过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社会改良、阶级革命、民族战争、集体动员、发展计划、运用人性自省、结盟协商等各种手段来校正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努力探索一种新的两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性别关系变革的新旧交替中,显现出性别文化的转换、重建、整合等复杂纷纭态势;同时也表现为由少数男女精英呼吁和实践妇女解放到阶级民族的动员,直到妇女群体力量的壮大与觉醒的过程。
(一)解放妇女与伸张女权:民族、阶级与性别关系的复杂态势
1848-1949年,妇女和性别曾几度成为文化思想界论述、政府改革、立法和政党鼓动民众的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生存危机引发启蒙先驱者的鼓荡呐喊(维新思想家和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家),随即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和运动(维新运动与五四运动),接着是政府的改良或改革(清末的现代化改革和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改良),不彻底的改良引致新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或者民族危机引起战争,导致对民众和妇女的进一步发动,从而孕育着新的变革与解放(辛亥革命与国内革命与抗战)。在此过程中,妇女议题得以凸现,一部分妇女作为解放的主体得到成长,传统的性别制度、观念和关系受到质疑、挑战与部分改变。
1.从“维新”到“革命”:男性精英解放妇女和精英妇女的解放 最初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从妇女的“放足”、“启智”为突破口的。维新人士在“天赋人权”思想启发下提倡“男女平权”。他们把“国家积弱”的主因之一归结为缠足,急切呼吁: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缠足恶习。(注:转引自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可见维新派受“进化论”和“生物学”影响,将妇女的身体、生育的功能与人种改进、富家富国、强种、繁种、优种联系在一起。“兴女学”也是建立在妇女传统家庭性别角色基础上来论述妇女受教育与强国的关系的,办女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妇女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另外,从强国富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女子受教育可以“执业自养”,为社会“生利”而不是“分利”。(注:分别见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女学”、“论幼学”。)尽管当时女子教育只是在少数上层妇女中实施,但孕育和培养了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也推动了清政府出于“自救”的改革。
新思潮的鼓荡、女学的启智、女子结团体的蔚成风气、女权意识的萌发,使得辛亥革命爆发时,一部分精英妇女积极投入武装起义。而当时国际女奴运动进入高潮,受到英国“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许多女子参政组织纷纷成立,甚至出现唐群英等人多次请愿、与议员辩论,甚至扭打政界要员要求参政权的事件。
2.渐进的“现代化”和战争中的中断:“女权”的式微与中共领导的“妇运” 在“五四”前后,新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女权主义……引进传入并杂糅并存,在提倡妇女解放、猛烈地抨击旧家族制度、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某种共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男性)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论述模式,他们呼唤“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带着双重焦虑——民族与国家的振兴、自身在婚姻家庭压抑中以求解脱,奔走呼号妇女解放。
20年代,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渐渐成为活跃于社会中的一支力量。除了在工厂从业的女工之外,新的职业女性群体在都市中活跃起来,妇女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家庭“闺阁”或“青楼”中的两种角色;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自我发现”,呼唤“先做人,再做女人”。她们或就业独立谋生;或出国勤工俭学,探索自我发展和救国之路;或在国内继续开展新的女权活动——当时进步知识界是把女权活动视为世界潮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和途径之一,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女权”与“人权”并提(注:梁启超:《人权与女权》,1922年11月6日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讲演,载《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6日。)。经济独立和职业平等也是努力的目标,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自办学校或实业,同时投入女权运动和社会活动。(注: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want:Oral andTextual Histori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尽管参政女权运动伴随着联省自治的退稳而式微;尽管在沿海都市,“文明”与“时髦”在女性身上折射出“现代化”的光怪陆离,同时也招致许多人对妇女解放的物议与反对,但自下而上的运动不但在敦促当局同意某些男女平等的具体倡议中发挥较大作用,也渐进地改变了世风民俗。仅以从民国四年开始制定、到1930年才出台的“民法草案”为例,其中也不乏承认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尽管其保留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精髓——夫权至上。
如果说从辛亥时期开始出现独立的解放妇女和妇女为主体的女权运动的话,那么从国共两党在1927年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至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就不再是独立的争取妇女权利的行动,而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总目标中。但争取妇女解放仍是共产党的主要工作。这种性别之间的“公开利益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革命队伍中处理性别关系上的棘手的问题。“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男女共同承受的压迫,而“四条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中的两条恰恰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用来束缚女人的。不只是婚姻关系,革命和家庭角色分工方面也出现了冲突。如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和蔡和森的龃牾(注:Christina K.Gilmartine,Engerdering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延安整风时批评那些“重感情”、“好高鹜远”、“幻想做政治家”的知识女性的“弱点”,要求她们“好好照顾革命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注:区梦觉:《改造我们的思想意识》,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科》(1937-1945),第733-738页。),都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男性主导下的性别紧张关系。
国统区妇运在两党首次合作破裂后,妇女独立组织活动也受到一定限制。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才开始又一次女界救亡行动的联合和对全国妇女的集体动员。但国统区更多是城市、知识界的参与。这时,女权的主张与呼吁被全民族的存亡大局所淹没,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一样暂时退隐在民族问题之下而处于次要位置。
(二)“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妇女、国家与社会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从立法来确立男女平等的原则和保护妇女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妇女动员,用集体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发动让妇女从家庭走上社会、生产活动。审视其间的妇女与国家、妇女与男性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改变或因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对妇女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1.制度建设和立法:平等与差别、保护与歧视 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沿袭了中共一贯的男女平等的原则,其后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1951),规定了女工与男工享有同样的劳动保护,并对妇女产前、产后做了特殊保护规定;1953年2月通过的“选举法”规定男女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性别关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既是对百年现代化运动中提倡男女平等遗产的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动员妇女参与中国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和逻辑延续。男女平等立法的真正意义不但使妇女得到事实上的许多好处,更重要的,由于平等立法所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渗透(民间和官方语言),无疑为日后的妇女发展以及最终的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检视50年代关于性别的立法,其不足之处为立法粗疏和理想主义,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缺乏更深入的反省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得到彻底改造。
80年代以来的妇女立法有了更大的进展。1980年修订婚姻法;80年代中期出台了“女职工健康保健暂行规定”(1986)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1992年颁布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重申男女平等,并主张保护法律赋予妇女的特殊权利和利益。这一时期立法更多地强调妇女的生理、生育的特点和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与50年代立法更多注重妇女的社会性解放、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有所不同。这些法规、条例的意图和效果是对妇女有利的,但其对女性生理、生育特点的强调本身是以女性有着先天的生理上的不利条件及能力的缺陷这一观念为指导的,从而掩蔽了历史上形成的性别不平等制度和观念。
2.集体动员的社会参与:“半边天”和性别分工 50年代初国家延续了革命时期对妇女的动员,开展了各项建设和政治的运动。其理论逻辑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带来妇女的解放,而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发动妇女参与革命和生产是革命利益和妇女利益的结合点。各级妇联贯彻“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使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此,要求妇女“提高觉悟,克服依赖男人、不愿劳动”的“落后思想”(注:转引自谭深:《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载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有相当多的妇女在集体劳动中获得了从来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至今中国劳动妇女还承袭这个时代的自信和意志力的遗产,但也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就宠观而言,集体化和普遍就业将家庭(族)对妇女的分隔改变为政策性利益的集体分隔——城乡二元分离的格局,使得城乡妇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活动,呈现出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性别关系几乎同样是权力关系上的男主女从,报酬上男高女低。从微观角度看,工业化与集体化“打散”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础,但消费和维持“再生产”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而在性别分工上立法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从未对传统的内外分工有过质疑,相反,妇女的家庭角色一直没被“淡化”,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被强化,加重了妇女双重角色的紧张。
(三)反思“解放”与“平等”;性别文化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共处
1.“一性化”与“回归女人” 文革沿袭了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别路线,并在“极左”的方向推到极致。有学者将这一时期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非性化”,准确地说应是“一性化”——即“男性化”。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男女,希望过世俗的日子时,“回归女人”就成了一种时髦。学界也以批判“非性化”为名,或提出“做女人”、强化“女性意识”的口号,或急于“淡化”、“超越”性别。殊不知未经过性别文化反思清理的虚幻的“淡化”、“超越”和一厢情愿地“做女人”,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男优女劣文化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将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等级主义合理化。
2.国家与市场:在夹缝中拓展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淡化、削弱,国家对妇女“保护”的部分减少。在男女同时受到体制转轨冲击的情况下,旧的性别关系格局和观念所起的消极作用是妇女首先失业下岗;而另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开始出于商业目的进行操作,妇女成为性剥削、侵犯、利用的对象,拐卖妇女、卖淫嫖娼、色情出版物泛滥……一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妇女也得到比以往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实现和选择的机会,如妇女组织的多样和活跃,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流动的频繁,寻求自给、致富之路的自觉性的加强……妇女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被安排、被塑造,需要“代言”、“保护”的被动角色。也正是这个时期,妇女越来越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根据各自的利益和作为女性的共同体寻找发展的空间。
3.社会性别意识:性别制度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男女平等”和“社会性别”这两个同是“泊来”的概念,并不是像人们理解得那么不可相容;相反,后者使我们理解不平等的深层根源和解决的策略,不再只以男性为标准,不再是男人、国家“解放”妇女,不再限定于“只有提高生产力”、“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只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才能以贡献求地位”……男女不平等也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和“封建残余”在“作怪”,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制度和观念体系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深层的文化反省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这一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基本还处于“失明”“失聪”和“失语”的状态。
主流和大众往往对性别(实际是妇女)采取惊人的矛盾的态度——在“姿态”和口号上重视,而在实质上和内心漠视,因而性别盲点无所不在。就拿生育来说,人们很少从性别制度分工、生物学本质的认识论来批判反思:如何站在妇女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节制生育难道只有妇女承担主要责任这一条出路吗?国家对生育控制真的意味着父权-夫权家庭控制的削弱吗?再如以“性别划线”的“妇女回家论”不断泛起,也反映出对旧的性别分工制度缺乏起码的反思。当然,更少有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资源配置等角度看待隐蔽而又日益突出的家庭暴力、健康、营养甚至商业性性交易泛滥等问题的。
不过,一种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理解、发声、行动的力量正在壮大,妇联组织和妇女研究学者两种力量的结合,正在试图说清楚文化中的性别议题,也企图诠释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与平等。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她们有不同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她们有权力和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应该不断满足这种需求。男女不是二元对立和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建构的,现在是到了共同磋商获得男女自我解放的时候了。
三、历史语境: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意义
妇女研究实际上是从性别的角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对中国性别制度——父权制的形成、演变、内部构成、特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尤其是对近代社会对这一制度的挑战和改变有较为全面深刻和理解,就成了这种对话的前提。同时,当妇女研究成为一种全球行动的时候,在与国外同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历史语境的把握就成了我们自己立足点和归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给我们提醒和启示:
(一)妇女研究:本土·区域·全球的关系
妇女研究正在世界兴起,女性主义理念的普及、社会性别概念的普遍使用这一全球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区域化、本土化更是呼声急切、行动迅猛。中国的妇女研究需要从全球妇女生存的历史、现状、运动和研究的趋势所体现的普遍性入手:比如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和共识。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制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但在研究的策略、概念的引进和运用上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要在本土的研究中检验其适用度并随时给予补充修正。这样做,不但能使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更真正凸现多元性和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本土性的研究和活动才真正能对妇女和人类的进步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对于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来说,对本土的两性生存及其关系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既要能追源溯流,又要善整体把握;既要建立一个从性别角度切入的观察和解释的初步框架,又需要多角度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的研究。
(二)从因变关系看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性
社会性别制度、两性关系和妇女状况地位,这些范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历史的造物。研究者要从变化中考察因循和积淀的成分、变革的内容、以及新旧因素如何共存起作用的。时间的座标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流动的,更是前后衔接的。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变革和滞留因循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原因,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性别关系向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方面转化。
(三)从经权关系知性别关系的复杂性
正如没有固定不变的妇女、性别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抽象的妇女和单一模式的性别关系,中国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作用下的两性关系呈复杂态势:父权制既有压迫、压抑妇女的一面,又有给妇女以生存空间甚至有妇女发挥能动性的机制的一面。所以,简单地用单一的“压迫-解放”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妇女的处境与反应是不全面的。必须深入到中国特定时代、特定的阶层、特定的民族或地域,认真构筑或尽可能复原当时妇女生活的真切的环境,才能看到一幅较为完整的妇女和两性活动的场景,任何理论和观点都将受到检验。另外,经权理论使我们在理解中国妇女的状况和地位时,避免折衷主义的做法。比如:将“权”的一面与“经”等量齐观,过分扩大妇女在传统时代的家庭地位,将其理想化——这就是把妇女的“生存策略史”混同于父权制控制妇女的“战略史”。
标签:社会性别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父系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男女婚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家庭论文; 男女平等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