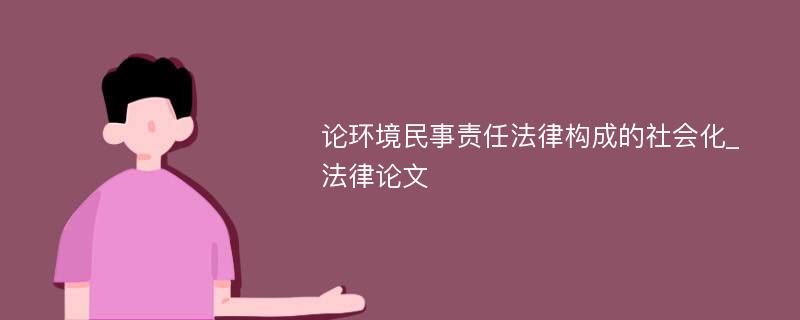
论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的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事责任论文,环境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环境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
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是法律规范的两个要素,法律构成给出规范效果的适用对象或适用条件的部分,法律构成要件具体由法律事实构成,法律效果是构成要件作为原因导致的法律上的结果。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是指影响环境民事责任成立、责任形式和范围的法律构成或者考量因素,即法律事实的集合。
在我国,追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以下条款:《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在判定责任归属和责任形式方面,我国环境民事责任立法有以下特点:第一,统一适用无过失责任。第二,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污染不要求行为人违法,其他污染要求行为人违法。第三,加害人主体特征抽象化,不考虑有无营业许可证、实施防止措施的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等方面的差异。第四,加害人行为特征抽象化,不考虑行为有无公共性、是否超标、是否选址合理、是否有公害防止设备(又分一般或者最高)、有无持续性和先后性关系。第五,侵害的客体笼统化,环境侵权客体无论是财产权或人身权,均适用相同的归责原则。
在我国,排放危险废物或者放射性废物的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的法律事实主要是加害人排放污染物引起财产或者人身损害。排放非危险废物或者非放射性废物的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主要有加害人排放污染物引起财产或者人身损害以及行为违法。
二、外国环境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
外国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包含了较多的生活因素,呈现社会化和多元化特征,以下仅就其中较为常见的法律事实进行列举。
(一)加害人有无营业许可证
在德国,根据《环境责任法》、《联邦污染控制法》等立法,行为人是否需要营业许可证对其产生的环境侵权到底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需要获得政府许可方可从事的营业活动和营业者界定为商行为和商主体的话,商主体就会被科以严格的环境侵权责任,实行无过失责任。其缘由在于:受害人往往是自然人,在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仅限于自然人,商主体较受害者依凭信息占有、财力等实质上处于优势地位,这就在形式平等之下掩藏了实质的不平等,而且,商主体可以通过市场行为将因赔偿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打入成本而转嫁给消费者。加害人是否获得政府许可也对民事责任的形式产生影响,即受害人不能对获得政府许可的加害人请求排除侵害,只能提出请求采取防止措施(设置除去妨害的除害设备)和损害赔偿,而能否请求采取防止措施(设置除去妨害的除害设备),又取决于加害人设置除去妨害和除害设备的技术水平实施的可能性或者实施措施经济上的困难大小。
在美国,“公害”主要是指被告的行为或者不行为妨碍、损害了社会公众行使其公共权利的事实或可能。美国侵权法学家普鲁斯尔将其归纳为包含部分环境侵权如释放难闻气体、烟雾、灰尘等但不限于环境侵权的其他行为如开设赌场和妓院等。当原告提起公害诉讼后,被告可以以他的活动是法律允许,或者政府给予执照作为抗辩事由[1]。
(二)加害人是否选址合理
日本四日市烟害案件的判决(津市地方裁判所四日市分所1972年7月)确认部分被告在选址方面的过失。判决认为,被告在选定厂址时,对于可能给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影响的问题未进行任何调查研究,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这是违反选定厂址的注意义务的 [2]。显然,在本案中,法院对被告科以严格的注意义务,即就公害损害人体健康而言,企业的注意义务不仅包括公害防止设备上的注意义务,甚至追溯到企业的操作以及选定工厂厂址方面的注意义务。
(三)加害行为是否违反公法要求
公法要求具有公法上的法律意义。对于符合公法要求特别是达标排污在私法上是否会当然引发法律后果的讨论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说,大众倾向于符合公法要求不能成为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的主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判决中指出,即使噪声值低于飞机噪声管制法规所定的标准,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超过民法典第906条所规定的得期待的干扰侵害;在1977年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空气质量维护法规所定的标准对于民事责任的拘束力;在1984年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个案的具体情况下,即使营运设施完全符合行政法上的规定,也有可能产生民事上的赔偿责任[3]。最新的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在轻微妨害的判断标准上采用法律或者法规命令确定的极限值或者标准值以及《联邦污染控制法》第48条颁布并反映技术水平的一般行政法规中的数值,可见,在德国,对于达标排放的不可量物的侵入,受害人有容忍的义务。
日本的一些案例也认为,环境侵权行为以及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不应当以是否遵循公法标准为其前提,如日本的水俣病一案的判决指出:“既然其行为对于人的生命、身体造成损害,那么,在民事上就不能不认为违法,而被告所主张的法令是管理法规,特别是根据这些法规,不能左右民事上的责任。”四日市哮喘病判决也认为:“被告即使遵守了排放标准,那也只是不受行政法制裁的依据,不能解释为被害人必须忍受的理由。从本案被侵害利益的严重性来看,归根到底难以用遵守上述标准而认定在忍受限度之内。”[3]
法国在学说,判例和立法原则上均肯认政府机关对加害人的行政许可以及加害人遵守行政法规的事实并非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4]。
在美国也有对于未超过法定限制的污染是否构成公害的争论。在City of Chicago v.Commonwealth Edison Co.321 N.E.2d412(ⅠⅡ.App.Ct.1974)案件的审理中,法官经调查发现,被告虽然会释放一些污染,但这些污染并没有超越联邦政府规定的限度,不会给当地居民带来重大伤害,因此,公害不成立[1]。
(四)加害行为侵害的利益特征
各国在环境侵权归责、责任形式等方面均考虑被侵害利益的特征。环境侵权的客体是人身权和财产权,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利益对峙表现为加害方的经济利益(核心是财产权)和受害人的人身利益或财产利益的冲突。环境侵权背后的权利冲突常常有两种表现形态: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冲突以及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一般认为,人身权优于财产权。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解决则从经济角度加以衡量,比较双方的经济利益谁重谁轻。
在德国,达标排放并不承担物质损害的赔偿责任,但并不免除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体现了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立法精神。根据德国《环境责任法》第5条的规定,如果设备是按照规定运营的,且该物质损害不大,则排除加害者对物质损害的赔偿责任。据此,设备运营者的利益在面对受害者的人身利益时,处于弱势地位,而面临受害者不大的物质损失时则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另外,根据德国《民法典》第906条之规定,受害人衡量补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是妨害必须“重大”。
依据1995年修订的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5条第1款和199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19条第1款之规定,对企业适用无过失责任,不过,其侵害客体限于人身权。大阪空港噪音案的二审判决认为人格权不容任何人擅加侵害,支持原告提出的停止侵害的请求[5]。在“四大公害诉讼”的一审判决中,在公害具有危及市民生命、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完全不应考虑被告企业为避免危害结果所花费用的多少,只要被告在生产的安全性上存在问题,则应确认被告企业负有停止生产的义务[6]。
在法国,通常以“近邻妨害”来表述环境侵权,从 1844年11月27日法国最高法院依据“近邻妨害理论”对工厂污染公害进行审判以来,判例在认定近邻妨害责任成立时,乃以加害人所引起损害的“异常性”或“过度性”作为惟一的实质性要件[3]。
在美国布默诉大西洋水泥公司一案中,法院发现,原告财产遭受的全部损害与被告工厂的价值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如果责令停止污染会迫使水泥厂关闭。同时,水泥厂已经采取了最好的减少污染的技术,另外,水泥厂又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鉴于此,法院判决同意了原告的临时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但拒绝颁布禁止该水泥厂继续污染的禁止令。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州法院一直使用的方法是“衡平法平衡”,并否决颁布禁令的提议[7]。另外,损害具有继续性或反复性,往往被视为“绝对妨害”(Absolute Nuisance),其状态本身即表明妨害“重大性”的成立[8]。
(五)先后住关系
各国都肯认先后住关系是环境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之一。一般认为,先占者相对于后住者,其利益更容易获得法律保护。但是,在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按照《德国民法典》第906条之规定,在决定加害人的责任形式时应该依据“妨害是否重大”,而“重大之妨害,系由该土地之惯行使用所引起”。“惯行使用”体现了对先占者的利益保护,因此,该条隐含了“先占污染”和“先占使用”的原则。
“都营地铁工程噪声案件”的判决(东京地方裁判所1964年6月22日)认为,工程噪声发生后,基于自己意思而居住在工程现场附近的原告甲、乙二人,其所受噪声损害大半系归责于受害者的事由所致,属于“自愿承受危险”,应当依据民法第722条第2款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加以斟酌[3]。
法国最高法院也坚持“先占使用”、“先占污染”原则,即后来的土地所有人和利用人在遭受损害时,应当忍受污染或减低损害赔偿额[4]。
在美国的公害案例中,常常有原告“自己迁入公害”的情况。过去,这常常可以被作为被告的抗辩事由。但现在,根据《侵权法重述》,法院一般只把它作为考虑被告行为的合理性以及伤害结果的一个因素。因为在美国,迁徙与买卖自由是公民的重要权利,非常受尊重。法院认为,人们不能因为行使了这样的自由而受到惩罚。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就比较灵活了。例如在 Spur Industries,Inc.v.DelE.Webb Development Co., 494P.2d 700(Ariz:1972)一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原告是“自己走到公害之中”,因此,他不能得到赔偿,但居民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所以,养牛场必须迁移,但被告的迁移费用要由原告来承担[1]。
(六)排放物质的性质
排放物质的性质也影响归责原则。依据日本199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5条和199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19条的规定,无过失责任仅限于排放的原因物质是有害物质。如果排放的是不含有害物质的废物,则适用过失责任。显然,排放物质的危险性程度在大气和水污染造成人身权侵害时,对于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评价
我国环境民事侵权法律制度,既忽视法律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又对加害人的主体特征、行为特征、侵害的法益性质、环境介质、责任形式等置之不管,将环境民事侵权法律制度变成一个仅追求抽象正义而否认具体正义的工具。我国立法的处理方式是概念法学式,“就法律之解释为逻辑演绎的操作,不为目的考量或者利益衡量,甚至认为社会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只须将各种法律概念如‘数学公式’般地演算一番,即可导出正确的答案”[9]。概念法学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陆盛极一时,由于概念法学割裂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为维持法律的逻辑体系,强调和陶醉于法律自身,悍然不顾社会事实,日益没落。庞德曾评论道:“19世纪的各种解释所思考的都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真正的行为人在他们看来只是种种工具而已。”[10]现代民法所依托的法学理论不是近代民法的概念法学而是自由法学、目的法学、利益法学等,侵权法奉行的理念是实质正义,强调法的妥当性,主张法律规范适用的灵活性,认为成文法并非完美无缺,而是经常存在漏洞,除成文法外,尚有真正的法律存在,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应作独立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在发现漏洞时,应用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予以补充”[11]。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设计应该适应社会的变迁,以单一的原则和制度解决环境民事责任,在“毕其功于一役”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以书面的法律去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无异于削足适履。在探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时,应该借鉴“法律共振峰”的思维方式,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我国立法中关于加害人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要件呈现简单化的特点,对各类污染行为均适用无过失责任,在此前提下只考虑排放物质的危险程度,以此作为是否构成行为违法这一客观要件的依据。相比而言,外国的立法和实践所体现的法律构成则由多个法律事实构成。导致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对法律事实的认识的差别。我国立法的思路事实上是将法律事实狭窄化,仅考虑主观因素和排放物质的危险程度。事实上,我国环境侵权立法将排放物质的危险程度也纳入法律事实,打开了考虑社会因素的缺口,只是这个缺口还不够大,许多应该纳入法律事实的生活事实被排除在外,或者说,我国环境侵权归责方面社会化已经初现端倪,但不够广泛,没有进一步向其他社会因素延伸。在18世纪、19世纪,就法学领域而言,其在西方社会处于一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法学家在其职业环境中形成的修饰过的典型的法律观使他们长久地过于自信,自以为理解得深刻,以至竭力抵制来自法律界以外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关于法律的本质和作用的观点。”[1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排斥社会因素对法律和审判结果的影响,陶醉于对法律事实作狭隘和封闭的理解。殊不知,法律事实本身是生活事实或社会因素,只不过法律赋予该种生活事实以影响法律后果的效力而已。法律事实和生活事实之间不是静态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任何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构成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现在不是法律事实的生活事实将来可能被法律所涵摄而成为法律事实,现在的法律事实也可能在将来被排除其对法律效果的影响,成为纯粹的生活事实。法律事实的构造,主要依赖于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设计,但是,它们最终是根据法律政策的考虑,以特定生活事实为原型拟制而成。生活事实是否具有民法意义,看其是否符合某一民法规范的法律要件,成为法律事实。认定某一生活事实构成法律事实时,意味可以发动特定民法规范,并不是一切具体的生活事实都能被纳入法律范围的,处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立法者总是根据其立法政策,选择一定的生活事实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事实设计必然是抽象的,这是因为法律规定是认识世界的产物,只有类的概括,不能达成真正具体现实的描述。人类无论如何精确思考,都只能到一定程度为止,不能穷尽一切现实具体细节。所以,法律无论如何趋向具体,也都只是抽象化的,采取类型化或概念化形式,而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具体[13]。
我们还可以从德国环境侵权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得出一个规律:法律事实构造是从简单向复杂进行演变的,或者说,法律涵摄的生活事实是逐渐呈现多样化的。早期,德国并无专门的环境侵权条款,而是适用民法典第906条解决与土地毗邻有关的少部分环境侵权案件,后来,规范环境侵权的还有《联邦污染控制法》和《环境责任法》等等,法律涵摄的生活事实越来越多。仅仅比较2002年德国《民法典》和1960年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具体规定就可窥斑见豹。2002年德国《民法典》相对于1960年《民法典》在第906条的变化是增加了轻微妨害的判断标准:轻微妨害的判断标准采用法律或者法规命令确定的极限值或者标准值以及《联邦污染控制法》第48条颁布并反映技术水平的一般行政法规中的数值。其他国家也多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判例体现法律对加害人有无营业许可证、加害人是否选址合理、加害行为是否违反公法要求、加害行为侵害的利益特征、先后住关系、排放物质的性质等因素影响归责原则和责任形式的肯认。
事实上,我国法院在审理环境侵权案件时,已经作出一些顺应法律发展趋势的判决。在我国法官素质总体相对较低、判例缺乏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完全将判决所考虑的法律规定之外的因素交由法官去决断,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将影响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确定性的期待。因此,通过立法将受害利益的性质(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或生活环境、精神感受),程度和范围,加害行为的公益性、地域性、继续性,受害人的特别情况,土地利用的先后关系,行政机关的许可,企业活动在社会评价上的必要性,是否遵守公法标准,是否采取了最完善的污染防治技术设备等社会生活因素中的一部分纳入法律规定,其余的留给法官进行取舍——也就是推进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的社会化,应是完善我国环境侵权立法和司法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