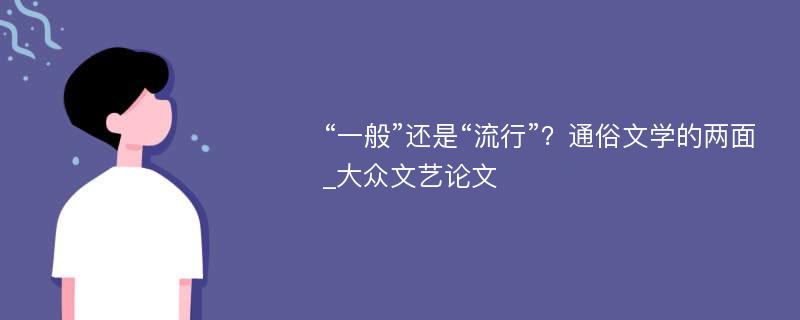
“普罗”还是“通俗”?——“大众文学”的两副面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罗论文,大众论文,通俗论文,面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从“民众”到“普罗”再到“全民”
考察“大众文学”一词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渊源流变过程,关键在对其定语“大众”能指与所指的把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所谓的“大众文学(艺)”实为“大众的文学(艺)”的代名词。因而,在直接探讨“大众文学”演变的轨迹之前,我们应先结合客观的时代背景,以“大众”一词内涵外延的变化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
先看“大众”一词能指的由来。“大众”者,中国古已有之。《汉语大词典简编》列出了“大众”一词的四种古义:“(1)古代对夫役、军卒等的总称。 《吕氏春秋·季夏》:‘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2)泛指民众、群众。 《东观汉记·铫期传》:‘大众披辟。’(3)犹言众人或大伙儿。 《潜夫论·浮侈》:‘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4)佛教对信众的称呼。”① 由此可见,早在古代,“大众”一词即已出现。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大众”的能指与其冠以翻译引介的产物,不如说发源自本土,尽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大众”作为专有名词,其所指曾受到外来(尤其以日俄两国为主)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极大影响。
乍看之下,似乎当下“大众文学”中“大众”之内涵,即“大众”古义(2)的延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日常理解的“大众”并非由上述古汉语词义的“民众、群众”一项直接化来,而是经历了日本学者的现代改造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后才再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大众”一词由古典内涵脱胎换骨为现代意义的功臣,当推日本“大众文艺”之父——白井乔二。尾崎秀树在《大众文学》中明确指出:“从佛教语言里将‘大众’一词转用过来的功臣正是白井乔二,时间是大正末到昭和初期(约20世纪20年代初叶——笔者)。”② 为了阐明以白井乔二为代表的一批大众文学的始作俑者与“大众”佛教古义间的关系,尾崎秀树写道:“本来,‘大众’二字相当于梵语的‘僧迦’、‘摩诃僧衹’,意指三个以上的僧侣集中在一起的场合,……中里介山、三田村鸢鱼等人对‘大众文学’这一称呼曾表示异议:‘大众一词过去……是指和尚,早先时候叫做‘南都六方大众’;即便是今天,禅宗仍然把僧堂僧人叫做大众。可见大众并没有‘民众’、‘庶民’这种意思。……’这种说法看来不无道理,但是‘大众’一旦脱离了‘僧侣’的意思之后, 用作people 也好, 用作popular、mass也好,都无伤大雅,因为词汇本来就是活的。”③ 也就是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驻日本的“大众”一词,原本并没有中国古汉语中“民众、群众”的义项。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批评家们未能完成“大众”词义的现代转换。这一过程却经由白井乔二等一批日本大众作家的创作及理论实践得以完成。“大众”一词由此逐步脱离其原先的宗教色彩,更多地与西方“市民社会”之“市民”、“民众”等概念相提并论。
反观中国文艺理论界,与日本“大众”一词大相径庭的是,自诞生伊始,中国文坛的“大众”便熏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十足的火药气息。比如高滔在1923年6月15日的“文学一周纪念特辑”征文中就曾提道:“好像因为谈到‘大众文学’这样问题的时候,便有高贵的作家宣告说他早已不要大众了。这‘不要大众’的理由据我想也不外下面两点:(一)‘大众’这字眼太‘红’,要不得,若是谈起这个来当容易使文人有摸摸颈后看看饭碗的恐惧,所以不肯要。(二)……属于前者是政治问题的,谁也没有强迫别人入狱,上绞台的权利,并且这不是不肯要,实是不敢要,……”④ 极言当时中国文坛“大众”二字背后蕴涵的阶级革命意味。这里的“大众”,恐怕早已不是日本“大众文艺”中所谓“全民”、“民众”等的代言词了。它更多的是与“普罗”、“无产阶级”、“工农先进分子”等政治概念紧密相连;因而同日本“大众文学”之“大众”有着本质的不同。
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时期,当时文坛的各位主将更是围绕“大众”一词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多次讨论。试举几例如下:
“大众文艺!你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郭沫若)
“‘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乃超)
“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王独清)⑤
“初期普罗文化运动所认定的大众——中学生,大学生,一般的店员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其他的知识分子,……然而构成社会基础的大众是工农。”(王一榴)
“然而所指的大众,是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并非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画室)⑥
很显然,以上罗列的“大众”正是无产阶级(或至少是工农)的代名词。不过“大众”一词的外延并非就此一成不变。“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随着全面抗战活动的展开,政治军事形势的急转直下,“大众”的所指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大众”进一步扩大为包括工农、小市民、商人、学生等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继而在1936年前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期,“大众”一词外延的扩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巩固。比如周扬一马当先,批评了那种“以为只有工农大众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的看法。茅盾的意见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譬如‘大众’两字,在向来是被解释作‘工农大众’的,工农大众当然是全民大众的‘主体’,但在现阶段的救亡运动中,……当然不限于工农大众,那么‘工农’这口号,是不是能够表现现阶段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此,徐非辰总结道:“我们如果单就字义上讲,则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民族主义的文学更相类似……盖先前他们把‘大众’两字是解释作‘工农大众’的,而现在他们已自动修正改为‘人民大众’了。”⑦ 则“大众”已由先前特指“工农”转而指代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与此相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文学”的起源流变——从“文艺大众化”到“大众文艺”再到“大众文学”,从“化大众”的文学理念之倡导到抗战文学全面大众化的展开——也呈现了类似的变化过程。
“大众文学”:从“通俗”到“普罗”
就“大众”的含义进行辨析无疑有助于我们勾勒“大众文学”的演变轨迹。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大众文学”这一术语的起源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时间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此时“大众文学”由日本翻译引介入中国,“大众文艺”一词出现;(以1928年《大众文艺》的创刊为代表性事件)
(二)酝酿期,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初中叶。经过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文艺大众化”、“大众文学”等词汇开始在文学批评界登台亮相;(有所谓“旧式大众文艺”与“革命大众文艺”之辨)
(三)成熟期,时间为1936年前后,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两个口号”的论争。至此,“大众文学”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确立了一席之地。
正如上文考究“大众”的渊源一样,我们先从日本“大众文学”一词的起源着眼,考察中日两国的文学理念在该术语诞生历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当“大众”的含义完成其现代化转变之后,“大众”与“文学(文艺)”结合的产物“大众文艺”继而在日本文坛登台亮相:“据本村毅的《大众文学十六讲》记载,大正十三年春天发行的《讲谈杂志》目录页上有‘请看,大众文艺的雄伟奇观’这样的广告文,这可以说是最早使用‘大众文艺’的例子。”⑧ 那么,真正实现“大众”与“文学”之结合的始作俑者是谁?白井乔二曾一度创造性运用了“大众”一词的现代意义,他是否也是第一位使用“大众文艺”这一术语的功臣?尾崎秀树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这些问题,而是转而以大量的文学史料和背景事件,从侧面巧妙论证了“大众文学”诞生与兴盛之必然。从尾崎秀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传媒技术就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随之而来的则是市民社会的崛起。因而无怪乎“日本的大众文学在震灾后的短短四年里”,就实现了“大众”含义的现代化更新,实现了“大众文艺”一词的普及——“经历了由‘新讲谈’到‘读物文艺’,再从‘读物文艺’发展到‘大众文艺’的变迁”,最后从“大众文艺”到“大众文学”,“走过了最后的行程,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⑨
回归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大众文学”这一新语词的诞生无疑同日本“大众文学”(Taishubungaku)一词的译介息息相关。 比如《大众文艺》的创办者、留日学生郁达夫就承认:“不过《大众文艺》这个名目,却是由我而取。”⑩ 在随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陶晶孙、瞿秋白等人也屡屡提到了“大众文艺”的这一异域渊源(尽管他们对此均持批判的态度)。郭沫若曾就此评论道:“日本近年新创大众文艺的名词,……现出的面孔是:在封建时代的遗臭中蒸发着的通俗小说!……和现在上海通行着的,甚么红绿小说黑幕小说是异母兄弟。这个新名词在去年又输进中国来了(指郁达夫编的《大众文艺》——笔者)……”(11) 陶晶孙和瞿秋白的看法与此相类:“大众听说是指佛教之僧侣团的。后来日本人把几种有关通俗小说题名为大众小说,……”(12) “大众文学这一名辞,颇有点来路货——尤其是东洋货的臭味,但在日本,大众文学也比较是新的出产;……中国一般劳苦大众目下所欢迎的这一大堆封建残余的文学,我们把它总括起来,也叫大众文学。”(13) 由此可见,就“大众文学(艺)”同日本“大众文艺”的词源传承关系来看,上述各位理论家并不存在多少争议。然而相较于日本“大众文学”自产生伊始就具备的浓重的通俗化色彩,中国的“大众文学”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综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大众文学”同本土特有的政治文化面貌相吻合,其演变轨迹遵循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道路。尽管大众文学的第一副面孔——通俗文学——也曾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坛上叱咤一时(正如范伯群所言:“从民国建立的1912年,到文学革命开始的1917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通俗文学独踞文坛中心的五年。”(14) 无论从创作手法、思想内容还是阅读对象来看,20世纪初风靡文坛的这些作品都与日本的“大众文学”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同是商品社会繁荣的产物,同是大众媒体进步的结果)。然而“大众文学”的这第一副面孔在中国文坛仅仅昙花一现便迅速销声匿迹了。它遭遇到的是两股强大力量的反对:一者来自“五四”以后,知识精英分子们“启蒙”式的批判传统;二者则是随后更为彻底的意识形态压制。
首先看萌芽期。中国文学历来的传统是重“雅”轻“俗”。既是“文以载道”,那么在知识精英们看来,文学就应当担负起社会改造、启蒙教育等等的义务。因而,迎合读者趣味、游戏人生的文学作品无疑难以见容于文坛——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都市消遣文学繁盛未几,便很快偃旗息鼓。前有刘半农等一批五四大将的猛烈攻击:“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15) 后为郑伯奇等人的围追堵截:“总而言之,投合没有自觉的大众嗜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媚俗的,同时自然也是堕落的。”(16) 在如此这般的前提背景之下,自日本引介入中国文坛的“大众文艺”,自然也无法置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知识精英分子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意识——于不顾。一言以蔽之,“大众文艺”之所以未能走上日本“通俗文学”式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只有引导大众进步、化大众的“大众文艺”,才能为中国文坛的精英集团所真正认可。
其次进入酝酿期以后,知识精英的启蒙意识开始为政治意味更加浓厚的自我改造要求所取代。以左联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文人不再满足于对“礼拜六派”等进行表面的批判,而是转而号召作家们从自身的文学实践出发,在“大众”中实现自我改造:由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走向大众,以完成普罗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成功取代。“革命的大众文学”如何才能战胜或消灭“反动(旧式)的大众文艺”,成为独踞文坛的“大众文学”?试图纠“普洛文学”不够“大众”之弊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由此应运而生。历次讨论中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是,左翼的文学家们特意在“大众文艺”一词前冠以“革命”和“反动”这两个定语以示区分。前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某种自上而下的文学理念之体现。后者则专指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通俗文艺,因而难逃左翼文人们的大肆攻击。比如瞿秋白就指出:“上中下三等的礼拜六派倒会很巧妙的运用着旧式大众文艺的体裁,写成《火烧红莲寺》等的‘大众文艺’……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之中,闹得乌烟瘴气的正是武侠剑仙的迷梦……”“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都有几百年的根底。”(17) 左联创作委员会更是将“反动(旧式)大众文艺”视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公然将其写入了工作的章程之中:“要加紧研究大众文艺,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以及批评一切反动的大众文艺。”“创委目前最紧要的工作:……(3)研究及批判现在最流行的一切反动大众文艺……”(18) 在第一阶段中,智识分子试图通过“启蒙”改造甚至全面抹杀民间的“大众文艺”;到了第二阶段,这一彻头彻尾的改造则经由政治的强力得以实现。
最后到了第三个时期。尽管从“大众文艺”到“大众文学”,其差异只在一字之间,但这显然又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转折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该转折点都意味着“大众文学”作为专有名词,最终在文学理论界稳固了自己的阵地。当剖析日本“大众文艺”至“大众文学”的转变时,尾崎秀树列举了如下两点理由。一是该转变体现了日本大众文学的自觉意识:“细心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改‘大众文艺’为‘大众文学’这一变化的实质,尽管从‘文艺’到‘文学’只有一字之差,但从中反映了大众作家对作品创作的自信心。”“在‘大众文艺’改名为‘大众文学’的背后,可以感受到大众作家对创作作品的自觉意识。”(19) 二是假如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则当时一些重要作品的问世也是推动“大众文艺”向“大众文学”迈进的一大因素——“大众文学”的地位是通过1927年(昭和二年)出版的《现代大众文学全集》方才得以巩固的。(20) 与之相对照,一方面,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界,精英分子们的文学自觉意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第二阶段“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时期,尽管讨论涉及的对象包罗万象,有大众电影、音乐、电视等多种艺术形式,但文学的专论为数最众,探讨也最为详尽——名为“文艺大众化”讨论,实则“文学大众化”讨论。足可见文学作为文艺的形态之一,其在中国现代文论界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大众文学”在中国文坛的最终稳固并非有赖强有力的作品的支持(虽然其间不乏许多作家如丁玲、老舍、赵树理等人不懈的创作努力),而是主要依靠众多评论家的理论建构,比方说1936年前后的“两个口号”论争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众文学”之复兴:回归通俗
四十年代以后,“大众文学”风光不再,其相关讨论不复为文艺理论界的中心话题。从解放初年直至“文革”结束,不但大众文学的第一副面孔在大陆偃旗息鼓(“礼拜六”等都市通俗文学的命脉在大陆之外的香港等地得以传承),而且“大众文学”的第二副面孔——普罗文学——也为新一批更加“革命”的“工农兵文学”等术语所取代,“大众文学”至此似乎气数已尽。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大众文化、大众媒体等当代文论术语的相继涌入,“大众文学”再度成为了文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21)。然而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文学”同八十年代后复兴的“大众文学”略做对比则可发现,虽然两个“大众文学”的能指相同,但是其内涵与所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众文学”之异域渊源来自日本。而八九十年代复兴的“大众文学”则更多受到了西方“mass media”(大众传媒)、“popular art”(大众艺术)等词汇的影响。因而,风靡中国当代文论界的“大众文学”一词并不是对先前现代文坛“大众文学”的继承。其次,如果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文学”指涉的对象为工农无产阶级文学,即大众文学的第二副面孔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大众文学”的所指已经转移到市民通俗文学,即大众文学的第一副面孔之上。在二三十年代“大众文学”这一专有名词的背后,矗立着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自上而下的启蒙意识,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自我改造意识。而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引介而死灰复燃的“大众文学”,其相应背景则可以追溯至一系列的时局变化:从政治的断层到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从文艺的商品化到思想的大解放,等等。由此可见,“大众文学”究竟将以何种面孔示人,其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大环境。
最后,引用《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大众文学”词条的一段注释为全文作结:
“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大众文学的发展遭受到了它们在西方世界未曾遭受过的阻碍。文学作品必须经政府机构的许可才能出版,而其能否出版通常不是由大众的趣味和爱好决定,而是取决于官员们的意见。这样政府就能够将那些对国家利益不利的作品剔除出流通领域,尽管它们可能深受大众喜爱。”(22)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该词条反映了东西方世界之间理解的误区,但是它也准确地传达了“大众文学”这一简单四字词语折射出的丰富的政治内涵、文学理念和世界观。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坛中“大众文学”一词的背后,始终蕴涵了某种自上而下,充斥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理念。它不同于日本近代文坛的“大众文学”现象,更迥异于西方当代学术界的大众文学传统;尽管在“大众文学”复兴乃至消费文化泛滥的今天,中国文论界的“大众文学”一词正在逐步向西方“大众文学”的理念靠拢。
注释:
① 汉语大词典简编委员会编,《汉语大词典简编》上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117页。
②③ 尾崎秀树著、徐萍飞等译:《大众文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20,21~22页。
④ 高滔:《关于“大众文学”的两个疑问》,引自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6月印行,据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150~151页。
⑤ 参见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乃超:《大众化的问题》;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引自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11、13、18页。
⑥ 参见《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原载1930年5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25、32页。
⑦ 参见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原载1936年6月25日《光明》第1卷第2号);茅盾,《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原载1936年7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2号);徐北辰,《新文学建设诸问题》(原载1937年1月1日《文艺月刊》第10卷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355、439、1111页。
⑧⑨ 尾崎秀树:《大众文学》,第19、30页。
⑩ 参见《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原载1930年5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20页。
(11) 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11页。
(12) 陶晶孙:《大众化文艺》,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12页。
(13) 何大白:《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原载1932年7月《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79页。
(14) 范伯群、孔庆东主编:《通俗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34页。
(15)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原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711页。
(16) 郑伯奇:《通俗和媚俗》。引自郑伯奇《两栖集》(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6月第1版,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1月初版本),第32页。
(17)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引自《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471页。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引自《瞿秋白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页。
(18) 左联秘书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和《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原载《秘书处消息》第1期)。引自《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4、6页。
(19) 尾崎秀树:《大众文学》,第30、32页。
(20) “下中先生跟我谈起出版一部《大众文艺全集》,我赞成他的意见,并建议名称是否把‘文艺’改为‘文学’更为妥当。……也许这‘大众文学’一词是我和下中先生共同想出来的。(《大众文学》,第31页)”以上是尾崎秀树引用的桥本宪三的原话。由此可见,“大众文学”一词之所以最终能够取代“大众文艺”,《现代大众文学全集》的策划人下中弥三郎和桥本宪三功不可没。
(21) 试举一例: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论文,以“大众文学”为关键词的命中42篇,以“通俗文学”为关键词的命中233篇。
(22) The New Encyclopcedia Britannica(Volume 9),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768 15[th]ed,[1998 rev.],第6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