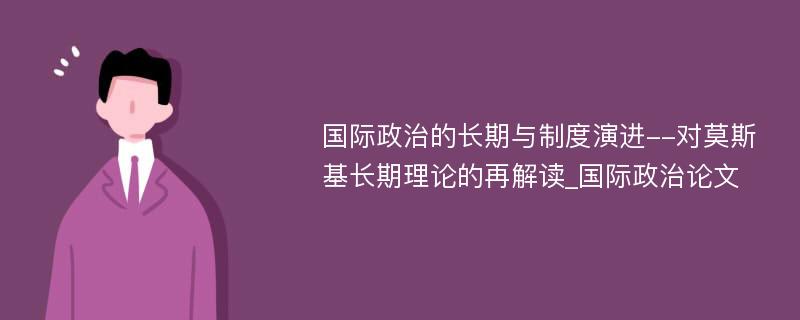
国际政治长周期与体系进化——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斯基论文,德尔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政治周期理论研究领域,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 基(George Modelski)提出并创立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他对历史 的总结分析,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可分为五个周期,每个周期大 约为100-120年,它们分别为葡萄牙周期(1494-1580年)、荷兰周期(1580-1688年)、英 国周期Ⅰ(1688-1792年)、英国周期Ⅱ(1792-1914年)和美国周期(1914年至今)。各个世 界领导国的盛衰更替和全球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关注的重点。对 于前者,莫强调的是基于海上(空中)实力的全球伸展能力(global reach)以及特定时期 内领导国兴衰的不可避免;而对于后者,莫指出,其动因是全球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通常表现为对领导国的挑战和领导权的争夺,其结果是全球政治体系新领导结构的产 生。如此,莫德尔斯基为国际政治体系的过去和未来提供了一种框架模式,即霸权的兴 衰和看似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全球战争。
国内外学者在对莫德尔斯基理解历史的全新视角和方法论作出肯定的同时,多集中于 其理论中周期性反复的内容上,往往忽视甚至无视其重视进化的一面。例如,部分体系 理论家认为莫德尔斯基为完成对长周期的时间和转换方式的规律性定位,有意忽略或减 弱了大规模陆上战争的实质作用,或笼统地将之归并到“全球战争”这一范畴中,如三 十年战争,也相应地忽视或弱化了陆上强国在长周期中的作用,如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 、20世纪的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注:Robert E.Harkavy,“long Cycle Theory
and the Hegemonic Powers'Basing Networks”,in Political Geography,Vol.18,199 9,pp.942-943.)新马克思主义者更认为莫氏长周期理论将军事安全和经济因素分离开来 ,(注:Ibid.P.943.)未看到经济发展对国际政治演变的重大影响。另有一部分学者认 为从属于霸权理论的莫氏长周期理论,从本质上讲属于周期理论(cyclic theory)而不 是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的范畴。(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 页。)他们指出,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的不足之处是把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看成 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他们对长周期的理解往往是: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国际社会如 何发展,每个国家都难以摆脱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轮番上台表演、有序与无序交替变化 的规律的束缚,认为这一理论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漠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 和一体化的作用。(注: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 1年版,第304-305页。)
的确,从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的研究起点和框架结构来看,它很容易让人理解成仅 是时间维度的、机械式的领导国和全球战争的往复更替。然而,如果我们对莫德尔斯基 的长周期作一系统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并非只是纯粹的周期理论,它同时包含了丰富 的“进化性”(注:莫德尔斯基把这种进化性称为“正面反馈”(positive feedback)或 “进化式学习”(evolutionary learning)。See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1987.)。
长周期与体系进化
长周期是全球政治体系的一种运行模式,也是全球政治中的一种结构性变革过程。对 历史中的长周期进行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一切国际事件,而在于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 变有一种宏观的、全面的认识。(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7.)就这一角度而言,长周期首先体现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特性。作为一种理 解方式,它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变动,引起这一变动的则是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 权势在一定时空里此消彼涨,也表现为该时空内的权力分配结构、力量组合(即联盟情 况)以及全球问题确定和处理等方面的变动。根据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由单元间能 力的分配来界定的结构决定了体系的状态,(注:沃尔兹认为,结构应根据三方面来界 定,分别是:系统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以及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在无政府 的国际政治中,在排列原则上是无政府,在各单元的功能上是同类单元基于本国利益的 对外行为,故沃尔兹认为前两方面不具意义,唯一能界定国际政治中结构的只能是各单 元间能力的分配。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年版,第五章。)在国际政治中,无论是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 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莫德尔斯基所强调的领导国权威的丧失(
delegitimation)和体系权力的分散(deconcentration)。当结构趋于稳定,处于这一结 构最高层的领导国凭借其内在条件或特质(如强有力的变革思想)使体系呈现出螺旋向上 的进化式学习模式。莫德尔斯基承认,基于自助原则的普遍行为使得国家不愿依附于他 国,这在强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同样属于社会体系的全球政治体系中,实力以及 行为能力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种依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如历史上领导国的同盟 对领导者的依附,虽然其动机仍是现实的国家安全)。(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12-13.)由此,长周期首先反映的是一个一定时期内具 有组织结构的政治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由结构决定(尤其是存在稳定领导的结构)的进化 式学习系统,是使各种行为体向更高层次过渡的安排。如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 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最初是少数民族国家的超欧洲和全球性活动,从15世纪末到17世 纪末,只是英、法、西、葡(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核心成员;(注:国际政治 体系初成的两个周期内,具备强大实力和国际秩序提供能力的民族国家的数量总是很小 的,在葡萄牙周期(1494-1580年)是葡、西、英、法,在荷兰周期(1580-1688年)则是荷 、西、英、法。见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1988,p.135.)其次是大国间的竞争;最后是民族国家的 普化。
莫德尔斯基构建的长周期有自己的发展演进阶段,它不止是全球层面的战争和系统更 替,每一个周期内也展示了一种“阶段性运动”(phase movement)。这种阶段性运动分 为全球战争(global war)、世界强国(world power)、权威丧失(delegitimation)、权 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四个阶段。如果将对秩序的需求性(或是对领导权的需求性) 和秩序的可用性(或是领导权的可用性)视为影响长周期宏观阶段演进的相关变量,那么 任何特定的体系即周期都能被理解为是在这两个变量之间浮动的过程。具体地说,由于 处于全球战争以及战后的混乱之中,第一、二阶段对秩序的需求性高,而第三、四阶段 则处于领导国地位确立后的相对稳定期,它们对秩序的需求性就低。就秩序的可用性这 一变量而言,第二、三阶段处于领导国权势影响之下,并建立起了该周期的体系秩序; 第一、四阶段分别是战争和权力分散状态,体系未提供任何秩序,则处于一种无序之中 。(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30-31.)在整个进程中 ,对秩序的需求恰好反映了体系阶段性变革进化的功能,而秩序的可用性则反映了领导 国在这一进化中的主导作用。这种周期内的进化性充分表明全球政治是在一种面显混乱 、实则有序的进程中实现的。近现代500年长周期的运动就代表着世界政治的不断进化 。
这种阶段性运动是根据各个时期在全球政治层面的不同状态来划分的,故称“体系周 期”,如果把关注点集中到世界强国,即领导国上面,相应地就会得出一个世界强国周 期也即领导周期。与体系周期中四阶段相对应,领导周期中的四阶段依次为:明确形势 阶段(clarification)、组合力量阶段(coalitioning)、宏观决策阶段(macrodecision) 、履行权力阶段(implementation)。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领导周期强调全球政治体系中 领导国产生过程,它的最终状态是世界强国领导地位的确立。在明确形势阶段,全球问 题的产生使得现有领导国权威日益丧失,各国根据现有局势对全球政治结构进行重新定 义;组合力量即指动员相关国家并向体系注入某种创新因素,此时体系权力已分散至几 个大国或国家联盟身上;宏观决策即是全球战争,它是之前各种发展创新因素的总结, 其结晶是完成体系的更替,由此将体系引入一种新状态,该状态的最终明朗则是在履行 权力阶段。(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64-67.)我们 注意到,就每一领导国而言,它的起点是前一领导国的衰落;体系层次的权力分散和无 序在国家层次变成了发展、学习、进化并产生新领导国的过程。由此,莫德尔斯基长周 期理论中的领导模式周期更能反映国际政治体系的进化。
从宏观历史演进的视角看,长周期还不断孕育并推动革新,使世界政治不断进化。每 次长周期都有别于并高于前一次周期的重大革新,但每次革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前 一次革新的起点上达到的;是对之前革新的积累,而不是机械反复。比如,葡萄牙开辟 了新航路,发展了洲际贸易;尼德兰人的突出贡献则在于一改葡萄牙周期中那种僵硬的 至非欧洲地区的航行仅由西、葡两国垄断的局面,而代之以新的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机制 ,实现这一进化的基础就是荷兰对新教伦理的全新诠释并由此建立的有效组织全球体系 的新教集团。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是旧秩序对大国(包括领导国和挑战国)扩张的限制过程 ,因为既定经济秩序、技术水平和其他因素决定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政治实体的 最适规模。不达到最适规模,国家便不能积聚足够的财力来保卫自己并生存下去;超过 最适规模,规模成本就会增加,妨碍其进一步扩张。(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 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规 模负担和技术能力的不平衡增加了体系对新秩序的需求,如与尼德兰对抗的西班牙国王 菲力浦二世试图恢复宗教秩序、与英国对抗的法王路易十四企图重建英国的正统形象, 它们的最终失败都是旧秩序过分扩张的后果。因此,新旧秩序的继承性转变在很大程度 上印证了莫德尔斯基对全球政治进程的进化式总结。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长周期这一框架中,周期性反复与体系进化是并重的两种属性, 前者解释了体系的可控和稳定,后者解释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影 响。
体系进化的主要动因
莫德尔斯基对全球政治体系的定义是,基于对某一特定范围的问题的共同关注而结成 的一系列关系,这种关系服务于全球层面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目标。它主要关注体系中领 导者与领导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7.)根据这一定义,全球层面有组织的行动有赖于这类特定范围内的问题对 体系各成员的向心作用。从长周期的整体理论架构出发,莫德尔斯基提出的全球问题可 解释为: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与现有秩序不相适应的且引起全球层面关注(主 要表现为各大国的强烈反应)的一种矛盾或冲突。每个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问题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复杂,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直至演变为全球问题, 其最终表现一般为权力分配失衡。
历史表明,表现为各大国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系结构性危机是全球问题和矛盾剧烈化尖 锐化的直接原因,而权力分配失衡通常又是由于某一地区性大国的崛起,进而影响到更 大范围体系的稳定,如18世纪俄国和普鲁士分别在东欧和中欧地区崛起,使得整个18世 纪欧洲的均势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近代大国的崛起一般可归结为两个因素作用的结 果: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逐步强化,二是经济、军事以及技术变革在国家利益原 则上的应用。对于新兴大国,经济、军事或者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扩大了其有 利可图的控制范围或其所扩展的有利可图的保护范围。(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54-55页。)当明确了实现这种利益增值所 要付出的成本和可预期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后,它往往就要扩大和加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 。(注: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取决于国家如何理解与变革体系有关的成 本与收益(即主观、心理成分),又取决于该国在某些领域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即客 观、技术成分),详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二章。但本 文所关注的并非国家对成分收益关系的分析,而是在扩张过程中其所占有的民族意识、 技术革新向体系传播的必然性,并由此引起的体系中独立主权与限制主权的矛盾。)体 系对新兴大国的扩张行为最直接的反应有两种:被侵略地区或国家起而反抗,催生相关 地区人民对本民族的认同,初步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概念;其他大国对新兴大国的 极度关注,并自觉地参与地区事务,适当遏制该国的行为以维持地区均势和本国利益。 这一过程对体系进化意味着三层含义:地区大国的崛起扩大了体系的界限,最终形成全 球体系;主权民族国家这一体系内政治单元的性质确定并进一步巩固;体系中逐渐发展 起一种交往原则,国际秩序渐渐形成。最典型的当属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首先国内革 命使法国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权民族国家,其次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使人民主权 的思想深入到整个体系,但是,由于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法国督政 府和拿破仑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号下将民族热情变成了民族征服的动力和工具, 它一方面强调本民族的道德和政治准则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们适用于所有其他 民族,并且应当由本民族加诸全世界。(注:时殷弘著:《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 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从某种角度说,具有先 进思想和技术的新兴大国成了阻碍体系进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近现代500年的世界历史 就是主权原则形成、普及和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最后,这种体 系权势分配的失衡也就成了该体系的全球性问题。
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也就是说,体系有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需要,或提供了一个 化解矛盾的环境或适当的位置,而填补这一位置的就是体系的进化性变革,在近代通常 表现为全球战争。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作出的反映是全球层面的,而有效参与者往往是体 系中的民族国家,其中被证明为最有能力的、最适合充当问题解决者的就是世界强国, 即领导者。综合而言,这也可理解为现有体系内部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内部因素 指体系本身的状态、各种周期性和进化性因素,诸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体系的全球问 题;外部因素指通过承认全球问题的存在而认可新的体系形势的一种趋势,它需要这种 环境来促使新的力量组成以解决全球问题。(注:即是长周期理论中体系进化三步骤中 的前两个步骤:信息的传播、体系形势的清晰化(a clar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 、议程的重新确定(a resetting of the agenda)和领导联盟的建立,最后是系统决策 的合法化。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Chapter 1.)
实现体系进化的主要机制
如上文所述,全球问题的突出要求体系提供一种机制以便加以解决,进而继续国际体 系的演进。在近现代,这种机制就是被莫德尔斯基称为体系宏观决策的全球战争。
作为莫氏长周期理论中周期性反复的主要表现,全球战争是近现代完成体系转换的主 要方式,又是实现体系进化的主要机制。莫德尔斯基本人明确指出,“长周期并不是战 争周期,而是通过全球战争的调节而形成的一种政治进程”。(注: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93.)他把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机制应用到国际体 系的进化中,将全球战争视为实现体系进化的“社会选择”。(注:他提出,生物进化 理论借助自然选择机制解释了物种起源及其特征,世界政治的进化则关注社会选择的机 制和过程,其重要表现有选举、竞争和战争。参见George Modelski,“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3),
September 1996,pp.321-342.)在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中,全球战争在过去500年的某些阶 段就是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在全球系统中起到促进“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 者存活”的作用;它选择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领导者,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不同的创新模 式和时代进步增长点。(注:George Modelski,“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1),Winter 1994,pp.18-21.转引自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 实证地看,历史上的全球战争有着固定的模式,即以谋求霸权的挑战国为一方,以维持 体系稳定(均势)的反霸同盟为另一方。战争的结束则宣告体系转变的完成,胜利方的某 一国成为新体系的主导国。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莫 不如此。但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全球战争的结果往往是确立或加速体系的进化,使体 系呈现出一种螺旋向上、更符合生产力发展原则的进化态势。17世纪英荷两个海洋国家 的崛起使得欧洲体系向世界性全球性体系演变,而通过1689-1713年的反法王路易十四 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不仅完成了新领导国的选择,而且确立了以英国为首的海 洋国家的全球主导地位,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全球互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启 蒙运动掀起了真正意义的民族主义,主权平等、国家利益至上等观念逐渐成为各国普遍 接受的国际交往原则,而通过拿破仑战争,这些观念进一步确立,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主权国家体系渐渐成熟。
同时,通过全球战争的选择产生的新领导国选择性地继承前周期的经验,最终具备足 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政治局面的技巧、资源和动力,这主要表现为体系领导国领导方式的 进化式转变以及由它主导的体系秩序的发展。以连续两个英国周期和美英之间领导地位 的交替为例。凭借英法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继承战争,英国成为欧陆事务的主导国和全球 海上霸权国,战后建立了乌得勒支体系,同时也找到了海陆政策之间的平衡点:在确保 海外扩张的前提下,有限地干预欧陆事务,维持欧洲均势。但到18世纪70、80年代,英 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使其在国际上几乎孤立,这与它传统的基于均势原则所取灵活 的结盟政策格格不入。可它很快认识到这点,之中的教训使其在第二周期中娴熟地运用 均势,成功地维持住了全球领导地位。到19世纪末期,当时德国正在破坏欧洲均势,但 英国却将欧陆事务让步于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体系并建立壁垒以维持印度、非洲及中东的现状。这为新近崛起的美国提供了借鉴,借助制度化的教育—科学—技术网络优势成功地主导了战后秩序的重建。美英两国三个周期的主导很好地说明了过去以全球战争为选择机制的领导国的自我教化功能。
从形式上看,解决由全球问题所带来的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并完成体系进化、更替的是 全球战争。但实质上,全球战争这种机制并非是纯粹的,它的前提是各种革新因素的综 合。莫德尔斯基本人也指出,解决全球问题实现体系进化的是全球战争和革新因素两者 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全球问题因革新因素而起,如民族主义的兴起、核武器的出现, 又由革新因素来解决。因此可以说,革新因素体系进化更替的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冷 战两极格局以非战争方式终结颇能说明这一点。根据莫氏长周期的演进框架,虽然冷战 格局的转换过程不是他所称的全球战争阶段,但它反而很好地说明了体系本身的进化功 能。毫无疑问,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和核武器的出现等诸多革新极大地影响了格局的终 结方式。
综合而言,作为体系转换的主要方式,规律性爆发的全球战争成功地解释了过去500年 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作为体系进化的主要机制,它维护并加速了体系的进化。当然, 推动国际体系进化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全球战争之外,还有工业科技、社会思想 、各国领导人的心理素质等因素。莫德尔斯基把这一系列复杂的动因都集中到长周期的 框架之中,最后是全球战争实现了体系的进化。
结语
作为对世界历史的一种理解模式,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对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分析 可谓独到,它向我们展示了国际体系演变规则、有序的一面;同时,莫本人在构建其理 论的过程中也强调:体系的周期性变革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轮回,全球战争也不一定会宿 命式地爆发,体系变革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政治性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因为国际政治体系具备进化式学习的特性。(注: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pp.93-98,223-224.)但是,莫氏长周期理论自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争 议的焦点也正如莫本人所料,其理论被视为宿命式的、缺乏发展性的理论。公允地说, 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不是以一系列业已受到历史事实科学验证的假说为基础的,而是 根据对历史经验的观察作出的归纳和总结;它并不也无法涵盖国际体系演进的所有方面 ,而只是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毕竟,重大的政治变革总是历史和一系列独特的、无法 预言的事态发展的综合体。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所言:“政治科学领域中以及国际 关系这一政治学分支中的大多数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某种分析性和描述性的 结构体;它们最多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概念框架和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分析和解 释某类现象。”(注:斯坦利·霍夫曼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新泽西1960年版,第40页。转引自罗伯特·吉 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页。)这也是本文的意图之一。
如果认为莫氏长周期理论在它所规定的框架内对历史的解释分析基本是合理的话,那 么就不能否认、至少不能完全否认该理论中所包含和体现的进化性,就像无法否认过去 500年历史所显现的进步一样。莫德尔斯基提出进化式学习的概念也为其理论的后续发 展留下了空间。他指出,“全球政治的进化是由在多样化政策组织和强化下的竞争与合 作机制达成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未来的观察方法,一种世界政治结构发展趋势 的指导”。(注:George Modelski:“What Is Evolutionary World Politics?”,1997 .http://www.faculty.washington.edu/modelski/)当然,理论总要与实践结合才能体 现它的价值。本文通过总结归纳莫氏长周期中的进化式学习而为其理论所作的“正名” ,也需要未来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