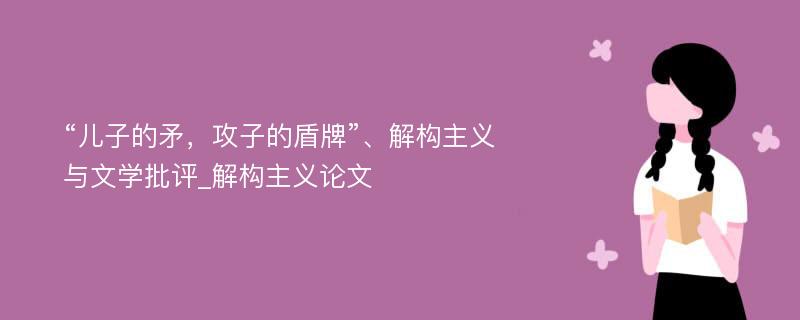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解构主义和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攻子之盾论文,以子之矛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到本文标题,人们不禁会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解构主义,一古一今,一中一外,风马牛不相及,怎能相提并论?然而它们在精神上确实是相通的。不惟如此,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相互辩诘驳难,西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降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叛逆和突破,无不包含有某种程度的解构活动,采用的多是或明或暗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自然,两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行为,是当代的一门显学,它具有目的上的彻底性,理论上的深刻性,意识上的自觉性和方法上的系统性。
一
说起解构主义,必然要提到雅克·德里达,两者合而为一,共生共荣,解构主义因德里达而勃发壮大,德里达因解构主义而成一大家。但解构主义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遵照“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的互文性原理,实际上也是特定语境中的一种产物。据艾琳·哈维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三个人对德里达产生过较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1](P127~147)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并对理性的局限性作了评析,德里达则深入一层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抨击和解构;尼采在《道德体系论》等著作中从词汇学和语义学等角度对形成善恶道德概念的历史起因、条件和基础探本溯源予以论辩,德里达则进而对是否存在固定不变的本源置疑,并相应指出意义具有不断地“隐现、流溢和扩散”的散播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选取Destruktion这一德文词,弃其“破坏”、“毁灭”等本义不用,而用其“颠覆性的分解”喻义,表示要把传统结构拆解得四分五裂以“去蔽”,德里达承继了海德格尔的定义,但没有采纳相对应的现成的法文词destruction,却另行创造一新词deconstruction以更明确地表达他的思想。然而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主义终究是史无前例的富有独创性的流派,哪怕他受到前人间接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通过他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解构姿态得以体现的。他为解构主义提供了哲学的纲领,以《知识考古学》著称的福柯提供了左倾的观点,保尔·德曼(Paul de Man)和他的同行以积极的实践形成了核心,他们一起开创了一片解构主义的新天地,在当代西方的思想界和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可说初成于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批评。索绪尔在他的书中说,书写语言只是为了表述口说语言而存在,语言的口说形式独自构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样他明白无误地确立了语言的口说形式高于书写形式的等级次序。[2](P1~10)但口说的语言一经出口即已消失,无影无踪,如何研究?即使现在有了录音机,能把声音留驻下来,反复播放,但用于语言科学的研究仍因能闻其声却不见其形而有种种不便。德里达在《论书写》一书中剖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比较对照了口说语言与书写语言的异同,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各自所寄身的物质形态不一样,前者为声音,后者为文字,而白纸上的黑字清晰持久,作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远较口说语言稳定牢靠。如此一来德里达把索绪尔所确立的次序予以颠覆性的解构,确立了书写形式高于口说形式的等级次序。[3](P94~119)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阐述的理论当然比上面提及的要丰富系统得多,德里达在《论书写》一书中对索绪尔所强调的西方传统一贯以声音与口语来贬抑书写文字的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也比上述的那一点要深刻全面得多。但德里达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也许可称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法。我们姑且把口说语言称之为矛,书写语言称之为盾。那么索绪尔夸的是口说语言的矛的锋利,贬的是书写语言的盾的不坚,按他的说法矛利盾脆,似乎并无自相矛盾之处。然而德里达证明,要满足索绪尔的语言研究的需要,口说语言必须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书写语言后方可细细琢磨探究,故而书写语言的重要性与口说语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是,则索绪尔的盾应该而且实际上是坚硬的,他的理论有内在的不妥之处,只不过索绪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构筑理论时无意中把它遮蔽起来了。
德里达揭露索绪尔理论中的内在矛盾的目的不在于证明其理论有谬误而不可信。他所从事的是一种解构性的批判(critique),而这种批判按芭芭拉·约翰逊的话来说,是要把文本内意指过程中的各种冲突的力量“逗引”出来,把一种理论在起始点上所掩盖的东西予以暴露,并据此置换和取代该理论所衍生的一切概念。[4](P141)德里达正是通过对索绪尔和他人的批判提出了他自己的用于置换和取代传统思想的诸如“在场的形而上学”、“语音中心主义”、“异延”、“补充”、“原型文字”、“播散”等解构主义的概念和术语,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二
如前所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具有强烈的理论倾向和哲学气质,而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则主要是美国耶鲁学派的贡献。该学派的四大主将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均有出色的文学解构的论著出版,如德曼的《读解的寓言》,米勒的《哈代:距离与欲望》,布鲁姆的《误读图示》,哈特曼的《超越形式主义》等等。其中德曼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在小学生中间》一诗结尾处的四行诗的解构性阅读堪称经典。[5l(P606~622)原诗行如下:
O chestnut free,great-rooted blossomer,
Are you the leaf,the blossom or the bole?
O body swayed to music,O brightening glance,
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
啊,根系粗壮、花朵怒放的栗树,
你是树叶,花朵,抑或树身?
啊,随乐婆娑的躯体,目光灼灼的流盼,
我们怎能辨分舞蹈和舞人?
对此诗的传统读法是把最后一行视为无需回答的反问句,其意是舞蹈美妙绝伦,舞者出神入化,两者融化为一体,犹如树叶、花朵和树身构成树一样不可分离,体现了形式与内容、创造者与创造物有机统一的观念。然而德曼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把最后一行看作亟待回答的真实问句,问者迫切希望知道他究竟怎样能把两者区别开来,从而能进一步探索两个个体在何种情况下会和谐一致或彼此抵牾。把叶芝的最后一行诗当作修辞性的设问句处理是较为简单无须多思的传统做法,而把它看作真实的问题对待则能引发复杂细致的思考。于是德曼这一问就问出了一条新的思路,得到一个传统阅读无法获取的结果。这就是解构式文学阅读的妙用。
或许我们能依此方法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来一番解构式的探讨。先重温一下韩非子的原文: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可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此短文的最后一句是一警句式的结论,人们对此似从未质疑过。但我们今天不妨来疑问一下:为什么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为什么非要把两者同立看成是荒谬的谵想而不是可以接受的事实?假如真有利矛和坚盾并存于世且相遭遇,结果将如何?也许结局是矛刺入了盾,但在矛头将折未折、盾牌将穿未穿时僵住了,于是同时满足了“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条件,两股力量相互抵消,处于均势状态。其实利矛与坚盾同世而立的现象比比皆是。阳刚无坚不摧,阴柔无物不克,阴阳同世而立,共处于太极之中。生命勃兴,无物能阻挡,死亡摧杀,无物能抵御,生死同世而立,各施其职。光明照亮一切,黑暗翳没一切,光明与黑暗同世而立。有人会说,白天光明,夜晚黑暗,两者时辰有别,并不同时并存。可有谁见过到了某一时刻天突然全黑了或全明了?可见白天里有黑夜的成分,黑夜中有白天的因素,两者并存,且逆向消长,而似明似暗的黎明与黄昏正是它们处于均势状态的时候。看来我们对“矛盾”一说的解构性思考有助于避免随意给某些事物扣上一顶“自相矛盾”的帽子、挥挥手把它们当作无稽之谈打发掉的简单化做法,而是一开始就不使两者敌对起来,通过仔细考察双方,妥善处理关系,让两者并立于世。利矛与坚盾不必非得相向而立,决个你死我活,斗个谁高谁低。两者完全可并肩作战,这样坚盾能起保护作用抵御伤害,利矛能发挥攻击作用克敌制胜。当今有不少“双雄争霸,一死一伤”转化为“强强联手,夺取双赢”的例子,怕也是冲破传统思维樊篱的这种解构性思考所结的果子吧。
德曼的范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内我们常常因循守旧困于传统思维而不自知,现在我们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解构姿态,对已被奉为法规、被虔诚地接受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审视与批判,以能另辟蹊径,有所创新。解构的目的不在于断然否定传统,正如德里达并不把索绪尔的理论说得一无是处,德曼也没有断言对叶芝的诗的传统读法毫无价值应予取消。解构主义求的是被传统所忽视或压抑的可能性受到重视并得以实现,从而打破传统的一统天下,求取新的发展。同理,我们对韩非子的短文的新解读也决不否定该文的原来意义,而只是表明该文还可以有别种读法,这种读法得到的新见解是有其意义和存在理由的,并且这种见解不通过解构式的阅读是难以获取的。
三
解构主义对传统阅读的自觉解构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勃勃生气,开拓了新的领域,以至作为一股思潮或一种流派它虽已过了鼎盛期,它的精神却因得到广泛的吸纳而继续留存,并不断开出新花。解构主义的奇葩之一是进一步颠覆了文学文本高踞于批评文本之上的传统局面,肯定了批评文本自身具有的文学性,终结了批评长期所处的奴婢地位。耶鲁学派的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评》一书中指出,“文学评论会跨越界线变得如同文学创作一样苛求……批评必须具有如此的洞察力与重新构筑语境的力量以至于它不应被视作他物的补充品。”[6](P201)不再是批评依附于文学,而是文学因批评而增添光彩,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批评,能使被有意无意掩盖的、甚至作者自己都未曾体察或酝酿的意义得以彰显。之所以能如此,德里达有过颇为简明透彻的阐释:[7](P94~119)
作家应用语言按照逻辑进行写作,而此语言和逻辑的自身体系、规则与活力按本义是他无法完全主宰的。他只有让自己按照某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被该体系控制后才能运用它们。阅读总是指向作者使用语言模式时他所掌握的与未掌握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对此种关系作者并无意识。此种关系不是明与暗或强与弱的定量分布,而是批判性阅读应该产生的一种意指结构。
换言之,作家用语言创作,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固然不能完全主宰他的语言的意义,作品完成后他更是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于是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对作品的解读。传统的文学批评对“作者未能完全主宰作品”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按着作者的意图、循着他的思路去分析作品挖掘意义。解构主义对于这一点有着自觉深刻的认识,因而它的文学批评常着眼于作者未曾意识未能主宰的部分做文章,以昭示作品中潜藏的意指结构。对文学作品的这种解构主义阅读常能取得别开生面、启人思迪、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活动范围广泛,课题繁多,其一是对小说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的解析。故事由按时间次序实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组成,情节指文本中按照叙述目的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安排和组织:或按照时序,或颠倒时序,或循因果关系单线直进,或由中心发散环环相扣,或从单一视角切入,或集多重视角叠合。故事有故事的逻辑,情节有情节的逻辑。按常理,情节的逻辑服从于故事的逻辑,情节的巧妙组合总是有助于故事的阐释,而故事则决定小说的主旨和意义。但解构主义批评家发现情节并不单纯地顺从于故事,两种逻辑有时各行其道,彼此相逆。彼德·布鲁克斯在《阅读情节:叙述的设计和意图》一书中指出如果故事和情节的两种逻辑出现不相调和的现象,它可能就是叙述的性质所致。[8](P137~157)他的话通俗地说,即叙述既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又要体现叙述者的情节设计,获取他所意图的效果,于是叙述本身兼有故事和情节的双重逻辑,两种逻辑的相合或相背直接蕴含在叙述之中。倘若两种逻辑发生矛盾,故事与情节出现冲突,问题往往出在叙述者身上,是他的道德标准、利害关系或心理状态使他所叙述的故事与真实故事不相吻合甚至截然相悖。传统的阅读一般注意到叙述中明显的逻辑而忽略了潜隐的逻辑,解构主义的阅读则把两种逻辑的不相调和视为叙述的内在特性加以考察,以求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作品。
利用叙述的“双重逻辑”评析某些文学作品时,我们有可能获得他种读法无法企及的意义和新见。亨利·詹姆斯的名作《拧紧螺丝》是一部类日记体的小说,其叙述者是一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她受聘前往偏僻之地的一个叫布赖的乡村庄园去照看两个孤儿。聘用她的人是个孤儿的叔叔,他对她的要求是全权负责处理好孩子和家务事,不来打搅他。她去了那儿,发现布赖是一舒适合意的庄园,管家格罗斯太太淳朴可亲,两个孩子迈尔斯和弗洛拉,出奇的美貌、聪慧和可爱。然而她不久就感受到一股邪恶势力的存在,并看到前主人的贴身男仆彼德·昆特和前任家庭女教师杰塞尔小姐出没无常。事实上此两人都已死去,但叙述者认为他们仍在活动,继续对两个孩子施加影响,要使他们陷入邪恶和罪孽的泥潭中去。叙述者决心全力拯救两个孩子。她相信弗洛拉在池塘边与杰塞尔小姐秘密相会,就赶去那儿,强行把弗洛拉带回交给管家格罗斯太太看管。她自己则在一个雨交加、雷电闪鸣的夜晚留在房内守护迈尔斯,与前来攫取迈尔斯的彼德·昆特的鬼魂殊死相斗,最终却发现迈尔斯已惊死在她的怀中。她所叙述的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从情节的逻辑来看,叙述者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家庭女教师,她忠于职守,对聘用她的人极端负责,千方百计地想把布赖庄园和两个孩子从已死的贴身男仆和前任女教师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至于她叙述中所出现的那男仆和女教师的鬼魂,只是他们身后留下的邪恶影响的象征性表现,从文学的角度考虑完全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接受。由此看来,叙述者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正面人物,她至少挽救了弗洛拉小姑娘。
但是从故事的逻辑看,事情并非那么一回事。小说作者亨利·詹姆斯把这乡村女教师的叙述放在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内,在这一框架层次上读者了解到女教师的受聘过程。女教师与聘用她的人见过两次面。第一次见面时,这个出身穷困、初次出门寻找工作的20岁乡村姑娘来到伦敦的一所豪宅里,面对一位只有在梦中或旧小说里见过的英姿勃勃而又举止随和的单身青年绅士,觉得既敬畏又亲近。但她没有立即接受聘用,因为她年轻,没有经验,深感责任重大,惟恐担当不起。然而丰厚的酬金远远超过她的期望,经过几天的犹豫和反复思考,她在第二次会面时决定应聘,承诺将自力承担一切,决不给他增添麻烦。当时那青年绅士如释重负,异常高兴,不由得抓住她的手,连声感谢她为此事作出牺牲。接着小说就转入该乡村女教师的自叙。于是从故事逻辑看,那女教师似乎对青年绅士产生了情意,她很可能潜意识地想赢得他的信任和喜爱,最后能与他缔结姻缘。她到了布赖庄园后使出浑身解数要博取两个孩子的好感,就是为达此目的。当她发现他们不愿听从她时,便怀疑原来的男仆和前任女教师从中作梗。她焦急的心理和扭曲的心态使她幻想出已经死去的两者的身影,并竭力逼迫两孩子与他们断绝关系。她把并不存在的虚幻景象强加于两颗稚嫩的心灵,结果是离异了弗洛拉,吓死了迈尔斯。由此观之,她决不是一个心灵高尚、充满爱心的好教师,而实际上是一个别有所图、心理变态、行为乖张的坏教师。
现在我们对《拧紧螺丝》这部小说有了两种迥然有异的解读。亨利·智姆斯并没有说明他这小说可有两种解读法,他当然更没有肯定一种读法而否定另一种,不然他的小说也不会如此模棱两可。此小说所以能有两种解读是因为故事逻辑与情节逻辑之间存在着差别,读者阅读时遵循情节逻辑,就得到前一种认识与感受,若他跟从故事逻辑,则得到后一种感悟和结论。此处两种逻辑互相解构,两种解读非此即彼,都有成立的理由。
我们或许也能运用这双重逻辑的说法来阅读唐代元稹所作的传奇《莺莺传》,而读出两种不同的见解来。按此作叙述的情节逻辑来看,张生“性温茂,美丰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分明是个正人君子。他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而使莺莺一家免遭兵乱之难,因此得晤莺莺,一见之下,“自是惑之,愿致其情”,藉红娘从中牵桥搭线,终与莺莺缱绻于西厢。之后张生以文调及期,欲西去长安求取功名,莺莺“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第二年,张生“文战不胜,遂止于京”,也不回蒲与莺莺相聚。文中说,“张之志,固绝之矣。稹特与张厚,因徵其辞。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可见张生并不为自己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做法感到愧疚不安,而认为是理由正当的明智之举。元稹在文中也肯定了这一点:“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可见以叙述者的身份在文中出现的元稹通过情节安排把张生描写成一个堪称楷模的“为之者不惑”、“善补过者”的正面人物。
然而按照故事的逻辑看,尤其是采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解构法阅读此作,只怕会看出一个自私自利、行为卑劣的张生来。不是说张生是“非礼不可入”、“终不能乱”吗?可他初见莺莺之后,便按捺不住,急不可待。红娘对他说:“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生回答说:“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可见他不管礼仪,只求自己情欲的立即满足,根本不顾及莺莺的身份和利益。莺莺多情而达理,她“朝隐而出,暮隐而入”与张生相会于西厢几一月后,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虽则莺莺愁怨之容动人,然“宛无难辞”,完全是一个举止有节的识大体的女子。张生在长安贻书于莺莺,她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张生“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张生却“发其书于所知”,把儿女私情任意公之于众,“由是时人多闻之”,这岂非是对莺莺一片真情的不尊和亵渎?不惟如此,他还对元稹和他人大谈“尤物祸害论”,为自己抛弃莺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甚工刀札,善属文”,“艺必穷极”,“言则敏辩”,且“善鼓琴”,而张生“往往自以文挑之”,莺莺却“亦不甚观览”,后张生赴京“文战不胜”,可见莺莺才艺当不在张生之下。极可能张生自知不及,出于妒忌心理反咬一口,说“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他在骗取了莺莺的身心之后,竟然污蔑她为“妖孽”,有何德可言?所以根据故事逻辑来判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元稹所以把张生描写成正人君子,完全是他身上的男权主义思想在作怪。
上述对《拧紧螺丝》和《莺莺传》的评析从某种角度讲即是以叙述的故事逻辑之矛攻它的情节逻辑之盾,以求得一种有异于习常的理解。一般地说,解构主义的文学阅读在于揭示被习惯阅读势力所压制的差异力量,并指明习惯势力与差异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攻防构成了解构阅读的意指过程的基础。对于这差异力量的承认不仅要求我们重新论析文学作品的语言及其意义的形成,而且促使我们重新评价已存的文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四
人们并不把解构主义简单地当作一种方法运用,它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拾起、放下或玩弄之物。必须把它理解为“实践智慧”,即一种能使人们对付某种局势的智慧。我的意思是,我们似乎总是处于传统的羁缚之中无法解脱,而解构主义正是我们应对这种受限定的生活的一种途径。这就是为什么说解构主义争论的并非知识和真理问题,它所针对的是权力和权威问题。解构主义并不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某种方式与它相处。
杰拉尔德·L·布伦斯在他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阐释学》一书中如是说。[9]解构主义是一种实践智慧,它遵从批判的策略,实行策略性的批评。它认为语言内在的歧义性决定语言所表达的知识和所阐释的意义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解构性。任何文本都自认为代表真理,意欲确立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力图把内在的异己力量抹杀或遮掩掉,从而能以统一的声音和面貌对外。解构主义旨在证明,如果对已被接受为正统的世界观、意识观和语言观仔细检视其细节的话,或许另一幅图画会呈现在我们眼前。解构主义并不自认它所展示的新图画更有真理性,但它针对权力和权威压制差异以造成知识和真理一统天下的幻象提供了一套戳穿幻象揭露矛盾的有效法则,点明正是文本对权力和权威的渴望埋下了它自我颠覆和解构的种子。解构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明智的,它首先承认自己无能提供更彻底更正确的真理,同时也承认自己的文本用语言写成,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具有被解构的可能性,正如德里达解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著作《论书写》也早已成为解构对象所表明的那样。
解构主义问世与盛行之后对它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它对一切都置疑,一味热衷于解构,把人们抛在批评的荒野之中,一眼望去,无物可以信赖,事事不能确定,从而使他们迷失方向,无所适从,精神焦虑,惶惶不可终日起来。二、它专门咬文嚼字,拘囿于文本中寻找语言的“踪迹”与“异延”等,而忽略语境和历史对形成意义的作用,可谓是形式主义的新翻版。确实,解构主义的所谓“彻底性”也就是它的局限性。它立足于破,原本不错,但破之无度,不屑于立,或即立即破,无休无止,这就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的味道了。人终究需要有确定性的东西,哪怕是暂时的;破说到底是为了立,在更高的层次、更合理的基础上有所立。所以解构主义的运用必须有个恰当的分寸,方能于人于己都有利,而这也正是历史的要求。解构主义在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天庭里大闹一番、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之后,现在多少收敛了些野性,在保持锋芒的同时,显得成熟稳重了。目下它虽已过了巅峰期,但活力犹存,余勇可贾,且其合理的内核也已被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吸纳和应用而继续施展影响。公允地说,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智慧、一种评析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已经融入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血肉之中:相信它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也能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09-12
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索绪尔论文; 德里达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