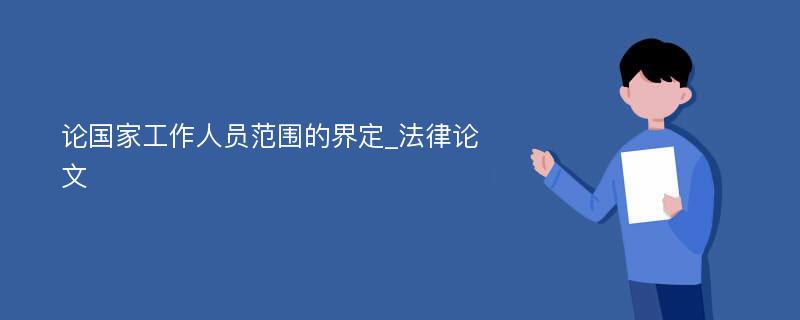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工作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刑法典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对于该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具体司法机关均存在不同认识,同时,这一相对过于概括的法条规定也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不少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具有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逻辑关系
根据1997年刑法典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两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可称为准国家工作人员。依照这一规定,结合新刑法典分则中的某些具体犯罪规定(如第397条的玩忽职守罪), 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个概念,即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刑法分则中,有的条文使用国家工作人员,有的条文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应当准确理解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即国家工作人员是上位概念,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则是下位概念。如果分则具体条文在犯罪主体上规定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即意味着该犯罪主体即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准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分则具体条文在犯罪主体上规定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意味着该犯罪主体并不包括准国家工作人员。简而言之,国家工作人员中包含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国家工作人员却不一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注:参见侯国云、白岫云著:《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在理解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逻辑关系时,庆当避免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即从刑法第93条规定看,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也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同一概念。从条文的逻辑性上分析,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却不能做这样的理解。例如,在实践中处理玩忽职守罪时,就有人这样认为,刑法第397条定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同一概念;同时,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等,所以,这些人员也可以是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这样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就是出于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逻辑关系上的混乱认识而得出的。
二、关于“国家机关”的范围界定
根据1997年刑法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如何界定国家机关的范围呢?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其一,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系统的各级机构(注:参见敬大力主编:《刑法修订要览》,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其二,认为国家机关除了上述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队内机关以外,还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以及政协的各级机关(注: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0页。)。其三, 主张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中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如石油天燃气总公司、电力总公司等)。这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从事的管理活动事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排除在国家机关之外。至于那些名为总公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并不适用企业的经营机制,而是依靠国家行政拨款,从事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所以其本质上仍属于国家机关(注:参见侯国云、白岫云著:《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国家机关”的范围,必须基于现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必须具有法律根据。依据我国宪法第三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应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军事机关。而且,在宪法中,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一样,都是和国家机关相并列的。例如,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另外,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 条就曾明确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尽管从我国的政体和国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从其性质上看,它毕竟还是一个政党,而不是国家机构。所以,还是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视为刑法第93条中所指的国家机关为宜。至于目前在我国存在的所谓名为总公司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我们认为更不应视为国家机关。尽管这些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存在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不断深入,作为政企分开的改革要求的具体体现,这些原先的行政管理机关正在逐步地转变成为一种国家的经营管理组织,其管理经济的模式也逐步地摆脱原来的行政管理而转向经济管理。所以,尽管这些组织在目前仍可能具有原来的行政机关的痕迹,但从其性质以及发展来看,把它们视为国家的行政机关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1997年刑法典第93条中所称的国家机关,就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务委员会;国家行政机关,就是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种管理机构;国家审判机关,就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国家检察机关,就是指各级人民检察院;军队系统中的机关,就是对国家武装力量实行管理的各级机构,如国家军事委员会、四总部等。至于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中以及前述在原先为行政机关而现在为总公司的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应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不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三、关于“从事公务”的应有之义
根据1997年刑法典第93条的规定,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其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从事公务”。因此,“从事公务”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关于“从事公务”的确切含义,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注: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其二,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注: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0页。)。其三,认为所谓从事公务,就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注: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0页。)。
我们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适用于司法实践,则显得仍然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前所述,“从事公务”是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对它的正确理解,不仅关系到在刑法第93条所列举的一些单位中工作的人员哪些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更关系到我们对准国家工作人员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界定。因此,我们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理解“从事公务”时,不能简单笼统因辞推义,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来深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
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犯罪。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犯罪所侵犯的共同客体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它们都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一般认为,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及以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无论是职务廉洁性还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遭到破坏,其最终都将破坏国家管理职能。
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是由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联所导致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6页。)。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与公务是有区别的,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妨碍职务行为,破坏职务应承担的责任并不一定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例如,一个非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受贿,只是破坏了该公司的正常业务活动和公司人员在业务活动中的廉洁性,并不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但是公务行为则不同,它的范围却是有一定的限制,即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力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在该种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可见,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公务的范围要比职务狭窄(注:参见孙廉、尹伊君:《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论》,《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综上所述,刑法典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它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的公共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国家事务,也可以是社会事务和集体事务,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体、卫生、科技以及同社会秩序有关的各种事务的管理;二是具有国家代表性,即这种活动是代表国家而进行的,它是一种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而不是代表某个人、某个集体、团体的行为。换句话说,这种活动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或是国家权力的派生权力的一种体现。
既然“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就应当从这个本质特征出发来准确判断和合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并同时避免仅仅从行为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考察其是否国家工作人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人事制度的变革也日趋深化,聘任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一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只要他被聘任从事管理工作,他就是在从事公务。这种情况在国有公司、企业中已较为普遍。另外,基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很多国有公司、企业已实现全员合同制,打破干部群众的身份界限,管理岗位实行竞争上岗。因此,以干部身份作为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在当前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显然也不合时宜。例如,国有企业的检验员、化验员等,所从事的都是管理性工作,无论这些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只要被聘任从事这项管理性工作,就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
四、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准国家工作人员,是指现行刑法典中规定“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三种:第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关于“委派”
所谓委派,就是委任、派遣,即派人担任职务。只要是受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就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无论该被委派的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也不论其是委派单位的原有职工,还是为了委派而从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人员。
(二)关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97年刑法典第93条规定了准国家工作人员中有一种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此种概括性规定导致理论理解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不同认识。目前存在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认为此类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选举或者任命产生,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注: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0页。)。其二,认为这类人员指除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外的,其他根据法律规定对公共事务承担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如党务人员、人大代表及其常务委员会委员等(注:参见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其三, 认为从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性质及其所从事的事务只是一种集体事务的情况出发,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同时还认为,党务人员应当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不应视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该观点主张,所谓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指受委托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依法从事组织、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该主张强调了四个条件,即必须从事公务、必须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必须是受委托从事公务、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根据这个定义,这种主张进而具体列举了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陪审员、受委托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注:参见侯国云、白岫云著:《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200页。)。
对以上几种观点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均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值得再考虑之处。例如,第一种观点认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就显得与这些组织的性质及其在现实生活所发挥的作用不相符合;而第三种观点完全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之外,显然未能充分考虑这些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和所承担的某些具体职责。再如,第一种、第三种观点提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受委托依法从事组织、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此种提法具有合理性,但第三种观点却坚持必须是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观点,这就显得有些偏颇。
我们认为,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法条的概括性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着眼于法条中列举性规定所表明的共同特征,只有从这共同特征出发理解概括性规定,才能保证法条规定的前后一致性与内在协调性。基于此,作为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括性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含着与法条列举性规定相同的特征,即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由此出发,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界定必须紧紧把握这一本质特征。
如前所述,“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机关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立法意愿。申言之,从事公务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体现,非正常地从事公务(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前者如贪污、受贿,后者如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就会使国家管理职能遭到破坏。同时,一定的人从事公务,就使得这些人获得某种相应的特定的身份。立法机关为了保护在从事公务中所体现的国家管理职能不遭受破坏,就必须对涉及具有上述特定身份的人的犯罪加以具体规定,相应地,这种具有从事公务的特定身份的人便与一般人员区分开来,即成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1997年刑法典第93条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列举性规定比较鲜明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国家管理职能的考虑。国家管理职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职能、行政职能、经济职能等。国家机关的任务就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所以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当然是国家工作人员。至于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以及人民团体,它们都是由国家投资建立或是由国家拨款设立并维持的,所以对其中的国有资产应当加以保护,这些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实际上属于国家委派经管国有资产的人员,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国家管理职能,所以,这些人员就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的职责是保护非国有单位中的国有资产或者行使着某种监督职能,所以他们的活动与国家管理职能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这些人员也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基于以上思路,在界定其他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时,就应当紧紧抓住“从事公务”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这些人员一般就要视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如前所述,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等活动。对从事公务这一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划分:第一,从获得“从事公务”资格的依据上看,可以分为法定的从事公务、受委派从事公务、受委托从事公务。法定的从事公务,是指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基于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而进行的选举、任命或是考核录用等,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是指从事公务是基于委任或派遣,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托而从事公务,是指行为人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基于有关机关单位的委托而产生的。委托与委派之间具有区别:委派是委任派遣,是一个单位任命某人到另一个单位任一定的职务,它实际是任命,不过不是向本单位的任命,而是向外单位任命。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或者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委托则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的结果由委托者承担。在1997年刑法典第93条中,规定了受委派从事公务的情况,而未明确规定受委托从事公务的情况。第二,从所从事的公务发生的单位来看,包括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和在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前者如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后者如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
我们认为,由于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而从事公务的内涵在于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从事公务本身并不应受取得从事公务资格的方式的限制,也不应受在何种单位从事公务的限制。所以,只要能认定行为人是在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领导、监督,只要行为人的这种公务活动具有法律依据,那么无论是被任命从事公务,还是受委派或受委托从事公务,也无论其是否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都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另外,行为人无论具有其他的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由此,我们认为,1997年刑法典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应当包括:(1)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4)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由于情况较为复杂而不能简单看待,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职责主要是管理一个村、一个居民点的集体性事务。但是应当注意,除了上述职责以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还经常协助行政机关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代行一些行政管理事务。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成员这一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详言之,如果其从事的仅是本集体组织的事务,如管理村中或者社会居民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是,如果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管理计划生育、发放救灾、救济款物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上是依法受委托在从事公务,对其就应视为1997年刑法典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