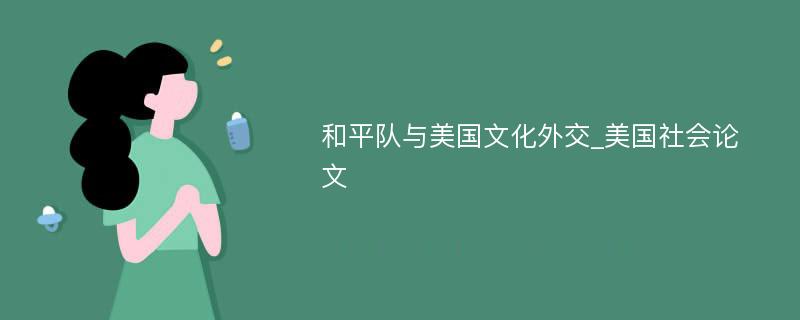
和平队与美国文化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和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外交就是一国政府向其他国家的公众描绘自己国家的形象,以实现本国特定的外交目标,描绘的手段包括资讯交流及人员交流。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即争取人心;而传播文化及价值观念,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外交的目的之一。同时,了解其他文化也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本国的外交决策更具针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外交受到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文化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抗过程中,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它出现在美苏冷战的高潮时期,体现了肯尼迪这位属于“冷战一代”总统的勃勃雄心,即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
文化外交与和平队的建立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心,并藉此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令政治人物颇有头痛,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低劣的素质。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和对南方和北方黑人的剥削,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① 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像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②。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他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他的拉美之行的境遇,是当时美国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和没有经验、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尽管是虚伪的但确是有效的,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③。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也是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④。
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他们“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⑤。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外交队伍中,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这些特性激发了我们很多国际政策。”⑥ 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指出:“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⑦
另外,作为肯尼迪政府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⑧。和平队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软”性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湮灭它在对外政策上的贡献。”⑨
作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莱弗十分重视文化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谈到冷战对手时说:“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进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为实现拯救所有遭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民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国际紧张状态,同共产主义世界建立一种新型的公众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间富于建设性的谈判达成协议。”⑩ 在另外一个场合,施莱弗又谈到,“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于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11)。
争取人心——和平队工作的核心
作为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赢得所在国家公众的好感,为美国赢得这些国家的民心。和平队工作的特点,有助于实现美国决策者创建和平队的初衷:
第一,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受援国工作,他们只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队还向志愿者提供全部的医疗费用及往返美国与东道国的交通费用。除此之外,两年的和平队工作结束后,志愿者还能够领取6000美元,用于回归美国社会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受援国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受援国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受援国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受援国的好感。实际上,大多数与和平队志愿者接触的受援国公众都会被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并对其做出相当高的评价。如《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就将在中国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的名称是“中美友好志愿者”)称为“劳动模范”。(12)
第二,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受援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如占志愿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队教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或职业学校;医生或护士则是活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层医院;而那些技术人员更是深入到农场、畜牧场、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受援国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的外援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受援国公众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地转向了受援国的普通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受援国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覆辙。和平队志愿者的这种行为方式,赢得了所在国官方及公众的好感。20世纪60年代的泰王国外交部长他那称赞说,和平队志愿者“不是与我们的人民一起生活在宾馆里,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农民的小棚屋里,与他们共享食品和茅舍”。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认为,树立这样的形象也许正是和平队最持久的贡献,“它体现了我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自私的社会,而是一个关心其他人的社会”(13)。美国的决策者希望透过和平队志愿者,让受援国人民看到美国及美国人的另一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平队志愿者通过自身的努力,确实为受援国基层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196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调查协会对和平队在菲律宾的工作进行了调查和评估,结果“发现了志愿者影响的明显迹象,接受我们调查员采访的92%的地区确实引进了教学设备和新的教育技术,在53.1%的和平队社区创立了奖学金,并以各种方式的物质援助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比例较小的和平队社区认可了和平队其他的创新:社区发展项目(51.3%),各种方式的志愿者组织(42.3%),娱乐设施(38.9%)”。该调查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者确实对所在社区产生了影响”。而同期,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康奈尔大学的评估组对活动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和平队进行了追踪调查,认为有志愿者工作的社区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发展要快三倍,“和平队项目对其所针对的社区确实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响”(14)。
和平队工作最大及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是在教育领域。和平队教师给受援国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扩大了教育范围,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不仅从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师奇缺,而且政府也不能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和平队教师就成为填补这些新兴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在喀麦隆,和平队教师进入该国的1962年,该国只有3所中学共882名学生;到1965年,该国中学数量就增加到14所,学生人数也上升到2250人。尽管多数新开张的学校是由教会所建,但教师则主要是由和平队志愿者担任。喀麦隆教育部长称,“由于和平队志愿者的到来,喀麦隆的教师问题得到了解决。”(15) 在埃塞俄比亚,300名和平队教师于1962年充实到该国中等教育领域后,使得埃塞俄比亚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分布在埃塞俄比亚所有城镇的中学里(16)。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队不同于世界银行,也不同于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技术或设备支持,它的视点在于那些被一般援助机构所忽视的乡村和小城镇,在于增强人们的自立能力,帮助相对弱势的群体改善生活条件等等。因此,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或某一地区这一层面上,它所带来的主要是微小的量变。然而,正是这种微小的量变,却能带来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对此,哥斯达黎加总统卡多佐·奥迪奥指出,尽管和平队在帮助哥斯达黎加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带来的是理解,那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建立不同与以往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我确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里,和平队志愿者有助于替代曾经到达过这里的军人(指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的美国军队——引者注),呈现美国人民的另一面。”(17)
和平队与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输出
和平队第一任队长施莱弗对和平队的榜样作用深信不疑,他认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仅仅是作为志愿的和熟练的工人,“而是作为最强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范……,他们不仅是被要求去帮助那些年轻国家的人民取得经济独立;他们还被邀请去重申我们对所有人民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他们还被邀请去展示我们民主社会的革命天性。”(18) 和平队要向受援国公众展示,并帮助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展示,在反对无知、贫困、疾病及各种压迫的斗争中,“民主方式是最终的和最成功的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⑩在和平队所开展的各类项目中,社区发展项目无疑是向受援国展示的典型案例。
社区发展计划的最初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停滞了几百甚至上千年,使得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在智力上麻木不仁,毫无创新精神,具体表现为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个体对生活没有信心,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不能独立地采取行动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这种广泛存在的消极和冷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平队的官员科比·琼斯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人的大脑的贫困”。如果和平队要想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必须首先救治“人的大脑的贫困”。在琼斯看来,和平队志愿者就是完成这一使命的理想工具,因为志愿者代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可以通过展示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动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的根基。由此,弗兰克·曼科耶维茨这样为和平队的社区发展计划做了定位:“我们的使命是本质上的革命,一场我们被授权进行的、在国家社会和经济模式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只能通过灌输和平队所代表的一种革命精神来实现”(20)。按照曼科耶维茨的设想,社区发展计划的实施将彻底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使它们更加接近美国的模式。
显然,和平队社区发展计划的政策制定者笃信美国文化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并希望志愿者能够将这一文化传统带到发展中国家,以弥补这些国家文化中的缺陷。如受美国国会委托对和平队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科罗拉多大学在其报告中就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该报告指出:“我国人民有一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传统,他们知道如何审时度势即通过有效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我们在学校和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吸收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年轻的美国人也有组织起来完成工作的经验。然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生活在其他文化类型及家长制的外在统治下的人们所缺乏的。他们希望享受变化带来的成果,但是,面对现实、分析现实、制定行动计划并按照计划行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育。这种能力是成功的‘制度建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社会的进步依赖于这种制度建设,包括创立政府、教育和工业制度。”(21)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平队志愿者被视为美国社会文化的完美传播媒介,通过志愿者的示范作用,向东道国的人民展示美国人是如何征服各种边疆的,并试图使他们确信,如果以美国为榜样,他们同样可以做到美国人已经做到的事情。
而对于和平队最大的单个项目——教育领域而言,其文化外交的特色更为明显。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和平队志愿者,无论是从事英语教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学,抑或是自然科学教学,他们都在课堂上或课余时间里,以各种方式向他们的学生描绘着美国。尤其是在和平队教师中,从事英语教学的志愿者所占比重最大。语言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文化载体,通过英语教学,甚至业余时间的娱乐活动,志愿者不知不觉中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及大众文化传播给受援国的学生。在冷战时期,和平队的官员也非常在意通过英语教学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重要官员、和平队驻埃塞俄比亚领队哈里斯·沃福德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和平队教师的这种功能,他在题为《英语作为学习和规范的语言》一文中说:“我认为,教授英语是和平队在埃塞俄比业或者非洲惟一最为重要的事业……当埃塞俄比亚完全进入了20世纪,它自然会有与我们小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将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讨论”。这里的“我们”自然是指美国而非埃塞俄比亚的方式。沃福德进一步强调:“让我把目标定的更高、更远。英语会成为促进20世纪发展最好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关于法定诉讼程序、平等保护法、言论自由和自治等方面的内容,你也不可能很好地阅读英语。”(22) 沃福德确实制定了一个很长远的目标,那就是将美国的政治文化体系通过英语教学传播出去,今天是埃塞俄比亚,明天是全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教师培养的很有可能就是某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和平队志愿者的学生成为一些国家的内阁部长、驻外使节、企业或贸易组织领导人,其中,加纳现任正副总统都曾受教于和平队志愿者。这些受美式教育的政治、经济领导人正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些国家的重大决策。这正是和平队所从事的文化外交的重大目标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肯尼迪总统高级幕僚小施莱辛格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分析说:“看到那些志愿人员把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的榜样传到穷乡僻壤去,人们会问,对于迄今尚未接近过民主思想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带去民主社会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未来的尼雷尔们和塞古·杜尔们,也许还有未来的恩克鲁玛们和卡斯特罗们,难道不会从他们的生气勃勃和献身精神中受到启发吗?”(23)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称:“对于作为美国及其价值观念的大使而言,没有比和平队更好的美国项目。”(24)
和平队与美国对外部环境的了解
了解外部环境、特别是了解美国需要与之打交道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会使美国的外交决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鲁门政府的国防部长助理、曾长期担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的罗伯特·布卢姆对此深有感触,他分析说:“为了有效地执行我们的国家政策,对有关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了解是必小可少的。”(25) 而作为美国文化外交重要工具的和平队,从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受援国的使命。和平队能够帮助美国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志愿者本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深入到东道国的最基层,与当地的普通民众居住在一起,因而对东道国的人民、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从和平队成立至今,归国的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17万人,再加上关注他们行踪的亲属和朋友,构成了一个关注和了解和平队国家的群体。可以说,通过和平队,首先使这一群体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并没有随着志愿者工作的结束而结束,很多志愿者因为对其工作的国家和地区的了解而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笔者访学所在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艾志瑞博士,其父亲曾经是和平队教师,在菲律宾从事教学工作长达三年,回国后开始从事菲律宾历史文化研究,现在是美同研究菲律宾问题的专家。而受其影响,艾志瑞博士也走上了研究东方文化和历史的道路,存中国近代地方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这些有和平队志愿者经历的学者,或深受和平队影响的学者,在美国的高校中还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次,通过归国志愿者,外面世界的情况被介绍给美国人民。很多志愿者对自己的和平队经历感到自豪和骄傲,归国后,有些人将自己的和平队经历记录下来,将他们了解到的受援国的人民、民族、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展现在国人面前,从而让更多的美国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并间接地让美国人对受援国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根据笔者2004年统计的数字,仅加入“和平队作者”这一写作组织的前志愿者就有593人,他们出版的有关自己和平队经历、或介绍受援国民族、文化、地理、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著作已经达到2292部。这些著作对和平队工作过的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使更大范围的美国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归国志愿者除了通过出版图书介绍外面的世界外,还成立了为数众多遍及美国各地的归国志愿者协会。根据笔者统计,美国建有自己刚站的归国志愿者协会数量已经达到17个,这些归国志愿者协会,通过其网站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讲座及座谈会,介绍志愿者的经历及受援国的文化。尽管其活动宗旨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自己的同胞分享和平队志愿者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再次,和平队的建立及其工作在美国大学里掀起了研究第三世界的热潮。和平队志愿者出国前的培训,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大学承担的,在整个培训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由该大学里的学者和受援国的学者对志愿者的语言进行强化训练,并介绍受援国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等。在训练过程中,来自受援国的学者与美国大学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激发了美国大学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趣,在此基础上,美国大学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大学的交流,部分美国大学还陆续设立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项目。例如,到1963年,北伊利诺大学先后培训了三批赴马来西亚的志愿者。其间,马来西亚政府派遣了6名教师到该大学教授这些志愿者语言,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及风土人情,而北伊利诺大学则派遣5名教师访问了马来西亚。这5名教师回国后,立即启动了一个东南亚研究项目,当地的报纸也开始大量发表关于东南亚的文章,从而使伊利诺这个美国内陆地区的人民对东南亚有了更多的了解。几乎在每一所与和平队合作的大学,其训练的志愿者被派往哪个国家或地区,它往往成为研究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学术中心。上述研究对美国人民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后,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机构之一,和平队为美国政府培养了大量了解国外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涉外人才。根据1985年美国国务院统计,这一年国务院招募的工作人员有10%来自和平队归国志愿者;这一年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AID)总部及海外工作的归国志愿者超过1000人。到1980年,10万名归国志愿者中有15%是在联邦政府的国内或国外机构中任职;在国际开发署,其雇员有12.5%来自归国志愿者。在哥斯达黎加,国际开发署的工作组成员53%是前和平队志愿者;在喀麦隆,这一比例达到了40%;在牙买加,比例是28%。在国际开发署驻55个国家的工作组中,每一个里面都有前和平队志愿者。为此,国际开发署主任道格拉斯·本尼特笑称:“和平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开发署的面孔。”即使在世界银行这样一个尽量避免过多雇佣美国公民的机构里,前和平队志愿者也占职业雇员总数的5%(26)。还有个别较为突出的归国志愿者,被选入了美国国会,或被遴选为美国内阁成员,成为美国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这些“外国通”在协助制定美国对外政策时,无疑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也使得美国外交政策更容易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和平队是肯尼迪政府推行文化外交的产物,其意图是通过和平队志愿者所体现出来的美国文化,改善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赢得受援国的民心,并让受援国公众更多的接受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外交的副产品,和平队也让美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并为美国的涉外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外国通”,这对美国外交决策同样大有裨益。
注释:
① John Spani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Washington,D.C.:CQ Press,1988,p.147.
② Elizabeth C.Hoffman,All You Need Is Love: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1960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8 - 29.
③⑨ Sargent Shriver,“The Peace Corps' First Two Years,” John F.Kennedy Library(hereafter cited as JFKL),Box86.
④ William J.Lederer and Eugene Burdick,The Ugly American,New York:Norton Company,1958,p.284.
⑤ David Burner,John F.Kennedy and the New Generati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8,p.85.
⑥ Sargent Shriver,“The Best Job in Washington,”JFKL,Box86.
⑦ “Kennedy's Speech to Peace Corps' Volunteers,”JFKL,Box86.
⑧⑩(11)(18) Sargent Shriver,Point of the Lance,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4,p.7; pp.28-29; p.48; p.50.
(12) 《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19日。
(13)(14)(20) Gerald T.Rice,The Bold Experiment:JFK's Peace Corp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5,p.289; p.285; p.167.
(15) Julius A.Amin,The Peace Corps in Cameroon,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13.
(16) “New Initiativ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anel Discussio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18,1966,p.89.
(17)(26) Milton Viorst,Making Difference:The Peace Corps at Twenty- Five,New York:Weidenfeld & Nicolson,1986,p.182.
(19) “Statement of Robert Sargent Shriver,in Chicago Illinois,May 17,1961,”JFKL,Box85.
(21) Albertson et al.,“Final Report:The Peace Corps,May,1962,”JFKL,Roll6.
(22) David Hapgood,Agents of Change:A Close Look at the Peace Corp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8,pp.53-54.
(23) Arthur M.Schlesinger,Jr.,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p.609.
(24) Julie R.Hirschfeld ,“House Passes Peace Corps Expansion Bill,” CQ Weekly,03/06/99,p.565.EBSCO Datebase.
(25) Robert Blum ed.,Culture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63,p.3.
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国际志愿者组织论文; 社区志愿者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