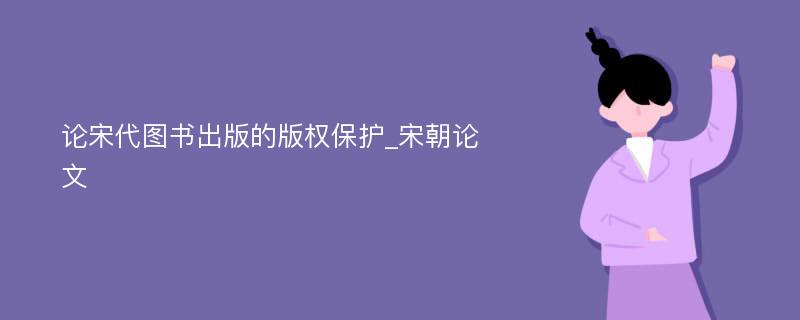
论宋代图书出版的版权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版权保护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0)02—0049—10
一、研究现状
近代以来对宋代版权问题的学术关注,始于清代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年)在其《书林清话》卷二“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文献记载。他在此文中披露了几条十分珍贵的宋代版权史料,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宋代版权问题最基本乃至仅有的几条史料。但是叶氏的贡献仅在于此,他并未从近代世界版权意义上作出任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及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以来,学术界、国家与社会对版权乃至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宋代版权问题的研究也明显增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一些论及宋代出版史的著作中有所研究,如郑成思先生之《知识产权论》、周宝荣先生之《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国版权研究会之《版权研究》等书中均有一定的论述。二是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念华先生之《盗版对宋代版权保护现象的影响》、祝尚书先生之《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邓建鹏先生之《宋代的版权问题》、周宝荣先生之《宋代打击非法出版活动述论》、徐枫先生之《论宋代版权意识的形成和特征》等。三是产生了以宋代相关内容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如四川大学林平博士之学位论文《宋代禁书研究》。四是产生了学术争论,如我国著名版权问题专家郑成思与美国学者安守廉在广义版权问题视阈中关于宋代版权问题的认识之争。
这些研究成果,从近现代版权观念及版权理论出发,对宋代版权问题作了学术考察。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在学术观点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对宋代版权问题的认识,尚需继续予以科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偏离乃至脱离宋代历史的倾向;(2)以宋代版权史料印证西方近代版权观念的思想及倾向;(3)对宋代版权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评价不一,差异较大,有的评论过高,有的干脆一笔抹杀;(4)历史与诠释之间合理性的“黏合”现象;(5)研究的非专业主义倾向。
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宋代版权问题从宋代历史实际出发作出新的诠释。本文认为,对宋代版权问题,既不可“揠苗助长”,给予过高的评价,也不可无视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作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非议”或评价。
二、宋代版权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宋代版权问题的产生,绝非空穴来风,也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科技、书籍生产等因素全面发展的产物。
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宋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社会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及条件和因素。宋代出版业既属于生产领域,又属于文化领域,具有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等多元意义。宋代整个社会的基本因子,都可以在其出版业中得以显示或蕴含。尤其是宋代社会的新质,更能在其出版业中得以体现。宋代出版业不仅是宋代物质生产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更是宋代精神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典型象征。它生产了技术,更生产了新的文化、观念与意义。
(一)政治因素
宋代立国之初,即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所谓“兴文教,抑武事”[1]394,崇尚文治。终宋之世,未改初衷。欧阳修于嘉祐五年(1060年)在其《免进五代史状》中称宋代为“文治之朝”[2]1706。这是宋朝文化事业——书籍出版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宋朝诸帝以天子之威,躬亲示范,在访书、藏书、著书、雕书(印书)、读书方面不遗余力,将之作为实行文治的主要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苛无书籍,何以取法?”[1]571“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3]253-254。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达,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结果。
宋朝政府的文化政策是十分明确的,是自由而宽松的。宋朝政府对书籍出版业的管理基本上采取了自由而宽松的政策。这是宋朝书籍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政治原因。宋朝书籍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必然要求规范书业秩序,有效管理并严厉惩治危害出版业的不法行为。无论是官方出版,还是私家出版、坊间出版,以及书院出版、寺院出版,书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一种有效的秩序及保障。宋朝的文化政策中也就必然包含并反映了这一书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宋朝政府对版权的保护,正是宋朝“文治”政策——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经济因素
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产物。
宋朝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矿冶、造船、制瓷、纺织等手工业部门均十分可观。在宋朝手工业生产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雕镂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讲还是在宋朝。例如在北宋京城东京繁华的大相国寺,在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鳞次栉比的手工业作坊阵营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业的身影。因此,宋朝手工业的发达不仅为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手工业提供了一般的产业生成背景与基础,而且也必然包括了这一手工业家族中的新锐成员。
宋朝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诚如姜锡东先生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大城市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毫不逊色。而中小城镇之多且发达,是前所未有的。”[4]283两宋都城开封、临安全盛时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人口数量超过了40~50万的水平线。洛阳、大名、江宁、潭州、福州、广州,居民数当在10万以上。两宋崛起的城市群,宛如“璀璨群星”,领先于当时世界。大都市之外,宋朝还形成了大量的城镇中心。
据研究,人口在1~10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100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3000个。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1150个以上。北宋小镇的总数肯定突破了1900个。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1200~1300个。南宋集市约有4000多个,北宋集市大约有5000~6000个[5]4-7。
宋朝的城市(镇)都是全国及地方上的商业中心,其商业功能十分显著。宋朝的商业行业也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时的400多行。宋朝城市的繁荣意味着宋朝已经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市民社会。这一市民阶层存在着巨大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的潜力与空间。与之相应,形成了宋朝的市民生活方式、市民消费方式与市民文化。货币功能与商业金融在宋朝城市的存在与繁荣中成为最活跃的因素。
宋朝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城市空间,从而使书籍生产中心赖以形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朝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这也正是宋朝书籍生产与销售中心主要集中于汴京、临安、成都、眉山、建阳等城市(镇)的原因所在。其实,宋朝城市之繁荣所赋予书籍生产乃至文化生产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如此直观、单纯,而是更综合、更丰富、更巨大。
宋朝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封建城市经济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一般商品(包括书籍商品)的商品属性及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货币功能。这正是宋朝版权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原因。
(三)文化因素
诚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6]《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245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7]201-206。
宋代出版业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宋朝书籍出版业的发达,是宋朝社会文明全面演进的结果,是宋朝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进步的结果。宋朝书籍出版业是宋朝社会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灿烂的一部分。宋朝由于普遍使用了雕版印刷术——一种书籍生产新技术,从而使书籍成为一种全社会普遍认可的精神产品、一种商品——一种具有极强传播力和创造力的知识与文化传播媒介。
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院出版、书坊出版四大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的机构、组织及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全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的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真正意义上全社会性质的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宋代雕版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成现实。这一点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之巨大之深远之丰富,实在是无法估量的。
宋代文化——书籍文化的发达,必然要导致版权文化的产生。
(四)法制因素
宋朝十分重视法制。终宋一代,所修法典至今有名可考者有242部,其中176部为官修,66部为私人修撰。梁启超先生称:“宋代法典之多,实前古所未闻,每易一帝,必编一次。”[8]27宋朝法典的大量刊行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因此,宋朝关于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及法律实践也应视为是宋朝法律建设的新的内容和新的进步。
(五)科技因素
宋代版权问题最直接的产生原因在于发明于隋末唐初的雕版印刷术在宋朝全社会的普遍应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书籍的大量生产或社会化生产。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9]287宋代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数学、天文、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
宋朝的科技进步不仅表现在诸多具体的科技创造及其应用上,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宋朝知识分子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科学研究意识上。伟大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布衣毕昇,就是以一个普通手工业生产技术工人的标准社会身份被沈括记录下来的。
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朝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朝前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而是宋朝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晶。例如印刷术,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制墨技术等相关技术的配合,就将无以施展其水平。实际上,印刷术应被理解为一种综合技术,即包含了造纸术、制墨术以及雕刻技术等相关技术在内的一个技术体系。细析之,如制墨术,则又必然涉及化学技术及烧造技术等技术。
宋朝的科技成就中,印刷术显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美国史学家亨利·查尔斯·李亚在其《基督教中圣职人员的独身史》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使只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人,都可以读懂神圣的经典,供其求知和解说,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够吸引读者,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遥远的地区。”[10]31,181宋朝正是此一意义上人类历史上这一知识普遍得以传播时代的开创者和实现者。
(六)书籍生产因素
宋代是我国古代书籍出版业的“黄金时期”与“经典时期”。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作出了伟大贡献。
宋代书籍的种类、产量及生产速度、效率各项主要指标,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文献记载中“今板本大备”[11]12798、“日传万纸”“多且易致”[12]《李氏山房藏书记》359-360、“近日雕板尤多”[2]1637-1638、“鋟梓遍天下”[13]《眉山孙氏书楼记》。元代理学家吴澄云:“宋三倍年间鋟板成市,布满天下。”[14]《赠鬻书人杨良甫序》《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文献通考》,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等公私书目的记载,足可窥知宋代图书出版之一斑。例如,宋高似孙《史略》记载:“濮安懿王之子荣王宗绰,聚书七万卷。”[15]82远超宋朝国家书目的记载数量。
宋朝书籍生产与传播中取得的成就,主要源于宋朝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术的书籍新生产方式。这种书籍新生产方式基于宋代社会封建商品生产非常活跃的社会经济基础,它使书籍生产成为宋朝社会中具有普遍价值和定义的一种精神商品生产。书籍在宋朝以被普遍认可的社会化商品的面目而客观存在。书籍作为一般商品,其价值与使用价值——成本、价格、等价交换、利润等商品属性,非常明确地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公共意识。尤其是宋朝异常活跃的坊间出版(民间出版),更是将书籍的商品属性空前地展示得淋漓尽致。
书籍一旦成为一种可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商品,可能创造的利润及财富也就势必引起宋朝社会生产者一致的期许和关注。在整个书籍生产领域中,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心理,也就势必会产生种种合法或不合法乃至违法的生产行为。
三、宋代书籍盗版现象及其他违法行为
宋代书籍出版业中的侵权行为,十分广泛,主要侵犯了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以下权利:(1)发表权;(2)署名权;(3)修改权;(4)保护作品完整权;(5)复制权;(6)发行权;(7)出租权;(8)展览权;(9)改编权;(10)汇编权。
宋代侵犯版权的主要表现有:(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2)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3)歪曲、篡改他人作品。(4)剽窃他人作品。(5)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又非法律许可,以改编、汇编、选编、注释等编辑方法使用他人的作品。(6)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7)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的版式设计。(8)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9)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
宋朝书籍生产中最大最普遍的违法行为即是盗版行为,包括翻版、盗印、窜改等。
宋朝书籍生产中的盗版现象屡见不鲜,不少著名作者的著作均有过盗版的遭遇[16]。例如,北宋早期思想家李觏(1009—1059年)在其《皇祐续稿》的序中即愤愤不平地写道:“庆历癸未三年(1043年)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心常恶之,而未能正。”[17]269这显然是一起十分明显的侵犯作者著作权的典型案例,给作者造成了长期的精神痛苦。
苏轼的作品,多次遭遇盗版。他生前从未出版过文集,然而书肆印行的苏轼文集竟达二十余种,有的还流传到了宋朝境外。宋朝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发生,即与苏轼文集的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结果给苏轼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灾难。苏轼在致友人信中披露了其作品遭到盗版的情况。他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18]《答陈传道》1574
傅增湘先生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中记载:苏东坡诗歌作品的闽中刊本,版式行格皆同,盖人士喜诵苏诗,风行一时,流播四出,闽中坊肆遂争先镌刻,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期于广销射利,故同时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于文字初无所更订也[19]《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苏诗跋》686。
王明清在其《挥麈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李仲宁的刻工,拒刻“元祐党祸”中的“党人碑”,理由是他的自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从中可以窥知苏轼、黄庭坚作品遭遇盗版的普遍性以及获利情况。
理学家张栻逝世后,朱熹为其编辑文集准备出版。不料朱熹“方将为之定著缮写,归之张氏,则或者已用别本摹印而流传广矣。遽取观之,盖多曏所讲焉而未定之论。而凡近岁以来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精语,反不与焉”[20]《张南轩文集序》3979。
宋朝盗版行为主要发生在民间书坊。书坊不仅盗印著名作者的作品,而且也盗印涉及国家政治机密的文字作品。只要有利可图,书坊就有可能伸出盗版之手予以盗版。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21]二之一二五,6558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二十八日,杭州上言:“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诏转运使鞫罪毁其板。”[21]二之二六,6508
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中,绍兴十五年(1145年)七月二日,两浙东路安抚司于办公事司马伋上言:“建州近日刊行《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政事。窃缘曾祖光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说。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并行毁弃。”[21]二之一五一,6574
宋代文人廖行之号省斋,著有《省斋集》。著名文人周必大也号省斋,盗版者故意“张冠李戴”,把周必大的大名署在廖行之所著《省斋集》上,以欺世盗名。今本《省斋集》潜敷跋称,嘉定己巳(1209年)春,向省斋之子(廖谦)“求其遗编读之,至骈四俪六,遽惊叹以尝载之《周益公表启》中。质诸小停,且称其先君子昔侍亲官沅陵,随兄仕澬阳,以笺翰供子弟职。既登第,尉巴陵,形之尺犊,履历可见。逮寺簿刘公守衡阳,委以图志,手泽具存。方其时益公已登政府,岂容远涉熊湘,俯从朱墨事也?此焉可诬!窃惟益公亦尝名斋以‘省’,岂书市之不审耶?抑故托之以售其书耶?又岂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22]《省斋集跋》
朱熹的著作更是数次被人盗印。淳熙四年(1177年),其《四书或问》刚一完成,“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故惟学者私传录之”[23]《宋朱子年谱》65。可见,盗版者早有预谋,采用卑鄙手段窃取作者的著作。《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24]438《论孟精义》,此书朱熹自印自销,因销路看好,义乌一书商以为有利可图,竟私自盗印起来。朱熹为此事致信求助于吕祖谦,信中说:“熹此粗如昨。岁前附一书于城中寻便,不知达否?纸尾所扣婺人番开《精义》事,不知如何?此近传闻稍的,云是义乌人,说者以为移书禁止,亦有故事。鄙意甚不欲为之,又以为此费用稍广,出于众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独熹不便也。试烦早为问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听。如其不然,即有一状烦封致沈丈处,唯速为佳。盖及其费用未多之时止之,则彼此无所伤耳。熹亦欲作沈丈书,又以顷辞免未获,不欲速通都下书,只烦书中为道此意。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25]盗印者的盗版行为使朱熹为此大伤脑筋,于此信可见一斑!《论孟解》,朱熹在《答苏晋叟》中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写道:“《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可四矣,问之当可得。”[20]《答苏晋叟》2810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行为令朱熹这样的著名作者遭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严重损失。
南宋初年,建阳书坊假冒浙江文人范浚(1102—1151年)之名,出版了一部《和元祐赋》的书,销路大畅。范浚得知后,在《答姚令声书》中说:“妄人假仆姓名《和元祐赋》,锓板散鬻……仆亦闻诸道路谓伪《和赋集》颇已流布……然似闻所《和赋》无一语可读者……近亦尝白官司,移文建阳破板矣。”[26]《答姚令声书》这是一起典型的假冒著名作者的侵权案件,直接侵犯了作者的人身权利,犯罪性质更为恶劣。
南宋文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讲过一个皇帝阅读盗版书的有趣故事,而所阅之书恰好是《容斋随笔》。
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因复裒臆说缀于后,懼与前书相乱,故别以一二数而目曰续,亦十六卷云。绍熙三年三月十日迈序。[27]215
“书生遭遇,可谓至荣”一句,含义丰富。问题在于,天下遭遇盗版的作者,有几人能有如此崇高无上的巧合!从古至今,有文献可考者,大概只此一人而已。迈洪此一序文,也肯定是自古及今天下书籍之序中绝无仅有的一篇妙文了!不过,宋朝书籍盗版之严重,于此可知矣。
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著作人的精神权利,而且也严重侵犯了著作人乃至出版人的财产权利。
有盗版就有反盗版。宋朝书籍生产中严重的盗版行为直接促成了宋朝版权观念的意义及版权保护的法律行为。宋朝的版权保护客观上因应于盗版现象的严重而涉及了版权的几乎所有基本方面,既包括著作人的精神权利,也包括其财产权利。
四、宋代版权保护的法制规范及案例分析
简论之,宋朝书籍生产中的版权保护,从权利主体角度考察,大概可以分为官方保护主体与民间保护主体二类,而以后者为更具有版权意义的保护主体。
(一)官方保护权利主体
即政府作为出版权利主体而应受到版权保护。宋朝对官方权利主体的版权保护,是宋朝整个出版政策及法制环境的一部分。宋朝自立国至灭亡,对书籍出版一直没有中断过必要的政策管理与法制管理。对官方权利主体的版权保护,正是其中具有新的生产意义及版权意义的突出篇章。例如,它同宋朝一直实行的禁书政策就存在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盖禁书即为保护,保护中寓有禁止。
兹以宋朝禁印历书及《九经》为例。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二十三日,“诏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28]2796。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十一日,“诏自今岁降大小历本,付川广福建江浙荆湖路转运司印卖,不得抑配……余路听商人指定路分卖”[28]2796。元丰四年(1081年)五月二十七日,“判太史局周彤奏乞令后应诸路转运司每年收到历日净利钱,并限次年四月一日以前,依条起发上京送纳尽绝。如违令,本路转运司取索点检究治施行。诏违限如上供法”[28]2797。其实,政府对民间印历的禁止早从唐代即已开始。《旧唐书·文宗纪》中记载,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版”[29]536。《全唐文》卷六二四中记载,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反映:“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30]458唐代民间私印历日已如此猖獗,宋代更是可想而知。
宋朝对民间私印历日的禁止是完全必要的。对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司天监)独家出版历日的版权保护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十分重要,民间私印历日则错谬百出,使得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这就破坏了历法出版的神圣性、专业性、权威性及科学性,诚所谓有违天道是也。一些论者不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殊性,以空对空,用法释法,以西方近现代版权的刀来削中国宋朝之足,严重偏离了中国古代历史实情,所言近于一己之空词,不足凭信。
五代时期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术出版的儒家《九经》,始于后梁长兴三年(932年),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22年始成。《九经》出版后,中央政府一直保护其专有出版权,禁止擅自翻印。宋代罗壁《罗氏识遗》卷一“成书得书难”条云:“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微,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监,熙宁后方尽驰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31]27事实上,所谓弛禁,也是有限度的,主要是允许国子监之外的政府部门雕印。自《九经》成书至方驰此禁(954—1068年),前后一百余年,《九经》的专有出版权一直受到政府的保护。对五代《九经》版权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部书是五代乱离中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印本《九经》,它同汉代熹平及其后的历代石本《九经》一样,均是封建中央政府专门出版的国家标准版本,旨在统一《九经》传播中出现的名称纰漏与差异。此种国颁版本,一般都是由其时著名的硕学鸿儒精心校勘的权威版本。所以,对《九经》版权的保护,岂止一个“版权”名词所能了得,其实是对《九经》文本质量的保护,是对《九经》的学术保护。一些论者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了解,拿西方人的帽子来罩中国人的头,所言空法,岂非盲人摸象乎!
针对上述绍熙四年(1193年)上奏盗版现象,下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21]二之一二五。
(二)民间保护权利主体
相对于官方而言,以著者个人身份及民间出版者身份而作为出版权保护主体者,即为民间保护权利主体。从现有文献来看,宋朝民间出版权利保护主体主要是著作人,其中又以著名的著作人为主,如前述的朱熹、洪迈、范浚以及三苏等。正因为他们是著名的著作人(作者),所以才更易遭致盗版,也才有更多的可能被历史文献记录下来。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代表宋朝一般的或全部的民间版权保护历史,这是因为一般人物或出版者在历史上很难被记载下来,以致文献无征而已。
清代著名版本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提供了几条民间版权主体申请保护的珍贵史料。
1.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叶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31]27-28
寥寥数语,表明了出版者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表明其时政府受理此类版权保护申请已有一定之规,而且政府在版权保护上态度明确,坚决反对盗版盗印,并将出版权视为出版者的一种私权,决不允许盗版者侵犯。虽然是眉人程舍人一宅的版权声明,但它决不是唯一的个案,而是当时坊间出版者普遍的版权保护内在要求。可以认为,此条版权声明反映了宋朝民间出版商普遍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宋朝版权保护的一般状况。
2.祝穆《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一卷。《自序》后有两浙转运司《录白》:
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劳心力,枉费本钱,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
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故榜。嘉熙二年十二月□□日榜。
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
转运副使曾□□□□□□台押
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31]28-29
这是一条非常完整的版权保护材料,反映了宋朝一般的盗版手法、著作人及出版人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政府受理版权保护申请及预防并处理盗版案件的整个过程。版权所有者经向政府申请并认定后,由政府部门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保护公文,并张贴在出版商聚集之地,如有违反者,即依法予以追惩。这一公文,其实就是宋朝政府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它不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且同时也保护出版人的权利。对于盗版者花样翻新的盗版行径,政府一律严予追究。著作权人和出版人在盗版威胁严重的环境中,只有借助政府的行政权力(包括司法权力)才有可能使其版权得到保护,有效防止盗版,并使盗版者受到法律的震慑与严惩。对于这样的政府榜文,出版者自然是奉若“尚方宝剑”。所以时隔二十多年后,祝宅出版的这4部书上,仍刊有版权保护的官方文告。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六月,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官府为保护祝宅出版的这4部书,在所发布的榜文中称《方舆胜览》是著者“一坐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已经“两浙转运使、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戟翻刊”,如有翻刊,允许祝宅“陈告、追人、断罪施刑,庶杜翻刊之患。”[32]6301这样的保护力度,在当时的世界书籍史上,恐怕也是最先进的。当然,宋朝版权保护中地方政府的颟顸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朱熹对此即有严厉的批评。
3.宋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三十卷。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曰:“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卯山罗使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汞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转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33]
这是一条宋朝国子监保护著作人与出版人的史料。著作人版权代理人是会昌县丞段维清,他通过自己的官方渠道请求国子监给予其先叔著作《丛桂毛诗集解》与此书出版者罗贡士以版权保护。国子监受理后,一方面发出公文(牒文),要求两浙路福建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一方面开出公文(公据)传予出版者罗贡士作为版权保护官方证明。本书《丛桂毛诗集解》著作权代理人段维清的版权保护申请理由表述得十分明确,即“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换言之,若书肆盗版,则既侵犯了出版者权利,又侵犯了著作者权利。史料表明,国子监乃至宋朝整个政府系统对于此类版权保护案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执法规范,这也是宋朝文官制度健全的一个体现。国子监在下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文中还明确了对盗版者的法治措施,即“追板辟毁,断罪施行”。这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订版)第四十七条中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没收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比《著作权法》之规定更为严厉。
著名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年)的著作遭遇盗版后,他的弟弟吕祖俭及从子吕乔年迅速编辑出版《东莱吕太公文集》四十卷,专门对付市面上的盗版伪作《东莱先生集》。吕乔年在《东莱吕太公文集跋》中曰:“自太史公(按:指吕祖谦)之没,不知何人刻所谓《东莱先生集》者,真赝错糅,殆不可读,而又假托门人名氏,以实其传,流布日广,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与一二友收拾整比,将付之锓木者,以易旧本之失。会言事贬,不果就。乔年追惟先绪之不可坠,因遂刊补是正,以定此本。……虽或年月之失次,访求之未备,未可谓无遗恨;至於绝旧传之缪,以终先君之志,则不敢缓,且不敢隐焉。”[34]《东莱吕太史文集跋》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上引书坊假冒司马光大名刊行《司马文公记闻》伪书一案,宋代朝廷即“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并行毁弃”[21]二之一五一,6571。
五、研究结论
宋朝产生了中国古代书籍生产与传播中比较显著的版权观念及相对成型的版权保护法制规范。可以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书籍著作者与生产者真正开始实现版权自觉的时代。
宋代版权问题是宋代商品经济与雕版书籍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了解宋代历史,就不可能对宋代版权的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安守廉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关出版的法令只不过反映了“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努力”,并认为这也是导致中国无法产生版权法以致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原因[35]。安守廉先生的这一观点,不仅不符合宋代的历史,而且也不符合中国清代的历史。这使我们怀疑安守廉先生对宋朝历史常识的了解与认识。宋朝雕版书籍生产的普及以及书籍的商品化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安先生严重忽视了这一历史实际,作出以上空论,使人难免再次产生“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联想。
宋朝的版权问题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宋朝的版权保护只有在宋朝的历史背景上才有它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至于宋代有没有产生出世界近代意义上的版权法以致知识产权法,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假设,因为宋代只能产生出属于宋代的版权问题。迄至清代,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所以安守廉先生的观点很可能犯了中国成语“削足适履”的历史的与逻辑的错误。
宋朝的“文治”政治总体上使其书籍生产的出版环境十分宽容,因而一直被称为中国古代书籍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虽然宋朝并未制定出专门的出版法,但是在宋朝的法律框架内,已经运用国家政权、法律以及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实施治理。从政府到民间,关于版权保护的一般观念已经普遍产生。眉山程舍人宅出版书籍上的刊语“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即是一句典型的版权保护语言符号。总之,宋朝已经形成了从版权及版权保护观念、法律申诉、依法断案、判决与执行乃至民间协调等一系列的版权保护程序。
收稿日期:2009—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