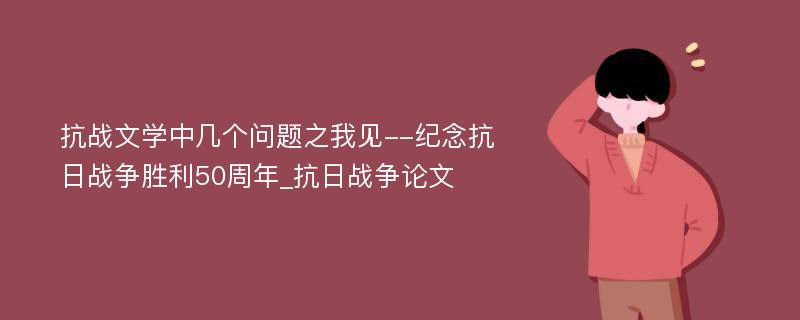
抗战文学几个问题的我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抗日战争胜利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抗战文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一个是时间方面的。从内容说,抗战文学的对立面,是“汉奸文学”,凡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或对抗日战争起了一定助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叫做抗战文学。从时间说,这种文学作品一定是要产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当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人们仍然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进行创作,那是不在抗战文学这个范围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种文学是“与抗战无关”的,它数量不大,可看作那一时期我国文学的支流,而主流则是抗战文学。
二
抗战文学有四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文学。在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斗争,狠狠地打击日寇以外,还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使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明显提高,生活有很大变化,不少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这为文学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文学作品最主要、最根本的接受群体。劳动群众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李有才式的“民间板人”、“民间故事手”,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取得了从未有过的紧密的结合。从文人文学说,根据地的作家队伍,大体由以下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进步作家,他们从大后方或者大城市(指抗战初期)来到根据地,溶入到革命队伍里,成了革命文学战士。另一种是在各根据地涌现出来的,如晋绥的马烽、西戎等人,延安的杜鹏程、王汶石等人,晋察冀的魏巍等人。赵树理虽然早在1930年前后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但他那时的作品发生的影响很小,所以也只能算在这群人之列。
第二个分支是“国统区文学”,或称“大后方文学”。像郭沫若、茅盾、田汉、老舍、胡风等,都是在国民党所统治的重庆、昆明、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的。他们一方面宣传抗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消极抗日政策,进行揭露和鞭挞。在重庆等地,成就最突出的是话剧剧本的创作,作家们借历史故事,影射当时的现实。郭沫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黑暗环境的指斥,曾经怎样地激动人心。在诗歌、小说等方面,也都产生了不少力作。
第三个分支是沦陷区文学。这又有几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东北沦陷区。这里的沦陷区文学,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就产生了,它的历史最长。但由于日寇统治的严酷和其他原因,原先的“东北作家群”,先后离开了东北,如肖军和肖红就到了上海,他们最重要的抗战文学作品是到上海以后,在鲁迅帮助下出版的。以后支撑着东北沦陷区文坛大厦的,是一些年轻的作家,如梅娘(孙加瑞)、袁犀和关沫南等。关沫南的《两船家》、袁犀的《邻三人》以及古丁、山丁、王秋莹的小说在日本翻译后,以《原野》的书名出版,连日本读者也体会到了作品中的反抗情绪和民主主义精神。再一种是华北和散居在华东、华中等地的沦陷区。这些地方先前的文学运动不够活跃,作家队伍相对薄弱。首先从青年人聚居的地方发出一点呢喃声,然后在报纸的副刊上,星星点点地燃起一些文学的篝火,明显的反抗是不多的,比较多的是情爱,他们以轻倩的情歌安慰读者受伤的心灵。梅娘于四十年代初到北平定居,其作品颇受读者欢迎,一时有“南玲(张爱玲)北梅”之称。第三种是上海“孤岛”。上海沦陷后,唐弢、许广平、李健吾、师陀等一批知名作家没有走,其中一些人是地下共产党员。这些作家在日本占领军文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以隐晦曲折的形式,表现人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和民族忧患,给人的审美意识是悲凉中透出正气。沦陷区文学的总的特色,是在高压下低吟,其反抗的烈火往往披一件灰色的外衣。
第四个分支是台湾文学。台湾人民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已有多年,抗战八年,只不过是那种日据文学的继续而已,它们有跟沦陷区文学相同的特色,又有其不同的特点。香港沦陷后的文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地作家在香港所写,如戴望舒的《狱中题壁》,另一种是当地人士所写。前一种,可以放在第三支里。后一种,由于香港长期处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它所表现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又与台湾的日据文学有相似之处,所以也可以划在这里。
三
抗战文学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上,有什么意义呢?
“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走过了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把旧文学改造成为新文学的阶段,一个是把新文学送到普通老百姓中去的阶段,或者叫文学与大众相结合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是全体国民的精神食粮,而不能仅仅限于一部分人享用。中国旧文学的根本弊端,就在于它只是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享用品,如鲁迅所说,成了“特权者的东西”,根本到不了老百姓手里,对这一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们已经有所认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这三种文学,核心是“贵族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倒“贵族文学”。经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新运动,诞生了一种新文学。但这种新文化,如瞿秋白所说,“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所以,从“五四”到二十年代后期,新文学还只停留在“交换文学”阶段,并没有找到它的真正的接受者,只是你写的我读,我写的你读。先觉们认识到了它的这个弊端,于是在二十年代末,明确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文学大众化,乃是文学寻找读者的要求,是“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发展、向深入推进的要求。
与此同时,文学还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早在晚清,人们就在议论文学究竟有什么社会功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要发挥教化作用,要给人以美感享受。陈独秀在前述引文中所说应该排斥的三种文学,是由于那三种文学已经成了单纯的消遣品。“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本身就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作用。“五四”以后,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二十年代,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需要文学来反映,也需要文学作为灯火来引导。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这种关系,对每一个正在发生剧变的社会和每一个具有社会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来说,都是必然的。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摆在我国作家面前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领土、中华民族如不奋起反抗就会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于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而要把这种心声变成物质力量,文学艺术便成了一种像轻骑兵一样的重要武器。随着日寇侵占地盘的扩大,人们利用文艺进行抗日宣传的声势也就越大。
为了发挥最大的革命功利主义,又使大众化显得更为迫切。上海革命文艺队伍关于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的1932年,便是这个关系的最好说明。大众化成了文学自身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学,从来都是多样化的,又从来都是有主流、主潮或说主旋律的,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我国文学中存在着一种不仅“与抗战无关”、也与当时的政治“无关”的文学,存在着一种主要写给知识分子享受的纯文学,但是,恐怕谁也不会否认,只有抗战文学,只有大众化的文学,才是主流。“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语文反对文言文,这是它走出的第一步,经过三十年代的讨论、摸索、实验,到四十年代初赵树理这位大众化的旗手的出现,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已经胜利地走上了第二步。在抗战文学的四个分支中,只有根据地文学充分具备着完成文学大众化任务的主客观条件,所以也只有在根据地完成得最好,赵树理也就成为根据地作家的杰出代表。由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所进行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根据地文学中所贯彻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到1949年以后,理所当然地居于统治地位,作家的创作方法和文学风貌,也是直接承袭根据地文学。这就决定了,我国五十年代的文学是根据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那种大众化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抗战文学把“五四”文学革命推向深入。作为抗战文学一个最主要分支的根据地文学,又为我国五十年代及其以后的文学奠定了基础。抗战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即在这里。
四
对抗战文学的研究,从田仲济先生《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出版(1947)算起,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这多年的研究成果不能说不丰富,但仍很难说使人满意。进一步加强对抗战文学的研究,我以为应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要有抗战文学的整体观。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真正把抗战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并不很多,大都偏重在某一个分支或某一个区域上。其所以要有整体观,首先因为抗战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文学的发展也是全民族的,文学问题的争论,文艺思潮的演变,都没有界限。比如1940年文艺界在形式问题上所展开的争论,就不论在大后方还是根据地,都有不少人参加,连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要“喜闻乐见”还是要“习闻常见”,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对赵树理大众化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次还因为,当时各分支之间的文学的交流十分频繁,既有人员的流动,更有书报刊物的流通。这种交流还表现在前述根据地的两部分作家之间。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能够很快地成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从大后方或大城市来的那批作家的影响和帮助;而从大后方或大城市来的作家文风能够转变,所写作品能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则又跟根据地成长起来的那批作家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第三,人们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实行国共合作,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作家,在大后方或沦陷区进行文学活动。比如1939年阎锡山二战区所办的《西线文艺》,许多作品都出自共产党人之手,他们同时还给根据地的文学刊物写稿,如果把各个分支孤立起来研究,对这部分人的研究就难免片面。
第二,要坚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去看待文学的大众化,也就是说,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近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赵树理写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是“迁就读者”。这是脱离开时代的要求,也脱离开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看待文学现象的结果。前已说过,“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二十年代,对大众化的要求和对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同时提了出来,以后愈益强烈。“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两个要求成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自觉追求,没有人号召,他们也会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要求上,必须从当时的现实出发,这也是个有无历史主义态度的问题。有些人用八十年代的眼光,去衡量四十年代的作品,从而得出“小儿科”的结论,这就违背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第三,发掘资料仍然是一项极其重要而且有很大迫切性的基础工作,必须用大力来做。据我所知,太行区的一些资料仍然存世,但很难找到,有的被当作“废旧物品”扔在一处,未作整理。还有,当年从事抗战文学活动的人,目前健在的,最小也在七十岁以上,许多人已很少写作。组织他们回忆,由专人记录整理,在当前来说,显得极为迫切。这是对资料的抢救,错过了时机,这一缺憾将永远无法弥补。从一些刊物上看到,台湾学者近年在抗战文学资料的整理上做了不少工作,这就又有一个加强交流的问题。
第四,加强对抗战题材创作问题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依然是许多国家作家的重要题材来源,而且不断出现精品。比如最近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的小说《辛德勒的方舟》改编的,它描写了主人公在二战时期如何保护了一群犹太人的故事。近十几年来,我国作家写了不少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它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但是比起其他题材来,抗战题材的作品仍嫌不足。有必要呼吁,抗日战争是作家的一块极为宝贵的题材矿藏,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去写抗日战争,必将会出现好作品、大作品。而为了促进抗战题材文学精品的产生,学术界必须加强对抗战题材创作问题的研究,以提升抗战题材作品的品位和艺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