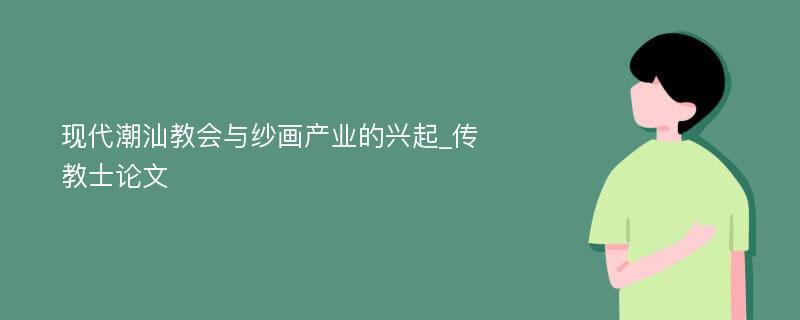
近代潮汕教会与抽纱业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汕论文,抽纱论文,近代论文,教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鸿生先生在研究历史上的尼姑群体时曾指出:“尼姑群中同样蕴藏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技术资源。”他通过考察宋代至清代尼姑群体的生产活动,发现莲花纱、宝阶罗(尼罗)和姑绒这三大纺织工艺出自尼姑之手。①与之相类似的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吸引信徒,同样在教团内部组织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如园艺、缝纫、钩针、制作蜡烛、编制草席和藤椅等等,一些西洋工艺也在此过程中传入中国。如19世纪中后期,抽纱与花边工艺即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沿海地区,包括烟台、青岛、宁波、常熟等地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20世纪初期也曾一度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乡村教会中传播。② 本文以潮汕抽纱为例,通过钩稽史料,力图梳理教会在当地信教妇女中传授技艺、组织生产经营,以及因技艺广泛传播而新兴的抽纱业在行业集中地、人员构成、生产组织乃至销售渠道等方面都深受教会和传教士影响的这一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抽纱工艺和行业对20世纪潮汕地区在多个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今抽纱工艺已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百余年间的“褪色”过程却让人莫辨其源。这种现象本身或许正是研究者应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所呈现的多层面相及其背后象征意义的原始动力。 一、潮汕抽纱的引入 晚晴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流行的抽纱工艺包括花边、补布、抽纱、刺绣和钩针(即勾花)。除了刺绣这一传统工种外,其他工种均由西方女传教士在19世纪80年代传入潮汕地区。将一部分纱线抽出,形成“轻盈、通透、淡雅”的艺术效果,③正是西方针线工艺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当地人因此在上世纪20年代正式用“抽纱”对译“Drawn-thread Work”④一词,用以统称上述各种西方针线工艺,而民间则称之为“番花”。又因为抽纱手帕在30年代是最大宗的产品,因此以抽纱工艺为生被称为“做手布”,抽纱厂亦被称为“手布厂”。抽纱工艺在西方被归为“白纱刺绣”(whitework embroidery)这一类型,因为它多用白纱线在白纱布上做十字绣、蕾花等工种。而传入潮汕后,受到传统潮绣斑斓色彩的影响,抽纱工艺在用色上也突破了以白纱为主的色调,色彩更加绚丽悦目。此外,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针线工艺还有用小棒槌(线辘)编制的花边,主要产地在山东烟台和广东南海等地,然而这一工种并没有在潮汕地区广泛传播。 虽然关于抽纱技艺传入潮汕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均与服务于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的女传教士有关。根据美国浸信会耶琳夫人的自述⑤、西奥多·赫尔曼(Theodore Herman)先生所援引的马禄夫先生(曾在汕头办抽纱厂)的说法⑥,以及澄海籍学者陈卓凡⑦和香港浸会大学李金强教授⑧等人的研究,均表明莱爱力夫人(即娜姑娘,Sophia Norwood)有首传之功。⑨实际上在英美教会传入抽纱技艺的问题上,1949年《潮汕抽纱业近况》一文的作者和李金强教授也都关注到耶琳夫人所起的作用。⑩而在教团内部的初期推广上,耶琳夫人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 娜姑娘与耶琳夫人均经由美国浸信会选派来到汕头礐石,前者于1877年到汕从事女子教育,后者也于1880年继踵而至,一起共事。娜姑娘后于1885年脱离美北浸信会,并于次年6月在伦敦与英国长老会的莱爱力医生(Alexander Lyall)结婚,返汕后服务于汕头的长老会教团。根据《潮汕抽纱发展史和基本情况(初稿)》的记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会内部只有二十来名妇女做抽纱,并以汕头淑德女校为中心。(11)而耶琳夫人在1896年已经开始利用抽纱所得开办了女子日间学校,(12)同时斥资兴建正光女学的新校舍,可见美国浸信会的抽纱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只是英国长老会容许信徒经营抽纱,1903至1907年先后成立了四家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这一工艺在教会外的传播。民国时期潮汕的大抽纱商多出自英会系统,他们不忘莱爱力夫人的贡献,再加上他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影响力,才使得她在现存的史料中更多被提及。 莱、耶二位女传教士会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将抽纱工艺引入各自所服务的教团,应受到当时西方教会的女子教育理念、美国“殖民地复兴运动”以及在汕头礐石共事的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缝纫手工在西方教会的女子教育中自古占有一席之地,其教育思想源于创办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的玛丽·莱昂(Mary Lyon)的三“H”方针(heart心灵、head智力和hand手艺)。训练女学生的动手能力被纳入教学当中,包括缝制自己的服装、自己种菜、洗衣以及其他能锻炼自立能力的工作。在美国的语境中,家政训练被视为女性自立的基础。(13) 而娜姑娘和耶琳夫人在华期间,兴起于美国的“殖民地复兴运动”刺激了美国市场对抽纱产品的需求。这场运动以1876年费城的国际博览会百年大会为起点,终于一战的爆发(亦有人主张将其下限延到1930年代)。与同时代一些美国女性为争取投票权和进入职场而抗争不同,“做针线活的女性被视为家庭至上的典范,因为这门手艺使人联想到看似更简单和更高贵的美国往事,体现了殖民地时代重视家庭、深居简出的生活”(14)。该博览会举办后,欧美越来越多的人将抽纱视为一种艺术品,以有别于工业化时代快速、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商品。与家乡的同事与亲友保持密切联系,以及在汕头的外国宗教团体之间紧密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使得当时服务于不同教团的娜姑娘(已成为莱爱力夫人)与耶琳夫人对欧美市场的新需求以及对方教团工作的新动向都了如指掌。 而对中国女性来说,“精于女工”更是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考量“妇德”的重要标准。在潮汕地区,潮绣的流行是妇女手工颇有基础的重要写照,这一点也为西方抽纱技艺的传入和快速传播提供了受众广泛的良好基础。正如赫尔曼所说,在抽纱工艺引入后,“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女孩能够快速、精确地操作这些技艺”(15)。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抽纱被成功地引入潮汕地区,并逐渐形成规模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长老会的莱爱力夫人、美国浸信会的耶琳夫人和天主教神甫和修女(沙尔德圣保禄与吴苏辣两个修女会)所属的各个教团在抽纱的生产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美国浸信会允许传教士以个人的身份投资抽纱生产,但所得须主要用于教会建设,成立抽纱基金,并禁止当地男信徒从事营利性的抽纱业,将其经营权牢牢掌握在传教士手中。这个政策后来也为在汕头的法国外方传道会和在南海地区传教的美国希伯伦堂宣道会所仿效。英国长老会则允许其男信徒经营抽纱业,先是组织教团内的女信徒从事生产,后也扩展到大批的教外妇女,传教士本身则不出面经营。据此,为了表述方便,可将其大致归纳为“教会管理”和“信徒经营”两种方式。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作为抽纱工艺的引入者与积极推广者,美国浸信会、英国长老会和巴黎外方传道会均对教会与抽纱业的关系三缄其口;但李金强教授的研究却揭示出,香港不少的潮汕基督教徒,不论男女,都以抽纱为业,由此形成了“同乡、同业、同信仰”的奇特现象(16),充分表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下文拟历时性的展现教会与抽纱业相互影响的关系,即教会、传教士关于抽纱技术的引进、生产组织的构建促进了抽纱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抽纱业的兴起也对潮汕地区教会在经济自立、组织扩张、社会影响力增强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二、教会管理 1885年,耶琳夫人从娜姑娘手中接管美国浸信会的妇女教育工作,出于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考虑,她开始在教团内传授抽纱技艺,并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随着教友人数的自然增长和教务的发展,她倡议在乡村堂会办日间学校(即走读学校),并开始收取学费。1898年,她利用设立的抽纱基金开设了五所女子走读学校。(17)正光女学因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不敷使用,耶琳夫人于是与其他传教士商议,“向母会申请一笔数额只有1000美金的经费用于建筑新校舍,并答应提供销售抽纱成品所得的600墨西哥银元”。新校舍于1899年落成,资金全部来自耶琳夫人的个人投资的抽纱所得,她还退还了母会的建设经费。(18)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抽纱事业对浸信会的影响,李期耀归纳了以下三点:第一、女子教育迅速发展;第二、入教人数迅速增加;第三,信徒捐献猛增,“虽然信徒增加和捐献猛增并非全是抽纱事业造成,但明显受其很大影响”(19)。这些情形同样适用于当时活跃在潮汕地区的其他教团。 耶琳夫人成功的经营策略为巴黎外方传道会所效仿。1903年,当梅神甫(Mérel)被派驻汕头管理账房时,潮汕地区尚未升格为一个宗座代牧区。杜士比神甫(Antoine Douspis)负责为在潮汕地区工作的其他法国传教士收发邮件和包裹,他预见法国天主教汕头教区将从广州教区中独立出来,于是便着手筹措资金,促使汕头教区早日成立。除了写信给欧洲和美国的捐献者,告知潮汕会务发展所需,以争取外国教会的捐献外,为当地天主教的信教妇女修建抽纱工场,将成品经香港出口到外国销售也是颇有前景的筹资办法。(20) 1910年,法国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St.Paul des Chartres)的两位修女应法国外方传道会汕头主教实茂芳(Adolphe Rayssac)之邀,从香港来到汕头。她们在此开设了一间孤儿院和一所小学。由于缺少经费,她们1913年便离开了。在停留的短短几年间,组织孤儿院幼童作抽纱也是等待她们开展的工作。1913年,杜士比走访了教团内部一个名为“利摩日”的抽纱工场,其实就在佩尼柯(Pénicaud)太太家中,有十六名当地妇女到此聚会。(21)由于长久没有神甫前来巡视,杜士比的到来使她们特别开心。看到这些妇女们制作的针线工艺,杜士比承认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绣品,并祈求上帝看顾和祝福“利摩日”抽纱工场的女工们。(22) 与之同时,潮州府城的守贞姑罗氏(Agathe Lo)也在天主教会的孤儿院中组织生产。1914年,邺神甫(Gervaix)在潮州的孤儿院中看到“孤女学习缝纫、织布、染布、制作假花、刺绣,等等”。另一位守贞姑林氏(Anne Lim)指导抽纱工场和文化课,“她向孤儿院年纪稍长的女孩展示所有各种抽纱技艺,并手把手教她们”(23)。这里的“所有各种抽纱技艺”指的应是抽纱传入潮汕地区初期有限的几种工艺。据《潮汕抽纱发展史和基本情况(初稿)》记述,1900至1914年之间,潮汕抽纱主要的工种是团花、水波痕、老大藤及很小部分的扎目、哥罗纱(crochet,即用钩针编织)花边。(24)而制作的产品主要是台布、垫布,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广东新会和揭阳本地产的夏布。 耶琳夫人投资生产抽纱的事很快遭到美国教会同行的质疑,并在教会内部的刊物上有一些不尽确实的报道。尽管耶琳夫人没有明说反对者的批评所指,但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有所回应,指出“这是她个人的商业投资,而且每一块(从当地妇女那里收购的)抽纱成品都付给了足额的价钱”,这一自我辩护透露出反对者质疑传教士从事营利性质事业的合法性,以及对当地信徒的盘剥。(25)天主教吴苏辣修女会在半个世纪后的1940年代也面临同样的指责。(26)日多达(Gertrude)修女管理天主教抽纱工场便被一些人视为在吴苏辣会职能的范围之外。另一个批评则指向制作抽纱对在学女生学业和健康的负面影响。在反对者看来,挣钱的欲望将使她们无心向学,此外,做抽纱这样的细致活对她们的视力伤害也很大。耶琳夫人反驳说,她正是为保护女学生视力考虑,才严禁正光女学的学生参与抽纱制作。(27)从事抽纱工艺的女信徒每月能挣10美元,这是其男同胞收入的三到五倍。抽纱成品在美国售出之后,教会才将工钱发给抽纱女工,通常要滞后数月才能领到。(28)尽管如此,做抽纱的丰厚收入仍吸引着正光女学的女孩子们加入做抽纱的行列中。当女传教士卫每拉(Myra Weld)在1904年替代耶琳夫人担任女学的校长时,她改变了耶琳夫人禁止女学生做抽纱的规定,允许她们做抽纱,但要捐出一部分收入用来资助1906年成立的正光女学宣道会。(29) 教会女校的学生做针线工艺,这在国内其他地方也不乏其例。1916年,来自美国加州的女传教士何义思(Ruth Howe Hitchock)考察了山东烟台的花边业,发现爱尔兰女传教士马茂兰(Mrs.McMullen)师母开设的女学校中,“学生们半日用来制作花边,半日用来上课”(30);何义思很快也在南海官山堂会开办“花边馆”,让教会中的女性一面自食其力,一面接受普通教育和“真道的栽培”(31)。参与制作花边的女性老、中、青、少几代都有,而“女孩子可以在那里(指“花边馆”)学织布,然后在晚上读书写字,不但不用缴学费,还有足够的工资让她们维持生活”(32)。何义思的“花边馆”收入一开始用于收容无依无靠的妇女,后来也负担少许差会的开支,用于聘请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到她主持的乡村堂会讲道。似乎在女学生制作针线工艺一事上,越来越多的在华教会达成了共识:这门手艺在支持妇女生计的同时,也有利于教会相关事业的发展,于是便不再如最初那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抽纱工种不断引进。汕头的耶琳夫人选择了一张照片展示潮汕信教妇女做针线活的情形。根据耶琳夫人的说明,这些针线活包括刺绣、穿珠、做流苏、做珠袋、钩针编织。第一种属于传统潮绣的范畴,而后两种则是典型的西方工艺。1924年,身在揭阳云路镇双山乡的吴韵香接到父亲吴雨三寄自礐石的信,言及“玉香姐上日来庐坐谈,言如有到礐石,可在伊家居住,学抽纱工夫,不患不能成功也!”吴雨三时任浸信会学校的国文教习,可见当时美会的总部礐石仍然是信徒学抽纱的主要去处。 美国浸信会和巴黎外方传道会没有改变“教会管理”的抽纱经营策略,都将抽纱工场的组织和生产置于传教士的管理之下,南海官山何义思所属的希伯伦堂宣道会也是如此。耶琳夫人是礐石浸信会抽纱生产的首位管理者。她于1916年退休,其职位或由林振声填补。林振声是美国浸信会的教友,曾留学美国。他于1910年代末归国,亦集资经营抽纱商行。(33)他在此时开始其抽纱事业与耶琳夫人的退休应不是巧合。林或受美国浸信会之托接手管理教会的抽纱基金,或受耶琳夫人个人嘱托继续她的“私人投资”,因为让当地信徒接管教会产业的情形在其他地方也能见到。1933年,南海官山希伯伦宣道会的花边馆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除了织布、制作花边、丝绵被外,还给几家基督教医院制造蚊帐。繁忙的教会管理工作使得何义思将花边馆的管理托付给一位在教会孤儿院长大的男青年“保德”,出任花边馆的主管,负责订货起货。(34)虽然有本地人主持抽纱、花边的生产,但工场所有权和管理还是掌握在教会/传教士手中。 1922至1949年,潮汕法国天主教会经营抽纱工场的历史比美国浸信会更有迹可寻。1922年7月底,三位加拿大吴苏辣修女刚到达汕头便很吃惊地发现抽纱是此地“西方传教士普遍经营的事业”。(35)主教实茂芳将在汕头和潮州府的抽纱工场交给她们管理。在那一年灾难性的“八二风灾”过后不久,玫瑰姑娘(Marie du Rosaire Audet)便到揭阳做“商业考察”,看“是否能收购一些抽纱产品到美国销售(36)。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开展,那么她代表的天主教会将能赚取成本的5%至7.5%作为佣金。然而,当揭阳当地的抽纱商人见到玫瑰姑娘是个“白人”时,便将价格抬高,收购的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而广东南海的何义思比较幸运,她的花边馆制作的花边都寄回远在美国加州的家乡,由推销经纪波特先生代理,不收取佣金。(37) 在潮州府城,训练孤儿院中的女孩做抽纱的事业仍继续进行。1924年,负责该地贞女培训工作的十字架姑娘(Marie de Ste.Croix Davis)为贫穷的妇女开设了一间抽纱工场。她写信给位于加拿大史坦斯岱(Standstead)的吴苏辣母会报告:“尽管我们很穷,我们仍很乐意帮助其他阶层的人:那些寻工无果的妇女。我们很乐意为这些可怜的妇女盖一间工场,否则她们将会因绝望而自杀。”(38)1929年底,主教实茂芳向巴黎母会报告,潮州府的抽纱工场接纳了200名妇女。(39)1932年,为躲避地方战乱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在玛丽·德·卢尔德(Marie de Lourdes)修女的建议下,潮州府年龄较大的孤女被转移到客家地区的河婆,吴苏辣修女会六年前便在此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这些女孩在此地又继续接受抽纱手艺的培训和制作。(40) 1949年以前,派到汕头来的吴苏辣修女不少是做抽纱的能手,如意大利籍的修女玛丽亚·路易莎·杰明娜蒂(Maria Luisa Geminati)。在到汕头之前,她已在曼谷的天主教会中工作了四年,当地有很多潮州移民,有些人也转信天主教。1931年,这位意大利修女与同样在汕头工作了四年的匈牙利修女库尼贡德·巴伊切扎(Kunigunde Bajczar)互调,到汕头来主持天主教会中的抽纱工场。(41)由潮汕天主教女信徒所制作的抽纱产品是通过三位加拿大修女的私人关系,由一家抽纱公司代理,从上海转运到加拿大的史坦斯岱和美国的波士顿销售。 1934至1941年是潮汕地区抽纱业的鼎盛时期,其原因与日本入侵华北使得抽纱业生产重心南移相关。山东烟台是华北地区最早的和最大的花边抽纱生产中心,日本入侵华北使该地的抽纱生产被迫中断。虽然汕头也在1939年6月遭日军入侵而沦陷,但外资抽纱洋行仍获准继续经营。(42)因此,在山东的外商转而到汕头这个位于东南沿海的抽纱生产中心订货,当地商人也开始囤积居奇,从而导致1939至1941年潮汕地区抽纱产量和出口量急剧增长。随后,日本入侵东南亚导致潮汕与南洋地区的交通和通讯中断(43),很多华侨家庭因收不到南洋亲属的侨汇而经济日窘,普通人家的父母也无力让儿女入学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妇女迫于生计,开始加入制作抽纱的行列以贴补家用。根据潮州府的吴苏辣修女报告,她们无法继续开办文化课。相反,她们将抽纱工场扩充,在工场做工的妇女从1929年的200人增加到1939年的750人。(44)一年之后,吴苏辣修女不得不关闭天主教学校,孤儿院也因汕头与潮州府之间铁路被毁而无法接收从汕头送来的孤儿。然而,抽纱工场的妇女人数却是前一年的三倍,她们都是为了挣点微薄的收入而加入做工的行列。(45)修女吴苏乐·布洛(Ursule Blot)在1941年向罗马母会报告说,由于仅有两名修女负责工场,管理大批抽纱女工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战争导致了生活和生产物资短缺,修女克洛蒂尔德·霍洛韦(Clotilde Holloway)在1940年春天报告说:“在这儿,成群的人在挨饿,市面上无米可卖。其他东西也渐渐用完,比如抽纱用的针,在这儿无法买到。”(46)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大部分抽纱进出口公司被迫关闭,(47)而主要依赖上海出口的潮汕抽纱业生产也因此被迫中断。 1945年8月,随着二战结束,潮汕抽纱业也开始复兴。此时原属天主教团的抽纱工厂的经营权似乎发生了转移。比如修女日多在得知抽纱女工在“很糟糕的条件下”工作,“遭到连奴隶都不如的对待”时,她尚需努力“为妇女争取到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48)如工厂管理仍在教会手中,此点似不难做到。笔者曾采访李绪珍修女,据云1946年她进入汕头天主教会开办的晨星女中读书时,也没有听说天主教会有经营抽纱工场之举。考虑到曾经有人批评经营抽纱并不在吴苏辣会的职能范围内,因此在战后,天主教会很可能将抽纱工场承包给私人经营,修女或者仅负责技术指导工作。例如在汕头抽纱业同业公会的会员名单中,有一家名为“光泰”的商号坐落于汕头天主堂一巷,1947年5月开业,其经营或与天主教会仍有一定联系。(49) 三、信徒经营 相对于美国浸信会和法国外方传道会而言,抽纱工艺在英国长老会教团内部的传播与生产则是另一番景象。来自澄海盐灶乡的长老会信徒林赛玉最先是在莱爱力夫妇家中帮佣。据卢继定说,她是做潮绣的能手。在与莱爱力夫人的朝夕相处中,林赛玉从她那里学到西式的针线技艺,比如墨西哥针法(俗称“美希哥”)和钩针编织技术(俗称“哥罗纱”、“通花”),她很快便熟练掌握了。(50)1894年,林赛玉的两个女儿徐淑静和徐淑英在汕头淑德女校读书。她们从母亲和莱爱力夫人那里学习针线技艺,挣得的钱用于缴学费。莱爱力夫人也教其他信教妇女,使她们在经济上得以自立。1895年,来自汕头附近内新乡的李得惜受洗,也与徐氏两姐妹一起受教于莱爱力夫人。林赛玉也将此技艺教给她的邻居祝婶。在世纪之交,英会内部只有二十来名妇女做抽纱,并以汕头淑德女校为中心。(51) 英国长老会没有像耶琳夫人那样“禁止”女学生做抽纱。相反,手工课被列入淑德女校的课程,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四名前校友——曾德容(约在1917年入校,下同)、笑姨(1924)、谢雪璋(1925)、林氏(1933)——仍记得学校非常重视手工课,教给女学生各种针线活,包括绣花、十字绣、抽纱,“每个人按照(学校规定的)样式自己做,大家做衣服都很在行”(52)。每月10美元的丰厚收入吸引着淑德女校其他女孩学做抽纱。很快,内地乡村的妇女也到汕头来学习抽纱技艺,有些人回家后将技艺传开,有些人则留下来,并劝说她们的家人到汕头加入抽纱制作的行列。这种人口流动最初是发生在教会内部。淑德女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的当老师,有的嫁给当地牧师、辅助丈夫传道。她们所到之处,便将抽纱技艺传授给乡村布道站的妇女,如澄海的盐灶、潮州府城、揭阳的五经富等地,(53)从这几个中心再向附近的村落传播。抽纱技艺在1900年之后的传播也带动了长老会新布道站的建立,比如惠来的靖海、揭阳的炮台、广美和渔湖乡等。黄树德在15岁时随同其母在广美堂受洗,母子俩正是在此堂会学习抽纱技艺。黄树德后来移居香港,以经营抽纱为生。(54)正如陈卓凡所指出的那样,“凡是基督教徒较为集中的地带,亦是抽纱加工的重点地区”。(55) 在美会和法会内部,抽纱经营权严格控制在传教士手中,而英会却不让传教士参与抽纱生产与销售,转而允许其信徒经营以积累财富,“藏富于民”。这也使得长老会教团内部出现不少大抽纱商。他们慷慨捐款反馈教会,使得英会自立的经济基础更加牢固。民国时期,在潮汕发生的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历次救济中,英会均比美会和法会得到更多的商业捐款。(56)英会的自由经营策略真正使抽纱技艺在潮汕地区迅速传播,并促使抽纱业迅猛发展。在与技艺娴熟的抽纱女工的配合下,长老会的男信徒也在潮汕抽纱业的起步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与女信徒的分工大致如下: 外销的抽纱产品基本上由妇女制作,而购买者多为在汕头的外国人,如水手、商人、潮海关和各洋行的洋雇员等等。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制约,妇女很少到洋人在汕头开设的抽纱工场工作,更遑论到汕头港的洋船上推销抽纱产品。因此,抽纱产品的销售只能由男性承担。每当外国洋船在汕头港湾中泊定,便被各式舢板团团围住。不少小贩沿着绳索登上洋船,向船上的乘客和水手兜售当地特产、各种日用品和一些传统绣品等。这些小贩将商品装在竹囊中,背在背上,他们也因此被称为“背囊仔”。曾以剃头为生的翁财源和长老会教友徐子祥据说是第一批以销售抽纱产品为生的背囊仔。(57)然而,另一位背囊仔林佳合的故事更能清楚展示男性商贩和抽纱女工在汕头抽纱业起步阶段的劳动分工。(58)林佳合是林赛玉的盐灶老乡,两人都是长老会教友。林佳合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便在1902年前后到汕头埠当背囊仔。在推销商品的同时,林佳合发现抽纱产品在外国人中间很受欢迎。他于是联系林赛玉,后者当时因莱爱力夫妇回英国休假而回到盐灶家中。林佳合向林赛玉订了一批抽纱产品,并带到汕头埠出售。其他背囊仔纷纷效仿,向附近村庄的抽纱女工收购成品,这促进了抽纱在汕头周边地区的生产。 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之后,曾为背囊仔的翁财源和徐子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1903至1907年间,四家华资抽纱公司先后在汕头开办,分别是“翁财源”、“汕头公司”、“华章公司”和“振潮公司”。其中徐子祥和另一位抽纱商人林俊良都是长老会信徒。(59)在那时,汕头尚无专门从事抽纱贸易的外资洋行。蔡汉源、徐子祥和林俊良随着传统的商贸网络到香港销售抽纱产品,并在那里扎下根。有的抽纱商人则选择去上海,因为当时沪港两个城市聚集着大批的西方人,有更多的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抽纱工艺也开始在汕头周边的城市和乡镇的非教会人群中传播,其中丁惠龙就是推动这门技艺在潮州府传播的重要人物。(60)他出生在府城西门外的陈桥村,而西门恰好是传统潮绣的制作中心。丁惠龙最初是一位潮绣商人,为了向西方顾客推销潮绣绣品,他经常往返于府城和汕头之间。后来他在汕头与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有了密切接触,从他们那里学习英语,并成为一名信徒。与林赛玉相识后,丁从林那里学到各种抽纱技艺,加上他之前销售潮绣绣品的经验和英语会话能力,他不久便被一间抽纱洋行雇用,负责从洋行领取制作抽纱所需的白布、彩线等原料,将它们发放给潮州城布梳巷的绣工加工。他也向林赛玉寻求帮助,让林给予这些绣工技术指导。这批绣工将西方的抽纱工艺与传统的潮绣工艺相结合,创造出独具风格的产品。丁惠龙又将产品回收,送到位于汕头的公司作最后的加工,最后由公司出口到美国和欧洲销售。丁惠龙不仅担任一家公司的放工员,而是为数家公司工作。随着订购量的增加,府城布梳巷的绣工人手有限,丁惠龙便将原材料派发到附近乡村的妇女手中。虽然这些妇女的手工技艺不如府城的绣工灵巧,需要派技术人员对她们进行指导,但她们的劳力也更加便宜。这便是后来在抽纱业中非常流行的“放工制”的开始。 林赛玉、林佳合和丁惠龙之间的分工清楚地展示了抽纱行业的性别差异:作为女性和抽纱制作能手,林赛玉负责在技术上指导抽纱女工;小商贩林佳合将抽纱成品分销给外国人,而放工员丁惠龙与汕头的抽纱商号密切合作,将抽纱原材料发放给农村妇女进行加工,并负责收回成品。后来,林赛玉进一步与丁惠龙合作,在潮州府城内开了第一间抽纱商号丁发合号。尽管林赛玉、林佳合和丁惠龙与基督教传教士多少有些联系,但他们都没有在教会学校受过正规教育,语言能力的局限阻碍了他们直接与洋商签订大宗贸易订单。而从1910年起,英国长老会开办的聿怀中学和淑德女学的毕业生纷纷加入到抽纱行业中来,语言能力与教友之间的互助确保了抽纱产品外销途径的畅通,进而促成潮汕抽纱业的全面勃兴。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侯乙初和张固纯分任英国长老会汕头堂的牧师和长老,同时也是汕头抽纱业同业公会的主席和常务理事。(61)侯乙初1867年生于揭阳的凤江镇,成年以后娶了曾就读于淑德女学的杨锦德为妻。她在学校中练就了一手娴熟的抽纱技艺,婚后便以此为业,补贴家用。1910年之后,侯乙初晋身为牧师,曾在长老会汕头堂任职。他也在汕头中会中负责诸多重要的事务,比如信徒的婚姻、移民信徒的教籍,并促成中会将所属各堂的小女学收归中会统一管辖,对长老会的管辖区域进行划分,修改长老会公例等。张固纯1871年出生于汕头,1887年11月11日由施饶理(George Smith)施洗入教。(62)1910年之后,他成为汕头堂长老,鼓励布道、主管会籍名册、小学束修、传道收银及分发、牧师束修、修堂等事宜。(63)侯乙初和张固纯既是教会中的同事,也是汕头抽纱同业公会的常务委员,他们曾合作起草文件为抽纱商争取利益,要求政府降低抽纱原材料的进口税、废除苛刻的海关花边检验则例,以保障汕头抽纱商的合法权益。 张固纯于1929至1949年担任抽纱同业公会的主席。抽纱业界的这一重要身份使他当之无愧地兼任长老会汕头堂司库之职。那些身为长老会教友的抽纱商都慷慨向教会捐献,以回馈教会,支持教会的发展。(64)1929至1931年,当长老会所属的教会学校聿怀中学被政府要求立案时,三个由信徒经营的抽纱公司——协成(65)、汕头和益汉——出面为该校担保。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学得以在教育部成功立案。(66)蔡汉源、徐子祥、林俊良、黄浩等也曾任汕头堂的长老或执事,后来他们都将生意扩展到香港(黄浩到北京)并定居下来,出资修建教堂,供到香港谋生的潮汕人礼拜与聚会之用,最终形成了“同乡、同业、同信仰”这一潮汕抽纱信徒的群体。(67) 四、推广与影响 民国初年,关于妇女能否走进职场的问题曾在教会内外引起热议。尽管各方意见不一,他们却一致认为刺绣、缝纫、烹调和教育是适合女子从事的工作。(68)虽然早在1904年,刺绣业发达的江苏常熟一带便有人在《女子世界》杂志上撰稿论刺绣之害。这位署名“尚声”的作者将刺绣与缠足对妇女身心的危害等量齐观,叹息道:“哀哉!我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之罪障何千重万叠而无尽期哉!有缠足之困苦,复有此刺绣之磨难。缠足极筋骨之害,刺绣有性命之虞;缠足发于逼迫,刺绣沦于淹滞。缠足刺绣二者,实无有异致,为害亦无有重轻。”他认为女子长时间从事刺绣工作会损害眼睛,长期久坐又会损害身体,并且浪费光阴。但很多女子却自觉地受此役而不自知,“尚声”将这归结于风俗所迫、父母所传、亲友所诱、心性所惑四个社会根源。(69) 清末新政提出兴办女学之后,一些受过教育的女子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兴办手工传习所(70),潮汕地区同样如此。如揭阳县城的陈宝莲(1878-1934),她于1905年“创闺秀女学于城西昭武第,授以幼学、四书及绘画、刺绣。……先后受聘于潮阳、普宁及县境各地女塾,致力于女子教育,终身独处”(71)。1912年,陈舒志女士在汕头近郊的崎碌创办了私立坤纲女子学校。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女性办学校格外困难。陈舒志常“亲自动手教学生绣花,又举办展览会,将精美的绣品出售或赠送,争取社会人士的支持,并以展览出售绣品的收入补充学校经费”(72)。嘉应懿德女学堂的初级科和高级科亦设有“女红”一科,内分裁工、缝工、机织工、刺绣工、造花工。(73) 民国成立后,这些女工传习所、女红会在全国各地更是层出不穷,不少学校添设手工专修科。(74)教会内外的女性杂志都用相当的篇幅登载这些手工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75)并连载裁缝科讲义供女读者学习。(76)这些民间兴办的手工培训机构引起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的重视。1918年,天津女子工艺传习所董事陈梁等因为女子手工实业成效昭著,具呈教育部,拟请通饬各直省女校手工科附授花边、抽丝(即抽纱)二项,以挽利权而裕民生。他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山东一带抽纱业的工种、从业人员和销售状况: 查女子特别工艺,畅销于欧洲各国者,其种类为花边、为抽丝、为发网、为绣花、为鲁山绸暨各种西洋手工,其他不具论。即以花边、抽丝、发网、绣花四项言之,类皆成本轻而获利巨。窃尝调查山东烟台等处,妇女经营此等手工生活者,不下三十余万人。以之运销欧美各国,犹有供不应求之势。 因此,陈梁等人向部员建议,“先就京中女师范校内,附授花边、抽丝二项科目,并通令各省一律仿办。经费既无须另筹,办理较易著成效。传习既久,则女子皆为有职业之人”。教育部采纳了此建议,于是咨请各省公署转饬各女校遵照将花边、抽丝列为附授课目。(77) 在政府支持下,抽纱工艺便在全国教会外的女学校中广为传习,潮汕地区也不例外。然而,抽纱工艺之所以在潮汕城乡女性中间广为传播,“放工制”的作用不可小觑。一战期间,欧洲成为战场,西方商人只好将抽纱的制作转到不受战争影响的亚、非与中美洲一带。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在汕头设厂,雇佣女工到工厂全职工作,以便直接管理。但由于招收不到能外出工作的年轻女性,该计划无法实施。西奥多·赫尔曼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有三:一是妇女更喜欢在家中,以自己的速度而非程序化的方式工作,因而不喜欢工厂中处于监管之下的规范化作业。二是男亲属也倾向于让女性在家工作,这样她们就不会在一个离家很远的社区中与陌生人,特别是陌生男人,有亲密接触。三是抽纱由内地农村妇女及女儿在家制作,其劳力远比在汕头工厂中的劳力便宜。因此,与“理性的”工业生产计划相比,潮汕的抽纱产品大部分是在汕头以外的农村地区加工而成,其中惠来县靖海这个抽纱加工中心离汕头最远,直线距离有50公里之遥。(78) 1920年,纽约的美乐洋行(Mallouk Brothers)在汕头设立第一家外资抽纱洋行。该行雇佣了一名瑞士籍图案设计师设计新式花样,来自意大利的新技术也纷纷引进。在原料方面,来自山东的柞绸和爱尔兰的细洋纱也取代南海和揭阳产的夏布。(79)继踵美乐洋行而来的有新昌洋行(Roese Brothers,Ashville,OH,USA)、乔治洋行(George)、双隆洋行(Shalom & Co.,New York)、倍利洋行(Jabara & Bros.,F.M.,Wichita,KS,USA)、柯宝洋行(Kohlberg,Mt.Kisco,NY,USA)及马禄孚洋行(Maloof,Columbus,OH,USA)。据《潮汕抽纱业发展史和基本情况(初稿)》记载,这些洋行的主人多为拥有美国国籍的犹太人或叙利亚人。(80)欧洲商人虽人数不如美国,但也在汕头设立了自己的行号,如德记洋行(Bradley & Co.,英国诺丁汉)、美最时洋行(Melchers,德国不莱梅)和仁德洋行(James McMullan Ltd.,爱尔兰,即山东烟台的传教士马茂兰在汕头开设的分行)。 在汕头设立的洋行,其商业运作将潮汕地区抽纱行业的生产营运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之中。汕头洋行的买办通常毕业于长老会的华英中学或聿怀中学,一些甚至在英国和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81)以张廷鉴为例,他既是美国柯宝洋行的买办,同时也是崎碌福音幼稚园及女子国民学校的校长。该学校的经费是由张廷鉴连同汕头的其他慈善会一起捐助。(82)马禄孚洋行的买办戴威廉也是长老会教友,毕业于华英中学。(83) 美、法会和英会采用不同的抽纱经营策略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影响。美、法会的“教会管理”的经营模式使得抽纱生产活动仅在教团内部的主要布道站流传,而英会让男女信徒自由从事抽纱业,却使抽纱技艺传遍了英国长老会内大大小小的布道站:先是在澄海的盐灶乡;接着到揭阳,以炮台为中心;然后传到潮阳,以灶浦为中心。很快,这些布道站周边的教外妇女也学到这门技术,一个成体系的抽纱业生产网络在潮汕地区逐渐形成,并以汕头作为原料入口和成品出口中心。 一件抽纱产品的制作包含不同的工种。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一人难以掌握所有的工种,西方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便应用到抽纱生产上,在潮汕地区逐渐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技术分工。一首潮州歌谣简明地总结了这种情形:“潮安长垫绣,揭阳会十字花,澄海人人会蕾花,潮阳雕窗上(最)出名,关埠擅长苧葛布,盐灶拿手‘哥罗纱’……”(84)在1934至1941年潮汕抽纱业的鼎盛时期,保守估计,约有五十万人从事抽纱生产,而当时潮汕地区的人口仅有七百余万。(85)由于不少男性出洋谋生,暂且假定其中的四百万是妇女,那么潮汕地区每八个女性当中便有一人以抽纱为业,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地区的女性。(86)在地区技术分工的基础上,1930年代形成了一个抽纱生产流程网络。(87)以一方女式手帕的生产流程为例,潮汕各地之间的技术分工、加工流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在汕头:在入口的细洋纱上印上抽纱花样,制作手帕时,一般是一块布上印着四块手帕的图形。 第二步,在揭阳县:有二十五万抽纱女工。放工员乘火轮或舢板溯鮀江到揭阳县城和它周边的农村,特别是炮台,挑担将布和纱线发放到妇女和女孩手中,她们擅长抽纱(根据花样要求将一块布的部分经纬线抽出)这一工种。做完后,这批布由放工员收回汕头。经检验合格后,将工钱付给放工员。放工员又将布料送到另一个地方继续下一道工序。除了抽纱外,揭阳的妇女还擅长对丝(picoting sewing)、网眼(eyelet stitch)、绣花(embroidery)、卷边(hemming)、扎边(binding)、贴布(applique)等工种。 第三步,在惠来县的靖海:如果需要蕾花(Worm stitch)这道工序,放工员便将布料送到靖海进行加工。在那里,甚至连七、八岁的女孩也受雇进行加工。完成后,布料再次被送回汕头。 第四步,在潮安县,有三十万抽纱女工。布料通过河道、铁路或公路系统被送到潮安县,以装点上精美的刺绣。 第五步,在汕头和潮阳县:完成刺绣工序,布料又一次被送回汕头市郊,或到潮阳去,将抽纱部分用针线固定住,并将布料上的四块手帕裁剪出来,进而手工卷边——这些程序各自有专门的工人负责。汕头市郊的村落专门负责卷边的工作,比如鸥汀、东墩、浮垅、金砂、华坞等。这些村子都位于澄海县南部。其北部如盐灶、樟林和东里等村子擅长钩针编织。在澄海县共有五万抽纱女工。潮阳县则有十万,补布是潮阳抽纱女工的专长。(88) 第六步,在汕头,在抽纱承包商和出口商的工厂中,约有五千名全职女工完成最后的几道工序:验收、洗、熨、折叠、贴标签和包装。(89) 1939至1941年,山东与上海的抽纱生产与营运因日军入侵而被迫中断,外商转而到潮汕寻求订单,造成当地抽纱产量飙升。因此,那三年的数据并不代表正常年份的产量。相比之下,1938年的数据颇能代表潮汕抽纱业鼎盛时期的水准。这一年,对外出口了360万打手帕、105万套台布、18000公斤花边和42000公斤用纱线编织的手套。(90)出口金额达到七百万美元。其中70%的产品是出口到美国。(91) 赫尔曼已经指出,在抽纱工艺引入到潮汕地区之前,中国其他城市——如山东的烟台和青岛、浙江的宁波和江苏的常熟——已有传教士组织抽纱生产。与汕头相比,有更多的洋轮抵达这些城市。(92)然而,汕头为何在一战后逐渐成为华南地区的抽纱生产中心?(93)笔者认为:在潮汕地区,制作抽纱是一种既符合女性身份与能力、收入又颇为丰厚的工作,大批闲散的农村女性劳力于是被调动起来。尽管这一工艺也被引进到长江和珠江流域,但当地的妇女手工业以织布和缫丝为主。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机械化生产的引进,江南和广府地区的织布厂和缫丝厂中雇有大量女工从事生产,因此在织布业和缫丝业发达的地方,抽纱业的发展空间反而受到限制。 五、迁徙与分工 富有进取心的潮汕抽纱商人沿着原有的贸易路线到上海和香港开设分行。在汕头有总公司,并在上海开设了分公司的商号有一价行(One Price lace Co.)、卢伟记(Loo Brothers)、凯记行、光成商行、潮汕抽纱商行、恒丰行;开设于香港的商号有汕头公司和复荣抽纱商行(Fook Weng & Co.)。这些位于汕头以外、由潮汕人开办的抽纱商号也有“旅馆”的功能,为那些外出谋生的潮汕同乡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9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劳工移民路线逐渐形成,正如俗语“一上、二香、三叻、四暹”所反映的,上海和香港逐渐超越实叻(新加坡)和暹罗(泰国),成为潮汕男青年外出谋生的首选地点。抽纱商的贸易网络也与这一劳工移民路线重合,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该线路的形成。 潮汕抽纱商也到青岛、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寻找机会。汕头的厚生抽纱公司便在山东烟台开设了子公司“宜生行”。(95)1927年,曾任长老会汕头堂执事的黄浩与他的妻子王佩芝到北京德胜门内簸罗仓胡同开设了宠锡挑补绣花工厂。(96)笑姨的舅舅在北京开抽纱店,她的二哥就到店中当学徒帮忙。夏天的时候,很多在京的西方人都到北戴河避暑,笑姨的二哥就带着抽纱商品到那里向他们推销,与外国人建立贸易联系。(97) 其他省份的抽纱从业人员也沿着潮汕抽纱的国内贸易网络移居到汕头。从江南和山东省抽纱产地不断有年轻人来汕头工作,并在此定居。张运生(Y.S.Chang)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是浙江宁波人。1920年代,他受派到德国抽纱洋行美最时的汕头分公司工作。(98)1934年,他在汕头开了自己的工厂“月明厂”,抽纱是其中一项产品。1945年11月,他也被雇为潮汕抽纱工业品产销合作社的副经理(99),同时担任汕头抽纱业同业公会的常务理事,任理事长的正是英国长老会的张固纯。(100)文讲到在山东烟台的爱尔兰传教士马茂兰夫妇在教会学校中推广花边制作的技艺,后来他们开设了仁德洋行(James McMullan Ltd.),1925年在汕头设立分公司,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受派从烟台到汕头工作。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和1941年入侵上海租界也使山东和上海的抽纱从业人员向汕头的流动。 与男性抽纱企业家充满艰辛和冒险色彩的奋斗之路相比,潮汕抽纱女工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太多的波澜。她们自小就学会靠“一支针求生存”。一些小女孩从襁褓中就看着妈妈、姐姐或其他女性亲属做抽纱,有的长到五、六岁,已经能熟悉技艺,协助其母亲干活。(101)抽纱也为妇女提供一种新的集体活动方式。卢继定描绘了一幅已经逝去的充满怀旧情调的生活场景:“抽纱只需一根长不过十几公分的不锈钢‘勾花针’,再加一只放纱线的小竹篮,便可以走到哪里‘勾’、‘抽’到哪里。所以以前的潮汕地区,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市镇,凡是妇女聚集的地方,上至五六十岁村妪,下至八九龄稚童,无不手拈不锈钢花针——只见银光闪闪,不见花针停歇,手工娴熟的还可以边抽勾边闲聊说话。妇女抽纱,成为潮汕城乡一景。”(102)肖姐也向笔者讲述了70年代末,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女学生们都在做针线活,有的甚至在课上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地做。有时候几个学生一起合作,用钩针编织一方大台布,挣到的钱按各自的劳动份额分摊。肖姐每天能挣三元钱,相比较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十八元,做抽纱的收入相当高,“只不过不是时时都能在抽纱站领到抽纱的活干罢了”,她不无感慨。肖姐的母亲一点都不会做抽纱,但小她几岁的弟弟却帮着姐姐一起做,姐弟俩都能为自己交学费。上世纪70年代末的学费是每学期两元钱。有一次,肖姐弟弟的老师来家访,发现他虽然是男孩,却很乖巧地跟姐姐一起做抽纱帮补家用,老师当时很感动,于是减免了他七毛钱学费。(103)但大部分的抽纱活计还是由女性做。据曾就读于淑德女校的林氏回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家里有时还弄点活让你干,给弟弟缝衣服,打毛衣什么的;学校放假的时候回家乡,回家了就要做抽纱挣钱帮助家庭。所以,好像在学校的生活比在家里还空闲些。”(104) 在西方国家,抽纱曾被视为妇女理家应有的手艺,是经营基督化家庭的重要技能。19世纪中后期,这门手艺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潮汕的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共同促成了这门技艺在教团中的传播。面临国内同行对传教士从事营利性事业的质疑,美会、法会和英会分别采用了教会管理与信徒经营两种策略经营抽纱。由于各会的官方文件对教会与抽纱业的关系三缄其口,目前尚不能根据较为充分的数据资料就此课题开展细致的量化分析。然而英会不以教会的名义参与抽纱生产与销售,转而允许其信徒经营抽纱,积累财富。这种“藏富于民”的策略即使英会免于母国宗教界的指责,也使潮汕的长老会教团内部出现不少大抽纱商。他们慷慨捐款反馈教会,使得英会自立的经济基础更加牢固。 最初由教会传入的抽纱工艺在潮汕地区找到了可以扎根的良性土壤。英美新教教会和法国天主教会的有效组织、潮汕大批农村闲置女性劳力的存在、传统的潮绣工艺以及国内外的政治举措、局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抽纱技艺和行业在潮汕地区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而基于性别、风俗差异的劳动分工也非常清晰:妇女是抽纱产品的制作者,男性则或为放工员,或是外资洋行中的买办,或者开办自己的抽纱行。 充满拼搏精神的潮汕抽纱商人甚至沿着原有的贸易移民路线到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开设分行,这种贸易路线与“一上、二香、三叻、四暹”这一新的移民路线相重合,甚至可能进一步促成了该移民路线的形成。不少人从国内其他抽纱产地移居汕头,也促进了国内跨省贸易、人员的流动,而围绕抽纱进行的进出口贸易也将潮汕地区纳入到世界经济图景之中,对20世纪该地区的经济格局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抽纱工艺传入潮汕的一百多年后,人们已逐渐忘记了其为舶来品的源头,反而作为潮汕传统工艺先后入选成为省级、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濒临失传的工艺而备受重视。这种西来工艺经过“褪色”过程而成为中国潮汕地区重要的文化象征,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所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①蔡鸿生著:《尼姑谭》,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0—173页。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花边工艺开始在广东南海地区乡村教会的推广。来自美国加州的女传教士何义思是在同工翟三姑和家乡的一位推销经纪波特先生的建议下,特地到山东烟台向爱尔兰女传教士马茂兰(Mrs.McMullen,亦译麦满伦)师母学到制作花边的技艺,并将它传授给南海官山堂会的妇女们。见何义思著,李思敬、卢詠仪译:《谁掌管明天》,香港:宣道会希伯伦堂,2012年,第40—42页。 ③⑧李金强、陈洁光、杨昱升著:《福源潮汕泽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香港:商务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④亦简称Drawn work,亦称lace and needle work。 ⑤耶琳夫人言及:“我将抽纱工艺引入到我们教会(浸信会),莱爱力夫人稍早已在英国长老会开始传授此技。”问卷“Information desired for our record”中第六个问题,参见ABHS:biographical file-William Ashmore,Jr.-folder William Ashmore,Jr.,Lida Scott(Lyons),多谢李期耀君将此条史料见示。 ⑥Theodore Herman,"Cultural Factors in the Location of the Swatow Lace and Needlework Industr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46,No.1,(Mar.,1956),note 12. ⑦陈卓凡:《潮汕抽纱业的起源及其概略》,原载于《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80年。重刊于《广东文史资料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⑨(12)(17)(19)李期耀认为莱爱力夫人传入抽纱的时间大致在1886年下半年。见李期耀:《差传教会与中西互动——粤东美北浸礼会差传教会研究(1858-1903)》,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7、177、177、178页。 ⑩《潮汕抽纱业近况》,《香港华侨日报》,1949年1月17日。亦见李金强、陈洁光、杨昱升:《福源潮汕泽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第50页,及李金强:《同乡、同业、同信仰——以“旅港潮人中华基督教会”为个案的研究(1923-1938)》,吴义雄主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11)潮汕抽纱公司档案小组编:《潮汕抽纱发展史和基本情况(初稿)》,1959年8月,第1页。按:此稿开篇提及“根据老前辈回忆,1886年在汕头的一位德籍领港员的妻子(姓名不详),当时妇女称她‘船主娘’,开始传授抽纱技术给基督教内的妇女,当时工种简单,制成品少,且均作为馈赠礼物或寄售国外教会团体之用”。因无进一步的史料参证,备考。 (13)Dana L.Robert,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97.Reprinted by McNaughton & Gunn,Inc.,1998,p.93. (14)Beverly Gordon,"Spinning Wheels,Samplers,and the Modern Priscilla:The Images and Paradoxes of Colonial Revival Needlework",Winterthur Port folio 33:2/3,p.164. (15)(78)(92)(93)同注⑥,pp.122、126、124、122. (16)李金强:《同乡、同业、同信仰——以“旅港潮人中华基督教会”为个案的研究(1923-1938)》,吴义雄主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5—243页。 (18)(27)Lida Scott Ashmore,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 f Sixty Years,Shanghai: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1920,p.112. (20)Antoine Douspis,Notice biographique,Archives of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法国外方传道会档案。 (21)佩尼科神甫(Jean-Baptiste Penicaud)1900年底曾任汕头天主教会财务主管,他的家乡正是法国的手工业中心利摩日。虽然他1902年底便调到广西的灵山工作,但汕头天主教会负责利摩日抽纱工场的佩尼科太太或与他同属一个家族。 (22)Une visite à l'ouvroir de Limoges,LETTRE DE M.DOUSPIS,1913,法国外方传道会档案。 (23)Gérvaix,"Pour le Prix Montyon",Les Missions Catholiques(1916),p.136. (24)(51)(57)同注(11),第1、3、2页。 (25)正光女学的历史也两度强调耶琳夫人“出己资”修建两栋教学楼。见《岭东浸信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岭东浸会干事局出版,1932年,第35页。 (26)(35)(36)(38)(40)(41)(44)(45)(46)(48)Irene Mahoney,Swatow:Ursulines in China,New York:Graphics/Print Production,1996,pp.232、71—73、73、75、150、128、210、211、212、231—232. (28)笔者访谈:黄志仁,1950年代生于汕头礐石,祖辈均为浸信会信徒,他现为汕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访谈时间:2010年5月27日。 (29)《卫每拉传记》,同注(25),第13页。 (30)(31)(32)(34)(37)同注②,第41、38、98、145、40—41页。 (33)(42)(53)(55)(81)(98)同注⑦,第329、334、334、334、329、331页。 (39)Rapport annuel des évêques de Swatow,1929:"Nos dévouées Ursulines viennent de construire là une école avec ouvroir,qui pourra recevoir 200 élèves."也见同注(26),p.115. (43)蔡鸿生先生告知,那些自己没有谋生手段、要依赖侨汇生存的侨眷很多在紧张年饿死。 (47)石干、刘咏兰:《历史的褒奖——潮人抽纱行业与印花手帕业掠影》,《潮人先辈在上海》,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第182页。 (49)(95)(99)汕头市档案馆(以下简称“汕档”)12—9—351:汕头抽纱业工业同业会会员名册,1948年。 (50)“1896年福音医院英籍医生‘莱爱力’带同其妻来汕头时,途径日本,在日本学到一些抽纱技术,并购备样品;抵汕后,再行传授;由此抽纱工作比较充实,除团花、美希哥、水波痕等工种外,还补充了扎目、哥罗纱花边(钩针花边),打定花边(梭仔边)等”,同注(11)。 (52)(97)(104)杜式敏:《20年代的基督教会女校——以汕头淑德女校为例》,汕头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8—89、77、89页。 (54)黄树德和黄仲山都来自揭阳广美堂,两人都是香港的基督教抽纱商人,同注(13),第231页。 (56)香玉:《潮汕教会与“八二风灾”救济》,待刊。 (58)卢继定:《汕头抽纱史上重要的普通人》,《汕头日报》2007年6月21日。 (59)蔡汉源、林俊良和徐子祥的小传,参同注(16),第231、236—237页。 (60)卢继定:《潮州对潮汕抽纱事业的贡献》,《潮州日报》2009年11月25日。 (61)汕档12—9—415:1929年1月5日的文件显示,汕头抽纱公会常务委员是侯乙初、张固纯、赵资光。 (62)张固纯之母1900年4月1日由王烈及牧师施洗。她住在崎碌,该地在20年代抽纱商行林立。她很可能以抽纱为生,与其他人子继母业的情形相同,张固纯也以经营抽纱为生。更多相似的例子可在长老会内部找到,见黄树德小传:“十五岁与母亲一同受洗于广美村礼拜堂,其母于教会习得抽纱手艺。黄氏因而从事抽纱业。1920年于香港弥敦道创办‘复荣公司’(Fook Weng & Co.),致富后奉献甚多,历任值理多届。”同注(16),第231页。 (63)见汕档:汕头区会记事册:1929年4月22日、1931年8月2日、1932年6月26日、1934年8月26日、1948年5月9日、1948年7月15日。 (64)参见胡卫清对教会经济方面的研究:《国家与教会——汕头基督教教会的自立与分离》,《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另参其《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五章“天路与商道:海外潮人与潮汕教会”。 (65)该公司由谢雪璋的兄长开办,同注(52),第70页。谢雪璋在1982年7月成为第一位女牧师,见汕头市基督教志编写组:《汕头市基督教志(征询稿)》,1988年,第3页。 (66)侯乙初参议的教务,见汕档:汕头中会记事册,1929年4月30日、1930年12月16日、1931年9月1日;张固纯的职务,同上,1931年4月28日。 (67)“其时发起重组教会,获得蔡汉源、黄树德、黄仲山、孙佳广、陈润生、柯宏楠、吴宠荣、林兆禧八位支持。八人多业抽纱。”同注(16),第231页。 (68)《女学宜注重缝纫烹调》、《女子工艺不可废绣论》,同见《妇女杂志》第l卷第4号,1915年。 (69)尚声:《论刺绣之害》,《女子世界》第1年第6期,1904年。 (70)《论中国今日亟宜普设手工女学校/传习所》,同注(69),第2年第6期,1905年。 (71)孙寒冰主编:《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志》,榕城镇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90年,第652页。 (72)“陈舒志女士,原名耀书,是十九世纪中后期香港潮商硕彦陈开泰(他最初到香港追随郭士立,成为汉会的信徒和男传道,后成为香港南北行的著名潮商——笔者注)的幼女,1880年农历9月19日生于潮州市沙溪镇仁里村。……首开家乡女子入学读书的先例,放缠足,易时装,负笈省城,进入广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广东省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前身)读书。”转引自陈启川:《潮汕第一位女校长》,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95年。 (73)《嘉应懿德女学堂简明章程》,《岭东日报》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1909)。 (74)同注(64),《约友发起女红会书》,第1卷第5期,1915年;《添设手工专修科》,第6卷第5期,1917年。 (75)《振坤女子裁缝学校招女生徒》,《女铎报》第2期第1册,1913年4月1日。 (76)《裁缝科讲义》,《妇女时报》第10—12期,1913年;《介绍女子必用第一机器(缝纫机器)》,第1期第9册,1912年12月1日;《缝纫机原始》,第11册,1913年2月1日,后两篇均同注(75)。 (77)《教育部注意女校手工》,同注(75),第7卷第8册,1918年11月1日。 (79)“工种又增加了意大利式扎目及对丝等”,同注(11)。 (80)“这些洋行的老板大部分是美籍犹太人或叙利亚人,精明圆滑,资力雄厚”,同注(11),第3页。在汕档1948年汕头抽纱业同业公会会友名录中,有一位名为达鲁祺(M.R.Dahrouge)的经理。荷兰莱顿大学宗教系的柏海伦教授(Heleen Murre-van den Berg)告知笔者,此名看似有法国渊源的阿拉伯名。 (82)马育航:《民国十年变——汕头近况之一斑》,1921年,第33页。 (83)“汕头市的张廷鉴、戴威廉,都是学英文后成为第一等洋商买办的”,陈泽霖:《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英国长老会传教入潮汕的情况》,原载于《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1963年。重刊于《广东文史资料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40页。 (84)见杨坚平著:《潮绣抽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79页。其中垫绣与织苧葛布属传统女红,而十字花(cross-stitch)、蕾花(Worm stitch)、雕窗(drawn-thread work)、哥罗纱(crochet,即通花)都是传教士传入的西式女红。 (85)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上海:上海中华浸会书局,1936年,第54页。 (86)抽纱工中也有少数男性。在70年代末做过抽纱的肖姐告知,当时大约有一成的抽纱工是男的。对肖姐的访谈,2011年1月30日。这在潮汕当地并不是很奇特的现象,因为潮州府潮绣最好的绣工大多为男性。历史上诸如官服、潮剧的戏服等的刺绣工作都不能假妇人之手做,必须由男绣工担任。当抽纱技艺最初传到府城西门的布梳巷时,开始做抽纱的多数也是男绣工,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逐渐成为做抽纱的主力。同注(11),第5页。 (87)同注⑥,p.127.也见汕头市抽纱工业同业公会编:《潮汕抽纱手工业之今昔概述》,1950年,第1—2页。“抽纱制造繁复之过程中,大别可分为两大部分及地域,汕头为收发之枢纽,各县农村为制造之中心,农村妇女以抽纱为副业,汕头市男女工人专司漂洗、烫熨”。陈卓凡也说“抽纱业的经营者,把加工的工种,分门别类就各地区的专长,分别送去加工。其中名贵的抽纱品种,都要包括几个不同的工种,而且还要经过几个不同的地区,进行不同的加工。例如白花绣手巾的加工先送揭阳县抽纱,次送潮安县绣花,后送汕头市郊卷边,然后制成。”同注⑦,第333—334页。 (88)“潮阳县专工贴布,澄海县的鸥汀乡以绣花及卷边为长,盐灶、樟林、东里等乡以织花边(又名珂罗纱)驰名,汕头市郊之东墩、浮垅、金砂、华坞等乡则专长卷边。”同注⑦,第334页。 (89)《潮汕抽纱今昔概述》提供的数字是10000人;《潮汕抽纱发展史和基本情况(初稿)》说汕头市的抽纱行中的雇工有6000人,90%的是妇女,即5400人。该数字与赫尔曼估计的数字很接近。 (90)同注(11),第7页,《潮汕抽纱今昔概述》(第3页)中的数据是:在1937至1941年之间,300万打手帕和175万套枱布出口。然而,赫尔曼(同注⑥,p.127)给出的数字却很低,每年约有“15万到20万打手帕出口”。 (91)赫尔曼说该数字是90%,同注⑥,p.127. (94)“谢牧师她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虽然相隔很远,但合办了一家‘志成抽纱公司’,协助接待家乡的牧师、长老。那时候不是轻易能住上旅社的,所以有乡下的亲人往来就(在志成公司)歇一晚或一天,就像(住)旅社一样;如果是信主的家庭,(志成公司)招待也就是请吃一餐。”笑姨口述史,同注(52),第81页。 (96)黄浩小传,见北京潮人人物志编委会:《北京潮人人物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 (100)汕档:汕头市抽纱特产改善意见书,理事长张固纯、常务理事林承之、常务理事张运生,1947年7月26日。 (101)同注(80),第78—79页。 (102)卢继定:《潮汕刺绣与抽纱》,《中华手工》,2006年第5期,第69—70页。 (103)笔者访谈:肖姐,1960年生于汕头,访谈时间:2011年1月30日。标签:传教士论文; 长老会论文; 浸信会论文; 1922年汕头台风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基督教论文; 修女论文; 天主教论文; 潮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