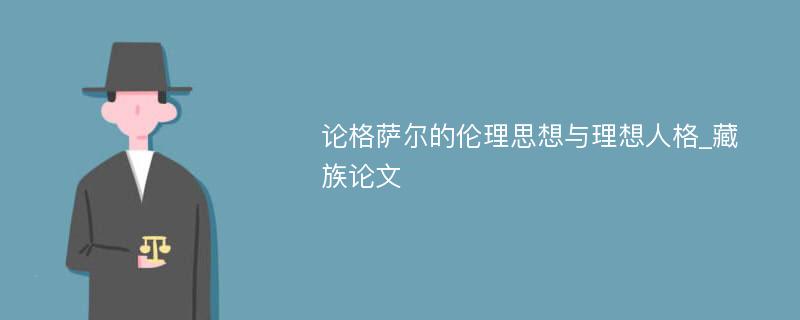
试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与格萨尔理想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萨尔论文,试论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3)-04-0032-08
《格萨尔》不仅是藏族历史上影响窎远的一部具有多学科价值的文学艺术珍品,也是藏族人民最喜爱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更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最辉煌的英雄史诗之一。它的价值,早已跨出了藏民族特定的时空范围而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和重视。本文仅从伦理学角度对《格萨尔》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格萨尔》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年代问题,学术界有“吐蕃时期说”(八至十世纪)、“宋元时期说”(十一至十三世纪)和“明清时期说”(十五世纪以后)等诸种观点。笔者赞同藏族学者降边嘉措的说法:“要确切地说出《格萨尔》究意产生在什么年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根据现有资料,它应当“产生在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即公元七至九世纪前后,基本形成。在吐蕃王朝崩溃,即公元十世纪之后,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开始广泛流传。”[1](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就是说,史诗发端于吐蕃社会之前,即“藏族氏族社会解体”的时期,但如果以“基本形成”为标志,则是在“公元五、六世纪吐蕃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
据《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教源流》等藏文典籍记载:藏族社会在没有文字之前,赞普和各地首领(相当于部落酋长)无不用“仲”、“德乌”和“苯”这三种方式来管理百姓,治理国政。“仲”,就是指民间故事(含史诗在内)。当时究竟有哪些民间故事和史诗,“仲肯”作为讲故事或说唱史诗的艺人,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参与国政,史书上则无记载。但这种管理方式说明,史诗和民间故事在古代藏族社会已经流传很广,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说唱史诗或故事的艺人甚至可以“参与国政”。在《格萨尔》未诞生之前,已有许多故事及一些小型史诗,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便“被融化、吸收到《格萨尔》这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史诗中去了”[2](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因此,“苯”当是史诗中神话的来源,“德乌”当是史诗中各种知识的来源,“仲”则直接成为史诗诞生的基础。直至现在,藏族人民还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称《格萨尔》为“仲”,称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为“仲肯”或“仲巴”,将记录成文字的《格萨尔》称为“仲译”[3](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由此亦可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的。藏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相传在松赞干布之前,藏区最初有互不统属的众多“小王”(相当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和若干小邦,相互间“喜争战格杀,不计善恶,定罪之后投之监牢”。当时,“小邦不给众生住地,居草原亦不允许,惟依持坚硬岩山(居住),饮食不获,饥饿干渴,藏地众生极为艰苦。”[4](注:智者喜筵·第七品[M].第11页.)人们饱受战乱之苦,衣食无着,性命不保的惨状已见一斑。到囊日论赞时,经过战争扩张和征服,好不容易才取得了部落联盟的“盟主”地位,为吐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至松赞干布,子承父业,施展宏图大略,终于统一了吐蕃全境,并通过发展生产,创立文字,制定法律,立官制、军制,建立起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使吐蕃社会和藏族人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时,吐蕃王朝再也无需用“仲”、“德乌”和“苯”来辅政治国了。虽然此时的巫师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但被称作“仲肯”的民间艺人,却再也无权参政了。自从有了文字后,便有专门的文职官员或文人墨客撰写史书,并为赞普及文臣武将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因而再也不需要“仲肯”即民间艺人来传唱历史了。于是,说唱史诗和故事的艺人们只好从宫廷走向民间,从象牙之塔的殿堂深入到草原牧区的家家户户,从而使史诗直接植根于藏族人民的肥土沃壤,在无限宽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格萨尔》史诗中的社会理想范型
藏族是一个富有道德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形成并发展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伦理思想。这一点,在英雄史诗《格萨尔》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印证。这部史诗不仅描绘了一种在当时情况下高不可及的社会理想范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藏族人民热爱并追求美好生活的道德理想愿望。
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对未来生活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上的表现。理想既高于现实,又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就成了纯粹的空想、幻想。任何理想,其价值在于它的完美性,因而被理想主体所热烈追求,成为奋斗的目标。社会理想是指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人们在为实现个人理想的奋斗中产生的,是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风尚、人的发展等方面的美好设想和高尚的追求。
在谈到史诗中的社会理想时,降边嘉措指出:“《格萨尔》在表现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的同时,深刻表达了藏族人民的社会理想,着意描绘了岭国这样一个藏族人民心中的理想王国。”[5](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的确,在《格萨尔》中,“岭国”完全是藏族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理想世界的范型。在那里,充满了和平与安宁,人们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按照藏文的理解,“岭”是“地方”之意,“查穆岭”即“美丽的地方”。关于岭国的地理位置,各分部本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多认为是在南瞻部洲[6](注:南瞻部洲:佛教所称四大洲之一,在须弥山南,亦叫阎浮提洲。)的中心,甚至认为“岭国”是世界的中心。《仙界遣使》中这样描写道:
在南瞻部洲北部,有个叫做佟瓦兖曼的地方,在雪域之邦所属的朵康地区。这里土地肥沃,百姓富庶,这个地方区域辽阔,包括黄河右岸的十八查浦滩、查浦赞隆山岗、查朵朗宗左翼等地[7](注:仙界遣使(藏文版)[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笫34页.)。
如果说《仙界遣使》里的寥寥数语,只是对“岭国”这个理想化世界范型做了粗线条勾勒的话,那么在《霍岭大战》中,则就有了更细致和详尽的描绘:
在人世间南瞻部洲中心东部,雪域所属朵康地方的富庶区域,人们都称作岭噶布。岭噶布又分上岭、中岭、下岭三部。上岭叫噶堆,也就是岭国的西部,地方宽阔,风景美丽,绿油油的草原,万花如绣,五彩斑斓。下岭叫岭麦,也就是岭国的东部,地方平坦,像无边无沿的大湖,凝结着坚冰,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灿烂夺目的银光。岭国的中部叫岭雄,这里的草原辽阔宽广,远远望去,一层薄雾笼罩着,好像一位仙女披着墨绿的头纱。岭噶布的前边,山形像箭杆一样的笔挺,岭噶布的后边,群峰像弓腰一样的弯曲。各部落所搭的帐房和土房,好像群星落地,密密麻麻,岭噶布这地方,真是个辽阔广大,景色如画的地方[8](注:霍岭大战·上册(汉文版)[M].青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笫1页.)。
以上的描写还只是侧重于自然方面,关于“岭国”中的社会性理想,也同样是令人羡慕和向往的:
岭国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过着和平安宁的日子。在岭国,虽然有贫富之分,那里的人分为三等九级,但人人可参与国政,享受平等的权利。虽有主仆之分,但没有终生为奴的,没有人生依附关系。岭国也没有法律,更没有监狱,人民不必担心遭受苛政酷刑之苦。同别国发生战争,大家都有抗击敌人、保卫家国的责任和义务。获得战利品,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自从格萨尔在岭国诞生,做了岭国国王之后,不断获得丰富的宝藏,使人民过着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岭国还有一个名称,叫‘佟兖曼’,意为人人羡慕的地方[9](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
岭国作为史诗中社会理想的范型,它的社会制度和人伦关系是那样的合理,合理得无可挑剔,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在这个被高度理想化了的境界中,从自然方面看,它“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地方”;从社会方面看,“人人可以参与国政,享受平等的权利”,“没有法律”,“没有监狱”,“不必担心遭受苛政酷刑之苦”,一旦遇到战争,“大家都有抗击敌人、保卫家国的责任和义务”,获得战利品,“人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在如此理想和美妙的优越环境及其社会制度下,“人民过着和平安宁的日子”,特别是有了格萨尔这样一位英明贤达的君主,人民便“不断获得丰富的宝藏”,“过着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在人类历史上,像这样的社会理想范型是否出现过呢?我们知道,以原始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理想的确是十分美妙的。恩格斯对此曾讲道: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都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10](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
原始公有制产生的道德是纯朴的,人人都排除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相互间在地位和权利上完全是平等的,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和义务。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何其美好,人们怎能不追求和向往呢?就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也还会认为它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社会理想境界。不过,社会和人的观点总是在发展进步的,决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年)在谈到民族道德的理想目标时认为:“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产,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义务和权利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管理上的民主、社会关系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教育的普及,将标志出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种制度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中的复活”。[11](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这种带有进化论同时也带有辩证法因素的观点,已比较明确地表达了民族道德是不断进步的思想。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原始公有制崩溃了,如此美妙的社会理想破灭了,但是它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美好的回忆。《格萨尔》对“岭国”这样一个社会理想范型的描写,就是藏族人民怀着童稚之情对自己远古社会亦即童年时代充满了神话般的遐想与怀想。
当然,青藏高原上究竟是否出现过“岭国”这样的社会理想范型,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降边嘉措对此断然否认:“没有,从来也没有。在藏文典籍里也没有记载。如此美丽的地方,只产生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是藏族人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12](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在原始氏族社会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恩格斯认为完全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外,我国古籍里也有类似生动、具体的描写,如在前面介绍的《礼记》中的记载。这种“大同”世界,是对原始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写照,也是人们历经千百年来还要经常怀想的一种社会理想范型。但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有些民族是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后阶段出现的民族不可能经历社会发展的前阶段。根据现有资料,证明藏民族是经历了原始社会这个阶段的。在这个阶段中,处于原始状态的藏族社会是否有过“岭国”这样的社会理想范型,笔者不敢妄断,希望引起人们的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阶级社会中,藏族乃至于世界各民族都不可能出现这种社会理想范型,但是对这种社会理想范型的追求,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愿望,因为它体现了人们企图超越现实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是不切实际的,但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慰籍和希望,使人们在严酷的现实中增强了忍受力,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看到了在无比遥远的天际中还存在一线不明不灭、隐约可见的曙光。
实际上,这种社会理想范型也并非永远不会实现。当阶级、国家、民族消亡以后,全世界结成为一个人类的整体时,“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能完全越出资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注:降边嘉措、吴伟.格萨尔全传·上册[M].宝文堂书店.1987年9月.第41、56、57页.)至此,一个具有更高形态、更加美好的人类理想世界就真正到来并完全实现了!
三、《格萨尔》史诗中的道德评价标准
道德评价标准是人们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民族或民族成员总是要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或价值尺度对本民族或其它民族集团和个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进行善恶判断。这种判断一般采取肯定或否定、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它是人们对各自的道德行为所进行的全面考察,通过考察来分析判断哪些行为是善的、好的,哪些行为是恶的、坏的,进而帮助人们认清道德选择的方向,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它可以揭示人们行为的善恶价值,判明这些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及道德理想,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以调整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定的客观标准是道德评价的基本依据,但它又往往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在《格萨尔》中,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是“曲”与“兑”,按汉语理解就是“善道”与“魔道”。“曲”,在藏语里“代表一切善良、正义、公平、合理、美好、光明的事物和行为”[14](注:降边嘉措、吴伟.格萨尔全传·上册[M].宝文堂书店.1987年9月.第41、56、57页.)。甚至格萨尔本人在史诗中也被称为“曲杰”,译成汉语就是“施行善道的国王”。“岭国”也被称为“曲德”,译成汉语就是“善道昌盛的地方”。而“兑”,在藏语里“则指一切邪恶、伪善、奸诈、残暴、丑恶、黑暗的事物和行为”[15](注:门岭大战[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凡是那些生性邪恶、施行暴政、残害人民的君主,都被称作“兑杰”,按汉语之意就是“魔王”。在史诗中,以格萨尔和岭国为一方,代表“善道”,以魔王为另一方,则代表“魔道”。综观史诗中的全部矛盾和斗争,基本上都是围绕“善道”与“魔道”来展开的。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人们概括德行与非德行的最一般的概念。通常意义上,善与道德,恶与不道德是同义语。在道德评价中,善具有肯定的道德意义,表示人们对某种行为和事件的赞赏,在生活中它常常获得善行、美德、正义等比较具体概念的形式;恶则表现为具有否定的道德意义,人们通过恶来谴责某种行为或社会现象,在生活中它又常常表达为邪恶、心术不良、卑劣、罪恶等等。简而言之,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行为,就被道德意识评价为善;凡是具有否定意义的非道德行为,就被评价为恶。
在史诗中,格萨尔秉承天神的旨意,到人间的职责和义务就是“降伏妖魔、抑强扶弱、救护生灵,使善良百姓能过太平安宁的生活。”他在降临尘世之前,就向其上师莲花生禀告道:“前世我曾发下誓愿,教化众生,降伏妖魔”/“为了降伏强大的妖魔,为了除净众生的孽障,慈悲的大师啊!请满足我的心愿!”[16](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莲花生大师也趁机对他进行训诫道:“唵,阿弥陀佛,在自明五光的佛土里,五位佛祖请鉴证/愿消除众生的五毒业障,谒见神圣智慧的尊容/有福份的好男儿你请听/完成和平、增广、权威、严厉的事业,教化五浊世间的众生,现已有了方法和助应/现成的土地和属民,生身的父亲和母亲,有保护你的佛和菩萨,有可依靠的护法空行(即护法女神),有保护善事的地方神,还有金刚护法神/本着你拯救世界的本分,按照预言依次做/对边地藏区的众生,慈悲不要太少,好男儿/对于应教化的罪恶众生,本事不要太少,好男儿!”[17](注:仙界遣使[M].(藏文版).笫1~3页.)分部本《仙界遣使》中说,格萨尔下凡尘世后,多次向人们宣称:“世上妖魔害百姓,抑强扶弱我方来”/“我要铲除不善之国王,我要镇压残暴和强梁”/“我要令强权者低头,要为受辱者撑腰”。后来他又告诫岭国的英雄们:“岭国的英雄们呵,你们可记得这样的谚语:白色善业的太阳不出来,黑色罪孽的迷雾不能消;冰雪若不被热气所融化,白色的狮子就捉不到;碧绿的海水里不放下钓钩,哪能尝到金眼鱼儿的好肉味?大家若不打开敌人的城堡,谁会给你想要的财宝?”[18](注:仙界遣使[M].(藏文版).笫1~3页.)
《格萨尔》一书,分别对黑、白两种颜色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意义、“白色”代表善业和正义,“黑色”则代表一切妖魔和邪恶。故史诗中多次强调了格萨尔立志要降服一切黑色妖魔并力图弘扬白色善业的决心。代表“善道”的格萨尔及其岭国英雄们,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在史诗中都获得了无可指责的肯定性道德评价。
史诗在尽情讴歌倡行善业的人们并对道德舆论上给予充分的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对一个个魔王即暴君在人世间所犯下的滔滔罪行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例如,它把格萨尔所征服的第一个北方魔王鲁赞,描写成一个“以一百个大人作早点,一百个男孩作午餐,一百个少女作晚餐”的极端残忍、暴戾的恶魔。像这样的恶魔,一天竟要用300人的血肉之躯来作为他的膳食,长此下去,人类岂不被他吃光了么?!面对这样的恶魔,人们怎能不从道德情感上对他产生憎恶和仇恨呢?格萨尔代表正义和善业,为了造福百姓,理所当然要铲除这样的妖魔了。史诗中的魔王并非一个,但他们的罪恶行径却如出一辙。如姜国的国王萨当是把“喝人血、吃人肉”当作过节佳肴的魔鬼,其他如霍尔的白帐王、门国的辛赤王等,都是凶恶残暴、嗜血成性、贪得无厌、不顾百姓死活的暴君。对于这些暴君的恶行,史诗通过生动的描绘和揭露,无疑会激起藏区善良人们的极端仇视和痛恨,必然要从社会舆论上给予谴责、批判和否定。
在人类道德史上,善与恶从来就是相伴相随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中,都有善与恶的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行为和实践中,都有善和恶的现象存在。无善则无恶,无恶则无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对照,互相映衬,在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中运动和发展。但从这对矛盾斗争的总趋势(或者说从它们矛盾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善总是要战胜恶,恶总是要被善所取代,就如同正义总是要战胜邪恶,光明总是要战胜黑暗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及其思想观念(其中包括伦理道德意识)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在某些时候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反复,遇到了特殊的意外情况,但这种趋势是无法改变的。综观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艺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善与恶的斗争结果,莫不如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所反映的善与恶的斗争结果,当然也不会例外。故史诗的最终结局,是善业战胜了恶业,善道取代了魔道。仅从这点来看,《史诗》中的道德评价标准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善与恶作为道德评价的两个不同标准,是对照映衬、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二者几乎成了人们衡量一切事物的“试金石”和辨别一切真伪的“是非镜”。凡是正义的、合乎道义的、具有人性的行为和事物,就被看成是善而予以褒奖;凡是非正义的、不讲道义的、践踏甚至摧残人性的行为和事物,就被看成是恶而加以否定。第二,在价值取向标准上,宣扬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亦即或善或恶自有报应的思想,进而引导人们应该扬善抑恶,向善去恶,择善弃恶,希望人们应该做到从善如流,嫉恶如仇,择善而从之,遇恶则弃之。应该说,史诗中对这种善恶标准的态度和对善恶价值取向的选择,如抛弃其某些时代的局限性,那么无疑都是正确的,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格萨尔是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人格典范
在道德理想上,史诗根据藏族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把格萨尔着意塑造为一个藏族人民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正如降边嘉措所说:史诗的作者在塑造格萨尔这个人物时,“着重表现了他所肩负的使命,通过对格萨尔完成自己使命的全过程的描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体现了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表达了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19](注:英雄诞生(藏文版)[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笫87页.)
史诗首先一开始,就描写了古时候藏族人民生活在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人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刮起一股邪风,这股风带着罪恶,带着魔怪刮到了藏区这个和平、安定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善良的人们变得邪恶,他们不再和睦相处,也不再相亲相爱。刹时间,刀兵四起,烽烟弥漫。”[20](注:赛马称王[M];降伏妖魔[M].)为了拯救藏族众生的痛苦和不幸,为了弘扬人间善业,格萨尔受天神驱遣,莅降人间,肩负的道德使命就是“教化民众,使藏区脱离恶道,众生享受太平安乐的生活。”[21](注:姜岭大战[M].)史诗把他描绘成集神、龙、念三者之精英为一体、神人相结合的大智大勇的英雄。在他未满五岁前,就“对杂曲河和金沙江一带的无形体的鬼神做了许多降伏、规劝、收管等数不胜数的好事”[22](注: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46页.),让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格萨尔降临尘世后的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在他五岁时,阴险毒辣的叔父晃通对他和他的母亲进行迫害,父亲和岭国百姓也对他产生误解,最后被驱逐到最边远、最贫穷的玛麦地方,生活贫困,处境艰险。即使如此,他仍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所肩负的道德使命,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故乡人民谋利益。后来他返回岭国参加赛马大会,他未来的岳父代表岭国百姓向他致祝辞,希望他成为一个专门“镇压邪鬼恶魔的人”,希望他做一个“扬弃不善的国王”。格萨尔也不负众望,当他赛马成功、登上岭国国王宝座后,立即向岭国百姓庄严宣称:“我是雄狮大王格萨尔,我要抑暴扶弱除民苦”;“我是黑色恶魔的死对头,我是黄色霍尔的制服者”;“我要革除不善之国王,我要镇压残暴和强梁”。他懂得光有决心不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他强调:“那危害百姓的黑色妖魔,若不用武力去讨伐,则无幸福与和平;为了把黑魔彻底来降伏,我又是武力征服的大将领。”[23](注:Fr·博厄斯.人类学和现代生活[M].纽约版.1928年.第195~196页.)言必行,行必果。他一生先后用武力降服了鲁赞、白帐王、萨当和辛赤等四大魔王,并征服了数十个魔国与敌国,用他那非凡的神威和超人的智慧,消灭、制服和收降了数不胜数的妖魔鬼怪,忠实地实践了他曾经立下的“降伏妖魔、造福百姓,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道德誓言。当功成名就,一切都如愿以偿时,他就辞别人间,返归天界。
格萨尔就是这样,用他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切实的道德实践,保卫了岭国的国土,给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雪域之邦”的“黑发藏民”们的爱戴和热烈拥护,成为藏区人民心目中光辉夺目、光彩照人的理想人格典范,被人们敬称为是“制服强暴者的铁锤,拯救弱小者的父母”。甚至连魔国的百姓也因格萨尔替他们消灭了妖魔、除却了苦难而对他感恩戴德。请听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
现在的霍尔国,可比以前不同了,托格萨尔大王的福,现在穷人变富了,老人变长寿了,小孩更快乐了,姑娘们更美丽了。牦牛、奶牛和犏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山羊、绵羊、小羊羔,好像白雪落山坡。无主的骡子赛过茜芨草,无主的马儿比野马多,无主的食品堆成山,无主的野谷开满了花朵。奶子像海酒像湖,没有人再愁吃喝。臣民夜里跳道舞,百姓白天唱善歌,人人欢喜人人乐,这都是格萨尔王的功德高,我们要再祝大王永康乐[24](注: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M].商务印书馆.1979年.笫154页.)。
关于格萨尔这一理想人格问题,降边嘉措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史诗虽然“一再宣称格萨尔是天神之子,但在具体的描写中,并没有把他塑造成头罩光环的可望而不可即、可敬而不可亲的神秘人物,而是更多地给予他人的禀赋和人的气质,使听众(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可亲可敬。在同敌人和魔王斗争时,他能够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变幻形体,具有无边的神力和大智大勇,他有着能够战胜一切妖魔鬼怪和艰难险阻的力量和智慧。但格萨尔又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有时他也会失算,会办糊涂事,会打败仗,会陷入困境。他不是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也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而,这并“没有损伤格萨尔的英雄形象,反而更接近生活真实,更富于生活气息,因而使这一艺术形象更加光彩照人”[25](注: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三联书店.1963年.第44~45页.)。
理想人格是指一种道德理想或道德上的完美典型。理想人格的突出特点是理想性和完美性。任何一个社会或一个阶级的理想人格,总是表现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或一定阶级的利益和道德原则,体现着该社会或该阶级的成员做人的基本方向和人格标准,是一定阶级的道德理想的化身。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理想人格是当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并不是绝对意义的“超人”或“完人”。因此理想人格的理想性和完美性,也不能超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本质上仍是阶级和社会的人格和理想。也许正是由于史诗的作者认识到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所以在塑造格萨尔这一特殊理想人格典范时,才没有把他看成是“全知全能”、“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既描绘出他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安宁,具有战胜一切妖魔鬼怪和艰难险阻的理想人格的同时,又刻画出他有时也会失算、办糊涂事、打败仗、陷入困境,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的人格特点。然而,这并不妨碍或损伤格萨尔这一理想人格的理想性和完美性,相反,使他更显得有血有肉,映衬出他人格形象上的伟大和光辉。
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费朗兹·博厄斯(1885-1942年)在谈到各民族的社会理想时曾举例说:“中央非洲的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同我们的社会理想是如此不同,以致他们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无法比较的。一些人认为是善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恶的。”[26](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M].三联书店.1978年.第76页.)德国早期裁缝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1808-1871年)也曾发出过如此感叹:“在这一个民族叫做善的事,在另一个民族叫做恶,在这里允许的行为,在那里就不允许;在某一种环境、某一些人身上是道德的,在另一个环境、另一些人身上就是不道德。”[27](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纽约版.1928年.笫201页.)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拉法格(1842-1911年)也曾说过“界分两国的河流足以使罪行变为善行”[28](注:熊坤新.论民族伦理学多元话结构[A].民族研究[J].1991年.笫1期.)的话。只受过中等教育的德国制革工人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则说得更明白:“民族不同,道德也不同”这些颇有见地的见解。这些都说明他们都认识到了道德的民族性与民族道德的特点问题。同时博厄斯还指出:“只有我们能够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深入每种文化,只有我们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理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28](注:熊坤新.论民族伦理学多元话结构[A].民族研究[J].1991年.笫1期.)基于此,博厄斯强调,不应当把“我们的”道德评价标准移植到另一类文化类型的各民族头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自己的道德规范。在这里,博厄斯过分看重各民族社会理想及其道德价值体系的差异性,而忽视其人类道德的共同性,显然给人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无论如何,将各民族伦理道德的差异性与人类道德的共同性割裂开来看待的观点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就如同在藏族社会一样,格萨尔这个“降伏妖魔,造福百姓,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道德楷模,不仅是藏族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想人格典范,就他的思想和行为而言,也堪称是世界各族人民在相同历史阶段的共同的理想人格典范。当然,格萨尔作为藏族人民所特有的理想人格典范,又具有藏族人民所特有的民族形式:他一开始就降生在藏族地区,并在藏族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生活、成长。具有藏族人民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心理素质和是非、善恶观念及价值标准。从人类道德的共性上看,格萨尔这一理想人格典范具有超民族性的特点,只要他的思想和事迹被别的民族的人们所了解,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会为别的民族的人们所认可、所称道。从民族道德的个性特征上看,格萨尔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只能采取藏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形式,否则,格萨尔其人的民族成分就得改变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有民族就必然有道德,没有道德的民族是没有的,根本就不讲道德,一点也不要道德的个人也是没有的。一定的道德形式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这就是我们在如何用比较民族伦理学的眼光来看待格萨尔这一理想人格典范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现阶段,先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沐浴下成长起来的一些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理想人格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脱离了低级趣味,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服务于人民,甚至不惜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英雄献身。这种理想人格,是在群众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在实践中成熟与发展的,不仅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而且是具体实践着的典型人物,因而是无产阶级道德理想的化身。这些在四化大业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的高尚品德和光辉人格,将永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进步人士所仰慕和追求。因此,现时代藏族人民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绝不能与古代藏族人民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同日而语、等量齐观。但是也必须看到,藏族社会由于过去的起点还比较低,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也较晚,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较深,人们的理想观念与过去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牧区,藏族人民的心灵深处仍然积淀、残存着旧社会的许多观念形态。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格萨尔》史诗对他们的影响是至深的,格萨尔这一古代藏族社会具有传奇神话色彩的理想人格典范仍然会在他们心中时时闪现。要使格萨尔的人格光辉在广大藏族群众中泯灭,可能还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就如同汉民族古代传说中的黄帝、羿、禹等英雄人物一样,他们在当时情况下所能体现并达到的理想人格典范,迄今还常常引起人们的怀想。这就使我们在看待《格萨尔》的伦理思想和格萨尔本人的理想人格时,需要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决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抹煞其历史价值。
《格萨尔》中伦理思想的意蕴是丰富的,格萨尔其人的人格是伟大的,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遗产时,很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