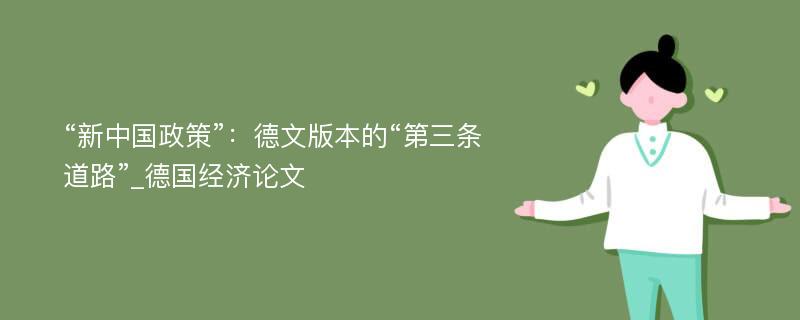
“新中派政策”:“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派论文,德国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去年9月27日举行的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会的选举中, 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格哈德·施罗德一举击败了执政长达16年之久的基民盟总理科尔。这给已是一片粉红色的欧洲政治版图又增添了一道迷人的瑰丽,被舆论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春天的到来和自由主义冬天的结束。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施罗德为使社会民主党尽早摆脱困境、获得生机,打出了“新中派政策”的旗帜,加入了风行于欧美政治舞台的“第三条道路”的大合唱。
一、“新中派政策”的实质
“第三条道路”是当今欧美社会民主党人为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环境等方面的全球性变化而提出的、试图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条中间路线。它在欧美的两个旗手分别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们改革了传统左翼主张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和高政府开支的政策,同时又借鉴右翼提出的自由市场学说,因此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对此,施罗德心驰神往并加以模仿。在98年的大选中,施罗德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作创造与中间阶级”的口号,迎合了不同阶层选民的心理需要。这表明以施罗德为代表的德国新一代社民党人认识到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政策纲领远远落后于九十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注意到了右翼政府推行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策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从而选择了一条超然左右、力求务实的中间道路。施罗德的政治偶像、英国工党的“政治神童”布莱尔在祝贺施罗德大选胜利时说,英德两国都是持有同样观点的政府。此后不久,在施罗德出访英国期间,两国还成立了一个由贸易和工业部长组成的具体负责“布莱尔主义”和“新中派政策”的英德委员会。施罗德因之而被世人称为“德国的布莱尔”、德国“第三条道路”的“总设计师”。1999年 4月,施罗德还在华盛顿与克林顿、布莱尔、达莱马、维姆·科克就“第三条道路”问题进行讨论。从理论上讲,其“新中派政策”实质上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版本。这是因为:
1、施罗德推行的“新中派政策”, 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具有务实性,即以实用主义为圭臬,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施罗德自我标榜既非左派、亦非右派,宣称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因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注:宋以敏:《西方新代领导人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5日。)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因过分囿于左右之别而陷于僵化的思维、行为模式之中,理论创新偏弱,缺少革新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在议会斗争中因拉不到大多数选民手中的选票而与执政无缘。有鉴于此,施罗德所谓的“新中派”包括了来自德国社会各行各业“创造效益的人们”、“想在职业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意愿的人”和“正在寻找培训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以及一切不甘忍受失业和不公正现象的人”。(注:《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第12页。)这些人约占德国总人口的70%,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的群众基础。为超越传统阶级政治的分野、寻求跨阶级的公民支持,施罗德的竞选纲领还针对当时高达10.2%的失业率,大肆宣扬社会公正的思想,其中写道:“我们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我们合作,为实现我们对现代化和公正的德国的设想而共同努力。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鸿沟,最终完成我国的内部统一。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注:《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第13页。)此外,施罗德还强调“现代性”和“技术创新”,主张用工作创造去代替福利救济的发放,这取悦了众多的青年选民。施罗德在大选中取得的佳绩,印证了他本人去年五月在社民党科隆会议上所说的话:“新中间道路不但对所有那些想拥有主动性、愿意体验劳动市场灵活性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对那些想实现自食其力的理想、甘愿承担风险的人们也是有吸引力的。”
2、“新中派政策”另一个特点就是其具体主张的妥协性。 施罗德在谈到“第三条道路”时说:“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主流是试图找到回答因全球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其中,最关键的是平衡,即如何保持社会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保障间的平衡”。 (注:Jordan Bonfante:Joining the Third way,Time Daily, July 20, 1998 Vol.152 No.3.)这一思想使“新中派政策”的具体主张具有明显的妥协性:1、兼顾供给和需求。施罗德认为, “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愤怒的不是什么左的或右的经济政策,而只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经济政策。”(注:霍姆巴赫:《突破》,杜塞尔多夫1998年版,第25页。)针对社民党强调政府干预的需求导向型传统经济政策已回天乏力、严重偏离社会现实,施罗德提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重新认识市场的作用,把侧重于供给的新自由主义与侧重于需求的新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就业,以此来增强对中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吸引力。2、兼顾公平与效率。 “新中派政策”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已失去往日的灵验这一现实出发,表示要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宣扬社会公正、反对失业的同时,适度调整福利政策,以刺激企业竞争、减少公共赤字。3、兼顾权利与责任。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只突出社会对个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利的保障,忽略了个人对社会尽职尽责的要求。因而,“新中派政策”强调了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促进并加强人们的自我负责能力”。借用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吉登斯的一句名言,就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二、“新中派政策”的德国特色
不同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由于所处思想及政治环境上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色。似乎有多少个信奉“第三条道路”的国家,就有多少种“第三条道路”。美国称之为“新进步主义”、英国称之为“布莱尔主义”、荷兰称之为“紫色联盟”。英美两国由于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经济政策上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荷兰的工党则采之以约翰·罗尔斯为理论来源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第三条道路”代表了北欧福利发展模式改革方向。
施罗德本人认为,由于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让德国采取另外一个国家的模式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它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市场模式,还是法国的国家模式。虽然他对布莱尔的理论推崇备至,但“新中派政策”决不仅仅是“布莱尔主义”的克隆物。首先,与之相比,“新中派政策”在目的、实现途径等方面都显得不成熟、不明确。其次,在被认为是德国“第三条道路”纲领的由社民党艾伯特基金会发表的《经济效率、社会团结、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一条道路》这一文件中,对生态负责的思想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此外,施罗德始终对“第三条道路”这个他所谓的“哲学流行语”保持着十分的谨慎,对于“新中派政策”,没有像布莱尔那样作过长篇大论般的系统阐述。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德国新政府由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 存在着两党协调关系的问题。施罗德推行“新中派政策”必须考虑到执政伙伴绿党的意愿与接受能力。这与单独执政的英国工党情况不同。英国工党在议会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拥有的议席比反对党多出177席,其内部麻烦比较少。
2、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130多年的历史,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主张通过改良、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公正、自由、互助”的价值观。这使得施罗德不得不谨言慎行。另外,社民党内在新政府成立之日起就存在“传统派”和“革新派”之争。以拉方丹为代表的传统派信奉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需求导向型经济政策;而以施罗德为代表的“革新派”则宣扬“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两派矛盾冲突的加剧导致了拉方丹于今年3月11日辞去一切政治职务。 虽然施罗德摆脱了推行“新中派政策”的绊脚石拉方丹,但是,社会民主党内的传统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施罗德对此顾虑重重。
3、 为两德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尔之所以败给了壮年得志的施罗德,是因为科尔政府时期失业人数高达600万, 而且社会福利被大大削减。施罗德在大选中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猛攻科尔这两个痛处,并向广大选民许下了娓娓动听的诺言,如表示要恢复被削弱的社会福利等。这博得了广大选民的欢心。科尔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施罗德在谈及主张改革福利制度的“第三条道路”时畏首畏尾。
三、“新中派政策”的产生原因
施罗德的“新中派政策”并非是空穴来风。其在当代德国的产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现实和个人等多方面原因的:
1、 “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施坦那里。他企图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伯恩施坦鼓吹对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结构分析等学说作根本修正;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德国社民党继承了伯恩施坦的衣钵,施罗德踏上“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2、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长期以来就流行着趋同论的思想。 它最为本质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之处越来越多,最终将趋同为一种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注:王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328页。)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现象相似即本质相同”这一逻辑,得出了两大社会制度趋同的结论。这使施罗德接受“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有了思想基础。
3、 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传统工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改变了德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传统工人比重下降到占德国总人口的20%以下,社民党原有的群众基础产生动摇。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这种变化还将更加明显。作为议会党,社民党要想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不得不调整其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原有立场,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4、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 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这要求德国社民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服从于市场规律和经济效益,着眼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可是,德国的福利制度却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它主张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高工资”的三高主义,用税收手段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用刺激消费方法发展生产,等等。这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影响了产品竞争能力,降低了经济效益,也挫伤了经济界的积极性。同时,它还滋生了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的懒汉作风。这都是与全球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成了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改革。
5、施罗德是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 成长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又具有敢于反叛的“68年人”的特征。清教徒的背景、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人格精神以及务实、善于折衷的办事作风,也使他敢于向社民党的陈规挑战,易于把握广大中产阶级的心理需要。这是他接受“第三条道路”的个人素质。早在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施罗德就既反对国家过分干预经济,主张减轻企业负担,又反对削减社会福利。
四、“新中派政策”的前景
“新中派政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使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及资本主义发展中左右两种政治派别趋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理论、政策的一种大胆的超越。它表明:作为传统的左翼政党,德国社民党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又向右发生了位移。目前,“第三条道路”从整体上来说是理论探索多于实际推行,而德国的“新中派政策”要付诸实践更是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而表现出忽左忽右、亦左亦右的特点。为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施罗德既不能大幅度削减让人敏感的社会福利,又要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提高了能源税,并征了生态税,取消了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希望以此来弥补因减税而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但是,这种措施收效甚微。
估计随着政权的稳固和“拉方丹后遗症”的清除,以及“第三条道路”影响的不断扩大,施罗德会以更大的力度推行其“新中派政策”。因为从历史上看,德国社民党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比英国工党所主张的混合经济模式,更具有侧重激励性的特点。它强调把竞争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以活跃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素有“老板的同志”这一雅号的施罗德,念念不忘“削减生产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加强机动性”(注:张慧君:《施罗德与新自由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21页。), 以维护德国企业在全球条件下的竞争力。他还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企业的竞争力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让员工作出牺牲和付出代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注:张慧君:《施罗德与新自由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21页。)究竟施罗德能否成功地把右翼的“硬心肠的资本主义”与左翼的“软心肠的资本主义”熔为一炉,这尚需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