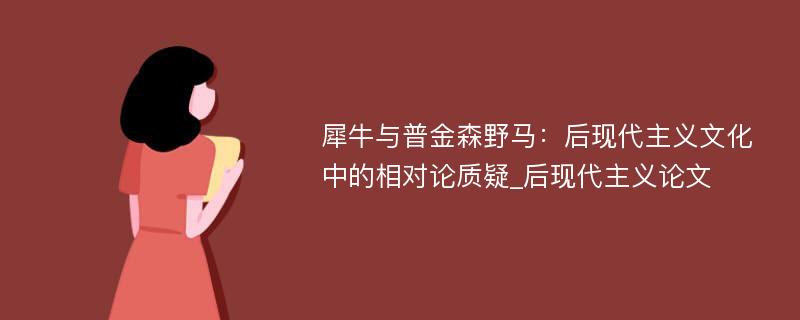
犀牛与普氏野马: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犀牛论文,相对论论文,野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与文学思潮,20世纪 80年代以后受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关注,其观念也被视为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理论和世界同步的一种模式。笔者强调,虽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对本质主义与理性主义、提倡差异逻辑等观念,对于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文化形成一定冲击,但是这种模式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不可通约性”、非确定性等观念有明显的局限,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极为不利。文化不可通约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当代文化相对论和本土文化论,尤其是受美国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的影响。应当说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否定理性中心原则的同时,把与理性相关的语言、思维的同一性也同时予以否定,这就使得原有的文化通约性原则在新的理论话语中受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者中有一种新型的文化相对论,步德国洪堡等人的文化相对论的后尘而出现。
“原始分类”的谬论
代表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观念的一个典型事例已经引起中国众多学者的关注①,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引用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段所谓“中国百科全书关于动物分类的条目”:(1)属皇帝所有的;(2)具有芳香味的;(3)驯顺的;(4)乳猪;(5)海牛目动物;(6)传说中的;(7)无主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用特别柔软的骆驼毛笔画出来的;(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 (14)远看似蝇的。福柯用这种分类来代表一种“异”,即不同于西方之“同”的异,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人的分类是如何的可笑,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共同的思维基础。
实际上,这则引文所代表的分类方法在中国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一种异想天开。据汉学家考证,因为博尔赫斯本人的文章是引自讨论17世纪英国切斯特主教约翰·威尔京斯的文章,为了说明这位主教的粗疏,博尔赫斯联想到德国学者弗兰兹·库恩曾经在一本名为《中国善知大全》的汉语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以上这一段话。而《中国善知大全》这部书又是这位博士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存在的“百科全书”。更可笑的是,西方学者一直贬低中国学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百科全书。可是,到了需要的时候,竟然自相矛盾地为中国找出一部无中生有的百科全书来了!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表演。同时,这种分类更不是中国式的,这种分类的描述与几个世纪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为了欺骗本国民众所写的那些描述中国人的文字是一样的。只要读过法国涂尔干和莫斯那本《原始分类》小册子的人就知道,福柯所引述的真是陈词滥调了。涂尔干关于中国的分类原则说: “事实上,这种分类首先是用来规定人们的行为的,而它之所以能够避免经验中的矛盾而做到这一点,全要归功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复杂性。”[1]
其实关于中国分类的以上说法全是谎言,我们以他们所说的“动物的分类”为例,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根据郭沫若考证,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养殖动物的文字,说明商代就有牧业与养殖的发生;而且动物分类明确:“观其牲牢品类,牛羊犬豚,无所不备。而用牲之数有多至三百四百者,实为后世所罕见。”[2]《诗经》中更有多种多样的动物分类,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正义曰:“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可见不止于分类,而且有更详细的关于形状和特征的分析。据顾栋高《毛诗类释》的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谷类有24种,蔬菜有38种,药物有17种,草有37种,花果有15种,木有43种,鸟名同样是43种,兽有 40种,虫有37种,鱼有16种。
中国最早的训释事物的专书《尔雅》中,专列“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章,区别类分了主要动物品种。其中第十五章“释虫”包括有天蝼、蜚、螗蜩、蜓、蝎、蜉蝣、蜾蛸、蛆等数十种,并且区分原则为“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第十六章“释鱼”不但有鲤、鲩、鳢、鲨、鲳、鲷、鲂等鱼类,还有科斗、贝类、蜥、龟等。第十七章释鸟有鸠、鸲、燕燕、鸱、鹣鹣、鹰、鹊、山雉等数十种;在鸟与兽之间进行了区分,其分类原则是“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第十八章释兽有鹿、麋、麇、狼、兔、虎、野猫、鼠、豺、狒狒、狸、蒙等数种,这些兽中还有当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犀牛,《尔雅》中记作“兕,似牛”,疏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无待发现的独角兽与野马
这就令人想起恩贝托·艾柯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中所提到的那个闻名遐迩的传说:“……欧洲人相信存着一种叫作独角兽(unicon)的动物,它看起来很温驯像一只头上长着触角的白马。经过多次周游欧洲之后,人们认为独角兽不大可能生活在欧洲。于是,传统认定,它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异国。”马可·波罗在爪哇最终看到犀牛,认定这就是传说中的独角兽。[3]
这种被欧洲人视为神奇的独角兽早在《尔雅》中就已经堂堂正正被列入兽类,并且指出它的基本特征“似牛”,可以说与现代动物学家的学科分类方法十分接近。第十九章释畜包括了人类所驯养的几乎所有动物,而且分类详细,如马中分出野马“如马而小,出塞外”,疏曰:“释曰,如马而小出塞外。案穆天子传云野马日走五百里也。”这种野马已区别于驯养的马,属于不同类别。这种分类的科学性已被证实,以后一个俄国军官在中国新疆等地发现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iskii)就是这种野马,现代动物学认为它属于“哺乳纲,马科,体形似家马。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野马”。以笔者之见,《尔雅》所列,正是这种野马,可以说我们的古人早在2000年前已经发现它并把它列为野马,无须等到俄国军官来发现它。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批判不能走向反理性,正像哈贝马斯所说,任何一种批判都已经含有理性的标准和理性的立场。也就是说,即使在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中也要以理性为原则,正如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所说,不能因为倒洗澡水而连婴儿一起倒掉。福柯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并没有看到辩证关系的实质,简单说,他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是对于唯一的“同”的批判,其途径是通过异来反对同。如他所说:“……从此出发,人们才有可能限定明确的同一性的巨大棋盘(damier),这里的同一性是在模糊的、不确定的、面目全非的和可以说是不偏不倚的差异性背景下确立起来的。癫狂史将是‘异’(I'Autre)之历史……”[4]福柯把中国文化看作是西方文化之异,看作是一种对于理性的“疯癫”,并据此展开自己对于理性的批判。但他的观念离辩证法太远,同与异其实从来不能分开,没有同就没有异,就像没有异就没有同一样。墨子早就说过“同异俱于一也”,东西方文化之间有差异,但中国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类型,它们在人类文化这一基础上是“同”。如果离开人类文化的大同去寻找怪异、以其取代人类理性,那将失去根本。
对话的共同话语建构
笔者一直反对把中国文化看作所谓“实践理性”或其他低于西方理性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存在,更不赞成看作是所谓怪异。任何涉足于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者,先要明确这是人类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类型,它同样是无限丰富、崇高和伟大的。当西方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时,莱布尼茨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先见之明,1716年他写给德雷蒙的信中说:“中国的版图很大,不比文明的欧洲小,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过欧洲。……虽然希腊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在《圣经》外的最早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方才脱离野蛮状态。若是因为如此古老的学说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与普通的经院哲学的理论有所不合,所以我们要谴责它的话,那真是愚蠢、狂妄的事!……因此,尽力给它正当的解释是合理的事,但愿我们拥有更完整的记载与更多的从中国经典中正确地抄录下来的讨论事物原则的述言。”[5]莱布尼茨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段历史的重演,他所告诫后来西方学者要“正当解释”从中国经典中正确抄录下来的述言,正是击中福柯等人这种解释的要害之言。
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是否有可通约性呢?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符号问题,而且关乎人类的心理经验和思维方式是否有共通性,而人类心理经验与思维方式又必然涉及到人类对于外界事物的反映方式如何。所以说,根本上是人类反映世界有没有同一性,我们认为,人类不同民族,从语言到思维之间都有共同性,彼此之间可以互为通译、交流。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6]
《礼记·王制》中所说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革是,北方曰译”,虽然没有讨论可通约性,但是已经默认了可通约性。而三国支谦的《法句经序》中说“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其实也是承认名物之间可以传实,不同语言之间是有同一性的。
简单说,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有同一性才有了对话的基础,而同时因为有了文化的差异性,才有了对话的必要,这是互为辩证的关系,通过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话,才有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建立一种对话的共同语言,是当代学者所思考的问题之一。如符号学家埃柯(Umberto Eco)就极力主张建立这样一种语言。他认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寻找过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他寻找一种数学语言,依靠这种语言的帮助,学者们争论问题时,可围坐桌旁,进行逻辑运算,然后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公理。简而言之,莱布尼茨是当代形式逻辑的先驱”。正像他所说,莱布尼茨正是从中国易经受到启发,才发展了自己的逻辑体系。他也看到,寻求普遍语言的方式是多样的:“我写了一本关于寻求完美语言的书。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即要寻求一种完美语言,一种高贵语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包括文化归属及硬科学的理解上设计一种语言,办法只有一个:必须建立多种语言的思想。”[7]
有人可能会感到这种说法有前后矛盾之处,既然是“一种完美语言”,如何又是“多种语言思想”?我们认为,这正是埃柯的观点有意义的地方,所谓“完美的语言”不应当是指一种具体的民族语言,而是一种对话双方或是多方都可以达到理解的道德与伦理价值的话语。当然,埃柯的思想显然受到符号学哲学的限制,没有能深入到把这种语言建构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地步,因为作为文化话语,这是无可回避的。所以,牛津大学的特雷·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的说法值得我们注意:“仅专注于能指产生所指这一途径的后现代符号学只是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用一种以担任世界组成角色的‘普遍语言’为中心的模式,将各种说话行为合并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尽管它有多元主义的证书,也已经决定性地超越了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一元论。”[8]
笔者认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伊格尔顿等,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理论对立起来,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误解。马克思在批判拜金主义的同时,也对商品的普遍价值作了最完美的阐释,他说:“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9]语言符号如同商品符号一样,它并不是与具有一定意识属性的文化话语相对立的,相反,它们的一致性远多过其不同之处。我们在寻求共通的文化符号方面,完全可以从中受到更大的启发,可以发展出一种多元文化的、不同语言的、但又有共同的辩证理性基础的全球话语。
注释:
①仅笔者所见,近期已有丁尔苏《无法沟通的神话——文化相对论的符号学批判》,参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详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车槿山《法国“如是派”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参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第 1卷)》,详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