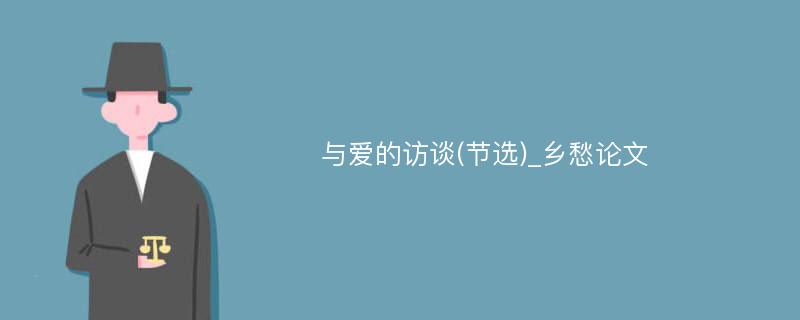
洛夫访谈录(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洛夫:我从事现代诗创作二十多年后,渐渐发现中国古典诗中蕴涵的东方智慧(如老庄 与禅宗思维)、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华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 乏的,我个人日后所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存的缺憾。40岁以前,我很向往李白的 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文化的风骨,但到了晚年,我却转而 欣赏王维恬淡隐退的心境。现代诗强调知性,强调直接介入现实人生,这固然有其时代 意义,但有时我也觉得现代诗太过犬儒与冷酷,不能与时空保持超然的距离。如以古典 诗的表现手法来处理现代生活中的题材,是否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 近二三十年来全力以赴的探索与实验。但不幸的是,有些不明究理的大陆诗人说我的“ 回归传统”是浪子回头,经常以我为例,作为批评先锋诗人的一项反面教材。其实这是 错误的,一来传统是不可能回去的,二来向古典诗借火不过是一种迂回侧进的策略,向 传统回眸,也只是在追求中国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权宜而已。
问:你怎样看待诗与宗教的关系?你认为诗是否应当具有广义的宗教情怀?你觉得禅宗 思维方式与诗的思维方式有何异同?
洛夫:我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家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做过传教士。少年时 在大陆受过一次洗,到台湾后,由于初临异乡,举目无亲,内心感到极端的孤寂,便经 常跪教会做礼拜,不久又受了第二次洗。可是后来一方面因为生计所迫,忙得没有时间 上教堂,再方面我日渐发现我对宗教仪式的厌烦而产生了疏离感,四十多年来我就再也 没有上过教堂,但冥冥中又觉得心中自有神在。我这一生大多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度过 ,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金门炮战、越战,见多了杀戮与死亡,无形中养成了一 种悲悯情怀,这对形成我诗中那种苦涩和沉郁的风格大有关系,尤其像《石室之死亡》 和《西贡诗抄》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会迫使读者不得不正视着生命内层最黑暗但也最 真实的部分。当然,诗有各种不同的内容与风格,诗与宗教并无必然的关系。我认为一 个诗人具有同情悲悯心的广义宗教情怀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无须要求每一诗人非这样不 可,诗毕竟是属于审美范畴。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论是诗或宗教,最关注的焦 点还是落在人的问题上,生命的问题上,尤其是对生命悲剧的关怀。我们经常在中外大 诗人的作品中(如杜甫和莎士比亚)感受到一种从悲剧中升起的永恒之美。
至于禅宗,在我的认知中,它是诗中的一个美学问题,也可说它是诗中的哲学。诗与 禅的结合绝对是一种革命性的东方智慧。唐代司空图及以后的诗评(诗话)家,虽也曾论 及一些诗与禅的关系,但说得较明确的要算宋代的严羽,他主张以禅喻诗,他说:“大 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里所谓的“妙悟”是什么?我们知道:禅宗的自 性相当于老子的“道”,宋明理学的“理”,是一种绝对的本体,是不可言说,不能以 理性分析的。我们只能以直觉的方法,渗进它的最深处,与它合而为一,靠亲身的感受 和体验,而不是站在外面去思考它、解说它。这种绝对的,不可思议的自性,如要表现 出来相当困难,所以必须采用一种象征性或暗示性的“比兴”手法,以达到“以有限暗 示无限,以具象暗示抽象”的妙悟效果。这种禅的“妙悟”之心理过程其实也就是诗的 “妙悟”之心理过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透过一连串意象来说明这个问题:“羚羊 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 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更指出:诗和禅的妙悟主要在“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如参照西方的现代美学来说,妙悟即是一种诉诸直觉的心灵感应,透过这种微妙的 感应,才能掌握到诗的本质,及其创作的规律。
通常所谓的禅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禅师写的诗,乃寓禅于诗,把诗当作宣示禅道 的工具,例如神秀的示法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就是这种徒具诗的形式而旨在说禅的诗。另一类是诗人所写,通过简单明彻的意象以 表示禅意或禅趣的诗,唐人以王维为代表,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其中景是禅景,趣是禅趣,什么也没有说,可好像又说了很多。再说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既是诗境,也是禅境, 诗禅交融,读后不禁使人感到,生命竟是如此的澄明和自在。
禅与诗都是一种神秘经验,但却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我对禅的理解是: 从生活中体验到空无,又从空无中体验到活泼的生机。诗与禅都在虚虚实实之间,我采 用生活的题材,写过不少意象单纯,含意则似有似无,若现若隐,表现方法在虚实之间 的诗,诗评家都说是禅诗,如《金龙禅寺》、《寻》、《水墨微笑》等。最近我写了这 么一首题名《禅味》的诗,可以说明我对禅的看法:
禅的味道如何?
当然不是咖啡之香
不是辣椒之辛
蜂蜜之甜
也非苦瓜之苦
更不是红烧肉那么艳丽,性感
那么腻人
说是鸟语
它又过分沉默
说是花香
它又带点旧袈裟的腐朽味
或许近乎一杯薄酒
一杯淡茶
或许更像一杯清水
其实,那禅么,
经常赤裸裸地藏身在
我那只
滴水不存的
杯子的
空空里
前面曾谈到超现实与禅的一些微妙关系,其实这二者不仅在本质上有某些相通之处, 就是在表现方法上也可相互参照。禅宗的表现方法有所谓“棒喝”、“参话头”、 “斗机锋”甚或以动作来暗示,如“拈花一笑”。譬如问:“如何是佛祖西来意?”或 答:“镇州大萝卜头。”或答:“青州布衫重七斤。”或答:“乾矢橛。”所答所问, 各不相干,看似胡说八道,其实无非在暗示,禅是不可以理性的语言诠释的。这不正是 超现实主义借“自动语言”摆脱理性的控制,以表现潜意识下的“真我”的手法吗?
北宋魏泰谈到禅与诗的关系时曾说:云门禅师论禅有三句,(一)随波逐浪句,意谓随 物应机,不主故常,(二)截断众流句,意谓超于言外,非情识所到,(三)涵盖乾坤句, 意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这段话如从西方现代美学来看,第一句正是现代主义的意识 流手法,第二句是超现实主义切断理性的语言结构,以表达潜意识的内涵,第三句则近 似纯粹经验,在于使时空的界限泯灭,万物融为一体。
现代诗看似西方的舶来品,但它的许多观念都暗合中国诗歌的古意古法。我相信,诗 歌艺术发展到某一高度,常会消除一些后设的界限而得以彼此汇通。
问:你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已走过了近六十年,你认为自己的诗艺探索大致可以分为 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何特点?风格上有何变化?
洛夫:曾有人论我的诗歌创作历程,就像有人论毕加索的画一样,分为“黑色时期” 、“蓝色时期”、“白色时期”等,这样大包大揽感觉式的划分法,我并不以为然。我 自己宁愿老老实实把将近六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分为五个时期:
一、抒情时期(1947-1952)
所谓“少年情怀总是诗”,写诗通常成了青少年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甚至可以代替 情书。可是我的情感生活发展得很迟,十七八岁还没谈过恋爱,诗的调子都比较低 沉而忧郁,有些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但也有些是针对社会乱象而抒发牢骚的作品, 应算是言之有物,但诗味差了些。念高中时(1946-1948年)曾写过三十多首新诗,其中 有二十多首已在家乡湖南的报纸副刊上发表。1949年渡海赴台,由于只身流落异乡,一 来忙于生计,二来心灵空虚寂寞,精神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故缺乏写作的完整时间和 安静的心灵空间,一直到1952年才写了旅台的第一首诗《火焰之歌》,在《宝岛文艺》 月刊上发表,可惜未能留下底稿与剪报资料。
这一时期的作品,一部分是描写台湾的岛国风情,一部分是写给当时女友的情诗,后 来都收进了处女诗集《灵河》(1957)中,诗集的扉页上还印有“赠给××”的字样。后 因女友家庭作梗,这段情感不久就结束了。一年后我认识了另一位女友,我送给她的第 一件礼物竟是这本《灵河》,却一时忘了把扉页上的四个字处理掉,当她接到这本书, 翻到第一页时,凝视了半天,脸色微微一变,但什么话也没说,我自己却尴尬极了。她 就是今天的老妻,数十年后谈起这件事,她还骂我荒唐。
二、现代诗探索时期(1954-1970)
1954年,我与张默在台湾南部的左营创办了《创世纪》诗刊,每年四期,一年后痖弦 也参加了我们的阵营。这是一支没有薪饷的队伍,而且同仁还得自掏腰包分摊印刷费。 后来阵营日渐扩大,凡有才气的诗人都成了《创世纪》的编委。当时台湾经济尚未起飞 ,大家都很穷困,为了办一份不赚钱的诗刊,同仁们真可说是荜路蓝缕,备尝艰苦,但 撑到80年代,《创世纪》已成为台湾三大诗刊之一,一直坚持到今天,它已是具有48年 历史,发行扩及中国内地、港澳与海外各地的权威诗刊了。
我担任《创世纪》的总编辑有24年之久(1952-1976),就任初期,正是台湾诗坛受到西 方新艺术思潮的冲击,诗人全面积极介入,进行实验性创作的高潮时期。这时诗人们意 气风发,前所未见的创新作品大量出炉,但也引起保守人士的疑虑和攻讦。在理论探讨 方面,有诗人与评论家之间的笔战,也有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争论,一时风云诡谲,高潮 迭起,诗坛热闹极了。
就我个人而言,年轻时写诗纯粹是一种兴趣,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也谈不上有什么 使命感,后来参与《创世纪》的编辑工作时,才日渐进入诗的状态,全心投入现代诗的 探索和创作。写诗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回报,非常之个人的工作。经常有人问 我,坚持写诗数十年,究竟靠一种什么力量来支持?我的答复是:我一向以价值取向来 规划我的创作生涯,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 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这个理念正是驱使我孜孜不息,从未 轻言放弃,而得以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信念。我的“以价值取向”这个理念,也许 有人不以为然,譬如有人认为“诗仅止于语言”,我完全同意语言的本体性和原创性, 诗歌先有语言,而后追加意义,这也许是可能的。但我更强调: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 任何没有意义的追求都是一种徒劳。
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石室之死亡》。这首长诗于1959年开始写于金门与厦门的炮 战中,是我诗歌创作历程中第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说是中国新诗史上一项空前的实 验,因为这是第一首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来捕捉战争与死亡阴影,描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 ,表现爱与性欲等主题的诗。我在这个集子的自序中开宗明义便说:“揽镜自照,我们 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 报复手段。”
现在听来,这话似乎有点暴力倾向,有悖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但《石室之死亡》表 现的本就是对现实冷冷的凝视,对生命荒原的深层探掘,对在战乱中生命被杀戮,人性 被扭曲被污蔑的愤怒与悲悯,对死亡的美好意象的营造,所以它不但不够温柔敦厚,甚 至远离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这个集子于1965年出版后,各方有着两极的反应,曾在评论界引起长时期的争议,争 议的关键主要在“艰涩难懂”,换句话说,当时我只求主观的表现而忽略了客观的传达 效果。我的想法是,这首长诗原本是一个极富原创性的实验作品,它并非一件写作的文 本,而是“存在”和现代的象征,是面对冷酷现实的所投射出的心灵图像,所以别人加 诸它的或毁或誉已不重要了。《石室之死亡》中的主题虽不受时空的限制,但它的价值 和历史定位,仍应放在它产生的时空背景中去衡量。有时我自忖:在这价值观大乱的今 天,一个诗人仍要坚持诗的某种价值,是不是有点迂?
三、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时期(1971-1985)
我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甚实很早,只不过在1954年倾注全力经营《创世纪》诗刊时, 便一头栽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迷宫,波德莱尔、兰波、里尔克、艾略特等现代诗人已取 代了李白、杜甫等在我心灵中的位置。当时台湾的年轻诗人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 与虚无》,谈论的都是法国象征派与超现实派的理论与作品。我除了大量地阅读这方面 的书籍之外,并在《创世纪》上连续有系统地推出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专辑。如此一 面倒的投入,正面的意义是,在西方新兴哲学与艺术思潮的刺激下,我们为诗歌创作的 想象与灵感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而负面的效果是,某些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十分晦涩,日 渐拉开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我们知道,诗歌比任何其他文类更需要读者,但的是,诗歌不是大众读物,它不可能有也不必有太多的读者。不过如果诗歌连小众读者都不 存在,这种诗显然大有问题。于是,先是几位学院派的评论家起而发难,提出严厉的批 评,继而诗人自己也有了自觉,开始对一些青涩的不成熟的、缺乏艺术性的怪诞的作品 有所反省与检讨。1972年以来,整个诗坛起了极大的骚动和变化。诗人们一度陷于“写 什么?”与“怎样写?”的两难的茫然困境,不过他们不久就调整过来了,开始坦然面对 现实,逐渐破除“诗是心灵的迷码”之类的迷思,一方面跨出封闭的心灵,走向人间烟 火,从生活中寻找诗的题材,语言也逐渐生活化,读起来显得更加鲜活、亲切,另一方 面诗人转过身来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的文学传统。我是在现代诗探索方面走得最远的一 个,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也是做得最彻底,最具体的一个。经过对中国古典诗美学的再 认与重新评价后,我惊奇地发现,古典诗中那种幽玄而精致的意象语言,那种超越时空 的深远意境,远非西洋诗可比。除了探寻到唐诗中那种比超现实主义更为周延的“无理 而妙”的表现手法之外,我更从苏东坡那里找到了一把开启诗歌秘宫的钥匙。他主张“ 反常合道”的诗观,正与我的修正超现实主义吻合。“反常”是对表面事物的扭曲,对 现实情景的调整,却能形成诗中的奇趣,造成诗的惊喜效果。但反常还须合道,即符合 我们的内在感应,也就是说:虽出意表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在反思传统,追求现代与古典的融会中,我曾以最崇敬最谦卑的心情向古代诗人学习 他们的表现手法,也曾运用古典题材,经过加工处理,写过不少现代诗,诸如《李白传 奇》、《猿之哀歌》、《与李贺共饮》、《走向王维》等,而最具个人风格的是以超现 实手法改写白居易的《长恨歌》。关于诗歌的传承问题,我在《诗的传承与创新》这篇 文章中谈得很详细,读者可找来参考。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魔歌》(1974),可说是自《石室之死亡》以后,我在创作上调 整语言改变风格以至整体诗观发生变化所呈现的新风貌。出版后备受诗坛注视,其中有 半数作品曾为人评论过,为各高等学院朗诵过,尤其像《金龙禅寺》、《子夜读信》、 《裸奔》、《舞者》、《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独饮十五行》、《长恨歌》、《巨 石之变》等,不仅被选入两岸的各大诗选,而且有几首选入了高中与大学国文课本。
1979年,事隔26年之后,《魔歌》被评选为30部“台湾文学经典”之一。当时有记者 访问我,在得知获选后有何感想。我的反应有点迟疑,因为多少感到有些意外。我以为 我诗集中最具原创性和思想高度的是《石室之死亡》,结果却是《魔歌》中选,但事后 细想,认为这一评选也不无道理,因《魔歌》毕竟是我的艺术生命和语言风格趋于成熟 的一个转折点。
四、乡愁诗时期(1985-1995)
以题材而论,我的诗大致上可分为爱情诗、战争诗、禅趣诗、哲理诗、旅游诗、乡愁 诗等类。其中乡愁诗为数不少,按理我初到台湾时乡愁最浓,应有大量乡愁诗产生,事 实不然,及到1971年台湾当局被迫退出联合国,一时悲从中来才写下《独饮十五行》。 这首诗有一“后记”:“此诗写于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次日,诗成沽酒一瓶,合泪而下。 ”但写得深刻动人,经常被传诵,多次被评论的乡愁诗则是《边界望乡》,写的是1979 年我初履香港,从落马洲边界眺望远别三十多年的中国内地的心情。当时是暮春三月, 轻雾氤氲,望远镜中的故国山河隐约可见,而耳边正响起数十年未闻的鹧鸪啼叫,声声 扣人心弦。其中有一节常被评论家引用: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我的乡愁诗又可分为“大乡愁”与“小乡愁”两种,大乡愁写的是对神州大地、故国 河山的怀念,牵动我心弦的都是那千丝万缕由历史地理积淀而成的中国情结,故我称之 为文化乡愁,譬如《国父纪念馆之晨》、《时间之伤》、《边界望乡》、《蟋蟀之歌》 、《车上读杜甫》、《登黄鹤楼》、《出三峡记》等都是。小乡愁是抒发浓厚个人情感 的乡愁诗,包括《家书》、《剁指》、《寄鞋》、《血的再版——悼亡母诗》、《湖南 大雪》、《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等,写的都是对亲人故友的深情眷恋。我的乡愁诗 ,灵感来源通常不是睹物思人,便是因特殊事件而引发诗情,前者如《登黄鹤楼》,这 是写给武汉诗人熊召政的,后者如《寄鞋》,这是为张拓芜带交一双布鞋而触动激情的 。但某些诗的创作过程颇为有趣,值得研究,例如我在1979年写了一首《我在长城上》 的诗,而我却晚于1988年才有机会亲身登上长城,《湖南大雪》也是如此,是我于1988 年湖南探亲的前一年写的。可见写诗,事必亲躬的经验并非必要,有时横空而来的想象 ,来去无踪的灵感,反而是构成一首诗的重要因素。
我在大陆先后出版了五本诗集,有花城的《诗魔之歌》,中国友谊的《洛夫诗选》、 《葬我于雪》,中国文联的《我的兽》和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的《洛夫精品》,这是一 部广纳我代表作的选集,以上所提的乡愁诗全都收入其中,最为大陆读者熟知的有《边 界望乡》、《金龙禅寺》、《湖南大雪》、《因为风的缘故》等首,因为这些诗曾多次 在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的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过。
五、天涯美学时期(1996- )
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我于1996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市,展开一个在生活上近乎半 隐、在创作上寄望更上层楼的新人生境遇,从此便有人把我归为“北美诗人”。杜甫诗 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但见宇宙间渺远苍茫,无边无际,其中只有一只沙 鸥在独自飞翔,这个镜头何其自由潇洒而又何其寂寞凄凉。我初临异国,正是这种心情 ,我自称为“二度流放”(第一度流放是1949年独自赴台湾),初期为了适应加国生活, 并做自我培训,以便能承受外在环境及内心孤寂所形成的双重压力,故诗写得不多,都 属小品,品质仅维持以往水平,没有大的突破。我来加国的第一年,两岸的诗友来信, 都对我寄以再攀创作高峰的厚望,那时我完全没有把握能满足他们的期望,内心的压力 相当沉重。我知道,创作的突破口主要在语言和新的表现形式与方法,如不能突破这两 点,要想攀登新的创作高峰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我移民北美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大冰河》是我企图在创作上有所突破的一个小小口子。1979年9月,我夫妇和老友叶 维廉教授伉俪同乘巨型邮轮“爱之船”游阿拉斯加海域,这是一次新奇而且震撼性的经 验,船在冰河湾内缓缓航行,厚达四千米,宽二十公里的巨大冰河,几乎伸手可及,这 时万籁俱寂,只听见千年的积冰嗤嗤作响,面对天地间如此古老而壮观的自然景象,一 种令人肃然的神奇的宇宙情怀不禁油然而生,这眼前的所见决不只是现象,而是一种凝 固的永恒。归来后我和叶维廉都写了一首长诗,我的《大冰河》长达一百二十多行,自 我感觉还不错,大概可以保住台湾时期的创作水平。不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一首三 千多行的长诗《漂木》。
很久以前我即酝酿要写一首不在叙事,而在表现形上思维的心灵史诗,但及到2000年 年初,我才发下狠心,摒除一切生活上的应酬与干扰,全心投入创作。这首长诗名曰《 漂木》,顾名思义,当知与我这几年在海外的流放生活有关,但它的主题却远远超过了 这点个人经验,而是宏观地写出我的哲学思考与文化反思,创作的基本理念则是根据我 近年来新开发且一直在探索的“天涯美学”。
这首诗共分四章:第一章《漂木》,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第三章《浮瓶中的 书札》(这一章又分四节,每节为一首书信体的诗,分别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致 诸神),第四章《向废墟致敬》,这一章主要表现我对佛的“空无”,禅的“虚静”, 以及老庄生命哲学的体悟。
《漂木》脱稿之后,我曾做过多次校正与修改,当校完最后一遍时,我才惊悟到,这 首三千多行的诗其实主要内容或可归纳为这么一句简单的命题:生命的无常和宿命的无 奈。
《漂木》于2000年1月开始写作,11月底脱稿,2001年元旦,也就是新世纪第一天的阳 光初照大地的那一刻,即开始在台北《自由时报》副刊正式登场,逐日连载,三个月刊 完,头两天都以全版刊出,轰动一时。日报副刊连载新诗,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一项破 天荒的创举,更是对今天商业文化的一次颠覆。《自由时报》刊完后,接着于同年8月 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并举办了发表会,又在2002年4月获得了“年度诗奖 ”。
问:可否请你对3000千行的长诗《漂木》再说得详细些,譬如前面你提到的“天涯美 学”,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漂木》和你早年的长诗《石室之死亡》有什么渊源?这两 部长诗的结构和语言有何不同?
洛夫:所谓“天涯美学”,是我移民北美后近年来我在认真思考的一个美学观念,它 的具体呈现就是《漂木》。最初我称之为“天涯文学”,其源起一是偶读张九龄的诗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触动灵感,一是由我的二度流放经验所激发。我认为, 如果说文学主要在表现作家的情感与心境,再没有任何名词比“天涯文学”更能表现海 外作家那种既凄凉的流亡心境,而又哀丽的浪子情怀。大家熟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感 受到肉体与心灵双重放逐的诗人是屈原,然后是苏东坡。屈原三度被楚怀王放逐湘南一 带,结果他将满腔的悲情化为《离骚》这样的千古奇文。苏东坡在政坛上也连栽了数个 跟斗,历尽沧桑后反而使他的气度更为恢宏,对生命的体验和观照更为深刻,结果写出 了不少传世之作。当然,不见得每位海外作家都有被放逐的悲情,但总难免有身世飘零 的感叹,这就是“天涯文学”的基调。
我所谓的“天涯”,其实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仅仅是空间 的含意,也是时间的,更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身处海外,如果只有移民做寓公的经验 ,而无大寂寞大失落的那种漂泊之感,就只能写出泛泛的作品。我觉得“天涯文学”应 具备两项重要因素,一是悲剧意识,它往往是个人悲剧经验与民族悲剧精神的结合,一 是宇宙境界,漂泊的心境不但可摆脱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且极易捕捉到超越时空的永恒 性。一个人惟有在大寂寞大失落中才能充分感受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人在天涯之 外,心在六合之内,“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天涯美学中已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 一种实质。
关于《漂木》和《石室之死亡》的关系,台北《自由时报》副刊主编蔡素芬小姐也曾 提到同样的问题,她说:“《漂木》这首长诗不论对时间、生命、历史的思考,其视野 都非常壮阔,对命运的悲剧也多有隐喻,是否企图与《石室之死亡》作前后的呼应?” 我的答复是:这两部诗集出版的时间相差35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世界变了,文 化生态也变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尤其诗的观念更是今非昔比,具体的创作自然 也就不同,最明显的有两点:第一,《石室之死亡》主要是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生 与死的形上思考,而《漂木》除了表现形上的意象思维外,也有老庄的生死辩证,宗教 的终极关怀,甚至对当代大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做出温和而严肃的批评。第二,《漂木》 的语言仍力求维持《石》诗中一定的张力和纯度,尽可能做到诗性的含蓄与蕴藉。象征 ,暗示,超现实等技巧的交互运用,构成了这首诗形式上的汪洋恣肆,语符飞扬,但内 在精神却沉潜得很深的特殊风格。
在创作这首长诗的语言策略上,曾有诗友建议应跳出旧思维的窠臼,但总觉得时不我 与,际此晚年再也没有颠覆自己在思维和写作习惯上重起炉灶的本钱。我无意搞后现代 ,诗人追求的是永恒,而不是流行。当然,在《漂木》的语言处理上,我已尽我所能不 使它再次陷于《石》诗那样的紧张与艰涩,但我仍不忘追求语言的原创性,调整语言的 习惯用法,使诗的声音成为生命的原音,语言不再是一种符号,而是生命的呼吸与脉搏 。
责任编辑注:因篇幅有限本刊只节选原文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