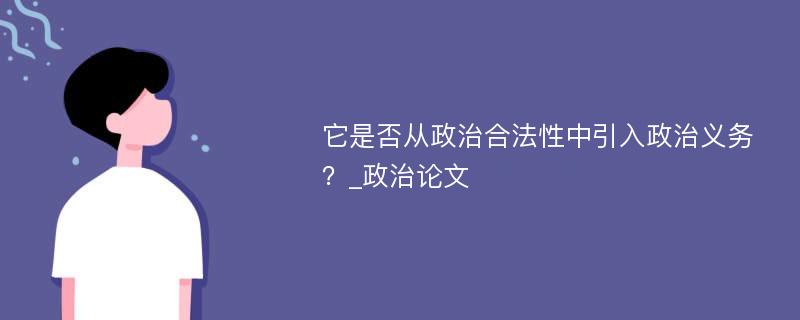
从政治正当性能推出政治义务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正当论文,义务论文,性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正当性探究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证成,或者说探求的是满足何种条件时政治权力的运用是正当的。这一任务的实质是:当我们把某国家或政府称作是正当的时候,若这一称呼是正确的,国家或政府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标准或条件。这也是通常所谓的概念分析的主要指向,即考察概念的正确运用之前提条件或标准。以“权利”这一概念为例,若想了解什么是“权利”,就必须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它。这些情况或条件就构成“权利”这一概念的含义。然而,正如拉兹(Joseph Raz)所言,对于规范性概念的解释而言,澄清它的使用条件固然重要,但这并非概念解释的全部。他指出,对规范性概念的解释必须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厘清它的正确运用之条件;其二,阐明它的规范性后果。①所谓规范性概念,主要指的是法律和道德语词,如“合法的”“正当”“权利”“责任”“义务”“好”“所有权”等概念,带有鲜明的评价色彩。规范性后果指的是概念的正确运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豁免等实践结果。仍以“权利”概念为例,我们不仅要知道它的使用条件,还要明白赋予人们某些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政府或他人带来什么样的要求或约束。 “正当性”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当然也必须接受这两方面的考察:第一,我们需要知道,只有当国家或政府满足什么条件时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作是正当的;第二,一个国家或政府若是正当的,这种正当性的规范性含义是什么,也即它会给国家或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权利,会给国家或政府何种道德地位,或者会给国家中的人们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关注“正当性”概念的第二个维度,也即一个正当的国家或政府所产生的规范性结果是什么。 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研究政治正当性问题的学者都同意的一点是,若一个国家是正当的,则该国家就具有统治的权利(the right to rule)。也就是说,国家正当性的规范性含义就是国家的统治权,就是赋予国家道德权威来施行统治。但不幸的是,当谈到这种权利的实质及其后果时,不同的学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正当的统治权利是否伴随着民众服从和支持统治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说,从政治正当性能否推出政治义务?对此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一种是认为政治正当性和政治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确立了政治正当性就定然会证成政治义务;另外一种则完全否认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的关联,把它们看作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那些接受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之逻辑关联的人仍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政治义务的实质内容。有人认为,与政治正当性相关的只是一种消极的义务,如不试图篡夺和竞争正当的统治权,不干涉法律的执行等,但另一些人却指出,消极的义务是不足够的,人们还必然会担负支持和服从正当统治的积极义务。本文力图辩护的观点是:政治义务是政治正当性的逻辑关联项,从政治正当性可以推出政治义务,且这里的政治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义务。 我们先从拉登森(Robert Ladenson)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开始。他在分析政府权威时谈到,政府的权威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政府的权力;其二是政府有权利运用权力,也即是有统治的权利。任何一个可信的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都必须包含统治的权利这一成分。但什么是统治的权利?或者说,统治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权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区分了两类权利,即由费因伯格(Joel Feinberg)所命名的基于正当要求的权利(claim rights)和基于证成的权利(justification rights)。可把它们简称为“正当要求权”与“证成权”。 我们先来看正当要求权。在拉登森看来,断言一种正当要求权就是明确地针对他人就某物或某事提出要求。这种权利预设存在一种背景制度,制度包含规则,个人正是通过诉求这些规则来证成自己的要求。它也包含权威的程序来评估个体就规则提出的要求,也包含能满足得到证成的要求的有效制度安排。正当要求权利必然与责任相关,因为当人们根据适当的规则断言这种权利时,人们对他人提出了做些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要求。②可以说,在拉登森这里,正当要求权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其一,它预设了一种背景制度,这种权利就基于这种背景制度中的规则体系;其二,它的存在必然会引发他人的某种责任和义务,也即这种权利总是与他人的义务相伴相随。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以说明之。当甲方向乙方借了一万元钱时,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如数归还。这种权利就是正当要求权,因为这一权利的基础是特定社会的法律规则或道德规则,也因为它是直接针对乙方提出的某种要求,且乙方有义务满足这种要求。同样的,当A对B承诺会帮助他补习功课时,B就获得了一种正当要求权,可以要求A帮助自己补习功课,而A同时也对B负有履行承诺的义务。 证成权与正当要求权的概念结构完全不同。当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断言证成权时,人们并非对他人提出某项要求,而是在证成自己的行为以回应他人的质疑。证成权既不预设任何背景制度,也不指向他人的某种责任和义务。在拉登森看来:“人们诉求证成权主要是为了在道德上或法律上来证成自己的行为。人们承认自己的行为违背了法律或道德规则,但却坚持认为,因为证成性考量的存在,自己的行为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自卫就是一个典型的可用于此类目的的证成权。其他的例子有:保护他人,同意,必要性,已证成的家长主义,以及家长的权威。”③ 拉登森虽然给出了上述解释,但他的证成权的含义仍然有些模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证成权的含义,即当我们有证成权去做某件事时,这也就意味着做这件事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反过来说,当做某件事是可以得到辩护的,那我们就有证成权去做这件事情。简言之,证成权等于可辩护的事情。这一理解应该能够准确地反映拉登森的想法。为了说明这种证成权,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例子:我的邻居不想让我在自家花园中种植很高的树木,因为这会严重损害他的利益,如遮挡他家里的光线,需要他花费时间清扫落叶,或招引来烦人的小虫子。为了阻止我,他威胁说要在两家相邻的地方焚烧垃圾。④我们假定,这个邻居这样做是可以得到辩护的,那他就具备一项证成权去做这件事情,但从常识的角度看,这一证成权并不意味着我因此就没有权利去反抗,或者说,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承担某种责任和义务。他有证成权仅仅意味着他这样做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仅此而已。或者考虑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突然攻击精神病院的护士,现场的工作人员迫不得已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将其制服。我们应该会同意,工作人员有证成权去如此行动,但这一权利却并不能课以该精神病人以某种责任和义务,因为他并非道德或法律评价的合适对象。或再设想下述情况:我答应参加朋友的婚礼,但在去婚礼的路上,看到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事故中只有一人幸存,但受伤严重,他请求我立即把他送入医院救治,我这样做了,但却错过了朋友的婚礼。我们会认为,这个人的行为可以得到证成,他有这样做的证成权,但这个权利会给他人带来何种义务或责任却并不明朗。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应该比较清楚证成权的实质了。当说甲有做某事的证成权时,我们是在断言,甲做这件事情可以得到证成。当我们说某件事可以得到证成时,大多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遭到了他人的质疑或挑战,为了给出回应,我们才努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力图表明,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或有权利如此行动。因而,正如拉登森所说的,人们诉求证成权的主要目的是要对自己的行为给出解释,应对他人提出的证成要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诉求证成权的重点就不是对他人提出某项要求,不会明确指向他人的某种责任或义务。就这点而言,它的确不同于正当要求权。 如果某件事可以得到辩护就等同于做这件事得到了许可(permission),那所谓的证成权其实就是许可。当说人们有证成权去采取某项行动时,就是说人们被许可去这样做。但这种许可却只是允许你去做相应的事情,它并不必然给他人带来什么责任。正如你可以选择在跑道上跑步,我也可以在跑道上跳绳。这两种行为都是被许可的,可它们并不会给彼此课以明显的义务。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证成权看作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权(liberty)。⑤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运用所有力量或手段。此类行为可以得到证成。但它们却并不会给他人的行为施加什么约束,因为他人也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去做保全自己的任何事情。具有证成权恰在于可以自由地去做得到证成的事情,但这种自由与他人的类似自由可以相容,并不必然会给他人施以义务或责任。 故而,我们最终可以把拉登森的证成权理解为一种纯然的许可或自由状态。这种状态的实质是:你可以做某件事情,或你有做某件事情的自由,但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做些什么,他人也没有义务去配合你正在做的事情。 拉登森认为,统治的权利就是这样一种证成权。因为我们可以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以说明当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来维系社会的和平状态时,政府的行为可以得到证成。但政府的统治权,“既不意味着人民对国家负有忠诚的责任,也不意味着他们有服从法律的责任。这是因为,统治权只是一种证成权,不是正当要求权,不蕴涵相关的责任。统治权和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以及服从法律等责任之间没有清晰的逻辑关联……从主权者有统治权不能推出人民因此就有不反抗主权者权力或服从法律的责任”⑥。换言之,人民的政治义务并非政府统治权的逻辑关联项。所谓政治义务,简单来说即是服从所在国家的法律并支持其政治制度的道德要求。但在拉登森看来,政府的统治权利和人民的政治义务毫不相关。一个有统治权的正当的政府可以运用强制性权力,或者说,有运用强制性权力的自由,但这就是它的统治权或正当性的全部含义了。政府的统治权可以和人民不服从其法令、不支持其统治等事情完全相容。 拉登森把统治权理解成证成权,进而斩断统治权和人民的政治义务之间的逻辑关联。但他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萨托鲁斯(Rolf Sartorius)也持有几乎相同的看法。他把事关政治权威的问题和政治义务的问题区分开来。政治权威处理的是掌权者是否有道德权利进行统治,而政治义务关系的是人民是否有道德义务服从掌权者。他认为,在很多时候,掌权者的确具有统治的权利,但那些受支配的人却并不因此就有相应的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恰恰是那些证成政治权威的理由挫败了为政治义务合理奠基的可能性。具有政治权威不是仅仅拥有政治权力,而是有正当的权利去做私人无权做的一些事情。政治权威是得到道德证成的能动者,具备相应的实施立法、司法或执法活动的道德能力,有使用强制力量的证成权,也有正当要求权。这一权威并不与承受权威者的忠诚或服从法律的责任相关。⑦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带来人民的政治义务。 西蒙斯(A.J.Simmons)把对统治权或正当性的这种理解称作是薄弱的正当性观念(weaker notion of legitimacy)。⑧与这种观念相对的是一种标准的或主导性的正当性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有正当权威的国家拥有统治的权利:有权利(在可接受的道德限度内)为那些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们制定法律,有权利通过法律制裁的威慑和(若有必要的话)实施来迫使人们服从法律。关于政治权威的主导性的哲学观点认为,与政治权威关联的权利的内容十分广泛。正当的国家不仅有命令和强制的权利,还有命令并要求服从的权利。一个正当的国家不但要求执行立法与执法的政治功能,还要求人民的服从和支持。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政治权威的权利被认为是人民的政治义务的逻辑关联项……按照这种观点,对政治权威和政治义务的证成至少部分等同”⑨。可以很容易看出,薄弱的正当性观念与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有政治义务与统治权相伴。我们有必要给这两种正当性观念以充分的检讨,看看哪种观念更合理一些。 西蒙斯对薄弱的正当性观念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批评。在他看来,若一个国家是正当的,拥有立法、司法和执法等统治权利,那它至少可以正当地要求他者不能涉足这些领域,如不能私设法庭,不能随意制定另外一套法律规则,不能擅自执法等。换言之,一个正当国家的存在,会使得人们至少有义务尊重它的统治,不与它竞争统治权。这是一个正当的国家之“正当性”的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事关政治权威的正当性观念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没有资格再使用正当性这个概念。因而,一个正当的国家所拥有的统治权至少相关于他者的一项义务,即不试图竞争或篡夺统治权。当然,这是一个消极的义务,其要求也颇为有限,不同于支持和服从政治权威这个积极的和广泛的义务。但在西蒙斯看来,一旦我们可以很好地证成尊重正当国家的统治权和不竞争统治权这项义务,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进一步证成为何人们还负有支持和服从国家的广泛义务。原因在于,这两项义务面对的挑战完全一样,即为何不能按照我们自己对事情的最佳判断而决定如何行动。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回应这个挑战,那就不仅会确立起不竞争这项义务,还会证成支持和服从的义务。⑩ 我认为,西蒙斯的以上论述的确很有说服力。从常识出发,我们会认为,若一个国家是正当的,若“正当的”这一语词真的有意义的话,那它至少意味着人们有义务尊重和不干涉国家的统治。单就这点而言,正当国家的统治权就不可能是拉登森所说的证成权,不能仅仅是可以进行统治或有统治的自由,而是必定包含正当要求权,以及由这一权利所派生的他人的义务。在现实生活或虚构的世界中,的确存在很多证成权的例子,但国家的统治权显然不能被称作证成权。进一步而言,若我们有尊重正当国家统治的义务,那这种尊重就不会仅限于不干涉或不竞争统治权,而必定同时体现为服从国家的法令,支持国家的各项制度。这些行为似乎与尊重国家的统治有自然而然的关联。若果真如此,那正当国家的统治权与人们因此担负的政治义务就定然难舍难分。国家的统治权与人们的政治义务在逻辑上就是关联的。 在西蒙斯看来,持有薄弱正当性观念的学者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即国家的正当性和国家的证成(11),进而导致他们把国家的统治权视为证成权,把政治义务与国家的统治权割裂开来。但证成一个国家和使国家正当化是不同的。他认为,证成一个国家是要阐明国家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或最理想的,是要证明接受国家是明智的或最理性的选择。但一个得到证成的国家并不一定就具有正当性,因为国家是否具有正当性依赖于对国家和每个人的互动关系的考察。那些把统治权仅仅看作证成权的学人其实谈论的是得到证成的国家,而不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何赋予这些国家如此稀薄的权利。 西蒙斯给出的正当性观念既然是标准的或主导性的,那它自然也会有很多支持者。拉兹和汉普顿(Jean Hampton)就持有同样的正当性观念。拉兹在讨论实践权威问题时给出了三个密切相关的规范性论题,其中的一个被称作取代论题(the preemption thesis)。按照这个论题,若权威是正当的,“权威要求采取某一行动这个事实就构成了做它的理由,这个理由不是要附加到用来评估我们如何行动的其他理由之中的,而是要排除和取代一些其他的理由”(12)。这段话稍显抽象,需作简单解释。拉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时,权威给出的指令就构成了采取某个行动的充分理由,不管我们已有的理由是否支持该行动。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权威的指令要优先于我们自身思考得出的结论。简言之,权威命令做一件事,我们就应当去做。也就是说,正当的权威总是会带来他人相关的义务。 汉普顿在分析政治权威时指出,政治权威不同于单纯的权力,它包含了统治的资格问题。与统治的资格密切相关的就是人民对统治者指令服从的义务。“如果我生活在被我认可的有权威的政府之下,那么当我服从国家的指令时,就不仅仅是因为担心不服从会被抓住并招致制裁,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相信自己应该服从……我可以痛恨或喜欢被命令做的事情,但只要命令来自于权威的政治统治者,我明白自己有义务服从它。”(13)可以看出,在汉普顿这里,拥有统治资格的政治权威与人们因此负有的政治义务是不可能分离的。统治资格不能只是一种证成权。 薄弱的和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之争还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即哪种正当性观念更值得追求和探讨。当我们给出一种正当性观念时,其实同时也就指明了一种研讨的方向。例如,如果你接受的是薄弱的正当性观念,那么接下来你应该考虑的就是:在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一个国家会具有证成权?但若你接受的是标准的正当性观念,那你下一步应该探讨的问题就变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具有统治的权利且人民负有服从和支持的政治义务?换言之,关于这两种正当性观念的争论就部分转变为:哪种正当性观念提出的问题更重要,更值得讨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至少部分解决了两种正当性观念之争。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一下,在讨论国家的正当性时,我们心中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只是想知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或者有自由运用强制性的权力,尽管人民对国家不负担政治义务。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它有证成权,但人民有抗拒统治的权利,没有任何服从和支持它的义务。这样一种国家观念值得追求吗?它似乎还构不成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想国家,因此不太具有讨论的价值。与此相对的是,标准的正当性观念较为符合我们对理想国家的想象,因而更有讨论的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兹对拉登森的政治权威观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拉登森的分析不仅不是对构成我们文化传统之一部分的权威概念的分析,他的分析在我们的世界中根本没有多大用处。”(14) 布坎南(Allen Buchanan)对我们这里的论述提出了挑战。他区别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和政治权威问题。在他看来,一个政治体是正当的意味着它对政治权力的运用可以得到道德证成,也即是拥有证成权,但它并非因此就享有政治权威,因为政治权威还需要另一条件被满足,即它有权利要求治下的人民服从,或者说治下的人民对它有服从的义务。政治权威的存在蕴涵着政治正当性,反之则不然。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权威的区分其实对应着我们提出的薄弱的正当性观念与标准的正当性观念的划分。布坎南这里的政治正当性观念就是薄弱的正当性观念,而政治权威观念就是标准的正当性观念。那么,是政治权威的观念更值得探讨,还是政治正当性观念提出的问题更加重要?布坎南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事关政治权力道德性的理论来说,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答两个问题:第一,在什么条件下运用政治权力可得到道德证成;第二,在什么条件下承受政治权力的人有充分的理由服从它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与政治权威问题无关,也即与政治体是否有权利要求人们服从或人们是否有义务服从政治体无关。(15)由此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政治正当性问题更重要。 布坎南承认,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是政治权威问题,或者说关注的是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但他认为,政治权威这个概念对于政治哲学没有那么重要。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其一,根据当前的研究,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是,没有政治体能拥有政治权威,因为公民对政治体负有政治义务需要的条件未能满足,并且也不可能满足。如此一来,我们自然可以质疑,在分析政治权力的道德问题时,是否应聚焦于或者说包括政治权威问题。其二,即便没有政治权威,政治权力的运用也可以得到道德证成,人们也会有很好的理由服从法律,政治体对于人们也可以是有权威的。他指出,人们之所以把政治权威问题放到如此高的地位,部分是因为未能明确区分政治正当性、政治权威、有充分的理由服从政治权力运用者施加的法律以及权威性。(16) 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理由。现有的主流意见的确认为政治权威需要的条件未能满足,因而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体几乎都不拥有权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探讨政治权威的条件就不重要。政治哲学毕竟是规范性的研究,探讨的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不能期待现实社会能立即符合理想标准。理想的与现实的永远是有距离的,但理想并不因此丧失意义。因此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不具说服力。 再看他的第二个理由。在没有政治权威的情况下,也即在人们对政治体没有政治义务的时候,人们的确也可以出于精明的考虑、宗教的戒条、道德的理由而服从法律,从而使政治体保持稳定,不至于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政治体也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来创造并维系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也就是说,政治权威的存在并非政治体稳定性的必要条件。那我们为何还要讨论理想的政治权威问题?对此,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政治体的稳定性的确是很重要的考虑,但它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应当区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使政治体保持稳定性;第二,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政治体?这两个问题其实同样重要。此外,若这一理由的逻辑能够成立,那我们也可以问布坎南一个问题:他为何如此专注于政治正当性问题?毕竟,即便一个政治体的政治权力没有得到道德证成,该政治体或许也会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若问题的焦点在于政治体的稳定性,关注点似乎不应是它的道德证成,而应是社会舆论、个人心理、思想控制等问题。 在布坎南的上述阐述中,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即政治正当性与政治权威问题可以判然二分。他似乎认为,解决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政治权威问题。但问题在于,一个正当的政治体难道不同时也是有权威的政治体吗?这事实上就回到了上面提到的西蒙斯对薄弱正当性观念的批评。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证成政治体对政治权力的运用,这个证成难道不同时意味着政治体有权利要求人们的服从或者说人们有义务服从政治体吗?政治体何时有权利运用政治权力与政治体何时有权利要求人们服从看上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如西蒙斯所言,实际上可能需要同样的答案。若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布坎南对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权威的区分就是无效的。换言之,只有标准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合理的。 韦尔曼(Christopher H.Wellman)认为,政治正当性不同于政治义务,两者有关联,但不能等同。政治正当性关注的是国家可以被许可做些什么,而政治义务关心的是公民有义务做些什么。即便证成了国家对公民的强制,也并不意味着就证成了公民有义务服从国家。政治正当性是政治义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么,政治正当性的规范性含义是什么呢?韦尔曼指出,政治正当性的规范性意义是:国家有道德权利进行强制,以及公民没有权利不被强制。国家有道德权利进行强制的逻辑关联项不是公民有道德责任服从,而只是公民没有权利不被强制。(17)国家有道德权利进行强制其实就是国家有统治的权利。故韦尔曼提出的问题是:国家统治权的逻辑关联项究竟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公民没有权利不被统治。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公民没有权利不被统治?从常理来看,当我们断言生活在国家A中的B没有权利不被统治时,最明显的含义是B没有权利抗拒A的统治。但为何没有权利抗拒呢?通常是因为有义务去服从。也就是说,没有权利不被统治与有义务服从统治之间是很难区分的。若这点可以成立,那韦尔曼在公民没有权利不被强制与公民有道德责任服从之间的区分就颇有问题。而且,若国家有道德权利进行统治,若道德权利这一概念有实质意义,那国家治下的人民有道德义务服从似乎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而,国家统治权利的逻辑关联项或者说规范性结果应该是公民的政治义务。韦尔曼给出的国家统治权的关联项就其实质而言也是公民服从统治的政治义务。 在讨论政治正当性和政治义务的关系时,柯普(David Copp)提出了一个更为细微的问题。他认为,对正当性的传统理解是把它理解为统治的权利,然后把统治的权利理解为国家有权利要求治下的人民服从法律,或者说,人民有道德义务服从法律。在他看来,当这一传统观点坚持认为生活在正当国家中的公民可以在道德上被要求服从法律时,它无疑是对的。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使用“义务”(obligation)这个褊狭的概念,因为“义务”是一类特殊的道德要求,以人们的自愿性活动为前提,总是指向某个具体的对象,并且能派生出他人的正当要求权。(18)他建议以“责任”(duty)来取代“义务”概念。(19)如此一来,国家统治权利的规范性含义就是人民有道德责任服从法律。说人民有道德责任服从法律和说人民有道德义务服从法律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按照“责任”和“义务”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在于:若人民有道德义务服从法律,则意味着人民对于国家有道德义务服从法律,且国家有权利可以正当要求人民对它服从法律。使用“责任”概念时则没有这两方面的含义。柯普的用意在于,承认公民应该服从正当国家的法律,但不承认国家有正当权利可以要求公民的服从。 柯普的这一精细的区分似乎没那么重要。毕竟,他也承认正当国家中的公民有服从法律的道德责任,由此确立起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之间的关联。与拉登森的正当性观念相比,柯普对政治正当性的理解其实距离标准的正当性观念并不远。而且,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柯普的这一区分。若正当国家中的公民有服从法律的道德责任,这难道不同时意味着正当的国家有权利要求公民的服从吗?这里的关键在于,公民为何有服从特定国家法律的道德责任?基于什么样的道德理由我们可以如此断言?该道德理由在证成公民道德责任的同时是否也证成了国家的正当要求权?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只有当人们真正同意特定国家的法律时,人们才负有服从法律的责任。而同意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总是意味着双方或多方处在某种规范性关系中。也就是说,当公民同意服从特定国家的法律时,这种同意总是向某个对象表示出来,这个对象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这样一来,国家或政府当然可以有权利要求人们服从法律。人们的同意就既证成了自己服从法律的责任,也证成了国家的正当要求权。除非柯普能对公民守法的道德责任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还不会证成国家的正当要求权,否则我们有理由质疑柯普区分的合理性。 在谈到正当国家的权利时,柯普认为,一个正当的国家有权力通过制定法律使其公民担负某种责任,如纳税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的责任。可是,承认这一点难道不就是承认国家可以有权利要求其公民担负责任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总之,柯普的细微区分似乎未能挑战到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之合理性。 对于政治正当性和政治义务的关系,艾德蒙森(William A.Edmundson)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他首先对拉登森和韦尔曼等人的正当性观念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若一个国家具有证成权,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权利至少蕴涵着一个“不干涉”的正当要求权。如果把权利看作是对他人的道德约束,那就不可能像拉登森认为的那样,在执行法律时,国家不会对他人提出任何正当要求,而只是在回应他者的质疑。也不会如韦尔曼所言,国家统治权的真正关联项只是公民没有权利不被强制。严格来说,若人们有权利做某件事,则它不能仅仅意味着人们有自由去做,而必定同时意味着他人有责任不干涉人们的行动。因此,要么拉登森和韦尔曼的统治权被理解为政治权威有自由执行法律,也有自由不执行法律,同时可以正当要求他人不干涉法律的执行,要么就根本不是一种权利。(20) 艾德蒙森清楚地看到了拉登森和韦尔曼正当性观念的缺陷。这种正当性观念完全割裂了政治正当性与人们的责任和义务的关联,从而使得正当性或统治权的概念几乎丧失意义。就这点来看,艾德蒙森似乎会承认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的逻辑关联。但事实上,他并不承认这一点,并且还试图阐述一种没有政治义务的正当权威概念。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会问,他和拉登森或韦尔曼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里的关键在于澄清他是如何理解正当权威的。他给出了三个不同的事关正当权威的论题,并分别把它们称作强正当性论题(strong legitimacy thesis),弱正当性论题(weak legitimacy thesis),以及适度正当性论题(modest legitimacy thesis)。强正当性论题的内容是:“成为一个正当的权威意味着,由自己发出的权威性指令能使民众产生一种可被执行的服从责任。”弱正当性论题的内容为:“成为一个正当的权威意味着有一种普遍的证成权可以强制推行自己的权威指令。”而适度的正当性论题为:“成为一个正当的权威意味着,由自己发出的权威性指令能使民众产生一种可被执行的不干涉权威指令之强制推行的责任。”(21) 这三个正当性论题需要稍作解释。如果以“法律”来代指这三个论题中的“权威性指令”,则强正当性论题的含义是:正当的权威意味着能使民众产生服从法律的责任,或者说,民众有服从法律的责任。弱正当性论题的意思是:正当的权威只意味着有权利强制推行法律,但民众并没有服从法律的责任,也没有不干涉法律之被执行的责任。而适度的正当性论题指的是:正当的权威意味着能使民众产生不干涉法律之被执行的责任,或者说,民众有服从法律之被执行的责任。若使用西蒙斯的概念来描述这三个论题,则强正当性论题对应于标准的正当性观念,弱正当性论题对应于薄弱的正当性观念。而适度的正当性论题则居于这两种正当性观念之间。现在的问题是,这三种正当性观念哪种更合理一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努力为标准正当性观念辩护。艾德蒙森也排斥薄弱的正当性观念,但他也不接受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他认同的是夹在两者之间的适度正当性论题。若接受这一论题,则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仍存在关联,但这里的政治义务是打了折扣的或不完全的政治义务,因为它只包括不干涉法律的执行之责任,不包括遵守法律的责任。这种义务和责任可被理解为消极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需要向艾德蒙森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他只接受适度的正当性论题而不是标准的正当性观念?沿着西蒙斯的思路,我们会问,若正当国家中的民众有不干涉法律之执行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服从法律的责任吗?不干涉法律之执行的责任与守法的责任难道可以作明确的区分吗?或者说,如果我们能证成民众不干涉法律执行的责任,同样的论据是否也可以证成民众守法的责任呢?艾德蒙森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量。事实上,他之所以接受适度的正当性论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想证成国家的正当性,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22)他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接受的一点是,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证明,民众具有普遍的、初确的(23)(prima facie)服从国家甚至是正义国家之法律的责任。若接受这一点的同时又采用强正当性论题,那就只能得出没有国家是正当的这一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但他不愿接受这一结果。为此,他才诉求于适度正当性论题。他认为,接受这一论题不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因为虽然民众没有普遍的服从法律的责任,但却有不干涉法律执行的责任。在他看来,接受适度正当性论题的优点是,既能确立起人们对国家正当性的信念,同时又采用的是强有力的而非薄弱的正当性观念,因为适度的正当性论题毕竟确立了民众对于正当国家的义务。 可以看出,艾德蒙森采用适度正当性论题而非标准正当性观念的主要理由是,前者可以保留国家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两种正当性观念时,他并非基于它们自身的优劣,而是根据它们的结论。他自身有一种先在的信念,即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正当的国家。但标准的正当性观念会与这种信念抵触,故只能放弃这种观念。显然,这种选择标准存在明显的问题。它的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先在信念的合理性。但这一事关国家正当性的信念远非自明正确,恰恰是需要充分证成的。在没有其他更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艾德蒙森的选择有点随意。而且,即便接受他的适度正当性论题,也不一定能证成国家的正当性,因为,若民众没有普遍的服从法律的责任,他们怎么会有不干涉法律执行或服从法律执行的责任呢?服从法律的责任似乎应该是不干涉法律执行之责任的前提。在我看来,艾德蒙森虽努力把这两者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分很难成功,因而他也未能充分地证成人们负有普遍的不干涉法律之执行的责任。 基于以上诸种考虑,我们并无理由接受艾德蒙森给出的政治正当性和打折扣的政治义务的关联,或者说,不能接受政治正当性只与消极的政治义务有关,而仍坚持西蒙斯意义上的标准正当性观念。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比较了薄弱的正当性观念与标准的正当性观念,回应了针对标准正当性观念的诸多批评。我们想要确立的一个结论是:政治正当性的规范性含义是统治的权利,而统治的权利密切相关于被统治者服从的义务。换言之,确立了政治正当性就同时确立了政治义务,且这种政治义务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 注释: ①Joseph Raz,“On Lawful Governments,”Ethics,Vol.80,No.4,1970,p.300. ②Robert Ladenson,“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9,No.2,1980,pp.137-138. ③Ladenson,“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pp.138-139. ④这个例子来自拉兹,但作了简单的补充。参见Joseph Raz,“Authority and Justific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4,No.1,1985,p.4。 ⑤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页。 ⑥Ladenson,“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p.141. ⑦Rolf Sartorius,“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Virginia Law Review,Vol.67,No.1,1981,pp.4-5.萨托鲁斯的观点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追随拉登森,认为从政治权威的统治权并不能得出人民的政治义务。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统治权包含正当要求权。司法或执法领域的权威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人不要试图从事类似的活动,不要篡夺官方的权威。他也同意,没有人有权利私设法庭,暴徒没有权利执行官方判决的死刑。这似乎意味着,这种包含正当要求权的统治权是可以产生人民的相应义务的,并非像他说的那样与他人的义务毫无关系。 ⑧A.J.Simmons,“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Ethics,Vol.109,No.4,1999,p.747. ⑨A.J.Simmons,“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Political Authority,”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Robert L.Simon ed.,Oxford:Blackwell,2002,pp.18-19. ⑩A.J.Simmons,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5. (11)Simmons,“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Political Authority,”p.18. (12)Joseph Raz,“Authority and Justific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4,No.1,1985,p.13. (13)Jean Hampton,Political Philosoph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7,pp.4-5. (14)Raz,“Authority and Justification,”p.6. (15)Allen Buchana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Ethics,Vol.112,No.4,2002,pp.691-695. (16)Buchana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pp.696-697. (17)Christopher H.Wellman,“Liberalism,Samaritanism,and Political Legitima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5,No.3,1996,p.212. (18)通常情况下,“义务”和“责任”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但柯普在这里把它们区分开来了,赋予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要了解这种区分,可参考Joseph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08-117; A.J.Simmons,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1-16。 (19)David Copp,“The Idea of a Legitimate Stat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8,No.1,1999,pp.10-16. (20)William A.Edmundson,Three Anarchical Fallacies:An Essay on Political Autho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61. (21)Edmundson,Three Anarchical Fallacies:An Essay on Political Authority,pp.38-43. (22)William A.Edmundson,“Legitimate Authority without Political Obligation,”Law and Philosophy,Vol.17,1998,p.43. (23)所谓初确的责任指的是初步确定的责任,并非经过全面考虑后的最终责任。“primafacie duties”通常译为“显见责任”。这里不采用这种译法,因为它未能准确达意。“初确责任”这个译法虽显生僻,但比较精确。关于这个译名,可参考毛兴贵主编的《政治义务:证成与反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的“编者导言”后的注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