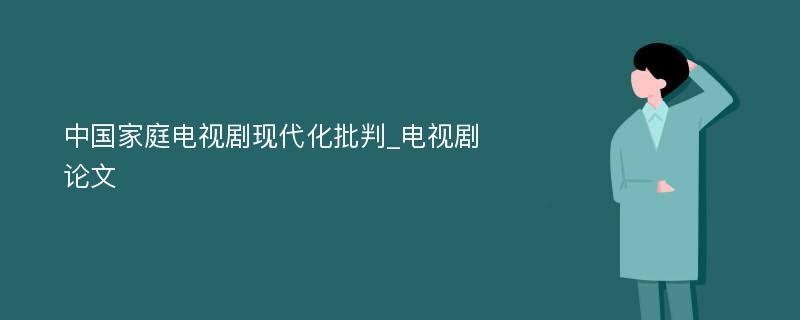
中国家族题材电视剧的现代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题材论文,电视剧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09)02-029-09
家族题材电视剧是电视剧创作中以家族母题作为审美表现对象,以三代及以上的大家族兴衰变迁作为叙事主干,以家族成员及家族间的关系作为叙事焦点,在家族史、民族史、个人史三者的交汇点上以家族命运反映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长篇镜像叙事艺术。中国家族题材电视剧进入21世纪开始崛起和繁荣。随着家族题材剧生产的大量增加,家族题材剧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是价值失范导致的创作观念错乱以及叙事失度。这些问题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既有创作主体自身的问题,也有媒介和剧种特性的限制,还有消费社会语境的影响。本文将在现代性的批判视野中对其进行考察。
一、“宅门文化”观: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失落
家族题材剧既然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单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家族作为叙事的对象,那么就必然离不开对家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对因家族而形成的家族文化的认知态度。这种价值判断和认知态度是对历史发展趋向的一种评价,它肯定社会的全面进步,批判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的力量。同时,家族题材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但要对历史理性做出肯定性的价值判断,也要对历史中的人物给予深刻的人文关怀。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应该是“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的和艺术本体三者的辩证统一”,[1]以此来观察家族题材剧,我们发现它在精神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在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并没有取得平衡,反而在有些作品中还出现了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匮乏。
“宅门文化”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源于《大宅门》的编剧、导演郭宝昌,他认为电视剧《大宅门》“跟任何一部电视剧都不同。它是通过人物来表现一种宅门文化,通过化妆、道具、人物、语言及所有的环境氛围来体现一种特殊文化,我觉得在以前没有过,与别的剧本也不一样”。“宅门文化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外国没有,‘文革’以后完全消失。它体现出来的东西独具特色,不雷同于过去任何豪门的、显贵的、官宦的或平民的,它吸收了很多皇家的东西,又具备了浓厚的民间色彩,是两者的结合,所以这些人物很特殊,你除了感到一种贵族气,也感到一种平民气,这两种文化的交合才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2](P.1)有人对此展开论述,认为“宅门文化”具有“庄重和谐、雅俗共赏、闲适自在”的特点,并认为,“宅门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种跨时代的文化,一种世界性文化,是历史留给北京和世界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3]果真是这样吗?所谓由皇家的贵族气息和浓厚的民间色彩与平民气相结合的“宅门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郭宝昌多次表示,《大宅门》写的就是同仁堂,白景琦的原型就是他的养父——同仁堂的董事长乐镜宇,白玉婷的原型是他的十二姑,三爷白颖宇和二奶奶白文氏则是几个原型的综合。既有历史原型和生活体验,又有长期的艺术准备,以中国百年老店同仁堂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宅门》表现了从清末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侧面,背景跨度很大,理应给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一个框架。然而,电视剧却在主题和情节中更多选择了血亲复仇、家庭争斗、妻妾成群以及破败家庭这样一些在其他家族题材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手段和场面,将注意力放在家族斗、官场斗、商场斗、妻妾斗等纠葛上。由于过多罗列家族陈年往事的纷纭表象,《大宅门》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显然没有被揭示出来,同时也没有从新的文化视角对家族兴衰史进行重新梳理和筛选。就其描写和刻画来讲,无论是两姓之家的世代恩怨、家族成员间的钩心斗角,还是对官场商场的尔虞我诈、行贿受贿;无论是描写二奶奶工于心计、杨九红歇斯底里的报复,还是白景琦在官商之中的周旋,平心而论,也可算入木三分。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关键是思想把握的深度,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来看待这些东西。将这些体现封建社会负面价值的图画罗列在一起,而且沿袭着一种陈旧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以把玩的心态进行艺术表现,这在文化意义上是陈旧与肤浅的。
在巴金的《家·春·秋》里,不但描写了旧式家族内外的斗争,而且通过家族不可避免的破败,预示了新生力量孕育的必然性。《大宅门》所展示的“宅门文化”,除了以玩味赞赏的姿态表达对封建腐朽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认同,对资本即银子力量的称颂外,实在看不到中国医药文化的踪迹,看不到同仁堂那种“炮制虽繁却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高尚医风,更难看到百年来中国医药人在国运衰微国难当头时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有学者批评道:“《大宅门》里的人物和故事,还有环境和氛围,都不是和历史的变故、时代的悲欢形影相随、声息与共的。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历史的印记,却没有那种生气灌注的历史沧桑感,在文化上也没有它应该凝聚的历史厚重感”,[4](P.165)“创作者们只是封闭在白氏家族的大宅门里絮絮叨叨诉说着家族成员们的一己的悲欢,并将这悲欢就看着了全世界”,“暴露了它对封建文化的一种崇拜和宣扬”。[4](P.166)
家族题材剧中这种将家族文化降格为宅门文化的潮流,很容易让创作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宅门内部的世事纷争和爱恨情仇中,去挖掘宅门深处那些能刺激人原始欲望的离奇故事,忘却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单元和文化承载体的多元丰富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忘记掉文艺作品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追求,丧失掉应有的批判反思意识,从而堕入庸俗化的泥淖之中。
二、媒介、剧种与家族题材剧的平面化
电视剧的产生是新媒介与传统艺术样式嫁接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媒介本身的性质以及技术手段的可能性既为电视剧的生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给了它限制性。加汉姆指出,“当代关于传媒的历史论争的要害是,传媒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本性,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5]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现代性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大众传媒的出现。其二是大众传媒产生之后,它就成为了现代性的某种标志,大众传媒表征了现代性的种种方面。
电视不但是文化生产的主要参与者,也越来越受制于以收视率为标志的商业逻辑。电视剧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承担着市场竞争的主要任务。同时,作为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电视媒体在中国还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对电视剧提出的要求就是既要“合目的性”地在意识形态规范里进行生产,也要“合规律性”地按照电视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则来生产。这两个方面对家族题材剧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其走向平面化。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它造成了家族题材剧思想的单一化。由于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扩散效应巨大,当前政府对电视影响力总体上持一种“强效果”观念,在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上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比如,电视剧的生产需要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制作许可证,电视剧生产前需要在广电总局进行题材备案(以前则是题材规划),电视剧制作完成之后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审片程序,特别是购片方会自觉以一定的标准来审看,符合要求才会购买。这种标准一般是导向正确(意识形态要求)、制作精良(制作技术要求)、观赏性强(艺术审美要求)。在中国目前的电视剧市场格局下,出现思想导向问题无疑等于直接宣布了投资的无效,因而电视剧生产者往往会自觉规避意识形态风险,避免在思想观念上冲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未必是正确的,但它居于主导地位)。所以电视剧中很难出现多元化或者具有深度和震撼力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电视剧并不希望冒犯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底线和观众的期待视野从而导致投资风险。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它也和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化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家庭化艺术形式有关系。电视作为一种公共传媒,是放在客厅里面供家庭成员共同娱乐的媒介,它在道德上负有诸多的责任,它所能表达和展现的内容是有很多限制的。家族题材剧首先是一种通俗艺术。它在思想蕴含和艺术手段上都不能一味地追求“高雅品位”而不顾观众的接受。通俗带给家族题材剧的直接结果,就是家族题材剧十分注意追求叙事情节的设计,将历史深度平面化甚至虚拟化,将社会冲突道德化,以传奇和通俗演义的方式来演绎家族故事。和这一特点相联系,是家族题材剧的类型化倾向。影视剧的类型化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以观众为中心,以社会心理为中介,并进行惯例化制作和创新性发展,以实现价值共享的艺术生产方式”。[6]中国电视剧生产在中国电视节目生产中最早,也最大程度“市场化”了。因此,家族题材剧对作为“上帝”的观众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需求必须要做出满足,要尊重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他们喜欢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模式。而这些,类型化生产都能够达到。它通过题材、主题、人物、情节构成等方面的固定程式,进行流水线般的生产并推向观众。比如,在家族题材剧的商业演义里,其固定的类型模式是以一个家族事业发展为核心构造几对矛盾线索,形成家族内部权力争斗、家族之间利益争夺、家族事业与王朝的关系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情爱生活等,在这其中要突出的是家族主要人物的宏图大略和英雄神话,为商的成功之道等。其中许多情节被多部电视剧所使用,如以石头装银车解决挤兑风潮,不畏艰难开辟新的商道,在朝廷危难之际慷慨解囊,商业竞争中同行之间经过尔虞我诈,最后在主人公的道德感召下达成和解。这就如同配方中的药材一样,可以在不同的家族题材剧里起到相同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类型化生产中同样也有创新发展的问题。“决定在艺术上是否优美的不是类型,而是艺术家如何很好地利用这种形式的程式”。[7](P.233)就如同程式化很强的京剧,各种流派的表演艺术家却也能自出机杼,做出自己的独创性。对家族题材剧而言,这种发展首先体现在思想含蕴的转变和深化上。
三、人物形象的悖论:家族叙事中的混乱与迷离
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描写什么样的人物命运,在叙事艺术作品中总是凝聚着创作者最多的心血。在前述宅门文化观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当前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下,家族题材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出现了价值的迷离,导致人物形象发生分裂,影响了观众对文本意义的顺利接受。让我们先来看几部家族题材剧中的人物形象是如何塑造的。
最典型的是《大宅门》里对七爷白景琦的刻画。对于白景琦,导演和编剧这样给他定位:“这是一个个性十分张扬的人,充满了一种叛逆的精神”。[8]从剧情的发展来看,白景琦一出生就不同凡响,有着诸多异于常人的表现。在成长过程中也显现出放荡不羁,敢于突破传统的所谓“叛逆”精神。这在他不顾母亲反对,要和黄春结合从而被撵出家门时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白景琦到济南之后,就开始展现出其心狠手辣的一面。如果说这还勉强可以说是表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充满血腥的一幕的话,那么他好色成性,几乎见一个爱一个的面目怎么也无法让人相信这就是他的“个性张扬”。他放荡不羁,又循规蹈矩,在封建礼教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杨九红为了他敢于献出一切,而他在母亲的家长权威面前,为了所谓的“孝道”,不但无法保护杨九红,在明知道母亲不对的情况下,甚至还以“错了也得听”为理由主动将杨九红的女儿无情地夺走,造成母女只能相对不相见的人间惨剧。这种人物性格前后的变化缺乏必要的逻辑铺垫与转化,结果导致了人物形象在观众心中的分裂。
我们再来看看《范府大院》里的郭彩三。《范府大院》贯穿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四个重要历史时期。围绕着范家总管郭彩三这个人物来展开,从清末到新中国,郭彩三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从孤儿到管家,最后成为了汉奸。郭彩三在范府大院中是一个小人物,他深受传统忠孝义气观念的影响,将收养了自己的范府视之为自己随时应该为之奉献的对象。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传统节气观念的人,在日本人面前却丧失掉了民族大义,做起了日本人的税务局长。剧中提供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范家一家人的性命安全。郭彩三为了家族的兴旺,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当上汉奸,给日本人办起事来。但在剧中,郭彩三也同情革命,在地下党蔡爷的引领下暗中帮助念人在内的共产党人。这样,郭彩三就成了背负家族安全与复兴的重任,忍受着被人误会的痛苦,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之间周旋,并为共产党转运过抗日物资的复杂的“汉奸”了。
在家族题材剧里出现的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逻辑混乱和价值迷离,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解叙事艺术在刻画人物时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人物性格本身具有丰富内容,但同时其中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方面,这种以主导性格凝聚着丰富性的人物性格才“成为本身坚定的性格”。[9](P.301)仲呈样将黑格尔塑造人物理想性格的思想总结为三句话,即:1.人物性格质的规定性。2.性格表象的丰富性。3.情致的始终如一性。[10](P.135)以此来检视家族题材剧中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其问题在于为了追求性格表象的丰富性,不惜破坏人物性格坚硬的质的规定性,结果导致人物性格前后逻辑断裂,无法形成始终如一的情致,这样就破坏了人物形象的完整,给观众的审美造成了混乱。
家族题材剧中人物形象塑造上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自身的文艺观出现了偏差。对于塑造怎样的人物形象,表现什么样的人物性格问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思潮中出现了一种写“复杂人性”的观点。人性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是禁区。在文学艺术泛政治化,泛革命化之后,我们就只剩下了单一的阶级性、革命性,人物形象也开始向“高、大、全”方向发展,最终离开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了欲望和情感,只有理想、目标与行动。这在17年文学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应该说,写复杂人性观点的提出,作为对这种长期以来的不正常文艺观的反拨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复杂人性论如果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基点,就很容易滑向随心所欲的深渊,过分展示生命原欲,丧失道德美感。有论者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人性化处理用得多了用得滥了,也容易变成了模式。倘若将杀人犯写成一个善人,将一个卖国贼刻画得忧国忧民、饱含苦衷,以人性的名义蹂躏历史,不成了以人性的名义蹂躏人性了?用所谓人性化来处理影视作品的内容、人物会把人们引向一条比‘戏说’更利害的迷茫之路”。他认为,和那些剧情错误、拍摄穿帮、史实混乱等“硬伤”相比,“‘人性论’是影视剧创作的内伤”。[11]这对当前家族题材剧创作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把握是一针清醒剂。
四、消费社会与家族题材剧改编的偏移
消费社会是西方学者用来描述当前西方社会不同于以往的种种特殊表征而提出的概念。美国学者詹明信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时期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12](P.399)他认为消费社会的出现在西方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在消费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它颠倒了经典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同时,消费社会里的消费也和以前任何社会的消费不同,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用来消费的商品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物品,形象、艺术、身体,一切都已经商品化了;二是的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的主导性方式,它推动并塑造着消费大众以及他们的消费欲望,意义而不是物品本身成为消费的核心。不难看出,消费社会的核心是商品逻辑,或者叫资本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所不在”。[13](P.162)
由于文化艺术成为了商品,因此,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就必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发挥作用。电视剧的生产受资本逻辑的影响,为着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来从事文本生产,结果导致文化艺术生产的媚俗。媚俗艺术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密不可分,卡琳内斯库甚至将其作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加以论述。对此,昆德拉说得更加明确:“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14](P.159)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来考察家族题材剧的生产,尤其是它对文学文本的改编情况,可以发现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倾向性问题。
首先是家族题材剧改编中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及其带来的对原著深度的消解。对于经典作品的改编,黑格尔早就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关于题材“是客观地按照它的内容和时代来处理呢,还是按照主观的方法来处理,使它完全适应现时代的文化和习俗呢”这一问题时认为,艺术家既不能纯然主观地对自己时代的文化发挥效力,也不能对过去时代谨守纯然客观的忠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艺术作品应该揭示心灵和意志的较为高远的旨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东西,内心的真正的深处;它所应尽的主要功能在于使这种内容透过现象的一切外在因素而显现出来,使这种内容的基调透过一切本来只是机械的无生气的东西中发生声响”。[9](P.354)如此看来,历史情境对于家族题材剧来说,就并不是无关轻重的了。但在家族题材剧的改编里,却常常出现对历史情境的弱化甚至取消。
以《京华烟云》为例。林语堂的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00年到1938年政权更迭、军阀混战的北平城,通过对姚家、曾家、牛家三大家族中各类人物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性格转变、命运选择来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和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展现了从义和团运动到“七七”抗战近四十年的广阔历史时空。文学史家称《京华烟云》为中国抗日题材小说开篇之作。林语堂抱着“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目的,通过书中人物对待世事和时局的态度,展现在儒、道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在民族命运转折关头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林如斯才说“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15]林语堂的小说比较散文化,故事情节不够集中却又跨度很大。这对于电视剧来说,显然是个难题。编剧在考虑的时候所采取的方法是“掐两头”、“取中间”,以矛盾冲突最突出的抗战前后12年作为载体,侧重“一个女人的成长史”。编剧忽略掉了人物生存的历史语境,改变了人物的性格设定和故事情节,以类型化的二元对立方式设计人物关系。这样的改编,固然适应了电视剧的艺术要求,但原著中所展现出来的“哲学意义”却荡然无存,其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文化寓意、中华民族的民俗风情全部被三个家族中婚姻纠葛、第三者插足等琐碎的剧情所掩盖。剧中除了结尾姚思安为保护甲骨在酒窖中自焚,与日本人同归于尽这一情节之外,很难再看到对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展示,从而彻底消解掉了原著的思想内涵的深度。恰恰与编剧所说的“改动的只是情节和结构,底色、主题、社会含义或者说它的‘魂’是没有变的,并且民族精神得到了加强”[16]这一说法相去甚远。
其次是家族题材剧改编中出现的滥情倾向与欲望叙事。电视剧《京华烟云》的编剧认为,林语堂原著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教会当代男女怎么去生存、怎么去爱,去吵架”这一主题,“我只是在单个人物上有所改变,但其实这个主题是与原著非常一致的,但是,电视剧在表现上不可能和小说一样,包含的范围那么广,一定要有所侧重,所以我选择了加重‘一个女人的成长史’这一部分,其实这也是对林语堂原著的升华”。[17]有了这样的思想观念,就免不了有这样的心思,“一个女人不离婚、不自杀,观众会看吗?没有主动出击,就不会好看。这样才有了曹丽华。原著中木兰宽容、隐忍、大度、智慧,但是太平淡了,就没人爱看了,必须遵循电视的艺术规律,增加木兰的主动性,强化冲突”。[18]所以,我们在剧中看到经过改造之后的木兰、莫愁、襟亚、孔立夫、曹丽华、牛怀玉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和情感纠葛就成了叙事的主线。编剧这样为观众着想,可观众呢?他们却并不买账,反而批评这是“一部‘枕头加拳头’的言情剧,充斥了暴力、第三者、婚外恋、强奸、杀人、阴谋”,“在浓厚的编造痕迹和猎奇心理之下,该剧俨然已经成了一部‘现代家庭犯罪启示录’”。“一部反映民族命运的小说被改编成这样,让人难以接受”。[19]这种滥情改编和欲望叙事的倾向,在家族题材剧中是比较普遍的,甚而成为创作者的一种共识。电视剧《雷雨》、《金锁记》等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第三是家族题材剧改编中的形象消费与快感追求。随着经济条件和技术手段的进步,电视剧在影像质量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改进。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家族题材剧相比,现在的家族题材剧在实景拍摄、室内布景、服装道具、人物化妆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当时,给创作者还原历史环境和事件氛围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但当下的家族题材剧在改编中出现了过度追求形象的倾向。1980年代改编的《家·春·秋》、《四世同堂》等电视剧,人物的形象及其周围环境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历史语境,显得比较协调,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之间也大都能够做到“形神兼备”,符合剧情的需要。而近几年的家族题材剧改编往往十分注意演员形象的选择,但有时候并不是基于“剧情所需”,而是基于其他考虑,使“想象力和求实”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和谐。新版《四世同堂》的导演表示,重拍《四世同堂》“希望整部剧比较养眼,让现在的观众看起来没有隔阂”。他同时也承认,“出于商业和年轻观众口味的考虑,此次遴选演员‘不太写实’,在形象上偏好看,不大符合生活在‘小羊圈胡同’里的真实样子”。[20]曾经出演过第一版《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的赵宝刚在新版里演冠晓荷,他也坦言,“感觉黄磊小了一号,蒋勤勤有点太漂亮了,朴实不够”。[21]同样,在新版《家·春,秋》里,主演也皆为青春偶像派演员,黄磊、陆毅、李小冉和黄奕等都是当前荧屏上的当红小生与花旦。在《京华烟云》中,赵薇、潘粤明、胡可等人,也都是偶像派的中坚。然而赵薇扮演的姚木兰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批评,认为她的形象与气质完全没有体现出姚木兰身上所应该具有的那种安宁、平静与智慧。家族题材剧改编中这种盲目追求形象消费,制造视觉快感的倾向,往往是只顾“养眼”,而忽视了“养心”这更重要的一面。
家族题材剧改编中出现的这种种问题,其实都表征出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在以受众为中心的思维导向的指引下,电视剧艺术创作体现出来的后现代特征。詹明信指出,在消费社会或者是后现代社会,美感的生产被纳入到文化工业体系的流水线上。这种艺术生产的产品倾向于以形象消费代替深度体验,历史感浅薄微弱,表现出歇斯底里性的释放。①我们自然不是说家族题材剧的改编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实际上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情况极为复杂。但家族题材剧的改编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后现代文化思潮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其实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电视剧创作是有负面影响的,呼吁“要警惕后现代主义的偷袭”。[4](P.124)这对于我们清晰认识包括家族题材剧在内的中国电视剧艺术生产,是有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参看詹明信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20-515页。
标签:电视剧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家族史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家族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现代性论文; 大宅门论文; 京华烟云论文; 四世同堂论文; 白景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