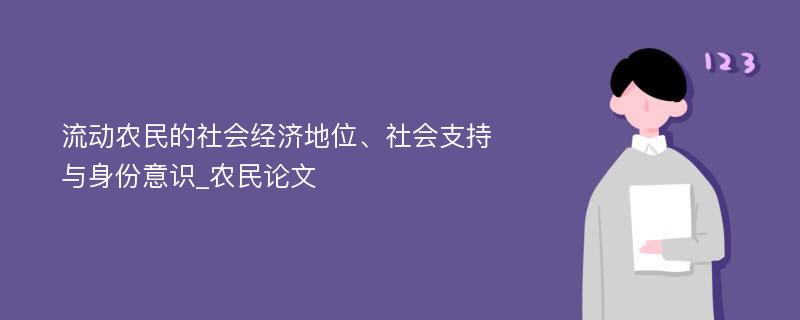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社会经济论文,地位论文,意识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大转型背景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导致城乡二元格局的社会制度也在发生着变革,这一变革对农民身份(Identification)发生着无论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时期,探讨流动农民这一界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际人或从农民到市民的过渡人的身份意识,就有其价值所在。
2 研究假设与变量设置
在学术界,对个体阶层身份认知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第一,具有结构主义取向的“静态”模型强调,人们在生产和劳作中的关系以及人们所得到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如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的决定作用;第二,“动态”模型强调,阶层意识并不都来自其拥有的社会地位,也来自阶层间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或社会场景变化的影响,马克思曾以小房子与周围房屋的比较导致其房主心态变化为例论述过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韦伯也认为,人们之间生活机遇的差别不管有多么大,都不会导致有意识的阶级行动,只有当人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形成鲜明的对比时,才导致人们对阶级处境与阶级行动的后果之间的理性认识。
来自静态模型的假设一,流动农民的收入越高,他对自己的农民身份越不认可。
以下三个假设均来自动态模型,假设二,流动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日常生活中难免与周围的城市居民发生来往,因而就会发生与这些城市居民进行比较,如果发现自己经济地位比较高或处于优势,则不会认可农民身份。
假设三,来自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的社会支持会使流动农民暂时忽视自己农民身份,或身份意识发生模糊,而来自他们的社会歧视则会强化其身份意识。
假设四,作为城乡社会的两栖人,也难免受到来自家庭和家乡对其外出务工经商态度的影响,如果他们抱有支持、羡慕的态度,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收入在家乡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则会促使流动农民强化其农民身份意识,反之,则弱化其身份意识。这是因为尤其是家乡居民的羡慕会给他们带来农村社会声望的提高,这些声望会作为拉力而存在。
根据上述假设需要用的自变量主要有:
(1)每月经济收入,为客观经济地位。
(2)自我感知的收入在城市居民中的位置。
(3)自我感知的收入在家乡居民中的位置。
(4)城市户口居民的社会支持,来自调查问卷中“社会支持网”部分,通过询问谁给予了流动农民在精神安慰、重要事讨论、借钱、帮助找工作、出面解决麻烦、外出陪伴、拜访7方面支持。
(5)感知的城市社会歧视。
(6)家庭对其在城市工作的态度。
(7)家乡对其在城市工作的态度。
3 研究发现
根据对南京市的调查显示:客观经济地位即月收入越高的,越不同意自己已经是城市人;主观经济地位越高的,越同意自己已经是城市人;家乡与家庭不支持、羡慕的,越可能不同意自己是城市人;社会支持网中有城市人的,则越有可能不同意自己是城市人;感受到的社会歧视越多,越不同意自己是城市人。
此外,影响身份意识的第一个因素是自我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位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若自我感知收入在城市社会处于上层,则“同意”自己是城里人的发生比是处于下层的10.830倍,处于中层的是下层的4.195倍;若感知处于中层,则“说不清”自己身份的发生比是下层的2.227倍。
影响身份意识的第二个因素:家庭是否支持其外出务工经商,非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不支持,则不同意自己是城里人,具体变化幅度是,控制其他因素后,若家庭不支持,则同意自己是城里人的发生比只是家庭支持的26.3%。其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员支持其外出务工经商,则成为将其推出农村社会的力量,若不支持则意味着期盼他们返回农村,因而这一推力促使他们成为“城市人”,而成为城市人得以摆脱农民身份和农村困境正是其家庭支持其外出的原因。
影响身份归类的第三个因素是:感知的城市歧视,非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歧视程度越高(即态度越差),则越不同意自己是城里人,具体变化程度是:歧视程度提高1分,则同意“自己是城里人”陈述的只是原来的0.854倍或85.4%,或比原来的发生比下降了14.6%。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客观经济地位指标的“月收入”、主观经济地位的“收入在农村位置”、社会支持的“家乡态度”、“城市人支持”四个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4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尽管流动农民的生活场景主要是在城市,但多数仍不同意自己身份发生转变,仍认可自己的制度性身份。
同时,虽然相关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各变量都影响着他们的身份意识,但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只有“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位置”、“感受到的城市社会歧视”、“家庭支持”3个变量,其余4个变量作用均没有达到最低显著要求。这至少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客观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其身份意识,真正发生影响的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对自已经济地位的感知,并且此时他们已经不是以农村居民为参照群体了。
第二,真正影响流动农民身份意识的是家庭,而不是家乡也不是社会支持中的有没有城市人,进一步分析他们社会支持网发现,家庭更可能提供的是重大支持,如帮助找工作、讨论重要事、精神安慰等方面支持,并且与城市人相比,家庭成员间关系要更为密切。
第三,再次证实了已有关于城市社会歧视研究。
